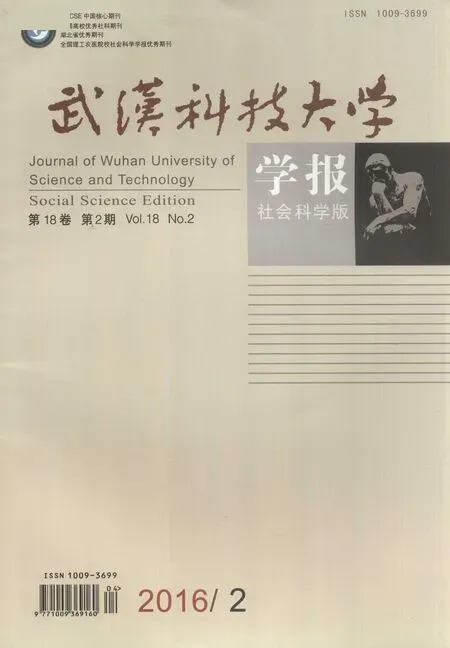民初北京政府设立过程中之权力纠葛
2016-03-14丁健
丁 健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民初北京政府设立过程中之权力纠葛
丁健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选为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南北剑拔弩张的局面暂告一段落。但就组织北京政府问题上,南北双方则从原来的明争,重新卷入到新一轮暗斗的漩涡里。他们分别就袁世凯的就职地点、新国务总理、国务总长的任命等问题上继续展开角逐。由于南北双方都想增加自己所占未来政府总长的名额,导致北京政府创建困难重重,给民初政局蒙上不祥的阴影。
关键词:民初政局;北京政府;袁世凯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府的筹建是民初民众不得不面临的一件大事,其组建过程尽管南北双方少有剑拔弩张的直接冲突,但暗自较劲互相博弈在所难免。为了尽快组成临时政府南北双方既有克制隐忍,亦有相互谅解,最终结束辛亥革命以来南北分裂对峙之局面。其实,民初北京政府的组建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政治斗争的继续,其亦为后来政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由于当时中国政局处于新旧交替的复杂时代,趋新的有之,怀旧者亦复不少,“半新半旧”者也有一定的势力,面对这样复杂的民初社会政局和社会心态,北京政府的筹建显得十分困难。但是,以往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多笼统地侧重强调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而对矛盾的具体体现及其社会反响着墨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民初政局的认识和把握,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这一问题展开述论,以见教于大方之家。
一、袁世凯就职地点问题
简言之,袁世凯就职地点问题,即总统与政府机关谁迁就谁的问题。对此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北既已联合,总统亦经选举,而统一政府所以不能尅期成立者,则以政府在南,总统在北,将强政府以就总统乎,则政府为机关,总统为个人,无强机关以就个人之理,将强总统以就政府乎,在理法上固为不易之条件。然当日者,北方秩序,正赖维持,东北人心,犹难一致,部署完密,尚费时日。总统南行,难期尅日。有此二故,遂致迁延。”[1]此可谓准确地概述了辛亥革命结束之初中国政局的尴尬状况,但也是不得不亟待解决的问题。
清帝退位后,按照南北达成的协议,袁世凯必须在南京就职。可是袁世凯迟迟其行,并发长电致孙中山等,表明不能立即赴宁之苦衷:“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2]
可是,革命派不依不饶,一定要袁世凯离京南下就职。为此,孙中山电告袁世凯:“袁公慰庭为民国之友,盖于民国成立事业,功绩极大。……至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南京。”[3]于是,有蔡元培等人一行于1912年2月27日抵达北京,准备迎袁南下,袁世凯亦隆重打开正阳门,以示欢迎,不料想,此时北京却发生了兵变。有人说这是袁世凯自导的一出好戏,以此拒绝南下,持这种观点之人未免有些武断,因为此事有悖常理。首先,袁世凯刚被选为大总统,各方贺电不断,皆曰:民国得人,无任欢忭,袁世凯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兵变;其次,袁世凯向来给人治兵有术的印象,他不会不考虑这次兵变将大大损害其形象;最后,袁世凯并不愿在其当政未几日,就出这么大的乱子,兵变发生后袁世凯不得不一再向外界致歉,天天跑外国使馆。其实,他也一直绷着外交这根弦,本来西方列强以国内秩序未稳为由而不承认中华民国,兵变发生正好授人以柄,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难度又加一层。事实上,尽管袁世凯曾经一度表露过不愿意南行之意,但他在与代表们商谈时从来没有明说过,蔡元培在当时发表的《告全国文》里就明确指出:“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4]
兵变发生后,北方局势不稳,袁世凯采取高压措施,严格实施宵禁,秩序得以逐渐稳定,这也便使得他有“借口”不南行。他在致孙中山、参议院电中说:“此次南京特派专使来迎凯,赴南京受职,凯极愿南行,与诸君相见,共筹国家大计。惟以北方秩序须人维持,正在拟议留守之人,不期变生仓猝,京师骚然,波及津保。……而南京政府亦鉴北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庶几大局早定,人心早安,对内而谋统一,对外而谋承认,已完全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是所深望。”[5]联系当时的实情,应该说袁世凯此番表白是十分诚恳的。
其实,蔡锷、张謇等先前早已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告诫袁氏不要南行。蔡锷说:“建都之议,章太炎、庄思缄及各报馆所论,已阐发无论。而鄙意所尤虑者,则建都南京后,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淩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都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6]张謇则说:“公膺众选,全国忭庆。要公南者固甚多,不可说。公不能南,须北数省咨局,恳切联争于参议会。若南,须以师从。今先陈亟应行之事:一、就近得各公使承认发表欢迎之意,取外交权。以五十万犒海陆军,认发海军月饷约十二万;令南方确查陆军人数,认饷。请酌。一、分别派蒙、藏、南洋宣抚使。蒙可河王,金还副,盛先觉参赞;藏可温宗尧,姚锡光副,范源濂参赞;盛范均尝留心蒙藏。南洋可汤寿潜,潜方辞交通,应华侨之约,胡国廉副,吴作镆参赞。请酌。一、宣布以公债票酬同盟光复党死事效命人。数自一万至五万,期自五年至廿五年,均五等。电孙查开各名籍,以消其隐私而杜其他望。请酌。余俟专函续详。”[7]面对民初政局的复杂形势,再有此推波助澜,更坚定了袁世凯不南行的决心。
南方代表目睹兵变,深感北方形势不妙,如袁离开,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因此蔡元培电告南京政府,历述兵变恐怖情况,“大局之危已如此,□□□□□言者均谓因争执地点,以致耽误大局,函电交至,外人亦啧有烦言。若不有以安人心,恐将败坏不可收拾。敢请尊处迅开会议,如赞同袁君不必南行就职及临时统一政府设在北京,请即电复,以拯危局。”[8]南京面对蔡元培的长电,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但必须遵参议院办法六条[9]。为此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因专使来电,知公不能刻日南行,……当经院议决,允公在北京受职。其办法六条,除由参议院电知外,今日一再电专使转达尊处。”[3]193于是,3月10日,袁世凯顺理成章地在北京宣誓就职,可事情还不算了结,袁世凯就职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以此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这明显带有因人立法倾向,张国淦回忆说:“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为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10]也有人认为:“与其谓为制度上之选择,无宁认为基于人事之考虑。”[11]由于袁世凯“一直坚持认为,摆在各派面前的头等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政府”[12],所以对革命派的限制意图并没有公开反对,而是积极组织选择统一政府人选,于是,南北双方又陷入到国务总理、国务总长人选的争夺中。
二、统一临时政府组建问题
统一政府的筹建,主要是国务总理、各部总长人选的确定,但是这谈何容易!以当时《盛京时报》、《申报》的报道为中心进行考察,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其中的明争暗斗。为什么要以当时的报纸为考察中心,是因为民初报刊舆论很发达,且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被民众接受。再说,当时的记者颇能通过各种途径与当政者或者官场消息灵通人士取得联系,以获取最新政界讯息,从这一点说,报纸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当然,有些报道尽管并非是对政治内幕的准确揭露,但也不至于毫无根据,退一步说,即便毫无根据,也在受众中产生了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当时的报纸舆论对政府组建的关注很有意义。
(一)各部机构的设置情况
《盛京时报》有过不同的表述。1912年3月14日,《盛京时报》说“闻临时政府之组织,司分十二部”[13],关于设置十二部的原因,除了将原有的邮传部、农工商部各划为两部外,主要是“唐绍仪以上级机关设立太少,则南北私人难得位置,恐酿成此争彼竞之风,于民国前途大生障碍”[14]。3月17日,其又有十四部之说,是为“农部,工部,商部,邮电部,船部,路部,外务部,法部,内务部,度支部,教育部,拓殖部,海军部,陆军部”[15]。3月20日,又报道说参议院“认可十一部”[16]。《申报》的报道是九部四院,即“闻统一政府之制,袁总统已经拟定,大致设立九部四院,其九部:一外交,二民政,三财政,四司法,五教育,六交通,七军事,八实业,九殖务。四院则一财政,二会计,三参议,四裁判”[17]。当然,这些报道与后来政府正式确定的十部有出入,但这十部正是在先前的南北讨论商议基础上成立的。
实际上,部务机构的设置多少,一方面固然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仍是南北权力之争的继续和发展。特别是十四部之说,看似荒唐,但考虑到对南北主要人员和社会名流的安置,恐怕这十四部也不够。况且,无论袁世凯还是唐绍仪当时都是以调和南北为宗旨。就南北商定的情况而言,十二部最为合适,当时袁世凯把十二部的情况告知孙中山,孙中山也很满意,就咨送参议院议决,可参议院不同意,认为应遵循其所议定的官制通则,为此电告袁世凯:“本日准孙中山咨送大总统拟派十二部国务员交由本院同意等因。查本院议决各部官制通则,原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十部,业于文电奉闻,兹大总统拟派各国务员与原案员数不符,未便遽付同意。仍请按照本院议决原案所设十部,开明姓名,电交本院同意。”[18]本来人员都已基本确定,而压缩至十部,必然要再更动人员,而更动人员,谁上谁下都是棘手的问题,因而它导致了《盛京时报》和《申报》以上报道不够准确。
(二)各部人选
国务总理袁世凯拟任唐绍仪,孙中山极为赞同[19],但其他国务员的确定就不是那么容易选定了。《申报》对此关注较早,甚至在清帝尚未退位时就说:“今日关系最要之事,则为选举内阁人员,闻南北两政府目下已在讨论此节。其人员大概如下:内阁总理唐绍仪,参谋总长黄兴,外务卿伍廷芳,海军卿程璧光,陆军卿黎元洪,司法卿王宠惠,度支卿陈锦涛,民政卿程德全,交通卿汤寿潜,教育卿蔡元培。”[20]这种情报《申报》是如何获取的不得而知,但这可以看出其对新政府的关心和关注。1912年2月29日,《申报》称:“统一政府人物闻已议有端倪,内阁总理拟用唐绍仪或徐世昌或程德全,陆军总长拟黄兴,司法长拟沈家本,交通长拟梁士诒,实业长拟张謇,教育长拟汤寿潜或章炳麟,民政长仍拟赵秉钧,其余各部及各省长官则尚未定局。”[21]3月4日,《申报》又有新的说法:“孙大总统昨接北京袁大总统来电,商议组织中央新政府,决计添设内阁,担负全国责任,拟以唐绍仪充任总理,其陆军部则以段祺瑞反正有功,民国拟畀之以总长,次长则为田文烈,海军部为程璧光,次长黄钟英,交通部为梁士诒,次长汤寿潜,外务部陆征祥,次长胡惟德,内务部为赵秉钧,次长乌珍。财政部为熊希龄,次长陈锦涛,司法部伍廷芳,次长沈家本,教育部为严修,次长蔡元培,实业部张謇,次长杨士琦,闻孙大总统以赵严胡乌杨诸人皆舆论所反对,拟俟袁来宁再行更定。”[22]实际上,袁世凯确实在3月16日之前把国务员姓名电告参议院,是为“外交部陆征祥,内务部赵秉钧,财政部熊希龄,教育部范源濂,陆军部段祺瑞,海军部蓝天蔚,司法部王宠惠,农林部宋教仁,工业部陈榥,商业部刘炳炎,交通部陈其美,邮电部梁士诒”[19],但是参议院不同意。于是,3月17日,又有报道称“孙总统以更改名单电商袁总统后,昨日(十五)又得袁总统唐总理合电,交来修正国务员名单如下,外交陆征祥或伍廷芳,司法王宠惠,陆军段祺瑞,海军蓝天蔚或刘冠雄,教育蔡元培,交通梁士诒,工商陈其美,财政熊希龄或陈锦涛,内务赵秉钧,农林严修”[23],之后又出现过许多内阁成员的新版本。其实,即使到了内阁名单正式公布前,《盛京时报》、《申报》、《民立报》等各执一词[24-26],皆未能准确地捕捉到真正的内阁名单,报纸舆论之所以莫衷一是,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阁员名单调整太频繁,南北双方争夺太激烈。
(三)各部部长人选的争论
用人的确是一件很费心力的事情,“将少用旧人,则旧人怨,将少用新人,则新人怒”[27],况且,“就今日之人材而论,有学识者未必有经验,有经验者未必有学识”,如果仅有学识而无经验,“过去之事实多所未习,其于凡百措施或不免悉以学理为准则”,结果窒碍难行;“然徒有经验而无学术,又不免狃于所见,安于所习,而于民国之事业或不足以应付”[28]。再说,当时向袁世凯推荐人才的也不少[29],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再加之政治因素,选定新政府阁员并非易事。
当时争论较大的是陆军总长,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兵权就是后盾,没了兵权,说话就不算数了,所以在陆军部人选上极力推举自己的老部下——逼宫有功的段祺瑞。而南方也是看到了掌握兵权的重要性,极力推荐黄兴做陆军总长,甚至“南京民军干部员等集议,全体赞成,决议公推黄兴令其就任陆军大臣”[30]。司法总长袁世凯本来想推荐沈家本,可是南方不同意,而沈家本也无意政界。教育部长袁世凯推荐严修,南方推荐蔡元培。在实业部方面,袁世凯起初想让张謇做实业部长,但是张謇婉拒了。其实,张謇的超脱对袁世凯来说更有利,在民初秩序紊乱之际,本来官位相对较少,如果任命张謇必然会给袁世凯造成压力,因为袁得为其尽力争取,由此可见,张謇处事之深谋远虑。后来,袁世凯意识到融合满汉关系的重要,便推荐溥伦为农林总长,曾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电商,南京亦表同情。袁大总统又商之溥伦,溥伦亦居然认可,自谓农林一席,已在掌握,可“不意事机中变,竟至落第”[31]。最终,南北双方经过商议和讨价还价,并通过参议院议决,3月30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公布了内阁人员名单:“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赵秉钧为内务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陈其美为工商总长,交通总长由国务总理唐绍仪兼任。”[32]
结果,即使到了名单最后通过时,还是出现了问题,当时参议院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不过二十票不算通过。当时投票情况是:“陆征祥三十八票,赵秉钧三十票,段祺瑞二十九票,刘冠雄三十五票,熊希龄三十票,蔡元培三十一票,王宠惠三十八票,宋教仁三十四票,陈其美二十四票,惟梁如浩十七票以少数未通过。”[33]所以才有唐绍仪兼任交通总长的结果,后又任命施肇基为交通总长。国务员本来打算4月1号之前公布,人们大都认为“组织临时政府各项问题,又多纠葛,且前拟各国务卿又多力辞,恐非仓卒所能成立。唐总理所预订四月一号以前成立之议,必难办到”[34]。之所以3月30日提前公布,是由于“内乱外患日迫一日”,“黎副总统及七省议事联合会暨军事统一会之电促”,外交上不时发生辱我五色旗事件[35],以及“苏州兵变的影响”[36]。看上去日期似乎是提前了,但是,对民众来说,它又是迟缓的。时人有论:“共和宣布已近五旬。临时政府尚未成立,列强承认更不知在于何日,南北兵警人心惶惶,望政府之成立,眼几欲穿,据个中要人云,此事极属不易,新官制共定十部,凡一国务卿须得五方面同意,始可作为定局,所谓五方面同意者,一须俟袁总统之同意,二须唐总理之同意,三须孙总统之同意,四须参议院之同意,五须本人之同意,国务卿共有十人,必须有五十个一致之同意,临时政府方可谓组织完成也。”[37]由此看来,组织临时政府之难可想而知。
临时政府成立后,接下来就是各部开始组建部务了,而南北的谣言却又沸沸扬扬起来,关于谣言产生的原因,张謇曾有过精辟的论断“南北谣言都极离奇,推考缘因,大略由于侦探而生者三之一,由于平空捏造以献勤,或构陷人者三之一,有其事者亦三之一。今论有其事者:其故由于积猜,而猜生于分之未定。所谓分者,位也,权也,利也,党也,人也;五者赅之。”[7]213处此境地,民初北京政府的组建无疑经受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三、结语
辛亥革命后,在北京政府筹组的过程中,由于南北双方都想增加未来政府总长的名额,所以北京政府重组困难重重。但从发表的阁员名单看,袁世凯派有:陆军部段祺瑞,内务部赵秉钧,财政部熊希龄;而来自南方革命阵营的有:海军部刘冠雄,工商部陈其美,教育部蔡元培,司法部王宠惠,农林部宋教仁。尽管南方没有控制新生政府的主要部务,但其所占的席位却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唐内阁为‘以同盟会为中心’之内阁”[38]。而教育、工商、农林、司法又和普通民众关系密切,如果能施政有方,必定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有了民众的支持,不就能逐渐掌握话语权?!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不久集体辞职,这真让人遗憾。其实,同盟会的这种做法有些固执己见,就当时情势而言,过分强调和迷信西方政党政治,多少有脱离中国的国情倾向。再说,辛亥革命的结局是多方妥协的结果,其间掩盖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而解决这些尖锐的矛盾,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立完全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但无论如何,北京临时政府终于成立了,这才是最可庆幸的事情,正如时人所言:“民国成立以来已两月,於兹其间,险象环生,祸机四伏,以言内政,则兵变之事层出不穷;以言外交,则强邻环伺,乘隙蹈暇,可惊可怖之事,接触于耳鼓,其所以致此之由,则以南北名为统一,而政府尚未组织,人人心目之中,不免有所疑惧也,今者阁员发表,南北一家,革命之事业可称完全,人民之希望可望满足,诚民国成立以来,最可庆幸之一事。”[39]然而,由于北京政府仍然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随着各方权势的消长,此种平衡必然被打破。再说,当时主要的政治力量,无论袁世凯还是革命派都不满意于北京政府的权力设置,因政治立场的差异,且互不谅解,争权贯穿袁世凯政府始终,这就给民初政局蒙上了层层阴影。
参考文献
[1]平佚.临时政府成立记[J].东方杂志,1911(11):14.
[2]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M].长沙:岳麓书社,2005:335-33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97-98.
[4]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2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1-33.
[5]公电[N].申报,1912-03-09(1).
[6]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23.
[7]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图书馆.张謇全集:第1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215-216.
[8]蔡专使致南京政府电[N].申报,1912-03-09(3).
[9]孙曜.中华民国史料[M].上海:中华书局,1929:56-57.
[10]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91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5.
[11]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8.
[12]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28.
[13]临时政府组织大纲[N].盛京时报,1912-03-14(2).
[14]位置私人之大舞台[N].盛京时报,1912-03-16(4).
[15]堂哉皇哉之十四部[N].盛京时报,1912-03-17(2).
[16]商定改拟国务人员名单[N].盛京时报,1912-03-20(4).
[17]专电[N].申报,1912-03-12(1).
[18]公电[N].申报,1912-03-20(1).
[19]大总统咨送袁大总统选派国务员姓名请参议院查照文[N].临时政府公报,1912-03-16.
[20]新国都与新内阁[N].申报,1912-02-10(3).
[21]专电[N].申报,1912-02-29(1) .
[22]袁总统假定之各部长[N].申报,1912-03-04(2).
[23]新内阁人员之纷议[N].申报,1912-03-17(2).
[24]新内阁人物表[N].盛京时报,1912-03-30(2).
[25]最后修正之国务员名单[N].申报,1912-03-26(2).
[26]专电[N].民立报,1912-03-27(3).
[27]清谈[N].申报,1912-05-23(3).
[28]对於阁员之忠告[N].申报,1912-04-04(1).
[2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15-619.
[30]黄兴将复任陆军大臣矣[N].盛京时报,1912-03-17(2).
[31]新北京宦海升沉记[N].申报,1912-04-09(2).
[32]大总统命令[N].申报,1912-04-01(1).
[33]记参议院表决国务员[N].申报,1912-4-1(2).
[34]临时政府成立之纠葛[N].盛京时报,1912-03-28(4).
[35]国务员提前发表之原因[N].盛京时报,1912-04-05(4).
[36]专电[N].民立报,1912-03-31(3).
[37]国务卿迟迟发表之原因[N].盛京时报,1912-03-31(4).
[38]谢彬.民国政党史[M]. 上海:上海学术研究会,1925:145.
[39]阁员发表之感言[N].申报,1912-04-01(1).
[责任编辑彭国庆]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6)02-0223-05
作者简介:丁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北洋集团和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GH-293).
收稿日期:2015-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