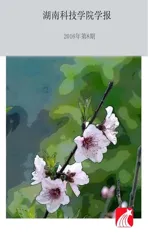加里·斯奈德的印第安情结
2016-03-07周善春信阳学院外语系河南信阳464000
周善春 马 娟(信阳学院 外语系,河南 信阳 464000)
加里·斯奈德的印第安情结
周善春 马 娟
(信阳学院 外语系,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加里·斯奈德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成长环境让他对印第安原始文化情有独钟。这一文化中的万物有灵伦,图腾崇拜和原始神话都先后在斯奈德的诗歌中呈现,并构成了诗人与众不同的生态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斯奈德;印第安文化;诗学观;影响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是“垮掉派诗人”中的常青树,被誉为美国深层生态学的桂冠诗人。因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创新和杰出成就,斯奈德先后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伯利根诗歌奖、约翰·黑自然书写奖和鲁斯·里利诗歌奖等多项殊荣。在接纳美国文学传统和主流文化的同时,诗人以博大的胸怀吸收借鉴印第安少数民族文化和以中日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在美国诗坛独树一帜。在环境问题日渐严重,生态危机困扰着每一个人的当今社会,斯奈德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被广泛地关注和发掘。国内外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关注斯奈德作品中的生态思想、诗学观、诗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着重分析斯奈德诗歌中的印第安情结以及这一少数民族文化对诗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 诗人迷恋印第安文化的成因
斯奈德从小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对其迷恋和倾心大自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诗人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家人生活困难举步维艰。为了生存,他们被迫搬迁到华盛顿州西雅图北部的克莱城,以种地为生。农庄周围的树林成了斯奈德童年的乐园和天堂,诗人小的时候经常跑到树林中露宿野营,生火做饭。家庭生活的拮据让他从小就有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在父亲的教导下,他10岁就学会了锯木、伐木、清除林地等技术。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对诗人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诗人经常用心探索森林、感受自然,投入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即便后来搬到了城市,他依旧怀恋在大山里度过的美好时光。随后的生活中,诗人经常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宿营,同时对背包旅游和登山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身临其境地感受荒野和山林,以及从阅读中了解的异样的山水,都给诗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51年斯奈德的一份特殊的工作(木厂测量员)让他有幸去了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去了解那里的印第安人,采集他们的口头文学。里德学院的大学生活影响了后来诗人的写作方向,同时也启蒙了诗人的思想,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在几个大学老师的耳濡目染下,斯奈德学会了如何使用图书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一次偶然的机会,斯奈德读到了印第安人诗歌和神话,从此便沉迷其中如痴如醉。他读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有关动物的书籍,尤其是被称为“动物小说之父”西顿的作品。印第安人民族敬畏自然,并与自然如此和谐地相处对后来斯奈德生态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接受美国主流文化如爱默生、梭罗的文学思想的同时,斯奈德怀着崇敬和向往,在印第安民族文化中开始了自己的原始寻根之旅。荒野中的别样体验,丰富的社会实践,印第安民族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神奇的原始仪式、奇妙的氏族传说都深深地镌刻在斯奈德的脑海里,并构成了诗人生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斯奈德诗歌中独特的印第安文化
斯奈德没有接受基督教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人类至高无上的思想。相反他坚决反对不计后果地野蛮征服自然,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互惠互利,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而印第安人诗意栖居自然的方式让斯奈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十分敬重他们“提倡保护型而非生产型、稳定型而非增长型、质量型而非数量型的生态文化”[4]P195。因此印第安文化中的万物有灵伦,图腾崇拜和原始神话都先后在斯奈德的诗歌中呈现,并构成了诗人与众不同的生态诗学的一部分。
(一)万物有灵伦
“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在印第安人的原始宗教之一。它相信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灵魂,人、动物、植物和山川河流都有灵魂。人死了,但灵魂不死;自然物体没有生命,但有灵魂。各种灵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善恶之分。人们想出一些乞求精灵保护的方法,由此产生了祈祷仪式,这便是宗教仪式的最早发端。”[6]P102-103由此可见,印第安民族宣扬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灵魂的,而且这些灵魂只有善恶两种,没有贵贱之分。就像美国《独立宣言》宣扬的那样人人生而平等,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既然众生平等,人类就不能让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要合理控制自己的行为,开发利用大自然的馈赠时要有心存感激和同情,要学会知恩图报。既然自然界的一切花草树木、高山流水、岩石土壤都有平等的灵魂,人类要摒弃我们是万物灵长而凌驾一切之上的思想,放弃过去滥砍滥杀的行为,用建设性的方式去开发自然,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地上的其它生物。正如《神话与文本》里面所描写的:“鹿不愿为我而死。/我将饮食海水/在雨中睡在海滩的碎石上/知道鹿下来送死/因为同情我的苦痛。”[2]P126正因为印第安人尊重所猎之物、并对它充满敬畏和感恩,诗中的鹿才自愿出来奉献自己的生命来同情我的痛苦,来满足我的生存所需。既然万物都有灵性、会互相体谅,我们需要更多的怜悯和关爱,互相尊重、互存感激,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的大同世界,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二)图腾崇拜
在原始部落,由于生产力低下,科技尚未起步,人们无法解释许多常见的自然现象,就想象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和能给部落祖先带来吉祥好运的图腾。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并把它们视为神物顶礼膜拜。民族学家研究发现图腾崇拜最早来自于北美印第安人,而且他们几乎每个氏族都把自己钟爱的动物视为图腾和氏族的象征。在印第安人的眼里,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特异功能,在某些方面具有超凡的能力,和人类一样聪明。因此它们不应该成为人类欺凌和征服的对象,而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斯奈德《神话与文本》的《狩猎》部分,充满了图腾崇拜的现象。鸟类,熊和土狼等是里面出现最多的动物。
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眼里,鸟可以搏击天空自由翱翔,具有神奇的魔力。它们是天地之间衔接的纽带,可以和神灵交流沟通。因此在宗教仪式中,印第安人常常披着鸟的翅膀,对着太阳祈祷,寻求灵魂超脱精神升空。就像在中国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成了商族的标志和图腾一样。斯奈德在《狩猎》中曾这样写到:“旋转的鸟儿飘向屋顶/风筝降落,摇晃地飞向海岸旋转的雾团:/形式:空中的点,一行变成另一行,/未来界定了。”[5]P140在诗中,鸟是一个预言家,可以预测天气和未来,因此充满智慧和力量。
熊也是印第安人极为崇拜的对象。作为丛林之王,它代表着大自然的博大胸襟和威武雄壮。在图腾柱上熊到处可见,它是信使,是世俗自然和超自然联系的重要纽带;它力大无穷勇猛彪悍,是丛林的守护神。因此,印第安人在举行隆重的仪式时,总是喜欢穿上熊皮外衣,把熊爪和牙齿做成的装饰品作为他们的护身符。印第安神话中人熊通婚更是象征着人和自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斯奈德《写给熊的诗》:“我是山神之子……/这个女孩嫁给了熊,/谁来统治山林,熊?”[2]P24就反映了诗人对熊的敬畏和喜爱。
最后,郊狼也是印第安神话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一个矛盾而又神秘的形象。一方面,它像希腊神话中勇敢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用神奇的尾巴为人类带来了火种,并教会人们怎样捕食鲑鱼,识别食物等。另一方面,它又有偷奸耍滑自以为是的捣蛋鬼形象,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充满了反叛的精神。斯奈德在诗中写到:“人和禽兽,禽兽和禽兽/全都获得佛性/只有郊狼/没有。”[3]P34因此,郊狼在印第安神话中既是创造者的角色,又是毁灭者的形象;既拥有超人的智慧,又是撒旦的化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三)原始神话
斯奈德很早就对印第安原始神话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他在父亲的村庄里猎鸟:海达神话的向度》就反映了他对印第安神话的关注和初步研究。诗人更是对印第安神话中的龟创世神话、鹰女人和熊丈夫的故事青睐有加。斯奈德的佳作《龟岛》就来源于印第安人的乌龟创世神话。北美大陆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由一只长生不老的巨型龟支撑着。所以诗人就用印第安口中的龟岛来指代北美大陆,用它来象征希望和平幸福之地。
鹰是印第安文化中的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向往自由而又能高傲地飞翔。有一则鹰女人的神话故事:一个出生上层社会的绝佳美人,邂逅了一个鹰化身的美男子,两个人喜结连理,并生育两孩子。但是对家人和故土的思念让她孤独寂寞。于是,她带着两个孩子从鹰村逃了出来,却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她灵机一动,用自己的两根辫子绑住孩子,腾出双手,顺利游到河对岸。而熊丈夫的故事更是让人嘘唏赞叹。印第安女人被迫嫁给黑熊首领,并和他生下两个半人半熊的儿子。后来,那女子的哥哥杀死了熊丈夫,救出了她们母子三。
三 印第安文化对其诗学观的影响
斯奈德在深受美国传统作家爱默生、梭罗、弗罗斯特等影响的同时,也从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如东方文学,印第安少数民族的神话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不断地学习、思考和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态诗学观。在生态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斯奈德希望现代人类能够像古老的印第安名族那样栖居荒野,重建人和自然和谐圆满的关系。首先诗人认为要有整体一盘棋的思想,相信世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因此诗人提倡回归自然,栖居自然,重建原始社会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完美状态,强调生态保护意识,而不是把人类凌驾到自然之上,随意地施虐和践踏。就像在《致万物》中所描写的那样:“我发誓效忠/龟岛的土地,/一个生态系/缤纷多样/在太阳下/欢乐地为众生讲话。”[1]P113-114另外,斯奈德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像梭罗那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用心去感受体会自然的美好,在生态社区中扎根,培养地方认同感。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幸福地栖居荒野,这既是文明人的责任感又是一种生态良心。诗人认为要想和自然和谐相处,我们需要顺天意尽人事,既要扎根脚下的土地,又要遵守自然界的法则。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践中与自然和平共处,在诗歌中实现诗意的栖居。
印第安原始部落的智慧以及与自然完美栖居的实践让斯奈德产生了敬畏和尊重,同时也影响到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的形成。正是由于这些印第安情结的影响,诗人才有幸成为深度生态学的桂冠诗人,在生态诗歌的世界里自由地徜徉,在荒野里完美栖居。
参考文献:
[1]Snyder,Gary.Axe Handles[M].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1983.
[2]Snyder,Gary.Myths and Texts[M].New York: New Directions Book,1960.
[3]Snyder,Gary.Myths and Texts[M].Toronto: Penguin Books Canada Limited Press,1978.
[4]陈小红.加里·斯奈德的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洪娜.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加里·斯奈德的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6]李玉君.印第安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责任编校:周欣)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8-0032-02
收稿日期:2016-04-19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青年项目“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加里·斯奈德诗学中的‘荒野’情结”(项目编号2016-qn-162)。
作者简介:周善春(1980-),男,河南固始人,信阳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教学。马娟(1983-),女,山东平阴人,信阳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