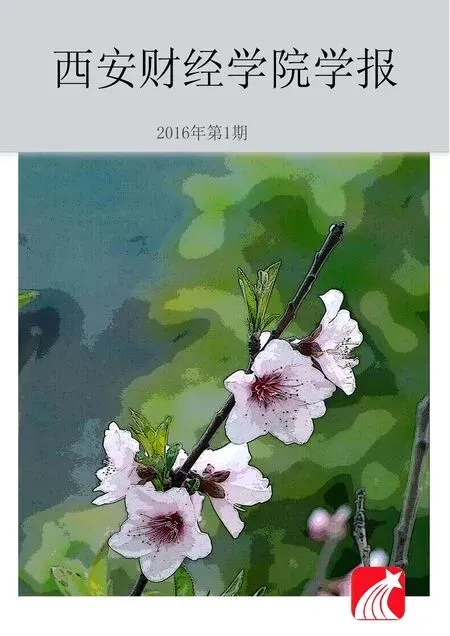《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及思想阐释——兼与秦始皇形象的历史比较
2016-03-03高旭
高 旭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 淮南 232001)
《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及思想阐释——兼与秦始皇形象的历史比较
高旭
(安徽理工大学 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 淮南232001)
摘要:《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阐释,主要受道、儒两家的深刻影响,具有道儒融合、以儒补道的思想特色。与重在批判秦始皇不同,《淮南子》对秦穆公着力于积极借鉴,因此二者的政治形象及思想内涵均有差异,内在反映出《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的双重汲取。对秦穆公史事的重视和阐释,使《淮南子》对待秦政治文化的历史理性,较同时期其他著作更为深刻丰富,充分展示出汉代黄老政治广阔包容的思想气度。
关键词:《淮南子》;秦穆公;秦始皇;秦政治文化;道家;儒家
在春秋时期的秦国史上,秦穆公(前659年-前621年)可谓声威赫赫,是秦立国以来最为“杰出的、有卓越贡献的君主”[1]之一。其继秦文公“踰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之后,勤于“修政”,进一步开疆拓土,使秦国“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2]685。秦穆公在位的三十九年,是秦国政治史上的关键时期,穆公政治霸业的不断开创,“不仅对秦国的历史走势和春秋时期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秦文化的区域互动发展也提供了新的契机”[3],最终为以后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秦人自己对穆公推崇有加,秦孝公就曾言:“昔我缪公(“缪”、“穆”二字相通)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2]202在后世的汉人看来,穆公也是秦国称霸诸侯、迈向统一天下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政治人物。贾谊在《过秦论》中便云:“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2]277司马迁说得更为深刻:“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2]276可见,秦穆公不论是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发展,还是对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演变,都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正因如此,对汉代思想家来说,秦穆公并非可有可无的历史人物,而是先秦政治史上应被重视和提及的贤能之君,其生平政治事业的得失成败,值得反思和借鉴。作为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理论总结之作,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著的《淮南子》一书,对秦穆公史事便有着较多论述,而且从道、儒立场出发,对其进行时代化的新阐释,以此丰富自身治国思想的政治内涵。
一、《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
作为先秦时期秦国声名卓著的国君之一,秦穆公在《淮南子》中出现多次,其政治史事不仅为后者所熟知,而且成为后者思想论述的历史载体,发挥了一定的理论构建作用。对秦穆公一生最为重要的政治史事,《淮南子》大都有所涉及,其中有的还不止一次提到,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赠送女乐,谋灭戎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4]《主术》194,“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4]《精神》194,对秦穆公征服西戎之事,《淮南子》有着深刻印象。在其看来,秦穆公是以政治权谋手段,消弭戎王对秦国的警惕,使其沉迷女乐之中,以此实现自己对西戎的蚕食兼并。
图谋西戎之地,这是秦自立国以来,历代国君的政治梦想。随着秦国的日渐发展,至穆公时期,如何解决周边戎族部落对其东进战略的严重掣肘和威胁,这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秦穆公在位期间,先后对“茅津之戎”、“陆浑之戎”进行战争,并着重谋划对西戎部落的彻底征服。在戎王派大臣由余使秦后,穆公设计使戎王疑心由余,迫其归顺秦国,而后采纳由余计策,以“女乐”赠送戎王,让其沉迷其中,放松对秦的警惕,最终使秦武力得逞,实现“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194的政治目的。由于秦穆公征服西戎之地的成功,这使得秦国再无后顾之忧,能尽力从事东进战略,因此“遂霸西戎”成为秦国兼并天下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不仅为中国古代“西部民族融合起了促进作用”,具有“一定贡献”[5]30-38,而且“为战国末年整个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6],影响极其深远。由此,在先秦时期,秦穆公谋取西戎之事,便广被史学家、思想家所重视,如《左传》、《战国策》、《墨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书,都有着相关记载和论述。时至西汉,同样如此,除《淮南子》外,《史记》、《说苑》等书也都有所提及。
2.使伯乐荐人求良马,举百里奚为秦相。在先秦政治史上,秦穆公向以知人善任著称,是“有名的尚贤的国君”,其“任用外贤的作法后来成为秦国的传统”,“对战国时秦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5]30-38。秦穆公计取西戎贤臣由余,拔擢百里奚于卑贱,都为后世所称道,《淮南子》对此也有突出反映。但《淮南子》中不仅对秦穆公的知人之明表示肯定和颂扬,而且通过伯乐荐人相马之事,批评其也有难以识人之时。
对相马之事,《淮南子》有详细叙述。伯乐年长,秦穆公问:“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说:“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认为其后代中并没有真正能鉴识良马之才,于是向穆公推荐九方堙。穆公相信伯乐,随后派遣九方堙去寻找良马。三个月后,九方堙回报穆公说已找到良马,是一匹黄色的雄马。穆公让人去取回良马,却发现是一匹纯黑色的雌马。于是穆公很不满,责怪伯乐荐人不明。伯乐并不以为然,说:“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4]《道应》859-862他认为九方堙透过表象抓住良马的本质精神,发现的正是良马。当马被赶回秦国后,穆公亲眼所见,方知九方堙所识之马确为“千里之马”。虽然《淮南子》对相马之事的叙述,主要重在阐发伯乐的相马之理,但借此事也间接批评了穆公缺少识人之明,说明为政者观人察贤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在政治用人方面,《淮南子》对秦穆公的这种批评是其次的,主要仍是肯定和称赞,这显著反映在秦穆公对百里奚的政治卓识上。《淮南子》认为,“百里奚之饭牛”,当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时,众人都“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看不到百里奚所具有的治国才干,而秦穆公却能慧眼识贤,让其“兴于牛颔之下”,并“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给予实际的重用,使之得以充分施展抱负,“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4]《氾论》967-969,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名相。在《淮南子》看来,“百里奚转鬻”,若不是秦穆公的政治见识和用人气魄,被作为奴仆来转卖的百里奚,根本无法“蒙耻辱以干世主”,更难以实现其“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4]《修务》1319-1320的政治理想。因此,从政治用人而言,《淮南子》认为秦穆公堪称英明之君,值得西汉统治者借鉴和取法。《淮南子》还指出:“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认为秦穆公在治国实践中不专己能,任贤而治,这体现出“君不与臣争功”的政治原则,内在合乎“治道”[4]《缪称》740,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3.袭郑而败殽,拒谏而悔过。“秦胜乎戎而败乎殽。”[4]《诠言》1004如果说谋取西戎带给秦穆公巨大的政治成功,为秦国实现了战胜强敌、拓土开疆的政治目的,那么因偷袭郑国而引发秦、晋两国的殽之战,则带给其重大的政治打击和耻辱,使其深为悔恨。这场春秋时期的著名战役,因其中所具有的复杂的政治内涵,而为世人所铭记和反思,其中便包括西汉前期产生的《淮南子》。
对殽之战,《淮南子》不仅多次提到,而且对其具体过程有着详细叙述。在同时代的思想论著中,对殽之战的历史叙事,其深入细致之处,唯有《史记》可与之相较。可见,《淮南子》对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殽之战,具有深刻的汉代记忆,十分重视其中深刻丰富的政治内涵,试图对其历史教训有所反思和借鉴。
《淮南子》不但着眼于秦穆公之史事,叙述殽之战的来龙去脉,而且还两次从郑国商人弦高的角度出发,具体论及这次战役,表彰弦高机智救郑、不图回报的爱国行为。
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的“袭郑”之举,是“违蹇叔,而以贪勤民”[7]497的消极结果,其实质是利欲熏心的不义之战。但事后,穆公“素服庙临,以说于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其内心的悔恨之意。与此不同,《淮南子》认为,商人弦高能不吝其财,勇于救国,最终使郑国免遭亡国之灾,这是正义之举,因而即使其“矫郑伯之命”以诓骗秦军,这也是正义性的权宜之行,值得褒扬。但《淮南子》同时指出:“弦高诞而存郑,诞者不可以为常”,认为这种矫制而为的欺诈行为,是“事有一应而不可循行”[4]《说山》1120,实际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举,具有破坏国家体制的消极作用,并不能以常态视之。
4.赠野人以马酒,因恩得其回报。秦穆公为君,具有一定的“重民思想”,“能够注意如何争取民心,借助民力”[8],因其善予人恩惠,能得其心而用其力。《淮南子》提及秦穆公与野人之事:“秦穆公为野人食骏马肉之伤也,饮之美酒,韩之战,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4]《泰族》1383
虽然野人偷食其马,但秦穆公对待这些普通民众的方式却出人意料。在追赶到野人时,不但没有追究其罪名,反而关心其“食骏马肉之伤也”,并以酒赏赐野人,随后“遍饮而去之”。这种极富政治胸怀的做法,反映出秦穆公的君主气度,因此在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中,当秦、晋之间进入胶着状态,而秦穆公险被晋军俘获时,曾偷食穆公之马的野人们,奋不顾身,“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最终改变了战争结果,不仅使穆公取胜,而且使秦军反过来虏获晋惠公。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之所以能为野人所救,得其死力而用,关键就在于他能以宽大恩惠的方式对待野人。需指出的是,《淮南子》中关于秦穆公与野人的历史叙事,主要本于《吕氏春秋·爱士》,二者文字所述基本相同。
从上可知,《淮南子》中保留有不少关于秦穆公的史事记载,对秦穆公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几乎都有所涉及。这反映出《淮南子》对秦穆公有着不同于其他秦国国君的“待遇”,实际上将秦穆公看作先秦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之一。正因如此,《淮南子》习惯于把秦穆公与齐桓公相提并论,视其为春秋时期政治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君主形象,并试图在秦汉时代下,对其史事进行深入诠解,以此丰富自身政治思想的历史内涵。
二、《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思想阐释
《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反复提及,与《史记》不同,并非出于历史记载的史学目的,而是从现实政治的发展着眼,以特定的思想观念对其进行阐释,赋予这些史事以新的政治内涵。虽然《淮南子》中蕴含多元的思想因素,是“在汉代条件下,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一个缩影,其中主要反映了道、儒、法、兵、阴阳和辩察之学”[9],但在对秦穆公史事的思想诠解中,却主要体现出道、儒两家的历史影响。经由这种时代化的理论阐发,秦穆公作为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化形象,在《淮南子》中得到符号化的凝练和提升,成为其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内容,显示出秦政治文化对后者所具有的独特影响。
1.《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较为侧重于为君之道的政治思考,具有一定的辩证性,充分体现出汉代黄老思想的历史特色。
《淮南子》论及秦穆公谋取西戎事时,以“胡王好音”为例,阐发道家的“无为”思想,要求君主以此“治身”,确保其根本的政治利益。“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4]《主术》669,《淮南子》反对君主将自身欲求外在化,致使他人能窥知和利用其喜好,造成“以利见制于人也”[4]《主术》667的政治恶果。《淮南子》特别着眼于现实的君臣关系,对此进行阐述:“喜怒形于心,嗜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4]《主术》669,认为君主违背“无为”、“无好”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只能是为臣下所利用,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政治利益。因此,《淮南子》明确强调老子所说“善建者不拔”的观点,要求君主深刻以史为鉴,能“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4]《主术》669,而非相反。
在伯乐向秦穆公阐述其相马之理时,《淮南子》对伯乐所言“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进行道家化的诠解,认为其体现出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的思想精神,突破了马的外在形象的局限,对良马之所以为“良”有着本质性的把握。这实际上已将相马之术带入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
对秦穆公在殽之战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淮南子》也以道家思想为依据,展开政治批评。秦穆公贪图郑国的利益,想要趁人不备,“袭国”而取之,但蹇叔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行为,极易失败,因为不但出兵的机密性难以确保,“为其谋未及发泄也”,而且“行数千里,又数绝诸侯之地”,军队的粮食后勤也无法有效补给。对待蹇叔的正确意见,“穆公不听”,甚至斥责蹇叔道:“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8]491,表现出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消极态度。正由于这种不明智之举,最终导致秦军劳而无功,乃至于在殽被晋国“大破之”,全军覆没。《淮南子》指出真正不知者,并非蹇叔,而是秦穆公,因此引老子之言批评后者:“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认为秦穆公在政治上是“不知而知”,缺少自知之明,其结果只能是自饮苦酒,悔不可及。鉴于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淮南子》在政治上主张君主应该善于“听治”,能“并用周听”,积极纳谏,而不是闭目塞听,“专己之能”。
2.《淮南子》在诠释秦穆公史事的过程中,也深入吸收儒家的思想因素,不仅强调仁义德治的重要性,表现出伦理政治的理论倾向,而且对儒家的政治“权”变主张也有一定的突出反映。
在“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一事中,《淮南子》记述商人弦高推辞郑伯对其“存国之功”的褒赏之语:“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4]《人间》1272在弦高看来,“矫郑伯之命”以欺秦军的行为,虽然出于爱国的目的,体现正义的性质,但终究是违制之举,对国家政治的良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而且这种缺乏诚信的行为如果得到鼓励,也将会败坏国家风俗,因此“诞而得赏”,此事“仁者弗为也”、“义者弗为也”,只能是权宜之计,并不值得鼓励和提倡。显然,弦高是从儒家意识出发,以仁义诚信的思想原则来理性审视自己的救郑行为,从而不居功自傲,主动辞赏而去。对弦高这种政治行为,《淮南子》一方面积极肯定:“故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认为不但是“圣人之思修”[4]《人间》1272的深谋远虑之举,而且内含重义轻利、“不以利害义”的政治精神,是对儒家义利思想的充分反映。另一方面,《淮南子》又指出:“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4]《氾论》954,认为弦高救郑是善于“知权”的表现,而“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是“忤而后合者”的结果,虽一时不合乎常规的政治原则,但却是“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的灵活行为,根本上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现实发展,因此并非是对仁义诚信思想的真正背离,而是具有政治的合理性。由此,《淮南子》还引孔子之言以证之:“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4]《氾论》956-957,认为弦高因“权”而救郑的政治行为,将正义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际上不可多得。
三、《淮南子》中秦穆公、秦始皇的形象比较
《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有着深入的历史汲取,这突出表现在其对秦穆公、秦始皇的思想认识上。在《淮南子》看来,此二者实际上可被视为秦政治发展之兴起、败亡的政治人格代表。如果说对秦穆公《淮南子》主要是肯定,那么对秦始皇则重在批判。这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既使《淮南子》对秦穆公、秦始皇的阐释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也使二者形成完全不同的政治形象。具体而言,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表现:
1.《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的政治用人举措不同,其治国效用也迥然有异。前者有知人之明,善于用贤;后者则昧于功利,用人求同。
“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淮南子》在治国上十分重视用人问题,强调为政者必须慎于选材用人,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发展的稳定与否,“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4]《主术》641。《淮南子》认为用人的关键在于“举贤”,要求为政者既能“无故无新,惟贤是亲”[4]《主术》694,也能“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4]《缪称》741。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对百里奚的慧眼卓识,与齐桓公用管仲一样,都是先秦政治史上“举贤”而用的历史典范。“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这种对“举贤”原则的积极贯彻,体现出君主真正的政治智慧,根本上符合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4]《缪称》740。《淮南子》指出,百里奚虽然有过“饭牛”、“转鬻”的卑辱经历,但其怀有“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4]《修务》1320的治国理念,始终以天下万民为己任,而非贪图私利禄位,因此在得到秦穆公的赏识和重用后,能“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成为“诸侯贤相”[4]《氾论》968-969。“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4]《缪称》709《淮南子》坚决反对为政者在用人上“求同乎己”,提出:“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4]《泰族》1408在其看来,秦穆公、齐桓公在“举贤”方面,可谓“圣主”,因为二者选材用人,都不“求同乎己”,而是唯贤是用。与此相反,秦始皇“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4]《泰族》1408。《淮南子》批判秦始皇的用人实践,认为其信用功利之臣,是“举所与同”,非但无益于矫正其极端功利化的治国歧向,反而变本加厉,更加造成虐民苛政。“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4]《人间》1273《淮南子》认为“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4]《人间》1255,这正是秦始皇所用非贤的政治恶果。
2.《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在现实政治中都有拒谏行为,对秦政治发展也均产生严重影响,但二者事后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却有着内在不同。
在秦穆公一生中,最严重的拒谏行为发生在殽之战前。秦穆公试图趁人不备,不“假道”于晋国,袭取和控制郑国,蹇叔对此表示反对,并极力劝阻穆公,但“穆公不听”。事后如蹇叔所预料,晋国不满于秦越境袭郑,在殽设伏,最终将秦“大破之,禽其三帅以归”,使秦军全军覆没。正因利令智昏,拒纳谏言,致使秦穆公作出袭取郑国的错误决策,使秦国在春秋时期的东进战略,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秦穆公并没有文过饰非,而是亡羊补牢,“素服庙临,以说于众”,不仅没有把战败罪责推诿给败军之将,而且坦承自己的拒谏错误,主动“罪己”,向臣民道歉,表示以此为鉴,在治国上坚持重用“良士”,积极纳谏,“尚猷询茲黃发,則罔所愆”[10]670,“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10]672。秦穆公这种认错悔过的政治行为,取得秦国臣民的谅解,重新凝聚人心,有利地稳定了现实的政治形势,为日后败晋复仇奠定基础。
与秦穆公的明智之举不同,《淮南子》指出:“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4]《氾论》942-943
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发展,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给广大民众带来空前灾难,以致出现“道路死人以沟量”的惨景。但是,始皇作为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对“忠谏者”所言有所积极采纳,而是忠言逆耳,以之为“不祥”。这种“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11]的政治作风,延及秦二世时期,更加严重,甚至于“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2]268,造成无人敢言的政治乱局,最终促使秦王朝在孤立无助中彻底崩解。时至汉初,贾谊对此仍深有反思和慨叹,认为:“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2]278
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的拒谏而悔过,与秦始皇的拒谏而不知悔,实际上形成强烈对照。这种对待“谏言”及“谏臣”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充分反映出二者政治见识及气度的优劣高下,而且其间的得失成败,在秦汉政治发展上也极具镜鉴意义。
3.《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的政治实践,还存在着德义内涵的差别,对社会民众产生不同的现实影响,也深刻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发展走向。
在秦、晋间的韩原之战中,秦穆公之所以能转败为胜,源于其曾对野人施加过恩惠。对那些饥不择食的普通民众,秦穆公非但没有惩罚其对骏马“屠而食之”的罪责,反而对后者言道:“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并以酒赏赐,“遍饮而去之”。秦穆公这种宽大为怀、重人轻物、施德行惠的做法,使野人为其“精诚”所感,故愿“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解救穆公于危难之中。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是“用约而为德者也”,作为一国之君,其对野人所施恩惠虽不可谓之重,但所获却极大,所谓:“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4]《氾论》973这充分展现其成熟务实的政治才干。《淮南子》进而强调:“故摅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4]《泰族》1384,主张为政者应如秦穆公那样,以诚心待民,布德施惠于民,从而得到其积极的政治支持和拥护。
《淮南子》认为,秦始皇的政治实践,与秦穆公“为德”于民正相反。秦始皇只知“兼吞天下”,而不知“布德施惠”于民,严重轻忽和背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的基本政理,无法以仁义之政作为王朝存在和发展的“厚基者”,最终只能是“积怨在于民也”[4]《兵略》1065,在“不增其德而累其高”的政治歧途上彻底败灭。两相比较,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在秦政治发展上,显然要优于秦始皇,因为其治国实践具有“用德”、“精诚”的“重民”内涵,并未视民众为草芥,毫不顾忌民众的生存利益。
由上可知,《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主要出于历史肯定,将后者看作秦政治发展中的杰出君主,认为其政治史事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试图在秦汉时代条件下,对其展开新的思想阐释和转化,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而对于秦始皇,《淮南子》则始终采取批判的历史态度,罕有肯定之辞,视之为秦政治发展史上的反面典范,力图汲取其负面性的历史教训,以此促使西汉统治者谨记“亡秦之鉴”,不重蹈亡秦之失。就某种程度而言,《淮南子》对秦穆公、秦始皇的不同认识,实际上相辅相成,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出秦政治文化对其所产生的复杂深刻的历史影响。
四、余论
作为西汉前期重要的思想论著,《淮南子》对秦穆公、秦始皇都有较多论及,并在其汉代叙事与阐释中,使二者的政治形象形成鲜明对照,成为体现秦政治发展经验的两种君主类型,即秦穆公所代表的正面性的贤明君主以及秦始皇所代表的负面性的贪主暴君。《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的历史汲取,主要是通过这两种不同的君主类型来体现的,进而表现出对秦政治发展的积极与消极经验的兼收并重。《淮南子》这种对秦政治文化的双重汲取,在同时代的论著中,并不多见。因为汉代思想家大都强调“过秦”之论,存在着“重其亡而忽其兴”,“对秦朝的兴盛过程研究不够”[12]的理论局限,在侧重于对秦始皇及二世的严厉批判的同时,较为缺少对先秦时期秦国兴起的政治经验的关注和总结。由此意义而言,对秦穆公史事的重视和诠解,实乃《淮南子》在汉代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之一。但也须指出,尽管《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十分重视,但从其汲取秦政治文化的总体来看,后者的重要性仍不及秦始皇。换言之,秦始皇所代表的“亡秦之鉴”,其强烈深刻的负面教训,使《淮南子》政治思考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并没有超脱出西汉前期“过秦”思潮的根本范畴。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部历史性总结西汉黄老政治的“王者之书”,《淮南子》这种对秦政治文化的双重汲取,充分展现了其广阔包容的思想气度,也反映出西汉统治阶层试图全面总结以往历史经验,力求开拓进取的治国精神。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秦国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1.
[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吴保传,刘哲.秦穆公称霸与秦文化的区域互动[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2):107-110.
[4]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林剑鸣,刘宝才.论秦穆公[J].人文杂志,1980(6):30-38.
[6]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50.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冯庆余.秦穆公的霸政[J].东疆学刊,1992(2):42-45.
[9]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7.
[10]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3.
[12] 王绍东.论汉代“过秦”思想的历史局限[J].史学史研究,2009(3):26-32.
(责任编辑:高士荣)
On Mu of Qin’s Narratives and Ideas of Han Dynasty inHuaiNanTzu:
With the Comparison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GAOXu
(ChuHuai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Among the emperors in the pre-Qin period, Mu of Qin, as well as the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 of politics, is mentioned the most inHuaiNanTzu.The interpretation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which reflec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th.Different from making critical comment on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HuaiNanTzufocuses on Mu of Qin positively, so the political image and the thinking connotation of them have differences.HuaiNanTzu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litical events of Mu of Qin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Qin Dynasty.Compared with other works, its interpretation is more profound.It fully displays broad and inclusive thoughts of Huang Lao of Han dynasty.
Keywords:HuaiNanTzu; Mu of Qin; First Emperor of Qin; political culture;Taoism;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16)01-0118-06
作者简介:高旭(1979-),男,陕西延安人,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淮南子》与道家道教研究所所长,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
收稿日期:2015-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