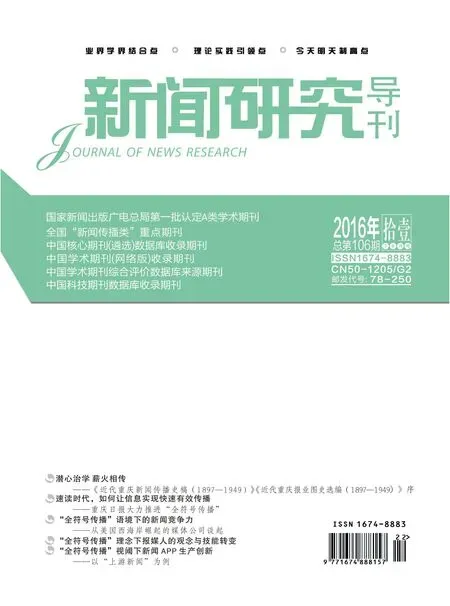仪式传播视域下网络直播节日庆典的神话塑造
2016-02-28魏涵玉
魏涵玉
(江西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仪式传播视域下网络直播节日庆典的神话塑造
魏涵玉
(江西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网络直播的节日仪式其本质在于塑造集体参演的仪式感来构建自身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而权威性与神圣性的构建不断地形塑着个体的认同,并建构了网络直播的神话空间。网络直播的庆典仪式通过观看个体的参与、共享,起到了凝聚个体力量、塑造共识的作用。网络直播的节日庆典仪式也被当作铭记集体记忆的形式。
网络直播;展演;媒介仪式;节日庆典
一、网络直播节日庆典仪式的个体认同的塑造
在仪式传播概念的界定与认知层面上虽存在模糊性与争议性,但本文的立场建立在刘建明等学者对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理解的共识之上。罗森布尔认为仪式传播包括“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前者指的是具有传播特性的仪式活动,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正式仪式(如宗教仪式、婚礼等)和非正式的仪式(如见面握手,分别说再见);后者指的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如我们常论及的媒介事件。[1]随着网络直播进入全民直播的时代,直播已经成为集体参演式的活动。但细致地梳理网络直播认同构建的流变过程,其实可以抓住一条主线脉络,也就是网络直播集体仪式参演的神话塑造。而这种神话构建源自直播中的节日庆典等系列媒介事件的呈现。在新媒体场域当中,信息传播所依赖的介质载体是多元的,媒介事件的呈现常常与个体的日常生活联结在一起。譬如2016年6月16日,新浪微博的“超级红人节”盛典在中国上海举办,网友通过票选的形式选出了十大顶级的网络主播;譬如2016年China Joy中网络主播和网红的展演以及2016年11月20日湖南的首届网络红人节;譬如“直播+综艺”而衍生的《Hello,女神》的节日盛典等,都说明了网络直播集体共享的节日是常态化存在的。节日庆典的仪式不仅建构了网络直播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而且还形塑着个体的认同。传播的主体在媒介仪式中通过自我的展演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节日仪式作为媒介镜像呈现的外化表征,使主体对象本身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在节日仪式的背后,观众始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观看的个体可以突破时空维度的束缚来观看网络直播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正是因为媒介技术的成熟实现了影像画面的高度仿真性,制造出与现实环境相差甚小的虚拟现实,观看的个体可以沉浸于媒介制造的幻象中获得非在场性的现实体验。无论是现实场域还是网络空间的虚拟场域,互动性是形塑认同、营造共识的关键。在节日仪式的媒介呈现中,观众可以作为参与见证历史时刻的个体,始终与他人共享着共同的意义,而这一系列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培植认同。无论是观众的投票行为还是银幕上漂移的弹幕,最终都把观众构筑成了媒介庆典仪式的一部分。有关网络直播的节日庆典仪式最终成为集体铭记的关键时刻,并且作为集体记忆的方式存留在观众个体的脑海中。
二、集体仪式的“礼拜”塑造与展演的竞赛、征服、加冕
媒介事件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重大新闻及突发事件,还在于媒介事件通常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是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2]在节日庆典的仪式上,“礼拜”的构造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语境的消除;其二是语境的再造。从语境的消除来说,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生态呈现,它有着民间性、草根性、娱乐性的特质。而在以往主流的话语语境中,直播并非是一种个体性倾向的行为;直播往往与严肃性新闻以及大型公众事件衔接在一起,而并非个人化的行为。礼拜仪式其实就是确立节日仪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关键所在;对过往语境的消除是确定网络直播节日仪式礼拜的前提条件。而再造语境,符合网络直播的现实需求。媒介通过礼拜仪式的呈现从而确定自身的权威性,其实质就是网络直播如何在群体间塑造共识的问题。在对网络直播行为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主播都能够以自身的表演来打动观众、劝服观众并使其产生打赏行为,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直播房间的进流量决定着主播的排名与等级,主播的表演需要参与竞争,并不断地完成各种观众提出的挑战诉求,从而实现对观众的征服。戴扬与卡茨将媒介事件分为“竞赛”“征服”“加冕”,诠释了当前网络直播的展演行为。他们认为竞赛能够增强主播之间的紧张感与刺激性,从而实现观众的视觉快感;而征服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更多的是突出了主播的超越性。展演的内容本身如何吸引眼球也成为主播征服他人的关键。在网络直播的节日庆典仪式上,由网友票选出的主播实际上就是依赖于媒介仪式的加冕为其确立身份。
三、集体仪式的无脚本参演呈现与观看的流散性
基于网络空间直播的展演活动界于真实与模糊之间,无从探究。无论是展演的前台呈现还是后台呈现,真实中有虚假,虚假中有真实。而在网络直播的节日庆典仪式中,往往是集体演员共同参与构筑的空间。媒介节日仪式往往是一种无脚本的存在,在舞台展演的传播主体往往能够流露出自身的真情状态,而不需要在角色定势的制约下做出符合这一角色的表演行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元的,节日庆典仪式的意义共享场域也是多元的。人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单一的固定场域观看,而网络社会的观看告别了传统意义上以家庭空间为主导性地位的时代。观看网络直播庆典仪式的场域是游动的,并不拘泥于某一固定的位置,所以称之为“观看的流散仪式”。节日庆典的仪式性,不仅仅表现在观看的个体可以共享同样的意义,而且还是凝聚共识、形成团体认同的关键。而詹姆斯·凯瑞在早年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中就明确地表明了传播的本质。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3]媒介仪式的效用正在于此。
四、结语
网络直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公众中引起广泛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仪式在培植与塑造个体认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媒介仪式塑造了网络直播的神话,赋予了其神圣性与权威性。回归理性,超越现实,是看待网络直播的重要原则。
[1] 刘建明.“传播仪式观”与“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与樊水科商榷[J].国际新闻界,2013(04):168-173.
[2] 丹尼尔.戴扬,等.历史的现场直播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
[3]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G206.3
A
1674-8883(2016)22-01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