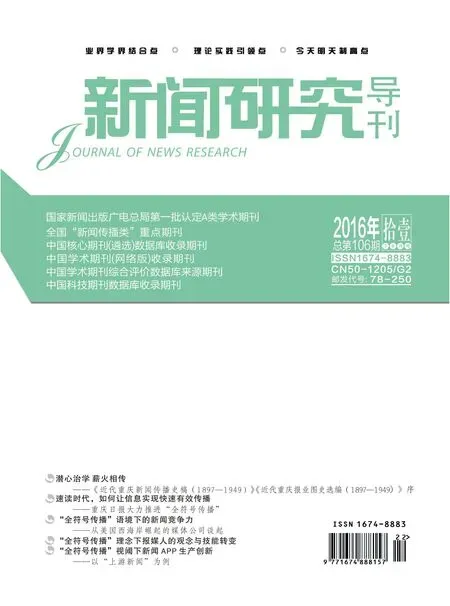技术善恶论的博弈:论技术观念在传播思想中的演变
2016-02-28郑照楠
郑照楠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技术善恶论的博弈:论技术观念在传播思想中的演变
郑照楠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技术是传播的助推器。传播历史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传播学者们关于技术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本文追溯技术争论的源头,结合传播学各个学派关于技术的核心观点,以期勾勒出技术观念在传播思想中的演变痕迹。
技术“善”论;技术“恶”论;技术观念之演变
技术伴随着人类传播的每一步发展。在传播的每一次巨大变革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其背后技术的助推作用。15世纪,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让中世纪的欧洲摆脱黑暗时代,新闻书和小册子开始流行,成为近代报纸的雏形;19世纪,电报电缆的实验成功让新闻跨越大洋,通讯社应运而生,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开始形成;20世纪,互联网的出现又让人类进入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主的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传播形态发生了新一轮的“洗牌”。可以说,技术引领着人类传播高歌猛进,一路前行。
技术使媒介呈现出新业态,将其触角深入到传播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宏观和微观上发生着影响。传播学者们对技术的论断也不一而足,但总体可归纳为三种:技术“善”论、技术“恶”论、技术“中性”论。媒介乐观主义和媒介悲观主义的阵营泾渭分明。那么,技术问题源起何处?技术“善”论和技术“恶”论的持有者分别都有什么说法?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技术观念在传播的思想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本文将从这三个问题入手,尝试梳理媒介乐观主义和媒介悲观主义对技术的不同看法,从而回答技术观念在传播思想中的演变问题。
一、技术问题的源起: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对技术问题的探讨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帝国的灭亡让整个欧洲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古罗马的先哲们对理性的推崇消失,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不复存在,粗俗和愚昧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幸福的标准仅仅只是达到物质的满足。马克思·韦伯将中世纪这种状态称为“魅”。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让作家开始记录自我,关注个人,“全人”的概念第一次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人们开始认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技术让启蒙精神萌芽,剥去了迷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这是理性“祛魅”的胜利。韦伯认为,技术是“社会理性化”的工具,即“工具理性”。[1]
印刷术让整个欧洲的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手工业者和科学家的信心。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对技术的欢呼和追捧逐渐蒙蔽了人们的双眼。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工具理性的关注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课题。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技术的过度褒扬使得工具理性变成需要批判的对象。在《启蒙辩证法》里,霍克海默等人认为,工具理性致使技术和科学意识形态化,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出现分裂与异化。文化工业和资本主义市场将一切纳入可被量化和复制的过程中,文化和个性濒临毁灭。马尔库塞直言,现代社会技术已失去中立性,成为统治工具或意识形态。
技术让文化产品失去原创的精神内涵,另外一位法兰克福的学者本雅明将其称为“灵韵”的消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本雅明把“灵韵”定义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呈现”。[2]简单地说,就是用时空感知范畴来表达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艺术作品,如达·芬奇的原作《蒙娜丽莎》只能被呈现在卢浮宫里,欣赏者所想感受其作品的灵韵,须跋山涉水跨越重洋叠嶂去卢浮宫。然而机械复制让摹本、复制品大行其道,观赏者尽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欣赏蒙娜丽莎的微笑。从感知方式上讲,机械复制让艺术作品的灵韵和仪式感急剧衰竭。
二、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芝加哥学派对技术的肯定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法兰克福学派表达的是对技术理性的焦虑,那么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芝加哥的学者们倒是对技术的态度颇为乐观。杜威对传播的兴趣集中在那些代表着速度、力量和效率的现代技术上,对于技术能够帮助科学研究表示热情的赞同。杜威认为,技术“将由工业创造的大社会改造成一个大共同体……传播技术是提升政治、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3]杜威的学生帕克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传媒与舆论相互影响。而一旦传媒与技术相结合,就能在更大范围上实现舆论的统一,可见传播技术是实现民主的手段。另一位学者米德一直在微观层面上关注传播对个人的社会化影响,他认为传播使个人的社会化得以完成,使社会的意义得以共享。
技术是民主社会共同体的基石。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一定是社会的进步。芝加哥学派这种对媒介技术的乐观态度并不难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理念早已全方位地渗透进各个学科的价值观。值得提出的是,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多伦多学派的大师——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
三、多伦多学派的传承:媒介与技术的深刻剖析
哈罗德·英尼斯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者。作为加拿大知名的经济学家,对技术和媒介是如何影响国家建设的研究让他的目光开始投向传播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著就《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传播三部曲,成为加拿大传播技术学派的先驱。作为导师,哈罗德·英尼斯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
对芝加哥学派将人类文明史看作媒介发展史的观点,英尼斯表示赞同。在《帝国与媒介》一书中,英尼斯考察了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中华帝国以及近现代各个大型政治机构的文明兴衰史,横跨东西,纵越千年。他着力论述了传播对文明的影响,以及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关键因素影响社会体制的变迁和文明的更替。在《传播的偏向》中,英尼斯匠心独运,首次指出了传播媒介时空上的偏向性。具有时间偏向性和空间偏向性的媒介在不同方面影响着帝国的扩张。英尼斯认为,媒介可分为两类:有利于时间上的延续的媒介和有利于空间上扩张的媒介。羊皮纸、黏土、石头等笨重、不易运输却很耐久的材料,具有时间的偏向,信仰、道德、宗教、文化等文明依靠此类媒介得以持久传承而稳定;纸张、电报、莎草纸等轻便却不易保存的材料,具有空间上的偏向,帝国依靠此类媒介将统治的触角一再延伸,以求政权在最大范围内的统治。英尼斯指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4]文明的发生依赖新的媒介形式的使用。同时,信息传送的技术结构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传播,关系着帝国的统治。文明的繁盛应该力求在传播的时空平衡。
值得提出的是,英尼斯十分推崇古希腊时期的口语传统,认为古希腊帝国的繁荣就是得益于口语传播。在他看来,口语传播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传播的理想平衡状态。《荷马史诗》就是在时间偏向的基础上表现对空间的强调。而随着15世纪以印刷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兴起之后,口语传播日渐衰弱。英尼斯抱着悲观的态度认为,这种偏向空间的媒介将导致文明的失衡。他直言,口语传统蕴含的是精神,文字和印刷的固有属性却是追求物质。[4]印刷带来了传播环境的大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演变为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5]
英尼斯认为:“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4]技术的进步导致文明的衰落,英尼斯对此深信不疑。面对电话、电报的普及,英尼斯十分忧虑。他认为,电子通讯将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增加帝国主义和文化入侵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可以减少技术和与技术挂钩的机构的影响,通过艺术、伦理、政治领域的教化,才能阻止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消亡。[3]
专注于媒介技术问题的多伦多学派的第二代旗手,便是声名远播的明星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刘易斯·芒福德对麦克卢汉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刘易斯·芒福德是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鼻祖,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在泛媒介层面上,芒福德认为,技术是人类机体的延伸。技术是人类征服、探索自然的媒介。铁路、汽车、发电站都可以被视为媒介。他认为这些技术不仅在表面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更在微观上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例如,玻璃的发明在始生代技术经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凸透镜制成眼镜可用来矫正视力;望远镜能让人类的视线投向外太空;显微镜的发明带领人类进入肉眼无法观看到的微生物世界。“玻璃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也拓展了人们的认知。”[6]此外,在心理层面上,镜子的出现让人开始关注自我、内审自我。毫无疑问,芒福德这种充满人文关怀,从心理视角切入探讨技术对人的影响,启发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如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介的划分,以及那句著名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论断。
尽管如此,说到麦克卢汉研究的真正指路者,还是哈罗德·英尼斯。麦克卢汉曾为老师的《传播的偏向》作序,谦称自己是英尼斯的“注脚”。我国学者何道宽这样形容两个人的关系:“麦克卢汉扛起了‘媒介决定论’的大旗,可这面帅旗的旗墩却是由英尼斯夯实的。”[7]
与老师所持的媒介悲观主义态度不同,马歇尔·麦克卢汉鲜明地站在媒介乐观主义的阵营。他的媒介三论,即“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冷热媒介论”无一不是为技术大唱赞歌。麦克卢汉考察了媒介技术对人的影响,提出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发明都是对人类感官的一次延伸。印刷是人类视觉的延伸;广播是人类听觉的延伸;电视是人类视听的双重延伸,后来的互联网更是被看作集人类多种器官于一体的综合媒介形式。同时他又指出,任何媒介的广泛使用都会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感官系统的力量对比。
麦氏对媒介技术的追捧在“媒介即讯息”中表达得更为露骨。人们总是看到,媒介新技术的运用带来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或更加快捷,或更加精准。然而,在麦克卢汉看来,这不是最重要的,新技术本身就是一次重大信息的诞生,将对社会生活产生极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媒介所传递的内容本身对社会发展没有实质意义,而这些内容的载体,媒介是最有意义的。这一理论打破了世人“内容为王”“渠道辅助”的观念,开始使人们关注媒介技术本身,开始意识到媒介技术悄无声息却时时刻刻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
四、纽约学派:电子媒介的研究先锋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纽约学派的一员重将,尼尔·波兹曼接棒第一代代表人物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关注技术与教育、媒介与文化。和英尼斯一样,波兹曼对技术表示了担心和焦虑。他的研究一直紧盯技术的负面影响,对媒介技术进行道德批判。面对技术的变革,他提醒人们:“一切技术变革都是浮士德的交易。”[8]“我们总是要为技术付出代价,技术越强大,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6]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波兹曼同意赫胥黎“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的预言,指出以美国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娱乐业掌握着教育的权利,奴役着人们的时间、注意力,改变着人们的认知习惯,最终将使人们变得更加单一、浅薄。在另一部作品《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则指出儿童正面临成人化的尴尬,传媒技术的现代发展弱化了读写的隔离,儿童与成人的界限正在模糊。
曾受教于麦克卢汉,师从波兹曼,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也是目前活跃在媒介环境学圈子里的纽约学派学者,保罗·莱文森经历了互联网的从无到有。他第一次有机会将研究的视角放在第四媒体——新媒体,他的研究理论也最贴近当下。
保罗·莱文森积极地探索新媒介,对网络、手机、虚拟空间等新的技术形态都进行了考察。他热烈地拥抱技术,特别是对新技术赋予媒介的无限权利和前景表示乐观,积极地捍卫和继承麦克卢汉的思想,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同时,他综合了媒介环境学派前辈们的观点,扬弃了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吸收波兹曼关于“技术变革是浮士德的交易”的论断,综合地提出技术是把双刃剑。正如枪械可以是犯罪的工具,也可以是防御的武器;枕头虽然柔软舒适,也可用来杀人(窒息而死)。[6]因此,技术的利弊发挥关键在使用者——人的立场。莱文森认为,对于媒介人有理性挑选和谋划的能力。在技术面前,人应该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做技术的主人。
可以明显地看出,新时代的保罗·莱文森在技术面前更多了一份理性,他中性的立场也正是辩证的学术态度的体现。
五、结语:技术只是一种工具
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看待技术的角色,如何在百年的变幻间为技术与媒介的关系把脉,一代代学者孜孜不息地追问。总体来说,早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持有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用警惕的口吻告诫人们技术必然带来文明的衰落和文化的迷失;北美芝加哥学派更多地从实用角度考量,技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工具性?如何最大效率地为传媒体制服务?杜威等人热情地拥抱技术,对技术报以无限的乐观。多伦多学派的双子星从一善一恶的角度,前者创造性地提出媒介技术存在时间和空间的两种偏向,担心媒介技术将导致集权和文明的瓦解;后者开始尝试将视角放在个人感官层面考量技术的微观效应,赞叹技术是人的力量的延伸。纽约学派将多伦多学派的研究更加深入,波兹曼从恶的角度提醒大家技术会将人类变成娱乐的奴隶,同时童年越来越成人化;莱文森则相对理智地认为技术的实质不过是工具,只会带来软效果,并不必然导致或利或弊的结果,其中的关键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
从最初面对新技术的欣喜与追捧,到技术造成种种问题时的困惑与悲观,再到今天技术并没有善恶之分的认识,通过对几个学派代表学者观点的梳理,我们得出结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与其担心传播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不如思考如何更理性、更谨慎地运用技术,以规避错误,减少风险。技术到底是福音还是猛兽?传统媒体如何搭载新技术实现顺利转型?未来的传播新模式又是什么样的?彼时传播与技术两者之间又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互动?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更多的思考与探索。
[1] 孟君.从技术理性批判、技术至上到技术主导——论技术对传媒权力的影响[J].当代传播,2012(1):33-34.
[2] 本雅明(德).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3.
[3] 詹姆斯·W凯瑞(美).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112,106.
[4] 哈罗德·伊尼斯(加).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105,74.
[5] 徐雁华.传播技术学派先驱哈罗德·伊尼斯传播思想研究[D].上海大学,2012:30.
[6] 刘婷.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坐标:基于技术/媒介为视角的范式[D].广西大学,2012:35,80,98.
[7] 哈罗德·伊尼斯(加).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8] 林文刚(美).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和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3.
G206
A
1674-8883(2016)22-0065-02
郑照楠(1992—),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