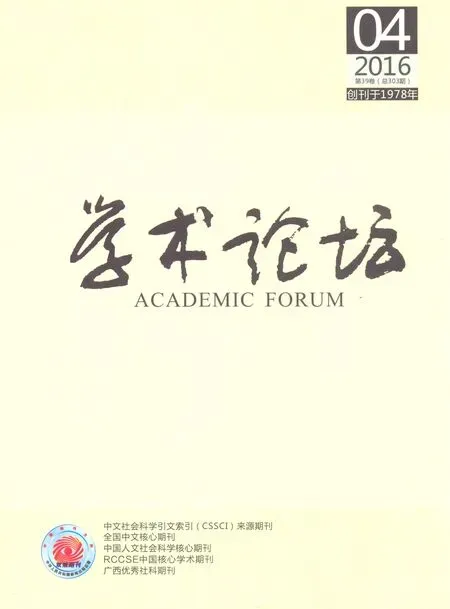我国非遗“群体”认定的缺失及日、韩经验的启示
2016-02-28赵云彩
赵云彩
我国非遗“群体”认定的缺失及日、韩经验的启示
赵云彩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主要是针对个人的认定,方式较为单一。通过梳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现状与特点,针对目前传承人认定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的客观现实,参照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较早的日本、韩国的相关经验,可以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若干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个人认定;团体认定;群体认定;人间国宝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是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呼声。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颁布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1989)、《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伊斯坦布尔宣言》(2002)等文件,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最终于2003年10月17日第32届大会上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的推动下,许多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了日程。我国是较早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在此之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与保护等一系列工作全面展开,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与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切实的保障。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从已经开展的工作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在实践操作与法律保护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我国非遗保护注重个体传承人的倾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明确的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P9)从中可以看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其“非物质性”,也即非实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传统、知识或技艺。这些非物质文化需要依附于具体的人而存在,借助人的相关表演或活动来展现。其传承离不开人的参与,主要是通过口传身授进行,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依靠实物传承的可见的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保护。
对传承人重要性的认知一直贯穿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我国于2004年8月正式宣布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为了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我国不但设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设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自2007年命名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国共计有1986人获此荣誉。在国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展开了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从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过程来看,在实际的操作中,不论国家级还是地方各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也不论是何种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都是命名个人传承人,以个体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主体。
国家还通过出台法律法规,切实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2008年5月,文化部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采取政策法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保护、认定与管理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的条件。《办法》第四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2](P79-80)。
上述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进行了制度的明确,为后续法律的出台奠定了基础。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多年积累,在人们的呼声中,我国于2011年2月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第四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中,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和明确,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及相应的义务,明确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传播的态度,规定由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关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与传承人管理办法的认定条件,可以看出二者尽管表述文字稍有差别,但是在内容指向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均是针对在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有卓越技能与影响力,并能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个体传承者。这样的个体传承者被国家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国家提供的各种优先条件和实际利益,并负有传承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根据法律制度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规定,结合在实际的操作中已经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来看,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主要针对的是自然人个体,有着明显的个体倾向性,并未包含团体或集体传承人。这就是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体系并未指向群体或团体传承主体,从而也未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团体属性或群体属性。
二、传承人认定“群体性”的缺失带来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特定的人群或社区,为这些特定的人群或社区所拥有并世代传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相当数量的门类或形式是为群体所创造和拥有、通过群体传承的方式世代相传至今天的。这种被称之为‘群体传承’的传承方式,也可以借用现在时髦的话叫做‘民间记忆’或者叫‘群体记忆’。”[3](P35)这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加强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强化群体的认同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定的群体或社区的紧密联系,其传承必须依靠群体、社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中,才能体现其独特的传承价值,显现出固有的生命力。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群体属性,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的是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被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往往成为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言人。这样的做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突出的问题:
(一)因利益之争,使其他从业人员丧失积极性
对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来说,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是引发其内部竞争和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为了鼓励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积极性,会给予其一定支持和扶助。经济方面的鼓励和支持,对于依靠某项传统的技艺为生,而目前市场需求不断缩小、收入微薄的传承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能够大大刺激其传承积极性。除此之外,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者会在多方面受益。如关于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有的学者在调研中发现,代表性传承人与非代表性传承人之间就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别:“国家级的传承人项老赛因这个身份获益不少,成为政府向外宣传的重点,他打的刀价格相对也较高,而他家的刀也较为畅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成本,在一个区域中形成了市场的垄断。”[4](P465)正如这个例子所体现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中,相对于被命名为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者来说,未被命名为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者,将享受不到相应的利益,也不会得到来自社会的较多的关注。在需求市场日益萎缩的情况下,其收入也会更加艰难,从业的积极性将大大受挫,有的甚至放弃原有的技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遴选与命名往往会引起人们的竞争,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影响原有传承群体之间的和谐,最终影响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的传承和发展。
(二)脱离了传承空间,将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某一社群的文化,其存在和发展体现为既定时空下的活态形式,是特定社区、人群、传承者组成的有机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特定群体的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需要不断地在活生生的生活中汲取养分,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延续的保证。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中,许多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人,往往被动或主动地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土壤。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被要求履行一定的义务,某种程度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对外宣传展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被要求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在各种场合表演、展示,传承人往往疲于应对。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许多商业机构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参加活动,借助其社会影响力,获取商业利益,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会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并且为了迎合市场和观众需求,会对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改造,使其失去原有的形态和韵味。类似的现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是非常普遍的。长此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可能会因失去与原生土壤的血肉联系而发生异化,成为一种孤立的存在,最终走向没落。
(三)一些传承项目的集体属性明显,仅仅认定个别传承人不够客观
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说,仅仅靠个人就能够完成,如书法、篆刻等,但是对于另一些项目来说,却有着明显的集体属性,无法由单个的个体来呈现,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才能够展现其全貌。如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侗族大歌,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传承历史,是流传于我国侗族地区的一种多声部、无指挥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形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侗族大歌由人们共同演绎,展现了侗族人民热情友好、团结友爱的社会风习。在侗族大歌被人们熟知后,其展现给世人、走出国门,仍是以集体合唱的形式亮相于表演舞台。多人演绎、合声配合也就成为侗族大歌的明显表征,人们提到侗族大歌,必然想到的是其指向的特定表演群体。
类似于侗族大歌这样集体性或团体性较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常必须由众多的人配合进行演绎,在传承地区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技艺高超者众多。而每个人在集体项目的演绎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均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在技艺水平相当、作用相当的众人之中,强制选出个别的个体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无论选谁作为传承人,对于未入选的其他传承者而言,都是一种相对的不公平。而这样的做法也有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不利于这种具有集体属性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三、日本、韩国的相关经验
与中国相比,日本、韩国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较早的国家,在长期的保护实践探索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走在世界前列。
(一)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无形文化财”(无形文化遗产)概念、将无形文化遗产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保护的国家。二战后,为了复兴民族文化,日本于1950年5月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赋予文化遗产保护以切实的保障。不同于以往只注重建筑、文物等有形的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该法律首次对无形文化遗产予以同样的重视。在《文化财保护法》的规定中,明确划定了文化遗产的内容,将文化遗产的范畴和涵盖面大为扩展,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埋藏文化财、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重要文化景观等几大类,统一列为保护对象。可以看到,这些文化遗产类别中的“无形文化财”,加上“民俗文化财”中的“无形的民俗文化财”所包含的范畴,与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基本一致。
对于无形文化财,按照法律的规定实行国家指定制度。同时,由于无形文化财主要依附于人而存在的特点,法律也明确了对无形文化财持有者的指定,这是无形文化财保护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步骤。在《文化财保护法》第四章“无形文化财”中有“文部科学大臣就前项之规定在实施指定时,必须认定该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持有者或者持有团体”,以及“文部科学大臣即便在实施第1项规定所产生的指定后,当认为作为该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持有者或持有团体还有其足以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时,其无形文化财作为持有者或持有团体所有可以被追加认定”[5](P226)的条文。也就是说,日本的重要无形文化财由文部科学大臣指定,持有者的指定的范围广泛,不仅针对个人,还可以是团体。这就充分考虑到了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特征。这样一来,无形文化财不只有个人或个体一种指定方式,而是包括多种,即学界通常所说的“个项认定”“综合认定”和“持有团体认定”三种方式[6](P206)。其中,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持有者个人,一般被人们称为“人间国宝”,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非常类似。而“综合认定”与“持有团体认定”,均是对无形文化财持有团体的认定。
此外,对于“无形民俗文化财”,因民俗文化鲜明的群体属性,法律规定并不设个人认定制度,认定的持有者并非个人,而是地方公共团体。这样,日本就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无形文化财传承人的认定标准与程序。对于被指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均负有传承和普及该项无形文化财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兼顾了无形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群体性特征。这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措施,针对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的指定,操作性较强,既有利于个人性较强的项目传承,也利于集体性较强的项目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这样的措施之下,日本许多濒危的传统技艺、艺术种类重新焕发生机,走向兴盛。
(二)韩国的“人间国宝”体系
与日本一样,韩国也是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较早的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许多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关联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受到冲击,面临消失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62年韩国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部法律将文化财的范围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纪念物、民俗文化财四个部分。这样韩国与日本的做法一样,也将无形文化遗产列入文化遗产的范围进行保护,为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实行的是传承人认定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人间国宝”(LIVING HUMAN TREASURES)体系。通过传承人的“人间国宝”认定体系,韩国强化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重要性的认识,对于传承和振兴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并对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1993年,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其“人间国宝”制度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议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审核认定,韩国实行的“人间国宝”体系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建议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和地区效仿韩国建立类似的机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方面,韩国文化遗产部的文化遗产委员会通常会将在一项文化遗产保持方面拥有最高技能的人认定为“人间国宝”,这是对于个人获得的荣誉而言,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认定。而另外的情况,则是针对集体的认定,正如韩国学者所介绍的那样:“对于戏剧、仪式和其他集体性活动,因为其艺术和功能特性无法通过个体展示出来,所以这个群体就会被认定为该项文化遗产的‘人间国宝’。”①韩国学者任敦姬2015年4月3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系列学术讲座”之《人间国宝与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挑战》观点。这说明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人间国宝”的认定,同样不仅面向个人,也面向团体或集体。通过“人间国宝”体系认定的“人间国宝”,不论个人还是团体,都负有传承和发展其技艺的义务,要将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社会公开,不定期进行公开表演和展示,以便更多的公众了解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参与到保护工作的实践中来。通过这样的体系,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传承和发展。
四、对我国传承人认定制度的启示和建议
中国与日本、韩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古以来在许多领域都有着密切的交流,文化存在着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相对于已经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本、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的时间较晚,相关制度尚处于摸索阶段。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积极性,促进全社会的自觉参与,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关重要。
(一)参照日本、韩国的经验,引进“团体”或“群体”传承的概念
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现有的传承人认定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出了较大的挑战。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可以看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与一个或几个较为著名的代表性传承人联系起来,由被命名为代表性传承人的个人演绎和传承传播。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代表性传承人往往能够展示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高技艺或水准。然而我国现实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既包括个人传承色彩鲜明的项目,也包括许多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的项目。需要依靠团体或群体的合作进行演绎或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靠个人的力量显然无法完成。若只是认定个人传承人,就割裂了那些具有群体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人主体的实际联系,将“团体”或“群体”传承主体排除在外。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仅仅针对个人传承人的认定方式,并不符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现实状况。我们应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引入“团体”或“群体”传承人的概念,将团体和集体也作为传承人主体进行认定,建立多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方式。这样才能使那些具有群体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得到较好的传承。
(二)密切联系生活,重视社区群体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性知识不同,后者是由特定的个人创造的,有着明确归属权或知识产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尽管离不开一些有才能的个人的创造,但是其本质属性仍然是其群体属性。除了“团体”或“群体”传承人的概念与认定,还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一方的水土之中,其产生和传承,不是孤立的存在。就传承过程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不但需要优秀的代表性传承人,也与普通传承人的贡献密不可分。综观日本、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可以看到,其不但会考虑到团体或群体为传承主体的设定,还会充分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特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环节,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传承人的认定,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都注重调动社区群众、公众的广泛参与。通过各种政策与活动,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增强了一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也应该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群众的联系;否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完善法律制度,为传承人认定提供政策依据
从日本、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经验来看,法律的保障是极为重要的。这两个国家较早地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法律,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使得各项工作能够持续有效地展开。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工作逐步展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11年我国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和依据。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这部法律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具体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只关乎个体传承人的认定以及权益、义务等,并没有涉及团体或群体传承人的内容。可以说,法律的条文和内容其实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实际操作情况的反映,并且经过法律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现有的传承人认定制度。因此,要想改变现实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现状,必须修正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的形式,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方式及程序,创建多元的、与现实状况相一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从而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逐步完善,更好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2]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A].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3]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承人[A].王文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王晓艳,王勤美.阿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问题[A].杨正文,金艺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东亚经验”[C].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5]日本《文化财保护法》[A].康保成,等.中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较与研究[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
[6]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陈梅云]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6)04- 0120 -05
[作者简介]赵云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