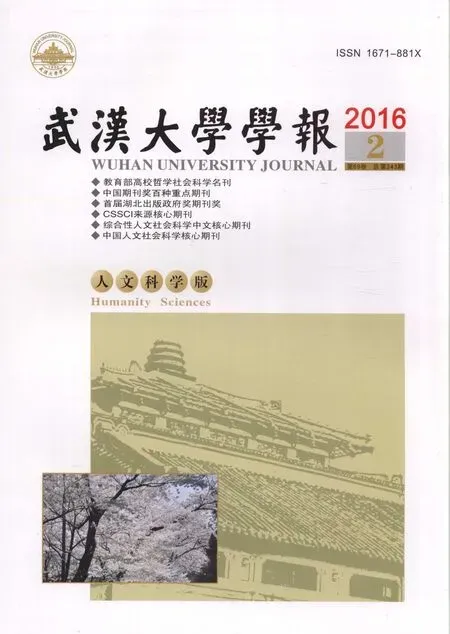农村环境: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
2016-02-20张玉林
张玉林
农村环境: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
张玉林
摘要: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特征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一道恶化并相互交织,而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复合性污染在当今世界的农村中也最为严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众多的污染主体和缺失的环境监管保护机构形成了共犯体系。如何改造碎片化而又非常低效的治理体系,接纳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已经成为重要挑战。
关键词:中国农村; 环境问题; 复合污染
一、 中国农村问题的环境维度:复合污染集大成
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以凋敝为主调的“农村问题”。但从数量规模和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农村问题像中国这般突兀。撇开20多年来城市化大跃进过程中已经消失或铲除的100多万个自然村*张玉林:《大清场: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及少数的各类明星村不论,大部分现存的中国村庄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一道恶化,而且相互交织。
从家庭破碎到社区分裂,社会生态的恶化及其伴随的混乱在近期已有较多的描述和解释,本文主要针对自然环境的恶化,并将它与社会生态的恶化、治理体系的弊端结合起来概括和分析。
按照环保部五年前的说法,在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20万个村庄的环境“迫切需要治理”*李干杰:《探索我国农村环保新道路》,载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13/c_121528816.htm,2011-06-13。。以笔者的观察和理解,迫切需要治理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有醒目的黑水存积或流淌、垃圾堆放的村庄,平原地带、大中城市郊区的大部分村庄都可归入此列。二是盘踞着各种污染工厂或养殖场的村庄,这在那些工业扩张迅猛的地区以及规模化养殖较发达的地区较为多见。三是有矿产资源开发的村庄,表现为严重的生态破坏,比如能源大省山西,它的“矿产资源型”村庄就达5266个,其中近3000个村庄(200万人)位于煤炭采空区,存在水源枯竭、土地沉陷、房屋开裂或坍塌的状况。
当然,三类现象在不少地方是叠加的,属于集大成。“20万个”也只是粗糙的推算,要准确把握农村环境,还需要注意一些宏观数据*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李干杰的文章。和经验资料:
——中国长期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消耗着世界35%左右的化肥,2014年化肥施用量达5996万吨(折纯量。是1978年的6.8倍,多于1970年代10年的用量),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用量的总和。其中冀、鲁、豫、苏、皖、鄂6省就达2523万吨,小麦大省河南则突出地达到706万吨,平均每公顷耕地施用800多公斤。
——农药的施用量没有公布,可参考的是生产量:从1978年的50多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180万吨(原药。部分出口,同时也有进口)。一些地方的个案资料显示其喷洒强度:一季水稻可达15次,果树从开花到采果约20次,青菜平均每周1次,草莓3天左右1次,苦瓜则到了“用刷子刷、用桶泡”的地步。
——作为世界最大的肉、蛋生产国(2014年肉类产量8700多万吨),对应的是15亿头/只猪牛羊和数百亿只鸡鸭鹅。它们大都不再是“家禽家畜”,而是肉蛋奶生产机器,也是造粪机器:仅猪、牛、鸡三大畜禽的粪便排放量即达27亿吨。为了让它们快速而又“可持续”地生长或生产,各种兴奋剂、消毒剂、抗生素等常规和非常规用药都是需要的。
——每年90多亿吨生活废水(平均每个行政村十几万吨)大都是直接排放,近3亿吨生活垃圾(不包括从城市运去的)大都是直接焚烧、填埋或丢弃。
总之,即便不包括工矿业的污染和破坏,仅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排放的污染物、废弃物,就已经超过水土所能容纳和自然降解的程度。按照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农业部门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到全国排放量的44%、57%和67%,以至于农业部门也认为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的“零增长”。笔者的判断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农村的环境形势可能最为严峻。有人会提到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农村也“很脏”,但那主要是可治理的“卫生”问题,而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已经较广泛地深入到土壤和地下水,其中有些地区到了一两代人之内“不可治理”的程度。
二、 结构性困境与共犯体系
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通常被归纳为点源和面源叠加、外源和内源叠加,更简单地说是点面结合、内外夹攻。当然,“源”之说并没有直指污染的主体。主体是谁呢?除了“不良企业”或企业家,还有“不道德的农民”——两亿左右的农户或相应数量的耕种者、养殖者。这意味着,在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层面上,存在着一个共犯体系。
这样说似乎令人难以接受,但却是真的。作为个体的农户,排放是分散的和有限的,但架不住面广量大,数十个农户足以造成一个村的环境恶化,数十万个村庄则造成农村整体的环境恶化。当然,与为了节约成本和追求利润而偷排、直排的企业不同,农户一般没有蓄意污染的主观动机,因为化肥和农药都是要花钱买的,农户不会故意跟自己过不去而多施滥用。在这个层面上,最终的滥用主要是缺少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造成的,同时也有明知影响很糟却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下述)。但也必须看到,随便抛却垃圾,甚至将厕所建在池边河畔而罔顾其为公共资源的人也所在多有。后者既可以解释为农民的社会文化逻辑(因感到污染解决无望而被动适应或主动开发出水体的“纳污功能”),也意味着“无公德的个人”*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载《学海》2007年第1期;阎云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有意识地加剧了污染。这里的社会—文化逻辑,与贯穿于企业污染过程的政治—经济逻辑*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载《洪范评论》第9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其实是相通的,而如果注意到许多工厂主和养殖大户本身就是壮大了的“农民”,就会发现,政治—经济逻辑是以社会—文化逻辑为基础的。
当然,理解农民的“环境不道德”,必须放到市场化、工业化、化学化了的农业结构体系中去分析。与传统的自然农业、自给自足型农业相比,现代农业体系有两个相互交织的特征。一是种植与养殖的分离,它割断了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相互依赖的内在循环,使原先的变废为宝转化成变宝为废,以至于秸秆燃烧和畜禽粪便都成了重要污染源。二是专业化、规模化必然伴随的品种单一化,又分别造成了两个被隔断了的领域的恶性循环:有机肥的减少和多种作物组合具有的抗病虫害能力的下降,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化肥和农药,这反过来造成土质的恶化和病虫害的增加;而高密度的规模化饲养,也更容易引起畜禽疾病频发。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已经形成了对化学品的路径依赖,即便察觉到恶性循环的链条和症结,也难以抽身回转。而在被锁定的格局中,他会在为“市场”生产而不顾环境和消费者的同时,种上一小块“不打药”的蔬菜供自己食用。
与生产领域的巨变相伴的是日常生活用品的化学化。由于大量供应和方便的缘故,洗涤剂和塑料袋等等已经牢固嵌入日常生活,尽管这些都是乡村的河塘土地无法消化的。在这样的结构中,即便农民形成了环境自觉,发现他原先拥抱的东西竟成了陷阱,要他冒着降低收成和收入的风险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是不可能的,因为众多的个体共同酿成的环境危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个人能解决的范围,甚至也超出了一个村庄所能解决的范围。
农民和村庄在没有意识和准备的情况下跳进了陷阱,政府却并没有及时出场。县和乡镇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招商引资,由此招来了污染企业;次要任务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由此也推动了农业内部的种养分离——再加上市场化的农资机构极力推销农药和化肥,被认为落后的“小而全”的小农经济形态的生态学优势终于败给了更强调产业化和规模效应的经济学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职能部门的环保机构大多“不在场”(直到2011年,仍然有95%以上的乡镇没有环保机构),而农业、水利、国土、建设等“有关部门”也极少会关注环境。在投入方面,国家财政更加热爱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建设主要依赖于窘困的乡镇财政。总之,人员、知识和资金(当然还有法律)都没有与污染一道下乡,农村环境治理大致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问题的呈现主要靠农民的“闹事”和闹事后媒体的介入。与此相应,迄今没有建立起关于农业农村污染的监测和管控体系。
或许正是有了公共权力的如此“低调”,农村环境污染的共犯体系才较为完整。
三、 治理危机:破碎的体系和尴尬结局
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三同时”和“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治理”等法律制度算起,治理一直是存在的,但估计环保部门也不好意思保证这套“理论体系”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以笔者之见,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在30多年来的中国可能是实施效果最差的国策。原因当然不在国策本身,而是它运行于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以营利为大的企业并不太在乎生态环境和其中的村民;负有监管职责的地方政府会为了GDP、税收乃至官员个人的寻租而闭上眼睛;处于分散状态的村民既缺少知情权和守卫乡土的意识,也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名义上代表着村庄利益的村干部,又恰恰可能是污染和破坏行为的先锋或内应。总之,市场、政府、社会同时失灵,而且是相互促进地失灵。结果是法律、政策和技术手段也随之失灵,“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偿”的综合防治体系也就经常落空。
那么,在为了应对“新农村建设”而开始重视农村环境——标志是2008年7月的全国农村环保会议,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务院召开的农村环保工作会议”——并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后,情况有什么变化吗?让我们来看看某能源大省(也是全国环境污染负荷最大的省)的两项大规模治理工程。
一项是“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中央政府要求从2003年起用三年完成,但该省到2005年才付诸实施,到2011年宣布“完工”后,覆盖的目标人口不到原计划的75%。与此相映,2007年启动的对地方煤矿沉陷区676个“采矿权灭失村”的集中治理,在实际解决了305个村之后却再无下文。结果是在中央号召“采煤沉陷区治理”十年之后,许多沉陷村仍处于求救状态;有的“新村”仍然建在采空区上,新房很快成了危房;有的村以让工程承包者开采当地的煤炭换取治理,原先未破坏的耕地成了露天采煤场。笔者在2015年8月调查获悉的四个村的状况,更是显得怪异:石村在2002年决定搬迁,并由三位副市长负责协调,但搬迁选址一直没有兑现;白村2006年纳入治理方案,但建好的高楼成了私营煤矿的“职工住宅楼”;郝村在30多年来3次搬迁,却始终离不开沉陷区,而最新分配给该村的安置房指标大多被转卖;南村在2005年纳入搬迁规划,但始终不见动静,上访村民得到的答复是“报表显示你们村已经集体搬迁”——村民推测,属于该村的安置房被大量的身份不明者顶替。
另一项是“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程”。作为2011年列入的第二批“示范省”,时间三年,计划投入15亿元,整治1200个村,村均投入125万元。但是在超出期限一年多之后的2015年5月,对三个示范点的随机调查发现,有的工程未建,有的设施建成后成为摆设,而耗资较大的设施往往是“缩水重点”,污水处理管网都未铺设到位,污水进不了收集站,仍然直接排放。在其中一个覆盖11个村的示范点,只有乡政府所在的侯村建成了污水处理站,却也是房门紧锁、门窗玻璃已被打碎*引自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2980,2015-05-20。。
确实让人无语!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无法不被看作治理危机。但问题不单单是“历史遗留问题”,有些是掀起反腐风暴后出现的新问题。按照笔者的调查所获,强力反腐固然显示了“塌方式腐败”的部分真相,但至少在中层和基层还没有触动既有的权力结构,制造了灾害和污染的政商关系或官煤关系在主导着、阻碍着灾害和污染的治理,因此高层的决断很容易遭遇肠梗阻。政出多门、彼此分离(同样是采煤沉陷区治理,领头的先是发改委,后是建设局,中间还有农委)、缺少监督的行政体系,既造成治理规划缺乏连贯性和周密,又导致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效应递减甚至改头换面。至于被治理的村庄,村干部大都在最近的十多年搬到了城里(在走访过的12个采煤沉陷村中,只有2个村的书记或主任还住在村里),平时靠遥控指挥,只在“选举”或有其他紧要事务时才回到村里;一般的青壮年农民当然也大都离去,留下的是缺少行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这也意味着,高度破碎了的农村社区,已经缺少最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重建能力。
是的,至少在环境治理的层面,结局的不堪主要是体系的破碎所造成。考虑到这种体系已经困扰着中国农村20余年,甚至将许多村庄推向了绝境,对它进行彻底改造是必需的。如果说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或“善治”并不是单靠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考核就能完成,也必须有农民的组织化参与作为保证,那么如何放开并接纳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就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实践或实验当然会带来对传统思维的“挑战”,但继续回避这种挑战,缺少主体性的“新农村建设”就只能变成换一种方式的旧农村破坏,而“美丽乡村”也只能停留于为旅游业打造的少数盆景。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2.002
●作者地址: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Email:yulinzhang@n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