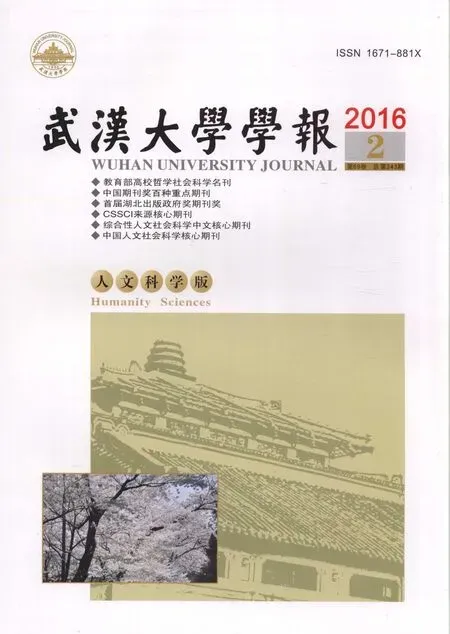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2016-02-20任红敏
任红敏
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任红敏
摘要: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幕府,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了在元代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都具有突出地位和影响的潜邸儒士群体。他们的学术主张、文化主张、文学主张,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文化政策,元代的文化政策又主导或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发展。不仅造成元代文学的雅俗分流,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而且影响了元代科举政策。元代文人更重视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从事诗文创作。幕府文人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并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成为官学。儒学与文学的全面融合,使得元代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同时,藩府文人集团是一个多种信仰并存的文人群体,多族文人互相学习和交流,构成多族作家共同创造元代文学繁荣的局面,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忽必烈等蒙古贵族产生影响,使元代宗教政策具有宽容和含弘性的特征。元代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元代文坛特征,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三教合一,释道文人化,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创作。
关键词:忽必烈潜邸; 儒士; 元代文化政策; 文学走向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幕府,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了在元代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都具有突出地位和影响的潜邸儒士群体。忽必烈潜邸的用人导向与幕府文人的学术取向,不仅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作家队伍雅俗分化与分流,也使得元代文坛以独特格局与风貌出现在文学史上。忽必烈潜邸儒士对元代政体与法制等的推动与建设,这些主要的社会重建问题影响着元代文人诗文的创作态度以及对诗文功用的理解,也影响诗文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忽必烈潜邸儒士的学术主张、文化主张、文学主张,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文化政策,元代的文化政策主导或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发展。因而,要全面认识元代文学的发展,应该了解潜邸文人如何为有元一代规划大政,研究这一文人群体及他们的创作,这对于认识元代文坛,认识元代文学,都是很有必要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元代文学,不仅仅是指被认为是元代文学代表的元曲,也不仅指传统的文学样式诗文,而是指元代文学各体式、各部分总和的整体的元代文学。本文即拟从忽必烈幕府文人与文化政策和文学走向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元代文学的发展,粗陈管见,以待引玉。
一、 忽必烈潜邸幕府用人导向与元代文人的大分化
忽必烈幕府用人主要是以经济和义理之士为主,一般不任用辞章之士。首先,经济与义理之士对学术的取向是尚实、尚用,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政权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用人倾向和学术倾向。其次,这些藩府文人也成为在元朝政权之中独享政治权利与社会荣耀的政治精英,构成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与文化力量,他们活跃于元初政坛和文坛,影响着忽必烈统治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进而也影响了元初的文化政策,也必然要影响元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及元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以义理之士和经济之士为重,不愿以辞章之士自居。这当然以入仕文人为主,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以经济之才或义理之学示人,诗文创作依然是他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馀力为诗文”,文学创作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乐趣而已。 再者,蒙古统治者尚武轻文,他们对中原地区历代相沿的文治不了解,造成了元初北方一批词章之士地位跌落,社会地位沉沦,造成了元代文人的大分化。可以说,忽必烈潜邸用人导向造成了元代文学的雅俗分流,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元代文学之大格局由此形成。
在元代,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就已把文人分为了三类:“若以读万卷书,作三场文,占奎甲第者,世不乏人。其或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亦多有之。但于学问之馀,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也。”*钟嗣成、贾仲明:《录鬼簿新校注》,马廉校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46页。以读万卷书而科举入仕者与乐道守志而隐居岩壑者,这两类是传统文士的人生选择,他们构成了元代文学史上的雅文学作者群。入仕的文人,能借仕途实现其匡扶天下、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他们虽然是“以馀力为诗文”,但依然是雅文学作者群构成的重要部分。还有一部分即隐居岩壑者,虽然被抛出了社会主流,远离统治权利,社会地位已然是大大跌落了,没有了富与贵,但人生不一定要治国平天下才有价值,他们还有“文”,“文”就是文人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只不过他们淡化了与政治的依附关系,在动乱扰攘时代大潮的冲击之下全节远害归隐,或隐居教授,或归隐田园,或隐于山林,或隐于释老,亦或隐于市井,“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第665页。,他们依然追求的是文人生活雅趣之乐,诗酒自娱本是文人的传统,以示无意于权势富贵,也是文士风流儒雅生活的标志,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独立。
诗文创作依然是元代文学的主体部分,元代作家队伍以入仕文人和归隐山林田园之士的雅文学作家为主,他们的文学创作依然是传统诗歌和文章。元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这样评价本朝文章:“我朝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欧阳玄:《罗舜美诗序》,载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刻本。在他看来,元代是文章盛世,当时人们依然看重的是文章和诗。元代诗文别集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清人修《四库全书》,收入元人别集171种,另存目36种*参见查洪德、李军:《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页。,而现存元人诗文集起码在450种以上,散佚(含未见)425种。元代诗文数量可观,质量也相当高。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撰的61册1880卷《全元文》,收录元代3200余作者的文章35000多篇;杨镰主编68册《全元诗》,收近5000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约14万首诗篇。由此可知元代诗文作家的数量庞大,而曲家只有二百多人。元代雅俗文学的分流,仍是以雅文学为主体。
第三类“以文章为戏玩者”,是那部分具有文学素养的下层文士,绝大部分终身布衣,自称“浪子”*参见查洪德:《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 当他们从“救世行道”之士中分离出来,不再背负经世大业,形成了一个“浪子”文人群体,多投身于元杂剧的创作,俗文学作家队伍由此而形成。当然,除“浪子”文人群体之外,元代还有一部分从雅文化群体分离出来的下层士人,可称之为江湖游士群。因元前期不设科举,仕途逼仄,再加上“士失其守,反不如农工商贾之定业”(陆文圭:《吴县学田记》)*李修生:《全元文》第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7页。,为了谋生,一部分士人转向术士或相士,成为以相术谋生的江湖游士,即“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方回:《瀛奎律髓汇评》,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0页。。这部分文人在元代人数较多,据刘克庄《术者施元龙行卷》载:“挟术浪走四方者如麻粟”*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13页。。另有一部分因元代科举长期废止,要么为了生计要么为了仕进求谒干进于权贵豪门、宗教宗师或蒙古色目近侍怯薛,或游者为道,或游者为利,以诗文谋生的江湖诗人往往是“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辄数千缗、以至万缗”*方回:《瀛奎律髓汇评》,第840页。,以诗文兜售权豪势要以所得谢礼而谋求生存。从戴复古诗中:“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平生知己管夷吾,得为万贡堂前客。嘲吟有罪遭天厄,谋归未办资身策。鸡林莫有买诗人,明日烦公问蕃舶。”(《市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戴复古全集校注》,吴茂云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2页。可以看到元代下层士人献诗于达官富户以获取生活资财的情形,这也是当时江湖文人的一种普遍现象。这部分从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江湖游士群,游谒于江湖以求生存。
元初北方那些既不能入仕从政又不甘于淡泊隐居只能走入市井谋生的才子文人,进入以市民为主体的商业化文化娱乐市场,悠游于歌伎艺人之间,以从事杂剧和散曲创作为谋生之道,从而形成了元代具有相当规模的俗文学作家队伍。元散曲家赵宏显【南吕·一枝花】《行乐》写到:“十年将黄卷习,半世把红妆赡。向莺花场上走,将风月担儿拈。……醉醺醺过如李白,乐醄醄胜似陶潜。春风和气咱独占。朝云画栋,暮雨朱帘。狂朋怪友,舞妓歌姬。喜孜孜诗酒相兼,争知我愁寂寂闷似江淹。……栋梁才怎受衠钢剑?经济手难拿桑木锨。堪笑多情老双渐,江洪茶价添。丑冯魁正忺,见个年小的苏卿望风儿闪。”*张月中、王钢:《全元曲》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46页。足可见到“浪子”文人翕然而乐的生活,虽然十年苦读诗书,但半世以来肩负的却是“风月担”,行走于“莺花场”,在舞妓歌姬风月场中消遣,诗酒忘忧。他们在市井这个文化空间,不受礼法与礼教在思想上的管辖与束缚,摆脱男女之大防,创造了俗文学的辉煌,扎拉嘎说:“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参见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元杂剧的创作相当兴盛,以《全元戏曲》收录为据,则元代南戏和杂剧两种类型的作品在200种以上*参见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其成就虽然不能和明清小说抗衡,但在俗文学发展史中,在小说戏曲发展历程中,为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石。元代戏曲作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读书人群体,钟嗣成《录鬼簿》收录的“浪子”文人——元杂剧作家群,如关汉卿、郑光祖一样硕果累累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且“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有56人,一大批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在元代出现。元代戏曲作家的人数难以确计,以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所考订的元杂剧作家来看,其中有名有姓的剧作家已达百人。
元代文人选择了不同人生道路,也选择了不同的创作道路。由此,元代作家队伍分雅分俗。
二、 幕府文人与元代科举及对文学的影响
忽必烈幕府的用人导向促成了“中统儒治”时期统治者任用经济、义理之士而不用或者少用词章之士的用人政策,甚至影响了元代科举。
从相关资料看大多忽必烈幕府文人反对科举,实则他们并非反对科举,而是针对科举以辞赋文章取士的方式。忽必烈统治时期,虽然多次有臣子上书要求开科取士,但终其忽必烈一朝始终未实施科举考试。一是元统治者有自己的一套选拔和用人制度,用人重“根脚”,上层官僚一般由蒙古、色目“大根脚”子弟充任,入主中原之后,即使沿袭中原传统的利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方式,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斟酌、内化,二者幕府文人多反对以辞赋取士。忽必烈藩府重要谋臣刘秉忠,于海迷失后二年(l250)夏,向忽必烈呈上“万言策”,谈到科举选才之事,建议重经义轻辞章,他说到:“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690页。刘秉忠的态度很明确。怀卫理学家郝经上书与杨奂论学,也认为:“自佛老盛而道之用杂,文章工而到之用晦,科举立而士无自得之学,道入于无用。”*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四,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认为科举妨碍实学,坚持着“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答冯文伯书》)的观点。许衡对科举的态度,从耶律由尚为许衡所作的《考岁略》中有一段记载也可看出:
庚申,上在正位宸极,应诏北行至上都。……问科举如何,日:“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名诞,朕所不取。”*许衡:《鲁斋遗书》卷一十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忽必烈治国以实用为根本,对宋金科举考试以辞赋为主要内容的取士之法缺少好感,务实的治国策略使他认为“科举虚诞”,所以“不取”,非常认可许衡对科举的态度。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他再次上疏“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宋濂:《元史》,第2018页。。提出科举应以经学为重,而罢黜诗赋取士。许衡不赞成科举,幕府侍卫谋臣董文忠也不赞成科举,他一语道出忽必烈幕府君臣关于学术的普遍看法,是尚实、尚用。据《董文忠神道碑》记载:“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言,乌知所谓道学哉?而俗儒守亡国馀习,求售己能,欲锢其说,恐非陛下上建皇极、下修人纪之赖也。”*姚燧:《姚燧集》,查洪德编辑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30页。他不满士子赋诗赋空文,也是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他们不赞成科举的原因实则是对待经义之学与词章之学的态度,认为宋金科举所采用的诗赋取士之法不妥,士子沉吟诗词歌赋,于经邦济世毫无用处,只会玩弄文字而于事无补。他们反对词赋取士,以为词赋害理。忽必烈重视实用,他所需要的是能帮助他安邦定国的经济或义理之士,不是吟诗赋词歌功颂德的风雅文士。
忽必烈藩府文人多处于元初政治的核心,很多国策的制定经由他们之手,自然他们的治国理念和方针会影响元朝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元代至仁宗时才正式下诏恢复科举。忽必烈“中统儒治”所形成的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倾向直接影响了元代的科举制度,对此《元史》科目有明确记载: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宋濂:《元史》,第2018页。
元代的科举政策导向非常明确,整个元代没有给辞章之士提供一条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而致显达之路。这也影响了元代论学论文尚实尚用的倾向,因此,造成了元代文人对诗文创作态度的转变。如藩府理学家许衡文章风格深稳,含蓄舒缓,朴实清峻,而且颇具文采,是值得称赏的元初北方儒者之文风特色。不过,许衡一生所致力的既非天理性命之奥,也不是以词采文章流芳百世,而是儒者以实干兴邦,不尚空谈,他学术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践履”,即实践性,他所关注的就是经世致用,他认为:“学以躬行为急,而不徒事乎语言文字之间;以致用为先,而不徒极乎性命之奥。”*许衡:《鲁斋遗书》卷一十四。著意于“修齐治平之方,义利取舍之分”*许衡:《鲁斋遗书》卷一十四。。许衡认为文士空谈于治国无用,对此,他有如下说辞:
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后世以智术文才之士君国子民,此等人岂可在君长之位?纵文章如苏、黄,也服不得不识字人。有德则万人皆服,是万人共尊者。非一艺一能服其同类者也。*许衡:《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按照许衡的说法,为政以德,有德才能赢得尊重,文高者未必德高。藩府儒臣郝经也非常重视文章之“实用”,为此,针对当时文坛“事虚文而弃实用”浮华之风,写《文弊解》一文,文中强调:“事虚文而弃实用,弊已久矣。”*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郝经特别强调文章质实朴素而切实用,摒弃浮华文风,他明确提出文章必须有实际的内容:“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以实为用乃是正道,他坚决反对工巧而无用之文,认为应该:“宜嘬六经之实,尽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革虚文之弊,断作为之工,存心养性,磨厉以须天下之清。”*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元代著名文臣王恽,善于文章写作,工诗词。王恽论文和许衡、郝经二人的表述和观点非常相似,他强调有社会功用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君子所学也要致力于实用,注重文章的社会功利:“君子之学,贵乎有用。不志于用,虽曰未学可也。”(《南墉诸君会射序》)*李修生:《全元文》第6册,第151页。他认为文章以自得有用为主,必须摒弃浮艳陈烂之风,需务实尚道义,理足而后词顺,“必需道义培植其根本,问学贮蓄其穰茹,有渊源,精尚其辞体。为之不辍,务至于圆熟。以自得、有用为主,浮艳陈烂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遗安郭先生文集引》)*吴文治:《辽金元诗话全编》第1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05页。程钜夫作为馆阁文臣,凡国家“累朝实录、诏制、典册纪之金石、垂之竹帛”多出自他手,为元世祖忽必烈江南求贤,对元代文坛南北融合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他所引荐的南方文士多是能治国安邦的实干实用之才,而且他在创作理念上也认为文章必须有实用价值*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其诗文创作风格也体现了这一点,他对浮靡奢华的文风很是反感,推崇朴素平易,在《送黄济川序》中曾尖锐批评:“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文儒轻介胄,高科厌州县,清流耻钱谷,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以虞集、揭傒斯、柳贯、欧阳玄等南方文士为主的奎章阁馆阁文人群体几乎牢笼了元代诗文创作的所有大家,正值南北文风融合,即元代文人所描述大元“华夷一统”“海宇混一”的盛世时期,他们文章创作也是本着服务于现实目的,“如实反映现实的传统创作精神,以实用为旨归,注重经史意义的体现”*《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的总体特征。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元代的入仕文人不喜欢被人以文学之士看待,诗文创作只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业余爱好,一种生活享受,一种乐趣而已。如幕府谋臣刘秉忠诗文创作是“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在公乃为余事”(阎复《藏春集序》)*刘秉忠:《藏春集》卷六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宋濂,作为元末代表性的文章家,虽好著文,但如若别人把他看做美词章的文人,则勃然大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白牛生传》)*罗月霞:《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0页。以发扬圣贤之道为己任。由此,元代不再区分道学家和文章家,宋濂等修撰的《元史》将前代史书往往分开的儒林传、文苑传合二为一,名为《儒学传》:“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为《儒学传》。”*宋濂:《元史》,第4313页。
受忽必烈幕府时期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用人政策影响,元代的科举政策重经义斥词章,且元代文人以自娱自乐的态度创作诗文,论学论文尚实尚用。
三、 潜邸儒士与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文学导向
在金末元初,战乱频繁,社会严重失序、缺乏道德规范。忽必烈潜邸儒士志在救世行道,在他们的努力下,保护了大批义理之士,保存了中原文化,弘扬了传统儒学。藩府儒臣注重儒学的经世治国的功用,竭力向元代统治者推崇儒学,尚实用的蒙古文化与崇实的北方儒学终于找到契合点,这为忽必烈重视儒学、遵行汉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幕府儒士的主张和努力,使儒家思想在元代社会得以渗入与传播,从而确立了儒学在元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儒学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归功于藩府文人姚枢、许衡、窦默、郝经等人,“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黄宗羲:《宋元学案》,黄百家辑,全祖望修定,王梓材等校定,中华书局1986年,第441页。首先,促进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姚枢和杨惟中保护了名儒江汉先生赵复,并北上燕京,建太极书院,请赵复、王粹等教授生徒,从此程朱理学在北方开始系统地传播。其次,忽必烈藩府儒臣对于理学在元代的发扬光大有传播之功。姚枢、许衡和窦默三人,都曾授徒讲学,传播理学,尤其是许衡任国子祭酒,教授了一批蒙古色目与汉族子弟,他们都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姚枢和窦默曾做过太子真金的老师,他们给真金论道讲学,又是深受忽必烈信任的潜邸幕僚,这样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容易对忽必烈产生影响。还有一点,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至后来正式成为元代的官学,与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崇尚也有着密切关系,是元朝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忽必烈作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封建帝王,早期就较为全面地接受了汉文化,而且在他的幕府聚集了很多北方的学者名儒,形成忽必烈幕府儒士群体,正是忽必烈的推崇与提倡,儒家学说在元代才得以迅猛发展。
藩府儒士通过跟忽必烈接触,让忽必烈耳濡目染,逐渐熟悉文教、礼乐以及尊孔的重要性。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都曾上书忽必烈中均谈到文教、礼乐问题。藩府儒臣王鹗于至元元年(1260)建议元世祖忽必烈设立翰林学士院,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设置翰林院。张文谦和窦默于至元七年(1271),请立国子学,忽必烈遂“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宋濂:《元史》,第3697页。由于藩府文臣大力提倡文教,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之下,忽必烈发布了一些兴办学校的命令。在燕京建周子祠,苏门山立圣庙,元朝各郡各县,各路设置学校,祠庙也几乎遍及诸郡路,并选拔精通儒学的学者教授子弟,最终形成中统、至元儒学大盛的局面*参见叶爱欣:《中州文士对元代儒学的贡献》,载《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元刘敏中概述元代前期的崇儒兴学之事说:“国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户以儒籍者世复其家,民之后学者复其身。中统、至元以来,通儒硕才,并进迭出,由是罢世侯,更制度,混一区夏,臣服绝域,典章礼文之懿,罔不备具。元贞、大德,重熙累洽,自京师达于郡邑,庙学一新,弦诵之声,盈于乡井,皇风炜烨,郁郁乎治与古比隆矣。”*刘敏中:《济南路文庙加封圣号记》,载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2册影清抄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忽必烈藩府的一批儒士,特别是崇尚理学的姚枢、窦默、许衡和王恂等人为儒学在北方的兴起直接地创造了条件,他们是当时北方通晓儒学的著名学者,大力提倡文教,还身体力行,建书院讲学其间,为元初教育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
元初理学的传播,许衡影响最大。许衡曾几次出任国子监祭酒。在国子监,许衡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教授了一批蒙古色目与汉族子弟,其中有很多成为元代重要官员,如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等。不仅使儒家学说获得了极大的传播空间,增强了元代儒学教化作用,也奠定了许衡在北方学坛的地位。许衡弟子耶律有尚,深受老师许衡教育思想的影响,五次掌管“国学”,并继续推行许衡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主要以程朱理学为主。许衡清新、明朗、务实的思想对元代儒学发展影响很大,受国子监的影响,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都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
由于忽必烈藩府文人的竭力倡导和推动,使儒学在学术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随着元代前期崇儒兴学,元代科举取士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元仁宗受教于名儒李孟,既通儒术,又“妙悟释典”,他对儒学非常肯定:“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于皇庆二年(1313)开科举,仁宗称:“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宋濂:《元史》,第558页。元代科举考试内容开始以程朱理学和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这些都说明着蒙古统治者对儒学的接受。延祐初年恢复科举取士并以朱学作为其惟一考试内容,正是由于许衡等人的大力推行,程朱理学才获得了元朝统治者的认可,在元代受到尊崇,其教学内容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主体科目和参考指南。其后元文宗又于天历二年(1329)在元大都设立兴隆国家文治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帝王万机之暇读书游艺而设,也是元朝发扬推广儒学的一个标志。
随着元代儒学地位的巩固和发扬光大,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理学升为官学,沿至于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因元政府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和元代文人发扬传播,带来了儒学与文学的全面融会,使得元代文学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参见任红敏:《忽必烈幕府文人与元代教育及对文学的影响》,载《殷都学刊》2015年第2期;《略论忽必烈潜邸少数民族谋臣侍从文人群体的历史地位及贡献》,载《前沿》2011年第5期。。元初北方文人王恽早已在《遗安郭先生文集引》一文中对这种平易正大文风有过阐述:“其资之深、学之博,与夫渊源讲习,可谓有素矣。故诗文温醇典雅,曲尽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类其行己,蔼然仁义道德之馀。”*参见王恽:《秋涧集》卷四十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这种诗文风格在元中期正式形成。在元中期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下,虞集、欧阳玄等人力倡并以其创作实践促成了这种平易正大的所谓盛世文风*参见查洪德:《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1期。,进而形成元代所特有的 “气象舒徐而俨雅,文章丰博而蔓衍”“元气之充硕,以发挥一代斯文之盛者”*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曹士开汉泉漫稿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景泰本。,体现儒家人格与风范的君子文风。
四、 幕府文人构成的多元以及多种信仰并存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忽必烈潜邸文人不仅构成多元,而且信仰多元。有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刘秉恕、张文谦、宋子贞、王磐、商挺、董文炳、许国祯、赵弼等金源文士和精通儒学的汉族侍卫谋士,有阔阔、脱脱、孟速思、廉希宪等蒙古侍从文人以及西域色目谋臣,还有禅宗僧人印简大师海云、子聪(后赐名刘秉忠)、至温,太一道大师萧辅道等人。
这是一个有着多种文化、多种学术观念与宗教信仰并存与融合的群体,呈现出多元一体性特征和深远的包容性*参见任红敏:《略论忽必烈潜邸少数民族谋臣侍从文人群体的历史地位及贡献》。。由于忽必烈幕府的特殊政治地位和对元代政局与文坛的影响,藩府成员间多元文化交流活跃,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通过互相之间的冲突交流融合也对元代社会政治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体现在元代社会文化精神和元代文化学术政策的宽容与含弘,文学的多元丰富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元代文学的一些特点:
其一,多族文人互相学习和交流,构成多族作家共同创造元代文学繁荣的局面。如上所言,忽必烈藩府侍从中,虽有着蒙族或西域色目血统,他们在藩府之中与汉族文士共事,相交甚善,接触较多,逐渐熟悉了中原文化。藩府儒士王鹗、赵璧、张德辉、李德辉、姚枢、窦默、王恂等都先后奉命教授太子或蒙古贵族子弟,在藩府之中,首先涌现了一批蒙古和色目儒者,如阔阔、秃忽鲁、乃燕、脱脱等*参见任红敏:《略论忽必烈潜邸少数民族谋臣侍从文人群体的历史地位及贡献》。,畏兀儿人廉希宪,嗜好读书,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这对元代多民族文人的融合有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在元代,出现很多优秀的蒙古、色目文人,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有的甚至是很有成就的学者或文学家,在文学、儒学或者书法、绘画艺术等方面卓有建树。顾嗣立曾对这一现象有过评价:“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遁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185—1186页。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尤其如贯云石、萨都剌那样的大家,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名家,他们的出现丰富了元代文坛,这在之前文学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据统计,元代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蒙古诗人有二十余人,色目诗人约一百人*参见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7页。。他们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又据萧启庆先生统计:“蒙古、色目汉学者增加的趋势,就人数而言,前期蒙古汉学者不过十七人,占总人数(包括一人兼一门以上而致重见者)10.90%。在中、后期则持续增加,分别增至28.21%与58.97%。前期色目汉学者仅占总人数的8.15%,在中、后期分别为40%与45.19%,显然是与日俱增。就专长而言,前期大多数之蒙古及色目汉学者皆为儒学者,长于文学、艺术者甚为少见。而在中、后期擅长文学、美术之人数皆有大幅成长。”*萧启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484页。蒙古、色目学者在元代前、中、后的不同时段,从人数上,由少到多,数量上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儒学、文学艺术均有。元代有不少蒙古、色目文人中很优秀杰出的人士,诸如廉希宪、贯云石、赵世延、马祖常、廼贤、孛术鲁翀、萨都剌、郝天挺、余阙、颜宗道、瞻思、辛文房等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元人》:“元名臣,如移剌楚材(按即耶律楚材),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兀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翀,女真人也;廼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按即伯颜宗道),哈剌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勒斯仁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均是在元代事功、节义、文章等各方面非常杰出的优秀士人,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各民族文士的赞誉。且元朝疆域广阔,国家一统,国内交流规模空前,东西来往频繁,从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因而,有元一代的文化和文学,是多族士人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共同创造的。
其二,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在元代更为密切,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释道文人化,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而达到了空前,这自然不可避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
忽必烈藩府文人信仰多元: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和智迂是理学家,张文谦、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刘肃、王鹗等是传统的儒生;印简大师海云和至温是禅宗,刘秉忠也曾身披僧衣多年,更是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太一道大师萧辅道;蒙古侍从文人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等,秉承了草原民族质朴讲求实利的性格,信仰萨满教并深受儒学影响,而且能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各种宗教;西域色目文人侍从畏兀儿人的孟速思、廉希宪等人,信奉萨满教,又接受了摩尼教、祆教、景教、佛教和中原道教,其后受伊斯兰教影响;以及被忽必烈封为国师的藏传佛教八思巴。从藩府文人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现象可以看到他们对各种宗教的包容以及对各种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这一点体现了蒙古统治者所奉行的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除蒙古族原有的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祅教等各种宗教都被兼收并蓄,元代社会中的各种宗教繁荣共处,宗教多元并存局面超越历代。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推动了南北文化融合以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在元代更为密切。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文人的禅道化。一是因为元朝有兼容各种宗教的国策,元代学者几乎无人公开排佛老,二是元代文人对佛、道思想的普遍认同,如忽必烈潜邸的重要谋士刘秉忠他一直以僧人身份陪侍忽必烈左右,为忽必烈谋划军政机要,长达二十余年,深受忽必烈信任,集书生、僧人、政治家、诗人于一身,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学养深厚。南方文士顾瑛有《自赞》诗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处青山骨可埋”(顾瑛《玉山逸稿》卷四)可见对佛教的认同。可以说,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已经成为元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还有一点,释道文人化。元代宗教的繁盛,以佛、道两教为最著。由于战乱,大批旧金亡宋文人士大夫避入佛寺道观,使释、道人数急剧增长,而且元代的佛徒道士,大多都是儒士,全真道士丘处机曾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段志坚:《清和真人北游语录》,《道藏》第3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比如北方的全真道教,其著名教士大多是通经达史、喜文善赋的文士。宋亡后的南方,士人入道虽不如北方之盛,但也为数不少。郑元祐《遂昌山樵杂录》就说:“宋亡,故官并中贵往往为道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2页。而且元代的儒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儒家学者的思想中往往包含着佛教禅宗的理念和道教的某些理论,融通三教而为一。
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使得宗教意识对文学和文学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文学精神的避世与内敛,禅道情趣在他们的诗作中表现得相当普遍,无论是入仕文人或隐逸文士在诗文中都常常表述有避世的田园之趣或者追求萧散闲淡的生活旨趣。还有一点,元代文士对宗教观念的认同,使他们丢掉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千古圣训,改变了鄙视“街谈巷议”、“小说家言”的观点,不再坚持传统学术与文章守持的基本原则,比如在为释子道徒们所写的碑传塔铭等文字中,把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写进了高文大册,如宋濂,曾因其文章多为释、道所作,而遭后世学者批评:“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为浮屠氏作。自以为淹贯释典,然而学术为不纯矣。不特非孔孟之门墙,抑亦倒韩欧之门户。八大家一脉,宋景濂决其防矣。”*参见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五《史籍类》。
在元代之前或以后的各个朝代,影响文学的宗教一般都只有佛道两教,元代则不然,在元代,除了佛道两教对文学影响外,萨满教、伊斯兰教(答失蛮)、基督教(也里可温)、犹太教、摩尼教都对当时的文学发生着影响。如著名的答失蛮诗人有萨都剌,著名的也里可温诗人有马祖常,他们创作中的异质文化色彩自然和他们本人所信仰的宗教也存在某种关系。
综上所论,忽必烈潜邸幕府是一个特殊的幕府。这一文人集团呈现出多元一体性的特征,多种学术观念与信仰的并存,多元思想文化并存,多元文学观念并存。由于忽必烈潜邸幕府的特殊性,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另外一个幕府文人群体像这一幕府一样,其文化与学术倾向影响了一个朝代的文化政策从而影响了一代的文学走向。其一,忽必烈幕府多用经济之士和义理之士而辞章之士受到排斥的用人导向造成了元代文学的雅俗分流,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其二,元代学术由湮晦渐复昌明,儒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程朱理学成为元代之"官学",而且,元代统治者重实惠、实用,有元一代的政治文化政策都崇尚实用有效,元代文人强调道德与文章并重,文学和儒学相融相济,形成了元代以儒学为精神根基的诗风文风。其三,忽必烈幕府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元代宗教政策的宽容和含弘,除蒙古族原有的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袄教,都被兼收并蓄,呈现出多元一体性的特征和深远的包容性。元代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宗教多种,互相之间的冲突融合与并存使得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密切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诸如元代文学精神的避世与内敛;全真教和佛教禅宗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全真教对散曲的影响,禅学、道家哲学及道教对文学理论以及文章写作的影响,并对后世神魔小说和传奇戏曲产生了很大影响。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Mansion Shogun of Kublai and the New Trend of Literature in Yuan Dynasty
RenHongmi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At the mansion shogun that belongs to the potential emperor Kublai khan gathered a groups of scholars who eventually formed into a " Shogun Confucian scholar group " accounting a prominent status and making a deep influence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rea of Yuan dynasty.Their academic,cultural and literary positions have affected the Yuan’s generation of cultural policy,which dominated or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Yuan dynasty’s literature.Composed of diversion from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ure,not only brought a major division of literati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but the Yuan dynasty’s imperial policy as well.Scholar of Yuan dynast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ir own,pure literati mentality and reading,engaged in poetry.At the same time,Kublai Khan shogun literati group was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e beliefs,many national scholars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communication,a multi-ethnic writers created literary prosperity of Yuan dynasty and made the religious policy t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lerance and wong.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of Yuan dynasty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ture,made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i to accept religion and identity,three kinds of fusion of religion,Buddhism and Taoism scholars,which influenced the literature of Yuan dynasty.
Key words:Kublai Khan Shogun; Confucian scholars; Cultural Policy in Yuan Dynasty;literary tendency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2.019
基金项目:●2016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016-CXTD-01);河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人才计划资助项目(2014);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ZW036)
●作者地址:任红敏,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安阳455000。Email:hbdxrhm@126.com。
●责任编辑:桂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