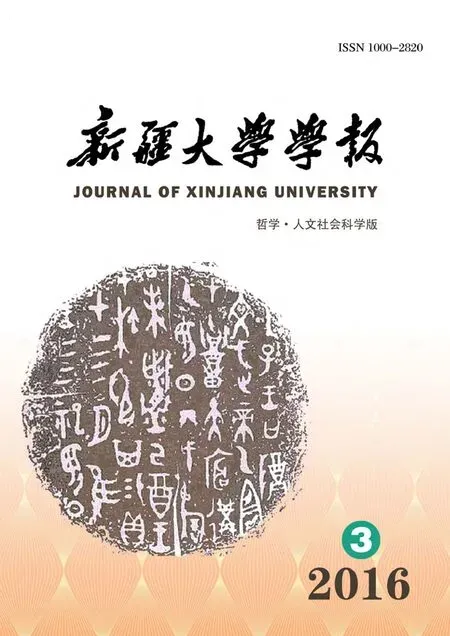论苏曼殊小说的传奇叙事*
2016-02-19仲雷
仲 雷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近年来,有些论者注意到了苏曼殊小说与“五四”新小说的历史联系,把苏曼殊视为文学现代性的最早尝试者,认为“五四”小说可以从苏曼殊的小说中寻找到更多的精神资源①钱雯在《“五四”新小说与苏曼殊资源》一文中认为,苏曼殊小说向“五四”新小说提供了情爱书写与对生命执着精神的两方面资源,成为考量“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参照,也有利于辨认“五四”新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载于《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这些论说发掘出了苏曼殊在新旧文学突变时期的“中间状态”,将其放置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加以重新审视,并以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文学新特点来定位苏曼殊的文学史意义。而在这重新定位文学新变的过渡性意义上,苏曼殊小说中所运用的传奇叙事传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的沿袭,也是文学自身发展渐变链条上循序表征的体现,可以成为评价苏曼殊小说的新视野。
一、传奇叙事:中国小说叙事的重要传统
随着20世纪西方小说叙事学的勃兴,对小说内部形式技巧和结构的研究成为学术界越来越热门的论题,而对中国小说传统叙事模式的研究也自然把西方叙事学视为借鉴的理论资源。杨义遵循“对行原理”努力寻找中西文化中存在可以沟通之处的叙事经验和理论,在以西方成果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发现“中国叙事文类的历史发展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从神话传说→史诗悲剧→罗曼司→小说的历史过程”[1]13,而是无法摆脱历史叙事的影响,“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规并进的景观”[1]15。而这种观点也可以在海外学者普实克、夏志清等人的论著中看到相似的说法。甚至,陈平原直接把“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视为影响中国小说发展的两大并行的传统模式,并将其纳入到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视野范围内,指出:“像中国古代小说一样,‘新小说’和‘五四’小说也深受‘史传’和‘诗骚’的影响,只是自有其侧重点:‘新小说’更偏于‘史传’而‘五四’小说更偏于‘诗骚’。”[2]但是,除了“史传”和“诗骚”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转变产生影响之外,中国古代小说中极为重要的传统叙事模式——传奇叙事,也参与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历史转变,体现出现代小说与传统文学潜在的承袭关系。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六朝以来的志怪传奇小说,并对志怪与传奇这两个小说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辨析,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六朝志怪书“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3]24。而发展到唐以后,“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3]44。因此,唐传奇的出现则视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带有志怪色彩的唐代传奇是文人的自觉创作,无论是叙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故传奇也可以理解为“是以情节的新异性和描写的想象性为中心的‘虚构’叙事”[4]。诚然,中国小说叙事一直深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使小说充当起弥补正史之缺的角色,但“作意好奇”的传奇叙事也是不容忽视的传统模式,它以追求虚拟的幻想世界和精神本质的浪漫特性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轨迹和艺术品质,与后来明清时期戏曲中的“传奇”以及明代的奇书小说保持着内在的精神统一。但作为中国小说重要的叙事传统之一,传奇叙事并没有随着20世纪之初的新旧文学转换而消失殆尽,现代小说的叙事资源除了可以在“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里挖掘之外,还应该在“传奇”传统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现代小说成长于欧风美雨的滋养中,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自觉地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但这种人为的自我割裂并不能真正断裂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并非是平地拔起、一蹴而就的,而是渗透在文学发展转换的内在机理上,对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也是呈现出不自觉状态,需要更为细致地考察与论证。传奇叙事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继承下来并呈现出不同的转化形式,有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历史神话传奇”,有以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为代表的“田园传奇”,有以表现上海为中心的海派小说中的“都市传奇”,有以无名氏与徐訏的小说为代表的“浪漫传奇”以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中的“革命传奇”,而且这种传奇因素还一直延伸到当代小说之中,从曲波的《林海雪原》到冯骥才的“俗事奇人小说”,皆可视为传奇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成功转型,并反过来影响着新文学发展的格局。正如有学者指出:“以反传统出身立命的新文学终究无法彻底割断传统的血脉,志怪与传奇因素的继承与滋养,使现代小说中的传奇流脉薪火相传,蔚成景色,也使现代文学免于单调而显得丰富多彩。”[5]86
处在社会文化巨大变革时代之中的苏曼殊,其创作的小说既有传统文言小说的形式,也体现出与传统文学相异的特点,如运用内心独白与心理刻画表现人物的现代手法以及充满悲剧性的抒情风格。但从整体上而言,苏曼殊的小说更多呈现的是传统小说的形态,其中传奇叙事便是苏曼殊从传统资源中借鉴而来的小说品质,而且这种传奇因素与西方文学资源融合在一起,对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以及叙事模式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苏曼殊小说成为了传奇叙事模式进行现代转型前的一种尝试形态。
二、世情与浪漫:苏曼殊小说传奇品格
以浪漫抒情风格见长、表现人的真实情感是苏曼殊小说的突出特征,这也决定了其小说中的传奇因素不是来自于奇谲的鬼怪、神话传说,而是向着生活化、世俗化甚至言情化的方向延展,形成了一种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展现庸凡世界的“世情传奇”,而苏曼殊小说中的这种“世情传奇”与后来现代小说中出现的“浪漫传奇”和“都市传奇”有着一定的相通性。
苏曼殊的小说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并与之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形成互文式的传奇叙述。从柳亚子给苏曼殊小说定义为“小说体自传”以来,学界普遍认同苏曼殊小说中的“自叙”特点,这应该与他在日本长期生活深受“私小说”表现形式的影响有关。苏曼殊的小说都带有一定的自叙性质,尤其是《断鸿零雁记》和《绛纱记》可看作是作者人生经历的缩影。苏曼殊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无论是他私生子的出身与坎坷的成长经历,还是徘徊于俗世情感与僧侣戒律之间的矛盾;也无论是其乖张的性格、纯真的品行,还是绝世的才华,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津津乐道的话题。苏曼殊小说中的人物三郎、薛瑛等,与作者的人生情感经历十分相似,都有着孤苦的身世和不幸的成长记忆,也都深深陷入了被两个痴情女子追求的三角恋爱痛苦之中,并以男子出家为僧、女子抱恨殉情为悲剧性结局,这种恨天爱海式的旷世恋情把俗尘杂恋渲染成带有传奇色彩的人间佳话。因此,在《断鸿零雁记》发表后便有人这样评说:“盖缘其人可钦,其文可赏,其事实之新奇可喜,其情节之哀艳可感也。”[6]263苏曼殊的小说大都创作于辛亥革命发生之后革命低潮期,是他在历经了人生种种磨难和革命义举之后的自我写照,其丰富而又短暂的人生阅历让小说在字里行间里折射出作者的传奇性影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苏曼殊本身的传奇经历也给小说的流通与阅读带来一定的传奇性的预期,许多人是因为苏曼殊的声望慕名而读,出于“知大师者固爱读之”的目的,试图在小说的阅读中反观苏曼殊的人生传奇和情感世界,也使后世论者通过小说里的人物和爱情悲剧为作者传奇的人生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评价,使其小说成为苏曼殊传奇品格的精神注脚。
苏曼殊小说中的传奇性也体现在传情之奇的表现上,其叙述的文字往往是对浪漫世情之奇的原态呈现。虽然苏曼殊小说留有才子佳人小说的许多痕迹,但他突破了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模式,注重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写尽了人世的悲情,写出了爱情的超凡脱俗与异奇尘绝。《断鸿零雁记》和《绛纱记》展现的不是俗世中痴男怨女的恋情,而是出家的僧人无法隔断与绝色才情的女子之间恩波怨海般的痴情;三郎、薛瑛、马玉鸾等人的出世不是看破尘寰的终极皈依,而是处在爱情两难选择中的精神逃避。这种悲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无法自觉的性格宿命。况且和尚加恋爱,其故事本身就颇具离奇的色彩,这让小说又增添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意味。苏曼殊小说中还突出了对生死的感悟,小说中殉情、自缢、病亡等情节,既渗透出哀艳的故事风格,又展示出作家在努力探寻人生难题之爱与死的哲学涵义,如陈独秀所言:“肉薄夫死与爱也各造其极。”[7]所以,苏曼殊所书写的生死之恋已经超越了爱情意义的本身价值,而是在脱欲求真中领悟形而上的思考。同时,苏曼殊笔下的恋情也有对异国之恋的展现,这主要体现在三郎与静子的情感纠葛之中。古代男女之恋多发生在亲邻兄妹之间,使得小说中的爱情描写趋于同质化,缺乏新鲜感。《断鸿零雁记》中对三郎与静子在日本所产生恋情的描绘,增大了情感表现的时空跨度,而在异国他乡与异域女子的不期爱情,在传之又奇的过程中,无形之中被披上了神秘的外纱。另外,苏曼殊善于在小说中营造朦胧哀婉的氛围,描绘特异的场景和神秘的画面,如《断鸿零雁记》中写到三郎与法忍在岸边看到数百只螃蟹在水中袭舟作怪,引得西风萧瑟,让人毛骨悚然,也颇有“奇趣”。苏曼殊还在小说中多次为人物设置了世外桃源的场景,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和自然之境进行乌托邦式的描绘,例如《天涯红泪记》中对燕影生无意间遇到的老人居住地方的描写,仿佛就是人间仙境,充满着奇幻色彩,在那里人、物、景都与众不同,已是脱离了尘世的太虚幻境。《绛纱记》里避世的隐者,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远离现代尘世,不读书识字却懂敬老怀幼、孝悌力行,不知所居何地、表为何物,却人际和睦、夜不闭户。小说中这些着墨于奇异之景与梦幻之境的表现,与文中叙述的旷世恋情相映成趣,共同呈现出一幅幅充满浪漫情怀的世情传奇画卷。
受传统小说志人志怪叙事因素的影响,苏曼殊小说中还含有一些异域人事的传奇叙事。苏曼殊塑造了一些超脱于人世恋情的人物形象,他们多是生活在桃源世外的隐士、奇人,或是嫉恶如仇的乱世怪侠。《天涯红泪记》中“神采英毅”“老态若骊龙”渔叟老人生活在非同凡常之地,不知名姓,言谈皆为剑术家言,为逃离乱世的世外奇人。《惨世界》里的明男德是一位带有侠客色彩的革命英雄,他仇视政府的腐败,为人正直,同情弱者,勇救金华贱,甚至谋划暗杀拿破仑以拯救旧世界,用他的行动实践着他充满传奇经历的人生。至于在《娑罗海滨遁迹记》中则是记叙了更为离奇的人物,他们亦神亦鬼,人首妖身,寓意明显,受到了魏晋志怪小说和《聊斋》的影响。在塑造奇人异物的同时,苏曼殊在小说中还插入了一些出奇古怪的故事情节。《焚剑记》中阿兰在行乞途中看见将军吃人腿为粮度日,惊骇不已,当询问一位老者时,老人厉声说道:“一何少见!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制,几忘之。”[6]227后阿兰到旅店求宿,恰是食人老者开的黑店,图将阿兰谋害分食。小说中这种对人食人现象的记录与纪昀的志异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载的“屠人鬻肉”之事颇有几分相似,也是作家对社会乱象的有力揭露。在苏曼殊小说里,描写殊为灵异的事件当属《绛纱记》里梦珠坐化之后为搭救蒙冤入狱的昙鸾而托梦巡抚的情节。这些行为怪诞的特异人物和让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增加了小说的传奇因素,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与思考,也体现出苏曼殊对传统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的自觉承袭。
三、婉转与逃离:取奇的叙事模式
苏曼殊的小说虽然着重于情感的抒发,却没有忽略对故事本身的讲述,如《绛纱记》把几个故事穿插、纠结在一起讲述,造成多层次的叙述者和虚拟的听众同时进入到作品叙述层面,而且结构严谨,繁而不乱,类似于复调小说的结构方式。苏曼殊小说在叙事上同样采取了一些趋向传奇因素的叙事方式,这些叙事技巧既来自于故事情节的处理方式上,又体现在小说叙事逻辑的模式上。
受“史传”传统和说书模式的影响,苏曼殊在处理故事情节方面呈多样化的方式。首先,除《断鸿零雁记》外,苏曼殊大部分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曲折,故事发展具有线条化的特点。《绛纱记》以昙鸾为第一人称叙述了四桩知识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把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作为叙事者。此外,在叙述上还将其它故事作为并行的情节线索贯穿全篇,使得这几条青年恋爱线索交织在一起,而且人物的经历又曲折复杂,既有逃难私奔、遇险搭救,又有陷害下狱、出家自缢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小说读起来饶有趣味,没有生厌之感。再如《焚剑记》中写阿兰似神诏般与独孤粲相见,与他在鬼村遇到了“起死回生”的阿大,而在她逃婚行乞中又勇救同病相怜的女子,二人误入食人的黑店,出逃后更是遇上了洪水等种种经历可谓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写尽了乱世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其次,苏曼殊把故事情节的发展放置在跳转的空间上,既展示出了人物历尽艰辛的人生轨迹,增强了人物无法逃脱命运摆布悲剧性,又加大了小说所表现的情感张力与思想深度。《断鸿零雁记》中叙述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在讲述三郎的经历时,把他放在“海云寺→波罗村→逗子驿→樱山村→小田原驿→姨家→樱山村→上海→灵隐寺→波罗村”频繁变化的空间之中,而且呈现出圆形的行动轨迹,最终又回到了原点,但已物是人非,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惨世界》《绛纱记》《焚剑记》等小说中都有类似的人物行动位移多变的设置,随着空间的扩大,许多奇人奇事便自然出现在人物的行动轨迹当中。最后,作者在安排人物行动轨迹时多运用偶遇与巧合的处理方式,在平淡的讲述中突显意外的效果,也使故事变得紧凑而离奇。传奇叙事离不开变化,“变化、转化是传奇中的基本的情节和叙事美学特征,但是,传奇中的变化往往是与巧合、机遇、偶然性、突然性、陡转联系在一起的,当把变化安排为一种预定的必然性而排除了偶然、巧合、陡转和突然性因素的时候,传奇的色彩与效果也随之减弱和淡出,传奇将失去它的传奇性。”[5]85小说里人物之间的偶遇能够直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服务于作家的传奇叙事策略。比如在《断鸿零雁记》中,三郎先后两次偶遇乳母的儿子潮儿。第一次相遇引出了三郎的身世之谜,促使其东归见母并与静子产生了恋情。当从日本回国后,三郎在荒庙里再次见到了潮儿,而此时已是时过境迁、人亡见背,预示着更大悲剧的发生。《惨世界》里明男德为救孔美丽于水火,二人终于逃出虎口,投宿一老者家中,并找到机会为之前偶遇的一村妇打抱不平,杀了恶人满周苟。巧合的是他们投宿的老者就是那村妇的叔父,老人感激明男德的恩情,帮助了明男德。虽然这种巧合有种说书的性质,但却是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既符合情节的逻辑发展,也暗合了读者好人有好报的阅读期待。
在小说的叙事逻辑上,苏曼殊往往采用“逃离”的方式来构成逻辑序列。在苏曼殊小说里,所谓的“逃离”式叙事是人物在遭受挫折或阻碍而影响其行动与情感时,采取退让、逃避的方式,并在人物的逃离与历险中,以奇异的事件反过来渲染现实压力对人物命运的巨大冲击,进一步烘托出作品的悲剧性主题。逃婚模式是苏曼殊小说中运用最多的叙事结构。在小说中,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追求都处于封建家长的压制之下,而他们对封建权威的唯一反抗就是采取出逃的策略,但伴随着逃跑途中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的出现,使得这种逃离终将以失败告终。《绛纱记》里记叙昙鸾与五姑私约乘船出逃,却在途中遇险沉船,二人从此分离。此后又衍生出昙鸾醒后偶遇世外老者和秋云,随即在海上又遭逢海盗的劫持等诸多离奇的故事情节,直到最后方知五姑病逝天国,以悲剧收场。同样,《焚剑记》中的阿兰也是被家长逼婚,她自知无力挽回,便私自出逃,一路行乞,这才引出了一系列人吃人的奇异事件和社会众多乱象,直到暴卒途中也未见到独孤粲。当然,除了小说人物的逃离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彻底的精神出逃,即出家向佛。《断鸿零雁记》里的三郎、湘僧,《绛纱记》里的梦珠、马玉鸾,《非梦记》里的燕海琴等,都是困于情爱之中无法自拔之后,以佛法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的避难所,而这种选择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可以视为奇人之举。可以说,没有人物行为轨迹的出逃经历就不会有小说中各种奇神轶事的描绘,因为“逃离”的叙事方式为作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便于记录一些惊险刺激的经历事件和新奇怪异的社会众生相,突出强调了生活的突发性、偶然性、异常性和超凡性,把个人的历险经历与社会寄托结合起来,使得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具有某种寓意,也使小说的奇与异少了些虚幻与失真,更多的则是基于现实的情感宣泄与社会想象。正如有论者指出:“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传奇叙事’,一方面有着追求‘特异’的艺术思维趣旨,同时又与‘本真’的艺术表现要求相统一。”[8]所以,小说中所传之“奇”其实是盛开在生活传奇与现实传奇土壤上的艳丽之花,并体现出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的寓言性品质。
四、结 语
“五四”后的中国小说深受西方影响,但传统的叙事资源仍然若隐若现地渗透在现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之中,并继续延伸到当代小说的叙事策略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苏曼殊:既有把他归类于鸳鸯蝴蝶派,评价不高,又有把他与五四浪漫派联系起来,肯定其艺术价值,尤其体现在与郁达夫的关系比较中。但有意思的是,郁达夫却对苏曼殊给予很低的评价,认为《断鸿零雁记》写得不自然,不写实,过于做作。而胡适的言辞则更为激烈,把《绛纱记》看作是兽性的肉欲,由几则无关的材料互相拼凑而成,而《焚剑记》更是胡说,价值不及《聊斋志异》的百分之一。但是,也应该看到苏曼殊小说中也有与五四新文学的新特点相匹配的因子,如在对爱情本真的追求与书写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执着与怀疑精神,大胆采用“自叙传”的方式专注于内心的挖掘与情感的抒发,使小说充满追求个性、崇尚自我的浪漫抒情味道,为五四小说的新变,特别是对由故事为中心到以情感为中心的叙事观念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不可否认,苏曼殊小说确实呈现模式化和类型化的特点,雷同的主题和故事构架,哀婉感伤的抒情风格,诗韵的类型式摹景与悲剧性的结局,再加上其文言小说形式等因素,都难免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学建设者攻击的靶子。作为传统叙事资源之一的传奇叙事,在苏曼殊的小说中更多地体现出与他者叙事手法相混合的状态,既有浪漫抒情的“诗骚”性特质,又有“作意好奇”的传奇性品格,形成传奇与抒情、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性张力。苏曼殊小说体现出文学转型新变过程中的“中间状态”,其表现出的桃花源式的田园传奇、忠于爱情的浪漫传奇、舍身取义的反抗传奇等,都可以在现代小说中找到相似的精神契合点,尤其小说中所展现的追求生命本真的情怀,让其传奇性因素更具有深刻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