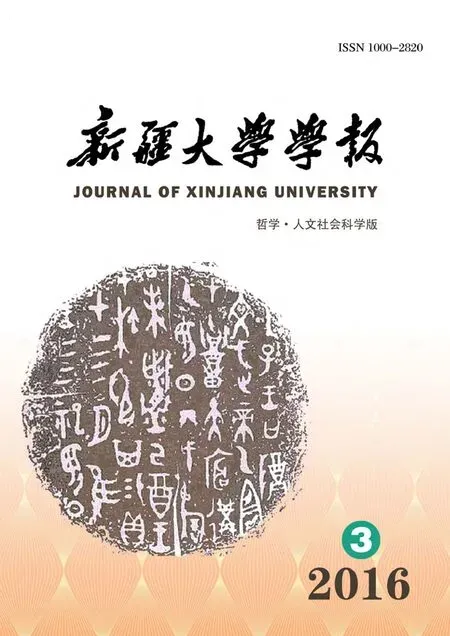试论1933—1937年伊犁土地纠纷原因及解决机制*
2016-09-29龙国仁
龙国仁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1933—1937年新疆经济的发展,史载多有肯定①从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以及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等著作来看,都肯定了这一时期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尤其在施行“农村救济”措施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牧业到1936年“大体已恢复战前的水准,则牧民不患食粮匮乏”[1]3516-3520。伴随着农牧业的恢复,土地利用虽然更为有效,但土地纠纷频发。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新疆土地之开垦——屯垦,而对新疆土地纠纷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已有的关于民国时期土地纠纷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也是以内地作为研究对象②参见把增强:《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调整与重构——以对“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土地纠纷类案件的分析为中心》,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产权变异: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纠纷之动因探研》,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契约与法院:民国时期土地交易与纠纷解决的二元嬗递》,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牛锦红:《民初土地纠纷案件判决依据解析——以〈江苏省司法汇报〉和〈司法公报〉为分析对象》,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孙琦,曹树基:《土地耕种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涉及新疆的就更少了。新疆土地纠纷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机制与内地除有一般的共性外,还有其独特性。这在《新疆历史资料(内部参考)》(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合编)中有所体现。该书根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所藏1931—1937年的档案汇编而成,共有两集,于2012年内部印刷。其中有涉及伊犁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方式的内容。本文以上述档案资料为依据,试对这一时期伊犁土地纠纷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机制,作粗略探讨。
一、土地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辛亥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落幕。这一革命浪潮也波及到新疆。杨增新窃取了伊犁起义胜利的果实,其主政下的新疆,经济发展缓慢,“杨增新主政时期的经济开发,仍然是沿着清代以来封建的农业开发为主的轨道前进,新的近代化的经济开发因素很微弱。”[2]金树仁主政新疆时期,新疆因长年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百废待举。面对这种情境,盛世才不得不制定和施行恢复经济的方案和措施。伊犁土地纠纷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土地纠纷指有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权利的争执。”[3]土地纠纷的类型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类型结果。按时间划分,可分为历史遗留和现实土地纠纷;按空间划分,可分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土地纠纷;按行业划分,可分为农业土地纠纷、牧业土地纠纷以及相互之间的土地纠纷等。在当时的伊犁社会中,存在着上述诸类型的土地纠纷。下文将对土地纠纷产生的具体原因,试作分析。
首先,农民之间发生的地亩之争。这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战乱平息后逃难农民返村时原有耕地被他人占据所造成的土地纠纷。战乱平息后,盛世才即着手安置流民,解送避难农民有序返乡。但在返乡后,难民的原有耕地被他人占据。这类纠纷在当时较为频发。以下两例即是这种情况:
伊宁玉曲温乡约马成得、马长明,五十户长暨众户民等,恳恩赏还原业,安属生计事。情因户民等,在玉曲温南滩新户务农,耕种四十余年,自伊逆匪变乱,焚杀掠夺,将民等抢掠一空,四壁如洗,民等携老扶弱,各逃性命,饥饿寒苦,寔是悲伤。于二十四年,蒙新政府宽恩厚德,众难民各回原籍,承领自业。据户民等,于二十四年移回玉曲温南滩难民四十四家,蒙逆产委员会调查,安属难民,十家基业不能归还自耕[4]397。
由喀什来伊第四批难民马黑牙、闫恒杰、闫中才、马有福、尕马、罗荣贵、马忠孝等,恳求赏还原业地亩房产事。据难民原在玉曲温务农,历有余年。自逆匪变乱焚杀掠夺,民等携老扶幼,各逃生命,奔走南疆。今蒙新政府宽恩厚德,解送难民,各回原籍,承领自业。难民到玉曲温……自今不能归还难民等。现时春暖耕种之时,难民不能各安生计。民等基业被他人占居(据)[4]398。
从上述两个案例中可看出,一方面,金树仁主政期间的战乱,致使生灵涂炭。据统计,“牲畜死亡损失的程度达70%—75%”、“北疆农村90%成为一片焦土,南疆的农村也有50%变为废墟”[1]3517。难民为逃乱,背井离乡。另一方面,在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解送难民返乡,各领家业,恢复生产。在难民返乡后,原有耕地常被他人占据,因而造成土地纠纷。
另一种是归化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地亩纠纷:
马木吐、牙合甫等禀称,民等在克孜勒库勒附近,置有房屋田产,已历三十余年,相安无事。今年,忽有克孜库勒归化民,无故霸占,并迫令迁移……据此,当经差传该归化乡约讯问,据云:……民等地亩,系在公家拨给我们地界以内,碍难划给[4]427。
归化民当时与原住民发生土地纠纷的情况比较多。归化军在盛世才谋取新疆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立下战功。也正因如此,盛世才害怕归化军日后威胁其统治。为除后患,盛世才于1934年秋,着手裁撤归化军。“他们由政府负责,分别被运送安置到伊犁、塔城、阿勒泰、奇台、沙湾及迪化南山拨地耕种。”“安置在伊犁的约有500多户,主要在巩留县、伊宁县等地”[5]31。在政府制定的“《划拨归化人民土地章程》第六条中规定:归化人民承领之荒地应按肥瘦、生熟及引用水源之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伊宁、特克斯、塔城三区定为上等”[5]32。承领上等土地的伊犁归化军经常与原住民发生土地纠葛,这主要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历史原因,即清末民初俄罗斯人享受着免税的特权和外国侨民之优待,以及“十月革命时期流入新疆的白军和难民大多数是上层贵族、官吏和军人”[5]17-18。这种特权和优待会形成一种惯性并加以延续。现实原因,即归化军为盛世才上台立下功劳,且当时苏联为世界强国,是盛世才治理新疆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这一现实是引发伊犁土地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牧民之间的牧场纠纷。由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草场归属争议与草场分配不均而引发草场纠纷。
如哈萨克族与柯尔克孜族之间的草场之争:
近年来,职等提倡扩大春耕,始多在各本牧春冬窝,播种旱田,间有耕地发生词讼者,亦经随到随结……原因伊区各牧草场向无一定界址,又无正式管业契约,每遇各族争占草场案件,处理颇形困难等[6]958-964。
再如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之间的草场之争:
蒙古牧民由前乾隆年间迁移此地,居住至今二百数十年,安居牧业……修筑房屋,迁家居住,牧放牲畜……上年,哈萨克民向职游牧,月出租金租借地点,牧放牲畜,至今将草场租金不给,反而越界霸占草场,私自筑房屋居住[4]395。
从以上两起案例中可以看出:一方面,草场归属争议。伊犁牧民在一年中要转场数次,游牧范围较大,逐水草而居。水草的枯荣与气候、季节密切相关,因而同一处草场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年份的长势和枯荣情况大不相同。如果遇上气候恶劣之年,对水草的争夺就事关生计。这时“往往因牧地水草,发生激烈之争执,强者既占良美之水草牧场,弱者则到处漂流”[7]。如尼勒克县城西北处的草场,在1877—1905年,原为哈萨克却鲁部落所属,1905年该部落被清廷谴往霍城县,1912年,该部落由霍城县返回,牧场已被蒙古族牧户占有,因而有着纷争[8]。牧区之间的土地纠纷大多有历史遗留问题,由于牧场归属权不断变化,导致各牧场之间界址不清而产生持久的争执。另一方面,草场分配不均。哈萨克族占有的牧场十分有限,“在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的牧地仍然主要须向蒙古封建主租用”[9]294,他们“只能借牧而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牧场”[10]。为了生存需要,牧场之争不可避免。因此,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草场归属争议与草场分配不均,都会造成土地使用权和归属权的争议与纠纷。
再次,农民与牧民之间发生的土地纠纷。如霍城城北山山口黄土台之争:
霍城城北山,山口左右,有黄土台数十里,无论何族人民均可在台上犁种旱田,已历二十余年,并无异议……不料,昨据北山苏完哈萨克千户长阿米拉、百户长坎吉等对众声言:现在,我部下人口过重,要求司令将旱田山划归我们耕种,业蒙允准。本年起,山外人民不得再来旱田山犁种旱田,违者送司令核办等语。查:……该千户长今以少数人民欲占若大之旱田山,藉图租佃渔利。彼等存心若此,不免大乖督办民众联合之本意,并且种旱田之家,各有界址,不能紊乱。每年加工生地犁熟,亦非容易也[4]278。
以上案例中的线索表明:一是人口增长激化人地矛盾,进而引发土地纠纷。一方面,伊犁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但毕竟面积有限。在历史上伊犁长期以畜牧业为主,游牧生产要占据大量土地,这使原本不宽裕的农业用地,更加捉襟见肘。尽管伊犁耕地面积“1933年计165万市亩……1937年则增加到300万市亩”[1]3581,但耕地有熟地和荒地之分。新增加的耕地主要属于荒地,如此一来,熟地的稀缺性就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伊犁人口的快速增长。以伊宁县和绥定县为例:伊宁(宁远)县1902年为2.5万人左右,1928年增长到12.7万人,再到1944年约为15万人;绥定县1902年为1.1万人左右,1928年增长到2万人,再到1944年约为4.5万人[11]。新增长的人口中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这种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关系在当时新疆的其它地区也有所体现,比如哈密。哈密事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土地与人口之间矛盾的激化[12]。二是清代以来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农业、牧业比重,使得农业与牧业相接的边缘区域更容易发生土地纠纷。民国时期,“游牧民族在原有牧地上也进行了农业生产”[9]108。哈萨克族本是以游牧为业,但迫于生计等原因,部分牧民开始转向农业。还有传统上以游牧为业的“一部分吉尔吉斯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13]。总之,由牧民转向农民所发生的身份转变,是产生土地纠纷的另一原因。
二、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
针对日常发生的土地纠纷,伊犁地方形成了解决纠纷的有效机制。这一机制内在地包含了民间和官方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从纠纷避免到纠纷调解、纠纷判决的解决机制。
一是纠纷避免。这主要根据民间契约。如下是卖地契约:
立卖田地文约人:库尔□、□□□兄弟二人,因为不便于将自己西八栅南巷子地(宽五丈、长二十丈)卖于阿不都拉名下,永远为业。同中言明,卖价市银一千五拾两。东至小路,西靠沙摆儿地界,南至阿不都热合满墙,北至小路,四至分明。恐后无凭,立此卖约为证。中人:热米图拉、五牧儿、毛拉二里[4]1。
从这份契约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在土地权的转移与转让方面,是通过契约来确定的。这有助于明确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同时也明晰了当时买卖田地时双方所必须履行的承诺,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纠纷。契约不单纯是民间的买卖文书,它也为官方所认可。在进行契约买卖时,政府是按“买价一两征银九分”的税率进行契税征收。如伊宁县于1934年11月征得契税总额为“银六万四千九百八十九两”[4]43。因此,契约是民间流行的、官方认可的文书。它在避免土地纠纷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纠纷调解。如果土地契约丢失、失效或仅凭地契不足以化解土地纠纷时,人们通常求助于本族或本地之乡约或千百户长,进行内部调解以息纠纷。如下案例说明千百户长在基层社会中调解土地纠纷的作用。
查伊犁哈萨克人民,向归屯垦使节制,所有诉讼案件均由各该千百户长人等,自行受理,随时讯断,相安无事,为年颇久。乃近来,特克斯辖境(阿勒班游牧六个千户长、黑宰两个千户长、柯尔格斯一个千户长)所属哈萨克民,不论何事,均问职局起诉,非偷牛盗马,即账债细故,很不重要。每日竟有十数件之多。若一一受理,恐终日讯判案件,无暇顾及行政……而公家委放千百户长,专为管民,若不理民事,未免等于虚设[4]338。
上述案例为特克斯设局后,先前由各该千百户长受理的民事权收归官府,但官府应接不暇。乡约或千百户长是清代民国时期新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管理者。
自废除伯克制以乡约取代后,新疆的乡约制逐渐普遍推行。1934年,盛世才颁布《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对全疆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改革,废除乡约制度,推行区村制。但这一章程在当时伊犁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农村社会基层仍是乡约制为主。游牧社会也有乡约,但其生活方式游居不定,所以基层管理相应的还设有千百户长,其职责与乡约相近。乡约的职责很多,民国时期的乡约职权还一度得到加强。如“对于农民之间发生的争执,财物之间的纷争,都由乡约协调双方来解决问题”[14]。千百户长的职权与乡约大致相当,基层游牧社会一般案件均由各该千百户长自行受理。再加上,伊犁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乡约或千百户长的基层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总之,在基层农牧社会产生的包括土地纠纷在内的民事纠纷,都先由乡约或千百户长来调停处理。而这种处理方式常以习惯或习俗为准,并无法律效力。
三是纠纷判决。这主要依赖于政府相关行政和司法机构的权力来进行。如下例中所示:
(伊宁县)原曲戎户民闫忠林禀称,该民祖居曲戎地方,置有水地一份,水磨两处,并托乎的圩子水地两份。因逃难出外,被附近侨居之归化人民一并占去。虽屡向当地官吏起诉追究,该归化人藐法违抗,仍然霸占不退。恳请追还,以惟生活等情。查该民所称□□如果属实,自应由伊犁行政长查明追还[4]963。
尽管契约习惯在伊犁基层社会中对解决土地纠纷占有重要地位,但不履行契约以及要求判决契约无效的情况也存在。订约各方都维护自己在田地买卖契文中所规定的权利,但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土地纠纷。当纠纷在各方所立契约内无法解决时,以及本族或本地乡约或千百户长内部调解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就得依赖当地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以强制性手段进行裁决。
为通令遵照事案:据伊犁地方法院院长彭会嘉呈报,该院已于本月十二日正式成立。除将审理词讼阶级明白规定另文布告周知外,自兹以往所有伊犁区各县人民之刑诉讼案件,应照此次规定办理[4]450-451。
上面是伊犁地方法院成立的通知。以1936年年底为划分,之前的纠纷由各行政公署处理,之后的则由新成立的伊犁地方法院负责审理。
查前按该员(富春——引者注)呈控孝林侵夺地亩一案,当经令行伊宁县彻底查核办理……该孝林坚不承认□,经该县函送法院依法办理……该孝林即便遵照将地退还富春耕种,以便结案。倘再执迷不悟,造起争端,即将现职取消,另委他人,并以法律裁判,决不姑宽[4]186。
呈为呈覆事案:奉钧署训令,饬将尼牙斯与巴海缠讼一案,查明判结,以清轇轕等。因奉此查此案前,在玉、张两前任任内,即已互相控告,缠讼不休,事经两年,未能断结。县长遵即差传该尼牙斯、巴海到案讯问,仍然各执一词,无法判断。遂即调阅地契,该尼牙斯确系由阿布尔拉合满手,价买而来,既有契又有凭,又有乡约为证。该巴海人证、物证完全无有,信口雌黄,一味争执。当经饬令,腾出房屋,交还尼牙斯管,业以资了结。而该巴海估抗不遵,任意狡展,实属横蛮已极,当即暂行管押,以儆刁顽。惟查地方法院现已成立,关于司法案件均应由该院审理。既涉司法范围,除咨请地方法院审判断结外,理合具文,呈请鉴核,示遵施行[4]610。
上面两例案件,都是由法院依法所作出的关于土地纠纷的强制性判决。由于民间有土地纠纷避免和调解机制,在契约文书约束下的很多纠纷往往被消除于萌芽状态。当然有时会遭遇地方豪强或横蛮之人不服宗族、乡约管束,或者超越了宗族、乡约的职能范围,民间土地纠纷才会上呈至政府和法院以求得裁断。即使土地纠纷仍然发生,规约可作为调解纠纷的依据。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政府和法院在处理具体土地纠纷上的压力,也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以下为土地纠纷的解决机制示意图:

三、结 语
第一,1933—1937年,伊犁因土地使用权和归属权问题而频繁引发土地纠纷,且类型多样。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农业类、牧业类及农牧间类的土地纠纷。农业类的土地纠纷,一是战后农民返村,其原地亩被他人占据而引发的土地纠纷;二是归化民与本地原住居民之间的土地纠纷。牧业类的土地纠纷,主要与草场有关,其原因是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草场归属争议与草场分配不均。农牧间类的土地纠纷,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人地矛盾,以及牧民逐渐转向农民所发生的身份转变。
第二,从避免产生纠纷到纠纷调解,直至对纠纷进行判决,这一过程构成了从民间到官方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纠纷避免依赖于民间的习惯性办法,即订立契约、划定界址。当立约各方对契约有异议或契约失去效力时,乡约或千百户长便承担起调停人的角色,将对土地纠纷进行调解。如若调解无效,则可以上诉至政府和法院,寻求以强制性和权威性的判决作为解决土地纠纷的终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