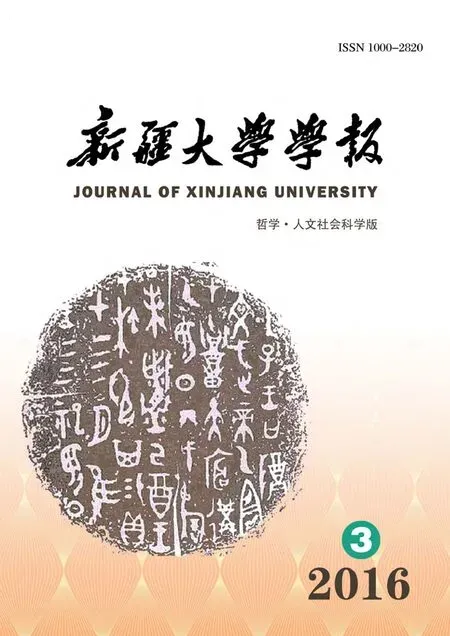论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
2016-02-19和谈
和 谈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唐末五代时期,契丹在我国北方兴起,国祚209年(不包括北辽与西辽),与北宋几乎相始终,其典章文物取自石晋,儒、释大行其道,文字则兼用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其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仍不可忽而略之。故《辽史》专立《文学传》,序其缘由曰:“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1]1445
辽代文学的分类,如果按照创作所用文字来分,可分为汉语文学和契丹语文学;如果按照创作主体的族属来分,则可分为汉人文学与契丹人文学。辽代汉人文学成就远远不及北宋文士,又无特殊之处,故置而不论;契丹语文学亡佚较多,目前能解读的契丹大小字不仅少,而且还有若干争议,难于着手;唯有契丹人用汉语所作诗文特异挺拔,令世人侧目,故可专门着墨进行探究。
一、契丹人如何能用汉语进行创作
能用汉语创作,其前提就是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契丹人亦不例外。早在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组织之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懂汉语、说汉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本人也会说汉语,据《辽史·韩延徽传》卷七十四载,韩延徽作为后唐使者往契丹,持节不屈,辽太祖甚怒,述律平劝谏,于是阿保机“召与语”,韩延徽所说“合上意”,于是“命参军事”[1]1231,从此大为倚重。韩延徽为汉人,长于文学,从史书记载来看,他主理朝廷仪礼制度及汉人事,大概不会说契丹话,因此,辽太祖“召与语”,与他交谈所用语言应该为汉语。辽太祖懂汉语的另一证据见于《辽史·耶律倍传》,耶律倍对太祖说祭祀当祭孔子,太祖大悦,令建孔子庙,并诏太子春秋释奠。由此可知,辽太祖对孔子十分熟悉和景仰,他对孔子崇敬的起源,就是对汉语及儒家思想的熟习。《辽史·太祖本纪》载,太祖曾亲自拜谒孔子庙,同时命皇后、皇太子拜谒寺观。而《辽会要》亦云:“上京国子监,太祖置。”[2]关于辽太祖懂汉语之事,除了《辽史》外,《旧五代史》亦有记载:“阿保机善汉语,谓(姚)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3]1831-1832
因为《辽史》的都总裁为蒙古人脱脱,没有今人所谓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所以《辽史》中的这些材料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首先,辽太祖认同自己为中国人,不祭祀佛祖而祭祀为中国人的“孔子”并亲自“谒孔子庙”,这与史书所载“辽本炎帝之后”、“辽为轩辕后”[1]949正相吻合。由此可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政权组织形式分分合合而形成的统一体,而当时的契丹政权对中华文化持认同态度,汉语普通话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语早有历史基础。其次,从皇太子耶律倍对孔子的推崇以及辽太祖对孔子的认可来看,他们对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极为熟悉,而这种熟悉和了解必定借助于对汉语的学习和掌握。
在辽代,不仅确立了孔子的地位,而且仿照唐代的制度建立了崇文馆和官学(包括国子监、府学、州学),这就使得学习汉语和儒家经典成为一种常态。汉语学习对其社会生活的影响是较为全面和巨大的,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在耶律氏统治期间,施行南北面官制,重视并任用汉人,推行汉法,仿照汉字而创制契丹大、小字,使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契丹人的汉语文学创作也从模仿阶段逐渐发展到独立写作阶段,《辽史·文学传》曰:“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1]1445辽代开科取士,皇帝亲自出题,以诗赋取进士,所以有辽一代文学渐趋兴盛。尤其是辽中期以后,在皇帝周围,也有一批契丹文学词臣,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应制诗、酬唱赠答诗,而这些文学词臣往往被皇帝“命为诗友”,其中著名者如辽圣宗的诗友萧劳古、耶律资忠、耶律国留,兴宗的诗友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萧孝忠、萧孝穆、耶律谷欲、耶律蒲鲁、耶律韩留、司空大师郎思孝,道宗的诗友耶律陈家奴、耶律良、耶律俨等。
但由于文献散佚,契丹诗文流传至今者并不多。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云:“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4]可见其传播基本限于北地,而金灭辽之后,其书籍文献亦多遭战火,故存世者极少。加上金章宗禁绝契丹文字,后人不再学习传承,故文献更遭毁弃。硕果仅存者,则保存在后人所辑的《辽诗话》《全辽诗话》《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全辽金诗》《全辽金文》中。
辽代契丹作家的汉语学习与文学创作既与中原汉人有较为显著之区别,也与传统草原部族有别。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文化性格之不同。契丹人初为游牧民族,后定居从事农耕渔猎,兼有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特征。其交游相处者既有汉人,又有女真、高句丽人,甚至还有西域“畏兀儿”人等,所用语言除汉语之外,尚有契丹语、女真语等,这种复杂的情况,均非中原汉人作家可比。从性格而言,北人率直刚烈,草原部族亦多如此。辽代契丹人虽汉化较深,但其本性如此,故其待人处事,均竭诚直言,发于诗文,亦不复有所顾虑,故诗风多豪健张扬,与中原汉人的“温柔敦厚”诗教大不相同。
其二,仕进之不同。与辽代同时的宋代汉人作家多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故科举对汉人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甚大。契丹人身处统治阶层,凡贵显者均以恩荫得官,无一通过科举入仕者(辽代曾有契丹文士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受到鞭打的惩罚),故科举对契丹人及其文学创作影响较小。
其三,教育之不同。汉人士子多究心于科举,皓首穷经,耽于经籍诗文,以修齐治平和经世致用为宗旨,而辽代契丹作家多出身贵族,无科举之压力,自幼即接受多种语言教育及艺术教育,既通多种语言,又通绘画、书法、鼓琴等艺术,以娱乐为目的,故其创作较少受经学影响,与宋代诗文多蕴含哲理之情况相异。
其四,宗族形制之不同。相对于辽代,宋代汉人家族之形制多演化为“敬宗睦族”或曰“敬宗收族”①如张剑在《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指出:“降及两宋,门阀世家庶几无存,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力量。”详见该书第76页。关于宋元之“敬宗收族”,详见刘晓的博士论文《元朝的家庭、家族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8年,第3页。,并且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族谱、祠堂与族田,而辽代契丹人则居处分散,同宗子弟各自独立,其宗祖观念较为淡薄,最终在金、元时期摇摆于蒙古化与汉化之间,湮没于民族融合之洪流,故往往缺乏家学渊源,积淀不深,虽亦出现文学家族,但与同时期的北宋文学家族(如苏轼家族)相比,则相形见绌。
二、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
契丹作家汉文化素养渐深,其中有诸多与汉人作家相同之处,但如上所述,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其创作具有不同于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汉语创作之处,故须辨而别之。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皇室首先参与并积极推动
虽然汉人皇室自秦、汉以来就有许多喜好文学并助推创作者,且其家族成员有相当数量的佳作传世,但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皇室成员来说,学习汉语已是困难,进行创作就更是难上加难。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辽代皇室成员对文学的推重与热爱可谓殊异。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多数辽代皇帝及皇室成员不仅学习汉语,而且能进行汉语创作。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辽施行南北面官制,汉族官吏所占比例较大,官府公文用契丹、汉文字,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必须兼通契丹文和汉文,久而久之,他们由需要而推动,由模拟而独创,终于形成了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文学。
辽太祖的长子、耶律楚材的八世祖耶律倍精通双语,《辽史》载其“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3]1211,还曾“作《乐田园诗》”[1]1210。《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载其通晓《左传》之事,汉使姚坤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帐中时,“其子突欲在侧,谓坤曰:‘汉使勿多谈。’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3]1831。突欲即耶律倍,能随口征引《左氏春秋》之典故,可见耶律倍汉文化水平之高。此外,《辽史拾遗》则曰:“东丹王归中国,赐姓李,名赞华,亦能为五言诗。”[5]383对于这一所赐姓名,耶律倍并不满意,他自取名为“黄居难,字乐地”,并说这是对“白居易”的模仿,“乐地”是对白居易字“乐天”的模仿。从耶律倍现存的一首五言诗来看,已能符合风雅之旨,且为契丹文与汉文合璧诗,故尤为难得。至于耶律倍翻译《阴符经》,则需要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和语言才能,大概他受后唐汉文化氛围影响较深,汉语水平有较大提升,故能完成此项工作。
辽太宗耶律德光汉语水平也很高,据《旧五代史》所载:“德光本名耀屈之,后慕中华文字,遂改焉。”[3]1832在皇后去世之后,他自己撰写文章进行哀悼,从谥号“彰德皇后”可知,他写的必定是汉语文章。后来他去弘福寺,见到父兄所布施的观音画像,也亲自写文章题于墙壁上,以表达自己的感伤之情,其文章极具感染力,以至于“读者悲之”[1]37。从施政方针来看,他也是推进契丹汉文化的开明皇帝,史书记载,他曾下诏让授与汉式官职的契丹人用汉人的礼仪,并允许他们与汉人通婚。这种情况到穆宗时有所延续,他下诏按太宗时的作法,在朝廷中用汉式礼仪,又一次用朝廷公文的形式把学习汉文化确定下来。
辽初皇室成员耶律倍所作汉文诗尚处于模拟阶段,至辽中期的圣宗才有大量的独立创作。从史料记载来看,辽圣宗十岁时就能写诗,而且还多才多艺,精通绘画、音律和射箭。关于他的汉语水平及文学才能,《契丹国志》载,圣宗亲自把白居易的讽喻诗翻译成契丹大字并让大臣诵读,“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6]。能“制曲百余首”,“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一方面说明了辽圣宗及其臣下的汉语水平确实很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语学习和汉语创作在辽中期的宫廷里已经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辽中期汉语学习和创作兴盛的局面,也得益于兴宗的推动。据《辽东行部志》载,兴宗曾因司空大师不肯赋诗而专门写了一首诗派人送去,诗题为《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7]。司空大师郎思孝果然写了两首和诗。这三首诗均用汉语创作,至今保存完整。由此可见,在当时皇帝倡导和鼓励之下,大有唐武后时群臣赋诗的势头。
辽道宗思想出入儒、释二教,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文学作品数量较多,在世时已经编成了《清宁集》。今存世诗文仅六篇(首),其余皆已亡佚。从其诗题《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可知,道宗曾与臣僚吟咏唱和,场面十分盛大。再从《题〈黄菊赋〉后》一诗可知,道宗对汉族丞相李俨的赋作十分欣赏,并费尽心思写了一首关于菊花的诗:“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8]从这首诗的艺术水平来看,已经完全可以与当时的汉族诗人相颉颃,再没有辽初模仿创作的那种稚拙了。另外,这首诗的意义还不仅在于艺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辽代君臣诗文唱和的情景。
皇室成员中,能诗文者还有平王耶律隆先、宁王耶律长没等。皇帝及皇室成员好文学,往往能聚集一批文人,从而形成文学团体,使文学创作蔚为风习。辽代皇帝多仰慕唐朝贞观、开元盛世,所以朝廷形制也多模仿唐朝,以诗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其中之一。而这种考试形制的建立,无疑会大大推动整个辽国的汉语普及进程,从而进一步促进汉语文学创作的繁荣。
2.诗文结集与家族文学的出现
辽初契丹人汉语水平不高,文学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尚不能独立结集,但此时汉语文学创作基础已渐渐牢固,积累渐多,颇有可观者。兹略举三例进行说明。
(1)耶律长没:“字和鲁堇,妃甄氏所生,世宗第三子。敏给好学,通契丹、汉字,能诗。保宁八年,夺爵,贬乌古部。赋《放鹤诗》,征还。统和元年,应太后命,赋《移芍药诗》。”[9]30
(2)耶律学古:“字乙辛隐,于越洼之庶孙。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1]1303
(3)耶律某:契丹将领。《杨文公谈苑》载,他经过旧时战斗的地方,“览其遗迹,作诗。矩记其两句云‘父子尽从蛇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9]35-36。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推断,耶律氏宗族兼通契丹字和汉字者大有人在。宁王耶律长没能作汉诗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史书记载他“应太后命”而作汉诗,这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句话证明了太后不仅会汉语,懂汉诗,而且还“命”后辈作汉诗,这就让皇族子孙们的汉诗创作成为一种基本能力。而耶律氏宗族佚名将领都能创作对仗工整的汉语格律诗,更可见当时汉语学习的普及。耶律学古工于翻译和作诗,正反映出当时契丹人有热切了解汉语文化的愿望和需要。由此可见,辽建立初期,契丹耶律氏宗族的知识分子不仅学习汉语和翻译汉语作品,而且已经开始独立进行汉语诗歌创作了。
平王耶律隆先是第一个有诗文集传世的契丹人。耶律隆先,字团隐,是东丹王耶律倍的第四个儿子。《辽史》载:“(平王)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1]1212耶律倍虽然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歌,但尚未结集。然而,在这种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子孙能作诗文者必定较多,而结集刊印也就是必然的趋势,平王《阆苑集》只是其中一例。
辽中后期契丹人创作的汉语文学作品很多,诗文结集的情况更加普遍。在耶律氏宗族中,如圣宗的《御制曲》(百余首)、道宗的《清宁集》、耶律资忠的《西亭集》、耶律庶成的《耶律庶成集》、耶律良的《庆会集》、耶律谷欲的《耶律谷欲集》、耶律孟简《耶律孟简集》等。萧氏宗族中也有结集者,如耶律观音奴“集(萧)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1]1317、萧孝穆著《宝老集》、萧韩家奴著《六义集》,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经、史、子书以及翻译作品的结集。
至辽中后期,兼通辽、汉双语且能写诗文的契丹人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众多的契丹文学家族。如皇室文学家族中的耶律倍、耶律德光、耶律隆先、耶律长没、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耶律延禧、萧观音、萧瑟瑟;耶律氏贵族家族中的耶律庶成、耶律庶箴兄弟,耶律资忠、耶律国留、耶律昭兄弟;萧氏家族中的萧劳古、萧朴父子,萧孝穆、萧孝忠兄弟等。关于皇室家族的汉语文学创作,前文已有所论述,兹不赘言。此处仅举耶律庶成一门三人的例子为证:
(1)耶律庶成:“字喜隐……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重熙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与萧韩家奴各进《四时逸乐赋》,帝嗟赏……有诗文行于世。弟庶箴。”[1]1349-1350
(2)耶律庶箴:“字陈甫,善属文……子蒲鲁……庶箴尝寄《诫谕诗》,蒲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1]1350-1351
(3)耶律蒲鲁:“字乃展。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应诏赋诗,立成以进。”[1]1351
由此可见,汉文化与汉语教育的普及,使得父子兄弟递相因袭和传承,遂使文学家族纷纷出现,而作品累积既多,则纷纷结集刊印,从而形成了契丹民族中汉语文学创作彬彬大盛的局面。
3.女性文学创作成就突出
遍查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能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女性数量极少,能用汉语进行创作者,就更是微乎其微。这一方面与缺乏史料记载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少数民族女性缺乏教育机会有关。
但在辽代,却有两位声名远播的契丹女诗人,一位是萧观音,一位是萧瑟瑟。这是值得研究者予以特别关注的现象。她们能用汉语进行创作,说明了汉语在辽代十分通行,而且汉语教育扩展至部分达官贵人家的闺阁,其教育的最高程度是能够用汉语独立创作,这在当时确实很了不起,其文化意义远比契丹男性用汉语创作重要。从史料记载来看,萧观音“幼能诵《诗》,旁及经、子”[5]376,长大后,“工诗,善谈论”[1]1205,而对于文妃萧瑟瑟的记载,则曰“善歌诗”[1]1206。由此可见,她们小时候除了学习《诗经》《易》《论语》等儒家的经典之外,还学习诸子的著作,等她们到十余岁时,就已经能“歌诗”了。这虽然属于个案,但从个案中可以推断,当时受这种汉语教育影响的女性,肯定不只她们二人。
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存的资料来看,除了萧观音和萧瑟瑟以外,契丹女性中还有能用汉语创作诗文者。《辽史·列女传》载一女子名耶律常哥,“能诗文”,当时的枢密使屡次向她求诗,“常哥遗以《回文》”[1]1472。耶律常哥没有萧观音和萧瑟瑟那样为后为妃的显赫地位,但她所受的教育并不比上述二人差。她读《通历》,知阴阳,懂政教,见得失,能品藻,且能作有较大难度的《回文诗》。据《辽艺文志》载,后人辑录有《耶律氏常哥集》,虽然诗集已佚,但由此可以证明她的诗文作品数量较多,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此,黄震云认为:“辽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女知识分子和女政治家,比起中原地区的女性教育来具有前卫性。”[10]契丹女作家能有诗集传世,可见辽代后期汉语创作之盛况,亦可见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之深。
由于懿德皇后萧观音不仅与辽道宗进行诗文唱和,而且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故被称作“女中才子”[5]376。从其现存的诗词来看,风格雄奇豪放,大胆泼辣,明显地表现出与农耕文化不同的审美特征。如著名的《伏虎林应制》诗:“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9]17从气势来看,绝不逊于刘邦的《大风歌》,当时中原男性作家的诗作都罕有其匹。至于《回心院》词,更是感情炽烈,大胆直露,毫无掩饰,所以吴梅先生评价其词“有宋人所不及者”[9]23。而“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于辽代作家中仅列其一人”[9]23,用一个契丹女性代表整个辽代的文学家,可能有故意突出其成就和地位的倾向,但如果萧观音的文学成就不高,恐怕也无人敢这样如此评价。她能够在辽代文坛上独领风骚,也确实算是名至实归。
萧瑟瑟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词,据《辽史》载,传世者有《讽谏歌》和《咏史诗》。《讽谏歌》用“兮”字句式,情词恳切,忧思深广,深得《离骚》旨趣。《咏史诗》的感情更加激切,矛头直指丞相和天祚皇帝,批评讽谏,毫不留情,是汉文诗歌中的罕见之作。正因这首诗,天祚皇帝“见而衔之”[1]1207,而枢密使(地位等同于丞相)萧奉先诬告文妃参与谋立晋王之事,天祚帝“以妃与闻,赐死”[1]1207。可见其诗作感情直露,笔锋犀利,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率直豪健的特色。
辽亡之后,契丹人的汉语创作并未戛然而止,至金代有耶律履,元代有耶律楚材、耶律铸、耶律有尚、耶律希逸、耶律希亮等人,由于他们的作品传世较多,成就也更突出,可称为契丹文学之集大成者。而究其根由,则是承其先祖余绪,为辽代文学所影响的结果。
契丹人的汉语文学创作,使中华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点得以充分体现,同时也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