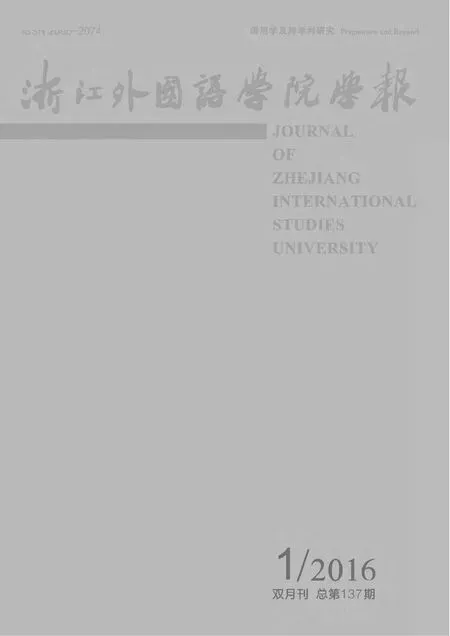京师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研究
2016-02-16张美平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京师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研究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外语学堂。作为直属于总理衙门的教学机构,同文馆有一套复杂而又独特的教学管理系统。对其教学管理系统组织结构的梳理及其利弊得失的分析,有助于对晚清外语学堂管理系统及学校组织机构变迁的了解。
京师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外语学堂
一、前言
京师同文馆(以下简称同文馆)作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外语学堂,在教学管理和组织机构方面进行了探索。在早期阶段,同文馆虽是一个教学机构,其实它更像一个衙门[1]63。同治六年(1867)天文算学馆设立以后,同文馆进行了制度改革,管理体系更趋完善,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教学组织机构,它既有纵向的层次结构,又有横向的部门结构。具体地说,同文馆的组织层次结构分为决策、执行两个层级;组织部门结构包括各外文教学馆、各科学教学馆、前馆和后馆以及各教学辅助机构等。这些构成了同文馆整体的组织架构。本文拟对同文馆管理系统中的组织层次结构及其利弊得失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晚清外语学堂管理系统及学校组织机构变迁的情形。
二、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概览
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系统分为决策和执行两个层级:决策层级包括总理衙门大臣、同文馆管理大臣和清廷总税务司兼任的监察官;执行层级则包括同文馆总教习、提调和帮提调、教习和副教习及助教等。
(一)决策层级
1.总理衙门大臣
总理衙门(又称总署、译署)是晚清主管外交、派遣驻外使节并兼管通商、关税、海防、路矿、军工、邮电、同文馆以及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由皇帝特简(按:皇帝对官员的破格选用)的大臣组成,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和章京两级职官。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成立,接管了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交往事务,由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三人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此后人数不断增加,光绪十一年(1885)曾一度达到13人。除奕、桂良、文祥以外,晚清重臣李鸿章、倭仁、翁同龢、郭嵩焘、曾纪泽、左宗棠等先后担任过此职。
《钦定大清会典》规定总理衙门的职责和议事方式为:“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制,书币聘飨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王大臣率属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每日集公廨以治庶务。”[2]1王大臣率部属“每日集公廨以治庶务”的这种全体大臣合议的决策方式,颇有现代行政组织中合议制的精神,总理衙门对于共同商酌的事项,由全体大臣联衔具奏于皇帝,或咨劄照会有关部院和人员。对于同文馆的馆务,同样是经由这一程序办理。若对该馆有所令示,则统称为“堂谕”,即表示该馆是在全体大臣隶属之下,即使在派有专管事务大臣期间,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仍经常参与馆务,甚至主持其事[3]20。虽然总理衙门大臣掌管的外交、商务、军事、经济等领域的事务非常多,但同文馆教育也是其关注的重点。他们事必躬亲,事无巨细,不仅参与同文馆的决策和大政方针制定,而且也参与接待新生、出题、监考、阅卷、巡视等非常具体的事务。翁同龢记述:“(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偕樵赴同文馆查课,与总教习款曲,提试六人,以洋译汉。”[4]2946这种处事方式虽有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善于抓主要问题之嫌,但也真切地反映出他们对同文馆的重视和对培养外语人才的渴望。
2.同文馆管理大臣
“同文馆管理大臣”一词来自《钦定大清会典》[2]2,但在奕呈奏的《请饬派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折》中,又称其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5]4437,《同文馆题名录》中则又称“同文馆专管大臣”。为方便讨论,本文一律称“同文馆管理大臣”。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同文馆管理大臣“于本衙门大臣内特简,无定员,掌通五大洲之学,以佐朝廷一声教”[2]2。因此,让堪称“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从事文治声教的事业,是奕等人奏请设立同文馆管理大臣的初衷之一,反映出总理衙门对同文馆的重视与期望。但由于同文馆之争①,招选学生学习科学的计划搁浅,徐继畲难以有所作为,只好于同治八年(1869)以老病乞休。
迄至光绪中叶,社会风气出现明显转变,对外语学习显示出进一步的认同,甚至光绪皇帝也都亲自过问同文馆的馆务状况及外国语文学习之情形。曾纪泽记述,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二十五日,他觐见光绪帝,后者“问中国通洋语者多少”。翌日,“皇上问同文馆事……问西洋语言文字之大凡”[7]4316-4317。同文馆因此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其学生人数、课程、规模等都已大为扩充。光绪十五年(1889),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考虑到“现在交涉事宜较前倍多,翻译言语文字最关紧要”,而近年“招考学生额数加添”“汉洋并习,功课较紧”“非有大臣总理其事,不足以专责成”[8]61,于是在二十余年后,再次简派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徐用仪二人为同文馆管理大臣。自徐继畲起,曾纪泽、徐用仪、张荫桓、翁同龢、崇礼、袁昶等人先后担任过同文馆管理大臣。
3.监察官
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的决策层级中,只有监察官由外籍人士担任,但“监察官”一词尚未见诸奏定章程或总理衙门的奏折。不过,自光绪五年(1879)起的历次《同文馆题名录》中都有“监察官”的记载。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文馆题名录》记载:“监察官,头品顶戴布政使衔,赫德。”[8]63监察官一职可能设于同治八年(1869)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之时,它一直由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其监察官职权包括同文馆经费的支应稽核、洋教习的任免迁调、采购器材设备等,特别是洋教习(包括总教习在内)的管理,赫德握有决定权。他还对该馆负监督之责,并参与馆务的管理。但是,法文馆教习李壁谐于1870年2月在致《北华捷报》编辑部的信中对赫德的官僚作风表达了强烈的不满[9]244-245。赫德还监督一切财政,由于他是海关总税务司,故总理衙门令拨该馆经费之船钞,亦由赫德经手。可见,赫德对同文馆的影响力之大,当不逊于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
赫德是爱尔兰波塔当(Portadown)人,于咸丰四年(1854)来华,先后在香港商务监督处、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以及粤海关担任翻译、助理及副税务司,又充港督书记官。同治二年(1863),他正式出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在主持清廷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而且其活动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至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赫德是“总理衙门的外籍总顾问,常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如推动始于1866年的半官方的斌椿使团等出使海外活动、扩大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等。他对外交政策的建议和在外交谈判中提供的帮助等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极大重视”[10]515。赫德是为数不多的受到清政府赏识的外国人之一,被清廷视为客卿,其官阶升至正一品。赫德去世后,清朝政府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纵观赫德一生,他对同文馆的贡献主要有三:第一,为同文馆选聘了合适的负责人。同文馆之争使学校陷入极大的困境,在“领袖无人,创始诸人也都不复再存奢望”[8]162的情况下,赫德接过同文馆这个烂摊子,动员刚从美国完成国际法进修回来的丁韪良出任这个“遂趋衰落”的机构负责人。第二,为同文馆选拔优质师资。同文馆甫一诞生,赫德就一直关注这一新兴的教育机构。同治五年(1866),赫德因私回国前,向总理衙门提出派遣一位使节和若干同文馆学生随他前往欧洲游历。他还希望获得授权,为同文馆招聘科学教习。总理衙门首肯了他的建议,将聘用教习的权限赋予了赫德,“延聘洋人一事一概由赫德代为招聘”[11]23。赫德为同文馆成功物色到了毕利干(化学)、李壁谐(法文)、额伯廉(英文)、欧礼斐(格致)、骆三畏(天文)、德贞(医学)、吉德(英文)等优秀教习。第三,为同文馆的运行提供强大的经费支持。丁韪良接受赫德要求其主持同文馆馆务的首要条件是他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拨出一笔经费来支持同文馆的正常运转[12]293。赫德没有食言,他“一直为同文馆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13]72。
(二)执行层级
1.总教习
同文馆成立之初,并无总教习之设。总教习一职设于同治八年(1869),由刚从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回华的丁韪良担任。对于总教习的任职条件和职责,《钦定大清会典》称,“总教习用洋人之兼通洋文洋学及熟中国语言文字者”,“设汉洋教习以分导之,立总教习以合语而董成之”[2]2。这样的说法很笼统,我们很难得知总教习的职责所在。从同文馆的运行规则来看,总教习的职责大致包含制定课程计划、督察各馆功课、聘用教习、组织编译教科书、组织招生考试、筹建教学设施以及每隔三年主持编纂反映同文馆办学状况的《同文馆题名录》等。就实际地位而言,在教务上,总教习虽居最高之职位,但如有条陈馆务情事,须由帮提调察其可行与否,会同正提调核办,要事则呈堂。
同文馆历史上,仅有丁韪良和欧礼斐两人担任过总教习一职。前者自同治八年(1869)担任斯职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退休,足历25年;后者系来自爱尔兰的同文馆原格致和英文教习,1895年接替丁韪良,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大学堂翻译科为止。限于篇幅,仅以丁韪良为例,对总教习一职在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中的位置及实际发挥的作用作简单讨论。
丁韪良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携妻子来到中国宁波,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传教生涯。作为传教士,丁韪良早年在宁波布道的直接效果并不明显。同治二年(1863),丁韪良来到北京传教,从此逐步形成“以教育和西方世俗科学为内容的自上而下的世俗化传教思想”[14]85。次年,他创办了一所主日学校,即崇实馆,教授英文、科学及中国经典。同治四年(1865),经美国公使蒲安臣和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引荐,正式出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治六年(1867),丁韪良被任命为国际法及政治经济学教习。为使自己更胜任教学,丁韪良专程返美师从著名法学家、耶鲁大学校长吴尔玺,研修国际公法。同治八年(1869),丁韪良回到中国,应赫德之邀,受聘为濒临崩溃的同文馆首任总教习。自是时起,丁韪良暂时脱离了传教活动,专注于同文馆的教育工作。他这样做,是因为相信“基督教真理可以首先通过对中国人的施教而得到传播”[15]27。从此,他在这一岗位上服务时间长达25年。丁韪良离开同文馆后,因孙家鼐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民国五年(1916)卒于北京。
丁韪良于道光三十年(1850)来华至殁,时间长达66年。除返美进修、休假约三四年以外,丁韪良基本都在中国。纵观丁韪良一生之事业,我们认为,其最具意义及不朽者有二:一是负责同文馆的日常教学管理,拯救同文馆于危难之中,使之成为清代最著名的外交官、外文教习等各类人才的培训基地之一,为清末其他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经营提供了借鉴;二是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翻译团队,组织翻译《万国公法》等30余部西学书籍,其中绝大多数系首次得以在中国传播,启动了近代中国团队有规模地译介西书的运动,对执掌中国朝政的士大夫们进行西学启蒙。但是,丁韪良是一个性格多元的人物,曾干过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功过得失系于一身”[16]139。从正面来说,他几乎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文教事业。在众多的来华传教士中,很少有人像丁韪良那样与一所外国语学堂的联系如此密切,既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又承担管理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丁韪良回国,该馆师生为之饯行并献颂词,称学堂人才辈出,赖总教习分门析类、督课有方。其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或奉差出洋,或充各埠领事,或在各省机器局、学堂当差[17]11297。西方世界对丁韪良的评价也很高。著名传教士明恩溥称:“丁韪良长期主持同文馆,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口笔译译员。”[18]2291917年4月出版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校友会季刊》发表的一篇纪念优秀校友的文章称:“有史以来至少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群体中,丁韪良是拥有最宽基座和最高塔顶的金字塔。”[19]134在19世纪末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称其为“最著名的在华美国人”[19]134-135。
2.提调、帮提调、助教
提调、帮提调、助教和总教习一样,是同文馆教学管理架构中的执行层级,即受总理衙门委托,主要负责同文馆日常的学生管理工作,直接从总理衙门的官员中选派。对于提调、帮提调的任职资格和职责,《钦定大清会典》有简略记载:“提调二人,于总办章京内派充。帮提调二人,于馆股资深章京内选充。掌经理训课及督察生徒勤惰之事,常日轮班驻馆,朝夕稽查馆事,治其文书,达其条议,督其训习,制其膏奖,纪其勤能,纠其游惰,典其锓籍。”[2]3-4
同文馆创办初期,即设满汉提调官各一人,由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内派充。但由于总办章京公务繁重,难以兼顾,一度曾委派原俄文馆助教国世春负责部分馆务。同治十年(1871)前后,整顿馆务期间,又添设帮提调二人,实际处理日常馆务。从《钦定大清会典》所载及各项规定来看,和提调一样,帮提调也掌管学生的考勤、稽查馆事、文书撰写、巡视督导、勤惰考核、成绩奖惩、膏火发放以及印书处的管理等事务,并要“常日轮班驻馆”,处理馆务。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文馆题名录》,在同文馆存续期间,共有42人担任过提调。担任提调的基本上是总理衙门大臣、道员及六部司官。其中,最初担任提调的成林、夏家镐、周家楣、吴廷芬、袁昶等五人系总理衙门大臣,说明了清廷对同文馆的重视。不过从斌椿开始(1884),不再有总理衙门大臣出任提调一职,这说明同文馆不如初期之受重视,以致同文馆的管理日渐松弛,陋弊丛生。光绪九年(1883)六月,御史陈锦上折朝廷,要求整顿同文馆并将提调苑棻池严惩,列举了同文馆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学生与教习、副教习协同作弊;学生叙补,仅靠关系;克扣膏火,以饱私囊;馆内事宜,概不管束。这些问题被陈锦概括为“考课不真”“铨补不公”“奖赏不实”“馆规不严”等四大问题,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且都与提调、帮提调大有关联[11]59-62。其实,由于体制的原因,同文馆提调官是一个很肥的缺,除课堂教学、教务诸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的事务,大都归其管。齐如山在其回忆录中详尽记述了同文馆提调肆意克扣、中饱私囊的事例[20]37。
早期同文馆曾沿用俄文馆旧例,设有助教一职。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奕制定了“酌拟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其中第三款对助教一职的职责、待遇等作出了规定:“请饬助教常川住馆以资照料也。查俄罗斯馆助教国世春,系元年奏明留充同文馆助教。该助教自留馆以后,每遇月课、季考、岁考,皆在馆照料收卷等事,并未议令值班住宿。……嗣后应饬令国世春常川在馆住宿,专司稽查三馆教习、学生出入,并随时约束苏拉,以防流弊,兼收掌该馆各项册籍。其每年俸银八十两,……由臣衙门按季给发,无庸行文户部支领。”[6]3537-3538从上述文献资料来看,助教的职责似乎在行政性事务管理方面,从事学生事务的管理,类似于今天的“学生辅导员”或“学生干事”,但权力似乎更大,因为他还可以“稽查三馆教习”。早期同文馆没有设置帮提调一职,设置助教可能是为了协助提调管理学生事务。
3.教习、副教习
同文馆的教习由三部分构成,即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总教习、教习类似于当下的正式在编教师,副教习由拔尖学生充任,协助教习开展教学工作,同时也承担教学工作,但其身份依然是学生,仍习功课,接受教习的管理。其中,总教习既是管理人员,又承担教学任务,如丁韪良是国际公法的教授,欧礼斐是英文和格致的教授。教习有汉教习和洋教习之分,汉教习负责汉文教学,先后有徐澍琳、杨亦铭等29人担任此职。同治六年(1867)以后还要负责算学教学,出任算学教习的有李善兰、席淦和王季同,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同文馆洋教习负责外国语文和各类西学课程的教学。同文馆在其存续期间,先后聘请了丁韪良、傅兰雅、毕利干等51名洋教习。《钦定大清会典》对各类教习的职责有简要介绍:“设汉洋教习以分导之,立总教习以合语而董成之。总教习用洋人之兼通洋文洋学及熟中国语言文字者,汉教习用汉人举人贡生出身者。洋教习用洋人,副教习由高足学生兼充,仍习学生功课。”[2]2
同文馆洋教习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还要译书和编写论著,以兹弥补教材之不足。以丁韪良为首的翻译团队,为世人贡献了30余部译作和论著,其中多数充作教材。虽然这些书籍中的学问,有不少在当时西方已有些陈旧过时,但对中国而言,仍属全新的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弥足珍贵。从文献记载来看,学堂兼作译书机构,虽不是同文馆首创,但从数量和质量来说,它可能是仅次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最出色的教学机构。教习译书一直是中国外语学堂的传统。例如,元代回回国子学、明代四夷馆,曾让各馆教习编纂了近似教材的各种译语,通称“华夷译语”,供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生使用。
我国自西周起一直是“官师合一”的官学体系,学校的教师都是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21]91。同文馆也沿袭这一传统。汉教习既是教师,也是官员,也就是说,具有一定资历和工作年限的教习,即可出任知县。例如,同治二年(1863)到馆的俄文馆汉教习杨亦铭、法文馆汉教习张旭升在两年的任期届满后,奕上奏要求对杨、张二人“照章奖叙,均以知县用”[6]3080。英文馆汉教习徐澍琳也照此办理,获得了知县的职位。对于洋教习,清政府也是用品级奖励的,如以三品衔(虚衔)赏总教习丁韪良,即是一例。
同文馆副教习职位介于教习和学生之间,虽兼具两者身份,但仍在学生之列,均如其他学生一样须每日按时到馆,“仍习学生功课”[2]2。违者以不到论,并扣罚膏火。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堂谕”规定:“同文馆前后馆以及副教习等,每日经提调于九、十点钟画到时有不到者,一律注不到字样,逾时不准补行画到。计日罚扣膏火。”[8]108和前后馆学生一样,他们还要参加口笔译考试。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堂谕”曾提及试署英文副教习文祐、茂连“以洋译汉试卷,均因翻译较逊,名列于后”[8]109。除笔试,还要每周参加口试,“除按月考试外,本大臣现定于每月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等日亲赴提调公所,分班接见洋汉教习,抽考副教习及前后馆生徒,面试洋汉文及各国言语,并一切技艺等项”[8]115。副教习除像普通学生那样参加学习和考试以外,还要承担教习的职责,担任后馆新生的教学,业绩突出的,还可获得奖励。例如,总教习丁韪良因试署英文副教习文祐、茂连“自试署以来,向来殷勤教授各生”,便要求销去其头上的“试”字,并加给津贴[8]109。此外,经总理衙门的同意,副教习还须协助教习的西书翻译工作。副教习汪凤藻等人就协助教习翻译了多部西学书籍。
各科基本上都设有副教习,每科通常设有一人,也有设二人及以上的。其名额似无定数,各馆人数也不相等。根据《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79),文续、那三(英文馆),席淦、汪凤藻、杜法孟、贵荣(算学馆),承霖(化学馆),巴克他讷(俄文馆)等人被任命为副教习。光绪十三年(1887)、二十二年(1896)、二十四年(1898),斌衡、贵荣、周自齐等28人任各馆副教习。就其待遇而言,不仅是学生中最高,甚至比汉教习还要高,“月给薪水十五两”[22]46,而汉教习仅有十二两(早期同文馆汉文教习仅有八两)。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介绍了副教习的职责:“同文馆的学生在外交界及领事署曾经任职一两期,现在尚在候差者,可以入馆复学。他们通常授以副教习名义,负领导一班之责,也有任为正式翻译官的。”[23]227
按照《钦定大清会典》,副教习“由高足学生兼充”[2]2。从相关文献来看,这些副教习确实是学生中之翘楚,“皆同文馆之一时俊彦”[24]185。首先,部分副教习的专业水准达到了业界的顶尖层次,如算学副教习席淦是清末继李善兰之后最著名的数学家。其次,多数副教习的外语水平相当高,已达到独立翻译专业书籍的程度。例如,算学副教习汪凤藻翻译了《公法便览》《富国策》等5部法学、经济学、语言学书籍;算学副教习贵荣翻译了《俄国史略》《西学考略》等;天文副教习熙璋翻译了多部《天文合历》;化学副教习承霖、王钟祥与教习合作翻译了《化学阐原》《分化津梁》等。用当下的话语来说,这些副教习均属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再次,部分副教习其后在政界、军界、外交界、教育界等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如周自齐,担任了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后来国立清华大学的奠基人。他还先后担任过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署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等职务。
三、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的利弊得失
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是总理衙门组织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系统中大部分的构成要素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生事物,对于后来的新式学堂教学管理系统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中的大部分职位在中国教育史上系首次出现,为后来的近代新式学堂教学管理职位的设置提供了示范。例如,总教习、提调、副教习等职位为不少新式学堂所沿用。光绪八年(1882)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聘请严复担任该校总教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成立伊始,聘请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出任该校总教习。又如,同治二年(1863)成立的上海广方言馆,仿照同文馆之例,除设置教习外,还设置英文、算学、天文等副教习。著名学者、原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章梫曾任同文馆的后继京师译学馆的提调。
其次,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严密、规范,虽然层次多,但依旧可以实行垂直管理,一旦发生教学乱象,能及时干预并整顿。同文馆作为总理衙门的直属机构,享有中国传统的官学、书院、私塾所不具有的地位,由总理衙门大臣或总理衙门委派的同文馆管理大臣直接管辖。同文馆未曾设置校长一职,教学由总教习丁韪良主管,学生和行政事务由提调或帮提调主管。这样的组织架构方便总理衙门垂直管理。同文馆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直接由总理衙门进行整顿的情形。最典型的是光绪十五年(1889),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奉命整顿同文馆。经过整顿,该馆教学秩序步入正常轨道。
再次,通过设立教习职位,聘用外籍教习,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外语和西学教育。此举为其他新式学堂所仿效。中国历史上有过聘请外籍教师的先例,如明代四夷馆的外文教习大多来自外国,“此四夷馆之设,猷虑甚弘远也。当是时为馆傅者多征自外国,简吾子弟之幼颖者而受学焉”[25]15。所以,同文馆和历史上的同类机构一样,一开始就选聘外籍人士充任教习。不同的是,四夷馆的外文教习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同文馆的外文和科学教习主要来自经济文化发达的欧美国家,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学养深厚的传教士出身,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同文馆的教学质量。
最后,聘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同文馆监察官,有利于同文馆各项事业的有序开展。一是利用赫德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聘请了不少来自欧美国家的优质师资长期服务于同文馆,如被丁韪良称为“中国化学之父”的毕利干(29年)、华毕乐(25年)、欧礼斐(22年)、骆三畏(21年)等;二是通过赫德掌管的中国海关,解决了办学中最重要的要素——经费问题,使得同文馆在四十年的运行中免受经费缺乏的困扰;三是利用赫德自身是爱尔兰人的英语优势,为同文馆外语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根据文献资料,赫德经常参与同文馆的教务,如充当大考的面试官、拟定试题、带领学生查核中外条约以及开展海外语言实践等活动。
凡事都有利弊。同文馆教学管理系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其一,虽然严密、多层次的管理体制有便利同文馆顺利运行的好处,但往往也会导致职责不明,甚至产生越权插手的现象。例如,同治四年(1865),首届30名学生学习届满举行大考,总理衙门大臣、监察官、提调、中外教习等都来监场。有时,拟定试题、批卷、外语口试等本该是教习的分内之事却都由总理衙门大臣代劳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经由通晓英文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所批改决定名次的英文试卷,同是总理衙门大臣的翁同龢竟能加以变动名次先后。这些都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引起的弊端。总之,同文馆的一切馆务无论大小巨细都由总理衙门大臣会商决策,并奏请皇帝批准。这一情形往好处说是总理衙门重视教学质量建设,事必躬亲,关怀体恤教师;往坏处说是越俎代庖,不分轻重缓急,毫无近代学校管理的理念与方法。
其二,聘用外籍人士掌控同文馆,弊端也很明显。虽然总理衙门对同文馆承担管理之责,并且管得非常具体,但在涉及诸如课程标准的制定、教学内容的安排、课堂教学的组织与开展、教习的选聘等学校具体的事务时却往往不知如何下手,只能将其托付给丁韪良、赫德等人,导致同文馆对外籍教习的教学缺乏有效的监督。外籍教习可以利用其教学便利,向学生灌输与中华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甚至是污蔑中国人的内容。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中记述:“在我刚来这所译员学校任教时,我在一堂英语课上让他们阅读一本地理书,书中有段话竟将中国人描述成‘肤色肮脏的黄牛皮’。学生并没有因为这句失敬的话而感到生气。”他竟然听之任之。他还提及,教室里有一块禁止在课堂教授《圣经》的牌子,但他依然故我,从不回避跟学生谈论这一问题,还要求其他教习不要在书上看到讨论宗教问题的段落时,就跳过去不读。作为一个传教士出身的教习,他在课堂上最乐于讨论的话题就是异教徒和基督教世界的信仰问题[12]325。
综上,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系统作为近代中国有条件实行开放后诞生的新生事物,有其积极的一面,并因而成为新式学堂仿效的样本,甚至在当下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它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同文馆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不利影响。
注释:
[1]O’brien M J. The Peking College [N].The North-China Herald,1870-01-25.
[2]钦定大清会典卷一百[M]. 昆岗,等,纂修.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戊申(1908)十一月.
[3]苏精. 清季同文馆及师生[M]. 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
[4]翁同龢. 翁同龢日记 第六卷[M]. 翁万戈,编. 翁以钧,校订.台北:中西书局,2012.
[5]皇朝政典类纂卷二百三十[M]. 席欲福,沈师徐,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6]宝鋆. 筹办夷务始末[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0.
[7]曾纪泽. 曾惠敏公手写日记[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65.
[8]高时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9]Lépissier E. The Peking College [N].The North-China Herald,1870-04-04.
[10]Fairbank J K,Liu K-C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I) [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11]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2]Martin W A P.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M]. 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00.
[13]Teng Ssu-yü,Fairbank J 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14]王文兵. 丁韪良与中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5]Liu K-C.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M].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16]陈平原. 老北大的故事(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7]佚名. 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先生纪略[C]//林乐知,主编. 万国公报. 上海:墨海书局,1890.
[18]Smith A H. China and American Today [M].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07.
[19]Foster J W. An Appreication of Dr. W. A. P. Martin [J].Indiana University Alumni Quarterly. Vol. IV,No.2,April,1917.
[20]齐如山. 齐如山回忆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21]黄运红. 晚清京师新式学堂教师聘任初探——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5):91-96.
[22]同文馆题名录(第四次)[Z]. 北京: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光绪十三年(1887).
[23]Morse H B,Martin W A P. 傅任敢,译. 同文馆记 [J].教育杂志,1937,27(4):215-231.
[24]孙子和. 清代同文馆之研究[M].台北:嘉新水泥公司,1977.
[25]王宗载. 四夷馆考[M].北京:东方学会印本,甲子(1924)夏六月.
StudiesonEducationManagementSystemofthePekingT’ung-wenKuan
ZHANGMeip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ejiangShurenUniversity,Hangzhou310015,China)
As the first new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established in modern China’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the Peking T’ung-wen Kuan is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Tsungli Yamen,the foreign office of the Qing Dynasty,and has a comparatively complete set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presents quite complicated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By analyzing the T’ung-wen Kuan’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is system,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school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Peking T’ung-wen Kuan;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foreign language school
H319
A
2095-2074(2016)01-0044-08
2015-12-24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234YB)
张美平(1964-),男,浙江遂昌人,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