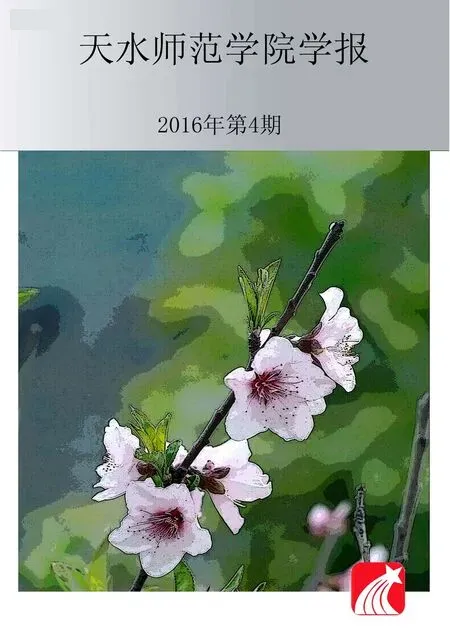人性诉求的多维镜像
——韩少功《日夜书》解读
2016-02-13王建斌许亚龙
王建斌,许亚龙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人性诉求的多维镜像
——韩少功《日夜书》解读
王建斌,许亚龙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对人性的理性观照与冷峻思考,是韩少功创作一贯坚持的内在追求与艺术品格。《日夜书》承继并拓展了新时期以来知青文学叙事的视角与限度,以“食”、“色”、“情”、“爱”等人性诉求的书写为线索,形成了一种线性与网状共生的叙述模式。
食与色;情与爱;人性;网状结构
20世纪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知青文学。“知青文学”为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系列具有文化反思意味的主题,如“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为了忘却的纪念”、“时代与人性的共谋”等。韩少功的《日夜书》无疑再一次打开了文化反思的闸门,而闸门开启之后,无论“罪与罚”有多偏狭,“潘多拉的盒子”有多虚妄,也无论“诺亚方舟”有多遥远,我们都有必要重新面对,并重新认识人性。《日夜书》共51章,每章没有固定的题目,但纵观全文,可分为四大板块:“食”、“色”、“情”、“爱”。食与色相生相克,指向人性的裂痕;情与爱相伴相随,指向人性的弥合。在食、色、情、爱与非常时代的“规训”下,知青们的人性诉求变得更为错杂。
一、食与色:身体的秘密
《礼记》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曰》曰:“食色,性也。”食、色作为人伦的基点,具有本源性。《日夜书》首先带我们进入了一个食、色为本的“白马湖世界”。
食和色作为人的最本能的欲望,源于人的身体需求,如小说所述,“人只能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身体的秘密用文学来表现时“显然不宜止于春宫诗和红灯区一类通俗话题,而应转向每一个人身体更为微妙的变化,转向一个个人性的丰富舞台。”[1]270食物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食物需求是人性最初的表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知青们下乡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肠胃问题”,姚大甲为乡妇设计刺绣图案,得到的回报是“糯米粑”,“我们”受了刺激,“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1]5同时,在白马湖知青的生活是简单反复的体力劳动:“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帻、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场,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1]9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条件不可谓不艰苦。
从下乡到回城,随着时空的转换,知青们对食欲的体验,经历了从饥饿感到富足感再到猎奇感的变化。新时代的万哥“显然已从企业家转型为活命家”,他告诫陶小布:“从你的疲惫嗜睡可以看出,你肯定肾虚,还缺硒。从你的脸色就可以看出,你肯定缺少维生素B2和B7.”[1]164不过,这种变化又是复杂的,贺亦民即使发家致富了,在口味上依然不改“穷人的重口味”,在一定程度上,“口味与身份”的关系是稳定不变的:口味成为个人历史的象征。
从食到色,小说中有一段精彩的类比:“自传统的礼教或宗教坍塌,隐私渐成热点,涉性的文字满大街,几近狂轰乱炸和暴饮暴食的程度。可惜的是,很多人看了百部以上粉色的电视连续剧,听过无数粗鄙话的黄段子,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不知‘泄点’与‘醉点’的区别——这样说吧,作为描述高潮的概念,这里说的‘泄点’,相当于饮食中的‘吃饱’,与人的生物性更为相关;这里说的‘醉点’,相当于饮食中的‘吃好’,与人的文化性更为相关。一般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难抵达,也更具幸福感的指标意义。”[1]74可见,韩少功不认同弗洛伊德理论所描述的,为了达到快乐就必须使自己的性本能任其发挥。后文接着写道:“无视文化对情欲的深度影响与制约,把人描写成千篇一律的发情机器,是不少研究者和写作者的粗心——哪怕他们一直在疾呼‘回到身体’,甚至有一种露阴癖式的文化兴趣。”[1]75食色的基本需求需要道德的制约,从易卜生到鲁迅都有此认识,韩少功延续了这种观点。
队长吴天保威逼知青万哥与“他不小心把肚子搞大”的瑞姑娘结婚,后来面对万哥的离婚坦白,直呼:“你是嫌瑞妹子不标致?瞎了眼呵。她奶子砣砣的,屁股大大的,一看就是个生崽婆,哪一块膘不好?贼养的,你看我家里那个苦瓜脸,胸脯像个搓衣板,还经常病在床,我不是也没离吗?告诉你,标致不能当饭吃。上了床,灯一黑,都一样。”[1]80在他看来,万哥所谓夫妻间的“共同语言”简直不值一提。吴天保与万哥的婚恋观体现着城乡差异,像吴天保这样的个体似乎更加真实。回城的贺亦民追求与妻子的两性快乐,在性方面,恰如对食物的获取,同样经历了从饥饿感到富足感到猎奇感的变化,“他征服的不仅是一个身体,还有一种身份和有关身份的想象,一种社会和历史中的心理幻境。”[1]84
无论是吴天保、万哥、贺亦民,还是陶小布、马楠,都逃不掉食与色所形成的人性枷锁。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写到:“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已经拜托了婚姻功能,丈夫的人为权威和家务的合理管理的束缚,从而表现为具有自身力量、问题、困难、责任、利益和快感的一种特殊关系。”[2]可见,无节制的食色追求必然会导致人性的裂痕,这在文本中有清晰的表现,例如,吴天宝只是单纯为了生存与繁衍,他没有所谓的“醉点”;贺亦民的“醉点”可以说已经是一种“烂醉”;马楠年轻时遭遇的强暴经历成为她非正常情欲观的根源。要弥补这种种裂痕,一方面需要道德的自律与宗教的劝诫。另一方面,小说给出了情与爱的解决方式。
二、情与爱:心性的秘密
情与爱之所以能弥补人性的裂痕,是因为情与爱相对食与色来说更加理性:“所有的‘瘾(别称为痴、迷、狂、癖、控等)’,无非是某些感官发达,又有某些感官关闭,对某些事物高度敏感,同时对某些事物低敏度,从而变异了人们的心理,滑向理性的瓦解——假如这个理性存在的话。”[1]151于是,缺乏理性的偏执狂们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生存安全感”、“社会承认感”,来弥补“七情内伤”。进而,小说举出了蔡海伦、马楠、万哥和马涛的例子,来说明“七情内伤”防治“神志病”的重要性。
笔者所述之“情”,特指知青与亲人、朋友和环境之间的感情;爱,特指知青与情人或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情来说,知青们即使是时隔多年,依然眷恋着白马湖那片净土,在郭友军等人的张罗下,“白马湖知青回城后的每年聚会,依照老习俗是定在大年初四。”每年的聚会成了联系感情的纽带,“大家也是被白马湖粘合在一起的。”然而,“从白马湖走出来的这一群要暧昧得多,三心二意得多。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1]180知青们不仅难以割舍彼此,也难以割舍那个时代。那是一个物资匮乏却精神高昂的时代,“少年男女纠合成群”,他们崇拜格瓦拉和甘地,为了理想“紧紧握手,吟诗赠别,严肃论争”,那个年代“任何人凭借一首《国际歌》,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同志”。[1]85精神的充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身体的疲乏,“这些《国际歌》的兑换品和增加值温暖旅途。”甚至是人与动物都充满了温情,白马湖有一只入室偷食的猴子——毛脸,“混迹于人群中,它不免人模人样。”它爱喝酒,“它一旦想讨我们的高兴,特别是想喝酒时,就傻乎乎地鞠躬和扣头,活像一个惊慌失措的老地主。”[1]247这种种情,夹杂了知青一代的苦涩,作为经历了文学寻根思潮的韩少功,再次用文学书写时代记忆时,难免表现出对文学寻根的热情。
就亲人、夫妻之间来说,生死离别无不牵动着由“爱”所生成的联系。陶小布久病离世的母亲,尸体在火葬场“飘出一道薄薄的青烟”,“最后完全消散在蓝天”。妻子马楠躲到汽车里放声大哭:“她是哭母亲这一次不仅带走了爱,也带走了自己的全部委屈——或者说与委屈等值的爱,让她哭得如此孤单。”[1]149梁队长三十岁那年,到两个妹妹的养父母前,双膝跪地,接回了妹妹。由此夫妇两获得了村里人“跷一根拇指”的赞扬,因为它们“硬是把两个妹妹养大,让他们补读了几年书,还给小妹治好了癞子,把她送去省城治好了眼疾。”[1]241待她们成人,风风光光地给嫁了出去。于是“两个妹妹出嫁时都是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送行的女人们无不撩起袖口或衣角暗自拭泪。”陶小布用一辈子的爱来呵护孩子气的马楠,马楠因为年轻时遭受强暴而不孕,于是敏感而多疑:“她对我多看两眼的那些封面女明星也警觉万分”,“似乎怕我一转眼就去杂志里偷情”,只是因为陶小布不同意她数落电视记者的言辞,便“哇的一声哭着跑出门”。为了找她,家里的水壶烧透了底差点酿成火灾,陶小布丢掉了几乎所有证件。“这乱糟糟的一切后果,就是她快意的惩罚?就是她不屈不饶的爱呵爱?”[1]160可以设想,没有陶小布的爱,马楠将不知如何弥补丧失母爱导致的人性缺失。
情与爱高于食与色,它们弥补了人性在食色诱发下的裂痕,指向人性的弥合。弗洛伊德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在大多数人身上都存在着一个极限,一旦超过这一极限,他们的天性就无法适应文化的要求;任何人如果想要变得比他们的天性所允许的更加高尚,就会患上神经病。”[3]知青一代遭遇食物匮乏、情感缺失、性爱异化的临界,回城后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弥补。同时,新的弥合又带来了新的裂痕,人性如同绿洲又如同荒原。
三、网状结构:喧哗与骚动的时代脉搏
从《马桥词典》到《暗示》,韩少功都在探索独特的“词典写作”,陈思和认为,“词条展开的叙事形式与作家在创作中发表某种评论的欲望是分不开的,当感性的艺术形象不足以表达作家对形象的特殊理解,他必须使用个性化的议论加以补充,而词条展开的叙事形式尤其适用于某些理性较强、希望通过对语言本身的重新解释以改变某些既定思路,从而改变读者对小说的常规理解的作家。”[4]无疑,韩少功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他不避讳地说《暗示》“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5]《日夜书》探索了一种词条与叙述互补的写作方式。叙述时间在小说中自由穿行,线性的叙述作为主线,网状叙述补充了线性叙述,叙述时空依据叙述逻辑自由转换。所谓线性指叙述基本按照“食”、“色”、“情”、“爱”的次序进行;所谓网状指小说所运用的“元叙述”方式与叙述干预策略的运用。正如叙述者自言:“我醒过来,再次醒过来,发现很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把事情说乱。”[1]9生活本身就是零散的:“因为我独自一人靠近上帝时(就像现在,在深夜的键盘前,在远处有轮船低鸣之际)心中闪烁的更多是零散往事,是生活的诸多碎片和毛边,不是某种严格的起承转合。”[1]239当然,小说作为语言艺术,文字的线性阅读方式决定了小说叙述必须遵循必要的逻辑,不同作家的叙述逻辑取决于其叙述内容与艺术创造。
结合上文论述,我们看到《日夜书》呈现出这样的文本叙述结构:食——停顿——色——停顿——情——停顿——爱。小说中的三次停顿在深层内蕴的表达上形成了铺展与漩涡的叙述特质。在对人性的铺展叙述下,又不能让人性过于偏狭,需要如漩涡般的聚合,于是巧妙地设置了三次停顿。第11章的词条依次是:泄点与醉点、关于N、关于安燕、关于姚大甲、关于吴天保、关于贺亦民。第25章的词条依次是:准精神病、关于蔡海伦、关于马楠、关于万哥、关于马涛。第43章的词条依次是:器官与身体、关于腿和腰、关于手、关于脑、关于舌、关于耳、关于心(或X)。小说的网状叙述对应了人性的网状形态。
同时,与铺展与漩涡的叙述特质对应的叙述功能分别是间离与暧昧。这体现在主客体关系上,所谓主体指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性,所谓客体指个体的人的生存环境与人性所面对环境时的主动适应。主动和被动的适应都取决于主体的身份,知青们即使主动地去融入农村,依然保留着最初的隔膜。如小说所述:“当时的乡都称‘公社’。这个公社的知青散落在山南岭北,总是在赶集时才集中出现于小镇。操一口外地腔,步态富有弹性的,领口缀有小花边但一脸晒得最黑的,或脚穿白球鞋但身上棉袄最破的,肯定就是知青崽了。他们坚守一种城市的高贵(小花边、白球鞋等),又极力夸张一种乡村的朴实(最黑的脸、最破的棉袄等),贵族与乞丐兼于一身,有一点自我矛盾的意味,似乎不知该把自己如何打扮。”[1]96可见,知青们对白马湖的认同感是逐渐淡化的,他们仿佛夹在城市与农村之中,农村有激昂的梦想,城市有离不开的现实价值。上山下乡运动始自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是一个喧哗与骚动的年代,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了个人的命运,所谓的“差别”并没有被消灭,下乡知青个性的被压抑注定了去政治后的释放。
四、人性的隐喻:泥淖中的纠葛
马克斯·韦伯认为,思想、环境与利益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是完全派生的。《日夜书》是一部透析人性深度的小说,它把人性置于复杂的时间、空间、环境、政治以及文化维度中,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将普遍的人生经验置于特殊的时空之中,引发了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
关于平衡点。人性有没有它应该的位置?从小说中可以看出,知青们下乡的初期,无论在物欲还是精神两方面,其人性诉求相对处于平衡状态,与普遍的人性走向契合,从而形成了平衡点。不得不说在食色的物欲无法获得满足时,是情爱精神的强大弥补了物欲的缺失。当然这种平衡是短暂的,它注定要被各种决定人性的因素打翻。人性很难有应该的位置,只能是短暂的平衡。
关于拐点。农村对知青们意味着什么?北岛、李陀等编选的知青回忆录《七十年代》在扉页上写着:“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6]开花和结果的正是人性这棵大树,它盘根交错、枝繁叶茂。农村不只意味着一次体力释放,更代表着精神的洗礼和人性的累加。
关于高点。现代人的人性诉求缘何显出病态?知青们回城之后,人性呈现出种种复杂性,每个人似乎都患上了种种现代社会病:小安子安燕的性受虐取向,姚大甲的伪成年倾向,贺亦民的疤子倾向,蔡海伦的偏执倾向,马楠的神经质倾向,马涛的警觉倾向等等。关于这种现代社会病,海德格尔曾提及“科技阱架”,上山下乡时代抑制了知青们的人性诉求,人性从本质上是追求“超常规变化”的,这迎合了返城后的改革时代,人性诉求走向客体化、符号化,达到夹杂意志、欲望的高点。
由此可以发现,时间所决定的年龄会影响人性的表达。小说叙述是从知青们青年时期开始的,结束于其壮年时期,人性诉求的走向是逐步向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性变得复杂,人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
生存环境决定人性的表达。知青们的一生经历了“下乡-回城”的转变,可以看出,下乡前知青们在城市的生活无论是物欲还是精神上都是比较充盈的,城市里不仅有相对完善的餐饮、医疗、教育条件,而且在亲人身边能够获得必须的情爱满足。下乡后,农村生活相对单调,迫于环境的压力,知青们的人性诉求随之降到了低点。知青们返城后恰逢改革开放,由此,人性的表达重新走向高点。
知识和文化决定人性的表达。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蔡海伦单身了一辈子,她笑点太高,“一辈子没笑过几次”,什么问题都是女权问题,男人只能是臭男人。女权主义带来的只是偏狭的两性对立,知识在人性面前的虚妄一览无遗。贺亦民外号疤子,没读过多少书,在惨遭电击无数,麻木晕倒无数次后,用“一种无法言传的猜读法”跟踪世界最新技术,首创了全球K型水表,当博士前来取经时,他憋出一句:“你们呀,就是书读的太好了。”贺亦民的“成功”是对知识的反讽,也是科技发展的悖论,他的技术发明更是简易与复杂的哲学悖论。大道至简,举重若轻。
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人性的表达。马涛因为一次政治纠纷而被判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受难者”。他自信自负、崇尚自由,“因一个观点上的分歧,他就与名流教授翻了脸”,差点退学,“他不习惯被别人支使的溜溜转”。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马涛,他遭遇的是自由的困惑,[7]自由的限度恰恰是人性的限度,在政治意识形态被放大的时代,马涛更加无法逃出人类的先天阈限,他的“逃离”,意味着永远无法回到故乡,他的身后是“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
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庞大的“迁徙”运动,知青们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是地理位置的转移,也是一次心理位置的转移。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理想主义潜藏于人的精神“原乡”,当代文学充满着对“原乡”的种种书写:阿来的创作是为“带着原乡人驱之不散的怀乡情结,寻找新的文化精神家园。”[8]李锐笔下的厚土、旧址,有着对古老文明的乌托邦想象。莫言的原乡夹杂了无尽的童年记忆,同时有着文化传统的承载。白马湖作为韩少功的原乡记忆,回得去的是记忆,回不去的是白马湖:“小船摇,桨声响,/湖面闪闪是月光。/两腿泥,一身汗,/天涯游子梦故乡。”[1]229种种原乡的书写,映照着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在现代性的话语下,人性似乎永远处在十字路口:站立着危机四伏,踏出去满是泥泞。
韩少功说:“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如此而已。”[9]也可以说,时代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有学者指出,文学的本质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它的最高宗旨是维护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不仅表现人的不自由和争取自由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人因丧失自由所致的内心痛苦与焦虑。文学以展示人性的深度为最高目标。”[10]《日夜书》以“食”、“色”、“情”、“爱”的人性书写为基线,在人性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中反思历史、正视人性。从《日夜书》的写作中,我们看到文学创作中理性与想象力在它们各自达到巅峰时的相互结合可以闪烁出何等恢弘的文学光辉。我们也看到了人性面对时代和文化,在其丧失理性时可以表达出何等奇异怪逆又坚挺温暖的繁冗景象。
[1]韩少功.日夜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福柯.性经验史[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58.
[3]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152.
[4]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J].当代作家评论,1997,(2).
[5]韩少功.暗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
[6]北岛,李陀.七十年代[M].北京:三联书店,2009.
[7]蒋承勇.普罗米修斯:自由的困惑——人与文化之起源诗性解说[J].外国文学,2000,(3).
[8]覃虹.舒邦泉.空灵的东方寓言,诗化的本体象征——评《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1).
[9]韩少功.进步的回退[M]∥韩少功自选集.海南:海南出版社,2008:414.
[10]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
〔责任编辑王小风〕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 Shaogong’s Book of Days and Nights
Wang Jianbin,Xu Yalo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In Han Shaogong’s writings,rational care and clear thinking about human being have always been writer’s inherent pursuit and artistic style.Book of Days and Nights inherits and develops literature of the educated since the new period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orms,and forms a net-structured narrative pattern.
sex and food;affection and love;net structure
I206
A
1671-1351(2016)04-0099-05
2016-05-11
王建斌(1974-),男,甘肃镇原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