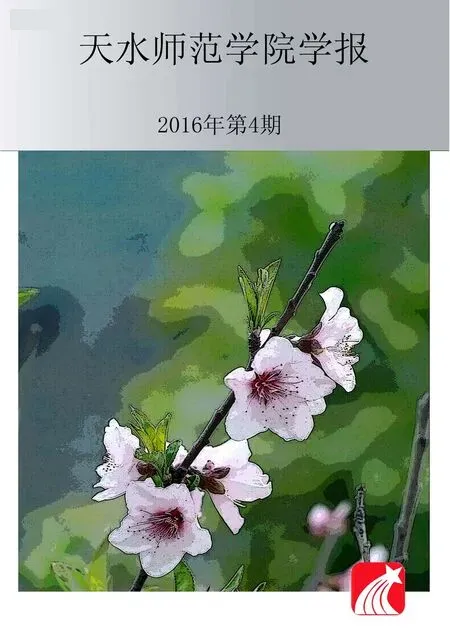基于《阿尼嘎萨》的陇南白马人的民族特性
2016-02-13潘江艳
潘江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甘肃成县742500)
基于《阿尼嘎萨》的陇南白马人的民族特性
潘江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甘肃成县742500)
陇南文县铁楼乡居住的白马人,历史悠久,且流传着许多故事,对陇南白马人民间故事《阿尼嘎萨》①解读,从陇南白马人求美的生活方式、坚韧、爽朗而又智慧的白马民族品质及白马人宗教信仰三个方面了解陇南白马人的民族特性,以期与同行在白马文化方面做一探讨。
《阿尼嘎萨》;陇南白马人;民族特性
在甘肃文县和四川的平武县、九寨沟县生活着一支少数民族——白马藏族,他们居住相对比较集中,但无论四川平武、还是九寨沟、抑或是甘肃文县,白马人的居住地都山大沟深,十分僻远落后。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客观因素,其风土人情及宗教信仰等还没有受到外界太多的干扰和影响,基本保持着原汁原味。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本族人“走出去”和外族人“走进来”,这种局面和状态一定会被打破,其原生态文化也要受到冲击。加之,白马人只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很多东西还没有被记载下来,那么,随着它周边汉、藏、羌等族的同化及外围诸多因素的渗透,那些应该保留的、积极的东西肯定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消亡。在世界文化大发展以及人们追求文化形态多样化的今天,很有必要把这个民族推介出去,一方面让世人了解它,另一方面让世人保护它。因为“陇南文县铁楼藏族乡白马河流域的十多个寨子将具有奇特性、唯一性、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白马文化,传承得最完整、最丰富、最古朴,是甘肃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27所以,这里以陇南文县铁楼乡白马人(以下均简称“陇南白马人”)的民间故事《阿尼嘎萨》为据,谈谈白马人的民族特性。文章拟从其求美的生活方式、民族品质及信仰崇拜等几方面做以申述,以期与同行在白马文化方面做以探讨。
一、求美的生活方式:沙嘎帽与歌舞
陇南白马人和四川的白马人一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他们生活艰辛,但这种艰辛却造就了他们勤劳与吃苦的品格。无论外界环境多么恶劣,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了无限期冀和憧憬,在一辈接一辈的民族繁衍中,他们用沙嘎帽展示特别,用歌声来编织生活,用舞蹈诠释激情。这种从外在形式到内在精神的求美方式,是他们对美之本质的深刻理解。
先来看沙嘎帽。白马藏族的“族徽”是沙嘎帽,它是最具特色的服饰。在《阿尼嘎萨》里,斜哦嘎萨(后来成为白马皇帝,被称为“阿尼嘎萨”)给妈妈描述白马皇帝的三公主时,亮开嗓门唱道:
……
头上戴着白帽子,
白帽子上插着白鸡毛。
帽子沿边十二角,
大小珠子三十颗。
珍珠玛瑙胸前佩,
蚌壳骨牌实在美。
腰系羊毛花腰带,
铜钱一圈圈闪光彩。
腿扎羊毛毡子带,
走起路来如风摆。①本文所依据的故事《阿尼嘎萨》见《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14-185页)(邱雷生,蒲向明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后文所引,不再一一赘述出处,仅标明具体页码。
……(53~54页)这里描述的是女性装束,有沙嘎帽、鱼骨牌、花腰带和羊毛毡子带。在故事中还有一处描述跟上面的唱词相得益彰。例文如下:
昼什姆(斜哦嘎萨的准妻子,白马皇帝的三女儿)头饰上佩着闪亮的鱼骨牌和珍珠玛瑙,身着五彩服,腰系花腰带,胸带鱼骨褂肚,腰缠铜板带,耳佩金耳环,手腕上戴着银手镯,脚穿一双绣花番鞋。(94页)
从此描述来看,白马女性服饰的颜色艳丽,对比鲜明,加上各种饰物恰到好处的搭配,把白马姑娘(皇家三公主)衬托得既高贵又漂亮。另外,故事第143页到第144页,白马皇帝向斜哦嘎萨提的第五个问题“白马姑娘的服饰”里,通过问答对白马女性装束有进一步的补充。至于白马男性装束,在故事里有两处描述,两处基本相似,择其全者如下:
阿扎伊(斜哦嘎萨的父亲)看到的情景,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就在远处他耕地的地方,有一个英俊潇洒的白马小伙子,头戴插着白鸡毛的沙嘎帽,身穿白麻布汗褂,外套黑坎肩,腰系黑羊毛腰带,黑裤子上系着绣花带子,脚穿一双毡筒蛙鞋(一种用牛皮做鞋底,麻布或毡做筒子的靴子),一副典型的白马人装束。(32页)
这段话交代了白马男子典型的装束有沙嘎帽、白麻布汗衫、黑坎肩、绣花带子和毡筒蛙鞋。颜色搭配主要是黑白二色,单纯的颜色和简单的打扮相结合,显示出白马男性粗犷、豪爽和雄壮的形貌特征。从以上对白马男女服饰的表述来分析,白马人无论男女老少,均戴沙嘎帽。其实,沙嘎帽是用羊毛擀制的白色盘状的帽子,其边荷叶状,也呈轻微的波浪形。这种帽子只是纯粹的一种装饰品,它既不能遮风挡雨,又不能抵御严寒。但白马人喜欢也善于用明亮耀眼的色彩来打扮自己,他们的沙嘎帽上面,往往用红蓝两色的细线绣着不同形状的图案。“在线与帽之间,才插着锦鸡翎或者白羽毛,男的大多插一支,显得英俊而潇洒,女的大多插两支或者三支,显得婀娜多姿。现在很多爱美的白马姑娘还喜欢把彩色的小珠珠串成一串缝在帽子上,顺着荷叶边吊下来,走在蓝天白云下,跃动的白色羽毛,随风摆动的五彩珠珠,显得分外的妩媚动人。”[2]19至此可看出,沙嘎帽是白马人鲜明的民族标志,同时也是白马人对外在美的一种选择。不只自己,也希望别的民族认同。
此外,“白马藏族是一个在歌声中度过漫漫人生的民族。”[2]16山歌、酒歌、蜂汤酒歌、催眠曲、祭祀歌、招魂歌、开春歌、耕地歌、割麦歌、掰玉米歌、打连枷歌、造屋歌、打猎歌、娶媳妇歌、嫁女歌、骑马歌、主人歌……《阿尼嘎萨》里共记录了76首歌,这些歌或歌唱生活劳作的艰辛与愉快,或抒发牵挂担心的忧伤和甜蜜,或鼓励人们敢于向艰难与妖魔去挑战,或努力追求爱情幸福的坚贞同美好。白马人无事不歌,无处不歌。一曲曲古老动听的歌,仿佛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民俗画卷,向人们诉说着他们的过往与历史。歌声粗犷豪迈,情感丰富饱满。虽原始古朴,但美妙动听。不一般的旋律往往承载着深厚的意蕴回荡在白马河畔的山水之间,萦绕在白马儿女的心中。敢问除过白马人,哪个民族把生活歌化了?恐怕唯有白马人。他们无论畅意与悲伤,也无论突遇灾难还是嘉宾来访,都可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们是敢于和勇于担当的民族,往往用歌声来演绎他们性格深处那种坚韧与执着的情愫。他们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把山水人情编织进美妙歌声的民族。倾听他们的歌声,就是与他们灵魂的对话!
最后,跳火圈舞(又名圆圆舞,白马语把跳火圈舞叫“改轴”)是陇南白马人的风俗特色。在《阿尼嘎萨》中有如下的描述:
寨子里的大场上,熊熊的篝火燃起来了,欢庆的锣鼓敲起来了,牛角号吹起来了,欢乐的歌声唱起来了,男女老少手拉手,跳起了欢乐的火圈舞。乡亲们通宵达旦的娱乐,庆贺皇帝的三公主成了白马山寨的媳妇。(101页)
从这段话来看,人们只有在欢庆的时候才会跳火圈舞,且不分男女老幼,人人可以参与。《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舞蹈卷》①张益琴,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记述,陇南白马人居住的麦贡山、入贡山、立志山、案板地、强曲、草坡地、枕头坝、薛堡寨、堡子坪、寨科桥和迭堡寨等十一个村寨,都有跳火圈舞的习俗,而且这种习俗从腊月初八会延续到正月十七,历时约四十天。这里,田野调查资料正好印证了《阿尼嘎萨》中所反映的白马人求美的方式,他们共饮咂杆酒,同跳火圈舞,借此来表达和宣泄对生活的激情。
二、民族性格:坚韧、爽朗和智慧
《阿尼嘎萨》是陇南白马人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话把”,②据赵逵夫2011年11月2日在《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序》(邱雷生,蒲向明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7页注释,白马人把能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或流传下来的故事或语言叫做“话把”。他们的说法是:“番人留文书,番人留话把”。集陇南白马人历史、信仰、农耕、狩猎等众多方面的信息。故事以阿尼嘎萨为主人公,抒写了其既多灾多难、又神奇而成功的一生。有神奇出世、初露身手、想要成家、托父提亲、进宫求婚、智胜恶棍、凤岭取宝、皇帝允婚、公主生爱、修身从军、情牵千里、鏖战妖魔、才赢皇位、降妖除魔、铲除恶霸和为民造福共十六个部分。情节离奇曲折,浪漫动人。叙述经历,委婉细腻,讲述爱情,缠绵感人,塑造英雄,伟大而又智慧……总之,此故事引人入胜,读之往往如享甘饴。
陇南白马人代代传说《阿尼嘎萨》,把阿尼嘎萨看成了自己民族的化身,虽历尽磨难,但终成正果。故事中的阿尼嘎萨一生下来,就是一只青蛙,父亲取名斜哦嘎萨(白马语为地上的青蛙),母亲叫他采石乃(白马语为可怜的小宝贝)。在母亲茨嫚娜姆的呵护下,十二岁忽言人语。从此有着人的思维和行为,会唱歌、会给父亲到田间送饭、会耕地、会打猎,还托父提亲,让父亲到皇宫给自己去说皇家三公主。托付不成,自己进宫求婚,冲破道道难关,使皇帝允婚,最后终于娶回公主。但为了去掉青蛙的外形而换成人形,他闭门修身,修成后又从军,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归家后,既得到了公主的真心爱情,又赢得白马皇帝的无限信任,在皇帝的坚持下,做了白马皇帝,被人称作“阿尼嘎萨”。阿尼嘎萨是走出皇宫的皇帝。即使做了皇帝,他还不忘降妖除魔、铲除恶霸和为民造福,由于他拥有伟大而辉煌的勋绩,才成为陇南白马人故事中最璀璨的一颗星星。
阿尼嘎萨是集坚韧、爽朗和智慧于一身的人物。而坚韧、爽朗和智慧这些品质也是陇南白马人这个伟大民族的特性之一,这也是值得他们骄傲的地方。阿尼嘎萨的这些优秀品质在故事的“初露身手”一节中开始显现。他刚出生时是一只青蛙,这个局限使其很难像常人那样生活,但十二岁的时候,他忽然会说话了,还会唱歌、会给父亲到田间送饭、会耕地、会打猎,并且做得不亚于常人。就像耕地,故事叙述道:
刚才发生的一切,仿佛梦幻一般。更让阿扎伊惊奇的是,他从清晨到中午一口气不歇地耕地,耕了大半天,才耕了不到半亩地。刚才小白马少年只耕了一口气,顶多只有一袋烟的功夫,却把两亩多地全部耕完了,耕得又深又匀。不仅把地耕了,而且还耙了,耙得又平整又松软,只等撒青稞籽。阿扎伊敢断言,白马少年的耕地本领,即使白马山寨最好的庄稼把式也比不过。(33页)
儿子这样超群的本领,使其父阿扎伊“心里比喝了一罐咂杆酒还舒坦”。不止耕地,阿尼嘎萨的打猎,也是非常出色。故事中阿尼嘎萨在《打猎歌》中唱道:
我们的猎枪瞄得准,
我们的弓箭射得好,
我们的眼睛像星星一样亮,
我们的身材像山峰一样壮,
虽然历尽了千难万险,
我们一定会有惊喜的收获,
只要枪声一响、利箭一射,
你看那,猎物就会倒下来……(36页)
阿妈接过捕获的猎物,
全家人高高兴兴欢聚一堂,
围坐在火塘边又说又笑,
鼎锅里煮熟的猎物喷喷香。
叫来寨子里的亲朋好友,
请大家一起来品尝,
端起咂杆美酒深情地祝福,
尊敬的山神啊,高高在上。(37页)
阿尼嘎萨每次打猎都是收获颇丰,而且他还会与乡里乡亲们分享打猎成果。此外,他还是歌手,经常在乡亲们嫁娶、祭祀、招魂和农耕等场合或仪式上唱歌,深受人们喜爱。
农耕、打猎、唱歌,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不到十八岁,要样样做得在行,那需经过少磨炼?“青蛙”出身的阿尼嘎萨在少年时期却具备这些能耐,说明他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忍耐磨难的坚韧。阿尼嘎萨经常与人分享打猎所获,说明他性格中的爽朗。他的生活充满歌声,说明他善于用歌声来编织生活,这就是智慧。故事后面所述的迎娶三公主、智胜九弟兄、凤岭取宝、降妖除魔、铲除恶霸及为民造福,虽似神话,却令人信服地塑造出了阿尼嘎萨大智大勇的形象。也表明,正因为阿尼嘎萨具备了坚韧、爽朗和智慧等优秀而伟大的品质,他才获得了成功,才赢取了白马人心目中英雄的美名,成为白马人模仿和崇拜的偶像。另外,白马人在传说《阿尼嘎萨》时,出现了诸多像“上山打老虎,就有打老虎的本领”、“人在甜言上栽跟头,马在软地上打前失”、“大路走不尽,河水背不干”、“悬崖上的树砍不着,海子里的石头磨不着刀”、“马走路是后脚踩着前脚印走,人上梯子要挨着来”等白马俗语,它们与阿尼嘎萨的智慧相辉映,无不表现了陇南白马人的智慧。
三、信仰崇拜:泛神性、自然性
陇南白马人的宗教信仰受跟他们毗邻的汉族、藏族和羌族的影响,与他们有较多相似的地方。如当地汉族敬拜和祭祀的主要神灵有山神、土地神、家神、二郎神、龙王和马王爷等,这些神也是白马人敬拜和祭祀的对象,但在崇拜心理及具体仪式上还是有区别,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汉族是通过在寺院神庙(或殿)中供奉神像(多为塑像)和在家中供奉小型塑像或画像来膜拜,以焚烧香火、祷告和诵经来完成拜祭仪式和祝愿(福)心理。宗教归属是佛、道,也有其他一些像崇拜家神等,其实为佛、道意识变异思想的崇拜。而藏、羌的民族信仰崇拜,则有一种念咒驱鬼的原始巫术的性质。他们手持“羊皮鼓”、反穿羊皮袄、戴着面具跳的“藏羌舞”形式似乎对白马人影响较大。像陇南白马人的池哥昼面具舞,就是白马人的傩祭舞蹈。这种舞蹈形式,跟“藏羌舞”一样,既是敬神,又是娱神性的狂欢。有专家说,白马人所戴的面具是研究古代氐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活化石”。①王国基的《甘肃文县白马氐人的“池哥昼”》,选自《傩苑——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1月);《白马人傩祭舞蹈三目神面具之源》发表于《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陇南白马人的信仰崇拜受汉、藏和羌族崇拜的影响是后来的事,而其本色的崇拜,则在《阿尼嘎萨》中有表现。看《阿尼嘎萨》中阿扎伊悲伤地唱道:
天神啊,你在哪里?请你快快来!
地神啊,你在哪里?请你快快来!
山神啊,你在哪里?请你快快来!
河神啊,你在哪里?请你快快来!
树神啊,你在哪里?请你快快来!
石神啊,你在哪里?请你快快来!
各路神灵啊,你在哪里?请你快快来!
天神啊,请你发发慈悲,快来帮帮我!
地神啊,请你发发慈悲,快来帮帮我!
山神啊,请你发发慈悲,快来帮帮我!
河神啊,请你发发慈悲,快来帮帮我!
树神啊,请你发发慈悲,快来帮帮我!
石神啊,请你发发慈悲,快来帮帮我!
各路神灵啊,请你发发慈悲,
快来帮帮我!(22~23页)
上面的歌是阿扎伊在悲苦无依,将要寻死之际向着苍天呼喊,呼唤神灵来帮助他时的悲伤唱词。唱词里涉及到了天、地、山、河、树、石诸神及各路神灵,说明陇南白马人信奉的是触目所见的一切自然物,这就是泛神意识,而这些都是归属自然的东西。“白马人认为万物有灵,万物皆种,属于多神宗教信仰之列,其原始拜物教的宗教意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崇拜山神、水神、火神、树神、天神、土地等,具有明显的原始图腾崇拜性质。”[3]88所以,陇南白马人的信仰崇拜有泛神性和自然性。
四、总论
陇南白马人生活在陇南的白马河流域,聚居在文县铁楼乡,他们有许多代代相传、美丽又动人的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构成了他们最重要的“集体记忆”,这也是他们对祖先历史的追忆,个个被深深地镌刻在一代又一代族民们的脑海中。它们中,《阿尼嘎萨》堪为陇南白马人的民间传说性的“史诗”,既全方位反映了这个民族,又放射着这个民族的智慧的光芒,显示了这个独一无二民族的特性。
陇南白马人善良、勤劳、勇敢,世世代代居住在文县西南部的深山中,恶劣、艰苦的自然条件使他们信仰和崇拜祖先、白马老爷和本家祖神,同时也具有坚韧、爽朗和智慧的民族品性。他们热爱甚至信奉他们赖以生活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及天地、日月和星辰,尊敬和爱戴无论男女老幼的乡民,执着地追求着具有自己特色的、完美的生活方式——戴着那种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沙嘎帽,痛饮自酿的咂杆酒(又名五色酒),跳着火圈舞,唱着自己民族的歌——一代又一代把自己民族的文化薪火相传下去。
[1]张金生,邱雷生,莫超.陇南白马人对传统文化传承之探究[J].甘肃高师学报,2014,(1).
[2]王艳.白马藏族社会文化研究——以文县铁楼为例[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0.
[3]崔峰.白马人“池哥昼”的原始崇拜和历史渊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88-92.
〔责任编辑王小风〕
G127
A
1671-1351(2016)04-0041-04
2016-05-11
潘江艳(1971-),男,甘肃天水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