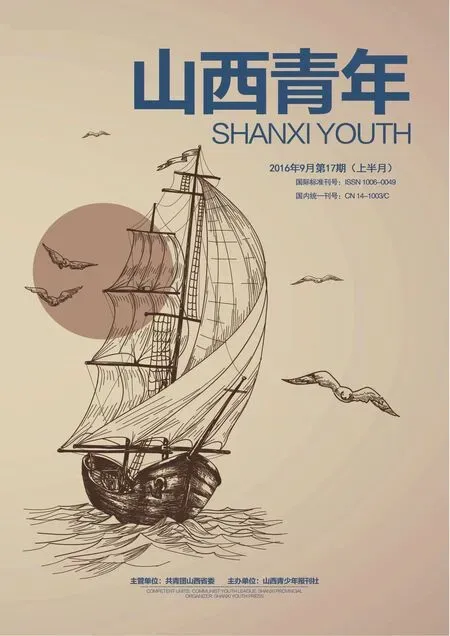《白鲸》中矛盾的宗教观*
——对上帝的批判与和解
2016-02-04张心嘉
张心嘉
长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白鲸》中矛盾的宗教观*
——对上帝的批判与和解
张心嘉**
长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白鲸》是一部关于宗教信仰的鸿篇巨著,整本书潜存的基调即是信仰的问题。在浪漫主义文学时期、超验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背负着加尔文教义的沉重枷锁,麦尔维尔通过《白鲸》探索上帝的形象,探求人、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在他的著作中他表现了自己的宗教困惑,也坚定了自己对信仰的探索与坚守。本文作者从两方面揭示《白鲸》中麦尔维尔隐含的宗教思想,一是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和宗教生活的不满与批判,二是由于无法摆脱的宗教观念,与上帝的和解。
《白鲸》;上帝;批判;和解
一、引言
1981年麦尔维尔完成他的代表作《白鲸》之后,给霍桑回信,“我写了一本邪恶的书,但是感觉自己纯洁得像一只羔羊”。此话包含了麦尔维尔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也表达了他的隐忧。那么麦尔维尔为什么担心?《白鲸》这本书到底有何邪恶之处,麦尔维尔为什么又声称自己纯洁无暇呢?细读小说,不难发现,麦尔维尔所谓的邪恶,乃是对上帝的亵渎和反叛。而为了减轻亵渎上帝的罪责,麦尔维尔安排以实玛利活了下来并作为本书的叙述者。在宗教思想依然盛行的19世纪,麦尔维尔无法预知读者能够多大程度得接受违背传统宗教教义的内容,因此他心怀忐忑。但是他并不肯缄口,而是固执地借叙述者以实玛利的讥讽口吻和主人公亚哈对上帝的激烈反抗,嘲弄支撑社会秩序的传统宗教观念,向上帝问责,向传统生活的欺骗性挑战。
麦尔维尔具有虔诚的宗教背景,其父母具有很深刻的宗教热忱,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虽然加尔文教义的影响根深蒂固,但麦尔维尔并未成为绝对忠实的加尔文主义者。麦尔维尔对加尔文教派长老会教义冷酷、沉闷深有体会,而海上提心吊胆、动荡不安的捕鲸生活,以及反复无常、冷酷无情的大自然无不让麦尔维尔对加尔文教义产生怀疑。另外,19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变化,这些都动摇了麦尔维尔对传统教义的虔诚态度。置身于先验主义与清教主义共存、科学思想与宗教上帝同在的这种文化背景中,麦尔维尔一直徘徊于正统加尔文主义与爱默生所提倡的超验主义之中。
二、“神性”和“人性”统一的上帝
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提出无神论思想,公开挑战宗教神学。1859年《物种起源》以及进化论打破了加尔文主义束缚人类的精神枷锁,慢慢揭开了加尔文主义的神秘面纱。19世纪初,独立战争结束,美利坚合众国高举着民主与平等的大旗,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人们生活也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西进运动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期望与遐想,可以说美国到处洋溢着乐观和希望的气氛。再加上来自英国作家如斯各特等人的影响,这片年轻而又热情的国土上迎来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关注尘世中凡人的喜怒哀乐,但上帝的身影依旧清晰可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19世纪30、40年代产生了以爱默生为代表人物的超验主义理论。
在超验主义运动中,人则可以通过直觉来认识上帝,或者通过置个人心灵于“超灵”之中来寻求人性和神性的统一,把上帝人性化,从而把人神关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它猛烈地冲击着旧思想和加尔文教义带给人们的思想束缚,给当时美国的思想文化方面带来空前的繁荣。爱默生的思想保存了唯一理教派中的积极成分(他们强调上帝的父性,而弱化上帝的权威),又吸收了德国康德唯心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思想材料,发展成超验主义的思想体系。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以乐观洋溢的精神诠释了人的本性,他宣告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即内在的上帝,因而人也是神圣的,人类具有救赎的潜力。内在的上帝意味着上帝与人类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被拉近了,从而也奠定了建立新型人神关系的基础。
在麦尔维尔笔下,大海被赋予了人的感情和灵性,他用充满深情的,赞美的语句来描述大海。在他看来,一方面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具有神性,理应也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关系密切,自然也带有人类的感情和意志,因此具有了人性。我们看出,麦尔维尔的确收到了超验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自然是有“灵”的,是“超灵”的一部分,而并不是完全物化的不带有灵性的。但是,他的观点与超验主义又不完全相同,在麦尔维尔看来,自然并非一直温柔善良,大海平静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危险与罪恶。“欣赏着大海安详的美和它光可照人的皮肤,人就忘了大洋那颗隐藏在风平浪静下的虎狼之心,也不愿去想它天鹅绒般的脚蹼中那恶狠狠地利爪”。随着迈尔维尔思想的延伸,上帝的形象变得有些抽象。变成了控制人类的,超自然的力量代表。上帝与人类之间仍然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虽然迈尔维尔处在以超验主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但是由于他自身根深蒂固的加尔文教义的影响,《白鲸》中的上帝仍旧是冷漠的,愤怒的形象。白鲸就是遵从上帝命令的,是上帝的仆人。鲸鱼庞大的身躯和它神秘不可知的威力,无不昭示着上帝的威严。
三、“亚哈”的抗争——批判
麦尔维尔在整本书中通过他的两个“自我”即故事的叙述者以实玛利和船长亚哈使用同样表白的语气来揭示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宗教感情。通过对季奎格宗教转变历程的描写,麦尔维尔痛快淋漓地批判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败。季奎格是西南方一个遥远岛屿上的大酋长的儿子,从小就受到基督教世界的吸引,渴望见识这个陌生的世界。长大后,他独自离开故土,不顾一切地上了捕鲸船。“他(季奎格)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深切的愿望,要到基督徒中去,向他们学本事,好使他的人民比他们目前更幸福”,麦尔维尔用极为讽刺的口吻描写了季奎格的愿望。然而,“捕鲸鱼这个行当很快使他相信,即使是基督教徒也可以是卑鄙而邪恶的,比起他的父亲属下所有的异教徒都要邪恶步子多少倍”。他最终宣称,“随你走到哪,这都是个邪恶的世界,我还是到死都当个异教徒吧”。麦尔维尔借助异教徒之口抨击了基督教的堕落,颠覆了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的二元对立关系,自基督教创建以来赋予的所谓优越性遭到沉痛打击。
另外,麦尔维尔也借助一个伪善的清教徒形象——披谷得号的船主之一比勒达船长,毫不客气地批判了基督教的虚伪性。比勒达曾宣称:“一个人信得教是一回事,而这实际的世道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世道是给人好处的。”在信仰和世俗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对离开海港去捕鲸的水手们说,“在主日里别捕鲸太凶,可也别错过好机会,老天爷送来的上好礼物不能不要”。他对手下的水手更是进行毫不留情地剥削,“每当返航到家,他手下的水手一个个筋疲力尽,多数得抬上岸来送进医院”。以实玛利也揭露其本质“他这个人恰好就是专讲功力的化身”。由此可见,一个伪善、吝啬、功利的基督教徒形象跃然纸上。
亚哈是麦尔维尔揭示人与上帝关系的重中之重。他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震撼心灵的人物,集圣徒与魔鬼于一身。亚哈名字起源于《旧约·列王纪上》,亚哈是以色列王。亚哈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在其统治期间,他娶西顿王之女耶洗别为妻,与强大的犹太国实行和平外交,并稳固周边局势。船长亚哈同亚哈王一样,船长亚哈也不乏机智与勇敢,小说中多次暗示他的《圣经》中的国王身份。“亚哈就是船上的可汗,海上的国王以及那些大海怪的伟大主宰。”他既是一个称职的船长,又是一个出色的捕鲸人。所有的船员,或是被他的魅力所折服,或是迫于他的威严,都追随于他而没有叛变,就足以证明他的影响力,而麦尔维尔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赞赏。难怪他在完成《白鲸》后,深有感触地声称自己写了本“邪恶的书”。在宗教信仰上,国王亚哈和船长亚哈也都是虔诚的异教徒。在上帝的眼中,他们都是罪恶的。亚哈王纵容耶洗别崇拜巴力神并建造巴力神庙,任耶洗别残害耶和华的先知,这些都是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上帝的先知指出:“你亚哈出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降临于你,将你除尽。凡属于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然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然被空中的鸟吃。”最终,亚哈王因不顾先知迈凯亚的劝阻,坚持进军亚叙,结果被流箭射死疆场。
船长亚哈“尽管名义上算是个基督徒,其实却是基督教外之人”。亚哈船长较亚哈王更甚,身为基督徒却祟拜火,像波斯袄教徒一样迷恋与火有关的光、太阳和夏辰,当“裴廓德号’,在日本海遭受台风雷电袭击、船上三根桅杆被燃着时,他声称自己是“火神的真正孩子”,析求火神保佑,但又叫嚣对火神的真正崇拜就是蔑视它。他蔑视一切神灵,这种傲慢与基督徒的谦卑精神背道而驰。他对火神的崇拜以及文中极富象征意义的一场对三个桅杆上的火的描写把亚哈列入了异教徒之列,但他在异教崇拜中也得不到任何的安慰,“我现在也知道了对你真正的礼拜便是造你的反。爱你敬你,并不会使你发善心”。他一面用假肢撑起自己,一面想方设法操控船员为自己报仇,他无视一切建议和劝说,他孤注一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为了报仇和重获尊严,他绞尽脑汁,并发誓“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也要和这种无条件主宰我的威力抗争。在那些似人非人之中,有一个有人格的人站在这儿。”这位偏执的船长向化身动物的神灵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最终失去理智和人性,栽进了绝望的深渊。然而,这使得原本是私人的复仇带上了悲壮的色彩,就好像是他带着全人类的仇恨与白鲸作战,就好像是他在为全人类有尊严地生存在宇宙中而战。在某种程度上,亚哈的这种态度就破坏了上帝与人的二元对立。在此之前,因为“原罪”的烙印,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人在与上帝的对立中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亚哈迈出了反抗上帝的重要一步。
四、人类的救赎——和解
人类的救赎是宗教的基本问题。加尔文教义断定人类无法为善,这就意味着,人类无法自救,救赎是上帝的恩典,因而,人类所要做的就是真心实意地忏悔。小说一开始,麦尔维尔通过梅布尔神父布道讲述了约拿的故事。这个故事贯穿了《白鲸》的始终,不同的是:在鲸鱼的肚子里,约拿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最终获得救赎。可见梅布尔神父强调的信条是人类唯一获得救赎的方式就是忏悔,是“真心实意的悔罪,不是吵吵闹闹要求宽恕,而是对处罚深怀感激”。而亚哈至死都没有彻底反省自己的所谓“罪恶”,更没有忏悔的迹象,因而他最终并未获得救赎。从亚哈的悲惨结局我们似乎看出,麦尔维尔对这种救赎方式似乎并不持反对意见。
然而书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人物以实玛利被拯救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实玛利更接近于梅布尔神父布道中的约拿形象:两者都在逃避(虽然我们一直都无从得知以实玛利到底要逃避什么);两者都是弃儿(《圣经》中的约拿连同母亲被父亲亚米太抛弃,而带有麦尔维尔个人早年丧父经历的以实玛利也视自己为孤儿);更重要的是最后两者都获得拯救。结局的雷同并不能让我们忘记救赎方式上的差异:《圣经》里的罪人约拿是幡然悔悟、真心悔罪后上帝的救赎,而以实玛利的获救却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他的生还与其说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不如说是人类的自救更为确切。
其实,关于自救和救赎的问题在书的开始部分已有涉及。在第18章里,麦尔维尔描写了披谷得号的两位东家比勒达和法勒船长的一场争论。当他们还在捕鲸时,有一次在日本海上船差点遭遇灭顶之灾,“三根桅杆都被台风吹到海里去了”,但两个人对此却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比勒达想到的是“死神和末日”,而法勒却“一直在想生,怎么生!怎么救大家的命!”“要赶紧竖起那应急的桅杆来,要赶紧把船开到最近的一个港口里去,要保住船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正是当时他的这种自救意识拯救了船和船员。这个争论的结局更是耐人寻味,一向喜欢夸夸其谈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比勒达“显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他的无言以对标志着法勒的胜利,也是人类自救的胜利。
麦尔维尔不再一味与上帝作形而上的纠缠,不再对冷漠的上帝愤恨不平,而是以更为理智的视角重新看待人在宇宙之间的地位、人与上帝的关系。当麦尔维尔把信仰当成一个可变的历程和循环,而不是对上帝盲目的笃信和绝对服从,当他开始放眼观察整个人类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友爱,而抛却了种族和信仰的偏见,他已经大大超越了他所负载的清教加尔文教教义的狭隘。在传统教义与新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的年代,麦尔维尔对加尔文主义提出了质疑。然而他既不能具有坚定的科学信念,也不能彻底否认上帝的存在,所以他只能踯躅于信奉与怀疑的对立中。一方面《白鲸》中的宗教思想深刻体现了其超越宗教寓意之上的超验主义,他对基督教的腐败世界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因为无法脱离正统加尔文教义的宗教困惑所以他最终与上帝和解。
五、结语
麦尔维尔带着一种灵魂的焦灼感纠缠于信与不信的问题,他以沉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把自己卷进信仰的漩涡,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与上帝和基督教做着形而上的争辩。他既批判又怀疑,既激进又妥协。在这本堪称巨著的《白鲸》中,麦尔维尔穷其毕生的心血,努力摆脱身上背负的加尔文教义的枷锁,在超验主义的感染下,寻找一个神性与人性相统一的上帝。
[1]洪增流.美国文学中上帝形象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薛小惠.《白鲸》中的加尔文主义宗教观透视[J].外语教学,2014,35(3):80-83.
[3]聂庆娟.由圣经情结看麦尔维尔的宗教审视与困惑[J].作家,2011(6):73-74.
[4]孙筱珍.《白鲸》的宗教意义透视[J].外国文学研究,2003(4):24-27.
I712.074
A
1006-0049-(2016)17-0013-02
*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上帝形象的产生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形象变化”(吉教科文合字[2013]第234号)。项目负责人:张心嘉,参与人贾丽婷,刘怡然。
**作者简介:张心嘉(1977-),女,汉族,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长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英语教师,讲师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