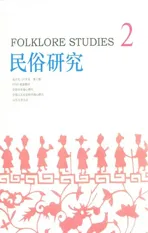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2016-02-03邱国良
邱国良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
——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邱国良
摘要:“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村庄纠纷;“龙脉”信仰;集体行动;文化认同
有关信仰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俗学与宗教学领域。在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著述颇多,其中首推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它从现代西方思想角度展示了中国宗教的特点和体系,并试图对儒教伦理未能激发中国资本主义的深层原因予以文化阐释:儒教并非是宗教,因而未能激发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杨庆堃在其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则反思了韦伯的宗教概念,并构建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分析框架,认为对于中国大众而言,尽管信仰不似西方有着规范仪式和一定的组织体系,但其内心深处的信仰却是不容置疑的。在韦思谛编著的《中国大众宗教》一书中,则改变先前研究儒、道、佛三大宗教的学术取向,转而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这种学术动态也反映了西方汉学界主流开始对中国宗教信仰重新认识和定位。近年来,国内关于信仰文化的研究也存在这一倾向。如关于客家文化信仰的研究,关于妈祖、张圣君以及东北民族天神的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大都属于所谓“大众宗教”的范畴。总体而言,有关中国社会信仰文化的研究取向呈现精英(主流)信仰向大众(民间)信仰转型的趋势,主要围绕民间信仰及其历史变迁展开研究。
除了民俗学与宗教学领域外,也有学者从国家政权建设或乡村治理层面对乡土文化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它以“大众文化”为切入视角,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论证了20世纪初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渗入社会底层的。此外,贺雪峰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也试图摆脱乡村治理研究的制度主义路径,转而关注制度实施的社会文化背景。党国英也曾撰文分析了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①党国英:《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2期。, 邱新有则通过考察江西铁村的文化活动,对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分析。②邱新有:《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稳定——对江西省铁村文化活动的解读》,《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6期。上述研究主要是围绕国家权力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或涉及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或讨论民间文化的制度环境等。
综上所述,学界对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遵循民俗文化的研究取向,或从文化嵌入性视角讨论乡村治理问题。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作为一种对中国农民心理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村落信仰,“龙脉”信仰甚少受到学界的关注。那么,作为一种非主流的传统民间文化,村落“龙脉”信仰置于怎样的社会及制度环境之中,其又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形成互动呢?本文拟选取若干个案,力图剖析村落“龙脉”信仰生成的心理动因、道德基础及制度环境,并藉此检讨和反思当前文化战略的价值取向。
一、族群意识:“龙脉”信仰的心理动因
每个族群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在族群内部也会有着不同的信仰标志。村落“龙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象征着村落的兴衰。与关帝、妈祖等普遍性信仰不同,村落“龙脉”信仰一般是以村落尤其是单一宗族性村落为单位的特殊信仰。大多数传统村落都有着自己的“龙脉”,村民们普遍相信它会庇佑村落兴旺及子孙后代的平安。从朝拜对象上看,其他有如关帝、妈祖等信仰均有实际的朝拜对象,对村民而言它们是一种“有形”的精神寄托;而村落“龙脉”信仰一般缺乏明确的朝拜实体,也不需要举行特别的祭祀仪式,但作为一种村落集体性信仰,其对村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时显得异常神秘而令人敬畏。
在传统农村社会实际生活中,国家权威(皇权)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有如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比起传统国家的政府形式,(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更为发达和集中,在传统文明中,政治权威(君主或帝王)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相对自治的地方村落臣民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美]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与此同时,以宗族为纽带的民间力量构成了中国大多数农村社会的实际主导力量,对促进与维护乡土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生活在村落的人们似乎远离了皇权和城市的尘嚣,世代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享受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
当然,要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及农民心理的特点,无疑须对乡村社会结构予以关切。“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4页。, 而村落社会结构则包括其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两个方面。从外部结构上看,传统农村社会是由群聚而居的各个自然形成的村落组成,每个自然村落实质是天然的“自治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间互相独立、相互联结,形成“蜂窝状结构”;而村庄的内部结构,则主要是指宗族性社会网络,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呈现出“差序格局”。当然,对于杂姓村而言,除了血缘因素外,地缘及其他关系也将成为联系村落内部结构的纽带。
由于个体意识的社会嵌入性,农民的文化心理与村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如前所述,村落的外部社会结构表现为相互独立、相互联结的“蜂窝状结构”,在缺乏外部力量推动的自然状态下,这种“蜂窝状结构”并不容易改变。这种村落外部结构的稳定性使得因血缘而结合起来的传统村落基本不发生流动,只有在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71页。,才会分裂出去另外繁殖成为新的村落。同时,这种长期相对稳定的村落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体之间的互动,不利于农村社会自发形成普遍性信仰。另一方面,在以宗族联系为纽带的自然村落内部,村民之间拥有共同祖先和深厚的血缘关系,他们经常性地聚集起来,共同进行祭祀祖先、编纂族谱及建设祠堂等活动,推动着其信仰趋向宗族同构性,并最终形成与宗族命运相联系的信仰标志——“龙脉”。只是,这种信仰标志是以村落为单位的特殊信仰,与国家意欲推行的普遍性信仰相悖,因而事实上两者往往并不相容。
下面是关于杨(谐音“羊”)村“龙脉”信仰的案例:
在距离杨村约1华里处,有一块面积约11亩的小山地。从地貌上看,这块地是梅陇岗(地名)的末端,杨村人称之为“亭子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村旁沿线公路尚未修建,杨村人经由小路而外出,“亭子边”正是当时杨村人出行的必经之处,故被视为杨村村头(谐音“羊头”)。由于当时国家山林政策几经变动,“亭子边”的权属并不十分清晰,解放前后这块地是杨村的,但土改后很长一段时间却一直由黄村在管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常住人口剧增的黄村便打算在这块山地上建房。对此,杨村表示坚决反对。杨村人认为,虽说这块地本身并不值钱,但它是杨村的村头,一旦在上面建了房,就意味着“羊头”上不长草,“羊”就会饿死。这对杨村人来说,断然不能接受。
尽管“羊头”之说在主流文化看来并不可取,甚至可能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打压,但这种风水之说的广泛流传,却无疑折射了乡土文化对农民心理所产生的微妙且深刻的影响。传统村落的“龙脉”信仰之所以在乡土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与悠久的宗族政治传统不无关系。自商代始,历代统治者为了强化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在农村基层普遍设置网络组织,商代有“族尹”,周代则在广大农村地区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分别设有邻长、里胥、酂师、鄙正、县师、遂大夫。这就是所谓的“乡遂制度”。周代以后的各个朝代,尽管基层组织设置各异,但基本上是沿袭这一轨迹发展的。*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不难发现,无论是商代的族尹、周代“乡遂制度”,或是周以后乡里制度及保甲制度,其统治基石无不是宗族力量。为此,历代统治者均注重加强与乡绅及宗族头人的政治联系。而且,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政治联系,统治者还极力宣扬“家国同构”思想,试图构建稳定的统治秩序。这在客观上催生了族群意识的普遍形成。因而从本质上讲,“龙脉”信仰是传统政治权威的产物,是统治者根据其自身政治统治需要所“刻划”出来的“文化标志”。这种“标志”通常会增强统治者的权威,使之获得更多的服从。杜赞奇也提到,清朝统治者就曾采取了类似手段,其“鼎盛时的权势许多都来源于它有能力在大众文化中表现其权威,尤其是通过形象刻划的手段”*[美]杜赞奇:《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美]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鉴于乡绅所代表的宗族势力对乡村社会形成实际统治,各个时期的传统政治权威普遍选择加强与宗族势力的密切合作,并努力刻划或承认对宗族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标志。这客观上赋予了“龙脉”信仰的村落或宗族因素。
二、神秘主义:“龙脉”信仰的道德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是伴随着西方国家武力入侵及文化渗透而展开的,是外发而非内生性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中国文明逐渐遭到摒弃,而西方文明则时常被奉为经典。与此同时,国家政权也试图在农村社会构建新的政权基础和社会秩序,无奈其多次努力并未获得农村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相反,“在竭尽全力放弃甚至摧毁文化网络之时,其建立新的沟通乡村社会的渠道又进展甚微,这只能削弱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中共执政以后,国家也曾试图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打压传统宗族势力,并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然而,村落“龙脉”信仰却始终未因之消失。
仲村与宋村均属于典型的南方宗族性村落,两村相距约3华里,地处丘陵地带,同属J省S镇管辖。两村在解放前并无宿怨,但解放后由于争夺官塘水库及附近山地的所有权,两村关系开始恶化,一度剑拔弩张。在当地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是一块方圆约1.5平方公里的山地,其中约1/4是仲村的山地,其余则归属宋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公社领导决定在“朱家岭”附近建造养猪场,需要大量石材。于是,宋村人便向公社领导建议选择在自家“朱家岭”开采红石。其实,“朱家岭”所在周边地形特殊,整个山地地形宛如一条长龙,“朱家岭”正好处于“龙头”位置。据当地人介绍,沿着朱家岭顺势而下,正契合着仲村的“龙脉”,仲村的兴衰与“朱家岭”有着不解之缘。基于这个理由,仲村人坚决反对在“朱家岭”破土。然而,时值“破四旧”时期,公社领导最终不顾仲村的反对,决定在“朱家岭”破土取材。巧合的是,之后的几年里,仲村陆续有村民英年早逝,且多为分布在村落中间线两侧居民,一时间仲村人心惶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对宗族文化采取了排斥立场,基于族群意识而形成的村落“龙脉”信仰日渐式微,再也无法像传统社会那样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或认可。然而,由于历史久远与世代传承,“龙脉”信仰已经与村落融为一体,其对村民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在大多数农民看来,“龙脉”像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时刻守护着村落福祉和安宁。
村落“龙脉”信仰之所以对村民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与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长期被奉为“正统”,成为封建社会多数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化。然而,其他一些思想潮流如阴阳、道家和墨家等却并未完全销声匿迹。作为底层民众的思想代表,墨子始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天神观念的束缚,他积极提倡“天志”,仍将“天”说成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在墨子这里,“天志”是劳动群众的意志,但是封建统治者却借用了“天”的概念,并将自己说成是“真命天子”,从而使帝王权威更加富于神秘性。因此,在封建社会历史上,鲜有对帝王权威提出质疑的,否则就是“逆天而行”。而如三国时期红巾军起义、清朝末期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甚至还制造了“神”、“天”等神秘角色,以迎合中国农民的“神秘主义”心理。
“神秘主义”既包括表层的巫术、魔法性质的东西和占卜术,也指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前者在中国神秘文化中带有工具的性质,而后者则是中国神秘文化的内核。*秦学颀:《论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由于“神秘主义”的文化极为贴近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心理,农民更倾向于信奉“天命”、畏惧“鬼神”。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人们往往会对于许多合乎客观规律的事实做出种种“猜测”,将之归结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继而对之敬畏、迷信。
在前述仲村的个案中,尽管村民暴毙与破土取材行为并无事实上的必然联系,但由于取材位置正好契合仲村的“龙脉”,人们便自然地将两件本无关联的事情牵扯在一起,并对之进行各种猜想。这种现象,既说明了村民对科学的无知,同时也折射了农民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和敬畏。其实,对于神秘的“龙脉”,村民内心里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固然担心“龙脉”遭到破坏会影响村落命运,另一方面,其也深知“龙脉”信仰为国家主流文化所不容。站在“无神论”者的立场看,“龙脉”信仰宣扬的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与“无神论”者所秉持的宗旨是相悖的。
三、工具主义:“龙脉”信仰的制度环境
(一)从打压、包容到利用:“龙脉”信仰政策的变迁
自近代以降,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西方文化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逐渐渗入中国社会,民主、科学观念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各种乡土文化极力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然而,由于受到主流文化的打压或抑制,边缘性的民间文化生存空间十分狭小,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反科学的“迷信”,尤其是在“文革”那样的政治动荡年代,不少民间文化处境甚为艰难。虽然慑于“破四旧”运动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人们可能对损害村落“龙脉”的行为选择忍让、退避,但其却心有不甘。
然而,在常态政治秩序下,“龙脉”文化对农民心理和行为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政府无法视而不见的,它的存在必然制约着政府的治理行为。在前文提及的杨村案例中,由于建国后发生了多次土地变动及社区的分合,双方均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对这块11.53亩山地的权属主张,最后政府采取折中处理的办法,裁定杨村和黄村各分取一半土地。同时,鉴于争议地涉及杨村的“龙脉”,政府要求黄村不得在该地建房。后来,随着黄村人口增多,村内已无可供建房用地,便有村民欲在争议地建房,双方再次发生纠纷,官司打到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最终判决3/4争议地归属黄村。尽管如此,乡政府以可能破坏杨村“龙脉”、激化双方矛盾为由,坚决不同意黄村在争议地上建房。无独有偶,仲村“龙脉”信仰也对乡村干部的行为选择或价值判断产生了影响。2005年左右,仲村有人打算在“龙脉”所经之地建房,遭到绝大部分村民的坚决反对,便由村民代表向村委会和乡政府反映此事。最终,乡政府在了解此事缘由后,对该村民下发了停建通知书。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基层政府对待“龙脉”的态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政治压力较强时,它无法顾及乡土社会传统及农民的“龙脉”信仰,甚至秉承国家意志将“龙脉”视为封建迷信而加以打压;而当政治趋于常态、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较小时,基层政府更倾向于理解和认同村落“龙脉”信仰。可见,面对“龙脉”信仰,基层政府陷入一种矛盾状态:它既要主张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也要兼顾乡土民间文化;既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深知“龙脉”信仰对农民的深刻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乡村治理变得愈加复杂,基层政府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明显不足。有鉴于此,基层政府开始更为重视利用各种乡土亚文化提升乡村治理的能力,甚至视之为实现有效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
在杨村和黄村发生械斗后,政府对杨村采取了打压政策,其三个主要责任人均被判处死刑。但杨村尤其是被判处死刑者家属心中甚是不服,认为政府明显偏袒黄村。因此,家属便将死刑者的骨灰一直放在祠堂,以示抗议。为了劝服死刑者家属,乡政府求助于邻村的风水先生胡某,约定由胡某出面劝死刑者家属把骨灰埋掉。此时,恰好家住杨村祠堂对面的杨龙火老伴被蛇咬死了,胡某趁势劝说杨龙火,说是因为其房屋风水遭到骨灰的破坏,才导致家遭厄运。杨龙火觉得胡某的话有道理,便要求死刑者家属尽快埋掉骨灰。
上述个案表明,尽管基层政府对乡土文化并无价值倾向性,甚至认为后者有违国家主流文化,但在实践中基层政府却倾向于包容甚至利用这些民间亚文化。这就说明,一方面,受各种民间信仰的阻击,国家主流文化难以深刻影响乡土社会;另一方面,与高层政府不同,基层政府已经意识到“龙脉”、“风水”等民间信仰对传统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并逐渐对之采取包容、开放的姿态,甚至还顺从和利用各种民间信仰,以便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目标。
(二)一致与冲突:政府内部如何对待“龙脉”文化?
从整个国家治理系统来看,乡镇政府是直接面对和接触农村社会及广大农民的最基层政府,是国家治理系统的末梢。相对于上级政府尤其是高层政府而言,广大基层干部置身于农村社会,他们更为了解和深刻体会农村社会现状,对农民的“龙脉”信仰则经历了从压制到包容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国家治理系统内部对待乡村“龙脉”文化的一致与冲突。在人民公社前后,为了实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目的,国家利用政治力量将触角伸展至农村社会的最底层,试图从社会结构、文化标志乃至内在信仰等方面对农村社会及农民进行彻底改造。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系统末梢的乡镇政府的前身——人民公社无疑首先遭到整合,彼时整个治理系统高度统一。然而,随着国家政治动员能力的弱化,乡镇基层政府的离心倾向开始显现,甚至蜕变为国家治理系统的“梗阻”。事实上,乡镇基层政府不仅与上级政府存在利益冲突,且在价值取向上,其也表现出了显著的相对独立性。
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后,二审法院终于通过再审终审判决,将争议地几乎全部判给黄村。当黄村小组组长熊清明手持判决书向乡(镇)政府提出建房申请时,立即遭到了拒绝,唯一理由是建房可能破坏杨村的“龙脉”。面对这一结果,黄村不甘心,便再次向上级土管部门请求批准建房,上级土管部门认真查看了法院判决书及其他有关材料,认为完全符合建房申请条件,便批准了黄村的建房申请。
从整个土地审批程序看,两级政府土管部门决定是否审批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第一,该土地权属是否清楚,申请人是否拥有该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第二,该土地是否属于国家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如耕地)。而对于乡镇政府做出“不批准建房”决定所依据的“龙脉”因素,则始终未能进入上级土管部门的视野。可见,乡镇基层政府与市县两级政府所做出的决定及其支撑依据泾渭分明,充分表明了政府体系内部对“龙脉”信仰取舍不一。
乡(镇)基层政府这种文化取向上的相对独立性,与之处于治理系统的“末梢”不无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主流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影响是伴随政策输入而发生的,因此,文化渗入同政策输入一样,也会产生一个“末梢”效应。随着文化传递层级的递减,国家主流文化对各级政府行为的影响也呈递减之势,及至基层政府,主流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变得更弱;另一方面,从乡镇干部个体来看,尽管大部分乡镇干部归属于体制内,具有所谓的“国家干部”的身份。但由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嵌入性,乡土社会庞大的文化网络不仅对农民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乡镇干部的行为和观念。
对于乡镇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在“龙脉”信仰方面的矛盾,似乎没有谁比农民有着更深的感悟。无论是在杨村或是仲村,当村民向村委会或乡镇政府主张权益时,他们敢于直白“龙脉”的说法,而当面对上级政府时,其诉求理由则明显发生了变化,转而从各种证据入手寻求政府支持。可见,他们也深知“龙脉”信仰难以获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与认同。
四、余论:合法性与乡土文化的前途
在传统农村社会里,大多数农民基本处于拥有共同文化基础和心理认同的社区边界内,受其所生存的社区文化制约,他们“从出生到死亡,人们就一直嵌入在文化的背景当中,这种文化背景为他提供了信仰体系,帮助指导他们的行动,并向他们灌输意义和提供领悟力。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孤立的文化行动者,因为他们还嵌入于结构的背景当中,这一结构背景形塑了他们的行动,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美]艾尔东·莫里斯:《政治意识和集体行动》,[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秦明瑞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9页。。中国农民并非没有信仰,只是他们不像西方基督教徒那样拥有规范性或制度性的宗教信仰,相反,在一些农村地区,“龙脉”观念却以一种“文化嵌入”的方式对农民心理和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根据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理论,国家起源于社会,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信赖。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针对基层政府的抗争事件频频爆发,大大削弱了国家在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并形成了乡村治理的“结构阻力”*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其实,“结构阻力”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中央——地方——农民”,这一分析框架改变了原先“国家——社会”的简单二元对立,揭示了科层体制内在的紧张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结构阻力”的判断确实指出了政府层级之间的矛盾,但却相对忽略了政府科层体系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利益冲突,如农业税费的收取与抗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文化冲突方面。由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两者之间的张力似乎无法避免,且这种张力一旦超出一定限度,势必损害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尽管“龙脉”信仰具有边缘性,但作为一种嵌入式的文化传统,其对农民心理及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故从文化层面看,“不能与人们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或是仍然保持意识形态的“去生活化”的趋势,难以形成有效的文化治理能力”*丁长艳:《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秩序建构与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相反,弥合文化之间的冲突,构建适当的“文化标志”,不仅维护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也有利于彰显文化治理能力,顺利实现乡村治理目标。从当前国家文化战略看,尽管不像“破四旧”时期那样对各种民间亚文化实施毁灭性打击,但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却是非常明确的,主流文化与各种民间亚文化的关系依然紧张。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政治运动的推动作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传统宗族意识开始复苏并对农村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且各种宗教思想正以组织或非组织的形式广泛传播,农村社会呈现多元文化博弈态势。在实践中,类似杨村案例中基层政府对法院判决的“变通”现象,无疑折射了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信仰之间的冲突。同时,它也表明,尽管“龙脉”信仰并未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接纳,但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却不容忽视,而这正是严格的“法治主义”者所忽略的。
[责任编辑龙圣]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城乡社区信任与融合研究”(14BSH054)和江西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社区信任研究”(SH14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邱国良,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