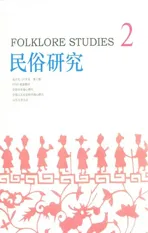神话的文化解读——从涿鹿之战看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
2016-02-03张和平
张和平
神话的文化解读
——从涿鹿之战看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
张和平
摘要:华夏文明是由两大不同类型的区域性文化融合而成的。由于这两大区域性文化在内在精神上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融合必然会充满了冲突与纷争,同时也决定了由这两大区域性文化所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必然是一个在其自体内部存在深刻矛盾的文明,而所有这些冲突、纷争与矛盾也就构成了涿鹿之战背后的历史真相。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涿鹿之战实际上是一个内含着华夏文明发生、发展及其内在特质等多重历史信息的神话符号。
关键词:涿鹿之战;华夏文明;原始圆满;自然情结
中国古史(或即中国上古神话)由于存在“层累地造成”的缘故,曾被学术界长期视为缺乏历史可信度的“伪造的历史”①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二”,中华书局,1988年。。对于这一看法,尽管拥有考据学方面的多重证据,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毕竟不能只在考据学的层面上理解古代神话的真实性。随着文化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当古代神话作为一种解释系统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其便开始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它另一种层面的历史真实性:一些外观显得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或许正内在地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原始信息甚或人类文明(文化)运演的真实轨迹。换句话说,上古神话决不能仅仅以“伪造的历史”一言了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它所具有的解密历史的特殊价值。
涿鹿之战,是相传在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炎帝与黄帝之间展开的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历史上,最早提到炎黄之间有过战争的是《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性则异德,异德则异类。”炎黄二帝因“异德”之故而“用师以相济”,至于二帝“异”的是什么“德”,《国语》并没有作更具体的交待,这就使我们对战争的起因及性质难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过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相关文献中被再度提到时似乎有了答案。马骕《绎史》卷五《黄帝纪》有载:“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仁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这一颇为人知的说法很容易让人对战争的性质作这样的归结,即炎帝的暴虐不仁导致了他与以“行仁道”为职志的黄帝之间的战争。对战争性质的这一认定尽管有力地呼应了战争的最终结果——正义战胜了非正义,但问题是暴虐不仁的炎帝后来何以能与黄帝一道被尊奉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再者,传说中的炎帝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主要事迹都尽显“仁慈”者的风范②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第70页。:教人制作耒耜、种五谷,为民求雨,尝百草为民治病,甚至最后为此献出了生命。说炎帝暴虐不仁,实在是于情于理俱有未安!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后人将不肯“行仁道”这样的评价加在炎帝身上的呢?围绕着行不行“仁道”而展开的涿鹿之战背后是否存在人们尚未解读的历史真相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天道”与“人道”之争:涿鹿之战的起因
作为传说中一位功德无量的古圣帝王,炎帝的精神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按理说,对于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再出现“不行仁道”之类说法的,除非“不行仁道”另有含义。稍作检索即可发现,道家学说中就存在与暴虐不仁含义完全不同的“不行仁道”。按《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若换一种说法其实就是“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德”恰恰是“上德”,“不仁”反而成了“大仁”。复按《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学术界,人们一直对老子何以将“天地”与“不仁”联系在一起很是费解。对此,王弼的解释就深得个中三昧:“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可见,这里的“不仁”恰恰就是道家所推崇的顺应自然、杜绝人为之义。可以说,正是在道家这种“正言若反”式的特殊表达方式中,文献中有关炎帝精神形象看似不合逻辑的表述才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统一:炎帝之所以不肯“行仁道”,是因为他要追求更为根本的“仁”。由此看来,首先给炎帝贴上“不行仁道”标签的极可能就是道家或道家者流。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因为炎帝的精神形象正是人格化了的道家之“道”。有鉴于此,故而在具有明显道家倾向的《淮南子》中,炎帝及其所象征的那个时代竟被描绘得如此的妙不可言: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弛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7-138页。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原始和乐图!而这一图景我们几乎能在所有的道家著作中读到,因为它寄寓了道家对人生及社会理想的至高企盼——道(或即“大仁”)。可以说,在道家的社会理想中,正是由于道的无处不在与无损无亏,才造就了无往而不自得其乐的至美人生与至善社会。也正因为如此,故主张“无为而治”的庄子才对他心目中的“神农之世”这样深情地说:“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庄子·胠箧》,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而同样具有道家倾向的《吕氏春秋》也有相类似的表述:“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然而,这一纯粹而至美的生命样态自从人类有了智谋机巧,以及随即而至的人为安排的是非善恶——尤其是文明器制世界——的出现而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最终导致道亏朴损,生命的昔日美满与原始和乐也就因此而“不复有其初”*《庄子·缮性》,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了:“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42页。从此,人类只能在他们的生命境遇中面对这样一个每况愈下式的递进阶梯:道→德→仁→义→礼。至礼义一出,社会便由此全面进入混乱不堪的所谓“衰世”。对此,《老子》第三十八章曾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对此“衰世”的成因和具体形成过程,《淮南子·本经训》也曾作如下表述:
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有鉴于此,我们对于炎帝为何坚决不肯 “行仁道”也就不难理解了:“仁”者“人”也,故“仁道”实即“人道”。“人道”乃是相对于“天道”而言的,是“天道”的一种堕落形态。如此,作为原始圆满化身的炎帝无非是割舍不下原始圆满的“天道”,进而堕入由“天道”至于“人道”(仁义)这样一个每况愈下式的递进阶梯,最终将生命领入一个“往而不返”的机械器数世界。事实已经证明,炎帝所信守的这一“通治”之“道”已难以应对日趋浇薄的“衰世”的治理:“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汉)刘安:《淮南子·泛论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即便如此,以原始圆满为职志的炎帝仍旧不肯轻言放弃,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通治”之“道”沿着每况愈下的递乱过程一直堕落下去。相比较而言,面对同样的问题,作为炎帝同母异父兄弟的黄帝似乎就显得现实多了:既然“通治”之“道”已经被证明难以应对“衰世”的治理,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采用“救败”之术了。换句话说,既然内外尽治的“通治”(或即“无为而治”)已经难以企及,那么追求以机械器数为手段的外治之术(即“救败”之术)也就成了虽属无奈但却合理的选择:“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君臣上下之人,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战国)商鞅等:《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7页。黄帝的这一心路历程,若是采用《礼记》一书的诠释方式,其具体表述也就成了:既然“大同”之世已经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那就只能退而求其“小康”了;尽管“小康”之世充满了太多的人伪与自私之诈,但毕竟也是一种打了折扣的“治世”。如此一来,主张 “行仁道”的黄帝与不肯“行仁道”的炎帝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甚至爆发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通过对道家学说内在理路的疏通,我们不仅弄清了涿鹿之战的起因,同时也大致知道了这场战争的基本性质。就是说,由“通治”之道(“天道”)与“救败”之术(“人道”)所引发的涿鹿之战,其实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复古主义与维新主义之间的分歧与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即“救败”之术(“人道”)对“通治”之道(“天道”)的胜利。尽管这场战争的胜负结果事先就已经是注定了的,因为相对于“通治”之道而言,“救败”之术更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但这场战争似乎又很难剖白其是非曲直,因为人们习惯上总是会对注定要失败的幻想主义者给予更多的同情和赞叹。尽管“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几成千古同叹,然道家对炎帝精神的认同却有别于通常意义上一个局外人对幻想主义者不幸命运的同情,因为道家本身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幻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但是,令道家无比陶醉的这一切——昔日田园诗般的温馨——都随着“行仁道”的黄帝的最终胜出而宣告结束。就此意义而言,也许在道家的历史记忆中,没有任何一次历史事件能够像涿鹿大战那样让他们的灵魂受到如此大的触动:“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其实就是黄帝与炎帝之战,详见下文),流血百里。”*《庄子·盗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从而使得黄帝在道家的眼里简直成了陷人类于无穷灾难的始作俑者:
昔者黄帝以仁撄人之心……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浪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庄子·在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浑沌一破,民智既开,后来者必将从而加其厉;至于尧舜之世,遂成乱阶,“人间世”从此也就成了角智者与角力者们作殊死决战的人间地狱——道家如此继续着他们对黄帝及其事业继承者们的申讨:
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230-231页。
在众多中国古代文献中,人们几乎看不到对于炎帝的非议之词,至于黄帝及其事业继承者尧舜,通常人们所见到的多半也都是赞美之词,唯有道家是一个例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正是在道家思想中,炎黄大战才真正像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或者说,道家思想中的内在张力正好对应了炎黄之间的对立与纷争,因此由道家来向人们诠释这场战争的空前悲壮与异常惨烈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二、南北文化及南北民性之争:涿鹿之战的文化背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了涿鹿之战是直接起因于“通治”与“救败”之争。弄清这一点固然是很重要的,但还不够,因为这一纷争背后其实还蕴藏着更大的文化背景,这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华夏文明主要是由分属于两大不同系统的区域性文化组成的,即由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北方文化)与属于长江流域的吴楚文化(南方文化)组成的,对此史学界曾经用“史官文化”与“巫官文化”来表述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的内在差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5页。具体而言,史官文化是一种实用性文化,它强调的是外在生活世界的合事实性;巫官文化是一种信仰性文化,它强调的是内在心灵世界的合感悟性。这两大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相对独立发展而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而这恰恰成了日后彼此间多重矛盾与冲突的导火索,同时也是引发涿鹿之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汤因比在谈及中国古代文明何以率先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他说:
让我们先举中国的这两条大河下游地区的不同困难情况为例。看起来好像是当人类最初接触到黄河下游的澎湃浊流时,这条河在一年四季都是无法通航的;在每年冬天它或是结成了坚冰,或是塞满了浮冰,而每年春天冰融解了的时候又发生破坏性极大的洪水,使得黄河不断地改道,造成了新道,而旧河道则变成丛林密布的沼泽地带。甚至在今天,在人类已经经营了三四千年,弄干了沼泽,修筑了大堤之后,洪水的祸患还是未能完全免除,一直到1852年,黄河下游还改过一次入海的河道,从山东半岛的南方移向它的北方,两条河道的距离在一百英里以上。而在另一方面,长江却是一直通航的,它的水患,虽然也偶然成灾,可是比黄河却少得多了。除此之外,长江流域的冬天也温和得多。然而古代中国文明却诞生在黄河岸上而不是诞生在长江流域。*[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汤因比的上述观点尽管并不全面(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其实是分属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明类型,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多的只是不同的区域性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地存在文明与非文明的问题),但他的观点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即必须充分考虑到环境因素对文明形成所构成的深刻影响。
的确,与生存环境相对严酷的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的生存环境要优裕的多。对此,《汉书·地理志》曾给我们作了这样的交待:“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 ,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这样的生活不仅塑造了相应的地方民性,也孕育出了与黄河文明颇为不同的长江文明:富于浪漫与幻想,神奇瑰丽,较多地保存了远古社会的信仰及生活方式。所以从总体上说,吴楚文化乃是一种高度心灵化的文化,其中不仅蕴含了大量神秘感动的成分,而且还保留了那份原始朴素与自由奔放的诗性风格。南方民性及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随意其表、精审其中的特性,一如干宝在《搜神记》中所表述的那样:“蛮夷者(蛮夷,古代南方人之统称——引者注),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南方文化的这一特性也就成了李泽厚先生引出如下结论的基本依据:“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艺审美领域,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而在北中国的广大地区,由于生存环境的相对严酷,如何生存下去便成为居住在这里人们的首要任务,为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以牺牲生命的自然情性为代价来赢得他们所需要的基本生存保障。这便是黄河文明形成的环境背景,因此实用理性也就成了黄河文明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并进而使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们形成了相应的性格定型。鲁迅先生曾对此作了这样的表述:“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鲁迅:《神话与传说》,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页。就是说,在实用理性主导下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它较少追求现实之外的玄想,而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中日用人伦的合规范性和合条理性,并以此最大可能性地组合社会的力量去迎接生存环境的严峻挑战。在这里,生命必须接受某一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制约,情感必须服从于理性,个性必须服从于社会性。这些最终都成为黄河文明内在精神的具体体现,即它体现在“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7页。。故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率先(或较早)诞生于黄河流域决不是偶然的。
上述两大文明类型都曾经孕育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即属于北方文化的儒家学派与属于南方文化的道家学派。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两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孟与老庄分别来自两大文化圈,更重要的还在于两家思想所内含的精神格调与彼此所代表的文化类型是一脉相承的。对此,刘光汉先生总结道:“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限,而学术所被,复以山国、泽国为区分……山国之地,地土硗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故学术互异,悉由民习之不同。”*刘光汉:《南北学派不同论》,转引自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页。所以《论语·述而》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孔子很少谈到怪异及鬼神之事。“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鲁迅:《神话与传说》,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页。,从而表现出了实用理性精神所特有的清醒态度。
儒家思想有一条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强调社会利益大于个体利益、个性情感必须服从社会规范的制约,因此儒家主张“礼”宣扬“仁”。与孔子不同,道家的老子则主张要顺物而行、因性而动,就是主张要顺乎性命之情,依照生命的内在本然来安顿人生的最终归宿。为此,老子再三强调,不要对个体谋求个性自由发展的行为施加任何人为因素的干涉,要让生命在“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中实现其内在本性所固有的“善”*《老子》第五十七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并进而使社会成为无官长、无统属、小国而寡民的田园诗般的国度,这与孔子主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正己正人的观点大异其趣。故而,在老子的笔下,我们就不可能见到那一套了。相反,他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第十九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0页。却成了标志道家思想内在精神的一个招牌性的话题。而在庄子那里,道家更是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一种高度心灵化的人生追求。在这里,生命已经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肉体躯壳,而是展现为神秘的情性体验与精神感动。故庄子主张要遗其粗(外在的世俗世界)而取其精(内在的心灵世界),否则就是对生命真实含义的颠倒:“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在道家看来,儒家就是这一价值颠倒的典型,因为他们所宣扬的“仁道”就是典型的以物异性、以外遗内:“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庄子·渔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对此,儒家的态度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识其二;治其内不治其外……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庄子·天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不过,与较为偏激的道家相比,儒家的态度似乎要客观一些,因为他们在宣扬北方文化精神的同时,多少还是认可了南方文化精神可取性的一面。但即便如此,儒家依旧认为南北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之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礼记·中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
儒道思想以充分演绎化与表述化的形式彰显了南北两大文化之间的差异。如果说这种差异落在表述性层面所引发的纷争,其适当的表现方式往往不过是“口诛笔伐”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运演过程,其最常见的历史场景极可能就是“刀光剑影”了。既然如此,那究竟该由谁来代表双方打这样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呢?当然是作为两大文化圈最高统治者的神——炎帝与黄帝最有这样的资格。因为在神话传说中,黄帝向称“中央之帝”:“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7页。“中央”即“中原”,其在古代与“中土”“中州”“中国”“中华”义皆大同小异,泛指黄河文化圈。炎帝作为黄帝的同母异父兄弟,他的主要事迹几乎都留在南方*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65-269页。,即留在了属于江、汉、湘水流域的长江文化圈,故有关炎帝的传说往往都是以“南方之帝”的形象出现的:“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汉)刘安:《淮南子·天文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页。,“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初学记》卷九,转引自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有鉴于此,这场关涉到华夏文明最终命运、即由南北文化的对立与纷争走向融合与统一的大决战,由炎黄二帝来充当战争双方的主角就显得既自然又必然了。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炎黄大战(涿鹿之战)视为承载着南北两大文化激烈纷争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的人们所熟悉的仅仅是这一符号纯形式的东西,而符号背后所承载的历史真相反而变得依稀难辨了。不过,依稀难辨不等于毫不可辨,比如文献中将炎黄大战归结为行不行“仁道”之争,其实就已经接近于历史真相了。因为尽管行不行“仁道”之争并不能反映南北文化之争的全部,但它显然是南北文化之争中最核心的环节。惟其如此,我们方能理解道家精神何以会与涿鹿之战的炎帝方有那么大的亲和力,而儒家精神却与黄帝方(确切地说应该是黄帝事业的继承人尧舜)有那么大的亲和力。*比如属于儒家著作的《周易·系辞传》就对炎黄易代之际的变革给予了充分肯定性的表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与道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据此我们不妨说,涿鹿之战其实就是变换了形式的儒道之争或南北文化、南北民性之争。
三、涿鹿之战:华夏文明内在矛盾的反映
涿鹿之战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这个问题尽管已无从考证,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对由这一神话传说所演绎的历史真相已经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不过,有了这样的认识依然不够,因为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南北文化之争随着熔南北文化于一炉的华夏文明的最后形成,其纷争的主体便开始由不同文化族群内化为华夏文明的内在矛盾,即内化成了诸如天与人、阴与阳、动与静、内与外、身与心、知与行、虚与实、质与文、野与史、本与末、方与圆、进与退、刚与柔,或即自强不息与清静无为、机械器数与原始朴鄙、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身在江湖与心存魏阙、内圣与外王、遁世与救世、自然与名教、出仕与归隐、入世与脱俗、人治与法治、理则与权变、大本与达道等等方面的矛盾与对立。这些矛盾与对立内在于中国人的心灵中,体现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表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中。就此而言,作为演绎这些矛盾与对立的涿鹿之战,不仅是一场胜负难分的绵延之战,甚至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永恒之战。
中国历史自从进入文明器制的时代以来,其阴性的一面(也就是对原始朴鄙生命样态的留念及回归情结)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人们还普遍认为理想的社会就应该是二者的协调与冲和,也就是“天(指自然朴鄙)人(指文明器制)合一”。这就像《老子》所表述的那样:“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生活在器制文明时代的古代中国人,他们的身(有形的生命)尽管属于这个器制文明的社会,但他们的心(无形的生命)却依然暗恋着那份原始古朴的温馨,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中国人一直延续着这个古老的梦,而且这个梦似乎总是以一种类似生存本能的形式提示人们:人类是不宜在器制文明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的。这种对器制文明的警觉、矛盾乃至不信任的心态,在庄子笔下被表述得淋漓尽致。《庄子·天地篇》曾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农夫,这位农夫自称他虽然知道机械巧作的用处,但他更清楚机械巧作的害处,因为有了机械巧作就会产生“机心”,有了“机心”就会纯白不备,就会有损于人的原始纯洁性。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他们一直死死地盯住人的这种原始纯洁性,而对与之对立的种种物化形式(即器制巧作)总认为是畏途,是“奇技淫巧”,是导致人性异化、人而不“仁”的最大危险。为了强调人的原始纯洁性,所以就要让它永远以突显的形式存在,务必不使种种物化形式淹没它,更不能取代它。在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的原始纯洁性看成是一个圆心,而把外在的物化形式看成是包围于其外的圆体,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器制文明有时也像圆体一样显出有些外拓的迹象,但那只是稍尝则止,固有的民族心理很快就会使这个好不容易展开的圆体再次归缩成一点(即圆心)。这个点就是古人一直推崇的“中”,所以《老子》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尚书·大禹谟》亦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种矛盾的心态难道不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残酷战争吗?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之一,然而内含在民族心灵深处的原始情结却使得这一文明之路总是显得那么的一步三回首,于是对文明前程缺乏足够信心以及使文明打上过多人性化色彩便成了华夏文明的特有标识之一。故而像如下这般对器制文巧世界忧惧有加的言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有其深刻文化背景的。对此,《淮南子·本经训》曾曰:
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殊]甘苦,则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未]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智]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法律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相传中国很早就有了“刑”与“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海潮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然而,与西方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人对外在的法律制度明显缺乏信心,他们似乎更看重人的内在心灵准则,进而使中国传统社会显现出明显的“人治”色彩,重“人”不重“法”成了华夏文明的显著特征。所以在中国古代,判断一个时代是不是“治世”,主要是看有无“治人”,而不是看有无“治法”,所以《荀子·君道》说“有治人,无治法”。而一向被人们奉为“治世”典范的上古时代就是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一,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21页。因而在本末关系上,“法”被看成是“械数”,是治之末,而“人”则被看成是“治世”的根本,是“治之原”。“治人”之存亡是政之息举的关键:“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9页。正是出于对内在心灵准则的信任与执守,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更像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柔性体系,人性化与适度化左右了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使其显得刚中有柔、严密中又充满了人情味。这就是李约瑟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原因,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反对法典化的倾向;审理案件坚持就事论事,强调妥协与和谐……上古和中世纪的中国人懂得法治的原则,但是他们有意识地采取平衡的原则”,“在中国人思想上,‘公正’的观念(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比‘成文法’的观念更重要得多。好像‘法律愈多,为害愈甚’这一类的成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是很难以理解的。阿瑟·韦利说得很好;他说,一个中世纪的中国县官,如果他内心意识到自己作了不公正的判决,他退出法庭时决不会因为自己忠实地引用了当地的法律条文而感到庆幸”。*[英]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4、77页。如果说法治化即意味着文明与进步,那么古代中国人似乎便是有意无意地在延缓着他们的文明脚步。就这点而言,你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注定是“早熟而又不成熟的”或“死的拖住了活的”*傅衣凌:《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也可以说中国人一直都是处在人类进化历程的“婴儿时期”*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或认为中国人属于“大洪水前的人”*[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36页。,甚至还可以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是“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象孩子一样的生活”*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总是要在内与外、进与退、出与入之间作两难抉择。一方面,他们既无法抵挡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生三不朽”的诱惑,并千方百计地为使自己最终能成为经邦济世的国家栋梁而皓首穷经;另一方面,他们又每每对自然适意的生命样态恋恋不舍,对原始纯朴的心灵生活羡慕有加。到底是退守心灵还是外求功名,抑或到底是出而经邦济世还是入而自乐其身?可以说,正是这两种相反方向的意志力不断地考验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进而使他们每每会从心底里发出类似于范仲淹那样的感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转引自《古文观止》卷九,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象陶渊明那样因退的意志力战胜进的意志力而归隐田园的人不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具有与陶渊明同样精神气质的人不多,而只能说更多的人乃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第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都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这就像他们经常被描述的那样,多半都是些“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之人。第二,正是自然情结造就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对此林语堂先生的相关表述可谓入木三分:“平静与和谐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它们源于中国艺术家的心灵。中国的艺术家是这样一个人:他与自然和睦相处,不受社会枷锁束缚和金钱的诱惑,他的精神深深地沉浸在山水和其他自然物象之中”,“正是这种平静和谐的精神,这种对山中空气‘山林气’的爱好,这种时常染上一些隐士的悠闲和孤独感的精神和爱好,造就了中国各种艺术的特性。于是,其特性便不是超越自然,而是与自然相融合”。*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4、256页。由于有了这样的艺术精神,也就难怪制造这种精神的专门场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书斋——往往会被冠以这样的称呼了,如“养心斋”“陶庵”“陶庐”“休休室”“茶香室”“庸闲斋”“慵庵”等。而书斋的主人相应地会有这样一些别号,如“江湖客”“××浪士”“××狂生”“××居士”“××山人”“××散人”“××散櫵”“××漫叟”“××野叟”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在心灵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将精神生活艺术化这一特殊手段,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内求心灵与外求事功的所谓“内圣外王”的道路上找到了某种平衡的支点,但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表面现象,很多人最终还是不免要像范仲淹那样难以坦然地面对人生际遇中的进退之道,始终无法将他们认为是象征生命本真样态的闲适、恬静、淡泊与从容从他们的原始记忆中抹去:“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明)洪应明:《菜根谭·应酬》第157条。,“峨冠大带之士,一旦睹轻蓑小笠,飘飘然逸也,未必不动其咨嗟;长筵广席之豪,一旦见净几疏帘,悠悠然静也,未必不增其绻恋。人奈何驱以火牛,诱以风马,而不思自适其性哉!”*(明)洪应明:《菜根谭续遗》第105条。之所以会如此,因为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这一内在情结,本质上不是一个生活艺术或生活技巧的问题,而是由夏华文明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问题。
四、结语
神话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既可能是历史真实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可能是历史留在人类原始记忆中的一个印迹,还可能是象征人类精神运演过程的一个文化符号。从种种迹象来看,涿鹿之战所内含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不过,就其所演绎的历史真相的生动性而言,它更可能是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人们可以认定涿鹿之战是一场虚构的战争,但它似乎又的确发生过;也许它并没有发生在历史的实际过程中,但它的确曾经而且一直发生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而且事实上,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再也没有将从原始完美向文明器制过程这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说成是一场惊天动地且又绵延不决的战争更能表达他们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态了。至于道家,我们把它确定为涿鹿之战话题的主要传播者是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原始情结的根主要是来自道家所在的长江文化圈,之后又随着这种文化精神融入到整个华夏文明之中,进而使其成为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格调的。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人是最具道家气质的,这也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页。亦如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英]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责任编辑王加华]
作者简介:张和平,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