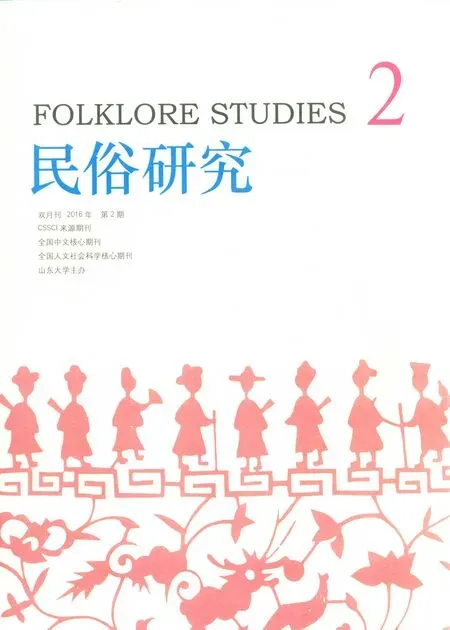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2016-02-03郭俊红
郭俊红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
——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郭俊红
摘要:“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关键词:丁戊奇荒;身体叙事;阳城县
众所周知,“丁戊奇荒”是指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干旱引起的华北地区大规模的社会灾荒,这次灾荒持续了四年,受灾地区主要包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此次灾荒,因灾情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被称为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后世学者将灾情最为严重的山西视为重点研究对象,产生了很多以山西为研究个案的“丁戊奇荒”研究成果。①具体如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时限和地域》,《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郝平、周亚:《丁戊奇荒时期的山西粮价》,《史林》2008年第5期;韩祥:《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谢忠强:《官赈、商赈与教赈:山西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等等。纵观已有研究,要么从灾荒本体角度入手就灾言灾,对灾荒发生原因、发生规律、发生频率以及灾后救助进行研究;要么属于因灾生灾范畴,主要讨论灾荒带来的次生灾害,包括瘟疫、虫鼠灾害以及灾荒对社会秩序、伦理、文化、经济、政治、民风民俗等各方面的破坏,而对正在经历灾荒的民众身体以及灾荒中民众对待身体的态度却缺少关注。
生理学的身体指一个由骨骼、肌肉、内脏和五官组成的实体。而作为学术研究的身体,更多与人类政治、文化、经济紧密相关,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身体,是指向人类社会存在方式不可或缺的标示。在西方,最早将身体纳入视野的是哲学研究者,他们对待身体的态度是贬损和不屑。其后,随着尼采、梅洛·庞蒂、福柯等哲学家对身体的重新认识,学界对身体的看法才逐渐发生转向,身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由于福柯的日渐流行,对于尼采重燃的兴趣,以及海德格尔持续的重要性共同使这些年有关身体的书近于泛滥”②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由此,借助身体揭示和认知社会习俗、规范乃至文化的建构性,成为许多研究者的选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丹尼尔·潘戴所开创的身体叙事研究开始兴起。这一研究试图把身体与叙事学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对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场景的影响及叙事中的身体体现,成为当前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只是,早期身体叙事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领域。此后,由于叙事载体的多样性,身体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不再只局限于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叙事作品,而是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只要能够完整呈现故事的文化产品均可进入身体叙事学的研究视野。*许德金、王莲香:《身体、身份与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借鉴“身体叙事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那些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碑刻中记载的灾民遭受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民众对待身体的态度变化为考察对象,将丁戊奇荒中阳城普通民众的身体重新放入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过程。
一、碑刻内被书写的身体
19世纪70年代,当法国哲学家尼采将目光投向人的身体、强调人的身体与灵魂同等重要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国华北地区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身体却正在饱受饥饿、疾病乃至死亡的痛苦。各种痛苦混杂聚集在民众的身体之上,使鲜活的生命、健壮的身体瞬间化为冰冷的尸体。命如草芥的身体能在这场灾荒中存活已属不易,遑论与灵魂平起平坐。与西方哲学家从思想上呼唤身体不同,东方华北地区的民众则是身体力行,通过真实的身体感受与变化,发现了人的肉身对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山西阳城位于晋豫相交地带,属于此次旱灾的重灾区。阳城县从光绪元年就渐露旱象,至三年更为严重。“光绪三年春季,雨泽旱少,自三月底得足雨一场,将谷种上。四五月无雨,夏麦均收不上一斗,晚田未种。各村社日日祷雨,至六七月仍无寸雨。下种者不止二三次,全未见苗。”*(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持续的旱灾导致粮食绝产,粮价腾高,普通民众既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也没有足够的货币购买粮食,因此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的身体。人的行为与个体的身体感受直接相关,民众对待身体的态度随着个体身体的饥饿程度而不断变化。在灾民眼里,身体(包括动植物)已经被区分为自我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这两种身体随着灾荒的加剧逐渐发展成为“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对立关系。
光绪三年之前,灾荒还不是特别严重,粮食虽减产,但民众还可以找到一些替代性食物,如树皮树叶、草根石髓等。“树皮草根其稍可入口者,莫不资以度命。禹粮石髓,即意想难到者,无不借以充饥”*(清)杨叔雅:《重修葺社庙碑记》,润城镇下庄村,光绪十六年。,“核桃柿不时而混摘充饥,榖黍稷半熟而强窃度命,草根挖尽,树叶遍尝,剥榆皮共蚕砂以延生,拾柿蒂和荆籽以求活。种种苦菜不堪尽述”*(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未熟之瓜果连蒂而吞,初秀之谷穗带糠而食”*(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相关记述碑刻中比比皆是。但随着旱情加重,这些非正常的食物也被消耗殆尽,捋荆子以疗饥,剥榆皮而充腹,桑叶柿叶待食而尽,开始出现了“野无青草,秋禾未登一粟”的局面。加之当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阴历九月天气便突然转冷,民众毫无御冬的准备,“个个哀鸿几泣,谁怜楚女之腰,人人鹄面鸠形。渐至天气寒冷,外无粗衣以御寒,内无淡饭以充饥”*(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
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以意识形态和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为据,归纳出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以及医学身体这五种身体形态。*[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但这种划分显然与西方社会、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相关,与我国的国情并不相符。因此,本文试图以性别、阶层、文化、身份等为标准,对灾荒中的身体进行区分。灾荒发生时,植物、动物乃至同类的身体都成了维持生命的食物。身体不再是鲜活的生命体,而仅仅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拥有别人的身体就等于拥有了存活下去的食物,于是争夺身体的战争弥漫于男/女、长/幼、生人/熟人、富/穷、官/民和人/物之间。
(一)男/女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将女性排斥在外,因此女性从出生起就已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人身完全依附于家中的男性,毫无自主人权可言。即使正常年景,卖掉自己的女儿以缓解家庭生存压力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女婴直到婚龄的女儿都可能被出卖。贫困加上“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的观念,也使得父母倾向于提前将女儿推出家门。当遭遇灾荒这种非常情况时,卖掉女儿或者以女换粮的事情则更是寻常不过的事情。女性成为每个家庭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二八佳人沿街卖”“鬻妻卖女”“无奈将少年妻女出卖外县”,此类记载不胜枚举。但大灾之下,即使已价如草芥却仍几乎无人购买,甚至出现了不要钱的情况:“妇女见了男人追着高声唤:‘叫声大哥你等等吧,我给你铺床叠被管做饭。’男子吓得撒腿跑:‘我没有吃的养老伴。’”*阳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阳城县志》,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432页。面对饥荒,女性的身体不再是男性垂涎的对象,反倒成为躲之不及的累赘。
传统社会中,女性服务于男性的最原初资本就是提供性服务。女性的年龄以及美貌等身体条件成为提供性服务的限制性因素,年轻美貌的女子可以凭此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但在灾荒中,这变得毫无价值,“很美丽的女人,不值一串铜钱,很年轻的闺女,即三升小米也没有人给”*(清)贾杶:《光绪三年的记荒碑》,凤城镇北安阳村,光绪七年。这通碑勒石于清光绪七年,但通篇白话,简化汉字,且有标点,疑为后人所刻。。饥肠辘辘的女子也完全忘却了平素礼义廉耻的道德教化,自行主张随便委身于可以提供食物的男性,“自行嫁人昨李今张”*(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崩塌。在家庭内部,丈夫和妻子也完全丧失伦理道德意识,凭情爱维系的恩爱夫妻仅视对方为果腹的食物,而女性较男性生理上的先天弱势,或被转手他人或被残忍杀害,使之成为家中男性的充饥食物。灾荒中大量女性的死亡和被贩卖他方,使得山西省区的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灾后人口的恢复。
(二)长/幼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指出,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或更成功地维持自身的繁衍。*[美]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陈午晴、唐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但面对灾荒,年幼的后代往往成为被舍弃的对象。中国人关于女儿在祭祀祖先中无用的种种说法,使得大量女婴或者幼女被出卖或者杀死也就不足为怪了。随着灾荒程度的加重,年幼的男孩也成为大人果腹的食物,甚至出现父母杀食自己子女身体的事情,“人相食矣,甚有母食其子者”*(清)杨叔雅:《重修葺社庙碑记》,润城镇下庄村,光绪十六年。;有些父母不忍杀食自己的孩子,就与别的家庭相互交换,杀食别人家的孩子。
人丁兴旺、子多福多的观念浸透于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家大业大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追求,并且由于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信仰,四世同堂被认为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幸福的生存模式,“上有老、下有小”是为中年人自豪感最深厚的基础。但面对灾荒,这些最幸福、最自豪的因素都成为个体身体自保的限制与拖累。年龄、健康等身体的生物性残缺都成为限制性条件,为了自保,减少家中人口就成为首选,而孩子由于先天弱势,成为首选的被击杀对象,“弃小儿”“毙童子”“小儿难养者,悉抛於安沟井泉”,“婴儿弃於厕坑”,碑刻中相关记载比比皆是。老年人也因为丧失了劳动力,成为被舍弃的对象,“老弱稚子□毙□□”,“负老持幼就食他乡。或有痛亲老而难行,弃之城郭;亦有恨稚子之带累,□诸道路”。年龄、性别、健康处于弱势的群体首先死于非命,“父子不相顾,兄弟各分张”的记载亦比比皆是。
(三)生人/熟人
据阳城相关资料整理记载,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阳城共发生旱灾52次,出现人相食的情况有6次,而尤以光绪年间的灾荒为最。*山西省阳城县农业局:《阳城县农业志》(内部资料),1987年,第285-295页。“人相食”不仅指将陌生人当做食物,连周遭的亲戚朋友、甚至家人都成为充饥的食物。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施坚雅在其著作中曾指出,农民的社会交往区域边界不是他所居住的村庄,而是他周期性赴会的农村集市,基层市场所覆盖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身穿长袍的地主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他认识在赶集的路上遇见的所有人,并且在他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4-45页。乡村中的男子因为要参与临近集市的经济活动,因此与周围的人有机会熟识并缔结各种关系。面对灾荒,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个体之间不再是熟悉的亲戚朋友,朋友间的脉脉温情荡然无存,而变成了他者眼中可以充饥的食物,熟人社会陌生化。“道路之间,知交遇知交过而不答;若遇不相识者皆战,而弱者遭毒手。”*《奇荒碑记》,东冶镇降区村,光绪六年。单个人为了自保,不敢单独出门活动,“东庄西庄一人谁敢冒往,朝时夕时单身畴敢出门,人啮人肉”*(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只身不敢行路,单人不敢投宿”*(清)王国祯:《南梁城荒年碑记》,河北镇南梁城村,光绪七年。。面对外来的陌生人,饥民痛下杀手,即使是熟人也毫无情感可言,磨刀霍霍向之,以致亲戚朋友之间都为了保命躲藏不见,“偶至亲友之家,皆躲藏不见”*《奇荒碑记》,东冶镇降区村,光绪六年。。灾荒面前,人类这种毫无感情的非理性行为与动物无异,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是荡然无存,人伦、道德、礼仪等道德规范在满足人身体基本欲望面前变得毫无价值,“始则剥食尸骸,终竟杀食活人,甚至父子相杀,兄弟相杀,夫妻相杀,其食人者以偷活者处处皆有”*(清)王国祯:《南梁城荒年碑记》,河北镇南梁城村,光绪七年。。
(四)富/穷
传统华北乡村中,富户屈指可数,穷者比比皆是。富户与穷者在人数、财富等方面悬殊较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拥有财富的村中富户一般也是村落的头面人物,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负责,掌握着村庄内的几乎所有资源与权力。但是,传统社会中,富户与穷者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剑拔弩张,对抗而立,而是相对和谐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空间范围内。灾荒发生时,由于富户拥有比穷人更多的粮食和金钱,所以他们遭受饥饿的威胁要比穷人迟缓得多。穷人无粮下锅的时候,会先到村中富裕家庭借粮,但随着灾荒的加重,穷民向富民借粮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穷民向殷实者祈救燃眉,始则登门强借,继而至室抢夺”*(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延至光绪四年,灾荒加剧,穷人更加无路可走,富户虽拥有更多的财物,但在灾荒中愿意舍财粮救助他人者并不多,因此他们更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与嫉恨。灾民无奈之下“各生奸计”,非偷盗即截路,非掘塚即食人;富户为了保障自家财物,与官府强强联手,招募壮丁,看家护院,共同打击灾荒中的暴乱者。这些暴乱者皆由灾荒中的难民而来,虽遭遇官府镇压,死饥甚于死法,虽钉至城门亦不畏惧。由财富不匀而引发的民众对抗与暴乱,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乡村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
(五)官/民
阳城县在遭遇旱灾之初,胡县令积极赈灾,将义仓中的粮食悉数分发给灾民,粮食不够时还向相邻的高平县借粮赈灾,民众对此感激涕零。无奈胡某高升它县,卢晓策在动荡的灾荒中就任阳城县令。起初,卢某也积极率领民众抗灾赈灾,无奈民多粮少,致使饿死之民尸骨累累。对于朝廷的赈灾,时人认为是地方官员救济不力,并且官绅勾结,克扣救灾物资,故碑文中多次出现“讵意县尊宠信绅士设立公局,任意编削”,“皇恩加惠,望救民生,在公吞赈,坐视民死”,“朝廷深仁厚泽,无非欲救人以不死;□□在城恶绅与领赈奸民,屡次克扣”的记载。于是,在“领赈者困毙城关,尸骸谁收?待赈者饿死门内,皮肉不留”的时候,即使面对官方请兵练勇、杀人街市或钉死城门的恐吓,民众也毫不畏惧,铤而走险成为匪徒。*(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身体是意识的物质基础,身体的饥寒交迫是历史的基础性动力,身体是改造的动力。*转引自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由于灾民对官方赈灾举措的不满,因此出现了“由民变匪”的情况。“更有驱民死者,自白云口以至前后要道,截路强夺,不时伤人。大社聚匪,东由沁岸,而抢至秋泉,土岭等村。训章聚匪西从莽山,而抢至桑林出水等村。吾社各村各庄,连日掳掠,各家各户,屡次搜寻”*(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土匪群积,抢掠沿村,或窬墙垣而窃马牛,或创坟墓而盗物什,种种弊害,更仆难数”*(清)时变雍:《莽河汤帝大殿重修碑记》,桑林乡蟒河村,光绪三十一年。。
由于灾荒,很多善良的民众铤而走险,由民成匪,社会身份被迫发生了变化,成为被官府镇压的刁民。“刁民”数量的扩大加剧了社会的混乱程度,激化了官方与民众的对立。为了镇压饥民的反抗,官府与豪绅联合发展武力,“团乡勇以练壮丁,抢夺者杀于街市,食人者钉于城门。如此镇法,而民之饥饿难忍者仍不畏,而尚敢为非也”*(清)王国祯:《南梁城荒年碑记》,河北镇南梁城村,光绪七年。。这些成匪的民众个体和家庭也因为社会身份的转变,成为被整个社会唾弃的对象,无形之中也恶化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造成整个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崩溃。“无耻者成群为暴,盗贼蜂起,非抢夺于家,即劫截于路;或掘墓窃物,或伤命图财,盗窃鸡犬,豕、豚、骡、马、牛、羊。”*(清)王国祯:《南梁城荒年碑记》,河北镇南梁城村,光绪七年。
(六)生/死
阳城官修志书中缺少被灾死亡人数的详细统计,仅以“人民死者不可胜计”*光绪《续阳城县志》卷十八《杂志》。一笔带过。散落民间的碑刻虽对全县死亡人数缺乏总计,但对本村及周围村落的死亡人口却多有计算。《刹树腰荒年碑记》(光绪七年)记载本社大约死亡了十分之九的人口,“屈指社中死者九分有余,生者一分未足”。《蒿峪大庙“皇恩赈恤”碑文》(光绪七年)载,“统计脱活之人东南十存其一,西北十存其二,城关十存其半。念及本村男妇七百有余人,今仅有三十七人;南窑四百有余人,尚存一百有余人”。《记荒碑叙》(光绪七年)载:“我村先年人丁二千有余口,二年中赖以存活者五百余口而已。”《记荒碑记》(光绪三年)载凤城镇北安阳村人口也仅剩十分之一。白桑乡通义村《记荒三年接替碑记》(光绪十四年),对比了本村经历光绪三年旱灾之后的人口变化,“查照村中户口人丁,在前三百余家,现留三十余家;人口一千八百有余,现存大小一百二十余口”。东冶镇降区村则“未荒以前,里中人数大约五千六百有零,谱计荒后共留人仅三百七十有零”*《奇荒碑记》,东冶镇降区村,光绪六年。;八甲口镇下孔村记本村“先年人丁二千有余口,二年中赖以存活者五百余口而已”*(清)成鲁云:《记荒碑叙》,八甲口镇下孔村,光绪七年。;润城镇下庄村记载本村在经历了丁戊灾荒之后,“所余人口不过十之三四”*(清)杨叔雅:《重修葺社庙碑记》,润城镇下庄村,光绪十六年。,并特意指明本村属于死伤人数较少的村庄。
因饿而死的灾民在死后成为其他灾民的食物,“生者死十之有七,活人之饭死者之尸”*《奇荒碑记》,东冶镇降区村,光绪六年。。当灾民缺钱少粮之际,就挖掘死人的墓穴,先是盗取其中的陪葬物品,换钱买粮,再是盗取新死之人的尸体,用以果腹,“掘古墓盗卖首饰,创新坟刮食人尸”*(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剥食尸骸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是鲜例,而是各村普遍皆有的现象,“各村皆有挖柩刨墓”*(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这种情况虽遭到官方的压制,但无奈官不敌饿,掘坟食尸的事情屡禁不止。
身体遭受各种磨难,吃食大量草根、树皮、树叶、鼠雀等非正常食物,致使体质和抵抗力大幅度下降,生病者众多。“无粮者死于饥饿,有粮者死于疾病”,“各村各庄,饿毙者半,瘟殁者半,十去九而仅存一”*(清)时变雍:《莽河汤帝大殿重修碑记》,桑林乡蟒河村,光绪三十一年。,“更加瘟疫之灾并至,饿死与病死者更甚”*(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
(七)人/物
这里所指的人/物之中的“物”包括动植物,其中尤以人与动物的关系为重。灾荒之初,灾民首先挖掘各种植物的根、叶、茎用以果腹,随后又将家中的鸡狗、牛马等动物宰杀,“各家的牛驴也都杀的吃尽了,鸡狗更不要说了,根本连鸡狗的声音也都听不到一点”*(清)贾杶:《光绪三年的记荒碑》,凤城镇北安阳村,光绪七年。。当灾荒严重加剧,人因饥饿而无缚鸡之力时,反倒成了豺狼野狗的食物。豺狼当道,成群结队的出来,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人;地里边的老鼠,在地里横过来,顺过去,到处乱跑,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一点禾苗,也不知道被吃了多少。*(清)贾杶:《光绪三年的记荒碑》,凤城镇北安阳村,光绪七年。灾荒面前万物平等,死人乃至活人亦可能成为低等动物口中的食物。
马斯洛曾指出,人的需求象阶梯一样可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个方面,而生理需要是最基础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没有区别,生理需要(除性以外)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人类个体的生理机能就无法正常运转。*转引自石岩:《高等教育心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4-7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首要动力。因为生理需要虽然级别最低,但却是其它需要的基础,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它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世俗生活中,身体是个体生命得以确立的物质性条件,只有拥有活着的身体,只有满足了身体的正常需求,人才有创造的动力。
动物与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听凭身体的及时性冲动,人则压抑和延缓这种冲动,并将这种及时性冲动看成是对人和人性的或多或少的羞辱性反应。这样,在人这里,自然身体的克制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灾荒导致的饥饿引爆了人的动物性冲动,人要摆脱自身的兽性,就必须以最大的可能性排斥自身的兽性基础——身体。*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在灾荒饥饿面前,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宇宙主宰,却因为满足自我身体的需要唤起了自身的兽性,并重新回归到众动物之列。身体是生物存在的本质,因此维持身体正常运转成为众生物的首要工作。
碑文中呈现的各种身体都呈现了这样一种事实:人的生理需要未被满足,此种情况下,作为个体的人什么都不想,只想让自己活下去,思考能力、道德观念明显变得脆弱。这不是民心变坏,人伦失常,也不是国家立法不严,实在是饥寒交迫,忍受不住。马克思指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因素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适应。但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归根究底都是人的因素,而人这种最终的决定因素首要的是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于柏拉图来说,欲望的身体无法接近作为真理的理念;对奥古斯丁来说,欲望的身体无法通达上帝之城。*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身体,尤其是性,是人接近上帝必须要克服的放肆本能。而对于马克思而言,身体的饥寒交迫是历史的基础性动力,身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物质性条件与动力。
二、碑刻书写者的身体
20世纪60年代初,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最重要、最具独创性的概念——“隐含作者”*程锡麟:《小说理论的里程碑——谈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从此文本外的真实作者就似乎隐身不见。综观以往的叙事学研究成果,此种论断也可得到检验,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常常淡出经典叙事学家的视线。身体叙事弥补了这种研究的不足,文本的创作者与阅读者的身体都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就像深受梅洛-庞蒂影响的现象学学者所认识的那样,“梅洛-庞蒂认为没有任何知觉可以超越特定的视角与特定的身体,有生命的肉体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
“即千百年以后,说起来也是耳不忍听,眼更不忍去看的。”*(清)贾杶:《光绪三年的记荒碑》,凤城镇北安阳村,光绪七年。“丁戊奇荒”中的少量幸存者虽也极力想忘却这场灾难,但是那种忍饥挨饿、饥寒交迫的身体痛苦感受却在提醒他们,应该把这场旷世仅有的灾难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时刻做好备荒抗灾的准备。因此,存在于碑刻之外的身体,就包括经受灾荒并将身体感受记载下来的碑文书写者和后世有机会阅读到这些碑刻的碑文阅读者。真实作者的身体是作家写作时赖以生存的“肉体”媒介,因此在进行文本的叙事分析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真实作者的肉体存在。这些书写者的性别、身份以及灾荒感受等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传统中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性掌控着所有的社会资源与权力,书写领域也不例外。阳城这些灾荒碑刻的书写者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他们出身于富庶或者殷实的家庭,都接受过或正在接受正规的教育,大都具有庠生或者太学生的身份。这种身份确保了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属于乡村中的头面人物,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与权力。这些书写者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灾难给他们的知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知都留下了痛苦的身体记忆。他们在灾难中有幸保全性命存活下来,因此他们有机会把身体的各种感受书写到碑文中,“余昔游怀古里汤王庙,见有纪荒碑。所载情形未尝不悚然惧而恍然。疑以为被灾之惨未必有如是之甚者。孰意二百四十年来,竟为身所亲历,而目所亲见耶”*(清)王国祯:《蒿峪大庙》,河北镇南梁城村,光绪七年。。
乡村头面人物处理的事务繁多,主要涉及与官府、村落及私人有关的三类事务。在有关官府的事务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管理和粮税征收。与村庄有关的事务则涉及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建筑或维修围墙、看护大门、组织看管农作物、惩罚违反公约的人、建造庙宇等。灾荒幸存者大都是这些头面人物,例如东冶镇索龙村的四位社首申锦松、马兆金、马成功与刘安琳,凤城镇北安阳村的社首贾杶,降区村的社首蔡世昌等。他们有感灾荒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危害,因此有意识地记载灾荒中各种变形的图景,每每提到或者想到此次灾荒,都是心有余悸,添伤莫已,身体乃至意识、理智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言未毕而伤心落泪滴湿衣襟”*(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他们将心灵的触动落实为具体的行动,延请乡村中有书写能力的人撰写碑文,以志荒事。
相比较碑刻书写者真实的身体,碑刻阅读者的身体是被想象、被虚构的,但在碑刻书写者那里,这些读碑者却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都拥有鲜活的生命与真实的身体。在碑刻书写者看来,这些读碑者没有经历过这次灾荒,没有灾荒带来的痛苦身体记忆,更缺乏如何安度灾荒的经验,因此刻碑者希望通过记录自己的身体体知与感悟,把如何备荒度荒的经验传授给这些读碑者,“虽系天灾,实属自作其孽,且若不计其饥之馑情形,死亡之景象,恐代远年湮,并不知有如此之苦楚矣。爰叙其大略于石,后之来者并将有鉴于斯人”*(清)王国祯:《蒿峪大庙》,河北镇南梁城村,光绪七年。。
书写者希望这些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灾荒记载能引起后世读碑者的警醒,并能适时调整、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警觉于世。甚望后人知孝、知悌、克勤、克俭。勿以乐岁饱暖,遂忘凶年困苦,勿以目前有余,须防将来不足。谚有云:年年防旱。诚哉!是言也。后之览者,亦当有鉴于斯文”*(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刻到碑上,使后人知道知道,丰收之年,要想到欠收之年,有粮的时候,要想想没粮的时候,细水长流,有备无患,再遭到灾荒年必须予有一个准备才好”*(清)贾杶:《光绪三年的记荒碑》,凤城镇北安阳村,光绪七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社会重视纵向代际互动的传统,深刻体现在这些碑刻书写者的意识之中。他们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灾荒感受通过勒石书写碑文的形式传递给后人,书写者与阅读者这种超越时空的对话深含着前世人对后世的谆谆教诲与关切。这里书写者的身体不单单指向身体的生物性感受,更多的是超越生理性的认知与思考。同样阅读者的身体也不仅仅是生物性的身体,而是包含真理认知的身体,这种身体能自觉从经验中调适和规训自我的行为与方式,是超出其他动物的身体之躯。
身体在人类知识和理性前进的道路上充当了一个捣蛋者的角色,为它们的顺利推进设置了障碍。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身体的欲望——食物、性、名利等——同牲畜一样低等任性,并可能导致疯狂的残杀。在哲学家那里,身体由于其生物性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如低级的、贪欲的、错误的、可见的、导致恶的、短暂的,有此导致身体离永恒而绝对的理念既陌生又遥远。但是对普通大众而言,尤其在灾荒面前,灵魂顿时变得渺小和卑微。再伟大的哲学家也得有面包果腹才能维持思考。世俗生活中,身体是所有行为的物质基础和原发性动力,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灵魂、知识、真理、道德等才有谈论的可能。理想的社会首先要让人的身体所需获得满足。正如尼采在其著作中指出的,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德]尼采:《权利意志》,孙周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四、余论
笔者作为有幸阅读到这些灾荒碑刻的后来者,在阅读这些碑刻时最大的震撼就是其中各种关于身体变化的书写,小时候父亲描述的各种饥饿感受一起涌入笔者的身体,我感同身受着这些痛苦的灾荒身体记忆。无生计者攒蹙街巷的身影,面对朝廷救济,“就食男儿临场厥地,踏死而不相顾,领赈女子□地折足,啼号更不堪闻”*(清)侯锡旗:《记荒三年接替碑记》,白桑乡通义村,光绪十四年。的各种灾民身体,“父子不相顾,兄弟各分张,妇女弃於他乡接踵成群,老弱死於非命,填转沟壑”*(清)李廷璧:《荒年碑记》,东冶镇索龙村,光绪七年。的累累尸骨都在逼问我,为什么深受“舍生取义”传统儒家思想教化的广大民众在灾荒面前举动会如此丧心病狂?
在海德格尔看来,动物性是身体化的,也就是说,它是充溢着压倒性的冲动的身体。*转引自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身体这个词指的是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这些冲动、驱力和激情都具有生命意志,因为动物性的生存仅仅是身体化的,它就是权力意志。*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面对灾荒,身体回归到动物性那里,身体等同于权力意志。身体和力是一体的,它不是力的表现形式、场所、媒介或战场,而就是力本身,是力和力的冲突本身,是竞技的力的关系本身。身体霸道地主宰着道德、知识和审美领域。
活生生的物质身体既非起点,亦非终点,它是书写主体性的基石,是社群对话与对抗权力中心的舞台。通过身体重新审视“丁戊奇荒”以及灾荒造成的社会混乱、道德败坏等问题,这也算是对“丁戊奇荒”的再认识吧。
[责任编辑王加华]
作者简介:郭俊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山西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