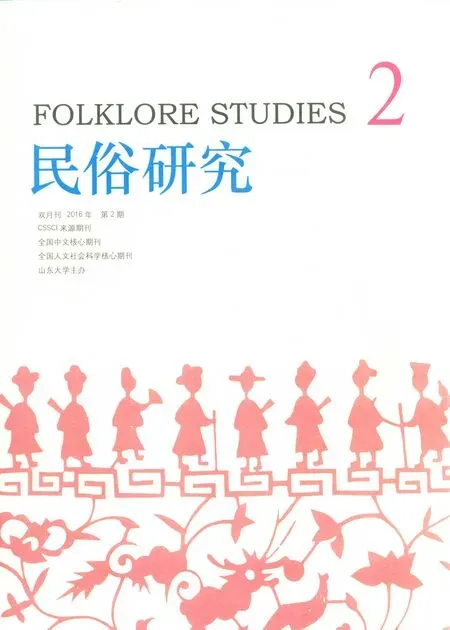“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2016-02-03王均霞
王均霞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王均霞
摘要: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关键词:妇女;女性民俗实践者;民俗学整体研究观;情境化知识;现象社会学
一、漫长研究史中“妇女”的在场与“女性民俗实践者”的缺席/失语
中国女性民俗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关于妇女(about women)和为了妇女(for women)的。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兴起之初,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关注到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认为无论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还是从研究学问的角度,都应该了解民众的生活状况,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①顾颉刚:《〈民俗〉发刊辞》,王文宝:《中国民俗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4页。,由此从前只限于经书的学问对象现在“变为全世界的事物了!”②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顾颉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326-327页。在这样的研究大环境下,一些研究者开始收集女性民俗资料(如妇女歌谣)、对女性民俗文化进行历史考据或者文化描述(如对缠足、娼妓等的历史钩沉),以为争取妇女解放提供助力。这些研究明确关注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试图为改变底层妇女受压迫的生存境况发声。例如,黄石以《东方杂志》和《新女性》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涉及婚姻习俗、性与贞操、女性服饰、娼妓等与女性相关的文章,其目的是为了“女子解放成功”③黄石:《〈家族制度史〉译后》,[美]顾素尔:《家族制度史》,黄石译,开明书店,1931年,第Ⅱ页。;刘经庵将妇女歌谣汇编成册,是为了揭示歌谣中反映的“妇女问题”④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4页。,使人们知道妇女生活“过去和现在的情形——与将来的妇女运动的方向”⑤周作人:《〈歌谣与妇女〉序》,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
比之民俗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女性民俗研究作为其中寂寂无声、至今未引起充分重视的一个领域,它在关注到女性民俗文化的同时,更密切而明确地关注到了妇女群体本身。它通过对女性民俗文化的研究来关注妇女及其生存境况,其落脚点其实是受压迫的妇女及其利益诉求的实现。女性民俗研究的这一逻辑贯穿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至20世纪末的女性民俗研究中,新文化运动时期、建国前后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女性民俗研究莫不如此。*详细论述请参见王均霞:《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然而,在以往的女性民俗研究中,尽管研究者在研究中同时关注到了女性民俗文化与受压迫的妇女群体,但研究者却忽视了在具体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之间的互动性与一体性。换而言之,研究者在对女性民俗文化进行解析的过程中,女性民俗实践者被从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剥离出来,并被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中的一员。富有个体性与独立性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过程中消失不见了。由此,女性民俗文化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女性民俗文化,女性民俗实践者也被泛化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二者双双失去了在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本应有之的地方性、鲜活性与动态性。
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歌谣研究为例。一方面,研究者承认歌谣的传唱者主要是女性,“乡间歌谣的‘大师’,不是文人学士,也不是小孩,是成年的女子或妇人。因为当孩子知道说话的时候,教之唱歌,也是母亲重要的职务之一”*黄朴:《歌谣谈》,《歌谣》第33号,1923年11月18日。。因此,其搜集来的歌谣中多有妇女歌谣。例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中就有关于“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这些歌谣多是从他的祖母、妻子以及帮佣的老妈子和婢女那儿搜集来的。*顾颉刚:《吴歌甲集》,顾颉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但另一方面,这些具有个体性的女性歌谣传唱者在研究中却常常消失不见。例如,刘经庵在《歌谣与妇女》中热情赞颂了妇女的文学才能,并对其受压迫的生活状态进行了揭示,但在其研究中,很难看到对这些妇女歌谣由以收集来的那些妇女只言片语的描述,更不见这些女性对这些歌谣的实际态度。*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当时的研究者黄朴抱怨过其中因由,
我的十二岁的小弟弟尝对我说:“三哥!寿山的媳妇多会唱歌。”我对他讲:“这个只好你去请她唱。”因为乡间年青男女对话,已足诱起蜚语,何况一个叫一个唱歌呢?我的弟弟不肯去,我又没有偶然听她唱,结果是许多新歌关在新娘肚里!*黄朴:《歌谣谈》,《歌谣》第33号,1923年11月18日。
由此看来,女性民俗实践者的缺席跟当时的研究者以男性学者为主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确立的男女交往界限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民俗研究领域逐渐由女性学者所主导,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动过程中的性别障碍解除,同时随着田野调查法在民俗学研究中的普及,民族志式的女性民俗研究开始触及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民俗实践者伴随着研究者对女性民俗文化的书写被裹挟进学术研究视野中,其个人生活史及其声音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民族志书写当中。然而,即便如此,女性民俗实践者本质上却仍难逃被客体化的命运:在民族志的书写中“女性群体仍然是高度同质化的,作为被研究者主体的女性群体在研究者的笔下仿如静物一般,任凭研究者观察与定性,而她/她们自身则几乎完全处于失语状态。”*王均霞:《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女性民俗实践者在女性民俗研究中的缺席/失语,意味着在女性民俗研究过程中女性民俗实践者视角的缺席。
近些年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不断引入,“社会性别”(gender)概念逐渐为女性民俗研究者所使用。例如,康丽的中国巧女故事研究,较早在民俗学研究中使用了社会性别概念。作者“借由民间女性观念的视角,切入到故事文化内涵层面”*康丽:《中国巧女故事叙事形态研究——兼论故事中的民间女性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页。,探讨中国巧女故事中的民间女性观念。由此,巧女故事研究从侧重于类型学的研究深入到对其社会文化内涵的考察。更进一步地,“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使得女性民俗研究逐渐聚焦到女性主体本身并开始凸显女性民俗实践者的主体性。例如,徐霄鹰对客家山歌与民间信仰两个领域里的客家妇女的研究,则更明确地借助女性研究的相关理念与方法探讨“妇女的身份与角色,影响与地位,选择与限制,以及她们的自我定义、观念与对自身行为的解释和评价”*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徐霄鹰敏锐地注意到了女性个人选择行为的重要性,在她的研究中充满了对出现在山歌与民间信仰两个领域里的女性的个人生活故事的描述及其自我观念的表达。但这种明确立足于女性民俗实践者的研究,相对还比较少。
总结起来,尽管中国女性民俗研究从一开始就同时关注到女性民俗文化和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但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女性民俗文化和女性民俗实践者的关注是相互分离的。研究者通过对女性民俗文化的研究切入对妇女群体利益诉求的关切,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又将女性民俗实践者从其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剥离了出来,将其抽象成具有普适性与泛化性的“妇女”一词,从而消解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本应有之的个性与主体性。女性研究的相关理念,尤其是“社会性别”概念在女性民俗研究中的使用,以及依赖于田野作业的民族志式的女性民俗研究的兴起使得女性民俗实践者重新回到研究者的民族志书写中,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女性民俗研究中被剥离的“民”重返女性民俗研究过程。但迄今为止,促成这种转变的研究者似乎尚缺乏将研究重心明确放在女性民俗实践者身上的自觉意识,这造成了女性民俗实践者的主体性在女性民族志书写中的游移性与模糊性。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承载起关于妇女和为了妇女的双重研究使命亦是其研究的题中之义,然而,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缺席/失语却将女性民俗研究推入一种吊诡的境地:我们宣称研究是“为了妇女”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抛弃或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妇女”的可操作化对象——女性民俗实践者——客体化处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那么,如果要在研究中恢复女性民俗实践者本应有之的位置,研究者又该如何在理念与技术上处理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鉴于现有的研究尚未涉及对该问题的讨论,本文尝试借助“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理念来探讨该问题可能的解决路径。
简而言之,“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力图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民俗实践过程。这一研究理念并非空穴来风。它首先来自于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梳理与反思,继而受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a Haraway)的“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的影响。下文将具体讨论中国民俗学的整体研究观与女性民俗研究的关系、唐娜·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概念对女性民俗研究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的可能架构。
二、回到作为女性民俗研究背景的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对女性民俗研究的启示及相关反思
作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女性民俗研究无法脱离中国民俗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而回顾中国民俗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它经历了从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到民俗学整体研究范式的转变,其学科性质也已经从人文学科转变为社会科学。*具体参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与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相比,民俗学整体研究范式“重新恢复被事象研究抽掉的人和情境的本来位置,它关心整个民俗事件,把民俗过程中的各个因素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它着眼于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生活来研究民俗。它依靠田野作业直接观察并参与到民俗事件中去获得资料,全面掌握事件中各个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意义”*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由此,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其研究目的也逐渐由文艺的、审美的,转变为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语境”*民俗学界对于“语境”的相关讨论可参见杨利慧:《从“自然语境”到“实际语境”——反思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追求》,《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等。、“主体间性”*对于“主体间性”的讨论,可参见吕微:《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反思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等。、民俗学的“身体性与情感维度”*刘铁梁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主要研究者,相关文章有:《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温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身体民俗学视角下的个人叙事——以中国春节为例,《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等。等问题。在这些讨论中,作为个体的人在其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从早期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对人的忽视,到人成为民俗学整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俗学整体研究观、语境研究),再到对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者主体的互动关系的探讨(主体间性),最后到“把人的生活实践作为观察和理解的对象”*刘铁梁:《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温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通过人的行动呈现生活的整体性(身体性与情感维度的考量),人及其实践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者开始强调“个人的故事”、“个人生活史”的重要性,吕微更是宣称,“人自身的主体性存在意义和价值”即为民俗学的基本问题,现代民俗学“以讲述人自身的主体性、当下性存在的‘个人的故事’为基本问题”*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自然影响到女性民俗研究,可以说,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我们今天能够讨论聚焦于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民俗实践的女性民俗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使得女性民俗研究不再仅仅通过对女性民俗文化的呈现与探讨来间接指向对女性民俗文化承载者的关切,相反,它通过对人及其文化的语境化研究使得女性民俗研究可以直接面对活生生的、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民俗实践。近些年出现的女性民族志,如徐霄鹰的《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卫华的《春节习俗与女性身份意识——以当代山东沂蒙山区榆钱村为个案》*王卫华:《春节习俗与女性身份意识——以当代山东沂蒙山区榆钱村为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王均霞的《礼物、关系与性别——礼物交换与纪村妇女生活》*王均霞:《礼物、关系与性别:礼物交换与纪村妇女生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陈秋的《屋里屋外——城镇化进程中温州柳村女性民俗生活研究》*陈秋:《屋里屋外——城镇化进程中温州柳村女性民俗生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均有明显的受民俗学整体研究观影响的痕迹。
然而,立足于前辈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之上,反思包括女性民俗研究在内的民俗学整体研究观念的实践,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1.当我们采用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范式时,我们所强调的整体性是谁的整体性?2.被“发现”的“民”在民俗学的整体研究中到底处于何种位置、承担了何种角色?
对于第一个问题,研究者似乎将其看作是不言自明、无需讨论的。当我们把民俗事象重新置于民俗事件、民俗发生情境中,并将与其相关的各个要件加以综合研究,民俗研究似乎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整体性。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同一时空中的同一民俗事象为出发点去进行整体研究,研究者A眼中的整体性是否等同于研究者B眼中的整体性?被研究者C眼中的整体性是否与被研究者D眼中的整体性意味相同?我们需要对包含了被看作是主体的人在内的整体研究进一步发问:研究者站在何种位置(视角)上宣称自己的研究是整体研究?民俗学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个超越个体视线、超越限制与说明责任的统一的整体性?
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学者们都承认并强调民在民俗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试图在民俗研究中植入理解“民”的使命*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但迄今为止,在中国民俗学的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中,“民”大致承担了两种功能:第一,将人作为整体研究的一个部件来保持民俗学整体研究的完整性;第二,将人视作社群意义上的人,通过对个体的研究透视整个社群的文化生活与生活文化。在前一种功能中,人的独立性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后一种功能中,研究者强调人作为社群成员的共同性,人的个体性(抑或独特性)被剥离,个体的自我性很大程度上被消解。这两种作用本质上都脱离不了从个体映射社群整体的研究路径,人被看作是呈现生活整体的中介,实践者身上作为社群整体一员的共同性受到重视,而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与民俗传统的微观互动以及个体的独立价值则是被忽视的。
可以说,立足于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范式的研究成果虽然宣称重视“民”并将“民”加诸具体的研究中,但在实践上它仍然没有摆脱以“俗”为中心的研究倾向。研究者无论是对语境的强调还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强调,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俗”,抑或由此理解地方社会(群体),而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独立个体的“民”。拥有主体性与个体性的民俗实践者没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是变成了理解“俗”、理解地方社会的中介。在此过程中,作为独立个体的实践者的个性的复杂性与不可化约性被抹去,他/她在根本上仍难逃被均质化的命运,这使得“民”在现有研究中的位置有着明显的游移性与模糊性。当民俗学从人文学科转向社会科学时,人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理应成为民俗学的关注点。因为,如果民俗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自身的主体性存在意义和价值”*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那么,民俗学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将民间看作是“可以清晰表述出来的个人,活生生的人”,强调“他们是主动者,有思想也有行动,会抗争也会合作”*高丙中:《民间文化的复兴:个人的故事》,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抑或如高丙中所言,“我们做‘民间’的学问,在心中要有‘民’,有积极行动的个人。当我们在谈论特定文化的渊源而使用‘folk’的时候,认真地把他们当作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的公民身份的成员来看待”*高丙中:《民间文化的复兴:个人的故事》,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在当下的民俗学研究中,研究者还应该回头将有积极行动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若不如此,即便在研究中引入“个人的故事”抑或“个人生活史”,我们仍难充分理解与尊重个体的存在意义与价值。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将民俗学研究人的最终目标设定为理解“俗”、理解地方社会,却忽视了首先去理解地方社会中的人及其实践的个体性与复杂性,致使民的个性不显、实践者之民俗实践的情境性与动态性不彰,那么,民俗研究其实仍然很难充分理解地方社会。因为,它首先轻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及个体作为社群一员所具有的结构化能力。其次,它忽视了作为个体的实践者的个性与独特性本身所具有的经验累积性。*现象社会学强调,在日常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成千上万种有问题的、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处理的具体情境,都是由人们根据个体现有的知识储备察觉并阐述的。这些被类型化的知识储备是其行动的基础。但在具体的情境中,人们还将面对新情况,他必须对这种新情况进行推断与即兴发挥。但“即使是即兴发挥也要沿着从类型的角度来看可能存在的轨道发展,并且要受个体所能想像到的那些可能性的限制。同样,这些可能性也植根于现有的知识储备之中。”[美]莫里斯·纳坦森:《〈社会实在问题〉绪论》,[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现象社会学家早已指出,个体身上的个性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过去的、被类型化了的知识储备。*[瑞]阿伦·古尔维奇:《〈现象哲学研究〉引论》,[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现象哲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说明,个体的实践者的个性与独特性中实际既包含着创造性,亦包含着过去的、被类型化了的知识储备,忽视了对这些知识的挖掘便影响到对“俗”的充分理解,亦影响到对地方社会的深度理解。
回到女性民俗研究本身,尽管现有的研究日益关注女性民俗实践者,但在现有的民俗学研究脉络里,它本质上依然没有摆脱均质化研究的倾向,没有走向彻底地深度理解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民俗实践之路,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民俗实践的个体性价值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女性民俗研究作为民俗学研究中特别将“为了妇女”视作自己研究使命的研究领域,它实际上更需要通过对女性民俗实践者与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考察来深度理解一个个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呈现个体的生命故事及其诉求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这是进一步理解女性群体,抑或说,思考如何充分理解女性群体的前提与基础。而现有的民俗学整体研究框架无助于女性民俗研究实现此目的。
三、去往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情境化知识”概念的相关理念及其启示性
就以上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a Haraway)的“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的概念是有启示性的。唐娜·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概念源于她对传统科学客观性的批判。哈拉维反对那种抽离了身体、超越一切限制与责任的客观性,她宣称,“女性主义的客观性指的是关于有限的地方(limited location)和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它不是具有超越性以及主体与客体分裂的知识”。*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Vol.14, No.3(Autumn, 1988),pp.583.
尽管哈拉维并没有明确阐释什么是“情境化知识”,但总结其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包含以下一些内容:
第一、情境化知识是一种视线(version)在场的知识宣称。哈拉维坚持一切视线的涉身性(embodiment),“强调视线不能脱离肉身,不能摆脱语境,不具有免受观看和检视的特权”*[美]章梅芳:《唐娜·哈拉维的科学客观性思想评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4页。。哈拉维强调,眼睛是一个主动的感知系统,它观看世界的方式受个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透过眼睛这个中介,视线所看到的永远是部分的、有限的而非具有超越性的全部。同时,视线本身所具有的涉身性也并非是关于在一个物化身体中被固定的位置,而是“诸多场域中的节点、动向的曲折(inflections in orientations),以及能对在意义的物质—符号场域中的差异负起责任的”。*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Vol.14, No.3(Autumn, 1988),pp.588.因而,涉身性意味着身体的在场的同时,也意味着流动性、复杂性与可以承担起责任的。
第二、情境化知识能够负担起说明与阐释的责任。情境化知识不是关于超越性的知识,视线的在场以及视线本身所具有的涉身性使得它是一种拥有中介轨迹的、可定位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部分的知识,呈现的是局部视角。而拥有中介轨迹的、可定位的局部视角是能够负担起说明与阐释责任的。“唯有部分观点许诺了客观的视线。这种客观视线会自动自发负起,而非躲闪,所有视觉实践的生成所涉及的责任问题”*[美]唐娜·哈洛威:《猿猴、赛伯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张君玫译,群学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
第三、情境化知识不是关于认同的知识,而是强调差异的知识。哈拉维所宣称的客观性是尊崇争议、强调分裂的,而分裂中包含着对异质多样性的推崇。因而,“这样的客观性要求尊重差异,认识到不同主客体之间及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并强调结盟而非认同,主张改造知识系统和观看方式”*章梅芳:《唐娜·哈拉维的科学客观性思想评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4期。。在此前提下,哈拉维对女性主义所推崇的底层视角进行了反思。她强调要建立一种从边缘和深处去看的能力,但亦担心较无权力者的视觉被浪漫化和(或)被占用,并被宣称可以从他们的立场去看。
“即便‘我们’‘自然地’栖居于受压迫的知识之伟大的地底地带,从底层去看,既不是可以轻易习得的,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从批判质询的符号学(semiological)与阐释学(hermeneutic)模式出发来看,受压迫者的定位并不能豁免于批判性的再检视(critical reexamination)、解码、解构与阐释。受压迫者的立场并非是‘无辜的’。……受压迫者的立场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他们似乎许诺对世界进行更充分的、持续的、客观的和有转变的描述。但如何从底层去看,至少还需要像‘最高的’科技科学视觉化一样多的、以视线为媒介的身体与语言的技术。”*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Vol.14, No.3(Autumn, 1988),pp.584.
由此,哈拉维解构了哈丁(Sandra Harding)的女性主义立场论,不承认有一个统一的女性主义底层立场,而是强调主体视角的联合。
借由这些概念,哈拉维打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观点,强调一种身体及视线在场的客观性。在她所探讨的诸多内容中,以下一些内容亦启示我们重新审视民俗学的整体研究观,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维度:1.在情境化知识中强调身体及视线的在场,不承认超越性视角的存在,这实际上确认了独立的主体在场的重要性;2.强调情境化知识的可定位性,中介轨迹的存在使得情境化知识变得可解释与可说明;3.强调差异性而非认同性,这使得主体之间的独立性得到尊重与承认。
四、女性民俗研究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的研究理念探讨
受以上研究观念的启发,本文试图构拟一种主体及其视线在场的女性民俗情境化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将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层面研究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民俗实践活动。*在2014年发表的《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一文中,笔者曾对中国女性民俗研究中的“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倾向进行过初步总结与思考。在该文中,笔者将2000年之后,中国女性民俗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概括为“‘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将女性及其相关民俗置于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注重对女性民俗实践过程的考察,在具体的日常生活情境中,探讨其日常生活实践与文化表达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本文是在该文基础上对“‘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思考。王均霞:《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这一范式首先是基于对现有的女性民俗研究中女性民俗实践者位置的模糊性与游移性的反思。尽管现有研究日益关注女性民俗实践者的主体性,但以笔者目力所及,尚未有研究将讨论的焦点聚焦于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在关注其作为社群一员的共同性的同时,考量其个体性的独特价值。其次,将女性民俗研究放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大框架里看,尽管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使得女性民俗研究关注到了女性民俗实践者,相关女性民族志的书写亦着力呈现女性民俗实践者的主体性,但民俗学的整体研究实践本质上依然以“俗”为中心的研究理路使“民”的个体性与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民俗学整体观整体上缺乏可定位性以及民俗实践者位置的游移性,一定程度上都显示了它对民俗实践者关注的不彻底性。而恰如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言,现阶段的女性民族志研究需要从抽象的“妇女”研究中解脱出来,充分关注女性民俗实践者,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以便深度理解女性群体,完成其“为了妇女”的研究使命。
受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概念的启示,同时借用现象社会学的观念,本文将作为个体实践者的身体及其视线引入女性民俗研究的整体研究中,力图使女性民俗研究的整体研究获得可定位性,同时亦试图定位女性民俗实践者在整体研究中的位置。
具体来说,强调以实践者为中心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应该包含以下一些要点:
首先,将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置于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身上,强调实践者的个体性,并坚持女性民俗实践者个性的复杂性及其个体价值的不可化约性与不可替代性。
将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置于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身上,是要强调对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的微观研究,试图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具有主体性与独立性的“民”的维度。它对从个体出发归纳群体特质的研究路径抱持审慎的态度,皆因这一路径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游离于群体特质之外的个体的独特个性的价值,忽视了个体的独特个性与具有模式性的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一路径也割裂了独立个体复杂多样的多面个性之间的关联性,亦即个体本身的整体性与复杂性。
其次,建构女性民俗实践者的个体情境——“我的情境”,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情境中考察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
现象社会学家宣称,任何一种理论分析,都必须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结构而存在的面对面关系出发*[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理解社会世界意味着理解人们界定其情境的方式”*[美]莫里斯·纳坦森:《〈社会实在问题〉引论》,[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而情境并非一个静止的概念,情境具有主观性与变动性。现象社会学家指出,行动者不仅要对他赋予他自己的活动的意义进行界定,而且还要对情境负责。行动者的情境首先是行动者的问题,确定和解释一个既定情境的方式是行动者的主观性所具有的功能。*[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从这个角度看,情境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是“我的情境”。阿尔弗雷德·许茨*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ütz),亦译作阿尔弗雷德·舒茨等,奥地利裔美籍哲学家、社会学家,现象社会学的创始人。解释说,“我的情境不仅包含我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包含我的人类环境,包含我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我的道德立场。”*[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2页。
当我们确定情境具有个体性与主观性之后,我们就必须从个体的视线出发去构拟情境,并在这个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个体性与动态性的情境中考察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强调女性民俗实践者的视线并非同质化的女性群体的视线,也非单一不变的视线,而是充满了个体性与情境性的视线,亦即强调视线所具有的植根于具体时空中的、身体在场的、个性化的、流动性的与多重性的特征。这一视线随着女性民俗实践者在情境中的经历以及与其他人、事、物的互动而产生的角色、地位、心态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在研究中引入个体视线使得研究有了可定位性与可解释性。正如哈拉维所言,视线在场的研究是关于局部的知识的,是能够看到中介轨迹的,是有人能够负担起说明与阐释的责任的。个体的人和情境之间因此而产生了深度关联。正是在这样的“我的情境”中,我们可以考察女性民俗实践者与民俗传统的互构关系,也即,从女性民俗实践者的“我的情境”中,审视她如何被民俗传统所建构以及她如何建构民俗传统。
第三,通过挖掘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的生平情境,将对个人生活史的解读纳入到对当下具体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当中。
阿尔弗雷德·许茨指出,“一个行动者所在的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仅仅是‘现在’ , 不仅仅是‘此时此刻’ , 它还是‘历史性的’。”*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页。许茨将普通人所经历的生活史称为“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宣称普通人所经历的现在与他以往的主观经验积淀密不可分。
在其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时刻,人都会发现他自己处在某种被从生平角度决定的情境之中,也就是说,发现他自己处在某种同样由他自己限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他在这种情境中拥有他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有他根据物理空间和外在时间确定的立场、或根据他在社会系统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确定的立场,而且还包括他的道德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说这种情境界定是被从生平角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它具有它的历史;它是一个人的所有以前经验的积淀,是通过他现有的知识储备所具有的习惯性所有物而得到组织的;它本身即是他唯一的所有物,是给予他并且仅仅给予他本人的。*[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因而,对处在眼下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进行研究,需要引入对女性民俗实践者的生平情境——亦即个人生活史——的关注,以更好地理解女性民俗实践者当下的行动。生平情境中既包含着受地方传统文化影响的具有普遍性的类型化知识,亦包含着复杂多样、具体而微的个人遭际。如许茨所言,这些知识作为经验累积下来影响着人接下来将要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实践者此时此地的行动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还与未出现在此时此地的情境中的其他“事物”产生关联。生平情境就在此时此地的情境之外,赋予实践者的当下行动以历史性。对于女性民俗实践者而言,我们尤其需要通过其生平情境考察具有普遍性与类型性的地方传统文化知识过去如何塑造了女性民俗实践者以及女性民俗实践者当下的民俗实践又如何影响地方传统文化知识。
总结而言,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从女性民俗实践者的视线出发,通过对女性民俗实践者的个人生活史的考察来理解女性民俗实践者在当下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行动,进而理解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限于篇幅,笔者将另辟专文做关于“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范式的案例分析,以探讨这一研究范式的可行性与操作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否定女性民俗研究的其他研究范式,只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为当下的女性民俗研究提供可能的研究进路。
五、“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范式的意义所在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力图以作为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来考察特定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民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是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此前提下,首先从历时维度(个人生活史)来理解女性民俗实践者,然后通过对具体社会互动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实践活动的微观分析,探讨女性民俗实践者与民俗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
提倡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范式,意义有二:
第一、将抽象的集合名词“妇女”还原成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凸显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在民俗研究中的重要性。
以往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太过关注作为社群整体意义上的“民”了。某种意义上,民俗实践者属于“民”的一部分,但民俗实践者不等于民。“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民俗实践者”是具象的,是身体在场的,是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个体。当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强调“民”的共性或代表性时,实际上忽视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作为实践者的“民”自身的意义与价值。现有的女性民俗研究亦倾向于剥离个体意义上的女性民俗实践者而通过集合意义上的“妇女”来关切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梳理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史,到今天,这一倾向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然而,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并不存在一个均质的女性群体,女性群体内部具有差异性(如年龄、民族、家庭经济状况、教育职业背景等),女性个体对民俗形式的运用策略及传达出的信息不尽相同。*李靖:《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理论之路——20世纪70至90年代》,《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同时,就女性民俗实践者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而言,女性民俗实践者与民俗文化的互动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博弈的动态扬弃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女性民俗实践者在被民俗文化塑造着的同时,亦塑造着民俗文化。因而,有必要将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从抽象的集合名词“妇女”中解放出来,将其还原成活生生的、拥有独立性的民俗实践者对其进行再研究,以为女性民俗研究找到新的研究进路。
第二、通过强调女性民俗实践者身体及其视线在场,建构一种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可定位的女性民族志书写模式。
恰如关注实践的理论家们构想的那样,实践是一种涉身的(embodied)、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系列的人类活动。涉身性强调人类活动形式是与人类身体纠缠在一起的。*Schatzki, Theodore R. “Introduction: Practice Theory”, in Theodore R. Schatzki and Karin Knorr Cetina, and Eike von Savigny(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1,p.1-14.由此,实践与身体之间具有了不可分离性。身体的在场使得正在进行着的日常生活实践具有了可定位性,亦使得日常生活的观看视角有了可定位性。而源自于身体的视线不是全知全能的,视线只能看到部分,而非整体。由视线所在的位置出发去看、去理解正在发生的行为与事件,使得这些行为与事件有了可定位性与可解释性,亦将整体性落实到实践者与其视线在场的局部视角之下。换而言之,整体性是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的局部视角之下的整体性,是从实践者的视线出发理解的整体性。在对女性民俗实践的考察中引入局部视角,其实是在女性民俗实践者与情境中发生的行为/事件之间建立起一种可定位与可解释的关联,并同时将女性民俗实践者作为理解情境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亦成为理解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工作生活实践的重要进路。
通过这一研究范式,研究者或许可以做到对民俗实践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明晰女性民俗实践者如何被地方传统文化所结构,同时她又如何结构着地方传统文化,以此实现对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最大限度的理解。
[责任编辑刁统菊]
An Exploration of Situated Studies Centered on Female Folk Practitioners
WANG Junxia
As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of folklore studies and women studies, women’s folklore studies have the mission of “about the women” and “for the women”. However, the female folk practitioner was often abstracted into collective noun “woman” in general, which made her absent or losing voice in women’s folklore studies thus far. Approaching women’s folklore under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 reflecting on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folklore studies,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term of “situated knowledges” from post-modern feminism as well as related ideas from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situated studies centered on female folk practitioners” tries to suggest a research paradigm that makes female folk practitioner as the center of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female folk practitioner, making her voice and vision present, this research paradigm attempts to explore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female folk practitioners and folk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situation.
Key Words:woman; female folk practitioner;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folklore studies; situated knowledge;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女性民俗学的‘情境化’研究实践——以鲁东南地区乡村女性交往习俗为中心”(项目编号:13YJC850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讲师(上海 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