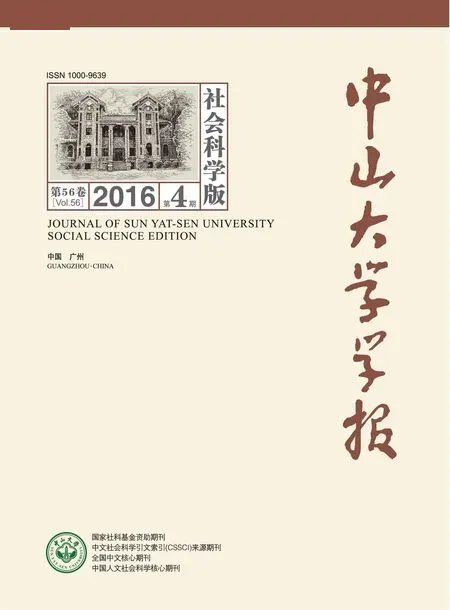中国地学会与科学地理的构建(1909
—1911)*
2016-01-27谢皆刚
谢 皆 刚
中国地学会与科学地理的构建(1909
—1911)*
谢 皆 刚
摘要:光宣之际新学萌发,旧学陵替,构建新知识成为学界当务之急。中国地学会舍旧谋新,倡言构建能与世界争先并进的科学地理。为此,其定调查为会员的义务,以植学术根基。基于新学眼光,中国是科学方兴的后进,引入东西学理是迎头赶上的前提,地理又是地域性较强的学科,借助外来基本原理与方法解释中国材料是发展学术的必然之路。囿于时代与出身,学会同人在讲求科学新知的同时,仍然深受固有学术的影响,试图以西学地理系统条理中学,贯通中西建立中国地理学统系。学术内外种种因素的叠加,致使科学地理的构建举步维艰,终因时局的变动而中止。
关键词:中国地学会;科学地理;构建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杂糅,各家观念歧异,竞相争锋。光宣之际新学渐有一统之势,然而中国科学方兴,学理尚极浅显,趋新者以鼓吹新知、构建科学为己任。乘势而起的中国地学会,以构建能与世界争先并进的科学地理为号召,几乎将新学地理名家尽数囊括,成为新学地理的旗帜、专门社团的代表。其构建科学地理的努力,是清季少见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建设新知识的行动,对中国地理、学术的发展与流变有重大影响。
既往学界对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已有所关注,但受派系眼光及研究观念的限制,认识相去甚远①典型的如身为竞争者的张其昀认为中国地学会对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历史地理学(《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科学》第19卷第10期至第20卷第7期,1935年10月至1936年7月)。曾为中国地学会后进的张天麟、林超则认为中国地学会的创建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产生的重要标志,并推动其发展(见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且大都关注中国地学会引入科学新知的一面,对其深受传统观念与行事影响,追求专门、古雅的另一面取向,以及为挽国难致富强,以学术研究参与时事时政,少有注意,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地学会在华洋新旧学理、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纠结与挣扎。本文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将其置入近代中国华洋新旧杂糅的历史现场,全面考察中国地学会构建科学地理的事实,尽力理解前人意图,体会前人创业的艰辛。
一、调查为基
清季学界华洋新旧争锋,如何取舍至为关键。趋新者认为中学不足以应变局,倡言“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智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智识”②《论本报第三年开办的意思》,《杭州白话报》第3年第1期,1903年7月。。日俄战后,时人深感日本对中国持侵略主义,忧虑新学步趋日本,称“故人而无精神上之独立,则人将非人;国而无学问上之独立,则国将不国”,若早得教育、学问的独立,“日本人虽有野心,奈何我国人”*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8期,1906年11月30日。。光宣之际,以“留学东西毕业专门者,及毕业本国高等以上学堂者”*李守郡:《清末结社集会档案》,《历史档案》2012年第1期。为主体的专门学者群体形成,科学学会蜂起,构建新知识的条件初步具备。
新学地理学者组建的中国地学会,认为人类聚族求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故疆域随民族的盛衰而盈缩,“然溯厥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近世以来中国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今日地理虽为学校重要学科,学者兢兢业业,“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但相比西人调查水陆要地“以资生利用者”*《地学协会启》,《大公报》(天津)1909年9月22日,第2张第3、4版。尤不足言,以致出现“近世地理诸书大抵译自外国,凡外人之所述者,则复冗无节;外人所未述者,则漏略弗详”*罗汝南撰,方新校绘:《中国近世舆地图说》,宣统元年,广东教忠学堂石印本,“自序”。的尴尬局面,亟需调查兴学,以竞争求存。
其时,在国人的认知中不仅地理,“西人各种事业皆以调查为起点”,甚至“俱有一种调查之学问”,“至于各种专门学会及一切企业会社,尤以调查为专务焉”*《顺直咨议局预备议案》,《大公报》(天津)1909年11月2日,第2张第3版。,因此朝野各方热议调查。中国调查方兴,只能通过外人调查了解自国,国人痛言:“鄙人有心于蒙古久矣,寄居异国,不能身入该地,从事调查,而又鲜国书参考,苦极苦极。不得已功课之暇,访问游蒙诸日友,及涉览外人之著作。”*《蒙藏宗教谭》,《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3月6日。而外人在华调查,限于中国地大,又有种族、语言、时间、交通诸多不便,范围有限。来华调查的外人抱怨:“盖外人旅行于中国内地,甚为困难。所可调查者,仅沿官道一线,及其附近之地而已。”且调查者又非必为专家,“其所报告大抵据土人传说”*史廷飏译:《中国矿产》,《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3月1日。。欲以此为基础构建科学地理显然不够。中国地学会认为中国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调查全国仅靠个人力有不逮,政府又不作为,惟有合群分测,因此定调查为会员的义务。为推行调查,会所暂时设在天津,日后拟在京师设干会,各省设分会,由此推及各府州县,以方便调查。
中国地学会重视调查,学术外兴学战保利权亦是重要考量。海通以来西人屡屡来华调查,“北自天山,西北至卫藏,东南际海,中国官吏,或有未至,欧人之车辙马迹,已无不交错于道”*王与龄:《忠告上篇》,《昌言报》第10册,1898年11月19日。。光宣之际,国势愈衰,外人来华调查几无忌惮。1909年6月21日,舆论报道入藏外人“无一而非野心家也”*《外人入藏如此之多》,《民呼日报》1909 年6月21日,第2页。,西藏不亡何待;6月23日,又谓日本政府数年来派法政学生赴中国调查,福建两广云贵皆已完成,“以视我特设之调查局其呈功为奚若也”*《日本调查浙江详情》,《民呼日报》1909年6月23日,第2页。。外人屡屡入华调查,国人则因地理不明,内政不修,外交失利,趋新国人呼吁“非正疆域无以策治理之方,非勘边界无以戢侵越之渐,非悉险要无以筹攻守之法”*《皇朝舆地通纪例言》,《申报》1898年7月26日,第2版。。随着地方人办地方事的地方自治主义兴起,各地纷纷设立调查会,调查本地各项事业,助力官绅办事。缘此中国地学会定调查兴学、资益内政外交为主要事业。
西人认为,地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之一是拥有专门报刊。甲午战后国人兴学会办报刊,倡议维新与新学,但多政论少专门。1910年前后,舆论认为专门报刊与学术关系甚大,“盖实业专门之学日盛,则其报日多,报日多则实业专门之学愈盛”*高松如:《农会报序言》,《湖北农会报》第1期,1910年5月23日。。中国地学会在发起时,即将编辑杂志列入章程。正式建立后,选举有编辑部长、编辑员。1909年10月3日,其自承应办事项甚多,暂时因经费支绌未能全部筹办,先按期出版杂志作为交通联络的机关,编辑由会员尽义务,印刷费则由张相文垫付,又预定下次会议筹议“发行杂志办法”,审定“调查册式样及条目”*《开会续志》,《大公报》1909年10月5日,第1张第6版。。
1910年3月1日,中国地学会正式出版会刊《地学杂志》,作为学会内外发表研究、交流学术以及推行全国调查的交通联络机关。《地学杂志叙例》写道:外人游历我国,辄就调查编著图说,“阳以饷其友群,或转而溉其馀沥于我国”,国人游域外,对彼邦“则耳熟焉而未能详也”。域外且不论,国内“间有之亦略而弗瞻,否则十年数十年以上之陈述无当于目前事实,否则日记月报一见再见而弗能为继,否则偏隅撮壤传闻异辞而未窥乎全局,皆非所以观变迁审形势也”。人类合群居住“竞争应事而生”,为唤醒国人特办刊,“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体裁则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内容注重民生、物产、疆域沿革,“国际为尚,教材次焉”*《地学杂志叙例》,《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3月1日,。其后,中国地学会发布启事,谓政学军商各界君子有调查所得、见闻所及,请予赐稿,“以期互相研究交换知识”*《启事》,《地学杂志》第1年第2号,1910年3月30日。。
《地学杂志》出版后各界对其甚有期望,舆论称世界进化需要专门人才愈多,“假令承学之子咸知自奋,则专科杂志之出也,适足以投其所好而已”。中国地学会诸君共同努力,“至吾国地学之发达,吾亦将于是杂志之风行卜之矣”*《绍介与批评:地学杂志》,《教育杂志》第2年第5期,1910年6月16日。。会员马登瀛、贾树模希望其能一扫中国地理学界的弊病,声称地理为施治基础,“且非知其最近情形不能应用。而吾国地理学图书或取材古籍,或则恃外国之本,实不免明日黄花及以讹传讹之弊。自有此会会员各尽调查之义务,有《地学杂志》以报告全国,从前之弊可一扫而空矣”*马登瀛、贾树模:《新疆行程记》,《地学杂志》第2年第11号,1911年2月18日。。
中国地学会虽极力推动国内调查,但经费匿乏,维持会务所需的每月200大洋,尚需张相文补贴,调查计划举步维艰。1910年5月8日,中国地学会总理、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致函各省提学使,称地理涉及甚广,“非联络各省各属不足以广调查”,今就《地学杂志》“以为交通之机关”*《三月二十九日总理傅咨送各省提学史札饬直属各学堂稿》,《地学杂志》第1年第4号,1910年5月28日。合力调查全国,并意图通过销行杂志,获得维持会务与推行调查的经费。然而《地学杂志》是受众有限的专门杂志,获利维持会务尚且勉强,求其用于全国调查,不啻杯水车薪。1911年3月20日,中国地学会禀请直督陈夔龙出面筹款,称调查全国、编印杂志“挹注为难,故东西各邦皆由其国家主之”,今日国家财政支绌,“拟即普告海内名公巨卿、通人学士量力捐助,请大帅登高而呼”,“异日地学昌明与世界各国争先并进,皆大帅维持之力也”。陈夔龙批示:“由本大臣捐助银圆伍百元,以资提倡。”*《二月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陈禀并批》,《地学杂志》第2年第14号,1911年5月18日。
中国地学会调查计划难行,除经费外人才缺乏亦是重要原因。其时趋新人士多为旧学出身,通过杂志、译书改宗西学;留日者则多为速成师范生,未经过专业训练又缺乏仪器,期望有成不亦强人所难。《地学杂志》刊载的会员调查报告,仅有张相文《大梁访碑记》《粤西琐谈》《冀北游览记》《滦阳纪行》《豫游小识》,英华《关外旅行小计》,马登瀛、贾树模《新疆行程记》等寥寥数篇。考各家作文目的,以文学知名的张相文主要是仿古与回忆旧闻,英华为病后散心,马登瀛、贾树模因为有事于新疆顺道而为,既非以调查为目的,又未进行实测,皆重文采轻专门,未脱固有游记的窠臼。1930年代,张其昀尚谓:“地理学固有赖于游历,但世人所发表之游记,其足称为地理著作者实甚少。余曾言从前游记之体,每重文辞之美,留连光景,低囘陈迹。是其所长,而今日学术之所尚则异焉。”*张其昀:《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科学》第20卷第6期,1936年6月。
中国地学会的调查计划搁浅,致使《地学杂志》所载调查报告多系译文,详外略内,兼且国事艰危,救国迫急,欲实行调查,时间难裕,只能采用旧有,其痛批的“略而弗瞻”、“陈迹”及“传闻异辞”等弊病自然难以避免。章太炎指出清季学术详于域外略于内政:“在清末叶,国事纷扰,外侮日迫,有志之士,欲唤醒国人迷梦,故对于域外记载,不厌其详,其流弊至使内政要点,处处从略”*章太炎:《在金陵教育改进社演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一九二四年七月上旬)》,章念驰编:《章太炎讲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3页。。中国地学会会员苏莘论调查全国,“以土地如此之广大,实测者百什不及一”,必须“分省分道分县实行调查”*苏莘:《地学丛书序》,张相文编订:《地学丛书》,民国十七年。,并有强大的人才、财力支撑,然而中国二者皆窘,调查难行。
二、引入学理
中国地学会建立时中西学术易势,早在1906年2月,在华传教士已感受到中国的变化,谓:“时至今日,华人之讲求洋务者众矣,仿效西法,崇尚西学者亦日益多。”*《商原》,《益智汇编》1906年2月,参见刘望龄:《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183页。西学的引入较西法又少政治等各种障碍,时人指出“惟学科之研究,器械者也”可以移花接木,因此学术的引入“交易之性质耳,无所谓权利于其间也”*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8期,1906年11月30日。,而欲谋学问独立首先应引进学理作“根本之改革”*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续)》,《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9期,1906年12月16日。。中国地学会认为地理旧籍不足用,科学还处萌芽时期尚极幼稚,引入东西学理是构建新知识的前提。其时,国人对此多有认同,雷铁崖称:“中国数千年来安于旧有学识,方自得为文明大国。今日欧潮东渐,民智渐开,乃觉人之文明优于我,我不追风步影,以求其可立于竞争之地位,则必归于天演之公理,此近日吾国民之心理也。”*雷铁崖:《谠言》,唐文权编:《雷铁崖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
中国地学会规定《地学杂志》刊文以国际为尚,意欲引入外来学理,兼通中西。纯粹学理代表学术的高度与成就,又是致用的基础,成为中国地学会输入的主要内容。引进外来地学学理,自以西洋为首选,若德国自然地理、法国人文地理、美国气象学之类。然而是时中国尚无在欧美学习地学回国的留学生,国人通西文者又无专门知识,求其做纯粹学理的翻译显然为难。中国地学会只能将名誉赞成员德瑞克在学会的演讲,以《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为名刊发,聊胜于无。其称中国地学“古有发明”,因未被学者列为专科研究“故后世卒鲜进步”。当今地理范围极广,关系各科甚深,研究地理学“须先明与地理关系最切之地质学”,盖地理学以考察山脉、海洋及生物分布为主,“而其生成及作用”无不关系地质学。至于讲演的来源:一由实地考察所得,一就地质学学理推断而来。此前中国锁国,旅行求学者绝少,故地理学不发达,现今中国地学会提倡实地调查,各处情形不难明白,“况地质学精则山海之成因,生物之分布,皆可推覆而明其故。地理之进步,不难一日千里矣”*德瑞克讲演,王世英口译,耿兆栋笔述:《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3月1日。。
德瑞克的讲演外,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之子,其时刚从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张星烺,翻译美国唐雷《地轴移动说》。文章以抽象理论解释现实中的国界争端,指出地球有绕日、自旋两种移动。自旋带来的极点变动、纬线变迁,导致国家边界改变,极易引起国际争端。美国与加拿大边境有一段以北纬49度为界,若发生边界争端,“必因实测之纬度,生出许多纠葛,可预言也”*[美]唐雷著,张星烺译:《地轴移动说(续前)》第1年第9号,1910年11月21日。。而其移动的规律,因地球“质体”不一,不能拘于一说,至今未有定论。由石焕如自东文转译的《人类起源之时代》,则是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宾古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说,内容主要是提倡综合各学科研究人类的起源*宾古演讲,石焕如译:《人类起源之时代》第2年第16号,1911年9月12日。。
西洋学理的引入因地理距离与语言的隔膜受阻,但中国地学会多有留日、知日的会员,熟知东京地学会及其会刊《地学杂志》,所以引入的学理大体为东学。时人亦称:“世界文化最高之国,无过于英法德美奥者。而东方新兴之国,厥惟日本。”*陆费逵:《论各国教科书制度(1910年)》,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75页。中国地学会编辑员史廷飏翻译中村清二的《极光之成因》,此文认为从极光的地理分布来看,距离地磁极愈近愈多。其出现的频度与太阳黑子的活跃度有密切联系,“黑点多时极光亦多”,且周期皆为11年。最后中村指出:“盖所谓极光者,即空气上层极稀薄处所存之一种真空放电也。以真空放电之故,而使地磁气变动,又使大气发光。极光之现,实由于此。”*[日]中村清二著,史廷飏译:《极光之成因》,《地学杂志》第1年第3号,1910年4月29日。
1910年5月28日,《地学杂志》刊发可权译佐藤传藏《冰河原始论》,指出冰河期的生成,前人“或谓当归于天文学者,或谓当归于地理学者”,今世学术进步,兼其两说,“且有确凿之证据,是亦一快事也” 。过往诸说无足取,其可信者如克罗尔的说法,根据有二:“一地球轨道之变化,一春分点之前进。”就地史来看冰河时代的中间,“似有消长痕迹,是必其时有一定季候,因间歇而生成者”*[日]佐藤传藏著,可权译:《冰河原始论》,《地学杂志》第1年第4号,1910年5月18日。。
中国地学会认为地理不明,每致交涉失败,丧权失地,欲研究地理以保利权,因此对涉及领土的新学理极为敏感。而此类问题亦是国人与舆论注目的焦点,典型的如飞行器,得到各界的关注与舆论连篇累牍的报道。《东方杂志》称飞行器开启了战术革命,欧美各国无不力求进步*《战术上之大革命》,《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1909年11月7日。军咨处会同海军处、陆军部通告各省,轻气球各国应用已久,“颇得效力,现拟先于全国陆军添备交通专队”,并着各省访查保送“曾在外洋习练熟谙此项制造运用专门人才”*《陆军飞球专队预备法》,《东方杂志》第6年第12期,1910年1月6日。。中国地学会从地理专门视角,重视随飞行器产生的空中领土论。1910年4月29日,《地学杂志》刊载《飞行器与空中领土》指出今日英美德法日均设有飞行器研究会,随其产生的领土问题,得到国际法学家的关注。若以飞行器“可得升上之范围”为领土违反国际法,“故领空之范围随飞行器之进步早晚必得有确定之一日”。现今各国热心研究“空中领土可得侵犯与否”*《飞行器与空中领土》,《地学杂志》第1年第3号,1910年4月29日。,以维护国权,中国亦不可不早作准备。稍后,舆论呼吁各国抢占空权,中国却茫然无知束手待毙,“恐大陆瓜分之局必一变而为空中瓜分之局,言念及此可为寒心,吾愿我国民勿以此为怪诞,勿以此事为夸大”*牛逊:《论航空事业我国急宜防备》,《民立报》1910年11月22日,第1页。,与地学会不谋而合。
中国地学会援引外来学理,发达学术外力求学以致用。梅雨是中国长江中下游、韩国南部、日本中南部,每年6月中下旬至7月上半月之间持续天阴有雨的地理现象,与生活、生产关系甚密。江苏全省皆有梅雨,苏人主导的中国地学会当然关注其研究。史廷飏译《梅雨发生论》,称梅雨的成因,气象地理两家说法不一。马场信伦主张低气压说,顿野广次郎则认为是高气压的作用。冈田武松为支持马场的低气压说,著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又批评“世人之论梅雨者,谓起于季节风交代时,因气流反对冲突,致令淫霖不止”,缺陷在“第一不知季节风之理由;第二不知时期之差异,勦袭旧史,诞妄不经,未足为据也”*史廷飏译:《梅雨发生论》,《地学杂志》第1年第4号,1910年5月28日。。
海通以来,外来专门学者的在华调查报告,以致用而言价值颇高,至于其本东、西学理条理、剖析中国地理材料,亦值得中国学者参考。1910年3月30日,《地学杂志》刊发杜之堂译石井八万次郎《楚蜀之山形地质谈》。石井自称1902年在宜昌至成都间旅行,考察地质。他记述湖北到四川大部分是片麻岩,“褶曲如磐城之高原”,其余赭土、沙岩、石灰岩“亦层累褶曲,不为水平线而为波动势”。经过外力的侵蚀,“向斜谷为赭土、为砂岩,其色如赤铁矿,小丘起伏,风景畅快,农园村镇所在多有。背斜谷之两侧,石灰岩耸立,谷幅峭狭,阴郁而险峻,中国画家每峭石壁立悬瀑奔湍即背斜谷之特色也”*[日]石井八万次郎著,杜之堂译:《楚蜀之山形地质谈》,《地学杂志》第1年第2号,1910年3月30日。。其后,史廷飏译《钱塘江沿岸之地质》,称江西与浙江之间“多赭色砂岩及中生代砂岩,因此砂岩之作用”*史廷飏译:《钱塘江沿岸之地质》,《地学杂志》第1年第7号,1910年9月23日。,成为鄱阳湖与钱塘江的分水岭。桐庐主要是花岗岩、石英斑岩,诸暨则大部分为结晶片岩。根据地质调查,衢州虽有煤炭,但运输不便,没有开采的经济价值。
中国地学会欲引入外来学理构建新知识,受时代、语言及自身学识的限制,输入的主要是新兴的东洋地学,而非高明的西洋学理。且日本地理面积狭小、环境单一,其研究难于对应面积辽阔、地形复杂数十倍于其的中国,以中国地学会极为重视的导淮研究而论,日本国小河短,没有治理大江大河的经验与学理,美国有治理大河及建设近代大型水利工程成功的案例,又引入无门,只能因循旧理。
三、洋为中用
清季中国科学幼稚,教育与学术多本译文。舆论反思学习外人以前太过保守,今日又有点过火,中国虽有不足,“岂能就把中国整个的不要了,改随外洋去吗?”故“只可以学他们的精神,不必尽求其形式”*《太过与不及》,《伊犁白话报》1911年4月23日,参见刘望龄:《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第345页。。尤其地理又是地域材料性较强的学科,外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国显然无法照搬。学界对此早有注意,张相文鉴于地理教科书取材域外,学生惘然不知,“就中国地文上事实,羼以普通地文学之教材”*《张相文呈新撰地文学改正再呈审定批》,《学部官报》第136期,1910年10月23日。编著《新撰地文学》,大受师生欢迎,热销二百万部。学术上光宣之际接受系统西式教育的学生开始进入学界,据新学学理以局中人的视角研究中国地理,自与外人有别。
中国地学会会员、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学生章鸿钊,1909年假期回乡省亲,游名胜黄龙洞,著《黄龙洞生成观》。文章谓,《吴兴志》记弁山黄龙洞“石随龙势”,相传有黄龙出而得名。历代游记多记形胜、雄奇,岩质及生成原因则未有涉及,于“是龙见之说所以历久未去”。据调查弁山是赤色砂岩,“其下恒有含炭之砂岩层”,且富含黄铁矿石。山道多是石英岩,洞外是方解石,洞内是石灰石,由岩石及地质构造证以地方志,山洞的生成“已彰彰无以遁其形矣”。洞南的圆石“为洞口沉积之证”,即所谓喷泉塔,与孟莫司泉的生成当“在伯仲之间”*章鸿钊:《黄龙洞生成观》,《地学杂志》第1年第2号,1910年3月30日。,可知黄龙洞的生成仅千余年。文章沟通中西,以地质学原理、方法解释地方志的轶闻传说及地理现象,可谓有得。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种族的生存基础,历来受国人重视。地理与农业关系甚大,中国地学会欲引外来学理研究农业,促进其发达。留学日本拟学习农科,受名额所限改学地质的章鸿钊,在调查时注意到杭州乡民将石灰作为肥料使用,甚为忧虑,遂着手研究肥料的要点,石灰为肥料的利害以及地质、气候与肥料的关系,撰为《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患》。文章指出农业生产必恃肥料,若选择不当则膏腴为石田,其他国家或许可以用工商业补助农业,工商凋敝的中国惟有束手待毙。
肥料学的要点在知道植物生长所需与所缺,所需十余种要素除窒素、磷酸、加里必须人为添加外,其余均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且用之不竭。农家不懂肥料学,只知沿袭先辈经验,而不知石灰是没有肥力的间接肥料,利在“(一)石灰能使土中有机物速为分解;(二)石灰能化土中不溶解物为溶解物;(三)石灰能治诸种之矿毒”,害处是“(一)耗竭地力;(二)消灭耕土;(三)能使产物品质渐劣”,长期使用地力渐竭。日本为指导农家施肥,设有肥料检查所,“以长官监督之”*章鸿钊:《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忧》,《地学杂志》第1年第10号,1910年12月21日。。中国应借鉴其办法,设立专门机关调查地质、物理的关系,以图农业的发达。
因地力关系国家盛衰、朝代更迭,日本札幌农科大学中国留学生陶昌善,议论地力养成的原理及方法,作《地力说》,刊载在1911年3月20日的《地学杂志》。文章称地力有广狭的分别,广义有负力、植力、养力;狭义仅指养力,即“土地之中贮其天然养分,供诸植物吸收,得助其生长者是也”。就农业经济学而言,地力是土地的生产力,土质不同地力有异。土地收获与养力正相关,中国“文化日进需要益奢,人口日众生计愈艰”,国土又遭外人侵蚀,“不足供四亿人民之食”。惟有恢复地力,“或灌溉以匀其养分,或排泄以除其卑湿,或用农业机械以深耕,或施人造肥料以肥土,或输作栽培使地力无偏枯之虞,或耕地整理使土地尽利用之道,或撒布细菌类以摄取空中窒素,或举行客土法以改良偏颇土质”,方能足食。纵观四千年历史,“吾中国地力之消长,实与朝代之隆替相循环于其间也”*陶昌善:《地力说》,《地学杂志》第2年第12号,1911年3月20日。,亟宜研究以为国用。
日俄战后,日本觊觎中国内海渤海,强指其为公海,征收渔业税,登刘公岛伐木*《第二之东沙岛又现》,《民吁日报》1909年10月23日,第2页。,挑起国际法、领海权的争论。中国地学会为维护国权,连续刊文与之相争。《渤海湾全部为中国领海说》阐述渤海为内海的理由,斥责“稍明国际公法及地理学者类能知之,乃日人故为异议,晓晓强辩”*《渤海湾全部为中国领海说》,《地学杂志》第1年第5号,1910年6月26日。。实际上渤海问题争论的本质不在地理或者国际法的证据,有贺长雄声称:“苟亦以国际法争之者,迂之极也。要惟在以实力速与对手国(即中国)结特殊之条约而已。”*《东三省中日交涉近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7月31日。《民立报》报道外务部与日本公使交涉,亦称:“探系确因该国兵队觊觎渤海,有实行占据之说,故极力要求撤退,否则另有办法云。”*《渤海之风声鹤唳》,《民立报》1910年12月24日,第3页。渤海之争在实力而非学术,然而书生舍学外夫复何为。
1911年3月1日,舆论谓渤海交涉尚未解决,外务部咨奉天省实地测量划清领海与公海,“以固疆圉而保主权”*《关于领海之部咨》,《民立报》1911年3月1日,第4页。。5月13日,又报道政府命各海关道“查明海权界线”*《嘻领海尚未划界》,《民立报》1911年5月13日,第5页。。缘此,中国地学会会员白月恒著《渤海过去与未来》,将渤海分为洪水以前、洪水以后、自今以往三个时期,论证渤海未来必然为桑田。其称,在冲积纪华北平原皆为大海,随着水力、风力等搬运的泥沙沉积,“水量日缩,陆地日增,四围山脉陡起,自然有海岸迥绕之势”。据地质及考历代史志推测,洪水期以后的渤海海岸线,“较今日渤海面积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间”。未来渤海若以每千年沉淀五十里的平均速度计算,二千年后“当半为桑田矣”*白月恒:《渤海过去与未来》,《地学杂志》第2年第14号,1911年5月18日。。白文本意在以学术参与交涉,但政府对外交持秘密主义,防范舆论,又严禁士子议政,所以文章只能据地理学理研究渤海海域的变迁及未来趋势,间接为争端寻证,并引起国人关注。
20世纪初,中国种族意识觉醒,各界热议人类及中国种族的起源、形成等问题。种族与黄祸论起自欧西,德皇首倡黄祸,“欲撩动欧美人之妒忌心以倾覆中国”*《论说:论世界之祸变》,《民立报》1911年9月30日,第1页。,同为黄种的日本人附和,因“日本自以为执东方各国之牛耳。以统一亚细亚人。抵制欧罗巴人之势力。为其目的之一”*《日本与印度》,《东方杂志》第8年第1号,1911年3月25日。。俄国为侵占蒙古,声称汉人移民蒙古,渐及俄国边境且日进不止,若任由四亿汉人蔓延,将影响俄国内地以及欧洲各文明大国。又在蒙古掘坟,以证其原有人种是白种人*《俄国对蒙之大阴谋》,《民立报》1911年3月1日,第1页。。学界关于人种起源主要有多源说、一源说,西人倡中国人种西来,国人看穿其在学术外为殖民张目的意图,力主国人“黄帝其祖,中国其名,满汉蒙回苗藏安南朝鲜其同谱而一系者也”*瓜刨:《中国学界联合会序》,《民立报》1911年5月27日,第1页。。
1911年11月10日,《地学杂志》刊载熊秉穗《中国种族考》,以中国古典附会西学,称人类起源有人认为全部发源于帕米尔,有人说各大洲人民都是发源于本土,然而“本世界以前,当有无数世界”。谭仲鸾说《河图》《洛书》即是此前世界刻石沉入水中,至大禹时被发现始得以再次出世。再证以墨西哥万年前的古碑,“盖荒古时文明之扫荡如此类者不可胜数也”。其又曲解外来学理混合多源与一源说,声称中国及巴比伦的古传说不足为据,然人类起源久远,“中西古籍所记皆同亦可异矣”。据近世地质学家论证人类遗迹在一万至十万年间,洪水时地势最高的葱岭成为人类的避难所,水退后分徙四方。“是故谓各洲人民皆发生本土者,乃洪水以前之事,谓来自帕米尔者乃洪水以后之事也。”洪水时避居本地高地的遗民,各据本土“蕃育子孙”,日久遂与外来的客民“相混合而不能辨”,为证此说,“试就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而纵论之”。
中国在黄帝前已有人类,如神农、炎帝、蚩尤等族,但黄帝来自西方的说法亦未错,《史记》记黄帝归老昆仑,因黄帝一族由帕米尔东迁中国,“既老,不能无故乡之思,故归于昆仑墟耳”。亚洲各大民族无一不有迁徙,“且多缘迁徙而盛强,几若自成一公例”。数千年来,“大抵能得善地则兴盛,不能得受善地则衰败”,黄帝率族东迁世君中国,“赫然为全国各族代表之故,可以类推矣”。沙漠种族匈奴、突厥、蒙古亦相继以迁徙得地利而强盛;通古斯种散居北方,鲜卑、回鹘、契丹、女真等各种相延,“今人以满洲为东三省地与人之总称,实非其旧”,至于各族内迁后汉化“皆顺天演之自然为同化也”*熊秉穗:《中国种族考》,《地学杂志》第2年第18号,1911年11月10日。。熊秉穗意图以地质、进化、种族说附会中国传说与古史,证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与西人各族并无不同,并欲寻种族盛衰的道理以为鉴戒。
近世以前国人基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包容,对待外来学术,每行取珠还椟之策,取其精华弃其形式,将其融入中学之中,从而造成一种新学问。地学的特质也决定了外人以域外为对象的研究难以符合中国情形,故中国地学会借外来原理、方法,解释中国地理问题,是为构建新知识的必由之路。但此种做法对学者自身的学术素养要求较高,高明者自能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平庸者则每易流于穿凿附会,但因其论证符合大众心理,往往较高明者更受欢迎。
四、条理旧学
光宣之际国内实行西式教育未久,新学中坚几乎皆是旧学出身,改宗西学,欲引进新理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贯通中西自创新法。仅就地理而言,西人公认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研究,是广博的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超过了同时代的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美]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如何处置考验学人智慧。高田早苗声称:“支那真有变法自强之一日,其必于在举支那旧来之学问与西洋新学而调和之”*韩梯云:《注日本高田早苗之支那教育论(续)》,《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19期,1906年12月16日。,方能自强。1906年11月,尚热衷西学的王国维,论文科大学欲聘遗老任本国学术教师,称遗老即使愿意应聘,“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疎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故若无合格的教授“则宁虚其讲座”。而学生经过大学的系统教育,通外国哲学、文学则研究本国学术必将超越老辈,“故真正之经学、国史、国文学之专门家,不能不望诸此辈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胡逢祥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6页。。其时学界不仅新学,旧学家亦有人主张灌输欧美文明,补救先儒学术*《广告:克复学报》,《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第1页。。
中国地学会宗科学地理,引入学理的目的之一在改造旧学,纳入新知识体系之中。1910年9月23日,《地学杂志》刊载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文章称古代地理学“非说古代平面地理,又与搜查邦邑建设之遗址,寻求人文发展之径路”的历史地理不同,其研究地球形成以来各个时代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对地形、自然界的影响。研究方法有纯属地质学范围的若岩石的生成与变迁、动植物的产生及分布等,“又有与考古学、历史学家调查,如制造之遗物,建筑之故址等”,另外地震等学科的方法亦值得借鉴。其意图引系统的外来古地理学体系入中国,上溯地理学至地质时代,补中国地理所缺,以使其“完成为一科学”*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地学杂志》第1年第7号,1910年9月23日。。
地图是地理发展的标帜,厘清地图学史则大体可知地学史的脉络,且直观易于比对,容易分别家派、形成系统。中国地学会编辑员陶懋立著《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引西法条理中国地图学,试图将其系统化,并建立清晰的学术脉络与学人谱系。其称中国偏居亚洲东部,自周至唐虽有地图传世,“然不知世界之大”。宋以后蒙古疆域达欧洲,得阿拉伯方法,地图学得以“大进”,知世界之大。今世五洲大同,西人地图学输入中国,“因是以有今日地图学之进步”。据此中国地图学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从上古至唐为中国自制地图的时代;第二期从宋元至明为阿拉伯地理学传入的时代;第三期从明末至现世为欧洲地理学传入的时代。
陶懋立在构建出完整的中国地图学系统后,又做出阐释,称中国地图学始于夏,“所谓一种之地籍图也”。晋裴秀制《禹贡地域图》,提出“制图六体”,被称为“吾国发明地图学之第一人也”。隋唐开拓疆域,西控西域,南达南海,“而地图学亦极发达”,其时一行“有用子午弧测定事业,是法或由阿拉伯传来而间接受希腊之影响者也”*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地学杂志》第2年第11号,1911年2月18日。。他强调地图学的发展需引入外来学理,声称欧人引东方的罗针、火器、活版印书,不以外来为耻,中国地图学引外来学理得进步,亦不需讳言。元得阿拉伯地球仪,知世界广大“益肆其扩张领土之雄心”,随着疆域渐广“因得以扩充地理上之智识”,故地图宋不如唐,明不如元。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入华,引西学入中国,地图学由不完善的方井式地图,进而为精确的经纬网。国初用西法测绘的地图,“记述大备,珍藏秘府,皆前古所未有者也”。《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历代沿革图》《大清一统舆地图》四家有世界观念的私家著述,“然皆本于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法,布设准望”。现今地图愈出愈精,大体可分为透视、投影、麦加多三方法,“然其轮廓方位,未尝稍变,故不复论及之也”。
陶懋立认为地图学的发展,除在学术外与政治强盛及疆域关系甚大,“大约国势经一次扰乱之后,地图必有一次更变”,或进或退,固“由其国力委缩,抑亦关系于学术者居多”。又以西法附会中国古法,谓西法以北极定纬度,中国“以星次定分野”。黄帝至春秋战国疆域狭小,分野星次的方法尚可。汉唐开疆拓土,分野星次不足用,“亦骎骎乎有变通统一之势矣”。其强调中国地图学的内生性,称若非宋明崇尚语录、科举败坏学术,“即无阿拉伯之科学,耶稣教之宗徒为之导线,必有人焉。俯仰六合出其伟大之思潮,祖裴秀、祢贾耽更为吾国地图学辟一门径,蜚声于世界之上可断言也”*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续第十一号)》,《地学杂志》第2年第13号,1911年4月18日。。故中国地图学当以固有为本,输入外来学理,发达学术以为国用,显示出中国地学会对待中西新旧学问的态度。
1911年6月16日,中国地学会《本会征文启》明确提出“顾维新知启迪,既有赖于专家旧学商量,期无封于故步”*《本会征文启》,《地学杂志》第2年第15号,1911年6月16日。,再次表达了构建新知有赖旧学的态度。1911年10月11日,陈学熙在《地学杂志》发表《中国地理学家家派》,赞誉地理学最为广博、实用,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智识,“向与历史学互相效用而并重者也”。西人当国者重视地理,以地理教育普及程度定国与民的强弱。印度土人不知地理,社稷倾覆。克莱武因知地理,以一介商会殖民印度。阿美利加著美洲地理,英、西次第殖民其地。就中国而言富源、矿产、边檄属地,“我尚茫然无知,或知焉不知所以藉手,彼已了如指掌,外交失败固亦宜矣”。据此,地理对于个人是谋生利器,对于国家是强弱的根源,对于世界是“天演淘汰之准绳”。故吉田松阴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先究地理。”
陈学熙主张学理上舍旧谋新,谓吾辈研究地理当摈弃无谓的考据、错误的事理,本“实地测践”以发达学问,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引新学学理改造旧学,称“欲知今当观古”,欲发达学问必先保存国粹,“而商量地理分别学派,以发挥而光大之,是亦保存国粹之一端也已”。
陈学熙附会中西,称地理学由希腊语地球与记录二字组成,我国向来称其为舆地。世界地理学始于公元前168年,我国的地理学则始于黄帝时期。上古中国地理首推八索九丘,次为《禹贡》《山海经》。《禹贡》为地理之祖,《山海经》后人不以地理书视之,然“人类未进化时地理学材料”皆如此,再证以西人地质学,其为地理书毋庸置疑。陈为与后世新学世界地理、中国地理的体系相合,曲解《禹贡》《山海经》二书“一则为域中地理学之鼻祖,一则为域外地理学派之鼻祖”。
其后,陈学熙以所谓古代中国地理学的禹贡、山海二派,系统地对中学地理进行了派分与整理。禹贡派即域中地理学派,古代地理书大半出自此派,“然其初属于财政范围”,班固继作一变而属于历史,皆未形成独立科学,其后学术昌明,离史独立。其分为:一地志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中国地理,取法《禹贡》,九州可分为郡国都城宫苑志、沿革志、形势志、利病志、游记五门;二水经家,“盖法禹贡导水而作”,可分为域于一地者、域于一水者、专志于海者三门;三山经家,“盖取法禹贡之导山”。古人自大不谈域外,故山海派势力稍弱,进步极迟,此派可分为:一瀛寰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外国地理家,有国志、游记二门;二自然家,即地质、地文学。二派五家或证经或考史,皆重在古今沿革,并非材料、学力不足,乃时势使然,“不能执此以咎古人之疏漏也”。
陈学熙又杂糅中西新旧学理,分萌芽阶段的新学地理为:一游记家,专志旅行兼及山川形势,为禹贡、山海二派的混合家,由王锡琪《小方壶舆地丛钞》开创,小学地理教员“多宗其意”;二新化家,研究山脉深得《禹贡》之意,创始人邹代钧办会译图,著述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沾溉士林;三中国地理学家,注重中国普通地理,由龚柴、张相文、屠寄、马晋义四家创始,为禹贡地志家的新学家;四外国地理家,以龚柴为鼻祖,《瀛寰全志》为代表;五自然家,多翻译少自著,张相文撰地文、地质两教科书,“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诚为教育国民的善本。文章最后感慨,在世界各国地理学中,“我国地理学派家数之多,学理之明,图籍之繁,大地世界雄飞突步,东西两洋奚多让焉;聊就所见,述为是编,贡献社会,为图史目录之一助,完全学说,是望通人”*陈学熙:《中国地理学家家派》,《地学杂志》第2年第17号,1911年10月11日。。由陈学熙派分的新学地理各家,著述多为译书或据译书编著的教科书,可见中国科学地理之幼稚。
中国地学会为纳旧学地理入新知识系统,引外来学理对其进行条理、改造,构建学科系统,编织学人谱系。其本意则较为复杂,后世研究者谓:“至少对清末的文人来讲,接受西学本身既非目的,亦非必然。为了捍卫中国文明的价值,他们必须重新组织自古相传的学术结构,以便跟海外传入的学术相衔接,并且主动地改变自己。”*严绍璗、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0页。至于其结果,早在1894年5月30日,国人就称中国格物与泰西“名同而实异”,如“仅赖传出,剽窃万一,类皆小试端绪,未能穷究根源,而欲以中西格致之学,合二为一,岂通论哉”*《西学以格致为要论》,《汉报》1894年5月30日,参见刘望龄:《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上卷,第31页。。1906年12月,章太炎指出:“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引西学“以徵经说,有异宋人以禅学说经耶?”“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二者议论的对象虽非地理,然亦能相合,中国地学会用力于此,结果却早已为高明者预见。
辛亥武昌事起,中国地学会实际负责人张相文、白毓昆、陶懋立等,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各项会务暂停。民初其人又借助中国地学会参与政治,构建科学地理的事业始终未能继续。至于清季中国地学会构建的科学地理,因调查全国的计划未获施行,早已失去根基,用力甚多的引入学理与改造旧学,又受时代及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引进的大体是经过日本条理的二手学理,改造更是穿凿附会多于真知卓见。其治学又掺杂功利目的,“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彼等于学问固无固有之兴味,则其中道而止,固不足怪也”*王国维:《教育小言》,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胡逢祥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4页。。构建科学地理的重任只能留待后人。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杨海文】
*收稿日期:2015—11—12
作者简介:谢皆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州 350007)。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