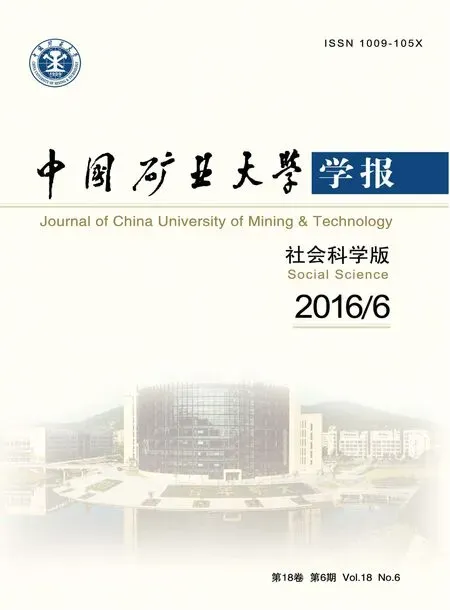历史的“再生”
——《再生》的一战想象与文化创伤重建
2016-01-23朱新福
朱 彦,朱新福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历史的“再生”
——《再生》的一战想象与文化创伤重建
朱 彦,朱新福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帕特·巴克尔的小说《再生》将文学想象融入历史事实,以克莱洛克哈特医院和伦敦国家医院作为主要场景重建一战叙事。文章将结合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揭示巴克尔将后方医院而非战场作为重写一战历史之场域的目的是在于英国一战文化创伤的重新建构——通过《再生》,巴克尔试图阐明一战中士兵和军官们的创伤被“医治”的过程也正是其逐渐被他者化和失去自己声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背后的父权体制运作才是一战文化创伤的真正根源。
帕特·巴克尔;《再生》;文化创伤;他者;父权体制
《再生》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帕特·巴克尔(Pat Barker)的代表作“再生三部曲”*“再生三部曲”包括《再生》、《门上的眼睛》和《鬼魂之路》,其中《门上的眼睛》获得了1993年的卫报小说奖(Guardian Fiction Prize),《鬼魂之路》获得了1995年的布克奖。的第一部。“再生三部曲”是英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正是凭借着一战题材的三部曲,巴克尔成功跻身英国当代经典作家行列,A.S.拜厄特将其称之为“英国不断涌现的一战小说中最优秀的、也是最有趣的作品”[1]。而《再生》(Regeneration,1991)对巴克尔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它是巴克尔写作生涯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部小说无论是在探讨的对象、主题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出版后给巴克尔带来的国际影响力方面,都是前期的作品无力企及的,“巴克尔早期的小说专注于特定区域的工人阶级女性故事……这一切随着1991年《再生》的出版彻底改变”[2]。小说一出版即在大西洋两岸大获成功,实现了极好的销售量,“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公众心理并没有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再生》也倾倒了无数读者”[3]65,《纽约时报》更是将其选为1992年最好的四种小说之一,该小说“给巴克尔赢得了英国女作家写作史上的非同寻常的地位”[3]69。
在《再生》出版至今的大量书评和论文中,评论家们从性别、阶级关系、互文性等方面进行过解读,但是很少有人将《再生》与八十年代后出现的记忆热潮和历史小说的繁荣联系起来,鲜有研究者考察《再生》的创伤记忆主题与英国当代历史反思的关系。本文将结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的文化创伤理论,解读《再生》所呈现的英国当代对于一战的再思考和文化创伤重构。文化创伤理论的提倡者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创伤并不是什么自然存在的东西,它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4]2,他批评那种认为创伤会随着灾难性事件而自然产生的观点并强调创伤的建构性,“事件本身并不会产生集体创伤。事件并非具有与生俱来的创伤性。创伤是一种以社会为媒介的产物,它可能是随着事件的展开而同时产生,也有可能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前作为暗示产生,或者在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之后,作为事后的重构”,甚至在创伤建构中也不排除因为各种目的而导致的创伤事件的被“想象”[4]8。《再生》中巴克尔将后方医院而非战场作为重写一战历史之场域的目的正是在于一战文化创伤的重构。通过《再生》,巴克尔试图阐明一战中士兵和军官们的创伤被“医治”的过程也正是其逐渐被他者化和失去自己声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背后的父权体制运作才是一战文化创伤的真正根源。
一、克莱洛克哈特医院:创伤记忆的幽闭
《再生》关注的一战对于英国人来说可谓影响巨大,战争中英国的士兵伤亡和财力损失都异常惨重,一战结束距今虽已近百年,但是在每年的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前后英国依然举行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对于出现在集体层面的创伤,社会危机必然转化为文化危机……事件与表征之间的过程被称为‘创伤建构过程’。”[4]10-11在英国历史上,一战早已被建构为文化创伤,“写战争经历的诗人、小说家、士兵和平民对于英国社会和战争相关的集体记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作者的创作见证了个人创伤如何转变为文化创伤……他们的个人叙事的出版和被接受的累积产生了集体叙事,这种集体叙事又成为英国社会文化创伤的基础”[5]55。根据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文化创伤建构包括痛苦的性质、受害者的性质、创伤受害者与广大受众的关系以及责任归属四个重要方面*参见Alexander, Jeffrey C, et al., eds.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3-15.。这些历史上的集体叙事将一战建构为“英国历史上的‘基本’创伤之一”,英国大众作为一个整体被建构为战争的受害者,创伤的责任归属也自然地指向了战争本身[5]53。
而《再生》对于一战文化创伤的阐释与历史上的集体建构明显不同,小说开篇即不同于以往的一战主题作品。巴克尔没有将目光投向惨烈的战场,而是转向了英国国内1917年7月到11月的克莱洛克哈特医院。这家设在英国爱丁堡的战时医院在一战时“主治患弹震症*弹震症是一个在一战中被首次使用的名词。1915年2月,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家查尔斯·S·迈尔斯首次发表文章,叙述了一战中在士兵中发现的精神崩溃症状和对其进行治疗的情况。因为迈尔斯猜想这一症状是因为炸弹在附近爆炸产生的物理力量或者化学效应引起,所以将其命名为“弹震症”。的军官”[6]164,当时“一些最为著名的弹震症病例——比如威尔弗雷德·欧文、西格弗里德·萨颂……”都曾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主治他们的医生是著名的精神病专家W.H.R.里弗斯[6]155-156。巴克尔正是选取了欧文(Wilfred Owen)、萨颂(Siegfried Sassoon)和里弗斯(W.H.R.Rivers)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主要角色,同时又在小说中增加了普莱尔和彭斯等虚构人物进行历史编纂,“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安排了某种张力”[7]104。萨颂和欧文不仅是里弗斯最有名的病人也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战诗人,小说正是从萨颂的《士兵宣言》开始的:
“我作出的这个声明是特意表示对军事权威的反抗,因为我认为这场战争正被那些本来有力量结束它的人故意延长……我相信这场我为了保护和解放的目的而参加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侵略和征服的战争……我亲眼目睹并承受了军队的痛苦,再也不想延长这种受苦,它的结果我认为将是邪恶和不公正的……我代表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抗议正被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欺骗。”*文中所引用的小说内容均为笔者自译,后面不再一一说明。[8]3
萨颂在声明中义正词严的反战态度使他险些被送进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幸亏萨颂的好友罗伯特“用尽办法说服上面萨颂是得了弹震症”[8]22,最终萨颂被认定为弹震症送进了克莱洛克哈特精神病医院。然而萨颂是否真正患有弹震症始终是令人怀疑的,小说中有许多细节都暗示萨颂似乎并没有得弹震症,比如萨颂的主治医生里弗斯对萨颂说:“我确定你没有疯。事实上,我甚至认为你连战争神经症都没有得……你似乎是有非常强烈的反战神经症。”[8]15弹震症作为战争导致的精神疾病,它的痛苦的源头向来被指向战争,而《再生》中对萨颂患弹震症的质疑却将萨颂痛苦的源头指向了英国国内。弹震症之于萨颂只是一个暂时缓解矛盾的方式,更进一步来说,萨颂弹震症的认定实际上展现的正是萨颂的声音被迫缄默的过程,萨颂危险的声音在弹震症的遮蔽下被转移到精神病院得以暂时免于被更多的人听见,而其抗议的声音也因此变成了疯话——“争议只有在病人被证明是精神病的时候才会终止。那就是这个事件的最重要部分。像萨颂这样的人总是个麻烦,但是如果他是有病的话麻烦就小多了”[8]9。对萨颂疯狂的认定也使得读者对克莱洛克哈特医院的性质产生了质疑,克莱洛克哈特医院在此过程中由精神病医院转变为萨颂反战的声音被转移和幽闭的场所,它的疯人院的性质就此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再生》的开篇即展现出巴克尔力图明确创伤受害者的性质和痛苦的性质的努力。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指出创伤建构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痛苦的性质和受害者的性质。巴克尔将萨颂的声明放在小说的最开始,在声明中,萨颂反复提到“受苦”(短短一段中提到三次),并提到要“代表那些正在受苦的人”进行抗议,萨颂将自己界定为受害者,并力图代表受害者发出声音,而最终萨颂抗议的结果是被以弹震症的名义送入精神病医院,这样从受害者的性质和痛苦的性质的阐释来说,《再生》似乎从一开篇就显示出与以往一战主题作品的不同。以往的一战主题作品多将士兵的受苦指向战争本身,而小说中萨颂等人的受苦不仅是因为战争,更是由于国内的“军事权威”,是那些“本来有力量结束它的人”,也即后来将萨颂送入克莱洛克哈特医院的人。在创伤受害者的性质和其痛苦的性质上,《再生》与以往的一战主题作品相比产生了根本的不同。
《再生》中的克莱洛克哈特医院也由此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无论是对于萨颂这样被以弹震症名义送入的反战军官,还是表现出歇斯底里等各种症状的弹震症患者,这里都隐藏和幽闭了其无法言说的创伤。而这种隐藏体现在诸多方面,不仅是萨颂抗议的声音,残疾的、畸形的身体在这里也被刻意地隐藏,比如同在克莱洛克哈特医院接受治疗的军官比利·普莱尔的女友萨拉在医院陪朋友探望病人时因迷路无意之中撞见了医院深处“一群身体出现残缺的人”:
他们不在医院前面,那样他们的残损会被路人看见。他们盯着她……这是一种完全空洞的凝视。如果包括什么内容的话,是恐惧。害怕她盯着空空的裤管。害怕她不看他们。她仅仅是在那里,成为一个不相干的,模糊却又是强大的角色:一个漂亮的女孩,她使得一切都变糟了[8]160。
这群伤兵的悲剧性不仅在于战争所造成的残损,更在于因为残损的丑陋而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国家隐藏,萨拉因此倍感愤怒:“尽管被迫扮演美杜莎的角色,其实她并不想伤害他们,她的无助感和某种愤怒融合在一起,她愤怒他们被像那样藏起来。如果国家需要那种代价,那就应该充分准备好正视这种结果。”[8]160
巴克尔在《再生》中首先是将这些被遮蔽和隐藏的创伤让读者“看见”——在《再生》中我们看到,一战的创伤,无论是有形的身体创伤还是无形的精神创伤,都失去了真正为人所知的可能。克莱洛克哈特医院成为创伤记忆幽闭的场所,那里的人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安度记忆深处创伤带来的痛苦,那些从战场带回来的记忆像幽灵一样,缠绕在军官和士兵们的周围,成为其挥之不去的噩梦。
二、伦敦国家医院:创伤记忆的“医治”
克莱洛克哈特医院转移并幽闭了战场归来的人们的创伤记忆,但它更是“医治”这些“弹震症”患者的场所。如果说弹震症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忆,治疗弹震症表现出的则是记忆被对待的态度。在创伤记忆被医治的过程中,《再生》进一步展现了病人的受苦,受害者的性质和痛苦的性质得以更深刻地揭示。
小说中创伤记忆的医治过程主要通过医生里弗斯的视角加以展现,里弗斯不仅医治弹震症患者,同时也对弹震症治疗进行不断的思考和反思。小说中提到医治弹震症的两种不同方法,除了里弗斯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鼓励病人通过回忆的方法从创伤中康复之外,小说中还提到里弗斯作为旁观者见到了医生耶兰采用电击疗法治疗弹震症的场面,它引发了里弗斯对于帝国医疗的反思。
里弗斯在伦敦国家医院的时候旁观了耶兰电击治疗弹震症的全过程。在此之前,里弗斯在观看耶兰巡视病房时就惊讶于耶兰绝对的“权威”地位,“虽然耶兰以前就给人权威的印象,但那也无法和现在比,他现在的腔调简直就是上帝一般”[8]226。之后旁观电击过程更让同样身为医生的里弗斯心生恐惧,“关窗帘,关灯,锁门”[8]229,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完全密闭和黑暗的环境中进行的,病人凯伦被捆绑在椅子上接受电击治疗,滚烫的金属片被反复送入喉咙深处。电击的目的是为了让病人开口说话,而经过持续数小时的电击,凯伦最终发出简单的单词并且按照要求对耶兰说“谢谢”。
旁观耶兰电击治疗之后的里弗斯在噩梦中又一次经历了这个场面,然而在噩梦中拼命把电极往病人嘴巴里塞的人换成了他自己,电极也变成了马嚼子:
马嚼子。毒舌钩在中世纪时候也被用来让不服从的妇女闭嘴*引文所对应的小说原文为silence recalcitrant women。在这两段引文中silence这个词被反复地使用和强调,比如silencing of a human being,the task of silencing somebody和he silenced his patients。,更近代的,是对付美国奴隶。然而在病房里,听着凯伦参加过的战役,他感觉凯伦无论说什么都比不上他的沉默更有力量。后来,在电击室里,当凯伦跟着耶兰来回走动并且开始慢慢地重复字母表时,在光圈内外,瑞沃斯已经感到他在目睹一个人的被缄默……
使之缄默。自己就处在耶兰的位置,在执行着使某人缄默的任务,椅子中是一个无法辨别身份的病人……正如耶兰通过消除瘫痪、耳聋、失明还有缄默等症状来压制病人无意识的反抗,他,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缄默着他的病人。因为军官们的结巴、噩梦、颤抖和记忆缺失只是和表现更明显的男性疯狂一样的无意识的反抗[8]238。
耶兰的电击疗法使里弗斯异常恐惧,而噩梦后里弗斯更加惊恐地发现自己和耶兰极度相似,他感到梦里在国家医院走廊深处碰见的脊柱严重挛缩的畸形人 “好像代表了萨颂”,而梦里那个被他塞入电极的病人“他确信不是凯伦”,而是自己正在治疗的普莱尔,又或者“只是一个以梦里所暗示的方式被缄默的人”[8]239。虽然表面上看来里弗斯和耶兰的治疗方法相去甚远,而且也人道得多*里弗斯和他的病人们保持着良好关系,病人们依赖并且信任他,甚至有的病人将他称为爸爸,甚至是“男性的母亲”(107),他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友善和同情的。,然而噩梦之后里弗斯却承认自己和耶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表面上他似乎是在祝贺自己用比耶兰更人道的方式对待病人,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自我谴责的感觉呢?在梦里他站在了耶兰的立场上。梦似乎是在以梦的语言在说:别夸自己了。没有区别。”[8]238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里弗斯曾经和弗洛伊德一样致力于梦的研究,“在其死后出版的《冲突与梦》中,里弗斯修正了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声称梦并非是愿望的实现,而是当前矛盾的无意识表达,‘在梦境中尝试通过有用的方式解决冲突。’”[9]662里弗斯的梦境其实正是其服务于帝国的地位和其对病人的同情之间的“冲突”的集中体现。在梦中,里弗斯经历了“一种最为痛苦的自我谴责”[8]237,为自己和耶兰一样压制和缄默着自己的病人而倍感内疚。如果里弗斯梦里的病人张大的嘴巴象征某种反抗的话,那么深入他们喉咙深处的带上电极的金属很显然是在执行压制反抗的任务,成为控制的力量。和历史上曾经“让不服从的妇女闭嘴”的工具的毒舌钩一样,带着强电流的滚烫金属也是让他们缄默的工具。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凯伦被缄默的表现却是开口说话。如果说凯伦之前的沉默和失语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反抗的体现,保存着抵抗的可能,那么在耶兰的电击疗法之后最终发声并对耶兰说“谢谢”的凯伦却完全丧失了所有可能的反抗能力,曾经缄默的凯伦用他的沉默实现着某种反抗,而现在开口说话的凯伦在治疗之后却是真正的被“缄默”了。
由此我们发现,在被“治疗”的过程中,士兵和军官们从战场带回的创伤记忆非但没有得到安度,相反地,一次次被控制与压抑的被“缄默”的过程造成了病人们更惨痛的创伤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里弗斯梦境中反复看见的畸形人的形象也可以被视为病人们在医院治疗的过程中更惨痛的创伤记忆的象征。如果说萨拉在医院里无意中遇见的残疾者是因为战争而畸形,又因为形体的丑陋被隐藏,那么里弗斯梦中的这个接近怪物的畸形人则是因被缄默的经历而产生的创伤个体的象征,是帝国军事医疗下诞生的他者。“再生”(regeneration)一词原本有精神病医生对精神的治疗和再生的意味,然而在《再生》中,巴克尔怀疑了创伤恢复和精神“再生”的本质和过程,赋予了“再生”以反讽的意味。
《再生》从开篇就已经通过萨颂的视角将痛苦的来源指向“军事权威”,在萨颂之后,巴克尔又选取了里弗斯作为聚焦人物,透过其视角继续展现克莱洛克哈特医院和伦敦国家医院中病人们被治疗的过程,一战受害者的性质和痛苦的性质也进一步被明确:从战场归来的士兵和军官们在后方医院遭遇了比战场更为惨痛的精神创伤,在“军事权威”的强权压制下,无数的受害者被“治愈”了战争创伤,继续奔赴前线,成为这场所谓“为了结束战争的战争”的牺牲品。
三、父与子:创伤记忆溯源
创伤建构除必须回答痛苦的性质和受害者的性质之外,还要回答责任归属的问题,也就是明确谁导致了创伤*参见Alexander, Jeffrey C, et al., eds.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3-15.。实际上,在阐明了痛苦的性质和受害者的性质之后,责任归属也就相应清晰起来。无论是克莱洛克哈特医院的“病人们”,还是医生里弗斯,都同时将一战受苦的来源指向了“军事权威”——那些“本来有力量结束它”却“故意延长”它的人。
然而巴克尔所揭示的创伤的责任归属并非仅限于此。小说中里弗斯在教堂时曾注意到教堂的彩绘玻璃上的圣经故事:
他抬眼向上,看见被垂下的旗帜半掩的祭坛,然后转向东边的窗户。窗户上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画面……下面更小的画面是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这东边的窗户表现着明显的选择:两个文明所声称的基于之上的血腥的契约。正是这个契约,里弗斯一边看着亚伯拉罕和伊萨克一边想着,这就是所有的父权社会所基于的契约。如果你,年轻又强壮的人,服从我这个衰弱老迈者,甚至达到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程度,那么,总有一天,你会得以从我这里平静地继承,并且也能够从你的儿子那里得到同样的服从[8]149。
巴克尔这里所提到的“血腥的契约”所指的正是圣经中的两个“父与子”的故事*圣经中的这两个父子故事英文表达分别为“Crucifixion”和“Aqah”。,其一是上帝为了救赎人类的恶让自己的独子耶稣受难于十字架之上,另一个是亚伯拉罕服从上帝的命令拿自己的儿子伊萨克献祭——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让其用自己的独子献祭,而最终因为亚伯拉罕的虔诚,上帝赦免了伊萨克,让他用一只公羊作为替代品。这两个父与子的故事代表了西方父权社会的基本准则,而巴克尔揭示了这种文明契约即父子关系背后的欺骗本质。这种要求“儿子”对“父亲”必须表现为绝对的忠诚和随时为之献身的契约是以“也能够从你的儿子那里得到同样的服从”为许诺的,而实际上,里弗斯看到的却是继承者相继死去,而“老年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聚集在一起唱着赞美诗的场面[8]149。“上帝献出自己的独子。但是他复活了。……那些在战场的烂泥之下的死尸没有被替代或是复活。一代人被像动物一样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继承之物。基督教的牺牲传统似乎崩溃了。”[10]106-107里弗斯对“两个契约”的思考提示我们“军事权威”所代表的英国父权社会的准则才是巴克尔所批判的最终对象,也是巴克尔所认定的责任的最终归属——“父子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简单,永远都不会结束。死亡也不会终结它”[8]156。在这种父权的体系之下,萨颂等人作为“儿子”变成了献祭的“伊萨克”,但是他们却没有伊萨克被赦免的幸运,等待他们的只有必死的命运。
在《再生》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父子关系,比如小说中对于萨颂、彭斯、普莱尔等人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都有描述,而这些父子关系都具有惊人的共性,即“父亲”对“儿子”的压抑和“儿子”的受苦,比如萨颂小时候:“一面黑色的椭圆型的镜子映出一个孩子小小的,苍白的脸。他自己。五岁吧,或许。为什么他现在会记起哪个?一天的喊叫,砰砰作响的门,还有眼泪,他不被允许进去。那天他的父亲离开了家。”[8]145不仅是病人,医生里弗斯的童年同样充满了对父亲的恐惧和愤恨,“作为一个言语治疗家和一个牧师,里弗斯的父亲象征了家庭、教育和教堂的男权权威的结合。”[3]34当里弗斯站在父亲的窗外,“他盯着父亲的脖子后面,这个人,他已经用某种方式杀死了。他根本不感到悲伤或者负罪。他感到快活”[8]155。小说中这些刻意安排的父子关系揭示了男权权威下“儿子”备受压抑的命运,加强了父权体制批判的力量。
同样,里弗斯和他的病人之间也有类似父子关系的成分,许多病人对里弗斯都有着儿子对父亲般的依赖。然而在小说的结尾,里弗斯这个一直处于痛苦挣扎中的“父亲”却将萨颂重新送回了战场——“里弗斯看见自己已经拿来了萨颂的档案……他没什么可以多说的了。他把最后一页打开,写到:1917年11月26日,结束治疗,回归职责”[8]249。对于里弗斯来说,给萨颂签字的这一刻他变成了那个自己曾经痛恨的“父亲”:“笔变成了献祭的刀子,但是却没有天使停留在他的手上。”[11]264里弗斯在这里扮演了亚伯拉罕的角色,尽管经历了自我谴责的痛苦挣扎,他最终却依然选择了成为父权体制的共谋。
对父权文化的揭示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前面提到的“军事权威”对于弹震症的恐慌、隐藏和压制。弹震症患者歇斯底里的表现完全颠覆了一战前人们对于男性的看法。在西方文化中,“疯狂具有着双重意象,它是妇女的一种缺陷,又是妇女的一种本质,妇女与疯狂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切断的关系。妇女与疯狂的文化关联性无处不在。而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也一直是精神病院内、院外的主要病人,以致人们把疯狂、歇斯底里、神经衰弱看作妇女病”[6]1-2。一直到一战前,歇斯底里都被打上了妇女病的标签而专属于女性,一战中出现的男性的歇斯底里的表现挑战了男性至上的文化,威胁了战争时期英雄崇拜的情结,必然引起当局的恐慌,无论是医生里弗斯还是耶兰,对弹震症的治疗,本质上无非都是对于父权体制的维护罢了。而如果说耶兰对弹震症的医治体现了对这种体制的坚定维护,里弗斯充满质疑之后的共谋则体现着妥协,“巴克尔理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揭露了男权体系与生俱来的矛盾,它建立在一定的被接受的男性气质的代码之上,在这个体系之中,主体发现自己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他们必须接受自己的位置和他们既定的角色。”[10]89
《再生》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场面:里弗斯的病人彭斯逃离了医院,在大雨中爬到山顶,他看见树上捆着鼹鼠和狐狸的尸体,于是他“把所有的尸体解下来,把它们围着大树排成一圈,他坐在里面,后背靠在树干上”[8]39。当离开大树之后,彭斯“回到了树林里,现在到了圈子外面,但是却看见自己还在里面”[8]40。这个仪式性的场面象征性地展现了无法逃离悲剧命运的悲哀,包围在动物死尸中的彭斯和动物们一样成为死神的祭品,无论彭斯和其他父权体制之中的“儿子们”怎样挣扎,重返战场终究是他们必然的命运。
结 语
《再生》不同于以往的一战主题作品,它将视角投向了英国国内,将后方医院建构为一战创伤记忆的真正来源之所,从战场归来的士兵和军官们在后方医院遭遇了比战场更为惨痛的精神创伤,他们在医院中被“医治”的过程成为其逐渐被他者化和失去自己声音的过程。小说还阐明了,无论是医院中弹震症患者的治疗还是以弹震症的名义将反战者送入医院的行为都服从并服务于英国父权体制下男性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和要求,而这种父权体制的存在本身正是巴克尔所建构的英国文化创伤的最终源头。“‘文化创伤’具有新的解释的潜力,将给予我们所熟知的事件和社会进程新的标记”[4]VIII。通过《再生》,巴克尔实现了英国文化创伤的重新建构,同时这种建构也成为英国九十年代后大量激增的历史小说反思英国历史的异质化声音的一部分,“《再生》是对战争和记忆重新关注的第一次浪潮的一部分,这个文化的潮流贯穿了整个的90年代。像《再生》这样的历史小说的流行加入了‘记忆’爆炸的潮流。”[3]66
巴克尔在小说中将萨颂和欧文等历史上著名的一战诗人作为主要人物也显然有着深刻的用意。除了创伤建构的主要问题,亚历山大还提出创伤建构必须具备三个要素——言说者(言说者也被称为载体群体)、听众和情境,文学家正是进行创伤建构的主要的言说者之一。《再生》中有相当的篇幅描写萨颂和欧文在医院治疗期间探讨诗歌写作的情景,他们的诗作反映了一战诗人创伤建构的意图:“一战诗人们寻找新的声音和意象表达荒谬的屠杀带来的无穷尽的痛苦。”[11]260通过在小说中插入一战时期知识分子进行创伤建构的过程,巴克尔的作品本身与其形成了对话的关系,表现了新时代的作家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一战重新言说的愿望——“载体群体也可以是代际传递的,代表了年轻一代在视角和兴趣上对老一代的否定”[4]11——通过事实与想象的高超融合,《再生》实现了历史的重新书写,这种历史的“再生”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对英国社会的再思考,是对历史上的创伤记忆集体建构的一次挑战。
[1] Byatt A S.On Histories and Stories:Selected Essays[M].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Rennison Nick.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s[M].London: Routledge,2005:27.
[3] Westman Karin.Pat Barker’s Regeneration:A Reader’s Guide[M].New York: Continuum,2001.
[4] Alexander Jeffrey C,et al.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M].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5] Knutsen Karen Patric.Reciprocal Haunting: Pat Barker’s Regeneration Trilogy[M].Münster:Waxmann Verlag GmbH,2010.
[6]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1980)[M].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7] Groot Jerome de.The Historical Novel[M].Abing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8] Barker Pat.Regeneration[M].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91.
[9] Shaddock Jennifer.Dreams of Melanesia:Masculinity and the Exorcism of War in Pat Barker’s The Ghost Road[J].Modern Ficton Studies,2006,52(3):656-673.
[10] Brannigan John.Pat Barker[M].Manchester,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
[11] Lanone Catherine.Scattering the Seed of Abraham:The Motif of Sacrifice in Pat Barker’s Regeneration and The Ghost Road[J].Literature and Theology,1999,13(3):259-268.
2016 - 03 - 17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帕特·巴克尔小说创伤记忆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SJB520)的阶段性成果。
朱 彦(1977—),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在读,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英国现当代小说; 朱新福(1963—),男,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I561
A
1009-105X(2016)06-0091-06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