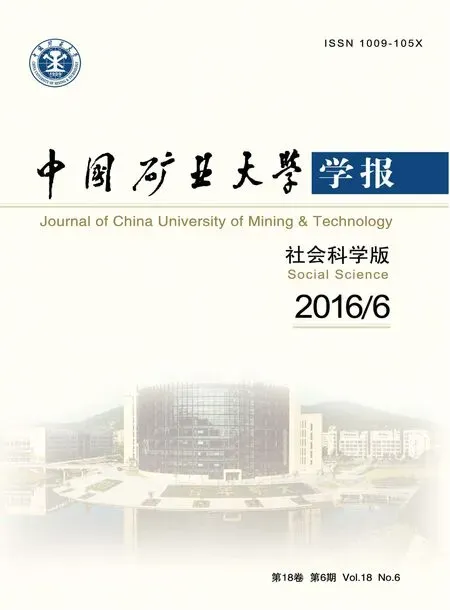学术史视阈下秦统一前后九原郡辖域变迁再探
2016-01-23尤佳
尤 佳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学术史视阈下秦统一前后九原郡辖域变迁再探
尤 佳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九原郡始置于赵,秦袭赵规。赵武灵王在赵国北境筑有内外两条长城,分别布列于阴山与狼山(阳山)山麓。赵人的势力曾越过阴山南麓的内长城,远涉狼山山脉的外长城,九原郡的西北边界也随之拓延至狼山山麓。自秦占有九原地到复夺“河南地”的这二十年间,九原地域并非固定、墨守于某一长城防线之内,而当处于一种复杂的盈缩变化之中,秦与匈奴之间势力的消长应是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
秦统一;九原郡;辖域变迁;学术史
关于秦郡问题,古今众多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尤以清代学者用功最勤、成果最著,然终未能形成统一意见。近年来,随着秦简、玺印、封泥等考古资料中秦代新郡名的不断出现,秦郡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如辛德勇对清季以来秦郡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仔细的整理和评述[1]3-59,林少平也对清代以来有关秦郡考证的论著进行了系统考察*参见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上编第一章《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页。。本文拟在学术史的视阈下,动态考察秦统一前后九原郡的辖域变迁及其原因,希冀不仅能有助于学界加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能对秦统一前后的边郡设置,乃至秦汉时期边疆政区变迁等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谬失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赵长城的分布与赵九原郡的辖域
史念海、辛德勇等先生认为,秦之九原郡沿袭于赵*林少平还认为,既有的研究成果在考证方法上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时间坐标体系,二是未考虑秦末变革因素,主张秦郡考证必须具有正确的思路,建立科学的方法。详参林少平:《秦郡考辨》,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23,2015年1月2日。实际上,关于秦郡问题,尤其是秦统一前后的置郡问题,一些研究论著已经通过建立时间坐标体系的方法,进行了动态考察,但林氏所强调的两点研究意见确实值得我们在现在及未来的秦郡研究中予以高度重视。。本文赞同其说,其论证过程周详、细密,于此不赘。囿于史料寡少,战国时期赵国九原郡的辖域情况,我们一直不甚明了,但赵之九原郡的辖域及其变化,对我们厘清秦统一前后九原地区的幅员广狭及其置郡问题,意义重大,是我们研究秦郡、秦代边疆政区地理时所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所以,重视使用考古材料与实地调查资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想廓清、厘定九原郡辖域问题的必由之路。
辛德勇曾对赵九原郡的边界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探研,他说,虽然九原确为赵郡,但是却不能简单地依据秦九原郡的疆域范围来推定赵九原郡的境域界线,从而也不能据此确定赵国的西北边界。赵国西北边界的具体走向,还需要通过其他因素来加以确定。九原的边界,既然不能作为确定高阙位置的依据,那么,依据前引《史记》卷一○○《匈奴列传》的记述,当时赵武灵王长城,是“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要想确定高阙的位置,就只有从高阙所在的赵武灵王长城和阴山山脉的走向入手了[1]191。实际上,关于赵九原郡域的考察,难点主要在于其西北边界的确定,而赵长城的分布则是我们推测赵九原郡界址的关键。
辛德勇依据文献史料和考古调查的成果得出,阴山(今乌拉前山和大青山)南麓的长城遗迹无疑就是赵武灵王所修“并阴山下”的长城,并以此为基础判定,至“并阴山下,高阙为塞”之长城上的高阙,不应是狼山上的石兰计山口,而只能是在乌拉前山上,推测乌拉特前旗张连喜店附近的大沟口很可能即为战国高阙的所在地。既已确定了赵武灵王长城的走向与高阙的位置,辛德勇最终得出结论,赵九原郡的西北边界也只能是阴山长城[1]199。
关于辛德勇推定赵九原郡西北边界的研究思路,笔者基本是赞同的,但关于其论证过程及所得结论,或许还存在进一步商榷的空间。在此,我们有必要明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赵国西北边境的长城并不只一条。阴山南麓筑有赵武灵王长城,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我们不宜以这条长城的存在而否认或忽略赵国西北境域抑或有长城的分布,如狼山(阳山)脚下的赵武灵王长城。
李晓杰曾对战国时期赵国北境之盈缩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一方面继承了谭其骧、杨宽、张维华等先生的意见*谭其骧先生在标注赵国西北边境阴山与狼山脚下的两条长城时,都注其为赵长城,详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此外,还可参阅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张维华:《赵长城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八、九合期。,一方面重视利用现存的长城遗迹。最终认为,赵武灵王在赵北境筑有长城,赵国的北长城大体有内外两条,外长城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沿今狼山一带而构筑;内长城则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向东,经包头北,沿乌拉山向东,沿大青山,经呼和浩特北、卓资和集宁南,一直到今河北省张北以南[2]492。
而且,在赵国西北边境这两条内外北长城之间及毗邻地域,还分布不少与赵长城防线关系密切的城塞、障燧等遗迹。“沿长城内外,凡重要的关口和适于瞭望的地方,都设置了烽台和城障,作为警讯和驻军之用。烽台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的距离不等,有的很近,有的远隔数峰。……在长城以南见到的一些小城,大约即障尉所在的‘障’。”[3]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乌拉特前旗小佘太公社的增龙昌古城和固阳县银号公社的三元成古城等。增龙昌古城周约一公里半,开有南门,墙为土筑,残高1~3米,城内建筑集中于东、北部,地面遍布生活、建筑用品残片。三元成古城周约二公里,墙亦为土筑,夯层9厘米,开有西门和南门,西门之外有瓮城遗迹。在烽隧和障城遗址中,常可拣到战国、秦至西汉初年的陶片[3]。唐晓峰根据以上考古遗迹及残存文物认为,这两座古城有关长城使用朝代的实证说明,这里最先是赵长城,后来是秦长城,到西汉初年,秦长城又被修缮使用,因此我们在遗址中可以看到直至汉初的遗物[3]。
乌拉特前旗位于九原郡治九原县(今包头市)以西,处于阴山南麓赵武灵王长城的西向延长线上,这说明赵国的势力已经延及赵武灵王长城防线以西。固阳县的三元成古城则南距阴山赵长城较远,依傍狼山南麓长城,约处于狼山脚下的赵武灵王长城的中段。上述这些障城、烽隧遗迹及其出土的建筑与生活用品残片等说明,赵人的势力曾越过阴山南麓的内长城,远涉狼山山脉的外长城,以上的城塞、障燧等,皆处于赵国九原郡辖域内。
其次,现在被我们视为秦长城遗迹的有相当一些是由他国始建、秦国后来加以修缮、连缀而成的,若我们想明确这些他国长城的走向、分布等,可能还需要从之后的秦长城遗迹去追根溯源。
唐晓峰曾系统考察了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遗迹。他认为,秦长城的遗迹,是由宁夏延伸至内蒙古后,即沿狼山而东,经固阳县北部的西斗铺、银号、大庙等公社,又经武川县南部的南乌不浪等公社,顺大青山而北过集宁市,最后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这些地区的秦长城大多蜿蜒于山岭之上。从秦长城的遗迹可以看出,它的修筑方法是因地制宜,山上用石垒,平地则土夯。石垒的部分保存较好,完整的段落高为4~5米,底厚4米。土夯的部分由于经年风雨,多数仅留一条公路路基似的痕迹,从断面可以看到清晰的夯层。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红旗店附近,有一处石墙倒塌的地方,露出了墙里面还有一段整齐的墙壁,说明这段城墙是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重修的,而且显然是嫌原来的石墙不够坚固,又用石块加厚了一层[3]。同时,观诸史籍,蒙恬来到这里修筑长城是“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4]2886。显然,内蒙古境内部分地段的秦长城是利用了部分赵国旧有长城修缮增补而成,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红旗店附近处的石墙长城很可能便属这种情形,唐晓峰所考察到的秦长城石墙倒塌后显露出的整齐墙壁应为赵国所建。所以,赵国西北边境的长城也曾修筑到了狼山。陈序经也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内战终止,最担心的是北边的匈奴。因此,他一方面派蒙恬率师出征,另一方面修筑长城防御。秦始皇遣蒙恬去筑长城,大体是在战国时边于匈奴的三国所修筑的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与增建,使首尾连贯起来,成为自东到西的一条防线。”[5]183陈先生所言的“边于匈奴的三国”即秦、赵、燕三国,而在今内蒙古境内的战国长城不少即为赵国所修。
综上,既然在阴山南麓赵长城以北,狼山山脉以南,河套内外的广大地域内*学界所称的“河套地区”,一般是指历史上的“北河”与“南河”之间这一地带。由于黄河在内蒙、宁夏、山西几省邻接地区的大转弯河段,过去也以其形如绳套而被称为“河套”,相对而言,后者称为“大套”,前者称为“后套”。语详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编第一章《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第183页。,布列有多处赵国的长城、城塞、烽燧遗迹,那我们当可推断,赵九原郡的西北疆界应到达了狼山山脉,与匈奴分界的赵长城不是阴山南麓的赵长城,而是狼山脚下的赵长城。史念海考察赵九原郡之辖域时认为,赵之九原郡相当广袤,其西部处于南北两派黄河流经之地[6]。李晓杰推定赵国九原郡辖域时也说,九原郡应领有云中郡以西至高阙一带,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后套及其以东至包头市的地区[2]493。我们认为,史念海、李晓杰两位先生关于赵国九原郡域的认识是允当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情形当是赵国强盛时期九原郡的郡域范围。秦始皇十三年(前234年),赵九原郡入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李牧被害,同年赵国亡;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直至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略取“河南地”。自秦占有九原地到复夺“河南地”的这二十年间,九原地域并非固定、墨守于某一长城防线之内,而当处于一种复杂的盈缩变化之中,秦与匈奴之间势力的消长应是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
二、匈奴南下与九原郡辖域变化
自战国时,北部疆界临近匈奴的秦、赵、燕诸国就经常受到日益强大的匈奴政权的进攻。尤其是“介在华、匈之间的其他各族有的也为匈奴所攻破和消灭,匈奴与中国的交涉更加直接、更加频繁。位于北边的秦、赵、燕虽然筑长城以拒胡,但是这时候各国的长城既非连接,恐怕也比较简陋,所以虽有长城,还要有相当的兵力去防守。因为匈奴经常南下侵扰,如果没有相当的兵力去防守,匈奴随时可以越长城而扰乱长城以南的地方”[5]181。史念海也说:“赵国于云中置郡,固在北防匈奴,其西南渡河,又可以防御林胡。九原在云中之西,其北隔着阴山就是匈奴。是九原置郡正与赵国其他诸郡相同,皆是为了防御匈奴。可见云中、九原本应相邻,设之为郡,固各有取意,不尽相同。”[6]赵之九原、云中、雁门诸郡与匈奴相邻,其设置本寓防御匈奴之意,故在匈奴南下时,这些边郡最先受到攻击与侵占,当可想见。史念海还认为,在李牧被诛、赵国灭亡之后,匈奴曾经乘隙南侵,其南侵之时应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和三十三年之间。其时正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踌躇满志之际,匈奴前来侵犯,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始皇的兴兵北征。北征取得了胜利,为了巩固边圉,就城河上为塞[6]。在此,史念海将匈奴南侵的时段定在了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这七年间。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陈序经就认为,匈奴南下的时间应当更早。他说:“李牧死,秦忙于并吞六国;其他各国,也忙于征伐或应付强秦。匈奴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这个时候,匈奴又必南下到农耕地区进行掠夺。因为这个时候,月氏与东胡仍然强盛,在匈奴之北,又是森林地带,不适宜于游牧,头曼掠夺最好的对象是农耕地区,这个地区既有丰饶的财富,又正忙于内战。”[6]182-183可见,陈序经认为,始皇十九年,李牧被害后,正值诸国混战之际,匈奴的入侵便已开始,这相比于史念海所界定的时间,提前了七年。两位先生的看法尽管有异,但也存在共识,即肯定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之间为秦与匈奴大规模交战时期,秦军的北伐最终在始皇三十三年取得了胜利。
关于战国时期匈奴南下的时间,本文更倾向于陈序经的看法,但笔者认为,匈奴南侵的时间或许还当提前,自始皇十三年赵九原郡入秦,至始皇十九年李牧死、赵国亡的这六年间,应该也存在匈奴南下的可能,在这一时期,秦之九原地被侵扰和蚕食可能既已发生。虽然《史记》卷一○○《匈奴列传》论赵国北境边事曰:“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4]2886。《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说,自李牧为边将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4]2450。李牧被杀三月后,赵为秦所灭。但我们需要明了的是,在李牧被害的六年前,即始皇十三年,赵国九原郡就已入为秦地。《史记》所言李牧生前的赵国边郡、边城只限于当时赵国实际统辖的边地郡县,自然不包括已为秦国所攻占的九原郡;同时,李牧也没有责任与义务去守卫已沦为秦地的赵国旧有领土。所以,始皇十三年至十九年间,秦国九原地区仍然存在被匈奴侵扰的可能,秦廷还能否拥有全赵时的九原郡域,恐难保证。
同时,还需要解释的一点是,陈序经言,匈奴南下必定到农耕地区进行掠夺,因为该地区既有丰饶的财富,又忙于内战。我们也赞同陈说,中国历史上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其主要目的是进行掠夺,而非据地固守*如有学者分析汉匈关系时就言:“匈奴进攻汉地,并非是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的,即使占有汉地,匈奴也难以利用,以故阏氏有‘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之语,平城围解之后,‘冒顿遂引兵而去’亦说明匈奴无久居汉地之志。匈奴更倾向于汉地的财物,即所谓‘(匈奴)贪汉重币’、‘匈奴好汉缯絮食物’是也。”语详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大多数时期游牧民族南下的主旨,但非全部时期,有些时候,游牧民族也以攻击和占据土地为目标,譬如河套地区。史念海在分析九原郡的始置时间与境域时就说,黄河南、北两河之间的土地相当肥沃,可农可牧。赵武灵王在阴山下筑长城,并至于高阙,就是为了据有这里肥沃的土地,不使之诿于匈奴之手,使它由此向赵国进行骚扰[6]。因为河套地区田土肥沃、灌溉便利,匈奴也正是看中了该地区“可农可牧”这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以,战国秦汉时期,河套地区遂成为华夏、匈奴争夺的核心区域,而这自然也会影响到九原地区辖域的盈缩变化。
已有学者意识到了匈奴南侵与九原辖域变迁的密切关系,如赵志强言:“九原、云中两郡位于秦汉王朝的北部边疆,系沿袭战国赵武灵王旧制而来,其地北与匈奴接壤。战国晚期,两郡属赵,与匈奴以赵武灵王长城为界,入秦之后,九原、云中界略有北移,秦末复退守‘故塞’,重新恢复到战国末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线。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取‘河南地’为止。”[7]关于秦末汉初九原地域的变化,赵志强还做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认为,入秦之后,九原北部边界仍沿袭赵武灵王长城为边界。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略取“河南地”,第二年,继续发动攻势,向西北斥逐匈奴。至此,秦朝边界向西拓展至黄河,向北渐次拓展至阴山和阳山,如此一来,九原、云中两郡的北边也相继向北推进。在这段时间里,上述两郡的区域随秦朝边界的拓展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7]。
我们赞同赵志强将九原境域的变迁与匈奴的南下相联系,但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九原辖域变化的具体情况,或可再商。如赵志强所言的赵武灵王长城指的是阴山南麓的内长城,而如前文所论,赵武灵王长城有两条:阴山南麓的内长城与狼山脚下的外长城,九原边地不少时候是以狼山脚下的赵国外长城为界址或参考坐标的。
还有,他认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时,九原地是以阴山赵长城为界邻于匈奴;至三十三年,始皇帝遣蒙恬率大军斥逐匈奴后,重又以狼山赵长城为界。笔者以为,赵氏关于这一时期九原地域变迁的描述似乎显得过于“齐整”,而非一种动态化的呈现。始皇三十三年,九原郡域确实拓至狼山一线*谭其骧先生考察始皇三十三年九原郡的境域时说:“今按纪传明言三十三年先收河南地,又渡河而北,知拓地跨河套内外。”语详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但前文已述,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间是秦、匈大规模交战的时期,三十三年时西北边境线的最终形成正是这几年双方角逐、秦廷不断拓疆的结果,因此九原地的边界自然也处于一种西进北延的动态变化中。
而且,关于蒙恬被遣征逐匈奴的时间是否就在始皇三十三年,学界也存在不同意见。尽管《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载此事于始皇三十三年,《资治通鉴》亦采此说,目前很多学者也都作如是观,但《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明言,蒙恬暴师在外十余年。
面对史籍记载的矛盾,陈序经进行了一番细密、严谨的考证。秦始皇、蒙恬均死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他认为,假如蒙恬是在始皇三十三年被遣去征伐匈奴与修建长城,那么蒙恬在外只有四年的时间,不能谓暴师在外十余年。若说暴师在外十余年是对的,那么蒙恬被遣征伐匈奴与修建长城应在始皇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加之,《史记》卷一○○《匈奴列传》指出,蒙恬北逐匈奴,头曼抵抗不住,北徙了十余年,这个十余年与蒙恬暴师十余年正相符合。所以,陈序经最终得出,征伐匈奴可能不止一次,而修建长城也非三四年间所能完成,所以暴师在外十余年这句话较为可靠,而蒙恬之被遣到边境备胡筑城似应以始皇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为合理[5]183-184。斥逐势力强大的匈奴,略取如此广袤的“河南地”恐非一年征战所能完成,相较而论,我们认为,陈序经的推导与结论似更允当。如果此说确实,那么始皇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间,九原地的北部边界显然不局限于阴山赵武灵王长城内,秦廷的势力已北越阴山,在广阔的河套平原不断向北挺进,逼近狼山山脉,最终在此与匈奴毗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将本文的结论归纳如下,以清眉目:
一、赵武灵王在赵国北境筑有内外两条长城,分别布列于阴山与狼山(阳山)山麓。赵人的势力曾越过阴山南麓的内长城,远涉狼山山脉的外长城,九原郡的西北边界也随之拓延至狼山山麓。
二、自秦占有九原地到复夺“河南地”的这二十年间,九原地域并非固定、墨守于某一长城防线之内,而当处于一种复杂的盈缩变化之中,秦与匈奴之间势力的消长应是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
三、战国时期匈奴南下的时间可能比较早,自始皇十三年赵九原郡入秦,至始皇十九年李牧死、赵国亡的这六年间,应该就存在匈奴南下的可能,在这一时期秦之九原地被侵扰和蚕食可能既已发生。
四、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间是秦、匈大规模交战的时期,三十三年时西北边境线的最终形成正是这几年双方角逐、秦廷不断拓疆的结果,因此九原地的边界也处于一种西进北延的动态变化中。这一时期,秦廷的势力已北越阴山,在广阔的河套平原不断向北挺进,逼近狼山山脉。
三、余论
最后,还需要附带一说的是九原郡设置的时间问题。全祖望、王国维、谭其骧等先生皆主张九原郡置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如王国维云:“(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又前年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是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匈奴列传》作‘四十四县’〕。此三十四县者,优足以置一大郡。以地理准之,实即九原郡之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自是九原之名始见于史。故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归,巡北边,自上郡入;至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其丧乃从井陉抵九原,从直道至咸阳,秦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也。”[8]538对王国维有关九原郡始置时间的看法,辛德勇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所谓“九原之名始见于史”的时间,是否确实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之后,乃是王国维的结论能否成立的关键因素[1]47。对此,辛德勇秉持史念海、陈仓等先生关于九原郡始置于赵、秦袭赵规的观点。
我们赞同辛说,其论证翔实、周密,恕不赘言。但需要对以上各家观点稍作补充的是,在始皇三十二年之前,九原郡名就已存在,但当其地入秦之后,九原之名也确实如王国维所论,始见于始皇三十五年。辛德勇认为,秦灭赵后一直沿承其旧有九原郡的建置[1]51。设若如此,那么在秦夺取赵九原郡后,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前的这二十余年中,史乘为何不见九原之名?当然,可能存在史籍失载的情形。加之始皇十三年秦据赵九原郡后,由于匈奴时常南侵,九原境域处于不断变动中,秦廷是否能始终保留其郡级建制,史无明言,我们似也不宜径做肯定的判断。所以,或许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九原郡确实始置于赵,而非始皇三十三年始置,但至此时,秦廷终于斥逐匈奴,复据“河南地”,遂重新设立九原郡。而在此之前,秦占有九原地的二十年间,九原郡的置废情况究竟如何,容后付专篇再做进一步讨论。
[1] 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J].文物,1977(5).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陈序经.匈奴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 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2).
[7] 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3).
[8] 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16 - 09 - 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8)。
尤 佳(1978—),男,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边疆史。
K233
A
1009-105X(2016)06-0008-05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