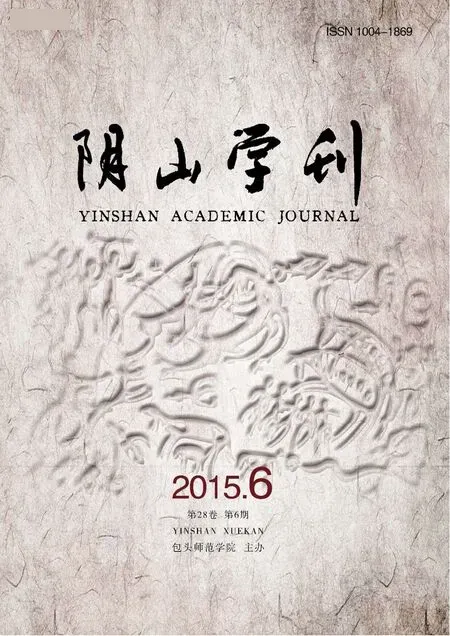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变迁
2016-01-21陈尚荣,郑朝成
陈 尚 荣,郑 朝 成
(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变迁
陈 尚 荣,郑 朝 成
(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的热点话题,也是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大众传媒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媒体呈现形成了这一群体拟态的媒介形象。我国不同时期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媒介形象建构总体呈现出“入侵者”、“受难者”及“融入者”的形象,而在不同时期形象建构的背后又表现出“被歧视”到“被接受”再到“被认同”的形象变迁特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媒介形象对其现代性建构从正负两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媒介形象;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他们有着“工人”与“农民”的双重身份,因此这一群体被人们称为“农民工”或“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被称为“民工书记”的农民工研究者刘怀廉曾这样描述到:“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但不是城市人;他们是农村人,却没有生活在农村,他们实际上是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人。”[1](P125)作为城市里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农民工群体一直备受媒体的关注,在各种媒体中呈现出不同的媒介形象。
媒介形象是指被传播者在媒体传播中再现出来的形象。曹宝剑在《媒介形象系统论》中,从系统论的角度将媒介形象分为“传播者媒介形象”和“被传播者媒介形象”。本文所要论述的农民工形象则属于“被传播者形象”,它是大众对于传播媒介组织再现的人或事物认知信息的总和。在日常生活中,公众了解某类人或某事的最直接手段便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获知。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报道形成了关于这一人群的拟态环境,人们根据这个拟态环境中农民工的媒介形象来认识、定义他们,并且把农民工的媒介形象类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
一、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媒介形象建构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城市化建设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农民工群体也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出现“民工潮”时,《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了有关“民工潮”的深度报道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报告。在报道中,农民工衣着破旧,背着麻袋,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但是到处打地铺,造成城市盗窃事件频发,遭到城市人的排斥和埋怨。那时的农民工在媒体上所呈现的不是为了城市人生活提供方便、为城市发展作贡献等正面形象,而是城里人眼中的“盲流”、“脏兮兮的外地人”的负面形象。
如今,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回顾包括大众传媒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以及电影、文学作品及其他各种媒介对这群影响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形象建构,我们发现虽然由于媒介的性质不同,对农民工的形象呈现方式有别,但是经过梳理研究得出,在不同的年代对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的建构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农民工在媒介上呈现的形象总体上表现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在城市里为生存打拼被同情的“受难者”形象;一类是在城市里艰苦奋斗被称赞的正直、善良的正面形象;一类是在城市里违法犯罪被“污名化”的素质低下的负面形象。
不同类型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视角会有所不同。以报纸为例,选择以《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和《华西都市报》等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其中《人民日报》为全国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中央机关党报,在党和政府发布最新决策信息方面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南方都市报》为广东省省级综合类日报,广东省是拥有我国最大劳动输入量的省份;而《华西都市报》位于西部人口最大的四川,四川省是我国西部劳务输出量最大的省份,两份报纸都为都市类报纸,以市场为导向,作为商业类媒体的代表。
关于《人民日报》历年来对农民工的报道,有文章曾对其在1983年至2011年期间的1077篇相关报道进行了统计分析,报道内容集中在以下十类话题:生存现状、培训与就业、权益保障、方针政策、关怀救助、违法犯罪、精神文化生活、家庭子女、流动管理以及其他。据统计,《人民日报》关于农民工的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生存状态、权益保障、培训与就业、方针政策和关怀救助上,报道所占比例超过75%。其中,对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描述与权益保障的报道占到半壁江山,说明了主流媒体对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报道趋于客观,并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关怀,代表着党和政府的态度和心声,充当的是一个“沐恩者”的角色。[2](P40)《人民日报》对于负面议题如违法犯罪等的报道,所占比例较小,只占9%。其中负面报道也多为早期的报道,如《人民日报》1988 年7 月报道《北京站人满为患探秘》,这则报道将农民工刻画成“无业流民和流窜犯”、“盲流”,描述了他们“行乞、诈骗、扒窃、伪造和倒卖票证,或以敲诈手段出卖劳动力”,认为“一些盲流人员已成为刑事犯罪活动的温床……她们中的一些人男女杂居,伤风败俗,使北京站已成为非婚生育和计划外超生的一个死角”。主流媒体就农民工问题上多为正面的事实报道,而对于一些负面的社会新闻则选择性忽略。
同时,本文还分别选取了2014年50期《南方都市报》和《华西都市报》作为研究样本。统计结果发现,两家都市报对农民工的报道,平均数量达到了1篇/期以上。由此可见,近年来,媒体较以前更加关注农民工的问题。在报道内容方面,集中于对农民工家庭生活问题、工作问题以及对农民工的政策福利方面的报道,还存在多篇文章涉及到农民工违法问题的报道,相关报道的数量虽占少数,但是影响却不小。其中就有《华西都市报》报道的一个农民工无证从事焊接被拘五天的新闻,为农民工树立了一个不懂基本常识的形象;《南方都市报》在报道违法犯罪事件时,用上了“农民工”、“打工仔”、“外地来的”等字样。“不懂常识”、“乱倒垃圾”、“偷东西”等标签贴在了农民工的身上,他们的形象遭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早前也有学者通过对2000年1月至2002年12月近三年间的相关农民工新闻报道做过类似系统研究。发现在对农民工群体的媒体形象“再现”上,“《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这三家具有一定市场取向的报纸具有共同性,他们对农民工最频繁的再现形象都为‘受难者’和‘负面行为者’”[3](P6)。都市类商业性的媒体为迎合市场和产生新闻效应,对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呈现则较之党报一类的主流媒体更倾向于负面形象的报道和再现。
通过对近年来相关媒体的农民工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呈现出的立场以中立、无倾向性居多,多数体现在关于农民工的政策解读、对农民工家庭生活及其工作方面的客观报道。关于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积极的、吃苦耐劳的正面形象以及逐渐融入城市生活的“新市民”形象,而报道农民工违法、破坏城市环境等的负面形象则明显减少。“网络上的新闻报道对农民工的污蔑和歧视性成分已经大大减少,即使是反映农民工受到歧视的报道里,也是客观叙述实际情况,报道本身并不带有媒介歧视现象。”[4](P92)这些现象是可喜的,说明我们的媒体农民工形象再现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真实和理性。
如今,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接过了老一辈农民工的远走他乡、挣钱养家的接力棒,但又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就职观念、权利意识等方面存在一些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他们诉诸精神需求,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还表现在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能够利用网络媒体争取话语权。同样地,相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也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以《人民日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为例,自2010年以来,《人民日报》因“三农问题”国家政策的推动,开始更高频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报道。不同于对传统农民工的报道,《人民日报》对他们的报道更集中在城市融入、精神文化生活和就业与发展等三大题材。媒介中呈现出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平等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形象。
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媒介形象的变迁
报刊类媒体在报道城市生活中的农民工时往往会遵循其身份特征,在承认其相对弱势的基础上,还会将其区别于城市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加以典型化提升,以形成新闻亮点并创造新闻价值。因此,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塑造某种程度上必然受到新闻效应的导向影响。而影视类媒体在塑造农民工媒介形象时同样也会受到编导的个体意识及栏目收视和电影市场的导向影响。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多面性和混杂性。然而,农民工在媒介中呈现的形象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总体特征。事实上,从历年对农民工相关报道及其媒介形象呈现来看,农民工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这种变化直接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国家政策的改变等有着紧密关联。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基于国家经济积弱现状及粮食供需紧张等客观需要,我国通过实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先后出台了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准予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长期务工的农民转为非农户口,成为集镇居民(1984年)、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1985年)和允许国有企业按照指标符合条件从农村招工(1986年)等系列规定。1988年,“民工潮”现象开始形成。伴随大量农民进城,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过热等社会问题出现。中央作出决定,对农民工流动的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加以控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目标的确立,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急剧增加,于是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引导农民进城务工。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下岗问题突出,就业岗位减少,就业压力加大,为了给城市下岗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全国各地都出台了各种限制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行业、工种等条件,这种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来促进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短视政策被讥讽为“腾笼换鸟”。2000年以后,中央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促进劳动力输出产业化、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工进城不合理限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文指出:“应打破‘正式工’与‘临时工’、本地职工与外来职工、城镇职工与农村职工等身份界限,按照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职工签订相同文本的劳动合同,在劳动条件、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等方面平等对待,并在劳动合同中予以明确。”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发展、融入城市以及真正获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方面给予了政策保障。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全面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指出要加大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培养,加快解决农民工工资增长、住房改善、子女上学、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
刘怀廉在《中国农民工问题》一书中,曾将我国农民工政策及其演变作了归纳,共分为五个阶段:控制流动阶段(1979—1983年)、允许流动阶段 (1984—1988年)、控制盲目流动阶段(1989—1991年)、规范流动阶段(1992—2000年)、公平流动阶段(2000年以后)。这样的时间段划分与我们上述的农民工政策演变的历史梳理是相符的。有论者据此时间段的划分将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变迁概括为(一)“生存者”形象(1979—1991年):1.“非法流动者”(1979—1983年)、2.“盲流”形象(1984—1991年)(二)“发展者”形象(1992—2007年):1.职业劳动者 (1992—2000年)、2.现代产业工人(2001—2007年)(三)“融入者”形象(2008年至今)[5](P92-95)三个阶段的划分也比较能够概况当代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总体发展面貌和变迁趋势。
在“生存者”形象阶段(1979—1991年),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往往呈现的是“盲流”—“入侵者”—“被歧视”的形象演变轨迹,背后体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媒体意识形态及城市意识形态的思维逻辑。如1989年春晚小品《胡椒面》,剧中的陈佩斯就塑造了一个衣着破烂、素质低下、贪小便宜的“盲流”和“入侵者”形象。[6](P72)1990年《社会》杂志第1期刊登了一篇“都市‘盲流’面面观”的文章,里面醒目的标题是“首都,人满为患”、“上海,拥塞不堪”、“羊城,叫苦不迭”。文章对盲流中的主体群体农民工的描述是:“大量外地农民进京务工、经商、从事服务工作,加快了首都的城市建设,方便了居民生活;但是,外地农民工源源不断地进京,也给首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给首都的就业问题增加了难度;建筑行业长期大量使用农民工,他们技术水平低,施工质量差;加重了首都公共交通和粮食、蔬菜、猪肉等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影响社会治安;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外来农民计划生育失控等。”显然,作者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总体态度是充满偏见和歧视的。在“生存者”阶段,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以负面形象呈现居多,这也反映了早期城市人对外来闯入者农民工抵拒排斥的心态。
在“发展者”形象阶段(1992—2007年),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则呈现出“边缘人”—“受难者”—“被接受”的形象演变轨迹。1993年春晚小品《擦皮鞋》,就反映了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巨大隔膜,农民工为跻身“主流社会”、摆脱“边缘人”的尴尬,不得不自我模仿城里人的生活,以取得城里人的认可。农民工遭受到的被歧视的城市生活经验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很难融入到城市现代化生活中去,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的“边缘人”成为这一群体的时代画像。这一阶段,城镇下岗社会矛盾的突出,更加造成了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者的冲突,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更加不易,所以,“发展者”阶段初期,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发展之路是充满了艰辛。因此,这一时期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则表现为“受难者”形象居多。以影视媒体为例,这一时期包括“第六代”在内有大量电影呈现了农民工群体“受难者”的银幕形象。如贾樟柯的《小山回家》(1995)反映了农民工王小山春节回家的艰难以及愿望不断的受阻过程;王小帅的《扁担·姑娘》(1997)反映了武汉挑夫的艰苦生活;管虎的《上车,走吧》(2000)反映了北京本地人对山东来京开小巴司机的歧视和迫害;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2001)讲述了青年农民工郭连贵与一辆跑快递用的自行车的悲剧故事;孙冰、王建为《人命关天》(2001)中的农民工成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生产安全的牺牲品;李杨的《盲井》(2002)揭露了矿井下的农民工的悲惨命运;杨亚洲的《泥鳅也是鱼》(2005)叙述了一个女农民工的悲剧爱情故事。电视剧《生存之民工》(2005)更是讲述了一群民工讨薪的血泪故事,成为当年多家电视台的收视冠军,引起一时轰动。有论者将这些银幕上的农民工“受难者”形象比喻为“泥鳅”,农民工好像“泥鳅”一样,在社会底层乱钻,到处碰壁,到头来难以摆脱煎熬的命运。“泥鳅”成为农民工苦难生活形象的写照。“这一时期的农民工电影,塑造了‘泥鳅’形象,刻意表现城乡人的冲突,渲染农民工的悲惨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的苦难。”[7](P17)2003年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民熊德明追讨工资,曾经轰动一时。王珈导演《回家》(2004)则讲述了银幕上一个市委书记为农民工讨薪的感人故事。2004年春晚小品《都市外乡人》,巩汉林扮演的进城打工者并被女经理“相中”,害怕被城市人看不起,让其母亲配合作假,女经理识破后却很高兴地接纳了这对母子的农村身份。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媒体中的政府官员、普通市民都开始关怀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艰难生活,逐渐接纳认同农民工,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城市意识形态、媒体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友善“接受”态度。
在“融入者”阶段(2008年至今),农民工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城市务工经历逐渐弥补了城乡之间巨大的二元对立的鸿沟,农民工以各种形式深度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户籍政策的改变,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买房落户,将妻儿子女迁移到城市安居乐业,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这一时期的农民工媒介形象则呈现出“准市民”—“新市民”—“被认同”的形象演变轨迹。2008年,一部主旋律电影《农民工》上映,影片根据9位成功的农民工原型改编,讲述了以陈大成为主的一群农民工在城市里创业、奋斗、成功的故事。片头题词是“谨以此片献给在改革开放30年中默默奉献的农民工兄弟姐妹”,电影塑造了正直、善良、诚信、勤奋的农民工近乎“完美”的媒介“正面形象”。 影片《所有梦想都开花》(2009),企业老板黄总裁在公司的高层会议上强调:“今后在我们厂里,不能再提什么农民工、外来妹,大家都是员工。”称谓的改变表明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真正接纳和认同,农民工以一个“准市民”的形象与城市市民生活在“同一片蓝天”(2008年一部反映农民工子女题材的电影就叫《同一片蓝天》)。不但城里人真正认同了农民工,农民工自身也在观念上认同城市,视城市为自己的家园,不再有一种“边缘人”的漂泊感。电影《高兴》(2008)里的男主人公农民工刘高兴对五福说:“城里就是咱的城里,要爱。”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真正融入城市、拥有城市、做城市主人公的态度和感情。《所有梦想都开花》电影塑造的新生代农民工,阅读时尚杂志、购买高档消费品、穿时尚服装、享受时尚的娱乐方式,进影院看电影、玩电子游戏、唱卡拉OK、开Party、旅游休闲,他们已经从语言行为到思想观念进行全方位的城市化、市民化,成为地地道道的“新市民”形象,真正实现了融入城市的“所有梦想”。
三、媒介形象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现代性建构的影响
“一个具备了现代素质或现代性的人应该具有一整套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比较顺利地顺应生活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8](P65)大众媒体塑造出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在影响着受众对农民工的态度与看法的同时,也在影响甚至改变着农民工阶层的自我形象的认知。同样的,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关于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也影响着农民工们现代性的建构。
媒体的正负面报道对农民工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不同。媒体对于农民工的多数报道是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呈现出的是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的媒介形象,如某农民工靠双手成立一家企业,获得了事业成功等。这些报道使得农民工不仅在社会大众心中树立了积极向上的形象,还能引起他们自己的共鸣,了解同一阶层群体的日常生活,并以此作为模范,改变原有生活中的不当行为方式。在这一层面上,媒介形象是在正确引导着农民工群体的行为方式。而对于有关农民工负面的新闻报道,媒体的初衷是让社会上的犯罪群体引以为戒。这些报道很容易引起公众对部分农民工的不当行为的反感,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这虽然只是其中的少数,但是也影响到他们对自身所在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还会引起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和“群体性歧视效应”。[9](P45)这给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相互认同和农民工城市化融入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从上述农民工媒介形象变迁的历史来看,农民工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较为漫长的从被歧视到被接受和被认同的阶段。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 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身上。”[10](P155)这种偏见和歧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早期大众媒介对农民工形象建构从“污名操作”到“标签定式”的“传媒歧视”结果。[11](P4)
农民工正负面的媒介形象也影响着农民工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媒介的相关报道,往往影响着农民工对自我社会地位的认知。正面的媒介报道会让农民工感觉自己所在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自信心得到了增强,其城市归属感也会相应提高;而相反,负面的媒介形象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为人所看不起,离城市人的生活也非常的遥远,城市归属感也有所降低,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受阻。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有关农民工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普遍反映,人际关系是他们目前最大的困扰之一,由于没有时间外出,接触不到太多的外面的人和事,因此,报纸、电视和手机媒体是他们获知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长期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得他们对媒体的信任度极高,农民工的正负面报道也相应地对他们的价值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改变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正面的媒介报道可以有效地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其作为新市民的公民素养,促进个人的现代化发展;而负面的媒介报道,虽然可以起到引以为戒的效果,但是会引起部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其所在群体的社会定位,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
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生活在城市里,始终缺少话语权和媒介表达权,作为“他者”的媒介形象也是完全被动地呈现和建构。而农民工媒介形象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融入和现代性建构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以上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形象变迁的分析,虽然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和演变呈现出越来越认同和正面化表达的趋势,但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得出一个完全乐观的结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媒介形象建构依然存在一定的媒介偏见和歧视,我们认为媒体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对农民工报道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彻底摒弃对农民工群体的成见,找到解决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的策略,真实还原农民工们的生活状态,重新建构规范、健康、和谐的农民工媒介形象。
参考文献〔〕
[1]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曾振华,杨丽,张思远.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再现与重构[J].统计与管理,2014,(1).
[3]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2).
[4]时潇锐,吴菲,屈雅利.网络中农民工形象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与媒体责任[J].新闻知识,2011,(4).
[5]董小玉, 宛月琴.文化生态视野的农民工形象变迁与话语建构:由媒体观察[J].改革,2013,(2).
[6]陈世海.农民工媒介形象再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央视春晚的分析[J].青年研究,2014,(5).
[7]张权生.从“报春花”、“泥鳅”到“向日葵”——农民工电影整体观[D].江苏:南京大学,2011.
[8]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8,(5).
[9]许向东.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投影——传媒再现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
[10]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董宽.传媒歧视遮蔽利益诉求——透视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媒介表达[J].新闻三味,2006,(12).
〔责任编辑韩芳〕

On the Media Image Construction and the Changes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CHEN Shang-rong, ZHENG Chao-cheng
(School of Design Art and Media,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Abstract:The issue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our society, and also the focus of media attention. Mass media presentation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forms their mimicry media image. Media images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our country were generally shown as the “intruders”, “victims” and “the ones being included”. Behind the image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times, the image changes could also been seen from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to “being accepted” to “being recognized”. Media image of urban migrant workers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modernity building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media image; 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6-0050-06
作者简介:陈尚荣(1964-),男,安徽和县人,博士,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形象传播、新媒体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大众传媒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现代性建构关系研究”(2010SJD860004)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