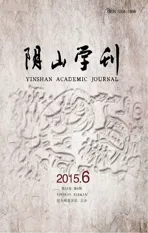渐行渐远的“美丽乡愁”总是挥之不去——对沈从文艺术作品审美个性的再认识
2016-01-21任志刚
任 志 刚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旗委宣传部,内蒙古 包头 014100)
渐行渐远的“美丽乡愁”总是挥之不去
——对沈从文艺术作品审美个性的再认识
任 志 刚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旗委宣传部,内蒙古 包头 014100)
摘要:沈从文笔下,湘西边寨有三美,即山水美、民俗美、人性美,凸显了一抹淡淡沉落的“乡愁”。他融合贯通政治观、宗教观、道德观、人生信仰和价值取舍等诸多文化要素,呈现了特定历史年代别致、善美而纯真的山水人情。他书写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对于当下亦有借鉴和反观意义:城镇化进程中,道德滑落、人性缺失、功利严重、价值扭曲等问题丛生,处理好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统一,有助于重铸民族精神,最终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沈从文;纯美人性;自然的和谐;审美个性;乡愁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始,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迎来莫大的创新改良之风,一批风格清新的艺术作品以及有视觉及内心感知的创作者脱颖而出。这其中,便有来自湘西一隅的沈从文。他只身来到北京,进行小说创作,那是一种抒情、浪漫的笔调,独特婉转;那是一种带有鲜明“地方风味”的“农家”艺术珍品,它渐行渐近, 挥之不去;那抹“美丽乡愁”渐入佳境,不断为文坛所瞩目,直至独领风骚。
沈从文的作品,大多数是以湘西边地作为背景,显著标志就是鲜明独特的湘西民俗风情,人物总是依附于自然背景之上,它和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统一和谐的整体。在这样的特有氛围中,沈从文艺术作品中的代表性人物总是释放着自然的人性,它灵动、纯真而富有临河凭风的野性,这种乡野人性与自然山水非常契合,是自然与肉体相投相通的人性。沈从文作品根植于本土,挖掘真正的人性,积极颂扬乡村世界的人情美好,同时将喧嚣嘈杂的都市社会作为乡村世界的参照,直面人性异化,揭示讽刺了都市社会的丑陋与腐朽。于是,为了保留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重铸我们国家的民族风格”[2],这位“乡愁”大家竭力歌颂湘西朴素的人性美、人情美、道德美,艺术作品的审美个性,最终在湘西乡民“生命形式”中得以确立。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作家重视写人,通过剖析国民灵魂的丑恶,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民的毒害。许多乡土派作家则把写作的眼光投注到乡村,去写那里的人物及自然的田园风光,力求使人性都回归到乡村古朴自然的环境中去,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沈作胜出一筹的魅力在于他深受湘西特殊地域文化的习染,更有机会接触边地的风土人情和鲜活人物——地气与“乡愁”是作品的灵魂。渐行渐远的那抹“乡愁”,时刻流连于大河上下、吊脚楼边,与风呢喃、与水嬉戏、抚摸黄狗、与翠翠对话,他在艺术上走出一条独具个性的创作道路。
苗族出身的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一块土地上,这一偏远地域有它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沈从文敏感捕捉这一地域文化场景下的人情世故和生活情趣,这就为他的创作思想和审美个性奠定了深厚基础。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特有的吊脚楼、小篷船,还有油坊、水车、苗民服饰,都是作家精心描绘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民族符号(凝聚着湘西地域文化意识的物象),无一不与湘西人民的生活连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奇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情趣。苗民特有的婚庆民俗、节日礼仪、地域民谣、古代传说、原始宗教代代相传,特有的地域文化气息浓厚、热烈,如同甘醇的美酒藏而愈纯,湘西人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息、繁衍。沈从文作品的美在于将这种文化生活艺术地表现出来,因此他的创作特色是能够把“一定的人类文化和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整体加以艺术的再现,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完整把握”[3](P17)。
在这种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纯朴习惯、遵从古礼”。这种“一定的人类文化和一定的地理环境相融合”的生存环境,形成湘西人安居乐业、信守命运、洁身自爱的生活趣味和作人准则。在这样的生活情趣中,“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吃、唱、笑,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的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4]在湘西人这种“生命形式”中,其性格上有着不畏艰辛、忍辱负重的特点,这正是一种纯正的人性。这些人正常的喜怒哀乐都是鲜明自然的,只是如此,他们执着地、扎扎实实地生活着,保持一种“纯正博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保持了我们民族勤劳向上、勇敢正直的伟大性格。
湘西乡村生活培养、教育了沈从文,源于这种湘西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沈从文眼里,喧嚣的都市文明并不能掩盖渐行渐远的乡村文明。基于这抹“美丽乡愁”,已是城里人的沈从文身体里依然是“乡下魂”。他的人生经历又加深了他对湘西乡村文明的再认识,这“感情里无法摆脱沈从文那份永不枯竭的湘西故土的温爱,对边城昔日人、事的亲情。这爱、这情正化为小说家特有的心理定势。这心理定势不仅对视觉经验的圆满构成起到通融作用,而且还像埋在文体内部的自动感应装置,神差鬼遣般地锁定他倾心的生活敏感区,圈定他可被内化的创作素材域。”[5](P17)因此,沈从文努力去捕捉湘西乡民纯朴友善的人情美,去提炼这种“纯正人性”,将写人生作为创作的主题,只有在这样的创作形式中,沈从文才有自我见识,努力表现出乡民完美的个性。
有了“美丽乡愁”的寄托,就会有塑造这样完美形象的冲动欲望,沈从文才情的表现自然而然就会迸发出来。《边城》中的翠翠、爷爷,《长河》中的天天、老船工,《三三》中的三三,这样的人物都可以视为完美纯正人性写实,是沈从文艺术创作审美的结晶。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物吧:
少年女子容貌都美得异常、品性皆善、温柔纯情;年老的男性长辈都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他们好施善,以助人为乐为快事,重义、轻利、诚实、守节,他们正直真诚的品格不仅习染着下一代,同时也影响、丰富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好品德。这些完美纯正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沈从文眷恋乡村感情的真实流露。沈从文精心塑造这些人物,旨在张扬人性,在宣泄作家内心对现实社会违背礼俗、人伦、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愤懑,这正是沈从文理想的审美情趣。沈从文说:“这是理想,即最美的生命形式”[4](P17)。沈从文的审美个性就是以理想的“生命形式”为创作标准,遵循这种创作标准,表现具有这种“生命形式”的纯正人格,讴歌湘西乡民的纯正人性,讴歌古朴纯真的乡村田园文明。
作为艺术审美活动,沈从文的作品展示出了完美纯真的人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沈从文曾经说过,“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在于‘用一种更坚固的材料和一种更完美的形式’将这‘生命的理想’保留下来,求得‘生命永生’”[4](P17)。这就是说,作家的创作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基础,用一种艺术审美活动,在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中,塑造形象;在理想的情境中,使审美观念得以确定、完成。这样,作家的创作愿望(即审美理想)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受到启发和影响。这无疑在客观上起到文学作品的美育作用。时值当下,沈从文艺术创作结合乡愁文明纯粹的审美意识,在较高层次上形成的新颖的文学观念及艺术作品,这无疑对现代文明社会中所暴露出的丑陋现象,能起到教育世人、陶冶情操的积极作用。
二
沈从文以湘西边地“乡下人”的“生命形式”作为审美标准,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写都市人性的异化,从而鞭挞和揭露都市人灵魂丑恶与腐朽的一面,但沈从文更多的是用自己逐步成熟的审美取向,尽心挽留那抹心中的“美丽乡愁”。“请你试从我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和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和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成为乡下人,如何鲜明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6]沈从文总是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厘定,通过“乡下人”朴素的道德美、人情美,直接针对城市人性异化,批判都市社会的丑陋。在这一点上,沈从文确实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边城》、《长河》作为沈从文的精品创作,作者对传统道德、民间纯朴人情美给予热情赞誉和肯定, “《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7](P17)
《边城》的问世就是作者对乡村田园文明进行的讴歌,《边城》中的理想人物是传统道德的化身,而《边城》中的人情世故,艺术地凝练了湘西文化生活的精神神韵。《边城》里,不仅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的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沈从文自己在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8]朱光潜理会了沈从文写《边城》的创作动机,指出作家审美理想和创作旨意最终要深刻描绘到人物身上,让社会洒满温情和欢乐,让社会存在一种自然的和谐美。
我们此刻再来感受一下《边城》。在《边城》中“翠翠”勤劳、朴实、善良、热情、富于幻想,青春少女努力信守人的初衷。在对待爱情婚姻上,她表现得自然、纯真、健康,完全没有悖离一点“人性”。“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8]。这是一种真切守信的恋爱观,纯情少女翠翠的形象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来。再来看看小伙子“傩送”,在对待爱情和婚姻上,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是为家里添碾坊呢,还是娶翠翠,他选择了爱情。这种真挚的人情和人生爱情选择,正是沈从文一贯捕捉的审美取向。同样“爷爷”这样的人物形象更是美好道德的化身。“爷爷”有着一切纯正的人性,守信、讲义、善良、勤劳、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正是如此博大厚重的人性支撑,现代湘西才会有古朴世风与人类美德。沈从文理想的“生命形式”就是一个又一个突出的“爷爷”、“翠翠”、“傩送”,沈从文的美学个性就是通过对“爷爷”们的阐释表达出来的。这一切纯美、善良、勤劳和忍耐,不正是我们古老民族性格的化身吗?沈从文视现代文明为“洪水猛兽”,现代文明对乡村的侵染和影响使作家不得不考虑这种真诚守信的人性究竟能够保留到什么时候。表现在《边城》中,爷爷对于翠翠傩送婚姻能否成功并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有着坎坷人生经历的爷爷,对于湘西文明能否经受得起时代的考验惴惴不安,终于在暴风骤雨来临的时刻死掉了。“美丽乡愁”渐行渐远,接近那抹最后的夕阳。为了保留这种纯朴世风,沈从文在创作中象征性地为边城树立起一座新白塔,寓示湘西朴素的人性美和美好的传统道德不会消亡,它将永远植根于这块古老的泥土。而这种艺术表达带给读者最深切的眷恋,渐行渐远的那抹“美丽乡愁”挥之不去,大如心中永远存在的“满月”。
沈从文努力建造他的《边城》,去描写边民纯正人性,引来不少作家对他的非议。这固然有时代的局限和创作取向上的不足,但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对于这位作家而言是两条相逆的平行线。敏感而内心深邃的沈从文无比孤独、痛苦,他心在湘西却身处北京。由于“乡下人”的“愚顽”,沈从文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总是保持在乡村田园文明的合理与近现代都市社会丑陋习气的对照中。他到北京后感叹道:“血管中流着你的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1](P17)这种都市人性异化、社会道德走向堕落的丑恶现象,正是当时逐步走向近现代的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一种真实写照。沈从文极其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恩格斯曾论述到:“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意味着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别一部分人的苦痛和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11](P17)沈从文艺术作品的审美取向毫无保留地指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只是在当时未有真的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最终验证。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不等同的“二律背反”现象,沈从文的创作实践做了有力回答。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是一个作家的头脑、良知和朴素的社会责任。沈从文艺术的审美个性,即讴歌乡村田园文明的积极方面——朴素纯真的人性,这在艺术领域中是能站得住脚的。许多作家正像沈从文一样,透过“人类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之间出现的二律背反现象,从历史评判和道德评判之间择取后者,凭借一种传统道德观,用无比眷恋的态度,深情地惋叹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给予的形式。”[10](P17)这种辨伪存真的方法使这些作家能够吸取现代社会合理真实的东西,剔除其腐朽、堕落、糟粕,在艺术表现上,显得更加准确、合理。从传播文明的角度,沈从文的艺术创作今天看来愈发显得光彩夺目。
三
再来领略一下沈从文艺术作品中的湘西乡村,那抹挥之不去、流光溢彩、渐行渐远的“美丽乡愁”。在艺术上表现上这是一种神奇、浪漫、浓重的抒情,它将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慨(表现“生命形式”)形象地表现出来,最终使沈从文的艺术作品别致、新颖而不拘一格。台湾作家尹雪曼在谈到沈从文创作风格时说:沈从文创作风格的特殊,也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至于他部分作品想象力的丰富,文字上表现得多姿多彩,更令人赞佩。奇异别致的创作风格使沈从文能够恰如其分、生动活泼地表现和叙述类似浪漫、传奇的故事。在这种形式的创作题材后面,孕育着沈从文表现“生命形式”,即纯正人性的创作思想。最为成功的是沈从文能够用清新朴讷的笔调,无声啜泣着我们民族及人生的苦难与悲凉,以田园文明对抗都市文明,这在《边城》中极其圆满地表现出来。
湘西有着深受楚地巫鬼文化习染的传统,“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混合为一”,湘西是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的境界,在这种环境中“人与自然契合”,人便是大自然的女儿,这种符合自然秉性的生活情愫,在小说创作中无不体现奇特神秘的特征。沈从文描绘这种生活情趣,去表现人,挖掘、抒写人性,努力去寄托人性理想,让人性回归到纯正博大的自然环境中来。正是由于这种表达方式,沈从文将诗和散文的因素输入到小说创作中,使情与理合二为一,使自然与人完美契合,通过景物的烘托,使人物和自然达到了统一和谐。这样的创作方法更加有利于创作思想尽情发挥以达到高超的艺术效果。例如:描写翠翠和三三两位少女的性格时,作家将两个人放置于河水的背景之上,因而人物就有了水一样的柔情,而将柏子和虎雏放置到山石怪峭的岸上,激流勇进的河水中进行描写,因此他们的性格就有粗犷、豪爽的特点。沈从文自己很推崇“人与自然契合”这种写作方式,当他阅读了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后,拍案叫绝,为有一位创作手法与自己相似的作家而感到高兴。他说:“从五四以来,以清新朴讷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字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种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作者(指废名)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11]这不仅是对别人的赞美,也是对自己创作手法的推崇。这种将笔触延伸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里,以溢美的言辞讴歌自然美景,将人性自然化,达到“人与自然契合”的艺术境界,这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比比皆是。这就是三十年代“京派”文人所谓的“纯正的文学趣味”。
像“京派”作家群落中的许多青年作家一样,沈从文过早受到特有的地域文化的洗礼,因此他们的创作很少受到殖民地色彩的现代派文化的侵蚀。他们大多来自乡村田园,而经过种种人生经历,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半封闭地带。在这样的地理文化环境中,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接受中外文学类似“杂居”的熏染,同时从他们根深蒂固的乡村地域文化出发,表现出区别于其它派别的文学旨趣,即努力超然于政治派别文学之外,又有别于亢奋、突兀、迷惘、骚动的现代派情趣,表现出“京派”文人所共有的“纯正的文学趣味”,即将纯美的人性放置于他们精心提炼出的理想境界中加以艺术地完美表达,从而使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一种从容、和谐、恰当的文学情愫。
沈从文正是凭借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以“乡村田园文明”为出发点,吸取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在写作实践中形成他艺术风格上的又一审美个性,即用清晰朴讷的笔调表现纯正与纯情。沈从文以人性的美丑作为衡量社会优劣的价值标准,这实为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而人性的美丑分析沈从文更多是一种道德分析),他将这种思想和价值标准放置到广博、深刻的社会生活中,并通过分析自我熟知的湘西“纯正人性”阐释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宗教观及美学观念,由这些文化构成因素精心创作自己的乡土边地文学作品,并通过作品赞美湘西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田园文明,用纯朴友善的乡村人性与都市异化了的人性进行对抗,从而深刻批判了都市社会的丑恶与黑暗。通过这些,我们无不体会到沈从文对“民族审美文化”的追根溯源,有着强烈的愿望。因为“文学应当在深刻程度上描写人、描写人的心态、社会心态和民族心态。而人、社会、民族又都是在一种文化系统中形成其独特的秉性和心态,他们既是文化的承受者,又是文化延续的载体。文化除了哲学、艺术、宗教以外,还有物化的精神创造和行为化的精神创造。尤其是这种行为化创造体现出人的衣食住行,生活形态方面的习惯、规范和特征,文学描写人,就是从这种行为化入手的。”沈从文对湘西地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把握,因而他能从“湘西审美文化”把握上看现代社会的不合理性,看清了现代都市文明正对乡村田园文明进行无情的冲击与吞噬,乡村文明正在遭受空前浩劫,在这种劫难下,传统道德失落了,人性异化了。这种文明失落的结果,使沈从文不得不以一种赤诚眷恋的心情,对乡村田园文明进行呼唤。以无比憎恶之情对都市丑恶、污秽的“文明病”,给予无情鞭笞和讽刺。因而,沈从文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写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对抗,并就城市和乡村进行对比,乡村人的宽容、纯正、洒脱、勇敢、灵秀,无一不与都市特权人的自私、虚伪、呆板、怯懦、庸俗发生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否定现代都市文明。沈从文对现代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否定程度,达到了与左翼作家从正面批判社会一样的文学效果。但沈从文的创作,更多地倾向和侧重于道德批判,他更多的是关心个体的人,通过道德分析的途径,衡量人性美与丑,注重人的道德世界,并怀有更多的感情色彩,努力用一支笔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给予的形式,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出最后一首抒情诗”。
沈从文想通过创作唤回那个美丽的边城世界,对这个世界里扶植纯正人性,这种对民族审美文化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时代发展的自然规律、城镇进化论又告诉我们:现代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城市的发展与古村落的衰亡,两者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有它不合理的因素。虽然早期中国都市在它发展进程中遭受到过多殖民地文化的侵蚀,近现代中国城市文明是一种扭曲与异化了的文明。沈从文创作的着眼点是从“人类历史发展与社会道德进步之间出现的二律背反现象”消极的方面着手,对近现代城市文明进行批判,而恰恰因为他只注意和领会了这一点,而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民族审美文化”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内含社会进步的因素),致使他的创作视野不够广泛,精神思想也过于局限。虽然,他已悟出了“湘西地方将来的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并衰亡消失”的道理,但由于创作思想的局限,使他无法掌握现代人的真正命运。
从“民族审美文化”的角度,评价沈从文讴歌纯正人性美、道德美的创作旨意,有着多种积极的元素。正是由于他能够用一种浪漫抒情的笔调写纯正的“人生形式”,他的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独具个性的特色,因而,沈从文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坛史上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而沈从文本人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坛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出色作家。再读沈从文艺术作品,其更大的积极作用是在城镇化进程中,面对道德滑落、人性缺失、功利严重、价值扭曲的社会趋势,能够重铸我们民族精神、实现“中国梦”,它警示着我们要进一步确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积极地看待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两者之间的合情合理的统一关系,促进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周定州. 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选集(第五卷)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沈从文.长河题记[A].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1984,(4).
[4]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A].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曾小逸主编. 走向世界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6]沈从文.泸溪浦市箱子岩[A].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花城杂志社.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创作[J].花城,1985,(1).
[8]沈从文.边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10]丁志琼.康德的二律背反论美[J].重庆大学学报,2008,(8).
[11]沈从文.论冯文炳[A].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常芳芳〕

Recognition of the Aesthetic Individuality of Shen Congwen’s Works
REN Zhi-gang
(Publicity Department, Party Committee of Tumote Qi; Baotou 014030)
Abstract:In Shen Congwen’s article, the beautiful scenery, folk customs and human nature in the remote western of Hunan,describes the nostalgia. Integrating politics,religion, morality and belief of life, he describes the specific landscape and human feelings.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his writings ar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the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a lot of morality and human nature problem appears,and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man and nature could help us recast national spirit,and realizes “the Chinese Dream”.
Key words:Shen Congwen; pure human; nature harmony; aesthetic individuality; nostalgia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6-0034-05
作者简介:任志刚(1966-),男,内蒙古包头人,包头市土右旗委常委、宣传部长,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2014-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