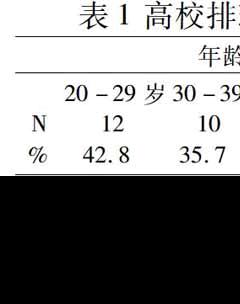徐懋庸的编辑生涯
2016-01-20李先国
李先国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网络传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徐懋庸的编辑生涯
李先国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网络传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徐懋庸的一生与编辑工作紧密相关。其编辑成果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编辑了自己的作品,二是主编了一些进步刊物,三是注释整理了与鲁迅的通信,从而为现代文学研究留下了许多一手资料。
徐懋庸 编辑 成果
一
1.因编获罪
1927年初,上虞县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门口挂着两幅大标语:“真革命的请进来,假革命的滚出去。”县党部主要的领导人是叶天底。徐懋庸的恩师徐用宾任组织部长,徐懋庸开始是组织部干事,后来又被分配在叶天底领导的宣传部当干事,负责编辑党报《南针报》。
编辑《南针报》之余,徐懋庸读了不少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陈独秀的《共产主义ABC》,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社会科学讲义》(上海大学的课本)等。此外,他还经常看中共的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读了这些书,徐懋庸觉得大开眼界,虽然理解得很少,却也据此为知识分子训练班讲过几次课。
上海“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两三天后就传到上虞,国民党的“清党”不久波及上虞。徐懋庸逃到慈溪。5月中旬,徐懋庸接到消息说,上虞的国民党县党部完全被反动分子把持,一些不显眼的左派都潜伏起来了。秘密转移到一个亲戚家养病的叶天底主张办一份秘密报纸,在上虞问题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对立的宣传。编辑由在慈溪的徐懋庸负责,印刷由在余姚的徐镜如负责,印刷费用由大家拼凑。印好以后,由钱念先、葛纪昌等在上虞秘密散发。因为是5月创刊的,故定名《石榴》。编辑期间,徐懋庸常与葛纪昌通信,谈些上虞情况和约稿的问题。6月20日左右,徐懋庸给葛纪昌的一封信被国民党反动派在上虞邮局查获了。信里提到的八个人包括他们两人都遭到国民党通缉。6月30日,得到消息的徐懋庸就在当天下午乘火车到宁波,换乘轮船逃往上海。后来他考进了上海劳动大学。
2.因编生隙
在劳动大学毕业后,徐懋庸到了临海回浦中学教书。1930年9月,徐懋庸把爱好文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艺波社”。“艺波社”曾编辑出版《波艺丛书》,第一辑收有作品20篇,于1931年6月出版。
该辑以《门槛》为名,因为首篇就是徐懋庸自己翻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名篇《门槛》。《门槛》描写一个俄罗斯少女决心为革命而奉献自己的一生。他在劳大读书时,这篇作品曾被选入教材,当时他读后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徐懋庸在本书的卷首,用分行的诗歌形式写了一篇《题辞》,鼓励青年参加革命。
徐懋庸的激进思想在一部分学生中产生极大影响,由此逐渐引起学校领导人的不安以至于不满,多次对徐懋庸提出了警告。1932年年底,他向陆翰文提出了辞呈。后来他闯入文坛,又回到上海。
1934年春徐懋庸加入“左联”后,因为鲁迅是“左联”的委员长,徐懋庸是“左联”理论研究会的一个组员,他同鲁迅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时候《自由谈》被国民党反动派所迫停刊,“左联”想办一个半月刊,代替《自由谈》这个阵地。恰好有一个惯于投机而不负责任的光华书局愿意出版这个刊物。光华书局想利用《自由谈》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主刊名为《自由谈半月刊》,“左联”让徐懋庸担任编辑。徐懋庸将这事请示鲁迅,鲁迅于5月26日的复信中劝他不要做编辑①。
徐懋庸曾经决定不干。鲁迅5月31日给杨霁云信中认为他拒绝得好。然而“左联”决定还是要在光华书店出版这半月刊,也还是要徐懋庸担任编辑,不过经过力争,名称改为《新语林》。徐懋庸为此还与鲁迅面谈。《鲁迅日记》也有记载。《新语林》办起来之后,鲁迅先生却是积极支持到底的,不但自己投过好几篇稿子,还介绍许多别人的稿件。徐懋庸由此认识到鲁迅先生很顾大局,决不固执己见。
但《新语林》才出了两三期就有问题了。首先是老板任意扣稿子,其次是拖欠稿费。于是徐懋庸又向鲁迅诉苦。鲁迅于8月3日给徐懋庸的信中劝他坚决放弃。8月间,经“左联”领导的同意,徐懋庸辞去了编辑。他编辑过四期《新语林》(半月刊)。接替他的人庄启东也只搞了两期,《新语林》终于夭折了。
1935年夏,“左联”想恢复两年多没有办的内部刊物。徐懋庸把这事向鲁迅报告,他表示同意。稿件凑齐以后,但碰到付印费的困难。要一百多元钱,从哪里来呢?办法是,第一,把大家在《时事新报》办的副刊《每周文学》的稿费充公,不给作者个人(作者都是常委会的几个人)。第二是募捐,在一次宴会上,徐懋庸请茅盾、胡愈之各捐了十元。当时鲁迅也在座,徐懋庸向他募捐,他却没有答应。徐懋庸着急得很,有一次同鲁迅面谈时,又向他要钱,他仍然说:“我没有。”这样拖了一个多月,最后《每周文学》又增加了一个月的稿费,徐懋庸自己也出了十来块钱,总算付清了印费,把叫做《文艺群众》的这批货取回来了。徐懋庸把这刊物寄给鲁迅两册,不料寄出的第三天,就收到他寄来的二十元钱。后来鲁迅先生给徐懋庸作了解释:开初不给钱是因为“左联”已经有两年多常说要出机关刊物,却总不见出。而且每月有人向他收取盟费二十元,也说是办机关杂志用的。现在刊物和他见面了,就给徐懋庸寄钱了。
鲁迅的解释,最主要的一点是反映了“左联”内部的矛盾和不协调,盟员之间缺乏了解,以致产生很多误会。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鲁迅与徐懋庸的关系原来并不是那么密切的。如果徐、鲁二人关系良好,鲁迅是不会拒绝捐款的,因为鲁迅完全知道这份刊物是由徐懋庸主编,更不要说徐懋庸曾经两次亲自向鲁迅募捐。即使鲁迅对周扬等人极为不满,也不应该把这不满情绪转嫁到徐懋庸身上去②。
3.因编怀念
1941年元旦,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李文、刘大明、王华三人在太行区创办的华北书店正式成立。1943年,该书店决定出版鲁迅作品选注本,其中的《阿Q正传》和《理水》的注释工作由到太行文联工作的徐懋庸担任。
当时鲁迅的作品在中国已广为人知。然而,由于含义深刻,取材精微,风格独特,语汇繁富,常使许多学识和经验较浅的青年难以理解。徐懋庸在平常学习讨论的时候,既能结合以前与鲁迅的接触与了解,又能结合马列主义和其他一些知识的帮助,往往被认为发言独到,见解深刻。抗大的一个同志曾提议把徐对这些作品的意见写出来发表。开始徐懋庸想到《阿Q正传》的读者最多,内容最丰富,就从它注起。此后的计划是,从《呐喊》里面选《孔乙己》、《明天》、《药》,从《彷徨》里面选《祝福》、《肥皂》、《伤逝》、《离婚》,还从《故事新编》里面选《铸剑》、《理水》、《采薇》、《出关》等篇或者选些论文来注释。实际上徐懋庸注释了鲁迅小说《阿Q正传》,之后从1943年到1946年还注释了鲁迅小说《理水》、杂文《拿来主义》及杂感《忽然想到》等篇目。
“文革”后期,政治动乱,经济萧条,文化凋零,许多人处在绝望的黑暗之中。这使徐懋庸想到了鲁迅。鲁迅在青年时期,就痛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黑暗,立志要加以改革。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于是他感到无聊,寂寞,以至于失去改革的希望。他把中国社会看成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人们只能在这里闷死,毫无出路。但是朋友的鼓励又让他充满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的思想,经常动摇于希望和绝望之间。1925年1月1日,他写了一首散文诗《希望》,认为希望和绝望同样是虚妄,但存在希望总比陷于绝望要好。这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徐懋庸要在1973年注释鲁迅的散文诗《希望》了。这一篇注释不同于四十年代的注释,以解释意义为主。在其后的《一点读后感》里,徐懋庸说:“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容易体会鲁迅在《希望》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心情了。但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的青年里面,倘有个别的人,只因为看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所不可避免的某些局部的,一时的消极现象,而看不到光明,失去了对前途的信心,甚至陷于绝望,那才是十分可悲的。这样的人,除了应该读马、恩、列、斯,毛主席的书以外,读读鲁迅的这篇散文诗,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的。”③
二
1.自编文集
上世纪三十年代徐懋庸是以写作杂文而出名的,他常在《文学》、《新语林》等几十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后收集出版的杂文集主要有:《不惊人集》,1934年编集,1937年出版,收有杂文五十二篇;《打杂集》,1935年出版,收有杂文五十四篇。
徐懋庸的文章,大部分是在生活书店办的刊物——《新生》、《大众生活》、《太白》、《世界知识》、《文学》、《世界文库》、《译文》上发表的。徐懋庸的译著《社会主义讲话》、《犹太人》、《伊特勒共和国》、《小鬼》等绝大部分是在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书店所付给徐懋庸的稿费,是徐懋庸1933—1937年的生活费的主要来源。1934年,他曾将自己的杂文作品编过一本《不惊人集》,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予通过,稿子也没有退回。1937年由千秋出版社出版。1935年徐懋庸出版另一本杂文集《打杂集》,二十万字。鲁迅给他作序。
这一段时期,徐懋庸用杂文的笔法,发表了不少谈文艺的短篇论文。收成集子的有《街头文谈》、《怎样从事文艺修养》、《文艺思潮小史》等。
《街头文谈》由上海光明书局于1936年5月出版,共收文章28篇,附录4篇。
在徐懋庸之前,用通俗的文笔写文学论文的,已有夏征农先生 《文学问答集》。徐懋庸起初却并没有效颦的念头。倒是《新生周刊》的编者艾寒松先生劝诱徐懋庸,说他可以写些这样的文章给《新生》的读者看看,徐随口答应了,便一礼拜一次地试写 “街头文谈”。徐懋庸用“力生”的笔名在《新生周刊》上按期发表。当发表到第十一篇的时候,《新生》便在“妨碍邦交”的罪名之下被禁止了,还有两篇写好了也不曾登出。隔了数月,《生活知识》创刊,要徐懋庸投稿,徐懋庸便寄去了那两篇存稿,但抹掉了“街头文谈”的总称,因为徐懋庸本来打算不再写了。不料《生活知识》的编者,仍给加上原来的总称,而且要徐懋庸继续写下去,也是每期一篇。情不可却,于是徐懋庸只好重新动手,但是不满十篇,终因忙于他事而停止了。1936年5月编印单行本时,还加了不少《街头文谈》之外的文艺论文进去。因为徐懋庸觉得自己的其他论文,也是“街头”的讲话。街头的讲话的特色是通俗,自然同时或者免不了浅薄。徐懋庸承认,《街头文谈》只是在学习中的笔记,虽然浅薄,却也曾获得不少读者喜爱④。
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小史》,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光华书店发行。1948年又在哈尔滨出东北版。
徐懋庸认为这一本小册子,不能算是一种著作,只是好几种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的内容撮述,尤以弗理契《欧洲文学发达史》和柯根《世界文学史纲》等几种为主要的根据。这两本书是中国当时仅有的较详细的唯物观世界文学史,徐认为青年们必须一读。
为什么有撮述的必要呢?徐懋庸解释:一则许多书卷帙太大,内容太繁,非自学的青年在短时间所能读完,并且倘没有一些预备的知识,读了也难以完全了解。二则原有各书,所叙的时代,大抵不完全,如《欧洲文艺发达史》,从中世纪说起,而忽略了古代,《世界文学史纲》则叙述现代处很简略,尤其是苏联的文艺思想,普通的文艺史上都还不曾说到。三则原有各书虽都有独到之见,但也各有错误的观点,初学的青年往往难以辨别。因此,徐懋庸认为有必要编一本简明的包括各时代的、采原有各书之长而舍其所短的小册子是必不可少的。故而,当“青年自学丛书”的编者向他征稿时,他就认定了这一工作。着手之后,他又想到普通的世界文艺思潮史都不涉及中国的一部分,这也是一种缺陷,最后又自撰《中国文艺思潮的演变》一章,说明五四以来直到目前的中国新文艺思想的发展。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徐懋庸的《街头文谈》的成功使他后来在《大众生活》上,又用了“林矛”的笔名,写起“文艺修养”来。可是后来《大众生活》也和《新生》一样,遭了禁止。“文艺修养”自然也像“街头文谈”那样中断了,先后只登了十二篇。徐懋庸想要留个纪念,所以决心把“文艺修养”编成一本书,除了已经发表的十二篇之外,又新写了九篇,并加三篇附录。《怎样从事文艺修养》由上海三江书店1936年12月15日初版。
2.主编刊物
三十年代徐懋庸除了主编《新语林》、“左联”机关内部刊物《文艺群众》外,编过的刊物还有:
《时势新报·青光》副刊《每周文学》,1935年9月15日创刊,1936年6月2日终刊,共出36期。每周文学社编,徐懋庸、王淑明主编。主要内容为刊登文艺作品,译文。有何家槐、风子、立波、林淡秋、林焕平、旅冈、梅雨等投稿,多是左联常委成员。
《新知识》半月刊,1936年12月10日创刊,1937年1月停刊。存见2期。编辑:王达夫、吕骥,徐懋庸、张庚、钱绍华,上海《新知识》社出版。
《希望》半月刊,1937年3月10日创刊,编辑人徐懋庸、王淑明,出一期后,徐懋庸辞去编辑职务,从第二期起,由王淑明编辑。共出2期,由希望出版社出版,上海中国图书杂志公司总发行。《希望》刊登各种短篇文艺作品,译文。撰稿人有乔木、沙丁、罗烽、周木斋、周扬、郭沫若、何家槐、梅雨、立波、林淡秋、张庚等。
另外,徐懋庸也参与过编辑《太白》半月刊。该刊是1934年9月20日创刊,1935年9月停刊,共出24期。编辑艾寒松、傅东华、郑振铎、朱自清、黎烈文、陈望道、徐调孚、徐懋庸、曹聚仁、叶绍钧、郁达夫。编辑人陈望道。上海生活书店发行,发行人徐伯昕。《太白》刊登各类文字,画稿、木刻也刊载。特约艾芜、巴金,冰心、草明、陈子展、丰子恺,夏丏尊、廖埜容、夏征农、任白戈、胡愈之、杜重远、黄源、风子、洪深、杨骚等撰稿。
《太白》办起的时候,正是中国出版界的困难时期的开头。那时候编辑委员会虽曾有过较远的志向,较大的计划,然而后来大抵不能实现。但在陈望道先生独力奋斗之下,这刊物在这困难的一年中,毕竟还成就了许多可贵的工作。手头文字的采用和推行的便是其一。其二则是编成了“小品文与漫画”特辑,将小品文和漫画的综合的知识提供给读者。
1934年9月20日《太白》半月刊创刊号上徐懋庸发表了《要办一个这样的杂志》一文,作为对于《太白》编辑委员会的提议。停刊后,徐懋庸作为编辑委员,曾经撰文谈到《太白》的停刊。他相信《太白》在扭转《论语》和《人间世》所造成的颓废的个人主义的小品文作风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4年七八两月中,徐懋庸编过四期《新语林》的半月刊,后来因为发行这刊物的书店对稿费不负责任,使他觉得对不起作者就辞职了。辞后不久,《社会日报》上登出一个消息,说徐懋庸将继《新语林》而编辑《芒种》半月刊。
辞掉《新语林》的编辑后,徐懋庸接着加入了生活书店的一个半月刊的编辑委员会。其时那个半月刊方在筹备,名称未定,大家分头拟想,他也想了几个,但都不好,最后是决定采用了陈望道先生所拟的“太白”。在《太白》定名的次日,徐懋庸忽然想起《律历志》上的二十四气的名目,觉得其中的“惊蛰”和“芒种”等几个颇可作刊物名之用;后与曹聚仁谈起,他也以为很好,而且特爱“芒种”这一个。
群众杂志公司要办一个刊物,请徐和曹先生合编;徐稍稍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并且和曹先生商定,乘机就把“芒种”两字用了出来。他们就把这个刊物办了起来。《芒种》半月刊,1935年3月5日创刊,1935年10月5日起,刊行第2卷第1期,存见11期(第1卷共10期,第2卷1期)。编辑人徐懋庸,曹聚仁。第1期起至第8期,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第9期起,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并组织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人还是徐懋庸、曹聚仁。《芒种》刊登对社会大小事件的小评论、长篇论文、半月读报记、国外消息、历史小说、讽刺小品、随笔,短长篇小说。投稿者有乔木、姚雪垠、方之中、陈子展、沙丁、韩滔、盛公木、李辉英,聂绀弩、鲁迅、林焕平等。
到延安后,徐懋庸编辑过《华北文化》半月刊。这是晋冀鲁豫文联办的刊物,《华北文化》社编辑,陈默君,张秀中主编,1942年1月25日创刊。出至第2卷第3期改刊,共9期。1943年4月25日改出革新号,由徐懋庸,林火主编,1944年2月25日停刊,共出16期,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华北文化》革新第3卷第3期徐懋庸发表了《写作者要请工农兵作顾问——向〈华北文化〉的投稿者提议》一文。针对当时文化界的写作者虽早就下了决心要把作品做到大众化通俗化,但是又苦于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决心,徐懋庸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写作者要请工农兵做顾问。文中徐懋庸通过实例总结请工农兵作顾问有五个好处:会启发我们的思想,会提供给我们很好的材料,会帮助我们想出很好的譬喻,会指教我们怎样很好地组织语言,会纠正我们的表现方法。还谈到请工农兵作顾问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希望大家都尝试。
此外,徐懋庸还和方纪主编过《热潮》半月刊,1946年6月创刊,承德《热潮》社编辑,存见3期。
3.释编通信
徐懋庸曾经根据巴比塞编的法文译本译出《列宁家书集》,三十多万字。1937年出版。此书稿费成为徐懋庸去延安的旅费。晚年他还编辑过自己与鲁迅先生的通信。
徐懋庸第一次同鲁迅通信,是1933年的11月间。那一年初,徐懋庸从黄岩到上海,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夏季开始写杂文投寄给黎烈文编辑,受到黎烈文的欢迎。此后徐懋庸便成为《自由谈》的撰稿者之一。11月间,徐懋庸翻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出版,就寄了一本给鲁迅,鲁迅当夜就作复。17日和19日他又给徐懋庸两封信,更正了他15日信中答复的一个错误,并指出徐懋庸的一句译文的错误。在首尾5天内,鲁迅给素未谋面的徐懋庸共写了3封信。事实上,这在鲁迅方面来说并不是很常有的。例如鲁迅在1926年1月17日接到胡风的信,便没有回信。1934年4月28日,叶紫给鲁迅的信,也是在三天后才作答。徐懋庸这次得到鲁迅的优待,可能是与他翻译《托尔斯泰传》有关,另外就是他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与鲁迅的基本是同一步伐的⑤。自此,徐懋庸便经常写信给鲁迅。据统计,自1933年11月15日鲁迅收到徐懋庸的第一封信起,到1936年8月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止,徐懋庸写给鲁迅的信共60封,鲁迅给徐懋庸的信也有52封(公开信不算在内),数目实在不小。不过,在王宏志看来,仔细分析现存鲁迅给徐懋庸的45封信后,便不难发觉其实鲁迅与徐懋庸并没有深厚的个人友谊。第一,鲁迅给徐懋庸的信,绝大部分都是篇幅短小的,四五百字的只有一两封,大部分只有一二百字左右,而短至100字以下,甚至只有二三十字的也很多,与其说是书信,倒不如说是便条。第二,书信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出版的问题,大多只是谈一些有关稿件的事,并不见有进一步涉及比较私人的事情。此外,比较鲁迅写给一些较亲密的朋友的信如曹靖华、萧军、萧红和胡风等,鲁迅在那些信中不但经常谈及自己的生活、思想及健康状况,对于对方的生活及近况也很清楚了解,且时常开玩笑、发牢骚等。这都是在写给徐懋庸的信中所没有的。此外,鲁迅给徐懋庸的信中,处处表现得很客气,例如始终称徐为“先生”,语气上也很能显出二人的距离。所以,书信的数目,实在不能证明二人关系密切。主要的原因是徐懋庸当时在编辑《新语林》和《芒种》等刊物,鲁迅经常投稿及介绍稿件,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书信往还。显然,这都是公事上的交往。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对鲁迅提出诘难。当时鲁迅在病中,身体很差,“因为没有气力,花了4天工夫”⑥,写成了公开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第1卷5号上。这就是当时上海文坛所称的“万言长文”。
徐懋庸跟着又写了一篇还击的文章 《还答鲁迅先生》,发表在一份较小的杂志《今代文艺》上。另外,还有一篇叫《一封真的想请发表的私信》,刊登在1936年9月1日的 《社会日报》上。
1937年1月,许广平在《中流》杂志发布《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
杨霁云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长虹、侍桁、徐懋庸等处藏鲁迅先生的信件谅亦不少,我望他们光明地能贡献出来。不过鲁迅先生的信札全部发表出来,我想将刺痛一部分鬼魔的心,阻碍一定不少。这点要先生继鲁迅先生之志毅力战斗才成。”⑦
高长虹、韩侍桁和徐懋庸,起初都是与鲁迅过从甚密的青年,深得鲁迅爱护提携,鲁迅与他们谈文论艺,信札往来频繁,最终他们却都与鲁迅反目成仇。许广平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发出后,果然不出杨霁云所料,高长虹、韩侍桁都没能将他们手中的任何一封鲁迅书信“光明地贡献出来”。直到1938年10月,许广平在提起韩侍桁时,还对他不愿出借鲁迅书信一事耿耿于怀⑧。
1937年1月13日,当徐懋庸在10日出版的《报告》杂志上看到许广平征集书信的启事,他当日就去函询问,显然他是一看到征集启事就行动起来了,可见其关切之情。但就徐懋庸信中所言,则他对出借鲁迅书简一事也顾虑重重,主要是顾忌到许广平等人是否“对收信者拟有所甄别”⑨,这里的“收信者”当然是指徐懋庸自己。这种疑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刚刚过去的鲁迅葬仪中,徐懋庸挽联被取消的遭遇,使此刻的他依然心有余悸,担心作为“收信者”的自己还会受到排斥。
当徐懋庸得到许广平回复,被告知征集鲁迅书信的原则是“对于征求信稿文件,是向各方普遍收集的”,并且保证“至于编辑方面,则请先生不必担心也”⑩之后,徐懋庸才将所集鲁迅手札一本,共四十余封通寄给许广平,但依然格外小心谨慎,不忘在信末附言中叮嘱许广平:“所有手札原件,希勿使多人看到,幸甚。”⑪后来《鲁迅书简》中印出来的是四十三封。
“文革”结束之后,徐懋庸应陈漱渝之邀决定整理注释他与鲁迅之间的通信。徐懋庸希望自己的注释,将与曹靖华的《鲁迅书简——致曹靖华》注释法不同,范围要宽一些,将说明一些事实,并对鲁迅先生的思想作些分析,有些地方,还要联系鲁迅先生给别人的一些信。计划在三四个月内完成。然而写作时面临的困难不少。一是当年冬天南京天气不好,他身体感到不适。二是缺少必要的资料和助手——没有帮助抄写的人,更没有复写、打印的条件。但徐懋庸以高昂的精神状态不断克服着面临的困难。在此期间,陈漱渝跟他书信往返频繁。
1976年12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电讯,刊登于次日《人民日报》第4版下方,题为《新发现一批鲁迅书信》。标题下有一段按语:“这些书信,都是鲁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最后十年写下的,其中对徐懋庸伙同周扬、张春桥之流,‘以文坛皇帝自居’,围攻鲁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对我们今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有重要意义。”这条电讯使徐懋庸大吃一惊。这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仅仅两个月,徐懋庸居然又跟“四人帮”成了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种荒谬是徐懋庸万万想不到的,对他的打击之大也是局外人难于体会到的。不久之后,徐懋庸含冤而逝。在病中,徐懋庸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写出了《对一条电讯的意见》,成为他四十余年文字生涯中的绝笔。徐懋庸对他与鲁迅的通信的注释和编辑工作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进行的无疑也是一份珍贵的鲁迅研究资料。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4.
②王宏志.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230.
③徐懋庸.释鲁迅散文《希望》·一点读后感.徐懋庸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72.
④徐懋庸.《街头文谈》小引.徐懋庸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304.
⑤王宏志.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221.
⑥鲁迅1936年9月15日给增田涉信.译文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6.
⑦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44.
⑧程振兴.鲁迅书信的征集与择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1).
⑨⑩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55.
⑪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56.
浙江省社科规划基地一般项目《越地现代文学理论研究》(12JDYW02YB)。国家留学基金项目: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中的“创伤”心理研究(20140833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