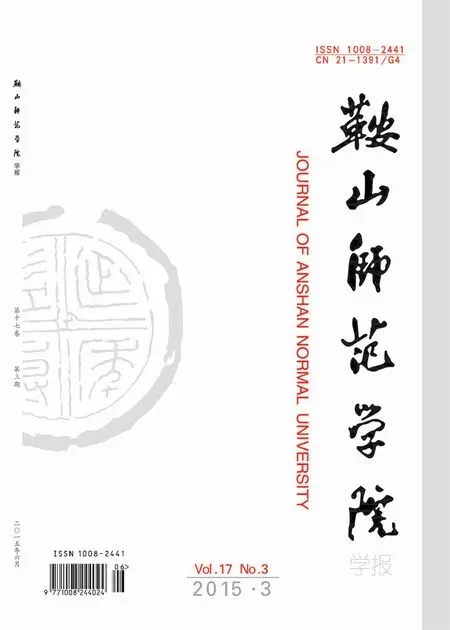陈子谦电影场景中歌台构建的意义——以《881》《12莲花》为例
2015-12-17蔡译萱
陈子谦电影场景中歌台构建的意义
——以《881》《12莲花》为例
蔡译萱
(鞍山师范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摘要本文选取新加坡导演陈子谦《881》与《12莲花》两部电影,以歌台为切入点,分析歌台在电影中的建构以及其所承载的主题、性质。通过时间空间所呈现的独特性,导演表达了对传统新加坡文化的怀念,并试图重新唤起人们对歌台文化的关注与喜爱。但在对歌台怀旧书写的同时,在不同程度对歌台文化却起到消解的反作用。因此,如何保护歌台文化仍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陈子谦;歌台;电影场景
与以往新加坡的电影套路不同,陈子谦在他的两部电影《881》及《12莲花》中并未采取政府祖屋这一新加坡特色建筑作为电影主要场景,转而架设了新马独有的七月歌台空间进行他的新加坡书写。“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某种意义”[1],歌台空间的使用,在电影层面如何支撑电影情节的铺排与怀旧情绪的宣泄、现实层面传达了对于新加坡的何种思考,即是本文要探讨的论题。本文拟从书写载体、书写性质及书写主题三个层面分而述之。
一、对歌台的时空塑造——《881》《12莲花》的书写载体
导演陈子谦在《881》与《12莲花》两部电影中选取歌台空间进行电影场景建构,力图通过其中的情节流变来展示新加坡独有的文化并使之在现实意义上得以延续。在《881》中,歌台被置于显性地位进行直接展现,《12莲花》中的歌台则相对隐性地退居幕后作为支撑电影情节发展的背景而存在。无论是怎样的处理方式,通过歌台的架构,两部电影具有了一定的潜在关联性。歌台本身在时空中具有可被扩大延伸的复杂性,通过对这种复杂性的再造和利用,陈子谦架构起两部电影的书写载体,即叙事整体的骨骼框架,为情节的流动和情绪的传达提供平台。在电影中,这种复杂性表现在歌台在空间中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并存,以及时间的相对停滞与发展。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论述作为承载电影情节内容的歌台是如何在时空中被构建,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保证故事的完整。
(一)自身的空间独立性与开放性
新加坡的大城市空间之中,歌台作为并不固定、相对临时的建筑空间,具有其自身的空间独立性,或可谓半封闭性。与现实生活中的歌台歌手情况类似,在《881》中的木瓜姐妹一样需要在繁忙的七月奔波于不同歌台之中,并且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即一旦没有赶上歌台表演时间便无法登台表演,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下一场歌台的到达。这些歌台错落分布在新加坡的各个角落,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有足够的容量来包容电影情节的推进,而这些空间彼此之间唯一之联系也仅仅是赶场其中的歌手们。置身于这些空间中的人物,其活动都围绕歌台而展开,外部新加坡空间的变化似乎被歌台的存在而分割开,歌台之上与歌台之间的空间成为了独立于外部的小世界。可以说,歌台空间的这种独立性便为电影情节中许多矛盾、冲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并藉由歌台上活动的人物来表现。《881》中,这种独立性的规则更是被放大到尖锐矛盾的程度:歌台的规矩是谁先到谁先唱,你方唱罢我登场,歌手们为了登台相互竞争。木瓜姐妹与榴莲姐妹的矛盾无疑就是围绕歌台而展开的,而在这其中所呈现的矛盾内容实质也可以看作新加坡社会矛盾的一个现实小缩影。无论从服装、语言或其他表现形式,可以看出陈子谦在塑造榴莲姐妹人物形象时,意图在其中注入现代性、全球化的元素,而木瓜姐妹相对则更为在地、传统,在歌台独立空间中,榴莲姐妹与木瓜姐妹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新加坡的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也反映出导演对此问题的思索。
同时,歌台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导演通过这种开放性将歌台延伸,与歌台外部的新加坡进行局部的融合,使之具有多元性。歌台的开放性由其观众而决定,作为中国福建沿海的七月中元节传统并在新加坡得以赓续的文化,歌台设立的初衷即是面向“鬼”,朝“鬼”开放。除此之外,歌台的主体受众是福建人后裔,并发逐步展向整个新加坡开放表演。通过这种具象的开放表演,陈子谦得以利用歌台的开放性将歌台内部的矛盾向外部空间进行延伸,在歌台与其外部新加坡社会空间之间建立关联,在避免二元对立的同时又重新审视歌台自身状况,达到为电影情节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的目的。这也是本文后半部分将要论证的关于陈子谦镜头下歌台的美化。
(二)歌台时间的相对停滞与外部新加坡的线性时间发展
在空间复杂性之外,歌台时间的复杂性也在电影中被建构用以铺叙情节与情绪。两部电影通过场景、服装的特色营造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情,然而若将故事时间加以考量,便会发现歌台电影中时间的相对现实后退的错觉。尤其《881》之中,电影开头便已通过木瓜姐妹的出生时间及年龄将时间定位于2007年,但歌台的繁荣、演出服装的华丽,种种现象都将电影中的时间进行了错位回溯至远离电影现实的从前,将电影中的歌台赋予怀旧审美与体验。
与歌台外部甚至现实世界人们惯于接受的时间线性流逝不同,歌台电影中的时间由于歌台表演的重复上演而产生循环。歌台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举行,这种固定的时间、相同的表演形式、年复一年的福建歌曲,包括电影的拍摄也主要集中在七月歌台,电影字幕简单出现的year1,year2,year3,都使电影故事永远是循环发生在七月看似没有前进。时间的循环带来时间的相对停滞,与线性时间之间的张力给怀旧情绪的宣泄留下余地。除此以外,陈子谦也用特殊的拍摄技巧给镜头中的环境蒙上一层怀旧色彩。《881》中“玲姨在看到电视上的陈金浪时,镜头是玲姨的脸部特写,但仅占了景框的一半。另一半是少年时期明珠姐妹的海报”。还有“许多在新加坡人生活中逐渐消失的地方如湿巴刹(即菜市场)和售卖宠物鸟的店面等”[2]。《12莲花》中受刺激的莲花则始终活在假想中,与时代脱节,甚至连信用卡都没听说过。以及十几年后与阿龙长相一样的年轻人的到来,时间在莲花的世界中以凝结的状态存在。
在电影中,歌台空间中的时间是相对静止的,与歌台之外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形成对比。歌台建构中时间的特殊性与外部新加坡时间线性快速发展形成剧烈对比,对昔日的缅怀可以将时间的逝去具体可感,传达出陈子谦意图表现的怀旧情感。
二、歌台的承载内容——《881》《12莲花》的书写主题
“作者所描绘的空间皆代表着他们所怀念和偏向的事物”[3],歌台便是导演陈子谦所怀念的传统事物之一。在导演陈子谦镜头下歌台是一个特殊又具体的空间,这个空间承载着生活在其中的小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表达方式与联系方式——福建话。而这些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同正在新加坡逐渐消失的方言共同将歌台的没落象征表现出来,歌台文化究竟如何延续,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寻求生机,也成为导演没有说出口的情节命题。
(一)人物的悲剧性
陈子谦两部歌台电影皆塑造了一些悲剧人物的形象,情节的离奇,并不只是将导演的眼界囿于表现命运的无常引人唏嘘,歌台人物不完满的结局更多是为契合暗示旧的、传统的事物没落。
在《881》中,木瓜姐妹舍弃自己的幸福受仙姑指点后成为歌台歌手并红透半边天。榴莲姐妹嫉妒木瓜姐妹,处处与她们为难。引发她们的最终对决,结果因小木瓜的病情而失败。电影中的陈金浪是现实生活中的“福建金曲歌王”,他因大肠癌于2006年七月初一死于新加坡。而《881》中,木瓜姐妹正是因为听他的歌而结识并最终决定成为歌台歌手。
《12莲花》中的莲花少年丧母,父亲嗜赌成性,又经常打她。为补贴家用,莲花少年就出来唱歌。可是祸不单行,父亲死亡,又惨遭恋人阿龙背叛,精神受到打击。待她重返歌台时,发现这个曾让自己光芒四射的歌台已将她抛弃。甚至一直在照顾莲花的小飞侠也与莲花产生巨大的鸿沟,小飞侠在门上贴的纸条写着“Dear policeman,my aunty got mental disablility”。小飞侠对莲花的称呼由姐姐转变为阿姨,暗示外在空间的时间化,莲花的时间停滞转变为封闭的空间,最终莲花死于非命。贯穿整部电影的歌曲《12莲花》也正是莲花一生的缩影,与《881》中木瓜姐妹最后唱的歌曲是同一首,“十二莲花无了时,堕落黑暗难见天。少年赚钱是一时,老来怎样过日子。”阿龙,金钱至上,为自己出人头地,计算并背叛莲花,最终离开歌台。
在这两部电影中,主角人物或死或离,宿命的颠沛流离暗合歌台的衰落无力,当支撑、热爱歌台的人群逐渐远离,歌台究竟如何延续而存,也成为电影没有直接点明的一个主题。陈子谦对歌台的怀念是毋庸置疑的,“七月歌台也见证了陈子谦的成长。每逢七月,年幼的陈子谦都会随家人去观赏歌台演出;长大了,他也会同朋友们‘跑台’,观赏七月歌台”[4]。陈子谦也在访谈中明确表示《881》是为他母亲拍的,而母亲那个年代兴盛的歌台,对陈子谦及那个年代成长而起的集体都是不可磨灭的回忆。
(二)使用语言的复杂性
新加坡最早由英国人弗莱士开埠,“年久日深,英语成为公用的沟通工具,另一方面压抑、剥夺了在地语言文化的原生性,一方面却也正因为在地的影响,宗主国的英语也变得驳杂而‘不纯正’起来。[5]” 在新加坡,华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4.2%,华语的使用应比英语的使用更为广泛,但在年轻一代的华人中则更多的使用英语,“双语教育”与华语自身的复杂性是其中重要的两点因素。然而在国际化的新加坡,甚至全球,英语已成为通行语言,潜意识里英语已比华语更具优先使用权。同时新加坡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这使方言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处于一种逐渐消失的状态。在这些政策推动下,新加坡英语的广泛使用似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潮。在《881》与《12莲花》两部电影中,人物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多样性,对白以福建话为主,掺杂使用华语与英语。
在《881》的歌台表演中,榴莲姐妹说着英语却在歌台上唱福建歌,被大木瓜说“华语讲得这样烂,还要学人家唱歌台”。英语是世界通用语,作为一对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交流的榴莲姐妹,选择唱歌台作为自己的职业,无疑可以看作是对歌台传统语言文化的一种潜在侵略。唱歌台对于榴莲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她们是否真的喜爱歌台并无从定论,然而她们与木瓜姐妹竞争是为自己的声望与利益,这一点是昭然若揭的。不妨设想,日后的歌台也许会为适应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出现英语歌曲而抹杀其传统意味。面对这种强势文化,已处于劣势的歌台更加岌岌可危。在《881》中,凯伦姐说:“现在的市场缺少了福建歌”。可见,福建歌曲等传统语言产品已并不如陈子谦所成长的那个年代般受到追捧,其在与英语等其他所谓国际性语言的博弈中逐渐成为那个逝去的年代的记忆烙印。
陈子谦在两部电影中通过歌台大范围地使用福建歌曲,其用意不仅在于表达怀旧情感,更是以电影这种大众传媒,通过方言的地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受众者——福建人,甚至是新加坡华人的认同感、亲切感,从而让人们重新关注、了解歌台。
(三)怀旧镜头下空间布局的现代化
在《12莲花》中,电影开头即是一段野台戏,人物造型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戏剧样式,贯穿其中的音乐伴奏也是二胡等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但随着故事情节时间发展,这种传统表象被五光十色、现代的样式取代。上文在论述时间的停滞性时已对镜头下事物所呈现的怀旧性进行了分析,但即使是叙述时间相对故事时间的后退,从舞台的炫目及歌台歌手的服饰来看,电影中歌台的空间布局和场景装扮仍不可避免充满了现代感,与意图表达的捍卫传统的怀旧情绪产生了深层的对比冲击。
舞台布置由具体的道具、生动的幕布打造出MV的视觉效果。如《12莲花》,导演为表现莲花的甜蜜恋情,将歌台布景装饰成公园,与西方戏剧一样追求布景的完整。除营造MV的视觉特效外,通过导演的拍摄镜头,观众仿佛置身在一场场演唱会中,正是观众的欢呼与掌声使之具有真实感。现代演唱会兴起才带来的舞台特效,例如灯光、烟雾、火焰、荧幕等被大量使用于歌台之上。甚至在《881》中,歌手可以飞起来,这是以往歌台所不具有的超越现实歌台状况的表现。在服饰方面,现代化体现的更加明显。木瓜姐妹与莲花在生活中的服饰日常化,但在舞台上,她们的服饰变得多元化且具有时尚感,充斥着大量的短裙、长靴、羽翼道具等当下流行元素。在木瓜姐妹与榴莲姐妹较量中,木瓜姐妹选择的服饰有泰式的、日式的、印第安服饰等各种国际性服饰,而中国传统元素已不见踪影。
“一方面关注离散境况里华人应该保有中国性,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华人必须融入新环境,并由此建立其 (少数族裔)代表性。[6]。” 面对不断朝着更加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加坡,纯正、传统的歌台为适应新的环境被迫必须做出自身的改变在电影中,他们唱着“12莲花”却以探戈来配舞,这样扭曲的组合却大量出现在两部电影之中。歌台在延续传统与接纳现实之中如何抉择,是像电影中呈现出来的对现代性进行妥协,还是继续坚持传统直至被浪潮淹没,这成为电影呼之欲出的一个诘问。
三、歌台的建构意义——《881》《12莲花》的书写性质
“整理个人心中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感受,发掘这个城市的潜藏能量,探讨城市的可能性,重新定义这座城市[7]。”
这两部电影分别拍摄于2007年与2008年,受众是当下的新加坡华人,而这些华人中很大一部分对歌台的认知感受已与老一辈人大为不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世界发展模式趋于相同,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经贸中心更不例外。“正如本雅明所说,那些征服者形成了一条连续的权力链,它不仅玷污了‘文化财产’自身,也玷污了它们从一代向另一代的传播[8]。”新一代对于过去历史的认知只能透过官方提供,他们只是旁观者,并不是作为一个参与者。独有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一个城市形成自身的在地文化,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京剧;上海的里弄、外滩。但是新加坡的主流是追求现代化、国际性,潘家福(教育部华文课程规划员)表示“缺乏使用价值的东西,迟早需要让位给财大气粗的高楼大厦。单薄的历史仿佛被人剥掉了一层寒酸的外衣”[9]。而陈子谦是一位具有怀旧情感的导演,他表示“在新加坡,我经常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因为它一直在改变……那就是为什么我试图在电影中尽量多的记录的原因”。“我拍摄的每一部电影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视觉图书馆,它记录人与事。我同一些地方有强烈的联系——老地方,旧咖啡店,旧电影——我喜欢把它们记录在我的电影中。” 那些旧的事物有许多,而只有四部长篇电影的导演却选择歌台为叙述载体拍摄了两部电影,这是值得注意的。它突出了一种通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叙述的心里幻想。因为对歌台的情有独钟,因此不难理解他想通过两部电影,引起观众对歌台的关注,同时试图通过歌台来构建独特的新加坡。
在陈子谦的镜头下,逐渐式微的歌台以一种悲伤的意识和一种喜剧性的表现形式向往着、追忆着它繁华的过去。《881》与《12莲花》是两部悲剧,喜剧元素主要体现在《881》,如“H.I.V”(Holy innocent virgins)组合,玲姨对techno的疑问等。不得不承认,《881》与《12莲花》中的歌台光芒四射,具有活力。歌台上的木瓜姐妹和莲花受人喜爱,阳光乐观,就连莲花与阿龙的恋情都甜蜜梦幻,然而歌台下的她们却千疮百孔,最终抛弃遗忘。无论歌台的过去具有怎样的辉煌,延续到现代社会它始终笼罩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论中。
陈子谦的歌台文化既是遗忘的文化又是记忆的文化,遗忘是因为歌台正在消失,记忆是因为它是新加坡独有的文化,它的延续记录了新加坡的传统。“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但是他们对其它时空依然残存着集体记忆,在想象中创造出自己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创造出‘想象的社群’。” 所以说,《881》与《12莲花》实际上是对歌台文化的宣传与推广。生活在当下的陈子谦始终与“旧”歌台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感,因此他把“旧”歌台中的消极一面去除,把歌台理想化、纯净化。所以,电影中所呈现的歌台已与传统的歌台大为不同,它具有兼容性,这是与现代化现实的一种妥协,反之,这种妥协性在陈子谦看来也是一种积极的进步性。
但是把歌台这种传统的文化单独列出并加以美化,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歌台的一种消解。陈子谦把歌台艺术化的做法会导致歌台失去其独特的活力。毕竟歌台的观众是普罗大众,不是社会精英。真实的歌台是不可能有“仙姑”、飞天的,而且歌台的一部分吸引力也正来源于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而这些消极负面的是社会主流文化所否定的,如色情笑话。经过消解重构的歌台变得类似于“同一首歌”这样的舞台表演。“新加坡歌台,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任由各类歌手表现的平台,然而实质上,它却不知不觉的,变成了 ‘夜总会歌台’,崇尚、鼓励华丽表象,曲风大多是适合在大夜总会的舞池跳舞的风格,而且近乎单一的闽南语苦情唱腔。” 的确,《881》上映之初,成功却暂时地引起人们对歌台的关注。如何把一个有传统意义、独具个性的文化长久地延续下去,“不可能只通过一个文本、一个事件或一个时代从概念和意识形态的抽象框架中孤立起来得以保存”。但是陈子谦的想法和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他试图从歌台的衰弱作为出发点,寻找并构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在地文化,既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是对新加坡发展优先的主流社会价值的质疑与全球同一性的内在抵抗。
在《881》与《12莲花》中,陈子谦用歌台空间的建构表达出对于过去独有的、美好的生活怀念,并将新旧文化碰撞状况的议题置于其中表现。尽管两部电影都带有了悲剧性意味,然而镜头之下的歌台依然绚丽华美,散发末日之前般的余晖。面对着快速变化的新加坡大环境,导演通过逐渐被遗忘的歌台向观众传达他所认为的新加坡在地文化。除电影自身的怀旧体验外,现实关怀也寄予于电影,从多角度去宣传、保护甚至复兴歌台。然而在取精华去糟粕的抉择美化中,不可避免使得歌台文化失去其原始体验,其本质上赓续的动力被消解,其在现实中的活力并没有在电影中得以完整展现。在如何保护、延续歌台文化的问题中,陈子谦选择的建构方式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本歌台的定义,这是否能达到他的初衷,是否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仍然亟待思考。
参考文献
[1] 李威颖.纵看电影《881》和《12 莲花》中的七月歌台[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4):68-71.
[2] Tan.Kenneth Paul.Cinema and television in Singapore:resistance in one dimension[M].In Social Sciences in Asia.Leiden :Brill,2008.
关键词[3] 王徳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J].华文文学,2014(3):41-45.
中图分类号J9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蔡译萱(1991-),女,辽宁鞍山人,鞍山师范学院教师,硕士生。
[4] 王振春.散文系列6:根的系列[M].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5] 孙慧纹.论新加坡怀旧书写中的身份建构:以〈联合早报文艺城之岛屿书写〉为个案硏究[D].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位论文,2009.
[6] 苏亚华.新加坡歌台的瓶颈与困境[EB/OL].http://www.zaobao.com.sg/forum/letter/singapore/story
20140407-329696.
[7] 赵琬仪.寻找新加坡101[N].联合早报-现在青春版,2003-01-01.
[8] 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非主流写作、及一个现代中国神话的消解[J].文学评论,2002(5):34-47.
[9]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Cinematic scene construction of Ko-tai and its manifestations:
A case study of Royston Tan’s 881 and 12Lotus
CAI Yixuan
(AnshanNormalUniversity,AnshanLiaoning114007,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Ko-tai in Royston Tan’s two films:881 and 12lotus.The paper analyzes the cinematic scene construction of Ko-tai and its theme in the films.It holds that through distinctive time and space in the films,Royston Tan expresses profound longing fo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ingapore and tries to recall people’s admiration to Ko-tai.However,the nostalg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scene also represents a decomposition of Ko-tai culture to a certain degree.How to protect Ko-tai culture thus remains an issue that needs reflection.
Key wordsRoyston Tan;Ko-tai;cinematic’scence
(责任编辑:刘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