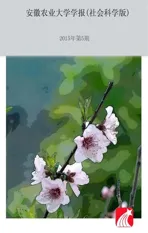松柏比德的历史演进*
2015-12-17王颖
王 颖
(安徽建筑大学 法律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173花卉草木是构成自然的一个重要部分,草木荣枯、花开花谢,容易唤起人生死、盛衰、成败的感应,更何况花木之为物,身旁眼前随处可见,所以古今文人所写的关联牵涉到花木的作品极多:“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2]5由于文人反复地描写,中国文学中一些重要的花木意象已经具有固定的意趣,成为某种人格类型的象征。清代的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玉兰,花中之伯夷也,高而且洁。葵,花中之伊尹,倾心向日。莲,花中之柳下惠也,污泥不染。”[3]54同样地,一提到菊,我们就会想到其简淡自然、凌寒而开的风致,就会联想到陶渊明。一提到梅,就会想到其清高芳洁、傲雪凌霜的特质,就会联想到林逋。
松柏是花木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其生性耐寒,品性贞刚,天然具备能暗示、象征主体品格内涵的特征,因此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象,累积起丰富的文化意蕴,成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松柏成了我们民族理想人格的符号,是“树”立的中国人。比德在各个时代都是松柏题材和意象文学表现的重点,说明这个符号不断地被重复、强化,表明了中国文人对节操的坚守和高洁人格的向往。
一、先秦松柏比德的形成
松柏四时常青,没有色彩的变化,也不像一般植物春荣秋零,容易引发人生盛衰的感慨,松柏在植物王国中是以比德见长的。松柏比德的起源很早,在先秦时期就获得了明确的人格内涵。《论语·子罕》记录下孔子关于松柏比德的经典之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4]92《庄子·让王》引孔子语并对其进行阐释:“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5]173将松柏的生物禀性与人物的道德品格直接联系起来。《荀子·大略》中也有关于松柏比德的言论:“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6]1305松柏耐寒、常青的本性被推演出道义自守、临难不移的气节操守之义,成为混乱之世中君子人格的象征。
松柏树干峭拔苍劲,材质密实坚韧,文人赋予其“有心”的品质,象征君子内心的坚贞不屈。《礼记·礼器》首次提出松柏“有心”之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这里“有心”当理解为内在的贞刚之性。唐孔颖达在为《礼器》中的这句话疏解时即云:“人经夷险,不变其德,由礼使然,譬如松柏凌寒而郁茂,由其内心贞和故也。”[7]448指出松柏贵在“有心”,惟其“有心”,才能岁寒不改、独立高标,成为君子志士的象征。
先秦儒家关于松柏“岁寒后凋“和“有心”的言论,揭开了松柏比德篇章的第一页,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学命题。此后随着它们在文学作品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逐步上升为文化符号,代表着困苦危乱之境中的不屈之节与坚贞之心。
二、魏晋六朝松柏比德的新变
魏晋六朝,松柏不但“岁寒后凋”的象征意义被继承和丰富,如:
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梁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早白,简文问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转茂。”(《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岁寒茂松”比喻张威伯仪表清朗、禀性坚明,松柏“隆冬转茂”形容简文帝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风采;而且人格寓意获得了新的发展,由贞心劲节的君子转而到洒脱俊逸的名士,由对人道德的关注变为对风韵的呈现。如:
南阳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李氏家传》)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飂飂”,形容松风强劲凛冽,比喻朱穆嫉恶、矜严的性情。“谡谡”,拟声词,形容风吹松林发出的肃肃之声,比喻李元礼为人严明刚正,其声威有如松涛,远播遐迩。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分析:“用‘飂飂如行松柏之下’来形容朱穆,完全是从一种对于风神仪态的感觉出发来评论的,行于松柏之下而觉其肃穆、摇曳,这是一种情韵的体验,用来状人,显然是指朱穆情操的高洁,表现在风神上,便有一种肃穆的风韵。”“所谓‘谡谡如劲松下风’,是指由内在道德情操所表现出来的风神气貌,给人以刚正不阿、不可侵犯的感觉。”[8]50
《世说新语》里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如:
庾子嵩目和峤:“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赏誉第八》)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第十四》)
请看这些修饰松柏的词语,“森森”“肃肃”“岩岩”,既是形容松柏,又是譬喻人。以“森森”之松状和峤,既有挺拔伟岸的形象展示,也有栋梁之材的能力比附,有形神兼备之感。“肃肃”,形容松风爽快清劲,用以比喻嵇康清正刚烈的人格。“岩岩”,雄伟高大的样子,比喻嵇康像孤松般傲然独立,令人一见倾心、肃然起敬。魏晋六朝文献中类似的描写还有不少。如:
桓帝时,南阳语曰:“朱公叔肃肃如松柏下风。”(晋·袁山松《后汉书》卷三《朱穆传》)
(嵇康)德行奇伟,风勋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晋·李氏《吊嵇中散文》)
以上例子都是借松柏喻人,这些比喻是建立在对松柏姿态、形体、颜色等物色美欣赏的基础上的,是由物及人的一种美感联想。
魏晋六朝松柏比德的新变,与魏晋名士崇尚玄学、钟情自然之风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文人的自然审美意识获得超前的发展,形成以自然美形容人物美的风气。这时的人物品藻很少见单纯的道德评价,而是着意对人的风姿、格调和才情的品评。在魏晋六朝松柏比德的具体例证中,松柏青翠挺拔的身姿与名士潇洒飘逸的风度、特立独行的气质表里辉映,自然之美与主体之美融为一体,形态之美与神韵之美打成一片,很难分别开来。
三、唐代松柏比德的丰富
唐代松柏比德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松柏成为文人托物自喻、感物咏怀的载体,是渴求世用而又不失自尊与个性的文士的象征,既饱含激情、信心,渴望建立功业,又耿介、孤直,不为世俗所容。
唐人在对松柏的描写中表现出个人昂扬的激情和强烈的自信。这在咏松诗中表现得犹为突出。如张说在《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中说:“不借流膏助仙鼎,愿将桢干捧明君。莫比冥灵楚南树,朽老江边代不闻。”此诗咏怀与咏物并重,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具有博大的情怀和高昂的格调。张宣明《山行见孤松成咏》托物言志:“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构,惜哉无人招。”借对孤松的描写,寄托了身世之感和对自身才能的自负,流露出希求用世的志向。至于李白《南轩松》中的“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的南轩松,则是诗仙才高气盛的形象写照。总之,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唐代松意象的主要格调。
这一点在对“岁寒后凋”典故的认识和应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唐以前,“岁寒后凋”多用来赞誉在乱离之世、危难之际依然能够保持节操、坚定如一的人生态度,表现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指导、约束自我行为的自律、自强,精神虽然可贵,却难免给人一种坚忍、沉重的感觉。唐人对松柏“岁寒后凋”的认识中有了新的变化,透露出了向上、乐观的积极心态。在唐人笔下,“岁寒”往往成为松柏展示风采、异于群芳的特殊机遇。如:“翠色本宜霜后见,寒声偏向月中闻”(韩溉《松》),“好是特凋群木后,护霜凌雪翠逾深”(王睿《松》),“唯助苦寒松,偏明后凋色”(钱起《松下雪》),都写出了松柏利用不利环境来表现自己的主动精神。
唐代文人特立独行的气质个性也在对松柏人格化的描写中展现出来。在吟咏松柏时,唐人常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寄寓其中,还将不合流俗的耿直、不甘沦落的倔强,也融入到松柏形象的塑造中。谢偃在《高松赋》中发出悲叹:“嗟美材之无用,悲侧路之崄巇。动跬步而致阻,投一足而必危。伤拙目之众毁,慨名工之独知。”[9]1593诗中那棵孤立无援、独处危境的高松分明是人物形象的写照:耿介孤傲、动辄得咎,与世俗格格不入。李绅在《寒松赋》中说:“负栋梁兮时不知,冒霜雪兮空自奇。谅可用而不用,固斯焉而取斯。”[10]474诗中的寒松读来多么像一位空怀抱负却无处施展才华的文人!卢仝《与马异结交诗》用“千岁万岁枯松枝”比喻马异:“半折半残压山谷,盘根蹙节成蛟螭。忽雷霹雳卒风暴雨撼不动,欲动不动千变万化总是鳞皴皮。此奇怪物不可欺。……风姿骨本恰如此。”诗歌中那棵狂风暴雨撼不动、雷霆霹雳击不倒的“千岁万岁枯松枝”便是马异不随流俗、卓然挺立的主体人格的象征。至于孟郊《罪松》中独立不羁、我行我素的松树则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诗歌正话反说:“天令既不从,甚不敬天时。松乃不臣木,青青独何为。”明显是借指责松树来抒写自己坚守正道却不为世俗所容的愤懑之情。
如果说先秦松柏人格象征偏重的是伦理道德的评判,魏晋六朝松柏人格意蕴注重的是风度个性的体现,唐代则兼而有之。唐代松柏意象中既寄托了唐代文士 “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建立不世功业的宏伟抱负心,又再现了个体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和性格的独特魅力。
四、宋代松柏比德的成熟
宋代儒、佛、道三家融合,儒学吸收了佛学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和心性方面的理论,又融合道家注重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内在精神,形成了内外兼修、圆转自如的时代文化精神。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渗透和影响下,宋代松柏比德思想发展成熟,松柏意象融合儒家的操守气节、佛家的超逸精神和道家的洒脱豁达,衍生出新的比德意义。
首先,松柏意象中寄托了文人士大夫对弘毅、刚大的儒者人格的追求。在宋代,松柏格外受到尊崇,其道德象征之义被进一步凸显。种松被视为“种德”,如林景熙《赋双松堂呈薛监簿》曰:“昔贤种松如种德,柯叶馀事根本丰。”有的甚至提升到“正声”“正色”“正性”等极富理学色彩的范畴加以阐释,如范仲淹《谢黄总太博见示文集》中言松桂:“金石有正声,讵将群响随。”李复《后园双松》曰:“坚姿不可回,正色少媚妩。”赵蕃《郊居秋晚五首》其四曰:“松柏有正性,风霜无横侵。”松柏品格中节义、贞刚、操守的一面被大力弘扬,用来比拟松柏的多是像叔齐、伯夷、“三君”“八俊”之类品德高尚的前世圣贤,如李廌《松菊堂赋》曰:“尝见美于仲尼,谓不凋于岁寒。犹称伯夷与叔齐兮,遂与贤人而并传。”[11]1908刘才邵《松》曰:“更与清风同烈烈,便先八俊继三君。”或者是勇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如宋张方平《咏松》诗云:“君子正容色,烈士全节操。”朱熹《跋苏文定公直节堂记》云:“庭中有老柏焉,焚斫之余,生意殆尽,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历变故,而刚毅独立,凛然不衰者。”[12]可以说,松柏身上寄寓了宋人对贞节、刚正的儒者人格的追求。
其二,宋人在松柏“岁寒后凋”的比德传统之外,生发出“青青自若”的精神内涵。先秦儒家着眼于松柏不畏严寒的本性赋予其“岁寒后凋”的比德寓意,用以象征君子临难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宋人在继承这一传统比德的同时,又由松柏四时常青、不与群芳争艳,生发出不随流俗、“青青自若”的含义。如邹浩的《四柏赋》:
其四时也,谢群芳之争艳,憩薰风而暑释。筛蟾光之十分,封雪霜而玉砾。若乃琼花兮一本,芍药兮十畦,蕙兰馥郁乎亭槛,锦绮焜煌乎涂泥。上由刺史,爰逮黔黎,咸择地而置酒,纷踵继以车驰。曾此柏之不顾兮,其青青固自若也。岂以此自少而遂衰?及夫时运遄往,木帝无为。骤雨滂沱以涤荡,狂飙奔腾而摧折。昔蕃鲜兮何在,今寂寞兮空枝,使当年之好事,惨搔首以兴悲。独此柏之不顾兮,其青青固自若也,亦岂以此自多而增奇。呜呼!柏之所以为柏兮,其常德若兹,仆幸得之而深兮,胜老马以为师[13]2628。
既描写了柏树不被狂风骤雨而摧折的可贵,又肯定了其不为热闹繁华所打动的淡泊,所谓的“青青自若”“常德”,既包含凌寒不改的操守气节,又具有超世越俗的内在精神,体现了儒、道合一的理想人格。
其三,宋人在“松柏有心”的传统比德基础上,又发展出“无心”“无情”之义。如张耒《太宁庭柏》曰:“谁能悟斯道,来此契无心。”韩维《和子华见寄》曰:“松柏无心自后凋,此心无物更寥寥。”“无心”也就是“无情”,因为无情,所以能不受外界影响,保持真我。松柏“无心”之说,打破了松柏“有心”的传统寓意,与佛、老“无心合道”“无心才能得道”的理念正相契合。
其四,宋人在松柏栋梁之才的常见比附外,又演绎出不求材用、安分随时的新理念。如蔡襄《古寺偃松》云:“须知才短为天幸,江上婆娑得所宜。”杨时《岩松》云:“臃肿不须逢匠伯,散材终得尽天年。”通过描写怪松因不能为世所用而免于斤斧,表达了不求材用、安于现状的观念,体现出道家全真保素、修身养性的哲学思想对松柏比德的渗透。
其五,宋人在松柏贞刚的比德主流外,又提出清与贞、刚与柔、高与卑应和谐一体的完备人格。如叶适《和答钱广文兰松有刚折之叹》借写松表达了过刚易折的深刻哲理:“兰居地之阴,蔼蔼含华滋。此本不以刚,而为刚者师。松无栋梁具,何用稼冰雪。终风挠长林,常恐浪摧折。”苏籀《灵岩寺偃松》则融合儒、庄二家,提出一种完备的人格:“揉刚为谦屈,至高而听卑。横秋老气逸,轶材那绁羁。高可容冠舆,清甚生泠飔。”高雅而又谦卑,温和而又刚强,傲岸而又清逸,这些原本相反的两极,在松的个性中奇妙地统一起来,达到平衡蕴藉的状态。范仲淹在《君子树》中称赞松:“可以为师,可以为友。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君子树”集“清”“劲”于一身,刚柔互补、相辅相成的理想人格,构成了宋代士大夫人格追求的普遍范式。
总之,宋代松柏比德发展成熟,不仅体现了宋人精神世界的深邃、内省和对道德名教的重视,而且反映出有宋一代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与完善。
五、明清松柏比德的承续
明清易代之际,松柏岁寒愈青的品性成为激励爱国志士舍身取义的原动力。如明遗民方文屡以岁寒不移的松柏为喻,自道怀抱或赞颂他人,如:“不是生来松柏性,谁人耐得此严寒。”(《雪舟》)“竹柏天然翠,风霜耐尔何。”(《响山访梅杓司及令弟昆白次日谈长益至各赋二首》)“不是繁霜后,谁知松柏青。”(《宿陈翼仲斋头》)清初杜濬《古树》则是直接为浙东抗清志士所谱的颂歌:“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松柏尚且有“心”,知感恩义、风霜不移,更何况人呢?
明清文学中有关松柏意象的作品数量众多,虽然比德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提高,但不乏松柏比德的集成、总结之作。如明代的何乔新以松为“益友”,其《友松诗序》云:
观其苍然黛色凛乎不可狎也,则思所以潜消吾暴慢之气;观其霜枝雪干挺乎其不可挠也,则思所以益励乎贞介之操;观其贯四时而不改,越千岁而不衰也,则思所以诚吾恒久之心;仰焉而睇俯焉,而思其有益于吾之进修多矣。松良吾友也,非特世俗之所谓友也[14]。
对松柏比德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岁寒后凋、劲挺有节、坚贞有心、恒久之志,松从形象到本性都给人以道德的启示,令人仰观俯察之际,涵养品德、改进气质。明姚绶《三松记》更借“松”标举文人理想的性格与人生:
养利器于盘错,保贞心于岁寒:众皆靡靡,吾独挺挺;众皆营营,吾独舒舒;众皆竞华敷荣,吾独完贞葆素!不炫材力而材力饶,不求闻达而闻达茂[15]13。
不随流俗、孤贞独守;世人贪竞浮靡、因循享乐之时,独振作警醒;世人追名逐利、奔走钻营之时,独养性怡心;世人炫耀展示之时,独养晦韬光;以身作则,无为而至,最终才名远播、显扬闻达。
总之,松柏比德源远流长,先秦时松柏是有道君子的象征,魏晋六朝时是名士风度节操的体现,唐代被托喻为渴望才用又个性鲜明的文士,宋代是士大夫完美人格的象征……。正直端方的君子一直是松柏人格寓意的主流,也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和其他植物意象君子人格象征,如竹、莲、菊等相较,松柏在体现君子人格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它兼备竹之贞劲、莲之高洁、菊之淡泊。华夏民族精神中的一些重要素质,如重节操、重道德、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安贫乐道、淡泊名利、人格独立等,在松柏意象的人格内涵中都有表现。可以说,松柏的生物特征显著,是文化中阳刚坚贞的经典。研究松柏比德,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1]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