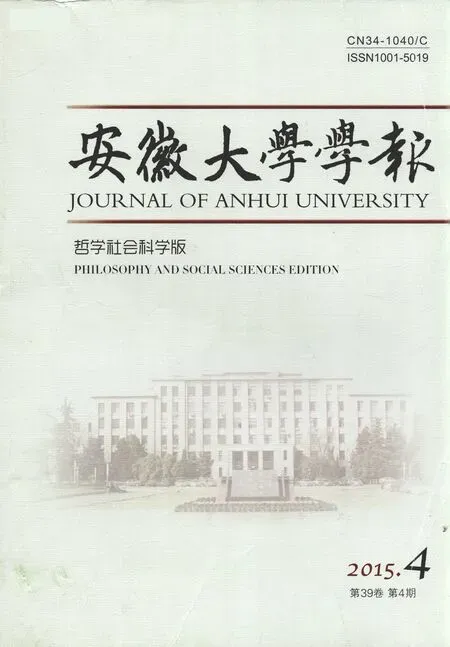近代汉字的字词关系探讨——以“嬿”“鹄”“蚖”三字为例
2015-12-17曾良
曾 良
隶变以后的汉字的隶楷阶段(或称今文字),唐兰先生称为“近代文字”。他认为“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并说道:“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①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页。在漫长的汉字使用过程中,字与词的关系较为复杂,还有不少可以研究的东西。有的字与词之间的对应未被今大型辞书所载录;有一些俗写相混的现象,因字形问题将A词的意义给了B词,从而音随形变。如此等等,复杂多样,值得我们在研究古籍时重视。黄德宽先生在研究汉字发展历史时,也谈到必须注意“汉字使用情况的全面考察”,指出:“汉字发展研究要注意通过动态比较分析,全面掌握某一时代汉字使用总量的变化,并将传承字、新增字、淘汰字的实际情况以及各个字使用的频率列为基本内容。汉字功能的变化调整也是在使用层面展现出来的。这主要表现为字词关系和字际关系的调整变化。同时,不同时代出土文献在文本层面展现的汉字书写现象也反映着汉字使用的状态,如文本的书写特征以及书写原因造成的讹误、类化、重文、合文乃至美饰(增饰笔画、变形体、鸟虫书)等现象,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②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页。这里我们以敦煌文献和其他古籍材料为例,对古籍文献中的某些字词关系作一点探讨。
一、嬿
《敦煌宝藏》第35册斯4325《出曜经》卷一:“时有一男子,将从严驾,随大导师,入海采宝,馀小贾人,以类相从,饮食嬿乐,施诸贫穷沙门婆罗门。”③黄永武:《敦煌宝藏》,第3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1~1986年,第344页。古籍中有宴会、燕娱义写“嬿”字者,今天的字书均不载录这一情况,其实这是必须关注的文字使用现象。《后汉书·皇后纪》论曰:“及至移意爱,析嬿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①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4页。《后汉书·文苑·边让传》:“于是欢嬿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清声发而响激,微音逝而流散。”②范晔:《后汉书》,第2642页。《法苑珠林校注》卷五《六道篇·诸天部·感应缘》:“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义起娶妇之后,分日而嫌,分夕而寝。”③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8页。“嫌”字不好理解。此段文字出自《搜神记》卷一,《搜神记》作“燕”④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页。,可从,谓燕会。《太平广记》卷六一《成公智琼》作“分日而燕”⑤所引《太平广记》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愚谓《法苑珠林》之“嫌”当是“嬿”字之讹,盖俗写“兼”旁或作“”,与“燕”形近致讹。《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双凤奇缘》第四十九回:“一路程而进,早到了雁门关。”⑥《双凤奇缘》,《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8页。古籍中表示宴会、娱燕或写作“嬿”,《大正藏》本《寂志果经》:“某有居跱,某馆某舍某堂怀躯,某堂嬿处,某有宫殿,为精进行,某有堂馆,无精进行。”(1/274/a)⑦《大正新修大藏經》(简称《大正藏》),日本1934年印行。所引《大正藏》本直接标明册数、页码和上下栏,下同。《径山藏》本《莲峰禅师语录》卷十《落花吟》三十首之廿二:“士女休嬿多变态,古今面目掷虚妆。”⑧《嘉兴大藏经》,第38册,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384页。《中华大藏经》本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六《六度集经》“娱嬿”条:“上牛俱反,下一见反。”(59/766/a)⑨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所引本书直接标明册数、页码和上下栏,下同。《大正藏》本《六度集经》卷五:“便命四邻学士儒生耆德云集,娱宴欢乐,并咨众疑靡不欣怿,终日极夜各疲眠寐。”(3/26/b)《碛砂藏》本《六度集经》卷五作“娱燕欢乐”(33/136/b)(10)《碛砂大藏经》,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所引《碛砂藏》本直接标明册数、页码和上下栏,下同。,卷末《音释》云:“娱嬿:上音愚,乐也。下於见反,正作‘醼’。”(33/149/a)说明“嬿”“宴”“醼”异文同义。《中华大藏经》本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一三《佛般泥洹经》“嬿坐”条:“上一见反。”(59/1017/c)《大正藏》本《佛般泥洹经》卷上作:“佛从宴坐起,出阿卫聚,更坐一处。”(1/162/c)又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一四《大迦叶本经》有“嬿坐”条:“上於见反。”(59/1097/c)而《大正藏》本《大迦叶本经》卷上作“宴坐”(14/761/b)。《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一《出曜经》“嬿乐”条:“上於见反,安也,正作‘宴’也。又於典反。”(60/193/b)《碛砂藏》本《出曜经》卷一:“时有一男子,将从严驾,随大导师,入海采宝,余小贾人,以类相从,饮食醼乐,施诸贫穷沙门婆罗门。”(89/134/a)《碛砂藏》本卷末《音释》:“醼,音燕。”(89/135/a)盖古人燕会往往有女乐、狎妓等,故或从女为“嬿”,又因饮酒或作“醼”。《诗经》的“宴尔新昏”,“宴”字或有写“嬿”者,《北史·柳彧传》:“〔唐〕君明忽劬劳之痛,惑嬿尔之亲,冒此苴衰,命彼褕翟。”(11)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23页。“宴尔”与女子有关,故或从女为“嬿”。娱嬿有时即指男女欢娱,如《新唐书·后妃传上》:“中叶以降,时多故矣,外有攻讨之勤,内寡嬿溺之私,群阉朋进,外戚势分,后妃无大善恶,取充职位而已。”宋本《艺文类聚》卷七十九“神”类引晋张敏《神女赋》:“于是寻房中之至嬿,极长夜之欢情。”(12)欧阳询:《宋本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28页。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八:“〔章〕沉共宿嬿接,更相问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吴县吴门,临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13)刘敬叔:《异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0页。“嬿接”谓男女交欢。同前:“甚羞,不及寝嬿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以下我们再举一些“宴”“燕”写“嬿”的例子,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友悌”类引宋颜延之《祖祭弟文》:“永怀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无荣嬿,没望归魂。”①欧阳询:《宋本艺文类聚》,第603页。同前卷五十七“七”类引汉枚乘《七发》:“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嬿服而御,此亦天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②欧阳询:《宋本艺文类聚》,第1545页。《全三国文》卷四十四阮籍《清思赋》:“假淳气之精微兮,幸备嬿以自私。”③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306页。《全三国文》卷四十六阮籍《乐论》:“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也。”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14页。宋俞德邻《佩韦斋集》卷三《次韵龙仁夫种菊》诗之二:“宁复饮我酒,欢饮均嬿私。”明代胡俨《颐庵文选》卷上《约斋记》:“夫妇嬿昵而无别,朋友凌傲以相高。”明王慎中《遵岩集》卷十一《丘中丞夫人六十寿序》:“公间谓予曰:恒言‘学弛于内嬿,仕败于室谪’,予所以得有立而无歉于为人者,有内友之助也。”《明文海》卷二百陈束《寄屠渐山书》:“伏承惠书惓惓,词文藻缋,情致专笃,陈昔时嬿乐之悰,叹数子飘零之迹。”
二、鹄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珠”字九七号《大般涅槃经》卷一:“尔时拘尸那城娑罗树林,其林变白,犹如白鹄。”《大正藏》本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一作“犹如白鹤”(1/369/b)。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五《大般涅槃经》“白鹄白鹤”条:“鹄,胡木反。《玉篇》:似鹅,黄白色。又云黄鹄,形如鹤,色苍黄。详此经文,其林变白,何得类于黄鹄?应为鹤字,何各反。”⑤慧琳:《一切经音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第962页。可见慧琳看到的本子作“白鹄”,而他认为当作“白鹤”,故在条目上特地补出“白鹤”二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人“鹄”“鹤”难辨。《中华大藏经》本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四《大般涅槃经》“白鹄”条:“何各反,正作鸖。又胡沃反,俗用。”(59/679/b)《法苑珠林校注》卷三二《眠梦篇·善性部第三》:“五、有四白鹤飞来向王。”⑥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第1020页。又“五、四白鹤来者,跋耆国王当献金宝,后日日中当至”⑦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第1021页。。《法苑珠林》此两例“鹤”字,据《大正藏》本,原经《杂宝藏经》均作“鹄”(4/490/a);《碛砂藏》本《杂宝藏经》卷七《迦旃延为恶生王解八梦缘》亦均作“鹄”(90/621/a)。按:古籍中“鹄”字或作“鹤”的俗写用,有许多语例可以证明这一点,研读古籍尤宜注意。《大正藏》本《长阿含经》卷二二:“七大国北有七大黑山:一曰裸土,二曰白鹤,三曰守宫,四者仙山,五者高山,六者禅山,七者土山。”(1/147/c)校勘记曰:“鹤”字,宋本、元本、明本作“鹄”。宋本《玉篇·鸟部》:“鹄,胡笃切,黄鹄,仙人所乘。《楚辞》:黄鹄之一举,知山川之纡曲;再举,知天地之圆方。”⑧《宋本玉篇》,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444页。古人对鹄、鹤是一种还是二种动物,看法也不尽相同。宋代罗愿《尔雅翼》卷一三《鹤》:“然《本草》云:鹤有玄、有黄、有白、有苍苍者,今人谓之赤颊玄,则鹤之老者;百六十年则有纯白、纯黑之异。若黄鹤,则古人常言之。古书又多言鹄,鹄即是鹤音之转。后人以鹄名颇著,谓鹤之外别有所谓鹄,故《埤雅》既有鹤,又有鹄。盖古之言鹄不日浴而白,白即鹤也。鹄名哠哠,哠哠,鹤也。以龟龙鸿鹄为寿,寿亦鹤也。故汉昭时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而歌则名《黄鹤》。《神异经》鹤国有海鹄,卫懿公好鹤,齐王使献鹄于楚,亦列国之君皆以为玩。其余诸书,文如‘蕙帐空兮夜鹤怨’,《楚辞》‘黄鹄一举’及田饶说鲁哀公言黄鹄,或为鹤、或为鹄者甚多。以此知鹤之外,无别有所谓鹄也。”清黄生《字诂》“鹄”字条云:“鹄,胡沃切,《说文》云:‘鸿鹄也。’《广韵》云:‘黄鹄。又射鹄。’师古注《相如赋》云:‘水鸟。’鹤,曷各切,《说文》:‘鸟名。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广韵》:‘似鹄,长喙,朱顶。’《诗注》:‘似鹳,善鸣。’据此,则鹄与鹤自是二种。然古人多以鹄字作鹤字用。如高祖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西京杂记》‘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曹洪马名白鹄,晋《拂舞歌》‘高举两手白鹄翔’,阮籍诗‘黄鹄呼子安’,诸鹄字,皆即鹤字。若《广韵》云‘鹤似鹄,长喙,丹顶’,则似谓不长喙丹顶者为鹄。然此鹳也,非鹄也。若师古云‘水鸟’,与古多以鸿鹄并言,则似是鸿雁之类。若《周礼·司裘》‘设其鹄’,注:‘鹄,小鸟,取其难中’则谬。鹄果小鸟,岂得与鸿并称?今人呼鹄为谷,则蒙古韵所转也。”①黄生撰、黄承吉合按:《字诂义府合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页。黄承吉按:“鹄即是鹤,从来以为两种者,泥于字形,昧于字声也。不知鹤、鹄正是一声,非可以字形拘别,承吉《经说》中详明之。”今天的辞书一般都把鹄、鹤以为两种:鹄指天鹅;鹤指头小颈长,嘴长而直,脚细长者。“鹄”字,《汉语大字典》曰:“鸿鹄。又名‘黄鹄’。即天鹅,也叫黄嘴天鹅。形状像鹅而形体较大,颈很长,嘴尖黑色,基部黄色。羽毛纯白或黑色,有光泽。飞行高而迅速。群栖于湖泊沼泽地带。《六书故·动物三》:‘鹄,辽人谓之天鹅。’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鸟部》:‘鹄,黄鹄也。凡经史言鸿鹄者,皆谓黄鹄也。或单言鹄,或单言鸿。’”《汉语大词典》:“通称天鹅。似雁而大,颈长,飞翔甚高,羽毛洁白。亦有黄、红者。”《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天鹅”。今天的字书均解释“鹄”为天鹅,属鹅雁类。鹅雁类与鹤类有一个典型区别,鹅雁脚有蹼;鹤的脚细长,无蹼。今天的字书都无视“鹄”字作“鹤”用的现象。“鹄”作“鹤”字用的更多语例,可参吴玉搢《别雅》卷五“鹄鹤也”条。即使“鸿鹄”并言者,也间或有认为“鹄”正字当作“鹤”,如《大正藏》本《佛说如来智印经》:“琴瑟铜钹箫笛声,击鼓鸣贝众妙音,紧陀罗声迦陵伽,哀鸾鸿鹄拘翅罗,鞞节箜篌俱畅发,不及如来一妙音。”(15/471/c)校勘记曰:“鹄”字,宋本、元本、明本、宫本作“鹤”。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六《佛说如来智印经》“鸿鹄”条:“户各反,正作鸖也。又户沃反。”(59/748/c)《大正藏》本《佛本行集经》卷二五:“水中鹅雁鸿鹄鸳鸯,充溢诸池。”(3/767/c)例中“鹅雁”与“鸿鹄”并举出现,不应该是同一种类,否则语义重沓。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一四《佛本行集经》“鸿鹄”条:“上音洪,下又作鸖,户各反。”(59/1081/b)《大正藏》本《起世经》卷七:“一切众生,受卵生者,所谓鹅雁鸿鹤、鸡鸭孔雀、鹦鹉鸜鹆、鸠鸽燕雀、雉鹊乌等,及余种种杂类众生,从卵生者,以彼从卵而得身故,一切皆以触为其食。”(1/345/c)《碛砂藏》本《大庄严经论》卷一三:“额广白毫相,今以尽消灭,如鹄在花上,为火所烧灭。”(51/176/b)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一一《大庄严论》“如鹄”条:“户沃反,又音鹤,俗。”(59/963/b)《大正藏》本《阿毘达磨藏显宗论》卷一二:“人卵生者,谓如世罗、邬波世罗,生从鹄卵。”(29/883/c)“鹄卵”即鹤卵,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〇《阿毘达磨显宗论》“鹄卵”条:“上音鹤,又胡沃反。”(60/147/a)《大正藏》本《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一二〇:“昔于此洲有商人,入海得一雌鹤,形色伟丽,奇而悦之。遂生二卵,于后卵开,出二童子,端正聪慧。年长出家,皆得阿罗汉果。小者名邬波世罗,大者名世罗。”(27/626/c)如上例子,户沃反是“鹄”字读音,户各反是“鹤”字读音,可见社会上对“鹄”“鹤”二者很难分辨。
今辞书“鹄”字只释为天鹅是无法解决古籍的具体实际的。明《正统道藏》本《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载者,终不集于树上也。”②葛洪:《抱朴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第15页。《四库全书》本《抱朴子》、四库本《山堂肆考》卷二百十一引《抱朴子》等均作“千岁之鹤”,而《太平御览》卷九百十六、《记纂渊海》卷九十七引《抱朴子》作“千岁之鹄”。我们不能说《抱朴子》写“千岁之鹄”时是天鹅,写“千岁之鹤”时是鹤。又如《西京杂记》卷一:“始元元年,黄鹄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衣肃兮行跄跄……’”《白孔六帖》卷九十五、《太平御览》卷五九二与卷九一六、《广博物志》卷四四、《古文苑》均作“黄鹄”,《初学记》卷三十《鹤第二》引《西京杂记》作“黄鹤”③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7页。。在这样的具体文献异文中,“黄鹄”“黄鹤”显然指的是同一鸟类。关于《黄鹄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案:“鹄、鹤,古率通用,故此鹄或作鹤。”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8页。安徽大学黄继省博士帮助收集了一些语例,谨致谢意。唐人崔颢《黄鹤楼》诗:“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的“黄鹤”也与“黄鹄”同义,故《别雅》云:“卫懿公事亦以鹄为鹤,今武昌黄鹤楼下曰黄鹄矶,亦一证也。”
《玉台新咏》卷一古乐府诗《双白鹄》:“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②徐陵:《玉台新咏》,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民国24年刊本,第9页。《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五《铜官渚守风》、《杜诗详注》卷二十二引古乐府并作“飞来双白鹤”。《文苑英华》卷二百六梁孝元帝诗题《飞来双白鹤》,原注:“一作‘鹄’。《庄子》鹄、鹤通用。”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八:“《石镇罔两赋》:‘虽凫鹄而异禀,将断续而则悲。’鹄,《庄子》作鹤。郑愔《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贵主悲黄鹤。’‘鹤’,《汉书》作‘鹄’。按《玉篇》:鹤,何各切;鹄,胡笃切。似是二物。然《庄子》‘鹄不日浴而白’,陆徳明音义直云:‘鹄,又作鹤,并胡洛切。’则是一物。又《艺文类聚·鹤门》亦有鹄事,乐府《飞来双白鹤》一作‘白鹄’,则鹄、鹤通用,不可轻改。”清毛奇龄《续诗传鸟名卷》卷三云:“鹤与鹄通字。《国策》魏文侯使献鹄于齐,一作‘献鹤’;汉时黄鹄下太液池,一作‘黄鹤’;故《别鹤操》亦名《别鹄操》,乐府《飞来双白鹤》亦称《双白鹄》,甚至刘孝标《辨命论》直称‘龟鹄千秋’,曹《捣衣》诗亦云:‘开缊舒龟鹄。’因有疑此鹤字是鹄字,以为鹙鹤不伦,惟鸿鹄鹙鸧皆水鸟一类,不知鹤亦水鸟,生淮之海州。《淮南子》‘鸿鹄鸧鹤’,《吴都赋》‘鹴鹄鶄鹤’,未尝不并称也。鹤、鹄本两鸟,但古字相通耳。今作字书者,必彼此交讦,谓鹤即是鹄,谓鹤必不是鹄,皆拘墟眇通之言。”
三、虺、蚖
斯3330《毛诗故训传》之《斯干》:“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又:“维虺维蛇,女子之祥。”③《英藏敦煌文献》,第5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页。作为毒蛇的“虺”字,《说文》作“虫”。《说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虺”字因作“”,往往或讹作“蚖”。《法苑珠林》卷三四《摄念篇·引证部第二》引《杂阿含经》:“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四蚖蛇,凶恶毒炽,盛一箧中。”④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第1078页。此“蚖蛇”即虺蛇,非有蚖和蛇两种。后文有“尔时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驱驰而走”之语,可知“蚖蛇”即毒蛇。《大正藏》本《杂阿含经》卷四三作“蚖”(2/313/b),而校勘记曰:宋本、元本、明本、圣本均作“虺”。《说文》:“蚖,荣蚖,它医,以注鸣者。”蚖是属于蜥蜴类,无毒。《说文》另有“虺”字,《说文》:“虺,虺以注鸣。《诗》曰:胡为虺蜥。”《说文》的这个“虺”也是属于蜥蜴类,跟毒蛇无关,这里不论。以下所说的“虺”均是指虺蝮的意思。翻检今诸大型辞书,“蚖”字有毒蛇的义项。我们认为“蚖”字的此义来自虺蛇的“”,盖古籍中“”“蚖”讹混所致。《尔雅·释鱼》:“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郭璞注:“身广三寸,头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种蛇,名为蝮、虺。”邢昺疏:“案: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孙炎曰:江淮以南谓虺为蝮,广三寸,头如拇指,有牙最毒。”可见,虺才是毒蛇。
《大正藏》本《佛本行经》卷五:“吾何为久与,此蛇虺箧俱?强曳无返复,仇怨对已尽。”(4/98/a)《中华大藏经》本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十一《佛本行赞》“箧”条:“上许鬼反,下苦协反。”(60/189/c)可洪《音义》的“虺”字已经从“元”了。《卍新续藏》本《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略疏》卷下:“蝮,蚖蛇;蝎,蝎虎。此二若触则螫。”(23/792/a)用“蚖蛇”解释“蝮”,“蚖”字显然是“虺”。
《大正藏》本《诸经要集》卷一二《欲盖部·五欲缘第二》:“蚖蛇含毒,犹可手捉;女情惑人,是不可触。”“蚖蛇”当作“虺蛇”。可洪《音义》卷二十三《诸经要集》“虵”条:“上许鬼反,正作虺。或作蚖,五官反,毒虵也。又五骨反,蛤蟹也,误。”(60/302/a)“”即“虺”的俗字。“兀”俗写作“”,或许也是易讹为“元”的原因之一。《地道经》:“是身为譬如地孔,虺止会。”可洪《音义》卷二一《地道经》“虺止”条:“上许鬼反,虵也,毒虵也。”(60/211/a)故训“虺,毒蛇也”。当“”讹成“蚖”之后,便让“蚖”字有了毒蛇的义项,于是被后世字书、韵书载录。《说文》《玉篇》中“蚖”字均无毒蛇的意思,说明“蚖”字最初没有此义。在《广韵·桓韵》《集韵·桓韵》有“蚖,毒蛇”的释义;《类篇》“蚖”字有“蚖,毒蛇”的义项。《康熙字典》“蚖”字条:“又《韵会》吾官切,音刓,《广韵》:毒蛇。《本草》:蚖与蝮同类,即虺也。”《康熙字典》应该是认为“蚖”的毒蛇义即是“虺”。我们来分析一下字词关系。在古文字阶段大概是用“虫”字表示虺蛇义,所以到《说文》中一直还是如此;而在《说文》中“蚖”“虺”二字都是表示蜥蜴类,大约古文字“元”“兀”,多一横少一横没有什么区别,参《战国古文字典》“元”字条。何琳仪先生云:“故兀、元为一字分化(均属疑纽)。”①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15页。又如“軏”或作“”。从音韵上说,“蚖”“虺”又常阴阳对转。《说文》:“元,始也,从一,兀声。”段注:“徐氏锴云:‘不当有声字。’以髡从兀声、从元声例之,徐说非,古音元、兀相为平入也。”表示虺蛇义的“虫”字为什么会写“虺”字?我估计是因为“虫”“虺”音同,便借用“虺”表示毒蛇义,如《诗经》的“维虺维蛇”、《尔雅》的“蝮虺”,即其例。在隶楷阶段“元”“兀”已显示文字的区别性,不再是多一横少一横没有意义区别了,故一般用“蚖”字表示蜥蜴类,“虺”表示毒蛇,字形的使用上有了分工。但由于俗写“”“蚖”往往讹混,故将“(虫)”的毒蛇义给了“蚖”字,并音随形变。《大正藏》后汉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卷中:“蚖蛇含毒诚可畏,见彼行者毒疾除。”(13/913/a)《大正藏》后汉天竺三藏支曜译《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坐蛇蚖之地,心念舍远之径。”(15/453/b)
四、结 语
中国古籍汗牛充栋,研究汉语史一定要与古籍打交道,这样研究汉语的历史就自然回避不了文字方面的问题。从汉语史的角度看,必须注意不同时期的汉字与词的对应关系或许会有些调整变化。“嬿”字在中古和近代汉语时期的古籍中,常作“宴”的异体使用,而现代汉语中“嬿”字已无此义项。大量的语例证明,古籍中“鹄”“鹤”往往混用,以“鹄”字作“鹤”用为多,今大型辞书没有反映古籍的这一使用情况,显然是不合适的。今辞书“鹄”字只释为“天鹅”是无法解决古籍的具体实际的。从古代《说文》等字书看来,“蚖”字最初无毒蛇义,因“虫”(许鬼反)或作“虺”“”,而古文字中“兀”“元”旁上一横的有无,意义无别,这种书写习惯,造成“”字或俗写成“蚖”,这样后世“蚖”字既表示蜥蜴义,又表示毒蛇义,而且音随形变。我们从这一例子也可看出文字对词音、词义的影响。
责任编校:徐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