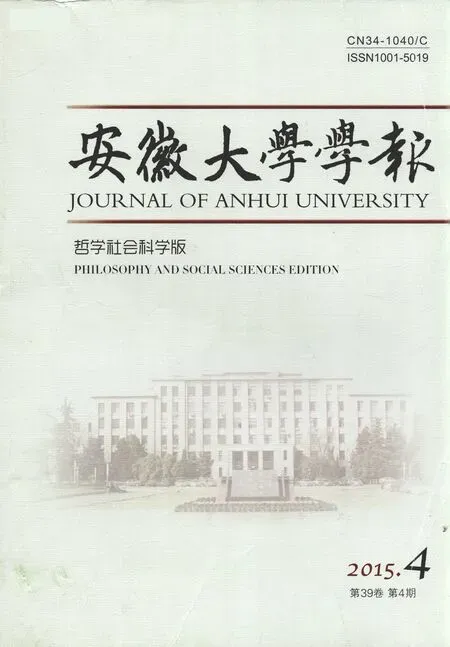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与肺病的互动关联
2015-12-17范蕊
范 蕊
一、肺结核:一种疾病的浪漫化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瘟疫便与人类如影随形,对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瘟疫的态度则反映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在很多古老文明中,人们把流行病视为众神随意的行为,无法解释,不可理喻。在古希腊,疾病被视为因违背神意而遭受的惩罚,《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冒犯了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降下瘟疫,几乎毁灭了远征特洛伊的希腊军队。在基督教文化里,疾病乃上帝惩罚的说法更是深入人心,中世纪流行的鼠疫、霍乱等被解释为不义或对上帝不虔诚的结果,一些患传染病的病人因此被歧视、隔离,甚至被遗弃,任其自生自灭。
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的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类似之前鼠疫那样令人恐惧的急性瘟疫似乎已销声匿迹,但有一类被称为“白色瘟疫”的慢性传染病——肺结核却成为主宰人类生死的“新死神”。结核病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据考古学发现,结核病的历史几乎同人类历史一样悠长,早在六千年前的意大利和埃及,人们就从古人的遗骸中寻得结核病的证据。18世纪以前,欧洲并没有结核病的大流行,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手工业生产时期,生产活动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结核病主要在家庭范围内流行,比如法国王室路易十三就死于“奔马痨”(急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他的王后和儿子路易十四也有,以至于当时人们认为结核病是一种家族遗传病。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许多人口密集的城市。许多工厂拥挤肮脏、卫生条件很差,生活困顿、饮食不良的人群成了结核病的温床,加上防疫知识的匮乏,导致结核病在社会上的大流行。
结核病在欧洲的流行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约四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被夺走,据统计,19世纪初德国汉堡结核病死亡率高达700/10万(即每10万人口1年有700人因结核病死亡),英国1799年则高达每3.8个死亡者中就有1人死于结核病。因此,结核病被称为“巨大白色的鼠疫”。与其他急性传染病相比,肺结核的死亡并不显得可怕,它会缓慢无情地消磨一个人的生命,患者被看作一个悲剧角色,他们一边看着生命流逝,一边满怀希望谋划永不可见的未来。
结核病患者一开始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要么是感性丰富的作家、艺术家,要么是贵族。从医学角度讲,作为当时社会的特殊群体,艺术家和贵族热衷交际应酬,生活放荡,天质纤弱,身体抵抗力差,容易罹患疾病。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横扫欧洲,贵族阶层丧失了政治权力,而仅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于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和民众而言,苍白、消瘦的肺结核患者成为贵族气质的新面孔。肺结核症状所表现出的正是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人们从中找到了审美价值,把肺结核患者所具有的特质,看作是令人羡慕的气质,健康则成了野蛮低等的象征。虽然贵族阶层的政治特权和经济权利被废黜,但他们在文化上仍然保留着影响力——浪漫主义成为他们的美学理想和伦理寄托。通过歌颂逐渐消逝的田园牧歌生活,宁静的大自然,苍白消瘦的身体,持续的病痛,缓慢的死亡……贵族从中找到了象征物和存在感,新兴资产阶级则全盘接受了这一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痛。
疾病与天才的关联现象自古皆有。若把人看作一个充满能量的整体系统,身体和精神能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此消彼长的对应关系。肉体能量的消耗和削弱,往往意味着精神能量的冲动和高扬,相反亦然。所以,当肉体衰弱时,往往是内心天赋激发的时候。肺结核给了病人最可贵的东西——自由,疾病将人从日常碎屑中解放出来,去思考自然、艺术、上帝和人生的本质问题,进入灵性生活的境界。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结核病和艺术家几乎可以画等号。一些艺术家也以肺结核的病态美为时髦。拜伦曾经对朋友说自己渴望死于结核病,“夫人们都会说:‘瞧那个可怜的拜伦,垂死之时也是那么的好看啊!’”①转引自余凤高《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48页。法国文艺批评家,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说:“身为一个抒情诗人,我难以接受任何体重超过四十五公斤的人”②[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41页。,可见当时文艺界对病态美的追求。在19世纪的法国,肺结核还与反传统的艺术家与作家群体——“波西米亚人”联系起来,成为这一阶层艺术气质的象征——不受传统的束缚、具有神秘气质和病态之美。波西米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诗人亨利·穆杰(Henry Murger,1822—1861)同时也是一名肺结核患者,他的代表作品《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情景》后来被意大利的作家普契尼(G.Puccini,1858—1924)改编为歌剧,使“波西米亚气质”深入人心。
结核病的流行给社会带来广泛影响,甚至反映在服饰和化妆上:男性为了隐藏颈部的肿胀——结核性淋巴腺炎而穿起高领衣服;女性则以柔弱、脸色粉白为美。由于不清楚发病原因,呼吸清新的空气、接受充足的阳光、保持丰富的营养,一度成为结核病治疗的主要措施。因此阳光明媚、风景优美的意大利地中海地区成为肺结核病人最向往的治疗场所。远离城市的不真实的氛围、专人的护理、良好的饮食、周围人的关注同情令病人容易产生幻觉,觉得疾病并不那么可怕,甚至带有超凡脱俗的意味。诗人和艺术家们对肺结核进行了浪漫化的描绘,淑女们被描写为纤弱、无声气的,极容易昏倒且有阵发性咳嗽,绅士则面色苍白消瘦,神情冷峻,结核病进入浪漫化时期。
西方文学的每个特定时期都有某种突出的疾病,文艺复兴时期是黑死病和鼠疫霍乱,18世纪文学喜爱热病和伤寒,19世纪则是肺结核的浪漫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角都是患病的美丽女子和英俊男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持续的咳嗽、沉重的喘息、苍白的脸色等。受到感染的文艺家陶醉于死亡逼近时的激情里,滋生出肺结核时代浪漫主义美学观及其一系列审美艺术符号:忧郁、悲观、纵欲,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升华。对于肺结核的浪漫化隐喻已成为影响人们审美和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从文化批评角度入手,探究西方社会疾病的象征化历史和精神隐喻意义,由此开拓了疾病文化批评的新领域,人们开始注意到隐蔽在社会意识背后的文化决定因素。国内也有学者关注肺结核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如余凤高的《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一书,对肺结核流行带来的复杂文化现象,尤其是对患病作家创作的影响,以及肺结核的研究和防治历史等进行了论述。余杰在《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一文中分析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肺结核对作家(鲁迅和加缪)创作的影响,有其独到之处③余杰:《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1期。。还有研究者试图通过《茶花女》《红楼梦》《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几部中外小说中患病主人公的塑造来阐述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复杂而又矛盾的浪漫化隐喻意义④马小麒:《隐喻和阐释——文学作品中的肺结核功能探微》,《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结核病并非与浪漫主义直接相联,更不是浪漫主义产生的原因,相反是浪漫主义作家及创作将肺结核象征化和隐喻化。苏珊·桑塔格、余凤高等学者主要以小说等为分析文本进行社会文化批判,但他们忽视了文学本体分析,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主要领域——诗歌,其实诗歌与肺结核浪漫化的互动关系更为密切,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在肺结核向浪漫化社会隐喻的转变过程起了重要的作用。诗歌作为西方文学经典形式,是最为正统高雅的贵族文学,最为公众所接受,进而影响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领域,浪漫主义文学理念与诗歌的体裁形式具有同构意义,肺结核与浪漫主义两种原本互不相干的事物被联系起来,诗歌也是重要的媒介。正是诗人、诗歌、公众与肺结核间的关联互动,将肺结核这一19世纪的“世纪之病”推向浪漫化的审美高潮。此外,将诗歌放在19世纪肺结核大流行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文本解读,使我们可以从微观的层次进一步了解疾病与文学的深度关联。
浪漫主义首先来自个人对生命的感悟,注重以强烈的情感作为美学经验的源泉,强调如不安、忧郁、伤感等情绪,以及人在遭遇到大自然的壮丽时表现出的崇高感与敬畏感。浪漫主义作家的此种精神内向性与疾病的存在启示效应具有同质性。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将痛苦视为诗歌的源泉,他认为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损失看成是一种无限的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的力量①[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06页。。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也从同样的角度阐释了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美丽的无情女子,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②[英]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年,第23页。
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将生命融入写作,个体生命体验在诗歌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③[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32页。。肺结核的主要症候是发烧,肺结核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④[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32、33页。。创作是对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消耗,一个情感丰富、执着的诗人如果患上结核病,他的生命就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在这两种极端力量的煎熬下,诗人的情感不受遏制地迸发出来,浪漫主义诗歌尤其强调情感,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在《〈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中就认为好的诗歌应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充沛的情感与关于肺结核的想象之间产生了互文性,诗人似乎成为肺结核最适合感染的人,诗歌也最能表现出肺结核的各种浪漫化意象。对于因患肺结核而早逝的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和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来说,肺结核影响甚至决定了其作品的风格。
二、诺瓦利斯:死亡与天国之爱
诺瓦利斯这样总结他思想的落脚点:“我总是在回家的路上,寻找我父亲的老宅。”⑤[英]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06页。这句充满象征意味诗句,蕴含了对那些关于异乡、陌生之地,关于死亡和寓言的不懈追寻,这是寻找无限的渴望,是自我与上帝合一的幻想。诺瓦利斯通过歌颂“黑夜”与“死亡”去感悟生命,表达对生的执着和死的救赎。
诺瓦利斯自幼体弱:“他的前额几乎是透明的,棕色眼睛放射着一种异样的光彩。在他生前最后三年间,就可以看出他是注定要短命的。”⑥[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刘半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可能早在1798年初夏,诺瓦利斯就被诊断出肺结核,随后他的健康状况一再恶化,勉强拖至1801年3月25日,留下未完成的《海因里希·封·奥弗特丁根》的残稿,离开了人世。
在诺瓦利斯短暂的生命及创作中,未婚妻索菲占重要地位,不幸的是两人订婚不久,十五岁的索菲就因肺结核去世。如同贝雅特丽丝之于但丁,索菲也是诺瓦利斯诗歌中的伟大典范与创作灵感之源,甚至成为沟通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中介者。诺瓦利斯的诗歌主要创作于索菲去世到1800年夏天他自己突发致命的肺结核这三四年间。索菲的早夭使他仿佛觉得一切都是“死亡的、荒凉的、腐烂的、僵滞的”,他“希望上帝把自己的余生缩短一些,以便早日与爱人在天堂相聚”⑦[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林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疾病和死亡占据了诗人生活的主导地位,它启示诺瓦利斯的是,死意味着有限的毁灭,人类似乎注定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饱受挫折与无意义的折磨。在《花粉》中他写道:“我们到处寻找绝对物,却始终只找到常物。”⑧[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173页。这是诗人纠结一生的矛盾:对无限的渴慕与追寻,以及他所遭遇的事物的有限和短暂。“爱的短暂”与“死的永恒”似乎是浪漫主义诗人宿命的主题,法国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与诺瓦利斯有同样境遇,他在布尔热湖疗养时,爱上少女朱莉·夏尔,可她不久就因肺结核发作而死去,拉马丁无比悲痛,故地重游,写下了怀念恋人的著名诗歌《湖》。在这首诗里他回忆了往昔爱情的美好,感叹伊人不在,悲愤地诘问:“永恒、虚无、往昔——黑洞洞的深渊!/你们吞没光阴,派作什么用场?/说呀:你们夺走我们迷醉缱绻,/何时能够归还!”①引自郑克鲁译《湖》,见郑克鲁:《心灵真诚的叹息——拉马丁的爱情诗〈湖〉》,《名作欣赏》1989年。肺结核的死亡在诗人的爱情悲剧里成为关键,短暂的青春,溘然地死亡,永恒地回忆,爱成全了生命的浪漫,而死却升华了浪漫。
诺瓦利斯写了大量关于死亡、黑夜和爱的诗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诗人像诺瓦利斯一样,以如此多变的形式歌颂这些一以贯之的主题。在他的诗歌里,弥漫着彻底的悲伤和绝望、孤独和失落。诺瓦利斯深刻理解疾病对人的意义:疾病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促使人们反思的动力和内容,是人们进行反思和活动的最有趣的刺激和材料,他相信从疾病中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②[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335页。——他甚至觉得疾病比健康更好,病人可以感知自己的身体,而健康人并不关心它。在他看来,疾病乃是最高的、唯一真实的生活③[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171页。。诺瓦利斯将痛苦视为快乐的根据:人若是开始喜爱疾病和痛苦,这时他的困苦中就会有最刺激的快感——最高的、肯定的快感会穿透他全身——痛苦愈深,其中隐藏的快感层次愈高④[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349页。。肺结核发病时的感觉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生命的极端体验,没有患病的人是无法体会和言说的,诺瓦利斯将痛苦与快感对立统一,也是他哲学思想的体现,对疾病的迷恋显示出诺瓦利斯心理的超常态,没有一个作家能对疾病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因此海涅说:“评判他们的著作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诺瓦利斯诗中的玫瑰光彩不是健康的,而是患肺病的颜色……”⑤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编:《欧洲文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3页。通过与亲人间相似的切肤之痛的疾病,诺瓦利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痛苦”,而且也是“爱和上帝”。痛苦让他思考疾病与人、人与上帝的关系;通过自己持续不断的病痛和早逝的情人,他进入一个充满和谐与爱的不可见的领域,那就是宗教。
在著名诗篇《夜颂》第一章,他热烈拥抱黑夜:天堂般的夜笼罩一切尘世之物,在神圣、隐秘、难以名状的夜里。诗人回忆起未婚妻索菲以及那些青春的心愿和童年的梦幻,短暂的欢乐如同白昼转瞬即逝,只有黑夜才是永恒的……⑥[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130页。在诺瓦利斯看来,“夜”是一个神秘的精神象征,它指向两层含义:夜指向质朴美好的远古,其实质是本真、虔诚;夜引入死亡,实际上是引入耶稣,其奥秘是爱和奉献⑦林克:《释〈夜颂〉之夜》,《外国文学》2000年第4期。。夜是永恒的,黑夜意味着光明,死亡意味着重生。在第三章,诗人深情悼念亡妻,在凋敝的坟冢旁苦苦思念爱人,期待自己死亡之后与爱人的灵魂相遇,而这只有在梦幻般洁净的天国才可以实现。诺瓦利斯将人间之爱延伸到宗教之爱,耶稣为世人背负十字架踏上死亡之路,为的是最真挚、最深沉的爱。在《夜颂》第六章,他表达自己死亡的愿望:“沉坠吧,向着甜美的新妇,/向着爱人耶稣-深情的恋人,/忧伤的信徒正安然隐入夜幕。/一个梦解开我们的镣铐,让我们沉入天父的怀抱。”⑧[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153页。诺瓦利斯将结核病的苦难和面对死亡的战栗引入宗教,进入天国的救赎。疾病让他得到一把钥匙,打开通往灵魂自由之门。疾病也连通了夜晚、爱人与天国,他把死亡与人间的爱同上帝之爱结合,这也是一个面临死亡的肺病患者的救赎之道。斯太尔夫人(Madame de Stael)分析德国诗人的这种超然的宗教倾向,她认为德国日耳曼民族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个分散的小共同体在自然的压迫下极为渺小,为寻找灵感,北方的德国诗人不得不转向内心,或仰望高山或仰望上帝,北方文学比较内向悲观,并在本质上有宗教意味⑨德·斯太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丁世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页,第44页,第200页。。但是诺瓦利斯的宗教不是社会宗教而是个人拯救的宗教。
诺瓦利斯短暂的生命如同“蓝花”一样神秘绽放又迅速凋谢。花乃是人类的精神秘密之象征(10)[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311页。,花的神秘和美如同宗教一样成为连接人与神的媒介,直达人的生存本质(11)[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165页。。在《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蓝花”进入主人公的梦境,诗人领悟到人类内心里的神性乃是一切自由和爱的本质,由此找到了自己存在之根。“蓝花”是一个神秘的象征,它寓含了一个身体日渐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它象征着心灵完全的满足,并最终演绎为德国浪漫派的图腾,这似乎也是浪漫主义的精髓:理性的追寻,非理性的狂热,灵性的超越,不是为了遗弃世界,而是更加热爱存在,最终在和谐统一中达到至高境界。
三、济慈:爱之永恒救赎
济慈的诗歌被誉为英国浪漫主义最为芬芳的花朵,他在26岁离世,通过他,浪漫主义与肺结核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雪莱写了长诗《阿童尼》献给这位因肺结核而早逝的年轻诗人,他在诗歌中表达了最深切的惋惜和哀悼——“他不会再醒了,哦,永不会再醒!昏暗的灵堂展开白色死亡的阴影,无形的腐败埋伏在门口,静候着,跟踪他前往她阴暗居处的最后途程。”①[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式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济慈命运多舛,15岁时母亲死于肺病,使得济慈较早思考生死问题,写于1814年的短诗《死》中,年轻的诗人将死比作睡眠,视为解脱。济慈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生命的脆弱,美好事物的易逝,与他敏感的心产生共鸣。对于自己的命运,他似乎也有某种预感,在1818年初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恐惧,我可能就要停止呼吸,/而我还没录下我的丰富的思想,/还没能像谷仓那样,使稿本山积,/在文字当中把成熟的谷粒收藏;……我自觉不久于人世,/将不再可能点铁成金地描绘那云块的异彩。”②[英]约翰·济慈:《济慈诗选》,屠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在当时的医学观念里,被压抑的情感是导致肺结核的重要原因,而火热的激情引发了肺结核的发作,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希望则是无望的希望。济慈罹患结核病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观念。
1818年秋,《恩狄弥翁》发表后,受到英国文学批评界的尖刻批评,这对济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他的早夭。1818年夏天,济慈旅行途中得知弟弟托马斯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他即刻赶回家悉心照顾,但托马斯最终还是死了。而他在照顾弟弟时也不幸受到感染。之后病情迅速恶化,日益加重。病入膏肓的济慈暂时放弃了其他企求,只是渴望能得到爱的安抚,他抛弃矜持和顾忌,追求早已倾心的邻家女孩芳妮。他在《致芳妮》中向心上人表达了自己对爱的渴求,他热切需要对方的爱和真情,不是那种只是挑逗而不与实惠的爱情③[英]约翰·济慈:《济慈诗选》,第125页。。接下来的几年中,情感、疾病与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济慈,在疾病的痛苦和爱情甜蜜的双重煎熬下,他写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包括《圣艾格尼丝之夜》《夜莺颂》《致秋天》等名作,表现出诗人对自然、美、爱情的强烈感受和热爱,赢得巨大声誉。
《夜莺颂》是济慈最为出色的抒情诗作,集中体现了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特色。济慈当时正跟芳妮热恋,想到自己的身体和经济状况,不胜烦恼,他想逃避现实,像夜莺一样飞走。诗人写道:“我要痛饮呵,再悄悄离开这世界,/同你一起隐入那幽深的林木;……忘掉这里的疲倦,热病,烦躁,/这里,人们对坐着互相听呻吟,/瘫痪病颤动着几根灰白发丝;/青春渐渐地苍白,瘦削,死亡……”④[英]约翰·济慈:《济慈诗选》,第11页。在幽暗的树林中,病痛引起的低烧使诗人感觉疲倦、烦躁,犹如痛饮后的麻醉昏沉,在死亡的威胁下,青春与年老、欢唱与呻吟再也难以区分。贫困的压力、婚姻的渺茫、疾病的折磨、爱情的痛苦,一切都使他苦恼不堪,他希望忘掉现实的苦难而不可得。他漫步林间,夜色温柔,花儿芬芳……如此良辰美景,诗人却笼罩在无限哀婉的氛围中,他预见到死亡即将到来,生命如同花儿即将凋零,但年轻的躯体即使死去,也会如夜莺一般美丽。此刻,夜莺的歌声婉转如同安魂曲,携着诗人飞向永恒宁静的安息——“堕入了死神安谧的爱情”,“无上幸福的停止呼吸”⑤[英]约翰·济慈:《济慈诗选》,第24页。,诗人希望在这样美的时刻死去,“趁这午夜,安详地向人世告别”,青春、美和爱将因此化为永恒,“你永远唱着,我已经失去听觉——你唱安魂歌,我已经变成一堆土”⑥[英]约翰·济慈:《济慈诗选》,第24页。。同样是面对死亡,济慈并没有如诺瓦利斯般遁入宗教,他将世间的美好和爱升华,凭借人的感官与大自然联通,在令人沉醉的花香鸟啼和似真似幻的现世中获得幸福和欢乐,到达至善至美,这是济慈的艺术信仰。
济慈的爱情叙事诗的主人公大都是面色苍白的病人,他们的爱情皆以死亡而终,死神终结了爱也成就了爱。在《冷酷的妖女》中,他把自己比喻为受到仙女诱惑的骑士,骑士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额角白如百合,渗出热汗像颗颗露珠(这是肺结核晚期的典型症状),仙女的美俘获了他,骑士为爱所引诱、迷惑。诗中充满了隐喻,仙女神秘的爱是危险的死亡诱惑,骑士最终被遗弃在凄冷的荒野,噩梦中的幽灵揭示了济慈内心对死亡的担忧恐惧。《伊萨贝拉》的主人公伊萨贝拉的情人罗伦佐也一脸病容,“额头苍白、清瘦”。罗伦佐被谋杀后化为幽魂前来诉衷肠,伊萨贝拉找到坟墓,割下爱人的头颅,埋入花盆日夜用泪水浇灌,死亡的爱情之花怒放,她枯萎憔悴地死去。济慈笔下,爱可超越生死,死并不可怕,没有爱的人生才是最凄惨的。在《拉米亚》中,济慈重新塑造了女妖拉米亚的形象,使之成为美丽、聪慧的仙女,勇于追求爱情并甘心为之放弃永生之神的身份。男主角里修斯沉溺在爱的幻觉中不能自拔,宁愿在幻觉和欢乐中死去。在济慈看来,所有的爱情都建立在美的幻象上,若没有幻想,爱难以为继。《圣尼亚节前夕》中的波菲罗“像一尊雕像,苍白,忧悒,无言”,他的爱情也难以实现,济慈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对爱情的忧虑,理想的爱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美好与丑恶如此接近,甚至美是那样脆弱,人们必须冲破重重阻隔来追求它。全诗结尾,梅德琳和波菲罗奔跑着冲进漫天的风雪,未来一片茫然而黯淡,正是济慈当时心境充满幻灭感的展现。
与济慈笔下爱的悲苦和幻灭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勃朗宁夫人爱的欢乐和重生。伊丽莎白·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的爱情诗歌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的珍品”,她在少女时代即患肺结核,后因咯血和伤病而常年卧床不起,人生黯淡。罗伯特倾慕她的才华,两人冲破阻碍,结为伉俪,爱的奇迹使伊丽莎白走下卧榻,身体逐渐康复。为了疗养,勃朗宁夫妇婚后迁居到意大利,随即发表了记录两人爱情的组诗《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最美的爱情商籁体诗(Sonnet),在组诗的第一首序曲,勃朗宁夫人表达了爱的拯救和重生:“……紧接着,我觉察(我哭了),/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而且一把揪住了我长发,往后拉,/还听得一声吆喝(我只是在挣扎):/‘这回是谁逮住你?猜!’‘死,’我答话。/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①《勃朗宁夫妇爱情诗选》,方平、飞白、汪晴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0页。爱的纯真美好使一个濒死的肺结核病人重获生机。
无论是济慈爱的希望,还是勃朗宁夫人爱的重生,爱都成为绝望的诗人最后的精神支柱,爱就是一切。1820年冬天,济慈在公共马车的露天座位上受了风寒,这更加重了他的病情。随着死期的临近,爱变成他唯一的牵挂,他写道:“纵使我的肉体本来能恢复健康,这种别离也会妨碍它痊愈。那最能促使我希望活下去的东西恰恰会成为促使我死亡的主要原因。我对此无可奈何。”②[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册,徐式谷等译,第148页。对爱的希冀和不可挽救的病症折磨着他,在离开英国去意大利疗养途中,济慈写给芳妮《亮星!愿我像你一样坚持》,他希望“枕在我爱人的正在成熟的胸脯上,以便感受它柔和的起伏,永远,永远清醒地感到那甜蜜的动荡;永远倾听她温柔的呼吸不止,就这样永远活下去——或昏醉而死”③[英]约翰·济慈:《济慈诗选》,第129页。。结核病与爱情是如此的密切,它被诗人想象成爱情的变体,甚至代替了爱情,成为爱欲本身,它可以使人生,也促人死。
与诺瓦利斯希望宗教救赎不同,济慈消解了宗教的个人救赎功能,他转向现世,在浓烈芬芳的“诗歌,名声,美人”中忘却生死(《为什么今夜我发笑,没人回答》),对人间爱的渴求和美的希冀成为他的救赎,情人和亲人的爱就是济慈的上帝,因为自然纯净的爱本身就足以净化人世,他对芳妮说:“爱是我的宗教——我能为此而死,我能为你而死么?我的信条就是爱,你是爱的唯一信条。你已凭借一种我无可抗拒的力量让我销魂夺魄——没有你,我就会死。”④[英]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选》,王若昕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这激情的表达中包含着情欲的超越。在济慈看来,情爱是欢乐的和神圣的,而基督教的禁欲和否定生命欢愉是丑恶的。济慈对人的感官描绘极为细腻,经常伴着一种特殊的情爱想象,这与他的肺结核发烧时的肉体状况紧密相连,通过一种获得满足之前刹那间永久延长的状态,诗人获得某种不朽和神圣——爱战胜了死亡,死亡也使爱成为永恒。
济慈之死如同一支过早燃烧的蜡烛,成为欧洲天才早夭的象征,他的死也标志着工业革命后,欧洲肺结核的大爆发:意大利的帕格尼尼,波兰的肖邦,英国的拜伦、雪莱、勃朗宁夫人、勃朗特三姐妹、史蒂文森、毛姆、龚古尔兄弟,德国的路德维希·赫尔蒂、伊丽莎白·库尔曼、托马斯·曼,法国的莫里哀、大仲马,俄国的契诃夫,奥地利的卡夫卡等先后得了结核病,许多作家因之早逝,在大众观念里肺结核普遍与艺术和天才联系在一起。
四、雪莱:自由与无限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Schsegel Friedrich von,1772—1829)认为浪漫主义有一种不可满足并想摆脱束缚的超越性渴望。这种超越性情感在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1815年春就有医生说他将因结核病而不久于人世;他天生敏感的神经,因健康而变得更加敏感和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认为,雪莱激烈偏执的个性,爱子死亡的打击,以及一系列的情感变故是他得病的原因。医生随后建议他去意大利治疗他的肺结核。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的健康已经大为恶化。我的感觉有时麻木而迟钝,有时又会变得敏锐异常,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半醒半睡地躺在沙发上,忍受思想烦恼痛苦的折磨。……症候充分表明我所患疾病的真正性质是肺结核。幸亏这种病发展较慢,如果患者活得足够长久,便有可能在病程的后期由于温暖的气候而痊愈。”①参见雪莱夫人有关《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的题记,见江枫选编《雪莱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932页。作为一名孤独的社会弃儿和自我流放的逃亡者,雪莱开始漂泊在地中海海滨和亚平宁山麓。
1818年,雪莱来到意大利,他心情一度低沉,既没有希望也没有健康,内心不安宁周围不平静,他慨叹世间人享受着荣名、权力、爱和闲逸,在虚幻繁华中欢度人生,而自己的生活之杯却斟满另一种滋味②江枫选编:《雪莱精选集》,第105页。。虽然身处逆境,雪莱依然关注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并完成了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表达对自由和革命的支持。这一期间,雪莱的诗歌风格出现了变化,从有节制的抑郁转向古典的和地中海式的明快,诗中兼有激情和悲哀两重情感。除了依旧激昂的自由和反抗之外,对死亡的描写和病痛的感受不断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更有濒死的幻觉、阴冷的坟墓、枯萎的花朵、疲倦的神色、苍白的脸颊等意象。在《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中,诗人自喻为一朵枯萎的紫罗兰,受到病痛的折磨生命日渐衰弱,如同一个萎缩、僵死、空虚的形体,搁置在自己被冷落的胸襟,以它冷漠、寂静、无声的气息嘲弄诗人依旧热烈的痴心③江枫选编:《雪莱精选集》,第83页。。1819年,他在《印度小夜曲》中描写自己患病时的感受:“哦,把我从草地上扶起,/我气促、无力,我昏迷,/让你的爱化作吻的密雨,/落在我苍白的嘴和眼皮;/我面颊冰冷,惨白无血!我心音沉重,跳动迅疾/——哦,再把它拥紧在心窝里,/它终将在你的心窝里碎裂。”④江枫选编:《雪莱精选集》,第152页。这是雪莱对疾病发作时的细致感受和描写,苍白、虚弱、无力是结核菌导致的热症,诗中还透露出他的心脏已受到疾病的影响(雪莱死后被火化时,人们发现他的心脏甚至是常人的三倍大——肺结核导致的心脏肥大症)。
病痛持续影响着诗人的生活,使得诗人感情格外脆弱,他在《致玛丽》中表达了希望妻子能陪在身边的愿望。写于1820年的《死亡》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复杂心境,在天灾人祸、疾病肆虐的世界里,人们随时会面对死亡,但诗人并不畏惧死亡,因为人们所爱的一切,所珍视的一切,都必定凋零毁灭,就像我们自己一样;这是有生者的无情命运⑤江枫选编:《雪莱精选集》,第247页。。雪莱认为一个人参透生死就无所畏惧,高尚的灵魂不会死去,死去的只是死亡本身,理性的人应当投身于造福人类的事业。雪莱自称无神论者,不愿遁入宗教以求心灵平静,他选择介入现实,直面人生,对苦难生活、社会不公、政治黑暗,发出不羁的呐喊,雪莱秉持的是现实主义的斗争精神,他在斗争中化解了病痛。
最能体现雪莱精神的《西风颂》也是在他患病之后写的,诗歌构思于佛罗伦萨附近阿诺河畔的一片树林里。他将狂野的西风称为“秋之生命的呼吸”,在这西风劲吹的时刻,“万木萧疏”,“枯死的落叶”,“黄的,黑的,灰的,红得像肺痨……”将秋风比为呼吸,以肺痨来比拟秋叶,明显出自于他自己患肺结核病的情感外化。以枯死的败叶象征着死亡,扫荡一切的西风就是挫折和磨难,诗人回顾自己所遭受的一切,不由发出感叹,那个骄傲、轻捷而不驯的生命,现在却如同秋叶一般跌落在生活的荆棘上流血,岁月如同沉重的铁链,压着自由的灵魂⑥[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式谷等译,第254页。他在另一首写于1820年的短诗《秋:葬歌》中也描绘了相似的意象:日渐冷却的阳光,在凛冽的寒风,秃裸的树枝,苍白的花朵零落凋敝,就连大地也被诗人比为灵床,裹着枯萎落叶的殓衣……⑦江枫选编:《雪莱精选集》,第244页。这些意象更细致地表现出诗人病痛缠身心力交瘁的悲怆情绪。但雪莱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必将有美好的未来,他的诗总是呈现出一贯的激情昂扬,《西风颂》中,西风也是革命的精神象征,虽然摧毁一切但也保存希望,到了春天西风又会“吹响她嘹亮的号角,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雪莱希望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能够获得意义,因此在最后做出预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⑧[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式谷等译,第255页。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可以说是诗人“骄傲、轻捷而不驯的灵魂”的自白,更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在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雪莱的自由精神也激励了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莱奥帕尔迪有着“意大利的雪莱”之称,他身患严重肺病,遭受眼疾和贫困的折磨却深具家国情怀,写下了《致意大利》(1818)、《但丁纪念碑》(1818)等优秀的抒情诗,他与雪莱遥相呼应,共同表达了争取自由和民族复兴的理想。
雪莱崇尚大海,大海变幻的性格正是人生无常的写照。诗人回望自己的人生,病痛阴霾在大海上一扫而光,他写出最美的自由诗篇。1822年,雪莱乘坐自制小舟“唐璜号”出海接友人,回来时斯贝齐亚海上突起风暴,雪莱等数人覆舟溺亡。雪莱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崇高与无限,如飞蛾扑火一样,即使牺牲也向着光明而生,直到用生命把这虚伪的世界炸裂。雪莱的贵族出身,他的俊美潇洒,与社会的激烈对抗,传奇般的死亡,悲怆而昂扬的诗歌,都化成某种符号,为结核病的社会隐喻增加了更深层优雅、敏感、忧伤的魅力。
五、结语
1882年,德国科学家科赫发现了致病的元凶——结核菌,揭开了肺结核病的神秘面纱,随着19世纪末殖民主义的扩张,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人们对待结核病的态度迅速转入另一个极端,肺结核患者不仅失去了神秘而迷人的魅力,还成为令人羞耻的给社会家庭带来麻烦的传染病人,肺结核的浪漫化时期结束了。1945年链霉素的发现成功治愈了部分肺结核患者,随着人类进入新世纪,对肺结核的治疗和研究已经有了极大的突破,许多人甚至乐观地认为纠缠人类的肺结核将在几十年后消失,然而事实是它不仅没有消失,很多地区的发病率甚至有所上升并重新流行,人类与疾病的斗争远未结束。面对疾病带来的痛苦、死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理性恐慌,文学成为一帖清凉的解毒药。百年前那些身患疾病的诗人以其不朽的诗篇启示我们:疾病的悲痛可以升华,以宗教来救赎悲哀的灵魂;死亡的恐惧可以战胜,用爱与美来治疗深刻的身心伤痛;死亡的无意义可以漠视,只要融入现实,不懈斗争,如水滴归入大海,个人可以达到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