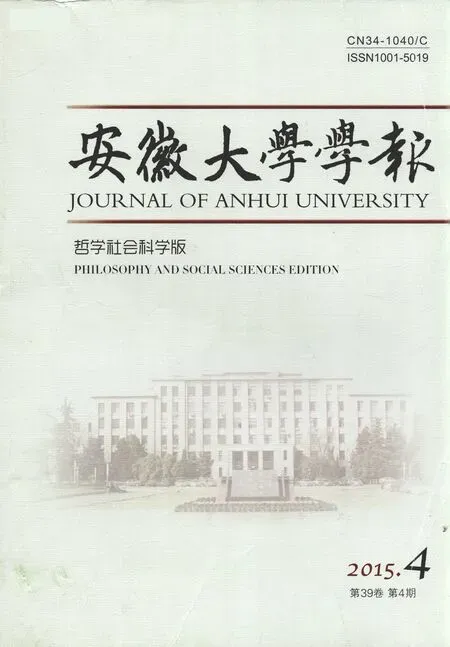论《卡彭塔尼亚湾》中土著性的混杂构建
2015-12-17詹春娟
詹春娟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澳大利亚政府对待土著人政策的转变、土著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土著人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土著文学以其鲜明的创作特色、强烈的政治诉求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澳大利亚主流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早期的土著作品多为自传体或传记体小说,如萨利·摩根(Sally Morgan)的《我的位置》(1987)以及马德鲁鲁(Mudrooroo)的《沃拉迪医生的世界末日良方》(1983)等,以寻根为主题,真实记录白人对土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土著对自身身份的内省和追寻。与这些纪录片式的口述文学不同的是,当代土著文学不再以抗议和控诉白人殖民者的罪行为主要使命,转而以文学的手段,在回溯历史经验中寻找和确立土著传统文化观念,同时借用主流文学模式和框架体系反写土著身份,将口述文学融于西方现代书写,在白人主宰的文化构架中创建出土著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1950~)的《卡彭塔尼亚湾》(Carpentaria,2006)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以澳大利亚北部的卡彭塔尼亚湾为背景,描述了原住民部落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虚实交替、混杂多样的方式再现了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传统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小说一经问世,便在澳大利亚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引起轰动。2007年,赖特成为第一个被授予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项——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土著作家。小说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颠覆了被曲解的历史,宣告了土著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而且对白人话语霸权进行了直接挑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论《卡彭塔尼亚湾》的写作”一文中,赖特强调,“我想探索那些古老传说如何立足于现代社会,探究土著的心灵之地如何被重压和欺侮,如何最终被迫成为关于我们本原的幻象,从而暴露这些心灵之地的防线是如何的脆弱”①Alexis Wright,On Writing Carpentaria,Heat 13,2007,p.81.。因此,小说在过去与现在、边缘与中心、口述传统与西方叙事之间交织回旋,形成一副想象力奇特、文体瑰丽、内容深刻的史诗画卷。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混杂性”并非是一种后现代文学技巧的简单卖弄和炫耀,而是一种“白人的形式和黑人的思想”的有意识的结合,意在揭示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土著与白人定居者之间的新型关系,彰显保存传统文化遗产,获取土著身份对于现代土著性的重要意义。
一、“混杂”的文化语境
“混杂”一词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词,指的是不同种族、族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的相互混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殖民文化与殖民权力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产生了冲突、矛盾与不确定性,从而动摇了殖民话语的防御机制,为建构后殖民文学话语提供了可能。作为土著人的后裔,亚历克西斯·赖特对于土著文化传统有着深深的认同感。在她看来,“祖母讲述的故事解释了一切——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过去以及这一片大陆上独特而亲切的热土”①Alexis Wright,Politics of Writing,Southerly 62.2,2002,p.10.。但与此同时,她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压迫,无论是土著个人,社团还是族群,我们做的所有努力看起来都是徒劳无功的”②Alexis Wright,Politics of Writing,Southerly 62.2,2002,p.12.。因为这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赖特有意识地在《卡彭塔尼亚湾》中呈现了一种混杂性,通过这种含混,赖特旨在说明,土著文化身份的确立,不仅需要保留土著文化传统,更要正视与白人殖民者文化的共谋关系,因为,“土著性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对于相互冲突和杂交性文化归属的认可”③彭青龙:《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外国语》2006年第3期。。
小说涉及三条主线,即白人的历史叙事与土著的本土叙事,土著内部的平行叙事,以及新老土著的自我叙述。这些主线既独立发展,又与其他主线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卡彭塔尼亚湾》中,白人定居者自称是德斯珀伦斯镇的合法土地拥有者,因为他们的踪迹有史可循,有家谱为证。但是在赖特看来,“他们的历史只是把事情真相的开关打开一半——比两代人生命期限中留下的记忆多不了多少”④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57.。他们在镇里无法找到一样标志性的东西来象征自己的存在。他们没有文化,没有歌曲,没有敬奉神灵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赖特宣称,白人只是他们自己梦幻的主人,而土著人才是当地一切的始祖。相较于白人短暂的、虚无的历史,土著一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祖先。土著人领袖诺姆·凡特姆是一段活着的记忆,曾目睹了白人对土著的殖民罪恶,“牧场主鞭打着土著人,巨石上有一个可以窥视的小孔,透过这个小孔,看得见对当地部落居民大屠杀的子弹就像石子儿一样,散落在大地之上”⑤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102.。米凯大叔也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他手上的弹药筒、地图、证人的名字和故事细节都是白人曾经对土著人部落大屠杀的铁证。同样,率领土著人重走梦幻之旅的莫吉·费希曼在幻象中,看到成千上万只白颜色的手,在无情地虐杀土著人。这些口述实录,跨越了白人设定的记忆,颠覆了已然定型的观点,还原了被白人竭力抹杀和掩盖的历史真相。霍米·巴巴认为,“另一种叙述”与“其他叙述”进行了互动和协商,会打开一片“罅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打开了文化混杂的可能性。赖特对“蜘蛛网似的殖民陷阱”⑥Alexis Wright,On Writing Carpentaria,Heat 13,2007,p.90.的逃离,正是对“无尽的分裂的主体”式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但是批判并不意味着走向“本质主义的身份模式”⑦Homi Bhabha,Between Identities,Migration and Identity.Ed.Rina Benmayor and Andor Skotnes.New York:Oxford UP,1994,p.187.。用赖特自己的话来说,她希望这本小说反映了一种心声,不仅是代表土著,而且代表着澳大利亚的每个人,在共同迈进未来的过程中可以彼此更加了解。
在“反历史”叙事之外,赖特清楚地意识到土著无法回归本真的文化窘境。在她看来,除却压倒一切的西方殖民话语,土著内部的分化以及诸多自身的问题和原因,如酗酒、暴力、自甘堕落等,成为现代土著进行身份诉求的主要障碍之一。小说《卡彭塔尼亚湾》的土著形成两大部落,城西人以诺姆为领袖,城东人以约瑟夫·迈德纳特为首领,以镇为中心,分而治之。面对白人的殖民压迫和怀柔政策,两派土著人反应不一。城东人采取了妥协忍让的策略,不惜出卖土地权,以便从殖民者手中换取微薄的利益。这种做法深深伤害了土著人自身权益,破坏了土著朴素的文化传统,侧面反映了部分土著麻木愚昧的心理状态。不仅如此,在强大的殖民文化面前,一些土著不自觉地模仿和认同白人价值观念,主动向白人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表现出一种保守、颓废、自甘停滞的状态。疯人院似的小酒馆里挤满了黑鬼;黑人女孩荒诞地希望黑屋子的生活能让她变成白皮肤的人。诺姆的妻子安吉尔·戴以捡拾现代文明的垃圾为生,她收集了许多亨氏铁皮罐头,螺钉螺帽,甚至一个黑色的座钟和一座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在她看来,这些东西代表着权力和话语,是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具体表现。有了这些象征物,她也会拥有白人的运气。这种对白人文化的盲目崇拜和追逐反映了土著在长期绝望之下对霸权文化的一种臣服,是殖民话语在被殖民者身上的直接体现。毫无疑问,在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较量中,失去了主权、土地、语言甚至精神信仰的土著只能沦落为白人的属下。正因为如此,在《卡彭塔尼亚湾》中,与大多数后殖民作家一样,赖特“转向过去”,以土著文化传统为自己的创作源泉,表达了一种抵制殖民者文化的同化,主张回归祖先精神家园的强烈愿望。
在马德鲁鲁看来,“土著作家就像门神一样,他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另一副面向未来,而他自己则存在于后现代的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①Mudrooroo,The Indigenous Literature of Australia,Melbourne:Hyland House,1997,p.40.。这种杂交性的文化视角在赖特的写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虽然赖特极力主张认同祖先传统,但是她并不沉湎过去,而是正视差异和多样性。首先,现代土著须团结一致,积极反抗殖民压迫,共同争取土著应有的权益。作为土著人的精神领袖,诺姆自知与白人无法抗争,干脆以海洋为伴,专心于鱼类标本的制作,以静制动,守住自己的梦幻世界。诺姆的儿子威尔激进、勇敢,富有斗争精神,与父亲保守、忍耐、逃避的隐士哲学形成鲜明对比。他背负着祖先梦想,勇敢地与资本扩张进行殊死战斗,对损毁家园的矿山建设进行了破坏,维护土著与生俱来的权利。最终威尔将矿山付之一炬,以理想化的方式阻止了现代科技对“梦幻哲学”的挑战和入侵。除了以不同方式主张土著权益,威尔还不顾父亲的阻拦,与父亲的宿敌迈德纳特的孙女霍普(Hope)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后代。这种联姻超越了种族内部矛盾,弥合了种族分歧,有助于土著以同一种声音出现在后殖民政治舞台上,更好地争取话语权。正如霍普(希望)的名字所喻,只有种族团结,才有战胜殖民者的希望,才有守护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能。其次,在多元混杂、异质共存的现代语境中,土著与白人之间的文化融合,文化共谋,成为土著在进行自我言说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事实。诺姆与白人埃利亚斯之间跨越种族的友情,以及诺姆将埃利亚斯的尸体运回传说中的土著神秘之地进行安葬的经历,都成为解构殖民主义的有力注脚,使得文化协商共存成为小说的主旨之一。正如马德鲁鲁的小说《沃拉迪医生的世界末日良方》中主人公所言,土著人要变得圆通活络一些,多找同盟军,要认天命。在《卡彭塔尼亚湾》的最后一幕中,如启示录般的滔天洪水摧毁了争议中的白人小镇,消解了种族冲突和对抗,留下一片新生和希望。新老土著冰释前嫌,一起进行重建家园的努力,而以威尔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开始对自我、种族和家园进行深刻反思。通过这样的自省和改变,赖特的用意不言而明。土著自身团结与种族融合是土著走向民族化,建立自己的身份的必经之路。为此,土著不应消极固守传统民族文化,在幻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而是积极应变,顺势而为。土著作家把土著文学分成两类,一类是“抗议性文学”(Literature of Pro-test),另一类是“理解性文学”(Literature of Understanding)①Narogin Mudrooroo,Writing from the Fringe,South Yarra:Hyland House Publishing Pty Ltd,1990,pp.14 -15.,即面向白人主流受众的解释性文学。从这部小说来看,赖特既没有单纯的抗议,也不是单一的解释,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又超乎两者之上,将现代土著性推向一个更复杂、更多变、更具政治意味的语境,力图在混杂性文化中生成新的土著身份认同。
二、“混杂”的文本
在一次访谈中,赖特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我们有着口述传统,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将有关我们是谁的记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留给后代”。在赖特看来,因为土著人既不说标准英语,也不以西方认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或是历史,故而成为被放逐的“他者”②Jean -Francois Vernay,An Interview with Alexis Wright,Antipodes:A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Vol.18(12),2004,p.121.。因此,土著传统应该吸纳西方文学形式以获得自己的声音,赢得更多的阅读受众。这种写作策略与不少后殖民地作家的创作思想不谋而合。巴巴认为,“通过对‘帝国’或前殖民宗主国语言的挪用(appropriation)和改写(rewriting),使得主子的语言变得混杂,从而达到对殖民话语权威的抵抗和解构”③Homi Bhaba,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33.。在《卡彭塔尼亚湾》中,赖特将神话传说融于现实世界,口述历史混杂于官方记载,土著方言土语结合标准英语,用反叙述的文本疏离了主体的特征,反映了一种话语的“流动性”和“弹性”。
小说一开篇,赖特便用丰富的想象将读者带入远古洪荒的年代。“创世虹蛇——一个比暴风雨中的乌云还大的怪物,满载着他自己创造的‘穷凶极恶’,从星星上盘旋而下”④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1.。虹蛇不仅能呼风唤雨,用“水火风气”等神力摧毁一切,也可呼唤新生,化身为美丽的河流和湖泊,因而是土著家园的守护神。当现代科技大肆掠夺土著人的资源,污染了原本圣洁的江河湖海,导致狗身上长满了癞皮癣,凤头鹦鹉发生了基因变异,虹蛇所代表的大自然用飓风洪水将德斯珀伦斯小镇夷为平地,以隐喻的方式将历史复原到白人殖民者入侵之前的年代。小说在神话与现实、梦幻与想象中更替,展示了土著人信奉的梦幻哲学以及对土地的依恋,表现出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不少评论家将此归结为“赖特受了白人作家的影响,如弗兰克·哈代、帕特里特·怀特、扎维尔·赫伯特等”⑤Ravenscroft,Alison,Dreaming of Others— Carpentaria and its Critics,Cultural Studies Review,Vol.16.(2),2010,p.194.。对于这一点,赖特并不否认她所受的西方文化标准的影响。她在墨尔本接受了高等教育,获得了多个学位,并在大学里从事研究工作。她广泛阅读了西方当代作家以及后殖民地国家本土作家的作品,其中《百年孤独》给了她很多启示和灵感。但是她并不认同自己的写作是对白人主流文学的模拟和效仿,否认了“《卡彭塔尼亚湾》是向白人作家赫伯特的《我可怜的祖国》(1975)致意”⑥Jane Perlez,Aboriginal Li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Nov 18,2007,p.31.。对于小说中的神话和魔幻因素,她认为,土著一直固守家族和族群的不可言说的秘密,以至于“集体失声”,因此,文学是创造一个“更为真实的现实复制品”⑦Alexis Wright,Politics of Writing,Southerly 62.2,2002,p.13.的一剂良方。对于代表着理性和科学的主流评论家的观点,如神话和梦幻代表着“不真实”,“欺骗”,以及“土著文学应被视为未开化的、甚至是不理性的、次宗教的观点”⑧Patrick Wolfe,The Dreamtime in Anthropology and in Australian Settler Cultur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 History 33.2,1991,pp.203-209.,赖特敏锐地指出,“主流话语创造出新词来攻击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根基,目的是为了置土著心声于不顾,为他们的种族主义开脱。由于我们的文化信仰,一种基于浪漫的原始主义的部落文化,我们的民族被认为是反社会的渣滓”⑨Alexis Wright,Politics of Writing,Southerly 62.2,2002,p.14.。不难看出,在语言的背后,隐藏着殖民者权力、殖民者意识对被殖民文化的宰制本性。因此,讲述土著人自己的故事,对赖特来说是一次反叙述,更是对西方主流文化视角的一次拨乱反正。
除了大量使用神话传说,发掘土著被隐藏的声音,赖特还对白人的“官方文件”用戏谑的方式进行反讽。例如,德斯珀伦斯镇第一件被载入史册的工作是“骆驼被赶走”,以及城里档案被大火化为灰烬后,小镇新史的第一页是从“一种阔嘴鹬的到来”开始的。白人殖民者急切地将微不足道的事件记载下来,用文字的方式证明他们对这块土地的归属权,恰恰说明白人历史的虚无和不堪一击。正因为如此,垃圾女王安吉尔·戴断定,那些写官方文件的人都是“胡说八道的伪君子”。而与之相对的是,土著人的记忆存在于那些部落的老人心中。那些白胡子老人知道每个家族的历史,部落久远的故事。他们“以一种有节制的兴趣看待镇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时隔不久,开始修正自己的记忆。这就是老人们为了大家的切身利益,津津有味地做的日常工作——口述关于小镇‘有争议财产的暂行保管人’的历史”①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51.。这种历史被口口相传,生生不息,虽然并没有文字的记载,但是在赭红色石壁的山洞里,兽骨、破玻璃瓶子、生了锈的铁火柴盒、古老的石头工具等祖先遗物是最有力的无声证物。这种非官方的、隐蔽的口述故事与居于统治地位的殖民叙述形成了鲜明对比,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真实”,使读者可以进行“对位阅读”来检视主流话语的可信度②Veronica Marrie Gregg,Jean Rhys’s Historical Imagination:Reading and Writing the Creole.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 of North Carolina P.1995,p.144.。在赖特看来,所有的时代都是重要的,因此写作就像是编绳,将所有故事,从古至今的一切现实,合而为一。
《回写帝国》的作者阿什克罗夫特指出,帝国压迫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语言的控制。在《卡彭塔尼亚湾》中,土著文化被白人殖民者文化所压制,土著的方言土语也日渐式微,成为一种遥远的幻象。如诺姆被搁浅荒岛后,在祖先幽灵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孙子巴拉。“这群黑天使用一种古怪的语言叫喊,让普通人注意他们说的话,却不想让别人看见”③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299.。这种古怪的语言就是前殖民时代的产物,而这些语言的拥有者并不想被教化,表明了他们主动与殖民语言使用者保持一种疏离,以维护本土文化的完整性。但是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梦幻的,因为现代土著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下,本土语言已被边缘化,殖民者的语言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在赖特看来,英语的写作语言是大势所趋。它能让土著的思想有更多的受众,从而为土著融入多元社会提供更多的可能。但是她没有完全套用或是仿拟殖民语言。她清楚地意识到殖民帝国的英语必然和土著文化语境中的元素混杂,产生有别于标准英语的变体。从发音到语法结构,现代土著英语里充斥着他们自己的本土思想和经验,因而语法错误频出,表达生硬,完全是一种与白人规范语言不同的“黑色语言”。它的存在不断提示宗主国语言与殖民地本土语言之间的对抗。如土著人塞拉·姆赤作白人的说客时,操一口很不流利的英语,说:“他们就是这样说你和大伙儿的,说——现在这儿,那儿,到处都是我们宿营地的破烂儿——都是从你这儿开始的。说——他们不得不阻止这一切。要表现一点对这个地方的尊重。这个地方属于德斯珀伦斯郡议会。别让这个地方像一个黑脑袋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出没的垃圾场”④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37.(That what’s what they is saying about you and all.Saying you started all of this town camps stuff springing up here and there for we mob.Saying they got to stop it.Show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ce.Place belonga Desperance Shire Council.Stop the place looking like an infestation of black heads and what have you.)对此,诺姆回答说:“你说的是哪门子英语?”因为语言的选择关系到立场的选择,“黑色语言”的使用向白人宣布了他们之间的差异,表明他们既在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之内,也在体系之外,是个有着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的群体。在土著的潜意识里,英语是属于白人的语言,因为他们会不小心使用了“他们”的语言,并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说过的话都被坏人偷走了”①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98.。通过对西方语言的“挪用”和“改写”,赖特使殖民者语言变得混杂,实现了对殖民主义所建构的二元对立的拆解。
三、“混杂”的反殖民主义策略
《卡彭塔尼亚湾》自出版以来收获了不少溢美之词,但是也遭到了不少批评。不少读者觉得小说晦涩难懂,因为它有“游移的叙述声音,多变的叙事角度以及不确定的时空”。但是这正是赖特匠心独运之处。她坦言自己一边写作一边倾听音乐,将“卡彭塔尼亚湾的不同声音混杂起来,一如将不同形式的音乐综合成一首绵长的乐曲”②Alexis Wright,On Writing Carpentaria,Heat 13,2007,p.86.。这种混杂性不仅充分体现在文化语境和文本形式上,更体现在复杂丰富的反殖民主义策略上。小说涉及种族、宗教、生态等多种问题,立体地揭示了土著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并对土著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中构建民族身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种族主义暴力一直是土著作家着力鞭挞的主要命题之一。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白人殖民者将土著定位成劣等民族,“不那么像人,不怎么开化,是小孩子,是原始人,是野人,是野兽,或者是乌合之众”③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0页。,因而对土著大肆屠杀、驱赶、隔离以及同化。在小说中,城里白人居住在德斯珀伦斯镇的中心,而土著只能住在小镇的边缘。中间的荒原地带成了天然的分界线,赋予了不同地理空间明显的政治意义。不仅如此,城里人还用石头围墙、带刺的铁丝网等象征物作为边界,将“黑魔鬼”御之门外。在强大的殖民压迫下,土著被剥夺了土地、丧失了语言、迷失了身份,从一个具有四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变成了一个“缺席”和“失语”的群体。德斯珀伦斯的镇长布鲁泽“吹嘘自己追遍了城里的土著女人,像给牲口打烙印一样,在她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④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41.。在他们眼中,土著与牲畜无异,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动物。正是在这种种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三名土著少年被认定为杀死白人的凶手,在监狱里惨遭折磨,最终含冤自杀。在长达四页的描写中,赖特不再使用晦涩的修辞、隐喻或梦境,而是用一种触手可及的愤怒,刻画出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土著的悲惨处境表示了无尽的同情。警察楚思福尔(Truthful)的名字看似代表了殖民者的主流价值观念,如“正义”和“公平”,实际上只是掩盖真相、混淆是非的幌子。以土著保护者自居的白人殖民者往往将土著视为“可鄙的救济对象,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智力低下、无法自食其力”⑤Alexis Wright,On Writing Carpentaria,Heat 13,2007,p.85.。针对这种土著人的滞定形象,赖特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歌颂了土著英雄诺姆以及他的儿子威尔,质疑并挑战了殖民主义话语。诺姆不仅熟知天象,与自然精神契合,还是一名出色的艺术家。他可以将死鱼制成栩栩如生的标本,化腐朽为神奇,引得慕名者纷至沓来。威尔机智勇敢,性格坚韧,是让白人殖民者大伤脑筋的头号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威尔(Will)所示,他是小说不受限制的主体,代表了土著的未来和希望。而这种未来和希望是白人殖民者无法掌控和限制的,因为威尔长得与其他土著人没有分别,简直是一模一样,像一个幻影一样,始终来去无踪。这种幻影式人物正是赖特政治思想的精髓,因为他们存在于每一个土著人的思想中,存在于山水万物之间,因而无法被白人殖民者彻底消除或抹杀。这些英雄式的人物有力地解构了帝国主义话语体系,成为土著民族身份建构的一个真实的注脚。
殖民主义除了以种族主义暴力推行殖民文化之外,还用宗教力量来控制和同化被殖民者的精神。在《卡彭塔尼亚湾》中,宗教的意象时隐时现,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殖民地的上空。为了一座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安吉尔·戴与另一部落的土著大打出手。但是代表着上帝的雕像却没有保佑她,她先是被情人费希曼遗弃,最后被一辆白人货车撞死,从此“生活在一个魔鬼横行的地方”①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453.。在土著人的信仰中,背叛祖先的下场是悲惨的。安吉尔的灵魂没能回归祖先栖息的圣地,而是在一个肮脏、可怕的白人之地里游荡。面对土著的精神困境,费希曼敏锐地指出,“天主教的教义如同格洛格酒一样,麻醉了土著人的思想,毒化了土著人的社会,都应该被禁止”②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142.。赖特以一种传统的诗意和神秘消解了基督教的教化作用,强调土著人与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渊源。不仅如此,赖特还对基督教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贬抑,如卡彭塔尼亚湾主教教区的丹尼神父是嬉皮士,更是一个拳击手。他“通过拳击、唱歌、谩骂传授基督教的教义,并通过许多次拳击比赛,造就出一大批天主教徒”③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159.。赖特利用黑色幽默和反讽抨击殖民文化,揭示殖民主体的虚伪和欺骗,从而动摇并疏离了殖民话语体系。
作为帝国主义扩张梦想的有力工具,殖民主义不仅在政治、文化上对土著人民进行无情压制和破坏,在经济上借助现代科技对土著的土地资源进行掠夺和剥削。在小说中,古福瑞特矿业公司对卡彭塔尼亚湾地区大肆开采,造成了大面积的环境污染,“矿山巨大的黄颜色的挖掘机,像可怕的魔鬼,在满眼碧绿的土地上挖出一个个巨大的窟窿”④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98,395.。但是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人们却视而不见。矿业公司以提供工作机会为幌子,用钱收买了越来越多的土著。面对家园被毁的危险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土著中的有识之士如威尔、费希曼终于以暴力方式来对抗白人的入侵,伸张土著人自己的法律。他们打开了“地狱之门”,让大火吞噬了矿山。法农曾把暴力革命视为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他认为,“被殖民的人民为重建民族主权而从事的有组织的、自觉的斗争是最充分的文化表现”⑤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p.172.。除了暴力革命,赖特还借用虹蛇的神力来彻底摧毁这黑暗的世界。龙卷风的到来,是“老祖宗伟大的魂灵从污染严重、粉尘肆虐的大海发出的愤怒的呼号”⑥Alexis Wright,Carpentaria,Artarmon,NSW:Giramondo,2006,p.401.。在飓风的作用下,白人小镇不复存在,他们的狗也不再吠叫。不难看出,在“梦幻”哲学的作用下,白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从占据统治地位到失却家园的“边缘人”,白人殖民者经历了类似被殖民者的经历,同样品尝了“失语”的滋味。通过这样的颠覆式叙述,赖特成功地反写土著的身份,让长期患有“失语”症的土著民族恢复了应有的声音。
通过诸多“混杂”,赖特以恢宏的气势、瑰丽的想象、丰富的意象发出了自殖民时代以来土著民族的最强音。在她看来,这种声音既要回溯过去,又应展望未来,以一种积极灵活的姿态适应现实,才能在多元文化时代构建现代社会中的土著身份。虽然她认为,在目前的阶段,真正的民族和解还不太可能实现,因为白人殖民者给土著带来了太多的伤害和痛苦的记忆。但是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自省将是种族和解的开端。我们深知,在帝国主义话语的干涉下,现代土著性的建构和认同将是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但是,赖特的混杂视角以及开放的写作态度无疑是对现代土著性建构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学尝试。
责任编校:刘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