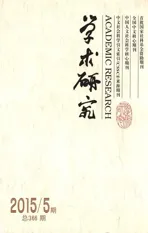《野草》中的“立人”维度及其诗学
2015-12-15朱崇科
朱崇科
《野草》中的“立人”维度及其诗学
朱崇科
鲁迅的 《野草》中有丰富的哲思,其中,“立人”思想也有其整体性观照。如果从单篇思考来看,他既有借助自然的抒情性策略,呈现出他对立人姿态和立场的描绘和情感投射 (比如 《雪》),又有对这种思想的中国践行可能性反思,呈现出对 “立人”思想的具化和丰富策略 (如 《这样的战士》);也借助 “互文性”诗学,无论是从立人思想正面/负面的繁复性考量还是从更宏阔的意义关联上都呈现出别致的匠心 (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从此视角看,《野草》真是鲁迅的精心创制,有不可踵武的经典性。
立人 诗学 《雪》 《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富含鲁迅哲思的 《野草》,也含有 “立人”思想。他在1907年写的 《文化偏至论》就很明确提出了此一思想,这个思想终其一生,成为不败的坚守和梦牵魂绕的精神探寻主题。然而,“立人”思想是一项相当繁复而深邃的系统工程和理念设计,①有关论述可参李新宇 《鲁迅的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钱理群 《与鲁迅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王得后 《鲁迅教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房向东 《鲁迅与胡适:“立人”与 “立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刘国胜 《渐远渐近:鲁迅 “立人”思想启示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如果要结合历史、现实中国的方方面面继续实践、总结、反思与深化 “立人”并形成立国思想的话,可以从更多复杂层面加以思考与处理,如制度设计、个体强化、身心提升等;若采用简单的二分法,如崔绍怀等人的 《论鲁迅 〈野草〉中的立人思想》,既从反面批判愚昧落后的消极形象,也有正面诉求,如直面现实的反抗者、顽强不屈的韧战者、美好理想的追求者等。[1]但 《野草》对此亦有整分结合、交叉连缀的描述策略,本文侧重借助文本细读探勘其间耐人寻味的诗学策略,代表性文本是 《雪》《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下简称 《聪明人》)。
一、自然风情:《雪》中的 “立人”姿态和立场
《雪》多风景描写,里面蕴含着作者的选择性情感,也包含了 “立人”思想的投射,既有对 “暖国的雨、江南的雪、朔方的雪”的态度呈现,又有立场凸显。 “立人”内容包含:批判依附性,弘扬 “奋飞”的独立性。
(一)鲁迅的态度演进。鲁迅对 《雪》中出现的各种雨、雪事物自有其认同和态度。
1.递进式认同。鲁迅对 “暖国的雨”的态度平静淡然,“暖国的雨”如人之初期,“江南的雪”算是青少年期,“朔方的雪”可谓壮年期。他对雨并无贬义,结尾写道,“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将雨的精魂和朔方的雪划等号,是对雨的形态的肯定。鲁迅对 “江南的雪”着墨甚多,态度上却一分为二。一方面是盛赞其美艳,“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特地衬托其春意盎然,另一方面,在精雕细琢的文字中,对孩子们堆罗汉的过程及结果有幽微细致的描述与揭示,而呈现遗憾态度的雪罗汉结
局,从精心装扮的神仙偶像变成孤单凄清,再到面目模糊乃至消失殆尽,可以看出鲁迅的遗憾和不满。 “朔方的雪”成为鲁迅高度礼赞的对象,不粘连而随风飘扬、弥漫苍穹,不受人操控,这是他最认可的雪的类型与精神品格。
2.态度对照。关于 “江南的雪” “朔方的雪”的精彩对照,孙玉石指出,“鲁迅在自然景物描写中寄托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向往江南雪景温暖的春天一般的美好理想,而憎恶把朔方的雪花变成孤独和冰冷的严酷的冬天,就是鲁迅在这篇散文诗中所寄寓的幽深的情怀。”[2]坦白说,论者把北方的自然空气和当时的政治气候隐喻相结合,会造成解读偏差的。 “朔方的雪”如此飘逸与别致,是因为温度较低,这是鲁迅尊重的科学事实。如果从深层的象征意义解读,“朔方的雪”的灵动、豁达、大气与 “江南的雪”的浓艳、粘连、沉沦,形成人格比拟与对照,可以看出鲁迅的取舍态度。
(二) “立人”的主体性层次。若从 “立人”思想关键词去重诠 《雪》,鲁迅其实还倾注了对主体性的思考,这已成为其受到褒贬和认同态度的主要标准。他批判依附性,大力弘扬独立性。
1.批判依附性。有论者把 《野草》中鲁迅的彷徨、苦闷和孤独感归结为未和革命群众结合及尚未找到中共指引,把鲁迅变为论证政治正确的既定结论的注脚。实际上,无论是中共还是人民群众都处于成长期,中共相对稚嫩,群众大多愚昧,甚至启蒙者/思想革命者都有缺陷,故鲁迅在 《雪》中批判了其依附性,这尤以 “江南的雪”为中心。
格局狭小。鲁迅对 “江南的雪”的美艳寄予了密集渲染与美誉,也不乏着力烘托,“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一副精致温暖的艳丽气象。他的小说 《在酒楼上》也有类似的书写,惊艳之感和主人公的颓唐心境颇有对比的张力。
任人揉捏。鲁迅还批评了 “江南的雪”的随遇而安和任人揉捏,这尤其是以塑雪罗汉为中心。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对这个罗汉结局的细描和情感投射,首先是他在喧嚣中的孤独;其次,他一任晴天蚕食,慢慢地不复罗汉模样,更显出他的寂寞、彷徨。雪罗汉的败落、消亡表面上看是它难以对抗晴天的温度,而实际上却是因为它自身的局限。对于雪罗汉的遭遇,有论者指出,“这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模式 ‘看——被看’的再现。在其他作品里,这种模式曾被鲁迅作为一种揭示国民劣根性的有效手段, 但是在本文里,这种 ‘被动性’模式很显然又具有了另外一重含义——不能把握自己命运,不具备独立品格,必将最终沉沦——的暗示。”[3]这里呈现出鲁迅的否定—肯定态度的辩证。
2.弘扬独立性。更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对独立性、自主人格和孤独感的坚守与弘扬。首先,“朔方的雪”象征孤独的独立性。 “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这当然也是一种反抗,拒绝依附,拒绝被收编和把玩,而且格局宏大开阔,三种形态的事物中间,它最具豪迈而不羁的性情,“即使身外的青春真正的已不再存在,那么,在他的 ‘死掉的精魂’之身上,也就是进行 ‘朔方雪花’所象征的孤独反抗的生命存在中,仍然有永不绝灭的希望在的!”[4]其次,《雪》透露出悲哀和彷徨的意向、情愫,但更强调内在的自由自我、不羁特异的灵魂高贵与无拘无束的创造力、冲击力,这是 “立人”的核心要素之一。最后,鲁迅亦关注孤独的奉献精神。 “朔方的雪”是主动赴死的大欢喜,“这不是被动的被人遗弃,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战士自己的 ‘绝不粘连’的性格所造就的。因此,这种孤独也是一种倔强的孤独,是将自我置之绝地之后所产生的孤独感。”[5]
有论者指出,《雪》的构思及表达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其中渗透了作者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思考;不同地方的雪的品质和作者的不同态度,象征性地表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也表现了作者情感生活中的矛盾心理和痛苦体验。[6]此论颇有新意,但有过度诠释之嫌,如何找寻情境描述和意义指涉之间的关联也成问题——必须有更多明确的过渡证据和论证。“江南的雪”中的雪罗汉事件或许可以反证出把玩和消费语境下精神信仰的游戏性、虚妄性,所谓 “吃教”、“无特操”等等,到了 “朔方的雪”中似乎变成了以自由、虚浮乃至虚无为信仰和追求了,而这都是主体的主动选择。
二、《这样的战士》:“立人”思想的践行者及其中国遭遇
《这样的战士》更是对 “立人”思想的纸上践行,也是对其小说 《呐喊》 《彷徨》的一种主题呼应、佐证和总结。“战士”角色既是他对自我的期许,更是对强力意志式的超人、启蒙者的设定,又是对这种思想革命精神的追寻与坚守。鲁迅设置了这样的战士所遭遇的中国语境:对手们的狡猾多变,以及战士可能的困境。从此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立足现实语境的执著与可能的形而上超越。

身份 特征 武器 备注亚洲土人 蒙昧 雪亮的毛瑟枪 X中国绿营兵 疲惫 盒子炮 X战士 只有自己 蛮人用投枪 不要甲胄(牛皮+废铁)
(一)战士与 “立人”。文本开头写道,“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这既是期待,又是指明。在上下文中,“立人”思想与战士角色有一种幽微的勾连。
1.赓续 “立人”。相当多论者忽略鲁迅此段书
写的丰富内涵,“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为了更清晰思考,我们不妨用表格来说明。从武器来看,战士用的只是相对落后的投枪,但他拥有的却是自己,具有高昂的斗志和强大的内在。鲁迅更强调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如果结合鲁迅留日时期的 “立人”思想论述 (如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其中强调的不是船坚炮利、唯 “物”主义,而更多是一种科学精神以及相关的文化土壤;强调的不是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更多是强力意志的生发。如乐黛云说的,“过客”和 “这样的战士” “都带着这种尼采式的强者的色彩,都是鲁迅认为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特别需要强韧的意志力这一思想的形象再现”。[7]这是升华的战士、超人/强人,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设定和期许。如李玉明指出,借助此文,鲁迅完成了对自我人格结构的形塑,主要分成如下几个层面:a.思维敏捷、敏于行动,“寸铁杀人”;b.清醒;c.冷静;d.有辨别、有主见;e.从容镇定、俯瞰人间;f.韧性十足;g.无赖精神;h.信念——反抗绝望。[8]
2.如何 “立人”。 “立人”的内在发动更多通过自己,好比 “启蒙”,在康德看来,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9]但由于漫长的封建统治、“瞒和骗”的传统根深蒂固,“立人”又需要先觉者/启蒙者的帮助,所以这就成为 “五四”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困境之一。所谓启蒙者并不深入钻研有关理论,救出自己,而是更急功近利地呼吁群众跟随,因此邓晓芒犀利地指出,“当这些自认为是 ‘启蒙’的思想家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他们已经在做一种反启蒙的工作了,并且总以盲目追随的群众的人数作为自己 ‘启蒙’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准。”[10]而鲁迅超出了同时代人的部分局限,是最具自我反省精神的启蒙者,深知自己的局限。回到文本中来,鲁迅更强调的也是自我的内驱力,为此,“立人”思想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口——战士。战士既能自我启蒙,又通过以身作则让民众见贤思齐。
(二)践行者及其中国遭遇。战士作为 “立人”思想的践行者,他担负的角色相当复杂,一方面,他是鲁迅的自画像,自我反省、激励与确认的载体;另一方面,作为战士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革命和战斗,尤其是思想革命必须毕生坚持。为此,他就必然面对外在的,内化的,环绕在战士周围的各色敌人。
1.对抗空头/点头。鲁迅对战士作战的对象设置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第一阶段,战士的敌人以头为武器。
点头。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点头貌似示好的标志,这是表面现象。中华文化传统相对缺乏如何面对陌生人的应对策略,点头之所以成为一种隐蔽的杀伤性武器,是因为它仿若糖衣炮弹,让观者麻痹大意或以为对方是熟人或同道,但一旦陷入后,就会被各种 “软实力”收编,如过继子嗣的封建伦理体系、道德规训、利益诱惑等。比如 《长明灯》中处理祖辈曾经当过官的叛逆者疯子,《孤独者》中族人对付魏连殳,策略都一脉相承。
空头。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上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到了空头策略中,“无物之阵”的头上是貌似名正言顺的好名声,但这些名词内容都已被偷梁换柱,却仍打着旗号来对付那些轻信者和愚昧之徒,鲁迅在写此文前其实已经对 “正人君子”之流加以打击了。清醒异常的战士不仅仅勇猛,而且也心细如发,颇有谋略,“但他举起了投枪”,一副不受收编、不受麻醉的战斗模样。
2.刺破瞒和骗。面对战士的坚守,“无物之阵”快速变阵,他们以发誓作为欺骗的手段和工具,继续虚假制造自己的特异,妄图说服战士。但战士既有韧性,又有理性,“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这种 “无物之阵”所实践的瞒和骗的传统也就是常年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统治逻辑, “与其说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意识形态的渗透功能,不如说在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战斗精神,实际上正是这种坚韧的永不放弃的战斗,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11]对于瞒和骗的传统,鲁迅一直坚守 “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无论是现实中的同道王金发没替遇害的秋瑾复仇,而被糖衣炮弹收编、日益堕落,乃至被反动势力杀害,还是小说 《药》中借助夏瑜的牺牲悲剧带来无药可救的结局,鲁迅 (也希望读者)都做出深刻反省。甚至到了杂文中,他也依旧不无苦口婆心之举。
3.启蒙的困境。 “无物之阵”还有更强大的围困策略,战士虽然一击而中,但 “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这种被误读、狙击和困境恰恰也是鲁迅自我和现实中国的投影,“正像竹内好所指出的那样,这篇作品并非只是单就具体事件所阐发的感想。应该说它是将中国 ‘黑暗’状况的特征以及与此进行持续战斗的鲁迅的特质进行形象化的艺术作品。”[12]坚守的战士亦会挫败,他终于英雄迟暮、繁华落尽、油尽灯枯,而 “无物
之物”必然以虚假的 “太平”(恍如 《希望》中形容青年们的 “平安”)粉饰太平、奴化中国。这种挫败感、荒诞感,既是鲁迅自身的深切体验,也是对预设 “立人”理念及践行此理念的战士命运的揭示。
如果回到女师大事件的现实中去,“无物之物”的策略——流言和谎话为鲁迅所深恶痛绝。但鲁迅终究是鲁迅,战士依旧是战士,明知自己会老化死去,墓碑亦指向进攻方向,“但他举起了投枪”,身躯已倒而战斗不息,精神不死。
三、《聪明人》:“立人”的繁复性及互文性诗学
《聪明人》一文内蕴丰腴,主要指向了 “立人”思想的繁复性。鲁迅对 “立人”的繁复思考之一是从反面切入,认真清理不同层次、类型人物身上各色各样乃至根深蒂固的奴性,另一方面则是采取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的诗学建构继续思考他留日时期就提出并阐发的 “立人”议题,其中包括打破 “铁屋子”的意象隐喻,同时亦有在中西文化序列中考察 “傻子”的位次并注入合理的新元素。
(一)反面切入:清理奴性。 《聪明人》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层面是从反面切入,对形形色色的奴性进行清理。
1.奴才的自奴化。奴才这个角色就是在接受意识形态规训后简单懦弱、自噬苦难、自我奴役的代言人。
精神欺骗法。这种自我慰安和阿Q的 “精神胜利法”有共通之处,但亦有差异。阿Q是一种自我欺骗、安慰的胜利法,而精神欺骗法则更被动——依赖于他人不痛不痒的鼓励,所以鲁迅在文中写道,“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他不是选择愤而反抗,而是时不时乞求别人的怜悯和廉价同情借此压抑可能的反抗,从而达到自我欺骗、自我奴役的效果,如奴才回答聪明人安抚之后的言辞,“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甘心自我奴役,其间只是牢骚得到慰安就变成了天理的安排和命定。
自奴与奴他。孙玉石指出,“鲁迅在这篇散文诗中所写的三个人物,是对现实斗争中某类人物命运和态度的集中概括,但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那一种阶级和阶层人物的直接代表。鲁迅所写的应该看做是一种诗的精神的象征,而并非小说的对真实人物性格的刻画,也不能当做带有历史性的典型人物来理解。”[13]此论相当中肯,作为来自于现实的感喟、反思与体悟的文本,《聪明人》中的指涉极可能关联了现实,但更可能又是一种诗学提炼和哲学总结。奴才角色亦有呈现鲁迅先生深刻性的层面,他却懦弱贫乏,没有勇气反抗,同时甚至没有勇气承担责任与接受别人施予的解放与自由,从而反映出其深重的 “奴他”(由被逼奴役辛勤劳作到自我奴役到按照此思维奴役他人)意识,最终出卖了傻子。习惯了自奴化的奴才不仅不能接受真正的自由,还不允许自由思想/载体的存在与蔓延。
2.帮闲与奴主。文本中还有其他样式的奴性,比如帮闲和奴才主人身上的奴性。
聪明人的利己本质。聪明人的出现有两次,两个场景中可以看出其立场、姿态和灵魂深处的奴性。第一个场景中他是奴才的诉苦对象,也是博取廉价同情的资源之一。第二个场景则是傻子被奴才们赶走后,主人出来夸奖了报警的奴才。聪明人的随口赞扬、信口开河安抚既方便了自己、得人赞誉或感激,同时又帮助主子——主人安抚奴才,为其站队服务。冯雪峰的见解一针见血,“‘聪明人’其实也是一种奴才,不过是高等的奴才;他很聪明,知道迎合世故和社会的落后性,以局外人或 ‘主子’的邻居的姿态替 ‘主子’宣传奴才主义哲学,所以也是一种做得很漂亮的走狗”。[14]
主人的奴化与自限。 《聪明人》中虽然极少出现却近乎无处不在的是主人,他是文本中 “主—奴结构”相对潜隐却又至关重要的存在一极,但他的身上也吊诡地存有奴化他人和难逃奴化的双重性。一方面,他是这种专制黑暗结构、制度和逻辑的暴力执行者,也是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主人也是 “主—奴结构”的牺牲品。在这种奴化思想中,他也是奴性十足的承载者和选择之一,在他之上还有更大的主人,或者是相关的奴役专制思想、逻辑结构,他必须借此结构榨取最大化利益,主人也因此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他也是臣服于 “主奴结构”牵涉的巨大利益和统治思想的,甚至他也可能随时被撤换。在 “主—奴结构”中,离开了奴才的主人并不能真正存在,这是他奴性和依附性的又一层体现。
(二) “立人”的繁复性:互文性诗学观照。鲁迅采取了多种策略来丰富和思考其 “立人”思想,而结合诗学创设考量,在 《聪明人》中相当突出的则是互文性①有关互文性的介绍和研究可参考王瑾 《互文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法]蒂费纳·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vault)著,邵炜译 《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诗学。这一方面是鲁迅对自我思路,尤其是互文本中呈现出有关主题的共享与深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鲁迅和其他思想之间的互文,尤其是鲁迅在借鉴这些思想之上的发展与再创造。
1.“铁屋子”隐喻及打破策略。 《聪明人》中所哭诉的状况,尤其是居住环境的恶劣令人不免想起 “铁屋子”意象,这是此文本和 《呐喊》进行互涉的表现之一。在这种互文性诗学中,我们看到 《呐喊》 《彷徨》时期的精神差异和鲁迅思想的嬗变特征。在 《呐喊》中,“我”对于能否打破铁屋子心存疑虑,但最终还是抱有希望,“听将令”并为前行的先驱者呐喊几声;而 《聪明人》一文中,傻子对于为铁屋子开窗的想法颇为赞同,热火朝天、雷厉风行,“傻子跟奴
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然后相当固执,“‘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直到被一群奴才赶走。这两种斗争策略,无论是过于绝望 (虽然深刻、洞察力强),还是过于激进(虽然行动力十足)都是更成熟之后的鲁迅着力反思和加以完善的对象,这和鲁迅偶有犹豫和彷徨,但更坚定反抗绝望、韧性战斗的策略有所差别。
2.“傻子”的文化角色吊诡。在 《聪明人》中,“傻子”的角色也颇耐人寻味:他如何从一个不甘于倾听诉苦、奋起助人为乐的勇士变成了一个被帮助者——奴才揭发/检举的 “强盗”?鲁迅将之命名为 “傻子”又有何深意?鲁迅在撰写 《野草》的时期还翻译了厨川白村的 《出了象牙之塔》,译本后记就刊登在1925年12月10日 《语丝》第57期上。半个月后 (26日),鲁迅写了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厨川白村有关于 “呆子”的介绍和论述,“所谓呆子者,其真解,就是踢开利害的打算,专凭不伪不饰的自己的本心而动的人;是绝不能姑且妥协,姑且敷衍,就算完事的人。是本质底地,彻底底地,第一义底地来思索事物,而能将这实现于自己的生活的人。是在炎炎地烧着的烈火似的内部生命的火焰里,常常加添新柴,而不怠于自我的充实的人。从聪明人的眼睛来看,也可以见得愚蠢罢,也可以当作任性罢。”[15]“呆子”和 “傻子”当然有差别,但 《聪明人》中的 “傻子”和厨川所言的 “呆子”有神似之处。
无独有偶,孙玉石甚至还考察了此文中的观点和尼采哲学的契合与差别,认为 “鲁迅在尼采的哲学中找到了自身生命哲学思考的基点。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艺术构思,就可能成为这种生命哲学化成的内在火焰的一种形象状态的释放。在鲁迅神圣的愤怒与讽刺中,隐藏着他对人民的大爱在内的。这也许正是鲁迅与尼采之间的一点区别罢。这篇散文诗似乎没有很深的哲学,而一向不被一些向潜深处开掘的研究者所注意。”[16]傻子身内的生命状态 (幼稚型 “强力意志”)也的确呈现出和周围形形色色奴性不同的内质,虽然略显粗糙。鲁迅很可能从厨川白村和尼采那里获得了某种精神资源,同时鲁迅也的确是扎根中国的 “民族魂”作家,毕竟 “傻子”本身作为助人为乐的启蒙者,他对奴才的表面诉苦实则寻求慰安继续忍受奴役的深层现实缺乏深切了解,从这个角度看,他又得面对自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依附性。
《聪明人》中的 “傻子”其实也是鲁迅对自我书写的一种有意互文,我们可以将之安放在鲁迅创造文本的狂/癫/疯谱系中,这在鲁迅的小说中有相当精彩的表现,可称为癫狂话语。[17]为此,我们要看到 “傻子”的独特性和锐利性,他有真情实感、具有即席行动力和主体性,他也具有坚守和信仰,是一种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象征。正是借助对“傻子”正反面 (尤其是正面冲击力)的缜密思索和象征诗学策略,鲁迅的 “立人”思想才呈现出多姿多彩性。
[1]崔绍怀、刘雨 《论鲁迅 〈野草〉中的立人思想》,《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2][13]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92页。
[3]李振峰、王硕:《精神的涅槃飞升与生命的超越性指向——重读鲁迅的散文诗 〈雪〉》,《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4]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 〈野草〉重释》,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101页。
[5]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 〈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133页。
[6]刘彦荣:《奇谲的心灵图影——〈野草〉意识与无意识关系之探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82-185页。
[7]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8]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9][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3页。
[10]邓晓芒:《启蒙的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11]强东红:《“无物之阵”与意识形态》,《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2]片山智行:《鲁迅 〈野草〉全释》,李冬木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14]冯雪峰:《论 〈野草〉》,《冯雪峰论文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1页。
[15]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何兆武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16]孙玉石:《关于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
[17]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10
A
1000-7326(2015)05-0135-05
朱崇科,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广东 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