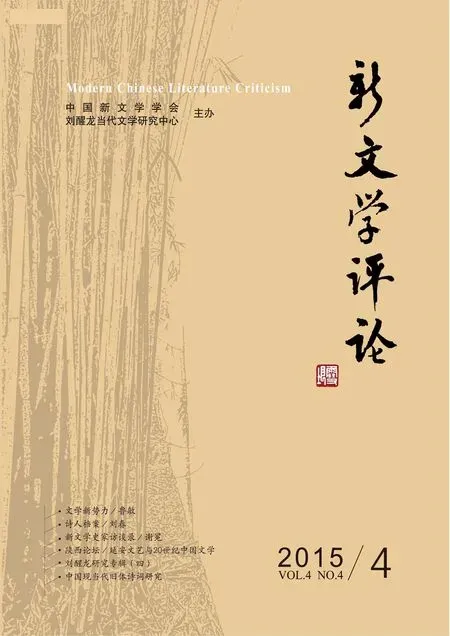从高亢到自然
———诗人刘春访谈
2015-11-14李小建
◆ 李小建 刘 春
从高亢到自然———诗人刘春访谈
◆ 李小建刘春
李小建:能谈一下你的个人诗歌写作历程吗?这中间在诗歌写作上有经过怎样的转型或者转变?
刘春:我的第一首诗歌大约是在1992年春天发表的,在四川都江堰一个名为《玉垒》的民间刊物上,当时我18岁。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好几年诗歌,内容无非是少年时期的惆怅感伤。我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本很厚的台湾诗选,杨牧、郑愁予以及后来的席慕蓉等台湾诗人对我这种青春情绪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的诗歌道路很顺畅,似乎没经历过什么坎坷。1993年我出版了一本叫《大地的婴儿》的诗集,然后开始在《诗歌报》、《诗神》、《星星》、《青年作家》、《江南》这类当年很有号召力的刊物上比较密集地发表作品。但现在看来,那些作品仍然是青春情怀的余绪,大部分可以扔进垃圾篓。
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伴随着新千年而开始的。或者可以说,2000年到2004年,是我诗歌写作的喷发期和转型期。那几年,我十分关注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争论,阅读了大量论争文章和相关的思想史书籍。与此同时,我已经在新闻单位工作了多年(我1995年进入新闻媒体工作),工作和阅读拓展了我的视野,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几年,我写了大量向思想者致敬的作品,以及一些关注民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名声。可以说,我作为“诗人”的地位,就是在新世纪最初几年奠定的。
李小建:从2000年后,我注意到你的写作在诗歌和诗歌评论上一直齐驱并进,你也一直以“诗人”和“诗评家”的身份为人熟知,近年来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等诗歌评论著作反响甚大;而自你2004年出版的诗集《幸福像花儿一样》之后,十年的时间再没有出新的诗集了。很多人感觉你的诗歌写作有所停滞,或者说是让位于诗歌评论写作?事实是这样的吗?
刘春:2005年,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反思自己的创作,我感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话,可能写作会出现障碍:题材已不新鲜,灵感会逐渐枯竭。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新鲜感”的缺失无疑是致命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开辟另一条道路,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于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把更多的精力让给了诗歌史的研究与写作(事实上,在此之前的2003年,我就开始在《星星》开诗歌评论专栏),诗歌作品的产量缩减到每年20首左右,个别年份甚至只写了10首。
随着《朦胧诗以后》、《一个人的诗歌史》等系列著作的出版,这几年,我似乎成了一个“诗歌批评家”了。如果说诗歌写作仅仅以数量而不是以质量为标准,那么,说我的诗歌写作“有所停滞”没什么错。而我暗自欣慰的是,这几年我仍然写下了一些满意的诗歌作品,诸如《月光》、《请允许我做一个怯懦的人》、《自省书》。
李小建:很多诗人包括普通读者非常喜欢你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作为一个诗人,你写下的这些“诗歌史”带着个人的经验和解读,没有高深的概念、术语,非常好读。但也有人批评说你的诗歌批评是“个人印象式批评”,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春:我一直认为文学批评要说人话,要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内心感想,而不是拿自己的发现去印证别人的话的正确性。我很敬佩那些真正搞学问的学者,但值得尊敬的好学者凤毛麟角。时下假大空的“学术文章”太多了,一些所谓的“文学批评”,不仅里面的思想是别人的东西,行文也是公式化,术语一个接一个,甚至不停地引用古今中外名人巨匠的言论,似乎没有那些伟人撑腰,自己就不知道如何下笔了。那样的文章是给人读的吗?也许吧,只是我才能有限,无法也无兴趣去理解作者的“博大精深”。因此,我从来不认为我的作品是文学批评,《一个人的诗歌史》出版时,编辑问我在封底的“上架建议”是写“理论、批评”还是“文艺评论”,我说,写“随笔”吧,我觉得随笔更合适,我本来就是写自己对诗歌、对诗人、对历史的印象嘛。“个人印象式批评”没什么不好,总胜于那些连“个人印象”都没有,只知道人云亦云、拉名言撑腰的“学术批评”吧!
李小建:很多诗人都兼具诗人和诗评家的双重身份,如T.S.艾略特、奥登、布罗茨基等,国内这类诗人评论家更多。你能谈一下你如何平衡、融合这两种身份吗?这两种身份对你的诗歌及诗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刘春:国内有很多所谓的“诗人评论家”,有一些还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写评论,首先不是因为我写不出诗歌而改行,我只是不想在诗歌上重复自己。其次,我写评论是因为我想写,而不是有人拿钱来诱惑,也不是因为有人拿枪来指着强迫着写。这两点决定了我平和的写作心态。我从来不会去考虑我到底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评论家,我只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不在乎那些虚的,我在乎有没有“自己的感想”。
李小建:你曾经说“诗歌是一种与心灵息息相关的技艺”。能具体谈谈这句话的含义吗?在诗歌写作上,心灵与技艺之间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因为很多人专注于“直抒胸臆”,而忽略了诗歌的技艺和技巧;而有些诗人则迷恋于诗歌的技艺、“智性写作”、“诗歌修辞术”而遮蔽了内心的真实,诗歌成为一种高难度的字谜游戏。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春:任何文学作品表达的都是人的感情,诗歌也不例外,因此,它必须与心灵相关。而作为一种文体,诗歌自然面临着“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说,诗歌属于一门技艺,有老手和生手之分。关于“心灵与技艺”的辩证关系,你已经表达得十分到位,在这里我要啰嗦几句的是:正因为诗歌与心灵相关,因此老手不一定比生手写得好。也许你过于追求技巧的完美而忽视了内涵的自然呈现,或者过于注重对意义的托举而在表达时弄巧成拙。诗歌写作的神秘之处在于能够让很多青年人甚至初学者获得必要的信心,古往今来,多少名作都是写于作者少年时!所以,我还是期待多读到一些语言质朴、不事雕琢的好诗,而不愿意绞尽脑汁去“猜谜”。生活已经够复杂的了,不是吗?
李小建:我注意到你近些年的诗歌写作,如《请允许我做一个怯懦的人》、《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自省书》等,有一种“介入现实”感,诗中充满自省与悲悯,但这种“介入”是源自内心的,不是一种激烈的控诉、抵抗与介入,而是一种“内心的现实主义”。相对于以往,你将眼光更多的投向“底层”、“日常”、“内心”、“小人物”、“卑微的事物”,这是否是你诗歌写作的一种新的转变和趋势呢?
刘春:你说得对。首先,我的作品中表露得更多的是自省,而不是控诉和指责。这也许和我的性情相关,在生活中发生什么麻烦时,我第一反应常常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古人说,一日三省吾身。我做不到,但必要时先自我反思,却是我的习惯。其次,近几年来,我的目光更多地回归到了身边的事物,而不是像2000年至2004年那个时期那样恢弘与高蹈,如果说当年我诗歌的思想性来自自己的阅读,那么近几年则是来自自身的思考。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转变,我觉得我的诗歌的声调不像以往那么高亢,而是自然了,平和了,但力量并未减弱。
李小建:在2002年左右,你写出了一批名作如《卡夫卡》、《艾略特》、《艾兹拉·庞德》等“致敬诗”,这种“西方资源”和“阅读经验”对你的诗歌写作有何影响?在“致敬”的同时,你是否更倾向于刻画自己,表现自己内心的状态和感受?近些年,这种“知识分子式”的诗歌写作好像在你诗歌中隐匿和消失了。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刘春:这一批作品就是我上面提及的“声调高亢”的作品,我在这些作品里对一系列事物进行了诘问、质疑、嘲讽,当然,落足点仍然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民生状况。那时候阅读的国内外思想性著作比较多,在不知不觉中受影响了,怀疑心特别浓,动不动就想站起来告诉旁人“你看看人家怎么怎么样(开放),我们自己又是怎么怎么样(保守)”,觉得自己挺有思想。所谓的“愤青”,或许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知识分子式”的诗歌写作为什么逐渐从我诗歌中隐匿和消失了呢?也许是因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和诗歌写作的双重复杂性。是不是非得走上前台振臂高呼才能表现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呢? 不过我并不后悔我的那些写作,相反,有一些作品至今我仍然喜欢。那是我的诗歌写作的驿站,正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我后来的作品才能从平静中寻求力量。
李小建:你曾经在《“爱”与“暧昧”:新世纪诗歌的两个关键词》中表达这样一种见解:最好的诗歌,是表达“爱”与“暧昧”的诗歌。“爱”很好理解,但“暧昧”作如何理解?我注意到你现在的诗歌写作,对“暧昧”的表达相对减弱了,而是回到一种“真诚、清醒、自省”的态度上,在表达上更为直接,而对“爱”则有着更深入和宽广的表达,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刘春:所谓“暧昧”,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感觉,有的事物真实存在但你无法伸手握住,比如风,比如烟,比如一些埋藏在心底但不合时宜的想法。无论从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而言,某些时候,我们的确面临一种临风独立的洒脱与“往前一步是深渊”的境地。对于诗歌而言,如何表达这种似风似烟的思想,是个极大的考验。其实说白了,当年倡导“暧昧”的诗歌写作,仍然出于对生活可能性的过分想象,我在诗歌里自顾自地把自己当作肩负重任的知识分子了。而“爱”,看似简单,其实是人类最深奥最伟大的词语,三岁孩童和百岁老叟都知道爱,但他们理解的“爱”肯定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富矿,值得一代代人书写下去。
李小建:你曾经说过“一个诗人能写出30首诗歌就够了”。如何理解这句话?在你写不出诗歌或长时间不写诗的时候你是否会有一种“焦虑感”?你现在一年的诗歌写作是否有30首?
刘春:我的准确意思是:一个诗人一辈子如果能够写得出30首自己满意的作品,就应该不枉此生了。30首,对于很多诗人而言,也许几天就可以完成。那么加上一个定语“满意的”,相信除了那些过于自恋的诗人,大部分诗人会谨慎得多。数千年来,我们能够数出几个诗人的30首作品?因此,如果可能,我想把这句话修改为“一个诗人能写出3首诗歌就够了”。至于我本人,就最近几年的创作状态和创作兴趣而言,30也是一个过于庞大的数字,更何况我满意的连3首都无法达到。不过我似乎也没有特别焦虑,诗人不是母鸡,不必要天天下一只蛋来证明自己。
李小建:“桂林诗会”今年已经举办到第六届了,现已成为全国知名的“诗会”,作为“桂林诗会”的创办者,能谈一些关于“桂林诗会”的情况吗?
刘春:桂林诗会是一个由所有桂林诗人合力举办的诗歌活动,从2010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6届。如果把2003年我和另外几个诗人倡导的“新世纪首届桂林诗会”算上,那就是7届了。桂林诗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那就是所有经费都由诗人们自愿捐助,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几年来,国内有近20个省市的诗人参加了桂林诗会,许多人把这个诗会赞誉为“桂林的一张文化名片”。桂林诗人一如既往欢迎所有热爱诗歌的人们。
李小建:能谈谈你现在的诗歌、诗评写作状态和计划吗?在写完《一个人的诗歌史》的第三部后,你是否还会继续写下去?你的下一部诗集将会在何时出版呢?
刘春:原本我以为第三部是终结篇,因为这三部书实在让我心力交瘁。但2014年初,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征集2014至2015年度重点扶持文学项目,我一冲动就报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四部的选题,然后很快就获得经费支持。于是我只能想办法进行第四部的写作。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目前第四部已经在整理之中,或许半年内就能出版。至于我的个人诗集,广西文艺界的一位非常有魄力的领导说可以支持出版,我希望他说的是真话。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