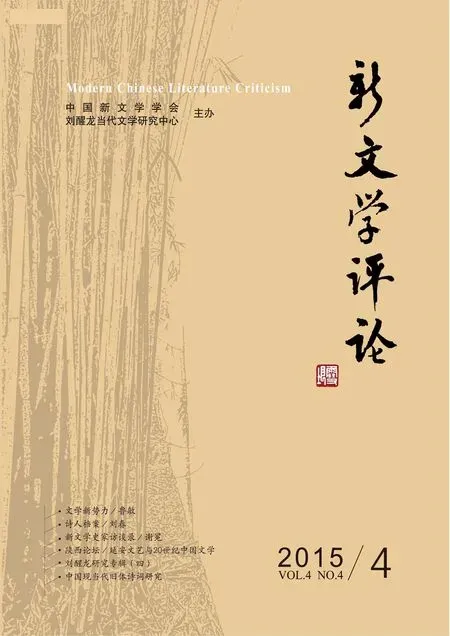诗性想象和文化观照
———评甘才志长篇历史小说《大儒陈诗》
2015-11-14夏元明
◆ 夏元明
诗性想象和文化观照———评甘才志长篇历史小说《大儒陈诗》
◆ 夏元明
甘才志自离开行政岗位后,仅用几年时间就实现了自己的身份转换,从一个相当级别的地方行政官员,变为一个初具影响的“作家”,可见其文学秉赋和不懈努力。其实甘才志并非写作界的“新兵”,早在若干年前,他就出版过几本文学品位不低的散文作品,其中《涅瓦河畔的沉思》,记录自己旅俄的见闻感受,颇富文化比较的深度,为他日后正式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离职以后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随笔,业已为圈内行家所首肯。特别是中篇小说《婶娘的天地》和《打工者》,以其扎实的生活内容和独特的叙述视角,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最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儒陈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更以其宏阔的历史视野,丰富的生活内容,多层次的文化含蕴,写实与抒情相交织的艺术手法,使他的“文学事业”更上一层楼。毫不夸张地说,《大儒陈诗》是一部厚重的地方文化献礼,也是当代历史文化小说可喜的收获。
据作者自云,《大儒陈诗》是应陈诗后人之请而执笔的。原拟写成传记,后因资料不足而改为小说。作为传记,陈诗后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通过陈姓大儒的记述,为陈氏后人树立文化榜样,同时光宗耀祖,以增强陈姓家族的自豪感。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中国有数千年的史传传统,国有国史,族有族谱,宗族名人传记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国史与家传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叙述,不仅为后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是传承历史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进行必要的道德训诫的有利途径。故中国作家大多有深厚的史传情结,借历史叙述发思古之幽情,通过历史的褒贬寄托现世的关怀,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注,补正史之阙,鉴古而知今,这几乎成为中国作家独特的文化品格。所以《大儒陈诗》不能仅看作家族内部的讲述行为,更与悠久的史传传统相一致,是作家家国情怀的表现。舍弃传记的忠实而采用小说的虚构,不仅回避了资料不足之短,更为作家发挥想象,驰骋文思,在更加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情境下,实现自己的历史批判与人文寄托提供了用武之地。不拘囿于历史真实,突破家族叙事的狭小格局,在更为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再现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风貌,这既是一种积极的叙述策略,更是一种文化胸襟,这种文化和艺术的双重聚焦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小说的叙事空间是广阔的。作者的想象既有厚实的地方文史知识作基础,又有丰富的生活积累的植入,故小说的时空呈现出一种立体的构架。檀林河的自然风光,蕲州城的人文掌故,乃至北京城的文化景观,使小说人物不是活在平面的纸上,而是活在活生生的历史氛围中。这种叙事方式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认识价值,使读者如同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历史的现场。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呈现出一幅风俗画般的场景:不同级别的地方官员,身着特殊服装的皂隶,热闹熙攘的货运码头,充满方言的对话,插科打诨,讨价还价,严肃认真,溜须拍马,官场的微妙心态,百姓的生活情形……虽说是闭塞的山区,却依然富有商业社会的生动气息。这就是主人公陈诗出生的时代,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典型环境。它使我们看到,陈诗的时代虽然充满阶级剥削和社会压榨,但总体上却是平静和繁荣的。生活在这种时代的陈诗家族,才可能有读书进学的追求和向往。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耗尽了家族所有的积蓄,几至衣食无着,他们也依然不放弃读书应试的决心。如果没有这种现实的文化土壤,人物的文化理想便成了空中楼阁,无法获得读者的认同和理解。然而作者在提供文化理想真实性的同时,又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进行了严肃反思和深入批判。中国农业社会有“耕读传家”的二元文化心理,以耕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凭读得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二者有时固然互补,但多数时候却成了对立。耕是立本,读是上进,但二者的精神内涵却统一于“勤”和“实”。没有了“勤”和“实”,便有可能危及生存之本。这方面作者的态度是暧昧的,他既通过陈诗家族“败落”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又不能不为陈诗一家人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以至当陈诗终于完成“大儒”文化人格的构成时,作者又不得不为之赞叹。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实际透露出作者务实的作风——他既看到了孔乙己式的科场悲剧,同时又为陈诗式的文化传承所感动,小说的文化精神在二者之间激荡。所以小说的广阔视野,并不单是求得叙述的生动,更意在将读者引向文化反思的深层,在一种更加深邃的时空里透视时代和人物的精神世界,并从而得到现实的启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小说的“当下”品质由此得以显现。
除了这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生活场景,小说的文化构成是多侧面、多层级的。文化叙事显然是作者所刻意打造的品格,也是《大儒陈诗》的特色所在。乡村文化、市井文化、官场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使小说成为一种文化的交响。小说人物活动于其中,不仅突显出人物的“大儒”身份,而且渗透了作者对各种历史文化的感性审美和理性思索。作为一种主体叙事策略,作者还大量引入诗词歌赋、经史百家、人文掌故,力求在更加坚实的台基上重塑人物的文化形象。小说甚至不惜中断故事的进程,静止地对主人公的诗词歌赋进行解读与阐释,以求通过人物的诗词歌赋,更加直接地进入人物的内心,还原人物的心路历程。这种富于“研究”色彩的叙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生动性,但在热爱理性的读者看来,这种叙事不仅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反而会增添阅读的情趣。作为事件的讲述,读者关注的重点在“后来会怎么样”;但作为理性的思考,它所提供给读者的却是“为什么会这样”。前者让我们徜徉于时间和事件先后顺序中,后者却更能揭示人物与时代的深层因果。文化并非抽象的存在,与文化相关联的现实生活场景,特别是主人公的创作本身所具有的形象性,无疑是对作者叙述的补充。作者的引入和解读,可以视为二度创作,这种二度创作所引发的审美联想,甚至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甚至认为这是作者的一个有益的尝试。作者在主体叙事的同时,常常引用诗词歌赋给予印证,这也是一种“互文”的手法。中国文学讲究用典,通过用典令读者的思维在相同或相类或相反的审美场景中穿越,这是中国式叙事所特有的风格。比如《红楼梦》,作为主体的宝黛故事,常常与《西厢记》、《牡丹亭》的故事相交织,在人物类比的同时,使读者获得多重审美感受,这在西方小说中是不常见的。西方小说传统中固然也有互文手法,如《堂吉诃德》对中古骑士文学的戏仿和解构,但在文字上的相互映衬、相互阐扬,却与中国文学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小说始终与诗性相联系的原因之一。中国小说家有意无意间总在向诗靠拢,这除了小说与诗先天的嫡庶地位,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边缘化身份外,同时也与中国文人的诗性审美趣味密不可分。小说是俗文学,稗官野史,街谈巷议,如果不能予人以诗性的体验,不能从叙事和文字中体会到诗的意境和张力,那么它永远无法获得文学史家的广泛认同。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三言二拍”永远不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在多数读者眼里永远高于《金瓶梅》,道理就在其中。其实中国读者先入为主地看重“雅”,而难以从“俗”的层面欣赏民间的生趣,这是中国式审美的局限。如果我们放弃所谓文人的“典雅”目光,从“俗”的角度体会《金瓶梅》等作品的市井和鲜活,《金瓶梅》自有《红楼梦》所不及之处。这种审美眼光的革命要到新文学发生后才会出现,比如鲁迅、刘半农等人对《何典》的推崇,这在“五四”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五四”文学革命,使文人审美向大众复活,从审美立场和趣味上与文化启蒙的大方向相呼应,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此是题外话,姑置不论。
甘才志的美文意识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前文所述,甘才志在从事行政工作之时,就已经出版过几部散文集,其中不乏精美的文字。而他对《古文观止》等经典文本的爱好,使他对其中许多名篇倒背如流。这大大增强了他文字的诗性和美感。小说中有很多描写风景的段落,完全可以当作写景美文来读,从其文字的简练和节奏的和谐,以及意境的优美中,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和功底。如:
竹田冲是一条季节性的河流,雨天它是河,晴天它是溪,一湾细水淙淙汩汩地流淌,浇灌着两岸的农田、滩地,使田野四季分明,银田似镜,翠峰如簇。……(P18)
一大早,陈诗与方铁门各乘一顶蓝布小轿来到襄阳城西,在一处竹制小阁楼前下了轿。曾省斋早早恭候着,见二人来忙放鞭,腾腾的烟雾让二人神仙般飘到阁楼前。烟雾散去后,陈诗定睛一看,门前小桥流水,屋后修竹茂林,两侧藤萝缠绕,四周鸟语花香,真乃怡情养性之处啊,于是赞叹。(P280)
写景如画,分明看得出《桃花源记》等美文的影响。作者并不用文言,但却不乏文言的韵致,干净利落,自然爽口,是文言与口语的成功结合。读这样的文字如饮甘醇,如品香茗,醉心悦目。小说文字应当是有意味的文字,若是随手一丢,连自己都不知所云,这显然不是对自己和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作为一部小说文本,不拘囿于事实是一回事,如何在不违背历史逻辑的前提下,对人物的文化心理做出全新的开拓,并与当下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下再现历史的可能性,这是作者给自己设置的课题,作者也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陈诗有许多历史“疑点”。如何解开这些疑点,通过合理想象,重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这也是作者致力的方向。正史上的陈诗是模糊的,而传说中的陈诗又难免有传奇色彩,而真实的陈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而这种隐含的真实里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历史情境?这便是小说主人公与实际模特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也许可以说,作者并不是在还原陈诗的本来面目,而是在历史人物的身上赋予了作者的再创造,而再创造的结果显然比历史记述更深切,更可靠,更广阔,更富于历史和文化的意味,更能引人反思。
比如陈诗的中年致仕,历史的记述是为了养母,突出了陈诗的“孝”。这固然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作者看来却未必可信。因为其一,作为京官的陈诗,既然供职于朝廷,位至太傅,完全有能力将寡母接至京城,奉养尽孝;二则忠孝不可两全,在封建社会,没有因为尽孝而可以置朝廷的事业于不顾的。这显然另有隐情。作者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结合陈诗的诗词作品,合理想象,还原了一个与官场不合,而又自感学浅而不能尽职的耿介书生形象。这不仅大大拓宽了叙事空间,令人物在仕与隐、官场与民间、忠与孝等挣扎中作出了艰难的抉择,而且更有利于多侧面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说,陈诗是官场的失意者,文场的成功者,而前者恰恰为后者提供了基础。官场不幸文场幸,如果不是官场的失意,我们就无法看到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教育家。这是历史的吊诡和辩证,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知识分子不无启发。世事无常,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者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也许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毋庸讳言,作者的历史想象和现实植入并不能做到完美无缺。大儒陈诗的“大”,有时是作者的经验所无法把握的,所以《大儒陈诗》偶尔也令人有“空洞”之感。著名作家王蒙曾经批评80年代版电视剧《红楼梦》,认为那些热衷于研究《红楼梦》结局的专家学者,固然可以通过《红楼梦》前80回文本的蛛丝马迹和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对人物命运作出合理的推论,但推论归推论,而小说却是讲究过程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过程的艺术”,空有结局,而不能提供使读者信服,使读者感动,使读者击节的过程,那小说就不能成其为小说。这方面甘才志还是存在先天不足的。时代的隔膜,视野的局限,加上艺术经验的相对缺乏,使小说多少带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化痕迹。引入诗词歌赋是好的,但如果以引用取代细致的叙述和描写,则值得商榷。而且所有的引用最好贴近人物,为人物塑造服务,如果与人物游离,变成作者的抒情与感慨,则会给人卖弄之感,不利于艺术的和谐和统一。但这是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无须求全责备。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