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伤怀
——读《老生》的随想
2015-11-14谢有顺苏沙丽
谢有顺 苏沙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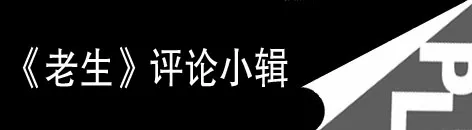
——读《老生》的随想
谢有顺 苏沙丽
一
《老生》发表于二〇一四年,是贾平凹的用心之作,我读完之后,最感新奇的是,作者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写史了。说它是在为一个村庄或一个民族写史,或许有点夸张,但这部作品时间跨度之长,确实在贾平凹之前的长篇小说中所未见。此前,贾平凹的长篇,即便篇幅浩大,写的也多是几个月或一年的事情。比如,《废都》里发生的故事,前后时间跨度一年左右;《高老庄》写的是一次返乡之行,前后一个月;《秦腔》、《古炉》所写的乡村变迁,大约一年多;《带灯》写的事,估计不到一年。这种能力,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如此长的篇幅,却只集中写一个月、几个月、一年左右的事情,这不仅需要作家有巨大的写实才华,他还要有一种细密、浑然的写作耐心。
“中国作家写长篇,大多数都喜欢写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跨度,动不动就是百年历史的变迁,或者几代家族史的演变,但贾平凹可以在非常短小的时间、非常狭窄的空间里,建立起恢弘、庞大的文学景象,这种写作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这种写法,贾平凹或许是受到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的影响,它可以把一个不起眼的场景,一些貌似不重要的人事,通过自己细微的笔法,把它放得很大;里面既有现实经验,也有作者自己的心理经验。所以,很多人只看到了贾平凹身上传统的一面,甚至称他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作家,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却不够全面。照我看来,贾平凹既传统,也现代。他的语言方式,现实情怀,或许是传统的,但他的小说写法,却求变、求新,有很多的现代品格,小说里的很多想法,也是有现代意识的——这些往往不太为人所注意。上面说的叙事时间的处理问题,就是一例。这种叙事方法,显然是现代的,不仅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不太有,当代的先锋作家也未必常用。可见,贾平凹是一个体量庞大的作家,这种体量,不单是说他的写作创造力旺盛,十年出了五部重要的长篇,也是指他的小说具有很大的精神和艺术容量。
《老生》写了中国近代百年史,四个故事,四个时期——闹革命、土改、“文革”前后、改革开放之后,从二十世纪早期,一直写到现在。故事还是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前后写了几个时代的变迁,把国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相结合起来写。四个独立的故事,以一个唱师的角色串在一起,既是散点透视,又有内在联系,这种写法,或许在文学史上并不新鲜,但对于贾平凹而言,却是一种创新,因为他开始在小说中处理真正的历史经验了。从之前只写一个月、一年的事情,到现在写百年史的中国,这不是简单的把时间拉长,而是包含着作者的一种写作旨趣,他大概想暂时从现实中跳脱出来,看远一点,从而为人和村庄的命运变迁找到新的观察视角。
贾平凹对这段百年史的处理,有两个特点是明显的:一是力图追求一种叙事的客观性。那些残酷的事、随时出现的死亡,作者均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写出来,有一种经历了各种世事变迁之后的超然。《老生》里的人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名字里有“老”、“生”这种字眼的,如老黑、马生、老皮、老余、戏生,他们往往是一个时期有话语权、有力量的人物,另外一类是被管理、改造的对象,如王财东、玉镯、白河、白土,等等,他们的地位更卑微,存在感更弱,但这两类人物,多数都在小说中出现之后又死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死,作者都写得不动声色,甚至有一种庄重感。二是尽量回避了正史的写法。写那些草莽英雄、民间人物,贾平凹保留了口传、稗史的风格,尤其是些带有土匪性质的“革命”人物,他们的“革命”动机都是千奇百怪的,比如,在老黑那里,“革命”是带着绿林好汉式的义气,跟谁“背枪”并不重要;在匡三那里,“革命”首要的意义在于能否有饭吃,他最为关心的只是伙房里每日三餐做的是什么;在马生、劳栓等人那里,革命、运动的结果,只是为了可以随意地占有一个女人,或者侵占几亩田地。这种略带滑稽色彩的心理描写,呈现的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只是,这种真实,是对正史的一种颠覆,在保持了小说阅读的趣味性的同时,多少也减弱了历史观察的深度。这是《老生》在叙事上的一种矛盾。作者既要追求客观、冷静的叙事效果,又脱不了小说家写史的趣味——以野史来修正、解构正史的同时,可能也使得一些人物的处理显得面目模糊、略显滑稽。但这些人物生动、有趣,由贾平凹写出来,自然也成了那段历史的补充。
贾平凹自己说,《老生》的写法,在思维方式上,受了《山海经》的影响,“《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或许正因为此,贾平凹才把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忧心藏得很深,静水深流,他在小说中搁置道德判断,抑制自己的情绪,更多的是想做一个观察者、记录者,而把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也有论者觉得,《老生》对《山海经》的穿插,多少显得生硬,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贾平凹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写法,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写史,想借此回望人和村庄的来处;他笔下的人事,其实也是一种心事。
二
《秦腔》之后,贾平凹开始在写作中确立起一种新的真实观,那就是摹写现实的细部,成为现实中人。尽管《老生》在现实之外,也写了历史,但它的写法,依然还是大处浑然、小处逼真的方式,以细节带动情节。有意思的是,贾平凹一旦成为现实中人,他其实就无法做到真正的超然与冷静,毕竟,他不愿意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稀释现实的沉重与疑难。他作为一个乡村之子,乡土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有关。他的根还是在乡土,在商洛,在棣花村,他的精神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最终也要回到那片土地上去,这是他的写作宿命。贾平凹曾说,“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正因为此,我能理解贾平凹在《秦腔》之后所投注到故土上的那份复杂情感:他爱这片土地,但又对这片土地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他试图写出故乡的灵魂,但心里明显感到故乡的灵魂已经破碎。
到《老生》这里,他仍然无法卸下自己身上的这个精神重担,无法摆脱做一个现实中人的那种焦灼感。历史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而现实,依然是如此破败而沉重。但贾平凹在《老生》中坦诚,“我有使命不敢怠”,为了使这个乡土的肉身更为真实,《老生》仍然不惜对现实、对日子做着社会学意义的忠实记录——这种写作变化,从《秦腔》就开始了,但很多人并不认同,也不能完全理解。读完《老生》之后,这个问题或许就更加明朗了:当乡土的现实形态无可挽回地在溃败,文学面对它的方式,真的只能限于审美或悼挽么?文学是否也可以对现实进行记录、勘探、考证、辨析?借由记录和还原,有没有可能触及到更为内在的乡土真实?《秦腔》之后的这十年,贾平凹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期,同时也创新了乡土文学的写法——《秦腔》仿写了日子的结构,以细节的洪流再现了一种总体性已经消失了的乡村生活;《带灯》貌似新笔记体,介于情节与细节之间,疏密有致,小处清楚,大处浑然,尽显生活中阳刚与阴柔、绝望与希望相交织的双重品质;《老生》则讲述了经验的历史,把物象形态与人事变迁糅合在一起来写,进而呈现一种现实的肉身是从哪里走来的。
这个探索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写到乡村的现状,当下的中国文学,几乎采取的都是现代化对乡土固有的美和安静的伤害,《老生》中也是如此,现代化一来,经济结构一发生变化,伦理、道德就坍塌,人心就溃散。这就是村庄必然的命运么?村庄就不配享有现代化,现代化所带来的就必然是一场灾难?千百年来,乡村一直是中国的根基,它的过去几乎是静态的,生活、生产方式一成不变,伦理结构也古老、稳固,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各种观念纷至沓来,各种变革也轮番在这里实验,但乡土的命运却不仅没有变好,甚至还显得更加晦暗。它的沉实和美,正在消失,而自身的惰性和痼疾,却正在生长;加上政策的多变、基层干部的胡来,乡土中国的地基已经松动,一些伟大的乡土品质正在死亡。孟德拉斯曾经这样分析农民农业的消失,“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力量的作用,勿宁说是由于把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决策运用于农业。”这个看法或许是一种社会学的理性分析,但对文学写作未尝没有参考价值。过去我们在讲述乡土中国时,总是从伦理、审美的角度去写,无非是表达一种令人心疼的美,一个质朴、自然的世界的消失,但乡土中国的困境,真的只是审美的溃败或现代化对自然的掠夺么?造成乡村衰亡的原因,真的是如此单一么?如果只是把乡村当作审美的对象,或许很容易就会得出这个结论,但如果看到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生活体,我们就会发现,乡村的变化,不仅是审美意义上的变化,它也是生活方式和价值方式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具体的,它需要有实证意义上的细节、场景作为支撑。甚至可以说,要写出这种变化的实质,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和审美的悼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贾平凹的《老生》,包括他之前的《秦腔》、《带灯》,我认为对观察中国乡土现实的变化,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不仅在于他呈现出了中国乡村的世情、世貌,更重要的是,他也回答和思索了孟德拉斯式的疑问——政策和制度的不合身、甚至失误,对于乡土的溃败,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乡土问题的复杂,尤其是现代化侵入以来,单从文化和乡情的角度,已经很难全面解读乡村的变迁;而贾平凹的写作,除了文化和乡情的关怀,他还描写乡村的经济活动,呈现“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决策运用于农业”之后的现状,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在当下中国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匮乏的品质。它看起来是很不文学的,但它又是文学必须面对的另一种坚硬的现实。
《老生》有一段写到,在那种整齐划一的经济建设年代,村民们只要一穿上那劳动服,人就变了,身子发木,脑袋发木,你得紧张地劳动,不能迟来,不得早起,“屙屎撒尿也得小跑”,这是很生动的描写,也充分说出一种制度不仅改造人的观念,也改造乡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后者的变化是具体的,却是不为人所注意的。贾平凹或许正是看到了记录这种变化的意义,才持续不断地把写作的焦点集中在同一时期的乡村,试图多侧面地写出一种乡土现实变化的真相,以自己的方式,来缅怀这一片土地,这一群人。
三
《老生》中,贾平凹依然还在探寻乡村的出路,人的出路。唱师的这个角色的设置,既起到了串联故事的作用,也暗含着对世相人心的洞察。他为每一个死者而歌,为当归村在一场温疫中的毁灭而歌,之后,自己也随着村庄的衰亡而亡。借由唱师的口,小说出示了一种慈悲的立场,并揭示出,世界的毁灭可能是整体性的,对它的拯救,也必然是整体性的。
一直以来,贾平凹的世界观中,人与物都是平等的,他笔下的人,可以和动物、植物,甚至可以和器物对话。他笔下的人物中,引生是通灵的疯子,可以与花、树对话,他还感谢来劲——来劲其实是手扶拖拉机。狗尿苔也是通灵的,他甚至能看到树在伸懒腰。铁栓家的猪告诉他,葫芦家的冒疙瘩鸡在村南口过生日,于是他看见了村里的鸡、猫、狗给古炉村年纪最大的鸡过生日的热闹场面。蚕婆也是神性附体的。而《高兴》里写到,皂角树、药树、楸树、香椿树、苦楝树与痒痒树这六棵树都是有故事的,也是有灵气的。“树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不是树影响了人,就是人影响了树。”树与人的生命是同构在一起的,毁掉树木也是在毁灭人的一部分。成百上千年的古树是有灵性的,《带灯》中松云寺的松就是汉代的松,可以给人们以佑护。从农村中走出的高兴也是信奉众生平等的,希望人与动物、植物、器物和谐相处,他甚至还和收破烂的架子车说话交流。这样一种思想表明,贾平凹在找寻一种精神出路的时候,他不像鲁迅先生那样,在与现实的对抗中批判,他也不像一些西方作家那样,无情地拷问灵魂的暗疾,他似乎还是信仰万物和谐,信仰生死轮回,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拯救,其实是自我的开悟。
《老生》中的唱师,就是一个开悟者,他穿越历史,见证生死。小说的结尾,是一场瘟疫袭来,村民迅速死亡,当归村几乎成了空心村,唱师和荞荞一起去村里为那些没来得及埋葬的村民唱阴歌,以安妥那些游荡的魂灵。这个场景是象征性的。一方面,是对一个村庄的人事的哀悼与怀想,在死亡面前,人世所有的恩怨、纷争都烟消云散了,魂灵与魂灵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另一方面,是对村庄所承载的物质和精神记忆的祭奠和纪念,为行将远去的这个社会形态——村庄——作一个告别。只是,这个结局的背后,也隐藏着作者的一丝忧虑:那些游离的魂灵是否能回归来处?
唱师的角色,令人想起贾平凹在《高兴》中写到的锁骨菩萨。锁骨菩萨是以妓女之身而行佛事,肮脏与干净同在,这包含了一种救赎的思想,所谓“道在屎溺”。污秽里的圣洁,与“道成肉身”的思想也是相通的。高兴是在沉重、苦难、肮脏中修行出轻松、快乐与干净。正如川端康成也不注重世俗的道德,他所描写的女人,大多是无智慧和无道德的,“但这种无智慧和无道德也和不守贞操一样,并不是我所考虑和表现的问题。我要写的或许可以称为生命的悲哀和自由的象征吧,但这样一说明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在《睡美人》里,川端康成也超越世俗的道德,让一个老人抱着一个裸体的姑娘,而作者把着个昏睡不醒的姑娘比作活佛,“姑娘年轻的肌肤和气味,仿佛原谅并安慰了悲哀的老人。”在一种悔恨中,也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
唱师的角色,也有点像《古炉》中的善人,善人说病,说的其实是一种人生的拯救之道。善人并非是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而是来自于中国民间的传道士,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是孔孟,也不是佛老耶回,我行的是人道,得的是天道。”不光善人,作为乡镇干部的带灯,也可看作是在处理上访问题时不断修行,她不是一般的女干部,而是身上有佛性、有慈悲心的修行人。
“我知道我老了,该回老家了。可是,哪儿是我的老家呢?就是在这年的冬天,天上刮西风,一刮就几个月,我便顺着风走。”——这是唱师最后的自白。或许有悲戚,但没有怨恨,也没有用强用狠的争夺、挣扎、呼告,它更多的是一种伤怀,一种面对现实之后的寂寥,隐约的,也有一种平静和安详。在面对乡土的衰亡时,唱师所获得的释然,或许只是个体的拯救,但除了借由饶恕和慈悲,并接受命运这一切的安排,人又能如何呢?释然的背后,也隐含着一种无奈与宿命。
因着有这一种情怀在,贾平凹的小说总有一种写意的色彩,有一种神秘气息萦绕在小说之中,他对生活、世界以及人的命运是有一种敬畏的。他一方面精细地写实,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伸张自己内心不屈服于现实的想象,他渴望看见命运下面的真相,看见世界有一个灵魂,一直在说话、在呻吟,也在歌唱。每读到这里,就会觉得贾平凹所写的现实突然被推到了很远,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更多的是个人的命运感,是飞翔起来的灵魂落往何处的问题。这些,也正是贾平凹小说的重量所在。只是,从锁骨菩萨、蚕婆、善人、唱师等一系列角色的设置上看,贾平凹写实能力毋庸置疑,写意的方面,却多少有点模式化。他习惯以一个超然角色来俯看人世、道出真谛,使之与现实的风云变幻形成两条线索,互相映衬,互相呼应,这固然拓展了小说的意蕴空间,但也容易给人留下生硬的感觉。因此,在实与虚的平衡上,贾平凹依然还要探索,还要在精神开掘的方式上,展示出新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应该是内在于人物的灵魂深处的,而不仅仅是把人物变成一个精神符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广州。
(责任编辑 韩春燕)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苏沙丽,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