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人话,抑或其他
——关于《老生》的阅读札记
2015-11-14王尧
王 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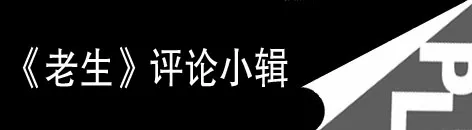
——关于《老生》的阅读札记
王 尧
贾平凹无疑是小说界“常谈”的“老生”了,但他常谈常新。《带灯》的余温尚存,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读到贾平凹刊发在《当代》上的《老生》。这部小说的“形式”与“内容”都给我震撼,以为《老生》是贾平凹近几年来“整理”自己创作道路,继《废都》、《秦腔》之后的“里程碑”式作品。
“整理”一词,见于《带灯》之“后记”,往往被论者疏忽。他说写《带灯》的过程,“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这里的“整理”不只是如何写作《带灯》,也是对他自己创作道路的整理。贾平凹的“整理”仍然是从“问题”出发。在“后记”中,贾平凹谈及许多重要问题,包括对社会基层问题的忧思。贾平凹深广的忧思不仅因《带灯》写作而起,《废都》也是一本忧思之书。之后,从《怀念狼》到《高老庄》、《高兴》再到《秦腔》,贾平凹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几乎都是忧思之书。在新作《老生》的第四个故事中,我们也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忧思的情怀。《带灯》后记中谈道:“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这是文学的表达方式。如果再对照《古炉》、《秦腔》,我们会发现,贾平凹这些年来始终在关注着“中国问题”,并且表现了不一样的“中国经验”。尽管贾平凹因《废都》遭遇挫折,甚至也因此改变过自己的写作方式,但他从不失赤子之心。《老生》又将如何表现“中国问题”?
我突出这一点,是因为在贾平凹的创作道路中,《废都》的遭遇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废都》当年受到宽容对待,贾平凹的创作会是怎样的景象?贾平凹在世界文学秩序中的位置又会怎样?我越来越意识到,《废都》的遭遇不仅挫伤了贾平凹,其实也挫伤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无法想象《废都》的遭遇给贾平凹多大的心理压力和阴影,这样的压力和阴影又在多长时间改变了贾平凹创作的路向。毋庸讳言,至少在《高老庄》之前,贾平凹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生活在压力和阴影之中的。在读完《老生》之后,我荒唐的想法是,如果这部小说成于九十年代初期,或许会是《废都》一样的遭遇,贾平凹呈现的历史可能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
但时过境迁,贾平凹已经是“老生”了,他已经有一种脚跟扎在现实之中,肩膀扛起历史的内心力量。也许因为我曾经研究散文的缘故,多年来我和许多人一样,喜欢在读贾平凹长篇小说之前,先读他的“后记”并从“后记”中摸索进入小说的路径。在他以往的“后记”中,或许还有些犹疑和低徊,或者是模糊和闪躲,但《老生》的“后记”是那样的直白、肯定、震撼,以尖锐敲击之。《老生》“后记”云:“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近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都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我很惊讶贾平凹既讲“荣光体面”,又不讳言“龌龊罪过”,愿意面对后者的作家学者实在太少。对这段话,或许可以加上几个注释:首先,《老生》试图写百余年中国,意味着《老生》是在重写《古炉》中的“文革”、《秦腔》和《带灯》中的“乡村”,还有他以前有所涉及不是重点的“革命”与“暴力”等。这无疑是一次大的“整理”,他由当下再返回历史,而且试图讲述“中国问题”的来龙去脉。其次,这句话的启示是,《老生》写了贾平凹以前不愿想不想讲、而现在却怎能不想不讲的事。在重新“想”与“讲”中,贾平凹有重新认识和表现“现代中国”的宏大抱负。
当贾平凹如是说时,我们要关注的焦点自然是他在《老生》中究竟想了什么和讲了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注意一下《老生》在贾平凹创作路向上的变化,这是我个人更为看重的贾平凹的另一种“整理”。《带灯》的写作最初透露了贾平凹“整理”之后的变化:“思索着书里的带灯应该生长个什么模样呢,她是怎么样的品格和面目区别于以前的《秦腔》、《高兴》、《古炉》,甚或更早的《废都》、《浮躁》、《高老庄》?”这一思索的结果,是分出“明清”、“两汉”两种叙事传统与他创作的关系。如我们所熟悉的,《废都》接续的是明清小说的叙事传统,而贾平凹早期的一些散文和文论则比较多的与“两汉”文章相关。在写作《带灯》时,贾平凹面临了选择:“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居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暴力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轻佻佻油油滑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其实,这些年来,贾平凹的创作一直在“两汉”与“明清”之间走动,有些作品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也正常,即便是明清散文,也有奇崛的文字。所以,考察《带灯》之后,贾平凹学两汉品格、近海风山骨,应该不只是观察其语言风格的变化。这不是重点所在。
“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我想要日月平顺,每晚如带灯一样关心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咀嚼着天气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间的万千变化。”贾平凹《带灯》后记中的这句话,已经为《老生》的写作路向埋下伏笔。而到了《老生》,贾平凹则明白地说:“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这期间我又反复读《山海经》,《山海经》是我今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我愿意在这样的关联中来讨论贾平凹和《老生》的创作。
如何解读《山海经》之于《老生》的意义,是解读《老生》的关键之一。
在结构上,《老生》无疑受到《山海经》影响:“《老生》是四个故事组成的,故事全都是往事,其中加进了《山海经》的许多篇章,《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众所周知,《山海经》记载了许多神话,如果说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那么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小说在它与神话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神话文体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因此,分析《山海经》之于《老生》的意义,并不是说《山海经》中的神话给这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以什么样的影响,《老生》并不是重新演绎《山海经》的神话。《老生》在叙事结构上的这样一个特点,是在方法论上受到《山海经》结构上的启示。研究《山海经》的学者研究认为,《山海经》对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创世神话、部族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等)记录较少,而对英雄神话、部族战争神话记录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我以为,这样的特点和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贾平凹《老生》写人与事的重点和方法,小说并无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人物和战争(斗争)是故事的主角,四个故事之间的相互关联除了“唱师”的讲述外,便是人物的隐与现,这和一般的写百年历史的“长河小说”不同。
但是,在我看来,这不是《山海经》影响《老生》的关键部分。鲁迅关于《山海经》为“古之巫书”的观点为我们所熟知,这是我们讨论《老生》与《山海经》关系的一个重要视点。《山海经》的“巫”或者荒诞不经,涉及到的是神话思维和神秘主义问题。关于这一点,贾平凹在《老生》出版后的几次访谈中都特别提及。很多研究者都谈到贾平凹创作的神秘主义色彩问题,其小说和文章中呈现或隐藏的梦境、宿命、巫术、传奇等神秘色彩,显示了他复杂、斑驳的文化构成与生命体验。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可能是少见的融合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作家,文本的意义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传统”的影响。熟悉贾平凹的朋友或许可以发现,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观察时事万象的方式也存在着神秘主义的影响。他的想象、叙事、话语方式都因此显得特别。——我有时觉得写作中的贾平凹就是《老生》中的那个“唱师”。
阅读《山海经》以及为写作《老生》而做的各种准备,让贾平凹对神话思维有了新认识,由此激活了他观察和书写历史的热情并转换了写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贾平凹看来神话的思维,其实仍然延续在当下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人中间。《老生》后记中有一段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字:“《山海经》里那些山水还在,上古时间有那么多的怪兽怪鸟怪鱼怪树,现在仍有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鱼虫花木让我们惊奇。《山海经》里有诸多的神话,那是神的年代,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现在我们的故事,在后代来看又该称之为人话吗?阅读着《山海经》,我又数次去了秦岭,西安的好处是离秦岭很近,从城里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山,但山如深海,进去却往往看着那梁上的一所茅屋,赶过却需要大半天。秦岭历来是隐者的去处,现在仍有千人修行其中。我去拜访了一位,他已经在山洞里住过了五年,对我的到来他既不拒绝也不热情,无视着,犹如我是草丛里走过的小兽,或者是风吹过来的一缕云朵。他坐在洞口一动不动,眼看着远方,远方是无数错落无序的群峰,我说:师傅是看落日吗?他说:不,我在看河。我说:河在沟底呀,你在峰头上看?他说:河就在峰头上流过。他的话让我大为吃惊,我回城后就画了一幅画。”这幅“过河山图”,水流不再在群山众沟里千回万转,而是无数的山头上有了一条汹涌的河。我想,影响了贾平凹观察和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只是这幅画,而是他的小说。《老生》开篇第一句话:“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无疑是这位看河在峰头流过的修行者给贾平凹的神来之笔。这位修行者想必是“唱师”的原型之一。
贾平凹所举的这个例子,当然不只是神话思维问题,还与儒释道、宗教和民间信仰有关。在《山海经》和日常生活的启示下,贾平凹以《老生》尝试用另一种思维、方法来讲述百余年的历史。这其实是个难题,因为即便是文学已很难讲历史神话化。但贾平凹巧妙地破解了这个难题,他将抽象的神话思维落实到了老生“唱师”身上。唱师延续了神话的思维方式并且保留了某种可以称为文化密码的质素。从叙事的角度看,唱师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部分故事的亲历者或者至少是在场的旁观者。如此,《山海经》与《老生》之间就有了血肉联系。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山海经》的引用及师生之间的问答,唱师即无立身之本,即缺少了唱师的灵魂;换言之,尽管唱师未读《山海经》,但两者之间互为表里。这是贾平凹的用心之处。
《老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这位“唱师”。不妨说,唱师是《老生》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之一。这位历史的讲述者,来无影去无踪,老而不死。“关于唱师的传说,玄乎得可以不信,但是,唱师就是神职,一辈子在阴阳界往来,和死人活人打交道。”不必说阴间,“单就说尘世,他能将秦岭里的驿站栈道,响马土匪,也懂得各处婚嫁丧葬衣食住行以及方言土语,各种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的形状、习性、声音和颜色,甚至能详细说出秦岭里最大人物匡三的家族史。”就此而言,这唱师是巫,是神,但活在尘世间,他这种“穿越”阴阳界的能力使他的讲述别开生面。这里的关键是唱师对尘世的洞悉。
我们都注意到,唱师出场时,已经说不出话。《老生》中的四个故事其实不是讲述的,而是这位唱师在弥留之际的无声的思维活动。《老生》的一些叙述文字不无滞涩,但在四个故事陆续展开之际,关于唱师的一段文字却是那样有弹性、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从而再现了唱师“讲述”故事的思维特征:
“唱师静静地在炕上躺着,身子动不了,耳朵还灵,脑子也清白,就听着老师给孩子讲授。这时候,风就从门外往里进,风进来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一缕缕云丝,窑洞里有了一种异香,招来一只蝴蝶。唱师唱了一辈子阴歌,他能把前朝后代的故事编进唱词里,可它没读过《山海经》,连听说过都没有,而老师念的说的却尽是山上海上的事,海他是没经过,秦岭里只说海吃海喝这个词,把太大的碗也叫做海碗,可山呀,秦岭里的山哪一处他没去过呢,哪一条沟壑哪一座崖岩不认识他呢?唱师就是想说话,又说不出来。连动一下舌头的气力也没有了,只是出气一阵急促一阵缓慢,再就是他感觉他的舌头还在长,胳膊上腿上的汗毛也在长,像草一样地长,他听得见炕席下蚂蚁在爬,蝴蝶的粉翅扇动了五十下才在空中走过一步,要出窑去。孩子也看见了那只蝴蝶,起身要去逮,老师用钢笔在孩子的头上敲了一下,说:专心!蝴蝶是飞出了窑门,栖在草丛里,却变成了一朵花。”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老生》也是一部当代之“巫书”。但是,贾平凹只是假托唱师之口,而写历史之实,这是贾平凹的匠心所在。在“人话”的“历史”遭到质疑之后,“神话”的“历史”能否呈现我们未曾相识的真相?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叙述转换。以巫师的眼光观察、叙述,是为了揭示“人话”的历史中被遮蔽的部分,被忽视的部分,被扭曲的部分。《老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写史,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将历史民间化。贾平凹试图以另一种话语体系来讲述历史的抱负在《老生》中基本实现了。
因此,当我们褪去那些神秘的色彩,忽略那些乱花迷人眼的枝节(这些枝节也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枝节就不是唱师的“讲述”,而且小说太需要闲笔了,需要空隙了),《老生》呈现了不一样的百余年中国历史。贾平凹在《老生》“后记”中,说到他曾经询问一位老人为何如此德高望重:“他说:我只是说些公道话么,再问他怎样才能把话说公道,他说没有私心偏见,你即便错了也错不到哪儿去。我认了这位老人是我的老师,写小说何尝不也就是说公道话吗?”这又回到了史传传统。
唱师死了。这个人唱了百多十年的阴歌,他终于唱死了。但历史因他死而不忘。
《老生》的四个故事,呈现了百余年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而核心的部分应该是:“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贾平凹显然现成了他对历史的新认知,这是我们理解小说故事的关键:“当文学在叙述记忆时,表达的是生活,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就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痛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一切似乎远了或渐渐远去,人的秉性是过上了好光景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并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但百多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就是如此的出身和履历,我们已经在苦味土壤上长成了苦菜。《老生》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重点仍然是历史,是革命,是人性,但历史、革命、人性中的重点除了清白和温暖外,多的是混乱和痛苦,残酷,血腥,丑恶和荒唐。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历史的全部,或者说革命、人性的全部,但无疑是历史、革命、人性中的重要部分。我们熟悉了革命的崇高与壮烈,但革命的草根性、暴力性以及在革命名义下发生的许多人事,并不全是理想主义的展开。《老生》“原生态”呈现了底层的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和改革,其中包括环环相扣的暴力,以及由于偶然的原因成长出来的革命人物。在这样的叙事中,贾平凹不仅重写了历史,又在重写历史中反省了“我们”的出身和履历,在来龙去脉中拆穿了很多虚幻的影像,从而对百余年的国民性问题作出了新的诠释。我们在小说中读到我爷爷、我奶奶、我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读到我的村庄,读到我们的革命导师和先驱。我觉得,这是《老生》最深刻之处。
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贾平凹同时也塑造了自己。这部小说当然不是什么“成长小说”,但确实让我读到了贾平凹的精神自叙。他在我们共同的出身背景和履历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判和升华。“我们既然是这些年代的人,我们就是这些年代的品种。”一个优秀的小说家,都会在杰出的作品中死去一次,“没有人不去死的,没有时代不去死。”但优秀的小说家总会死而复生。贾平凹是那个唱师,是讲《山海经》的那位老师,是听《山海经》的那个放羊人的孩子。读《老生》,我看见“在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贾平凹“人是走着,走过来了”。
(责任编辑 韩春燕)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