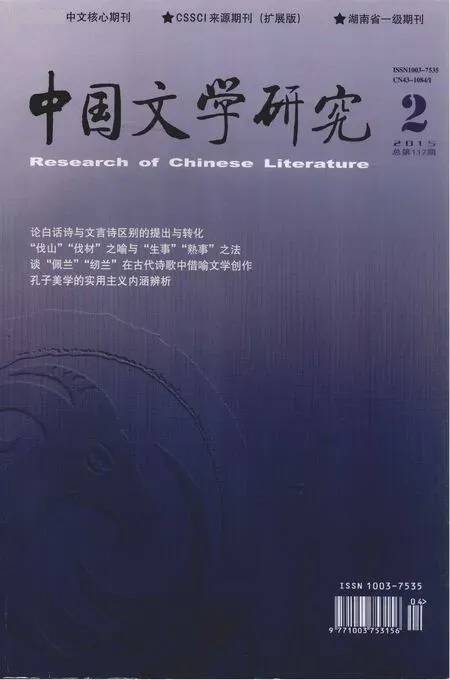论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提出与转化
2015-11-14李丹
李 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胡适文学革命前后的一系列活动都围绕白话问题展开,他不仅从理论上倡导白话文学,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等文,还从创作上进行探索,出版《尝试集》,而且梳理中国文学史中的白话线索,著写《白话文学史》,他的多方面努力一定程度促成了文学革命的成功。对此,已有研究多表现在探讨前两者的贡献和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后者,尚未出现将胡适所谓的白话诗与文言诗当作一个整体的研究。实际上,胡适所谓的白话诗是作为文言诗的对立面出现的,也就是说,白话诗与文言诗是一对互相依存的概念;整体地考察这一组概念的提出与转化,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诗歌演变的相关规律。
一
针对中国小说、散文、话剧创作都已采用白话口语,唯有诗歌还在沿用旧体诗语言模式的状况,又因其脱离现实生活且多数沦为空洞的习套,胡适遂于1916 年提出文学改良的设想,认为文言在今天是死去的语言,唯有人们正在使用的口语才是活的语言,活的语言才能产生活的文学,于是提倡白话入诗,并将这种诗命名为“白话诗”;相对应地,传统诗词所用的是古人的语言,是书面语,故称“文言诗”〔、。
虽未明确界定文言诗,但从胡适提出改变现状的主张,即可见出其所指,“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须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日之诗(南社之诗即其一例)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form 胜质matter。”就是说,胡适所谓的文言诗是特别指向在1910 年代已沦为套路的旧体诗,它的形式已经成为汉语言诗歌的习惯,对套用者来说很方便,但对于诗歌艺术而言,则不利于创新,因为“实用性是审美经验的一个敌人;习惯是审美经验的另一个敌人,它是在由实用性所铺设的道路上对审美经验起障碍作用的。”“人们对老一套的陈腐语言的反应可以说是一种‘常规的反应’,这种反应要求是遵循熟悉的渠道,视而不见,要么是表示腻烦。……语言必须加以‘变形’”、,改变旧的是为了建构新的。因而胡适更关注白话诗,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时间向度上。一是对于白话诗未来的确信。他以欧洲国别文学演变自拉丁语文学的历史事实为参照,确认白话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大胆假设中国诗歌语言也必将由文言转向白话,并倡导中国诗歌革新;后来文学革命的胜利证实了他的假设。二是促成现代白话诗的实现。这是较前一点更为重要的环节,胡适着手求证其假设,即尝试白话入诗,经过3 年多的艰苦努力,《尝试集》的出版证明其可以成立。三是梳理中国白话诗的历史。在中国诗歌史中搜求白话诗存在的轨迹,为胡适在20 世纪倡导白话诗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白话文学史》是其考察的结果。在这三项活动之中,前两者属于从无到有的产物,获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可就是其成功的标志;唯有后者,由于涉及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可从多角度进行探讨,本文仅就白话诗的相关问题而论。
整理白话诗的历史实际上是改变它历来位于诗歌史边缘的处境。“当日在士大夫的贵族文学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文学”,“从此(按:汉)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白话文学史》主要考察对象是汉代至唐代的白话诗。即使注重白话的运用,胡适并未将白话诗局限于浅白之作,他更赞赏有意境有哲理的白话诗,并以陶潜为例进行阐释,“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诗人。”这样,白话诗就从民间作品提升至文人创作的领域。
《白话文学史》突出了白话诗的两个特征:一是真实。包括外在真实和内在真实,胡适在关注诗作歌唱自然的倾向即注重外在真实的同时,也强调内在真实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他十分欣赏杜诗及大历长庆间的诗歌,认为这些诗人有“严肃的态度,说老实话的精神,……这样的认真的态度,便是杜甫以后的新风气。从此以后,做诗不是给贵人贵公主做玩物的了,也不仅是应试应制的工具了。做诗成了诗人的第二生命,‘至亲唯有诗’,是值得用全副精神去做的。”、这些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传达了诗人的生命体验,将真实的精神、真切的品格灌注诗中。二是作诗如作文。胡适特别推重韩愈的诗,因韩愈秉持的作诗如作文的方法正与自己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相吻合,“韩愈是个有名的文家,他用作文的章法来作诗,故意思往往能流畅通达,一扫六朝初唐诗人扭扭捏捏的丑态。这种‘作诗如作文’的方法,最高的地界往往可到‘作诗如说话’的地位,便开了宋朝诗人‘作诗如说话’的风气。”、韩愈“作诗如作文”的方法,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讲究诗歌形式作风的反拨。至此,胡适对白话诗的界定已较明确了,即在运用通俗语言的基础上,自然地表露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情感来自真实的生活,同时需要诗人率真的人格作底子;进一步地,这种真实还需像作文说话一样质朴地表达出来,以摆脱雕琢的人工气。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所肯定的白话诗的特征,是为自己正在推行的现代白话诗寻找历史依据,意即文学革命时期倡导的白话诗也具有相应的优长。在此情形之下,胡适所谓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就是将被赋予优势的白话诗与静止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处于劣势的旧体诗相比较,两者的高下自见分晓。第一,用语的区别。文言诗所用的文字是“死”文字,在古人诗中是活的文字,在今人诗中则是死的文字;白话诗所用的语言是“活”语言,它是来自当下人们口中的语言,是鲜活的。第二,态度的区别。作文言诗的态度是“模仿的”、“沿袭的”,也就是以古典诗歌为模仿对象,囿于传统的套路,以至于抒发与古人相同的思想情感;作白话诗则需要诗人摆脱传统的老例,从日常口语中挖掘诗意,每首诗依据内容而铸词造句,因而是创新的。第三,目的的区别。旧体诗多是为了应景、酬和而作的,往往成为缺乏新意的俗套的应对,目的多为了交游;白话诗则出自新鲜的发现,表达的是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可以达到创作的目的。
胡适的这种比较,一方面基于辛亥革命前后文人诗词的写作状况,一方面基于倡导现代诗的立场。尽管相当程度地带有功利色彩,但当时确实存在泥古的旧体诗,而即将诞生的新诗作为新生事物又面临外在的阻力和内在的艺术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可以起到排斥旧体诗而提倡现代诗的作用。这是改变旧体诗形式大于内容这一现状的必由之路,也是促使中国诗歌语言向白话转型的首要步骤。
二
因聚焦于白话的应用,胡适从诗歌用语角度切入而又未能写竣,致使《白话文学史》遗留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白话诗”的名称问题。既然白话诗自古就存在,胡适也称自己倡导的采用口语的诗为白话诗,那么两者是不是一回事呢?如果是,那不就是复古吗?其结果还是落入了传统的老套;如果不是,那采用相同的名称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正是胡适当年未能明确解决的问题,而在今天看来两者是不同的。古代白话诗即使采用口语,也需遵守一定的诗歌规则,即近体诗需符合字数、平仄、押韵、对偶的要求,歌行体也需遵循诗行字数的定规;而胡适倡导的白话诗则摆脱了古代诗歌的体式束缚,也就是“诗体大解放”了的现代白话诗。这种新的诗歌语言形式,既是现代汉语语法规则的产物,也一定程度受到汉译英语自由诗的影响;被胡适定为新诗成立标志的《关不住了》就是一首汉译英诗:
我说“我把心收起,/像人家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但是五月的湿风,/时时从屋顶上吹来;/还有那街心的琴调/一阵阵的飞来。//一屋里都是太阳光,/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这里的词语及诗句与古代白话诗不同。第一,古代诗歌的词语多是单字的,而现代诗歌的词语往往是两字或三字的。废名就曾指出,“初期提倡白话诗的人,以为旧诗词当中有许多用了白话,因而把那些诗词认为白话诗,我以为那是不对的,就是此,即我所称的‘旧诗’,实在是在一个性质之下运用文字,那里头的‘白话’是同单音字一样的功用,这便是我总称之曰‘旧诗’之故。”第二,诗句构成模式不同。古代诗句不论五言抑或七言,字数多是固定的;现代诗句遵循现代汉语语法规则,字数难免不固定(顿数则可以固定)。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海上的太阳从残夜中生出,江南的春天伸入旧年的末尾”,诗句字数在古代是相同的,在现代则不同。再如“浮云游子意”,现代诗则说成“游子的心意像白云一样飘浮不定”,后者不能缺少语法成分。因此,即使都采用白话口语,古代诗句一般字数相等,现代诗句则长短不一。第三,如果说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跳跃性的言语结构,那么古代诗的跳跃不仅发生在句与句之间,而且可以发生在一句之内亦即词与词之间,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句各由三个并置的名词组成,其间没有谓语动词;而现代诗的语句须主谓完整,因而其跳跃多出现在句子之间,如“像人家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显然,现代白话诗的语言样态即诗体形式不同于古代,如果笼统地称所有采用口语的诗为白话诗,就抹杀了古今的区别;因此在文学革命达到高潮之后,《谈新诗》的发表就标志着现代白话诗这一名称的权宜性和“新诗”这一名称的启用。胡适由此成功地改称“白话诗”为“新诗”。当新诗之称代替白话诗之称后,文言诗之称亦不再使用,这是由白话诗与文言诗两者的互生性决定的。于是,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就转化为新诗与旧体诗之别。由于后者符合古今诗歌的演变情况,故沿用至今。
针对同一个诗歌革新运动,而先后采用不同的称谓,该现象一定程度反映了新诗初创时期的探索性质。在这同一性质之下,《白话文学史》只出版了上卷,提纲里拟定的中、下卷最终没有问世。其原因也许是由于现代白话诗名称改为新诗而影响到古代白话诗的名称问题,但胡适并没有像新诗那样以改称来解决;未完成的白话文学史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一现象本身就是问题没有解决的表现。实际上,就内容而言,《白话文学史》更适于称为“民间文学史”、“平民文学史”或“通俗文学史”。总之,从胡适自身的角度看,对现代白话诗名称的更改和对白话文学史的腰斩,实际上标志着对诗歌革新活动的进一步修正和调整。在以旧体诗与新诗指称中国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区别之后,对于两者内部存在的大众化和高雅化之分,后来的诗歌理论批评则或称其为民间诗(民歌)与文人诗、口语的诗与书面语的诗,或称其为大众的诗与布尔乔亚的诗,以替代胡适所谓的白话诗与文言诗所指的相应内容。
二是关于区分诗歌类型的问题。胡适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分,是按照用语来划分诗歌类型的,运用口语的往往是大众化的诗,如乐府诗或歌行体,运用书面语的主要是文人诗,如律绝体;这实际上是对作者所属阶层及诗歌风格类型的区分,即胡适所谓的民间文学与贵族文学之别,前者语言质朴、率直,后者则雕琢、引经据典。运用口头语言的诗显得自然、清新;运用书面语的诗则高古、晦涩,流衍至1910 年代,其遵循古人传统乃至于堆砌故实的弊病加重从而失去了往日的优势;至此,又演变出诗歌价值取向的区别,前者是艺术上的新作,后者是技术上的复制。还有,如果有诗人一边用口语写诗,一边采用书面语写诗,则情况更为复杂。由此可见,按照诗歌用语分类产生了更多的分歧。这说明胡适的目的并不在区分诗歌类型,而是站在文学革命倡导者的立场,针对当时旧体诗的空洞形式及其放逐时代精神的弊病而强调运用白话口语进行矫正,以促使新诗的成立。
从文化思潮层面看,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分是具有进步性的。《白话文学史》作为五四精神的产物,突破了传统的以等级观念划分诗歌的标准,贯穿着贵族文学与民间文学平等的文学史观,设立了民间诗与文人诗等同的标准。在古代社会,士大夫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的诗歌因语言、题材、受众等因素属于等级社会里的高等阶层,而大众的诗歌相应地属于低等阶层;此前的研究甚少涉及后者,即其被边缘化的明证。随着社会文化的推演,西方民主与平等观念的东渐,封建时代的等级观念逐渐遭到瓦解,尤其在标举民主与科学大纛的新文化运动中,站在民主主义高度,反观历史上的民间诗与文人诗,就会对两者持同等的观照态度,并对其历史地位报以客观的审视;故对自古就存在的民间诗历史的梳理是胡适顺应时代潮流的结果。《白话文学史》首次以大众化的诗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正是为了打破封建时代的偏见,提高了民间诗的文化地位。
然而,即使顺应时代文化大潮,如果不满足诗歌艺术自身的条件,其倡导也会遭遇挫折。区分诗歌类型必然伴随诗歌的出现而出现,如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史诗、抒情诗、戏剧诗的三分法在西方产生两千多年的影响,再如我国的风雅颂之分,美刺之分,民歌与文人诗之分,古体诗与近体诗之分,五言七言之分,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景物诗之分,等等,虽然各种划分各有其根据,却都不曾论及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以用语为尺度将诗歌划分为白话与文言是胡适的首创,再将其作为评判诗歌优劣的标准,这是由文学革命时期的现实状况和预期目标决定的。也就是说,在文学革命的特定氛围里,胡适秉持的白话标准是有效的,但从诗歌史看,这一标准又是暂时的。因为用语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划分诗歌优劣还需要第二步的标准即美学标准,且是第一步的旨归;如果缺少第二步的要求,也就失去了诗之为诗的价值。这一论断已被古今诗论所证实。中国古代诗学就注重用语艺术,“诗以一字论工拙”,其判断标准在于恰切与否,而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如“床前明月光”,“李白乘舟将欲行”,“细雨鱼儿出”,“两个黄鹂鸣翠柳”,“春眠不觉晓”等,带有口语的意味;“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更多书面语的意味;虽然这些诗句属于两种语言类型,却因表现出真景物真情感而被认作经典诗句。王国维1908 年发表的《人间词话》提出以境界来划分诗歌优劣的标准,认为诗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即评判诗歌之优劣,以是否达到艺术的审美意境来衡量,而不以语言的浅白与否来衡量。诗歌的美离不开语言文字,但不能停留于语言文字的表面,应以达到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不隔”境界为目标。这是稍早于胡适的诗歌优劣评判标准,也是受到公认的。
由于存在为了文学革命的实用性因素,也就将《白话文学史》的影响局限于文学革命时期;离开这一时代语境,其意义也就失去了依凭。
三
自新诗确立其文学史地位之后,胡适提出的白话诗与文言诗二分法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此后的新诗理论研究仍在探讨相关问题,这既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的必要步骤,也是对文学革命时期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进一步反思和阐释。
朱光潜于1925-1933 年在英法留学期间接受西方诗学影响并完成《诗论》初稿,其中论及新诗与旧体诗的相关问题。一是关于文字的“死”与“活”。他同意文字有死与活之分的说法,但区别的标准与胡适不同:“以文字的古今定文字的死活,是提倡白话者的偏见。散在字典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为今,都是死的:嵌在有生命的谈话或诗文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为今,都是活的。”诗歌用语的死与活也应以情思的有无来划分,而不是依据文言与白话。现代诗人应用白话,不仅因为其与现代生活、现代情思关系密切,还因为更利于与现代人沟通。二是关于白话入诗的问题。朱光潜肯定白话入诗的必要性,认为诗需要与当下文化语境相符合,这必然包括用语的问题,即白话诗是诗歌发展的趋势。但他同时指出白话入诗不就是以日常所说的口语为诗,而是发挥“说的语言”对“写的语言”的活化作用,前者的流动性决定了它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能力,这是后者的保守性所缺少的,也是诗歌需要白话化的原因。“现代人做诗文,不应该学周诰殷盘那样诘屈聱牙,为的是传达的便利。不过提倡白话者所标出的‘做诗如说话’的口号也有危险。日常的情思多粗浅芜乱,不尽可以入诗;入诗的情思都须经过一番洗炼,所以比日常的情思较为精妙有剪裁。语言是情思的结晶,诗的语言亦应与日常语言有别。无论在哪一国,‘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都有很大的分别。”就用语而言,诗歌比日常口语及其他文体更精练,且写的语言有“文法”和“用字”两方面的要求,故虽然白话可以入诗,但入诗的语言比所说的语言更有选择。
朱光潜进一步分析了“说的语言”与“写的语言”的转化关系:
“写的语言”比“说的语言”也较守旧,因为说的是流动的,写的就成为固定的。“写的语言”常有不肯放弃陈规的倾向,这是一种毛病,也是一种方便。它是一种毛病,因为它容易僵硬化,失去语言的活性;它是一种便利,因为它在流动变化中抓住一个固定的基础。在历史上有人看重这种毛病,也有人看重这种方便。看重这种方便的人总想保持“写的语言”的特性,维持它和“说的语言”的距离。在诗的方面,把这种态度推到极端的人主张诗有特殊的“诗的文字”(Poetic diction)。这论调在欧洲假古典主义时代最占势力。另外一派人看重“写的语言”守旧的毛病,竭力拿“说的语言”来活化“写的语言”,使它们的距离尽量地缩短。这就是诗方面的“白话运动”。
胡适与朱光潜都从欧洲文学史借鉴诗歌白话运动的经验,前者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有首倡之功;后者却比前者更切入诗的白话化问题。从应用的层面看,白话入诗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具体操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朝向白话方向的同时应符合诗歌语言艺术的本质要求,同时还应重视“写的语言”与“说的语言”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而非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
1940 年代即闻名文坛的徐訏从时代发展与诗歌形式演变的关系角度观照问题,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体,不论形式如何变化,诗歌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内容则是不变的:
“如果某种文学的形式无法容纳新的生活内容之时,这个文学形式自然而然就要改变。……中国旧诗词的形式,似已无法容纳由现代生活而产生的新的内容。……其实词汇都是从生活中来,语言文字都代表生活的内容。……我认为,旧诗词这些形式,是只限于表现某种范围内的形式,以情诗而论,如果是用‘小桥’‘栏杆’‘满阶花影’‘银缸’‘残更’这类的情趣,自然很合适,倘若你要用‘咖啡馆’‘跳舞场’‘爵士’‘摇滚’‘高速火车’‘地道车’‘公路车’‘冷气’等词汇那就全弄得无意味了。
……如果一个现代诗人想用旧形式来表现的话,那么你必须,而且很自然地会削足适履地把生活掩饰装潢,以配合这个精致的形式了。
……文学的业绩虽是一首诗一篇文的累积,但代表的是一个作家的生命,我们专心学杜甫,或李义山,自然很可能写出一首可乱真的诗,但是决不是说你已经是杜甫或李义山了。杜甫所代表的是杜甫的一个生命,李义山所代表的是李义山的一个生命,一个诗人的生命是他的时代与社会所产生,他的作品一定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的时代与社会。”
诗人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论及诗歌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特别是他提出的诗是诗人生命之表现的观点,突出了诗歌语言的生命力来自切身生活的原理。如果诗人脱离了时代,则诗歌就是技术的、雕琢的,到了极端则是没有生命的空洞的形式;诗歌脱离了时代也就沦为一种游戏了。这不失为对胡适文学革命时期的倡导之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一种阐释。
当代美籍学者高友工认为,“‘可说’的语言和‘可写’的语言只是一种风格上的区别”,“并不只是文言与白话的问题,而是‘文字语言’和‘声传语言’对立的问题”,“故非‘文语’、‘口语’之互补,而是‘字语’与‘声语’的并存。”“在中国由‘乐府’转向到‘古诗’时,这正意识到由表演艺术转入抒情艺术的时际。这同时也正是口语诗开始与书面诗做真正对立的时期。当然也可以看成口语与文字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的重要性不在界限分明的两个传统,而在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这里,诗歌语言的书面化与口语化并存的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诗歌风格的区别,是由诗人创作心理决定的观点,可看作对胡适偏颇的补充。
以上三者分别阐述了诗歌运用“说的语言”与“写的语言”之差异及其互相转化的关系,新的诗歌语言样式反映新的社会生活以及中国诗歌口语与书面语并存的传统等观点,相对澄清了有关胡适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之转化的问题。
四
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及其后的改称和转化现象,反映出自觉不自觉地对汉语言诗歌规律的遵循与认识。
当胡适提倡白话诗的时候,说明他认识到诗歌语言与日常口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即现代诗歌应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感受,符合诗歌创作源于当下社会生活的规律。这可看作对诗歌现代性规律的遵循,也是胡适的倡导得以成功的基点。中国诗歌在此被历时地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传统延续至近现代的古代文言诗,一个是从现代即将启用的现代白话诗;在《白话文学史》里,胡适提出白话诗自古就存在的观点,将传统诗歌也分为文言诗与白话诗。至此,胡适的观点遇到了两个的阻碍:一是混淆诗歌语言与诗歌体式的差异所遭遇的阻碍,前者属于用语问题,后者是诗体形式问题,由于没能分清这两个概念,且胡适以用语问题代替诗体形式问题,导致了无法解释古代白话诗与现代白话诗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古今诗歌的区别不在用语是白话还是文言即口语的诗与书面语的诗之区别,而在于诗歌体式之新与旧的区别。这是促使胡适将现代白话诗改称为新诗的原因,也是其对中国诗歌发展规律进一步认识的表现。二是割裂中国诗歌传统中两种语言风格所遭遇的阻碍,中国诗歌传统中口语的诗与书面语的诗是并存的,且两者相互作用甚至不断转化,如文人乐府诗等;而胡适将古代诗歌划分为文言诗与白话诗,且仅就口语的诗而论,使两者对立起来,割裂了它们相辅相成的关系,导致了难以解释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既用口语又用书面语的创作现象。这两个阻碍的出现,是汉语言诗歌规律对其产生反作用的表现。胡适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却是不同的,由于第一个问题属于现实问题,当时解决与否,代表着文学革命的完成与否;而第二个属于历史问题,由于不影响文学革命活动的进程,就被搁置下来。
虽然起初对诗歌语言与诗歌体式的认识不够明确,也出现了分拆中国诗歌传统中两种语言取向的现象,而实际上胡适从用语问题入手,摆脱了旧体诗形式的束缚,创立了具有革新性质的诗体形式——自由体新诗,实现了中国诗歌体式的现代转换。这是他逐渐自觉地对汉语言诗歌艺术规律的遵循。
综上所述,关于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提出与转化所涉及的诗歌语言问题,实质上首先属于诗体形式的问题,其次属于用语风格的问题;古今诗歌用语风格可以一致,但古今诗体形式却不相同。胡适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最终得以圆满完成,在于他通过修正实践活动中不恰当的环节,满足了诗歌形式革新的要求。这一现象表明,即使在符合文学演变大趋势的情况下,亦须遵从汉语言诗歌的艺术规律,方能促成文学革命的成功。
〔1〕胡适书信集〔M〕.1916 年7 月26 日致任鸿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胡适留学日记,下册〔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3〕胡适.自序〔A〕.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5〕胡适.白话文学史.〔M〕.胡适文集〔M〕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废名.新诗问答〔J〕.人间世,第15 期,1934(11).
〔7〕胡适.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J〕.星期评论,1919(10).
〔8〕李丹.论胡适改称“白话诗”为“新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6).
〔9〕黄霖.导读〔A〕.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12〕徐訏.禅境与诗境〔A〕.徐訏文集:第11 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3〕高友工.中国语言文字对诗歌的影响〔A〕.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