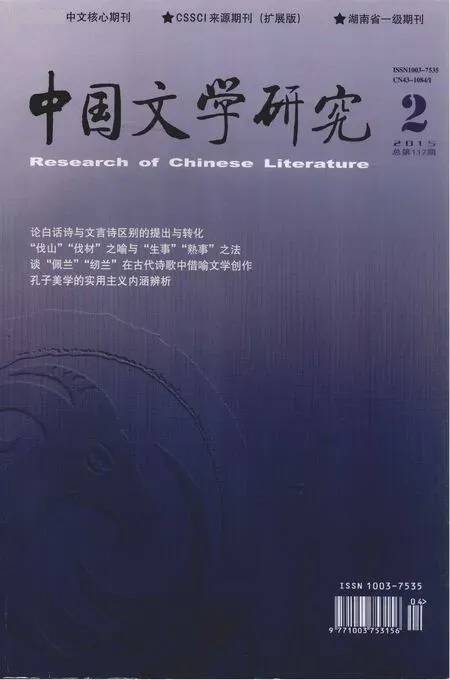战争叙述的启蒙追求与民族历史化实践——满族作家庞天舒战争小说
2015-11-14范庆超
范庆超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对中越边境战争的反复书写,国内的军事文学创作一度出现劳顿疲惫的状态,在题材开掘上举步维艰、难有新意,“80 年代的作家们在反映边境战争上,已经从诸多方面把它榨取殆尽”。面对这种情况,庞天舒能够主动调整创作姿态,结合自己对战争的深度理解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储藏、同时凭借一名满族作家的民族热情,开始从文化、人性、民族、历史的维度开展“战争叙述”,极大拓展了战争小说的蕴含。
中篇小说集《蓝旗兵巴图鲁》、长篇小说《落日之战》《王昭君·出塞曲》《汉帝国的进攻》等作品的涌现,标志着庞天舒战争小说创作走向成熟。它们常被称为“历史战争小说”或“民族战争小说”而受到军事文学、历史文学和民族文学批评界的重视。尽管进入21 世纪以来,庞天舒的创作逐渐显出淡化民族、历史,日趋现代、主流、多元的趋势(比如创作了反映未来战争的长篇小说《陆军特战队》《特战先锋》,并涉足于生态环保、文化纪实类的流行题材,还写出许多科普人文作品),但从作品的整体质量和评论界的反响来看,此类创作还难以逾越其“民族历史战争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可以这样说,对战争的持续关注构成了庞天舒基本的创作取向,而将战争书写同民族、历史书写的有机结合则拓宽了庞天舒的创作天地。
一、战争叙述的启蒙性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庞天舒关注战争叙述的意义。通过书写战争,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这是庞天舒战争叙述的基本落脚点,亦即战争叙述的启蒙性。这种启蒙性,不仅体现在“兵书战策”的表层,更体现在“战争启示录”形而上的深层。
庞天舒的很多小说展现了成熟的战争经验和智慧,是可以当成“兵书战策”来读的。《蓝旗兵巴图鲁》写到了努尔哈赤先派“死兵”冲锋、后用“锐兵”打散明军的策略,《控弦之士》将匈奴冒顿大单于对“上兵伐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胜,不贵久”、“无考而易敌者,必擒于人”等《孙子兵法》精髓的理解展示出来,《汉帝国的进攻》更是用卫青智破茏城的破釜沉舟之举生动诠释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战争要义。这些战争智慧的艺术表达,的确让我们感到了“兵书战策”的气息。
但文学意义上的战争叙述显然不能停留于“兵书战策”的“智谋学”层次。因为战争本身是一个胶着着复杂意蕴的宽广范畴。它常会与其他因素相互勾连,诸如生命、道德、人性、情感等等。因此,战争文学的更大价值在于由战争牵发的一系列形而上的启蒙性思考。在这方面,庞天舒的战争小说用力甚深。《战争神话》中的俄木列深夜躺卧在地、仰望星空,突然对征伐产生怀疑:
我们是与大明争天下,还是仅仅为填满爱新觉罗的马褡子?如果是这样,我为何离开库伦卡勒,抛下白鹿萨里甘和沙拉甘追儿们?……他想:我原先那疯狂的热情从何而来?现在又向何而去?荒原中游动的汉人闪避他如闪恶鬼……
这是在质疑、思索战争的代价。战争取胜又能怎样?在骨肉分离、亲情离散面前,即使胜利也显得脆弱、即使胜利者也要背负“恶鬼”的道德自谴。既然战争的代价如此令人心灵不安,那么为何人类还要执着于战争?《控弦之士》用冒顿单于渗透血液的占有欲、权利欲、征服欲给了我们基于人欲层面的答案。
欲望支配下的战争,充满了冷酷、冷血的意味儿,这必将与人的血肉之情发生冲突。常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固然是一种战争所需的精神武器,但带有十足功利色彩的、不容置疑的、铁的命令和军纪不知需要踩踏、压制多少鲜活、自然、合理,甚至是基本的生命欲求。所以军纪和人性有时是矛盾的,这也是战争逻辑的一种两难。在庞天舒笔下,总可以见到对这种两难。《白桦树小屋》中的黄左无比珍视自己对于军队的誓言和承诺:“我还有重任在身,我怎么能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中而抛掉了军人赋予的使命呢?”但接下来小白娃的反问:“可你我呢?难道我们就没有誓言和承诺吗?”将爱情的责任感摆放到军人的使命感面前,这种并置给人一种抉择的两难。类似的两难还表现在《落日之战》中,“《落日之战》关于战争与爱情的描写,却有着自己的独到性。这种独到性归结到一点,就是战争与爱情的难分难舍的牵连扭结,导致了一种难于控制与预测的矛盾状态”。庞天舒意在籍此引发有关战争纪律与人性关系的深度思考。
在两难的战争逻辑中,庞天舒还表现出对英雄主义的复杂态度。试图引起人们对“英雄气”与“人气”的辩证观察。“蓝旗兵巴图鲁”、“冒顿单于”、“耶律大石”、“卫青”等英雄身上一方面显出勇气、豪气与胆气,另一方面也常常露出英雄气短的悲壮、衰残与凄凉。《落日之战》中的耶律大石,在契丹人眼中永远都不会疲倦,长期顶着英雄的光环,可在他心力交瘁的那一刻却显得如此可怜:
我累,我的的确确累了……但我不能,我甚至不敢合一眼,我怕我会睡过去,永不再醒来……夫人……只要你的眼睛永远这么安静、温暖地注视我,只要你伴在我身旁,大石就像一只鹰,不会停止扇动翅膀……
如果英雄主义需要这般苦苦的支撑、如果苦苦支撑的英雄是这般渴求那基本的“安静与温暖”,那么,战争制造的英雄是否就只剩下了理性的外壳、像陈列品或标本那样徒具观览的意义?庞天舒无疑在挑战英雄主义的的神话,她试图告诉人们:英雄主义有时只是战争名利驱使下的一种勉强维持、是压抑人性基础上的痛苦经营、是战争的负产品。这样的启蒙性思索,着实体现出庞天舒对战争话语的解剖深度。
二、战争叙述的民族化
在纵深开掘战争话语的同时,庞天舒还积极引入民族话语来横向拓展小说的表达空间。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强烈的满族女作家,庞天舒的这种选择应该是积极主动的。80年代初文学界的“寻根”热潮,以及因抵制全球化而导致的民族认同感的加强,促使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主动伸张民族意识,庞天舒也位于这些作家的行列。她曾经说:
突然有一天,人说:你是满人,你的血管中流动着马背民族蓬勃的血。心忽地苍茫了,孩子般地环顾四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儿去?重新审视先祖的历史,倾听那些遥远的记忆,这时,你是站在人类学的高度,你不是在赞颂侵略和暴行,你是去寻找那种永恒的精神,那种遗失了的马背民族的神秘伟力。
这颇可说明20 世纪末的少数民族作家其民族意识的复苏、强化,以及进行民族文化书写的动因。在庞天舒那里,对满族的书写既是一种纪念和重温,更是站在一定高度对民族精神的追寻、发掘、彰显甚至是反思。“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庞天舒是试图在十一世纪的背景下,还原满族先驱之魂魄雄姿的第一人”,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庞天舒在满族书写方面的实绩。
庞天舒小说的满族书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对满族文化的“展览性”素描、对萨满文化的生动呈现以及对满族民族精神的艺术诠释。
第一、对满族文化的“展览性”素描
为了增添作品的民族文学味道,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倾向于直观展览本民族文化,以此作为民族性阐释的“首选”。满族作家庞天舒也是如此。她常将满族的历史、语言、民俗、艺术、宗教等文化元素揉进小说,形成一种直观、浓厚的满族文化氛围。比如《蓝旗兵巴图鲁》《战争神话》中频繁出现的满语称谓、地名、人名,《落日之战》关于满族骑射、饮食、婚嫁、祭祀等习俗的多样描绘等等。这种文化素描的目的主要在于民族追忆,是民族亲缘感、自豪感驱使下的自觉行为。它们作为一种铺垫性的工作,为民族书写的深入开展提供了素材和文化场域。
第二、对萨满文化的生动呈现
在满族文化的展示过程中,庞天舒对于满族古老的宗教形态——萨满教,表现出格外的关注,并予以生动地表现。由于萨满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民间文化样态,所以庞天舒在表现萨满文化时特别注重从满族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当中汲取营养。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民族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本来就存在着亲缘性: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共同处在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中,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而产生,是作家书面文学创作出现以前具有全民性质的唯一的文学样式……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和重要载体,民间文学不仅哺育作家的成长,给作家以多方面的艺术熏陶,而且直接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
庞天舒战争小说中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显然脱胎于满族民间的“萨满教文学”(如萨满神歌、古曲等)。《蓝骑兵巴图鲁》曾写到这样一个情节:每逢战争、灾害来袭之前,柔顺的狼毛突然会竖立起来,这明显带有满族民间传说的味道,是萨满教“万物有灵”观的民间变种。此外,这篇小说还对萨满祭祀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萨满作法的场地、环境、器具、配饰、具体活动、吟唱的歌词都在不断变换,类似于“上刀山下火海”、“呼风唤雨”、“穿越古今”、“神灵附体”等奇异场面也多有出现,烘托出神秘的满族宗教文化氛围。
应该说,依托萨满文化描写凸显神性是庞天舒民族历史小说的惯用手法。作家试图通过这种象征性描绘,引导人们走向满族精神文化的原始深处,去思考民间信仰是如何烙印在满民族精神的嬗变历程中。这是一个宏大的、艰巨的、甚至是难以把握的工程。尽管从字里行间,我们已经依稀感受到一些“局部性的成功”,但由于这种架设本身的难度,以及作者思考得尚未成熟,所以有关萨满教的神性描写只能更多流于文化展览或是炫奇,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尽管小说赋予萨满教以斑斓的色彩,但是它作为小说中文化风俗描写不可缺少的部分,却多少游离于小说所提供的深刻反思的主线。浪漫的传奇给人以绚丽,却多少冲淡了厚重”。这当然包含着对萨满教描写的误读,但至少反映出庞天舒还没有更明确地揭示萨满神性描写之于小说主题表达的象征性意义。即便如此,这些描写已经显出“斑斓”、“传奇”、“绚丽”的色彩,足以使小说笼罩在一种丰饶多姿的满族文化氛围之下。
也许是出于萨满描写的惯性,庞天舒还时而写出“天人际会”的相通(或许受到萨满于神人间“沟通”的启发)。《王昭君·出塞曲》一开始便显出萨满教的痕迹(尽管是非满族题材),小说设计了昭君在月夜降生、给秭归带来丰收的传奇情节,秭归的乡亲们感受到了上天的美好用意:
这晚的月亮实在是好呵,澄明瓦亮地挂在穹空为劳作的农人照拂着,人们直起腰,举目向上,辽阔天空,长空深处,人们似乎感到了某一位大神的亲切目光,哦,神在注视登坪村的人们。
这显然在强调“天人际会”的默契状态。而且,小说还不止一次地写到人向神的虔敬祈祷,比如匈奴百姓向天神的感恩敬拜,那种郑重的深沉和火热的感情,正是对神的一种呼应,这种呼应令王昭君感到血液沸腾,“情不自禁地加入那澎湃的合唱”,人性融入了神性的怀抱。从此以后,昭君的每一次重大决定,无不重视从神那里获得应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感到神与她同在:
明月之光照耀着她,神圣的天父正以它慈祥的目光在注视她。宁胡阏氏忽然有了一种贴近上天的奇异感觉……她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仿佛正在投入天父的怀抱……
在死亡的背景下,想象人性和神性的这种相遇,无疑具有更大的神秘性与超越性。
第三、对满族民族精神的艺术诠释
除了萨满文化描写,庞天舒还诉诸笔墨透视满族的民族精神,这无疑是庞天舒“民族化”叙述实践的重心。她从发掘满族的精神“正能量”开始。《蓝旗兵巴图鲁》仅从题目当中便折射出一股英雄气,在具体的战事活动描写中更是极力凸显满族上升期的那种勇敢、韧性、粗犷、强悍、拼搏进取的精神气质,“这野气与满民的发祥地长白山也许有着某种神秘的沟通。那神山定是将岩石的坚硬,冰雪的冷酷,大森林勃发的生命力,还有仙药人参的奇功汇于一股,滋长在每一个后金兵的身上”对于满族的这种精神“正能量”,庞天舒格外地看重,并尽可能地去强化和彰显。在那些书写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比如古羌、匈奴等)的篇什当中,我们看到庞天舒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这些民族精神性格当中的“正能量”。《古羌热血》这样写道:
你不能不感到蕴藏在这个远古民族的血液中那股柔韧与顽梗,那就是西部地壳深处涌荡的力量,是古老的地台,是不老的山脉,是永恒的冰川腾生的力量,它让土地之上的长河奔流不止,让荒漠尽头的大湖死而复生,让古老的羌血滚荡沸腾,生生不息。
《王昭君·出塞曲》也有类似的笔致:
一串串有力的异族语音在昭君的耳畔盘旋,携着一股蓬勃的热腾腾的生命力,这百余名匈奴人,男人和女人的声音汇成一股飞扬天地的长风……
他们要把自己的骨头造硬,让周身泛起热腾腾的火力,然后走向风雪。
不错,大单于的脊骨折断了,他的气力游散了,他不再能挽弓取马,不再能站立起来,但他却有强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走向死亡。
据此我们可以提取出诸如“顽韧”、“奔流”、“腾生”、“滚荡”、“蓬勃的力”、“勇气”、“坚忍不拔”等“正能量”,它们与满族的精神“正能量”是何其相似!北方少数民族固然存在着精神气质的相似性,但竭力将这种相似性进行反复重写和大规模渲染,是否带有作家的某种特殊用意?很显然,作为满族作家的庞天舒,其笔下的民族书写最直接的服膺对象应该是其所属的民族。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庞天舒出于兴趣、情结和开拓题材领域等需要,进行了满族以外的民族书写。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使她自觉地将满族的精神“正能量”嫁接给其他的北方少数民族,进而达到烘托、凸显、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之目的。
当然,庞天舒所理解的优秀的民族精神还不止于“勇武、强悍、坚韧、顽强进取”等“力”的层面,还包括满族的文化胸襟、眼光等“智”的素质。作为一个发轫于白山黑水、社会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少数民族,满族能够入主中原并一度开创盛世局面,与他们主动吸纳汉族文明密不可分。这种对先进文化的归趋,正折射出一个不甘示弱的民族修补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的信念和理想,以及他们对于民族文化融合大趋势的直觉性判断。庞天舒显然同满族这种宝贵的精神素质存在呼应,《生存与繁衍》艺术化地想象了马背民族是如何尽释勇悍、像学生一般凝神静听儒道哲学的动人情景;《王昭君·出塞曲》曾不止一次地凸显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灿烂文明的欣赏和向往之情,甚至虚构假想了呼韩邪单于之子伊屠知牙师取经于汉地、意欲通过农耕文明改造匈奴游牧传统、进而实现繁荣昌盛的美好局面,这些都是对满族师法汉族先进文明的间接肯定。而且,满族主动学习汉族的姿态也势必符合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历史大趋势。庞天舒作为一个满族镶蓝旗的后裔,对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与她的老祖先深有共鸣:
当今的世界各个民族就是历史上的民族、人种相互融合的产物,民族文学也必然如此,必然优势互补,比如我自己,虽然身为满族,却是被汉文化养育大,长成之后再重新走入民族历史,血液深处的记忆被一点点唤醒,开始去写我的民族。因此,我本人的创作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庞天舒何以在《龟兹岁月》里那么强调胡风胡韵对于大唐文化的重要影响。在她看来,大唐文化中的开放和率真、铿锵与雄健、狂放与豪气正是融合了西域胡乐的因子。也就是说,汉文化因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积极介入而变得更精彩、更具包容性、更有中华大文化的开放景观。这样的意旨出自于满族作家之笔,难免会让人联想庞天舒凸显满文化在丰富、充实汉文化乃至中华文化方面之作用的特殊用意。但民族文化交融毕竟是一把“双刃剑”,它造成了文化的彼此吸纳与共存共荣,同时也很容易导致“彼此的失去”,“在《落日之战》中,作家通过女性命运的遭际来反观民族发展的事实:融合与排斥”。很显然,庞天舒已经察觉到了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悖论现象。那么,她也同样会意识到满族文化在与汉文化融合的同时必将失去自我的某些原初特质。比如作为北方马背民族与生俱来的那种刚健勇武的初民精神。这种宝贵的“初民精神”、“猎人文化”很可能被“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所改造。《蓝旗兵巴图鲁》塑造了巴布阿形象。这个形象凝聚了满族没落期八旗子弟的负面素质:丧失尚武精神、萎靡不振(满敦王爷雇人替巴布阿参加骑射大赛,巴布阿整日抽大烟连拉弓的气力都没有),强烈的等级身份意识、阶级压迫观念(认为自己高贵,靠权势和地位强夺佟家小庙的小狗)……庞天舒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审丑”来宣告满族上升期的骨气与血性已经荡然无存!批判反讽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悲戚。但悲戚并不意味着绝望,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促使庞天舒努力呼召、寻回那宝贵的、带有原初意味的“血性”、“刚强”、“顽韧”、“力”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为此,她着力描绘了野萨满的形象,凸显了民间的、原始的神奇伟力,表达对庙堂化与程式化的疏离与抗拒,并试图再一次引发我们对满族精神“正能量”的共鸣以及对其渐行渐远的惋惜与思考。至此,庞天舒完成了对满族民族精神的透析,在“肯定——否定——肯定”的循环与轮回中勾勒出一条满族精神的演进轨迹。
三、战争叙述的历史化
庞天舒笔下的民族战争多为古代历史中的战争,所以作家可借助战争叙述的契机一遣历史情怀。这其中包括对历史的认知、艺术化处理、感悟与揣度等。
从《落日之战》《汉帝国的进攻》《王昭君·出塞曲》等小说的内容来看,庞天舒十分注重对历史的认知,倾向于搭建较为清晰、明确的历史框架。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往往都有相对确凿的史料支撑。如《落日之战》,无论是后金征辽灭宋以及西辽复苏、崛起、灭亡的大背景,还是故事中的耶律淳、耶律大石、完颜阿骨打等历史人物的活动,亦或是黄龙府、鸭子河、夹山等具体的事发地,都主要以《金史》为依据。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据《金史》记载……”云云,固然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造就‘真实感’的艺术传达方式(或手法)”,但也可视做庞天舒积极借鉴史料的证明。
和许多优秀的历史小说家一样,庞天舒并没有拘泥于历史,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大胆发挥艺术想象,尤其能够结合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思考与情感体验,对历史进行了艺术化处理。这包括对历史的传奇化、浪漫化、诗化。传统的历史文学往往喜欢板着面孔说话,而庞天舒的小说则竭力让历史鲜活起来。《蓝旗兵巴图鲁》写到皇太极谋害袁崇焕所使用的“反间计”,这一广为人知的史实被庞天舒设计成“珠狼毒草”。整个过程布局精密、扣人心弦,这其中不乏作者的艺术虚构与夸张,但传奇化了的“反间计”确实显得更加有趣。类似的处理还表现在《汉帝国的进攻》中,卫青和汉武帝的相识被庞天舒理解成一种偶然,而历史往往就是必然中充满了偶然、偶然中充满了必然。所以对这种“偶然”的假设并不违反历史的逻辑。如果没有馆陶长公主帮助女儿阿娇与卫美人争宠、设计陷害其弟卫青,如果没有卫青的好友、皇帝的近侍孙敖劫法场,继而密奏汉武帝,恐怕卫青就会与汉武帝擦肩而过,历史上就不会有伟大帝王与将军的相遇。这样的想象充满了奇思,在不违拗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对历史的细节和逻辑进行了艺术化的填充和假想。
这种艺术化的处理有时还显出浪漫和诗意的格调,《文明布道者》追忆文成公主入藏时的心境,是在赤岭登高、东望长安、河流西去的诗性氛围下展开的。《母性草原》对草原文化的寻根,是建立在对盘古神话浪漫解读的基础之上的:
北方草原就那么坦荡、空旷、没遮没拦地延续下来了,带着盘古仰躺的姿势和人类始祖那横亘万里的浩瀚苍茫的巨大神情延续下来。
对历史的浪漫化与诗化,离不开庞天舒个人对历史的主动渗入。她常把个人的感情、艺术性情赋予给历史中的人事,以一个女作家的心智去感悟、揣度历史。很多被史学研究忽视的、或者说是很难介入的环节,经过庞天舒的感悟与揣度往往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比如对历史女性行踪心路的把握,便是对严肃的史学研究的一种另类的充实与丰富,并为历史研究提供人性化的文学参照。在《王昭君·出塞曲》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庞天舒“用文学填补、充实、感悟历史”的不懈努力。关于昭君出塞,史载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出塞后的生活,更因匈奴的无文字而鲜有记录。从汉家典籍只言片语的记述中,仅可得知昭君先后嫁给匈奴父子两代君王,并育有一男两女。这段历史的断层无疑留给文学更大的阐释空间。而且,昭君入塞后的生活也一定是她生命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因为她要适应陌生、艰苦的环境,接受胡俗、融入草原,“在大草原上,她完成了一个年轻单纯的汉家女儿到一个情感饱满的女人、妻子和母亲的过渡”她也甚至要为和亲使命忍辱负重,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精神重压。这些极有可能发生的心理机制需要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用心灵去体验、把握。庞天舒就是那个与昭君心灵相通的女人。从昭君入塞之初喝奶茶、饮酒吃肉的心理变化,到对匈奴生活方式的思索、接受与欣赏,再到痛失前夫、忍受“子蒸其母”的侮辱、再嫁其子的内心挣扎……每一种对昭君心灵的揣度都显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为之动容。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庞天舒结合自己的人格以及对母性、责任、道德、尊严的理解,对历史上的王昭君进行了精神的修饰、完善与升华。使得王昭君不再是一个概念化的“和亲使者”,而是一个能够启发、健全现代人的生命意识、使命感、道德观的历史形象。这样的历史翻新与重释无疑具备了较高的现代价值。
〔1〕张志忠.强化与超越——略论90 年代战争文学的新趋向〔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1999(1).
〔2〕庞天舒.蓝旗兵巴图鲁〔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
〔3〕庞天舒.白桦树小屋〔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4〕周政保. 关于战争与爱情的故事——庞天舒长篇小说《落日之战》评述〔J〕.当代作家评论,1995(6).
〔5〕庞天舒.落日之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庞天舒.踏上神秘之旅〔J〕.当代作家评论,1995(6).
〔7〕朱晖.《落日之战》琐谈〔J〕.当代作家评论,1995(6).
〔8〕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黄国柱.民族军事文化意识的高扬——评《蓝骑兵巴图鲁》〔J〕.当代作家评论,1991(4).
〔10〕庞天舒.王昭君·出塞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庞天舒.汉帝国的进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12〕庞天舒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答〔J〕.南方文坛,1999(1).
〔13〕田泥.谁在边缘地吟唱?——转型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写作〔J〕.民族文学研究,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