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咏叹”
2015-10-15卜大炜
卜大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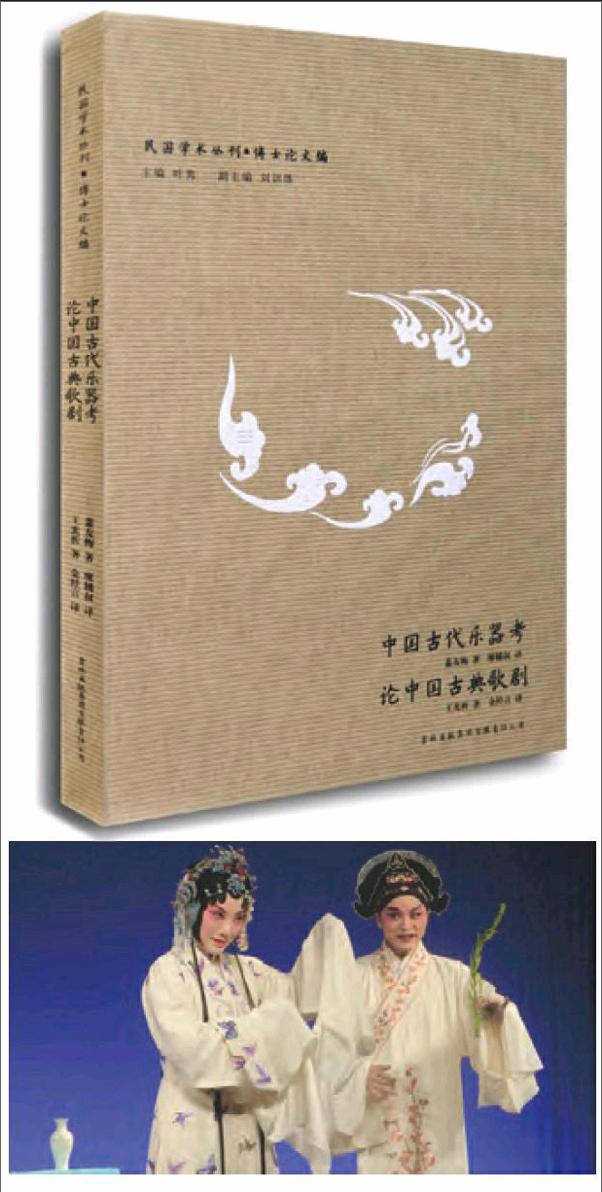


民族歌剧自信的苏醒
2011年4月,文化部主办的第11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开幕音乐会暨澳大利亚文化年闭幕音乐会在保利剧院举行,在北京交响乐团的伴奏下,澳大利亚国家歌剧院的美声歌唱家与中国京剧、昆曲名家联袂演绎了“中澳之夜——歌剧对话京昆”的主题。音乐会上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进行“对话”,西洋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唐乔瓦尼》和《弄臣》中的咏叹调与中国京剧、昆曲传统戏《铡美案》《锁麟囊》和《吕布与貂蝉·小宴》中的唱腔穿插演出。最后与普契尼歌剧《波希米亚人》中的咏叹调一起压轴的是于魁智和李胜素搭档的现代京剧《大唐贵妃》选段,取材于梅兰芳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名剧《太真外传》,融入了歌剧、舞蹈、交响等艺术表现手法。类似的“对话”也曾发生在2014年9月柏林举行的欧洲青年古典音乐节上,苏州昆剧团上演了中国明代昆曲《牡丹亭》中《游园》和《惊梦》两场折子戏,德方则上演两场早期意大利歌剧一幕情歌剧。
如此的“对话”在当今的音乐舞台上经常以各种形式出现,这些“对话”性质都是尝试对我们民族歌剧的寻根溯源,意在表明中国的传统戏曲与西洋歌剧均为各自文化领域里的音乐一戏剧最高表演形式。我国早期音乐学家王光祈在《论中国古典歌剧》一书中提出:“昆曲就是中国的古典歌剧”。如果将以京剧一昆曲为代表、集诸多地方戏剧种的戏曲赋予中国古典歌剧的意义,那么从京昆到新歌剧《白毛女》到今天的中国原创歌剧不就形成一个有源有流的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演化链吗?尽管戏曲与我们当代歌剧在形式上相去甚远,但这个演化链足以促使我们民族歌剧自信意识的苏醒。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中国歌剧创作
如果这个演化链成立,那么从戏曲到《白毛女》之间又似乎缺少了一环,这一环应该处于中国近代时期。
千百年来,中国古典歌剧——戏曲也一直在进行着改革和渐变,明代魏良辅革新昆腔,清代徽调、汉调合流为京剧。中国古典歌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鼎盛时期,以“京·昆”为代表包括各地方戏剧种在内的戏曲,其程式性达到了高峰。中国的古典歌剧本应该也像西洋歌剧那样,经过解构阶段一路发展为中国的现代歌剧,但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的外来文化入侵、文化裂变和社会转型,中国古典歌剧所依存的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新的文体和文化“语境”与古典歌剧的声乐形态无法匹配了,原有的古典歌剧形式无法和新文化对接了。因此,中国古典歌剧没能蜕变为现代歌剧,被迫终止了“进化”程序,“定格”为“国粹”——戏曲。
中国经历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基因突变,迫使汉语产生了巨大的裂变,我们的母语从文言文进入到白话文。我们甚至阻挡不住外来文化的入侵。例如国家广电总局在2010年4月下发通知,要求央视等媒体尽量屏蔽英语缩略词,转而使用中文全称或添加中文解释,然而却无法剔除央视台标中的英文字母“CCTV”。我们根据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成功后,近两年又进行了重拍,而重拍时都对来自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那些源自古典戏曲的一些表现手法进行了解构。因此,我们身处一个传统文化加速解构的时代。今天,我们一直处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中,至今没有完成两种基因的充分融合,仍处于不融合的困惑之中。我们的思想也已经融入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已经不是一句“天人合一”就能解释一切了,演绎法更多地取代了归纳法,这说明我们的大文化肌体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我们身处一个传统文化加速解构的时代。我们一直处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中,至今没有完成两种基因的充分融合,仍处于这种不融合的困惑之中。
同样,我们的音乐也是“华洋杂处”。自1840年中国近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后,一切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符号受到挤压,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白话文中的西方文化符号相碰撞,无法完全沿用中国古典歌剧的程式性套路,无奈之下大小调体系被引入,这种引入对冲和稀释了中国古典歌剧凝练的音乐,多声部、“无调性”无孔不入。这样。我们的新歌剧创作同样处于文化困惑之中,也就是民族歌剧在创作中产生了两种审美的对置——民族化和西洋化的问题。
中国民族歌剧演化链上的对接
所幸,在我们民族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一“进化”程序的中断没有经历太长的时间,我们现代史中的前辈艺术家便以自己创新性的艺术实践对中国古典歌剧进行了解构和发展,这就是作曲家马可为首的几位作曲家合作谱曲的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跨越了“相对论”的时空阶段,直接进入或说开创了中国现代歌剧阶段。《白毛女》解构戏曲的板式将戏曲音乐戏剧化,创立了“板腔体”,开创了中国民族歌剧的新纪元。《白毛女》的声乐形态是站在新文化和现代汉语的角度,因此称之为“新歌剧”。它将中国戏曲唱腔和民歌元素与西洋歌剧咏叹调等形式熔为一炉,从而与中国古典歌剧的声乐形态进行了成功的对接,这种对接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声乐写作形态的成功典范。
《白毛女》的成功并不是探索的终点和唯一出路,《白毛女》的诞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探索之门。其后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新歌剧进行着探索。这些新歌剧大都引入了和声和多声部等源自西方的写作技巧,但在新的“声腔”也就是咏叹调旋律写作方面的探索是艰难的,因为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与我们固有的语言、语音体系存在裂隙,夹杂着外来文化影响的文本及文体似乎需要外来调式相配,却又与汉语语音的四声及方正的节奏形成无法回避的矛盾。于是人们尝试用不同风格的写作形态来弥合这种裂隙。由于《白毛女》的诞生,使得戏曲音乐在其后年代的新歌剧创作中得到一席之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原创歌剧中的板腔体唱段以浓郁的戏曲音乐风格唱遍大江南北,这些中国新歌剧因充满戏曲音乐元素而广受欢迎,如《白毛女》的秦腔和河北梆子,《小二黑结婚》的山西梆子,《柯山红日》中的藏剧,《洪湖赤卫队》的汉剧,《江姐》中的昆曲、四川清音和甬剧等。这些作品在中西音乐手法的交融中既有对中国传统音乐核心价值的保留,又有对传统戏曲音乐程式性的进一步解构。通过速度、节奏、旋律的扩充或缩减等变奏手法演化出一系列不同板式,体现人物戏剧情绪的发展。歌剧理论家居其宏认为:“中国歌剧作曲家在民族歌剧借鉴戏曲板腔体作为戏曲展开性的手法,这是中国作曲家在人类歌剧史上的重大贡献。中国歌剧的戏剧性思维方式与西方完全不同,马可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不止‘一黑一白与‘四红,铸就了中国歌剧的辉煌,当时任何舞台戏剧的成就和影响都没有超过中国歌剧。新时期以后,中国民族歌剧还是有了一些发展。《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两部都是在借鉴了戏曲板腔体的基础上创作发展的。”笔者连续观看了2013年和2014年两届总政歌剧团青年演员的年度业务汇报音乐会,音乐会上每人选取一段歌剧咏叹调或音乐剧唱段,大多数演员选取的都是中国作品,在诸多各种风格的咏叹调中,民族风格浓郁的板腔体作品今天听来仍然独具艺术魅力。
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京剧现代戏是一场对传统戏曲的革命,虽属戏曲暨中国古典歌剧的写作形态,却局部融入了西洋歌剧咏叹调和歌曲的元素。革命是从现代京剧《沙家浜》开始的,其后连续出现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和《磐石湾》等现代京剧,均配有西洋管弦乐队,配器越来越丰富,唱腔越来越富于歌唱性,《海港》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具“歌剧性”的一部。“细读了全会公报”一段,将传统京剧板式进行扩充,创新出“西皮宽板”,对人物情感的发展做出戏剧性处理,音乐听起来宽广舒展,全曲从调式调性都具有时代感,便于咏唱,非常优美;加上伴奏部分单管制西洋管弦乐队,配器色彩丰富,成为一曲清新的“戏曲咏叹调”。这种创作从客观上看是古典歌剧形式向新歌剧形式“对接”的尝试,是促使中国古典歌剧进入现代歌剧阶段的实践,又似乎意在将我们民族歌剧演化链中缺少的一环补上。
但是。历史真实感和艺术真实感的统一也是歌剧创作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看到,30多年前人们创作的那些现代京剧,尽管像“细读了全会公报”这样的名段已经非常“咏叹调”化了,但近些年来很少有人再用现代题材创作京剧了。因为,古典歌剧形式写成的“现代戏”无法使人将历史真实感与艺术真实感重合起来,“样板戏”的“旧戏”形式无法与“新文化”社会的文本环境相适应,现实主义题材无法套用古典歌剧的体裁。回想当年,梅兰芳也曾以“移步不换形”的方式尝试时装京剧却以失败告终。《白毛女》之所以成功,就是选择新歌剧的外在形式表达新文化的文本,站在这个角度与古典歌剧外在形式对接,因此成功了:而京剧现代戏选择中国古典歌剧外在形式表达新文化的文本,站在这个角度向新歌剧外在形式反向对接之路无法走到底,只能昙花一现。
近些年,音乐会舞台出现了又一波以“跨界”名义进行京剧与交响乐融合的实践,以古典戏曲的全新形式向新歌剧形式对接。2009年5月,第九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中的重点项目交响京剧音乐会《国韵华章》,迟小秋等12位新老梨园名家登台北京保利剧院,首次集中回顾中国交响京剧成就,上演一台集聚传世名段与现代红色经典的京剧交响音乐会。曲目除上述的京剧现代戏选段外,更有传统京剧《夜深沉》《锁麟囊》《苏三组曲》《铡美案》《贵妃醉酒》《四郎探母》中的名段以交响化编配呈现,非常令人惊喜。2010年,中国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东西方在歌剧中相遇:京剧与西洋歌剧咏叹调选萃》,京剧表演艺术家演唱传统京剧《铡美案》《贵妃醉酒》《甘露寺》等选段,京剧配乐与交响乐完美融合,令观众赏心悦目,现场京剧票友鼓掌非常热烈。2011年,上海大剧院联合上海京剧院、上海交响乐团推出上海大剧院版交响京剧《杨门女将》。2012年中国爱乐乐团推出了京剧交响乐《贵妃醉酒》。
这一波最具典型性的实践当数2009年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制作的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该剧汲取了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并引进了西洋歌剧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使用了二声部和三声部的轮唱及合唱,使用了管弦乐团,这样就用到了和声与复调来与京剧的板腔体结合,使之更活跃。让观众一听就知道是京剧,但又感觉非常新鲜。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一波促使中国古典歌剧现代化的实践看作是当年“样板戏”忽略了的一个方面,即以古典歌剧形式表达古典题材,从而达到了历史真实感与艺术真实感的统一。2009年,还有台湾来的京剧《弄臣》更是歌曲式的京剧,也属同样的实践。
其实,《白毛女》一《赤壁》,就是现代歌剧的“板腔”化和戏曲的“歌剧”化这两种倾向的相向而行。
中国风的咏叹调
歌剧《白毛女》对中国民族新歌剧起到了开一代之风的奠基作用。2009年,《白毛女》由中央歌剧院在人民大会堂再现,这是封存了30多年后的再现,但是这次演出没有对这部历史经典画上句号,其后陆续在各地引发了其他的制作,它已经不仅是一部民族歌剧的图腾,而是一部极具欣赏价值、常演常新的经典。从《白毛女》今天焕发出新的光辉,看到这部浓郁民族风格的歌剧具有巨大的前瞻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西洋经典歌剧不绝于耳的今天听起来,《白毛女》的那些咏叹调是多么动人呀!艺术手法是多么超前呀!
《白毛女》使用了许多中国地方戏声腔元素,例如咏叹调《刀杀我,斧砍我,你不该这么糟蹋我》中的秦腔悲调的元素、《我要活》的河北梆子音调等。第四幕中喜儿的咏叹调《恨似高山愁似海》一段,出神入化运用了秦晋冀地区典型的旋律流动方式和节奏、板式风格。《白毛女》中一些唱、念相间的乐句,似是咏叹调和宣叙调相交使用,成为一种优美的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形式。这些唱段在声乐方面有着较高的难度,对我们今天的歌唱家来说仍具有经典性。作曲家还将民歌和戏曲的音调和唱腔做了歌曲化的处理,其中著名的唱段《北风吹》唱红了全国。歌剧《白毛女》之所以说它“新”,除因内容表达了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现实生活,还因为它融会了民歌、戏曲音乐和西洋歌剧咏叹调手法,将戏剧性融入音乐中形成新歌剧的“板腔体”咏叹形式,这与格鲁克的歌剧改革理念异曲同工,也是对中国戏曲音乐的一种提升。《白毛女》复排重新进入我们观照的视野,正是我们对中国古典歌剧的追索之下中国古典歌剧的传统核心价值在我们心中的苏醒。争相上演《白毛女》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对民族歌剧的创作日趋理性,从而才重新认识到《白毛女》那非比寻常的艺术价值和无比深远的启示性意义。
2001年10月,一台名为“东方的咏叹:太阳出来了”音乐会在北京上演。音乐会的发起、组织、主持者是女高音歌唱家——第三代“江姐”扮演者金曼,她在音乐会上演唱了大部分曲目。这台音乐会汇集了六七十年代京剧现代戏中的经典唱腔,但“解构”了配器中的“四大件”(京胡、京二胡、板鼓、锣等传统京剧中的“文”、“武”场乐器),丰富充实了交响乐队的手法:同时在声乐表演形态上以美声为主,融入民族与戏曲的特色,保留京剧演唱的韵味,以“歌剧化”的方式来表演30年前创作的中国古典戏曲形式。这台音乐会无疑意在促使东西方两种歌剧形式的结合,打破西方人无法逾越的中国古典歌剧的异质外壳,借以打开一条让中国古典歌剧通往世界舞台之路。这台音乐会又反映了人们急迫地希望中国古典歌剧与新歌剧对接、新歌剧向中国古典歌剧对接的潜意识。音乐会名称中的“咏叹”一词,意在探索中国式歌剧咏叹调,更向我们发出强烈的信号:人们在呼唤建立中国民族歌剧艺术形式的新审美,这种审美应该建立在中国古典歌剧审美之上。
2003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了郭文景的原创歌剧《夜宴》和《狂人日记》。《夜宴》打破了和声的框架,《狂人日记》消解了大小调性,两部歌剧都从现代作曲技法出发,却以戏曲的面目出现。突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线性思维,在音乐形式上模拟出中国戏曲唱腔的神韵。
关峡2004年创作的民族歌剧《木兰诗篇》,运用了许多典型河南豫剧音乐的特色音程、旋律、乐句收束方式,还有意识地融入了如道情、曲剧和二夹弦等音乐元素,形成极强的河南民间音乐特色,融化弥漫在音乐中,再充分调动发展和再现等作曲手法的效果,音乐充满动力性的发展,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又有清新的现代气息,形成“戏曲风格咏叹调”。这种“戏曲风格咏叹调”手法提升了戏曲音乐和地域音乐,同时又比板腔体手法更为自由,更便于音乐的扩展,使得剧中人物的情感得以更为淋漓尽致的抒发。该剧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演出获得“五声音阶浪漫主义”美称。
2010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的作曲家叶小纲的《咏·别》,剧中大量设置了京剧的场面,甚至将京剧《霸王别姬》的场景作为戏中戏来呈现。作曲家在声乐写作部分解构了旋律,而在乐队写作部分则呈现精致华丽的五声写作很有特色。
以上几部中国歌剧不约而同地以京剧作为创作的切入点,都从京剧汲取创作灵感,这说明对于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者们来说,向中国古典歌剧对接这一命题,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中。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古典歌剧一戏曲音乐在新歌剧创作者心中的重要分量,他们都力图从戏曲音乐中找到立足的支点。当然,新歌剧向中国古典歌剧对接,汲取古典歌剧的传统,需要有度,需要解构,进而建构出新的咏叹风格。
综上所述,古典题材的新歌剧如果采用新歌剧的形式。音乐上便于产生更丰富的发展,而现实题材的歌剧如果不融入中国古典歌剧的核心价值体系,便无法满足人们的民族审美期待,因为我们歌剧中使用的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它仍含有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余韵。因此中国当代歌剧和戏曲应该寻找到一个审美对接点,中国歌剧流派形成在这个点上,这里就是我们民族歌剧的审美期待所在。本文认为,从当代艺术文本与中国古典歌剧的对接点应该是一种能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形式,“戏曲风格咏叹调”等形式的手法是尝试创造中国现代新歌剧“东方咏叹调”途径之一。
中国风的宜叙调
宣叙调是西洋歌剧中一个强有力的艺术手段,它如同芭蕾舞剧中的场景音乐一样,其外形是交代剧情的发展,而本质上是推进戏剧矛盾的发展。歌剧在意大利的初创时期,剧中只有大量的宣叙调,还没有咏叹调,咏叹调是后来在宣叙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宣叙调与意大利语相配极为熨帖。莫扎特的歌剧大部分是意大利歌剧,他写意大利宣叙调得心应手。而他在后期使用自己的母语德语创作的《魔笛》,或许是为避开意大利式宣叙调,则采用了带对白的德国民族歌唱剧(singspiel)。瓦格纳的德语乐剧不分宣叙调还是咏叹调,成为了一种一唱到底的“无终旋律”,或许也不排除瓦格纳有刻意规避意大利宣叙调的初衷。到了普契尼等人那里,有了宣叙调与咏叹调界限模糊的所谓咏叙调。其实,无论是无终旋律还是咏叙调,本质上都是将宣叙调更加旋律化。对于中国的民族歌剧来说,宣叙调音乐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些翻译成中文的西洋歌剧,宣叙调成为了“鸡肋”,因为音乐是按照原文的语言特征谱曲的,用中文唱不仅使音乐失色,甚至唱起来拗口,听起来逆耳。那么中国民族歌剧的宣叙调音乐是为中文谱写,就能一蹴而就吗?未必如此,因为歌剧是外来艺术形式,它带有先天的它文化异质外壳,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与传统戏曲的韵白、念白既相异又相通的说唱形式,来打破这种外壳,使得群众能喜闻乐见。中国歌剧的宣叙调音乐,如果曲作者没能把握好中国语言的音调特征和音韵,那么创作出来的宣叙调也无法令观众接受和欣赏。在西洋歌剧中的喜歌剧或轻歌剧中是用说白或对白来交待戏剧发展情节的,而在正歌剧或大歌剧中则用宣叙调来完成这一功能。中国传统戏曲中有“念”的形式,也就是韵白或念白,“念”虽不是唱,但又有别于说白: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骚,在古代是用来入乐唱的,如今唱的方法因没有曲谱记录而失传了,但可以用“吟”的方式,这种“吟”也不同于今天的所谓朗诵。我们的民族歌剧如果要借鉴西洋歌剧的形式采用宣叙调,那么这种宣叙调则要找到一条“念”和“吟”之外的路子,但又要符合中国语言的特征和习惯,符合中国人在音调上的审美习惯。
新中国的第一部美声歌剧《草原之歌》就开始了对宣叙调的探索,我们的歌剧创作者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艺术手段的重要性。《草原之歌》运用了对白,同时,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对此前的一些歌剧指责是“话剧加唱”,曲作者又在这部歌剧中尝试着使用了部分的“朗诵调”,我们可以从广义上将这种形式归为宣叙调。
由中央歌剧院1962年上演的歌剧《望夫云》是中国第一部“一唱到底”的美声歌剧。郑律成在这部民族题材的歌剧中,对创立中国宣叙调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成功地找到了一条路。《望夫云》中的许多宣叙调巧妙地运用了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对歌的形式和音调,听起来既有别于咏叹调,又有别于说白。这些对歌宣叙调的律动与节奏、速度都是按照歌剧进行中的场景和剧情需要来设计:或抒情,或叙事,或激动,或急促,但又非常旋律化:既有宣叙调的叙事性,又有咏叹调的歌唱性,还出现了歌剧的主题音乐,在矛盾发展的关键之处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这些宣叙调——对唱的形式非常有民族特点,一听就可以联想到这些民族同胞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如劳动歌、生活歌、青年男女谈恋爱时的对歌等。郑律成借鉴了普契尼和瓦格纳等西方歌剧作曲家在歌剧中对于宣叙调、咏叙调和无终旋律的处理理念,但又不是机械地摹仿,而是运用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形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富于民族风情的宣叙调形式,构建了一个完整而有特色的宣叙调音乐体系,这些宣叙调使得全剧的音乐非常统一。这种“一唱到底”的歌剧形式当时显得有些“超前”。但在今天看来,这些探索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应该在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史上重重地书上一笔。
歌剧《白毛女》中一些唱、念相间的乐句,似是咏叹调和宣叙调相交使用,成为一种优美的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形式。这些唱段在声乐方面有着较高的难度,对我们今天的歌唱家来说仍具有经典性:歌剧《木兰诗篇》用合唱画外音形式演唱《木兰辞》来交代戏剧线索的发展和烘托情感的发展,类似中国戏曲中的帮腔和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是明智之举和创新之举。中国曲艺的说唱艺术、中国戏曲的韵白都讲究“腔从词出”,“声随字转”,也可以成为中国民族歌剧中宣叙调形式的借鉴。歌剧《彝红》则是对白与原生态演唱形式“吟唱者”并存,既有促进戏剧矛盾发展的功能又有画外音的效果。
旅美作曲家周龙的歌剧《白蛇传》获得2011年第95届普利策音乐奖,该剧因“是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为题材、以高度表达手法呈现的歌剧,并成功地将中西方的音乐传统共熔一炉”。在这部英文脚本的歌剧中,巧妙地运用无调性大幅度跳进音程的手法,让剧中人物的宣叙调听来有京剧念白的韵味,这是对中国五声性戏曲音调的抽象呈现。
结束语
前面所述中国民族歌剧演化链之“对接”就是对古典歌剧中包含的民族音乐之根的追寻,这个根就是五声性的音调,没有这个根,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中国原创歌剧中,无论是咏叹调还是宣叙调,无论是板腔体还是咏叹体,都凝聚着几代人的戏曲音乐情结,绵绵不断。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板腔体”歌剧不再是唯一的道路,人们尝试更为自由的歌剧曲体。施光南作曲的歌剧《伤逝》和《屈原》是后“板腔体”时代的标志性作品,金湘作曲的歌剧《原野》在民族风格的基础上对调性进行了扩张,成为后“板腔体”歌剧的旗帜性作品。三部歌剧都是现实批判主义文本中的新歌剧力作,都运用了现代作曲技巧,其中《原野》更强化了乐队写作对声乐推进与催化作用,但都有鲜明的五声风格。2014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团上演的歌剧《彝红》则是彝族民歌旋律与流行歌曲的架构相融合,同样形成优美动听又有时尚感的浓郁民族风格,闯出另外一条道路。这些作品虽没有引入戏曲的程式性元素,但同样蕴含了中国古典歌剧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体系——五声性音乐,正是这一体系令中国古典歌剧的演化链得以贯通。
今天,我们的民族歌剧要提高到中西方歌剧艺术对话的层面,仍有赖于对于这一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多样化的发扬。当今的新歌剧作曲家们都在自己的歌剧声乐写作中恪守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力图建立起中国民族歌剧的声乐艺术标准和艺术期望值,提升中国新歌剧的审美期望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