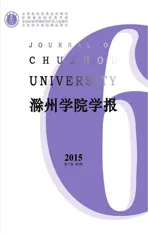欧阳修的古今之变思想
2015-09-19杨元超
杨元超
欧阳修的古今之变思想
杨元超
欧阳修在天人之间推重人事,认为决定历史兴亡治乱的是人事而非天命。决定历史变化之人事,即人情之理,其主要内容是礼义纲常和经验常识。欧阳修考察历史盛衰及历史中的常与变,都以人情之理为基本出发点。
欧阳修;古今之变;人情之理;常与变
作为史学家,欧阳修十分重视探讨历史兴亡治乱的原因。他把脉历史盛衰,往往以道德纲常为历史变化的动因。吴怀祺先生认为“欧阳修视纲常伦理为支配历史兴亡之‘道’,思考历史盛衰之理,引‘理’入史,以《易》解史。把纲常伦理的维系作为‘人理’的内涵,是欧阳修的贡献。但欧阳修的认识还不深刻,还是在现象上观察思考兴亡问题,‘人理’兴亡论失之浅也在这里。……欧阳修总结历史兴亡,不是空论人理,而是思考解决北宋的社会危机”。[1]吴先生的文章较全面地概括了欧阳修历史兴亡论的主要特点,但未及系统梳理欧氏兴亡论和欧论古今变革的具体内容,而学界其它研究欧阳修史学的论著亦未对这一问题展开充分讨论。本文延续前人的思路,对欧阳修的古今之变思想进行深入、全面地探究。
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古代,不少思想家都用天人关系来解释人世间的盛衰与祸福,有时候还用这种关系来解释历史演变的原因”,[2]欧阳修亦是如此。他以人事而非天命为历史演变的原因,并以人情之理考察古今之变,寻找历史兴衰中的常与变。
一、天命与人事
欧阳修是一个天人感应论者,这是基于古人对气化论的认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天作为人格神的有意志的行动,一种是以气为中介的感通。在欧阳修笔下,“天”有时候也有人格神意味,但那不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两种模式中,欧阳修比较认同的是后者。人和万物都由气构成,“生禀阴阳之和”,[3]1031民有怨气,阴阳就会失调,“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4]872自然界就会发生灾异。不过,他也认为,不是每个天灾都由人怨、人事造成,也可能只是自然运动。他在奏疏里屡言天谴,甚至采用阴阳五行之说,以劝谏皇帝修正政策,这并不单单是政治惯例使然,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观念。
的确,欧阳修批判过一些古代灾异祥瑞论和神怪之说,但他批判的只限于他所谓的“异端”(《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二》:“圣人既没而异端起。”)灾异论的异端,是“灾异先于人事”和“事事皆有应”的情况。神怪说的异端,是不合人情常理的谶纬、神话,以及无来由的神仙和神仙术。他坚持天人感应和他批判异端并不矛盾,坚持天人感应是强调天道与人道的一致性,在不废天道,顺应天道的前提下,才可以发挥人事的能动作用而求治。批判异端是强调灾祥无涉兴亡,德政才是根本。在天人两极之见,欧阳修的重点落在人上,继承了孔子“存而不究”、“道不远人”的态度。
欧阳修认为“人事者,天意也”,[5]706天人之理不二,而天不易知,能确切认知的只是人事。那么,人们就应该采取圣人的态度,“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3]1109“使其(天)不与于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与于人乎,与人之情无以异也,亦修吾人事而已”,[3]879重心都落在修人事上。由此,欧阳修提出“治乱在人而天不与”。
或曰:“《易》之为说,一本于天乎?其兼于人事乎?”曰:“止于人事而已,天不与也。”……问者曰:“君子小人所以进退者,其不本于天乎?”曰:“不也。……此人事也,天何与焉?……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者,《否》、《泰》之《彖》详矣。”[3]878-879
泰卦《彖》传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卦《彖》传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进,小人不得不退,天下就治。小人进,君子不得不退,天下就乱。世间的治乱只在于人本身,而不在于天。以这种观点考察历史,就会得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5]397的结论。
欧阳修有时候会沿用传统的天命随德转移的说法,“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圣贤之通论也。……然所谓天命有德者,非天谆谆有言语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则辅之以兴尔”,[6]但在具体考察历史时,他明显减少了天命的内容。据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统计,《旧五代史》至少有18处涉及天命的内容为《新五代史》所不取。[7]所谓“治乱在人而天不与”,实际上就是虚悬天命的概念,将其内容置换为人事,从而架空天命的主导作用,把历史兴亡的原因都归于人事。
从重人事出发,欧阳修强调人的能动作用。
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为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圣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时无不可为。[3]877
卦有善恶吉凶,时有治乱。按《易传》思想,即使是凶卦,圣人君子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有能动性。凶卦也可以求治。即使是吉卦,也有悔吝凶咎的爻,意味着也可能有乱时。吉凶的关键在于君子本身的作为。在《易童子问》中,他多次强调了这个思想,见表1。

表1 欧阳修论《易》理中的人事能动性
此《易》理体现在历史思想中,就是历史的治乱取决于人的能动,在适当的时机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就可以创造治世。
二、人情之理与历史变化的原因
(一)人情之理的内容
欧阳修认为,历史演变取决于人事,确切说就是人情之理。在欧阳修笔下,“‘人情’是对‘理’的具体说明,这与道学将‘情’和‘理’对置的做法不同,……人情就是 理,就是自然”。[8]55“人 情”和“……之理”这两个词在欧阳修的文章里被广泛使用,覆盖经解、政论、史论、文论各个领域,显然,在他看来,所有领域的理都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都是符合人情的,人情可知的。
人情莫不欲寿。[3]868生为可乐,而死为可哀,人之常情也。[3]708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5]408
人情之理的第一层含义,是人顺其自然的生存需求。按照儒家一贯的观点,这种需求应该是欲而不贪,是无过无不及的,要由礼来节制,即人情表现为礼。由此引出第二层含义:
夫礼之为物也,圣人之所以饰人之情而闲其邪僻之具也。其文为制度,皆因民以为节,而为之大防而已。[3]882
圣人之于人情也,一本于仁义,……圣人之以人情而制礼也,顺适其性而为之节文尔。……知仁义相为用,以曲尽人情,而善养人之天性,使不入于伪,惟达于礼者可以得圣人之深意也。[3]1873
甚矣,人之好为礼也!在上者不以礼示之,使人不见其本,而传其习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5]633
人情好礼,以礼为外在形式。礼也者,理也。其内容为礼义纲常,它不仅是道德,也是制度,是为人情之理的第二层含义。
无论是自然需求,还是礼义纲常,都是人的日常生活能够体验到的,不脱离经验和习惯,“人情应该是得到众人认可的东西,时而被当作与常识相等的概念来使用”。[8]55经验常识,是为人情之理的第三层含义。
毫无疑问,礼义纲常是最核心的含义。
(二)历史变化的原因
历史的变化是正常现象,盛极必衰,困极而亨,这是天理法则,也是人情必然。即使人事再修明,也难逃积久成弊的一天,即使人事再不修,也终究会迎来治世,这都是“势使之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事对历史变化的支配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过,在这个限度之内,人事完全可以左右兴亡治乱,这种决定性的力量就是人情之理,确切说就是道德和制度意义上的礼义纲常。这是欧阳修反思唐季五代以来的混乱得出的结论。
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5]713
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4]960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5]611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5]514
方唐之盛时,……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4]1181
夫欲民之暴者兴仁,智者无讼,在乎设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贪者守廉,在乎严督责而明科条。为治之方,不过乎是而已。[3]1040
凡治世,既有道德的遵守,又有制度的维系。制度,包括礼制和法制。
先看礼制如何发挥作用。礼的作用,不在于形式上的仪文细目,那只是礼之末节。礼之本意,在于教化人民,形成道德习俗,“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4]307三代之所以治,是因为仪文与教化合一,仪文渗透于人民的日用常行之间,“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而人自从之”,[3]866在这种风俗的浸润下,“士生其间,其势不得不至于为善也”,[3]627人民为善成为一种“势”,想为恶也不可能。
三代以后,“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礼制废弛,治国“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仅把礼的细目保存于有司,偶尔用之,仪文与教化分离,人们“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4]308礼名存实亡,风俗变得苟伪。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个别人想为善为贤,其“势”亦难。
其次看法制的作用。欧阳修持“刑为德之辅”的传统观点,“故礼防民之欲也周,乐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则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3]673礼对兴亡起决定作用,但法作为辅助,有益于维系礼义风俗。在礼义蔚然成风的时代,法的作用或许有限,在风俗未成或衰坏之时,法可以为之设防,故三王之治,亦不敢废刑,只是宽简而已。后世之民尚未知德,一旦法废,“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由积水而决其防”,[4]1407从此礼与法坏乱相乘。法本乎人情,其目的不在于杀伐立威,而在于维护道德纲常。法不可以使世治,但没有法,纲常便难以维持。
大体上,历史治乱取决于道德、礼制、法制三个要素,道德为根本,礼制主浸润教化,法制主维系设防。
欧阳修常在史论中阐发治乱问题。《新五代史·周本纪十二》提及五代父子相残,居丧、立后非礼,用俚俗和夷狄之礼,妄杀大臣,礼乐刑政大坏,而周世宗“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所以能威震夷夏。《新五代史·唐臣传四》记载李从珂造反时,信任术士张濛,濛问于太白山神,说大事可成,后果成,是为唐废帝,但他治国无能,旋为石敬瑭联合契丹所灭。欧阳修评论说“考其逆顺之理,虽有智者为之谋,未必不能败”,在这里,他实际表达了三层含义:第一,兴亡不在于神的庇佑,而在于人事;第二,李从珂造反弑君,违背臣道,是丧失礼义;第三,李从珂任用权奸,是丧失法纪。无礼义无法纪,必然败亡。《新五代史·周臣传第十九》论治乱的关键在于用人,“夫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国之君,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表面是讲用人之法,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使小人和君子各适其分,是儒家正名、分位的思想,仍然属于纲常范畴。
三、历史中的常与变
(一)历史中的常与变
客观的历史过程总是常与变的结合,司马迁以考察并解释历史中的“常”与“变”,而达到“通古今之变”。欧阳修虽不似司马迁那样明确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其考察历史的主要意图也不在于解释常与变,但他的历史思想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对常与变的认识。
历史中的“常”有两种,恒常存在的因素和恒常的支配法则。历史中的“变”也有两种,变化的现象和非常的法则。
在欧阳修看来,历史中恒常存在的因素是礼义纲常。世道有沉浮,但纲常的至高地位万古不移,对纲常的需要也万古不移。即使在人伦扫地的时代,也有忠臣孝子。恒常的支配法则即人情之理(礼义纲常)决定兴亡。
欧阳修对“变”的认识,不停留于制度损益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上的“变”,而是探究变化的规律。人道与天道一致,天地有阴阳转化,人事就有盛衰交替,天地有履霜之渐,人事就有祸患积于忽微。当社会现状达到极盛时,开始向对立方向转化,由微至著地产生一种“习”或“俗”,积习成弊,以至于极衰,这种趋势叫做“势”。极衰之后,复向极盛转化。欧阳修说的“势”,跟柳宗元说的“势”有同有异。两者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必然性,这种客观形势要求现实制度不得不损益或变革。不同的是,关于造成这种势的原因,柳宗元认为主要是失政,如不能任人唯贤之类,而欧阳修认为是礼义纲常的衰坏。
如何干预“势”,以保持长期兴盛呢?
阴阳反复,天地之常理也。圣人于阳,尽变通之道;于阴,则有所戒焉。[3]305
昔三代之为政,皆圣人之事业;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术,皆变其质文而相救。[3]293
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5]514
一方面要适时变通,盛世久而有弊,必须变通,如三代之政以文、质相替救弊。(欧谈《易》理与谈历史有一定错位。谈《易》理认为在盛时就变通,侧重预备。谈历史认为在衰时变通,侧重补救。)另一方面要防微杜渐,《新五代史》论女祸、宦官专权、伶官乱国、禁军势重,都强调戒备履霜之渐。
与司马迁一样,欧阳修也注意到“以德受命”的恒常法则时有例外: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4]1323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论者乃谓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积功累仁,其来也远,故其为世尤长。然考于《世本》,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夏自鲧以前,商自契至于成汤,其间寂寥无闻,与周之兴异矣。而汉亦起于亭长叛亡之徒。及其兴也,有天下皆数百年而后已。由是言之,天命岂易知哉!然考其终始治乱,顾其功德有厚薄与其制度纪纲所以维持者何如,而其后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坏乱,或渐以陵迟,或能振而复起,或遂至于不可支持,虽各因其势,然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岂非所谓天命者常不显其符,而俾有国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4]20
夏、商是一两代人有德,就受命了,周是积功累仁数百年才受命,汉谈不上有德就受命,唐也没有累世功德,唐高祖是“因时而特起”,只是把握时势才得以受命,但最终夏、商、周、汉、唐俱享数百年国祚。似乎支配历史兴亡的恒常法则并不灵验,这应该如何解释?欧阳修强调,虽然历代兴起时功德有薄厚,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有功德,人厌隋乱,李唐结束乱世,使人民蒙受德泽,这本身就是大功德。“汉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义而起”,[3]277取代暴秦,也是功德。而他们能够维持数百年国祚,也是施德政,肃纪纲的结果,仍然验证了“有德则兴,无德则绝”的法则。
由此也引出常与变的关系。三代以文、质相救,是以变通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持续性,欧阳修解恒卦说:“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3]1111“常”(恒久)是以“变”的形式实现的,是为常中有变。夏、商、周、汉、唐的兴起,虽有不同,但都遵循“有德则兴,无德则绝”的法则,是为变中有常。变中有常还明显体现在君子与小人的身上,《新唐书·武后中宗本纪》说:“夫吉凶之于人,犹影响也,而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于凶者有矣;为恶者未始不及于凶,其幸而免者亦时有焉。而小人之虑,遂以为天道难知,为善未必福,而为恶未必祸也”。一般来说,善人有吉报,恶人有凶报,但偶尔也有善人倒霉,恶人侥幸的情况,武则天就是恶人侥幸,这是历史中的变。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恒常的法则下,“君子之罹非祸者,未必不为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尝不及祸”,小人必无好结果,如韦后。[5]464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不是一个历史进步论者。他评价唐太宗“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4]48“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隆”,[3]2261叶适由此认为欧阳修“其言则虽以三代为是,而其意则不以汉唐为非。岂特不以为非,而直谓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则三代固不必论矣。故其制度纪纲,仪物名数,皆以唐为是而详著之。……欧阳氏之学,非能陋汉唐而复三代,盖助汉唐而黜三代者也”。[9]叶适似乎误解了欧阳修的真实观点,欧的总体论调都以三代为典范,认为后世无法达到三代盛世。他肯定后世制度,是肯定历史的变通。相对于三代,汉唐属于衰世,衰世通过制度变通,比如建立完备的法制,仍然可以为治,但这并不说明法制本身是最好的。“且夫歃血以莅盟约,要之于信者,由不信而然也;为刑以残肌骨,威之使从者,由不从而设也。……诅民于神明,狃民于赏罚,而违之者,末世之为也”,[3]866向神明起誓和刑罚是因为民不信、不从才出现的,是末世之为,是为了变通不得不如此。
(二)改革中的变与常
欧阳修总结历史兴亡,是经世致用,思考改革的理论依据,其中也体现了他对变与常的认识。
第一,什么时候改革?乘其由盛而衰时
欧阳修认为,改革的对象“患深势盛则难与敌”,必须“乘其穷极之时,可以反而变之,不难也”。[3]292
第二,怎么改?要徐徐引导,潜移默化
例如排佛复礼,“佛之说,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礼义之事,则未尝见闻。今将号于众曰:禁汝之佛而为吾礼义!则民将骇而走矣。莫若为之以渐,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渐,则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后仁”。[3]291-292在欧阳修看来,韩愈主张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行灭佛方式,是不会有效果的,古代每次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灭佛过后,佛教都会反弹。事物的变化是由微至著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第三,用什么改?用王道礼义,或者说采用古法
仍以排佛为例,“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时,虽有佛而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受患之本。”佛教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王道礼义衰落了,国人“中心茫然无所守”。要排佛,就要“修其本以胜之”“中心有所守以胜之”,“本”即井田和礼义。[3]288-290要 排 异端,必 须 依 靠常道,树 立自己牢固的价值信仰。以兵制改革为例,他认为历代兵制都“因时制变”,但变通还是要本着三代王道的主旨,后世的兵制只有唐代府兵制值得称道,因为三代兵制以井田制为基础,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其余兵制变革,都是为了一时便利,不遵循常道,所以其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4]1323
欧阳修认为变通要以常道为法,但这种常道能否适用于当代,他又是怀疑的。他所谓的效法三代,并不是机械复古。北宋不少士人热衷于恢复周礼和井田,李覯曾作《周礼致太平论》,后来王安石也依会《周礼》推动新法,李覯、苏洵、张载、二程等十分关注井田问题。欧阳修对此是质疑的。
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此又可疑也。[3]674
这是欧阳修在庆历二年给考生出的考题,当时他可能在思考新政的相关问题。抛开他对《周礼》内容真伪的质疑不说,当时他已经感觉到,历史证明古法行不通,只能继续行秦制。在十五年后针对井田的考题里,他又深化了思考。
自周衰迄今,田制废而不复者千有余岁。凡为天下国家者,其善治之迹虽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礼乐、刑政未尝不法三代,而于井田之制独废而不取,岂其不可用乎,岂惮其难而不为乎?然亦不害其为治也。仁政果始于经界乎?不可用与难为者,果万世之通法乎?王莽尝依古制更名民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恶加于人者虽非一,而更田之制,当时民特为不便也。呜呼!孟子之所先者,后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为不便,则孟子谓之仁政,可乎?《记》曰:“异世殊时,不相沿袭。”《书》又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书》、传之言,其戾如此,而孰从乎?孟子,世之所师也。岂其泥于古而不通于后世乎?[3]679
欧阳修仍然坚持师古,要奉行常道,但不能泥于古,要根据后世特点,有所变通。刘子健说,欧阳修“最重视合乎时宜的礼,换言之,即能实行的制度”。[10]土田健次郎说:“(欧认为)古代的制度实际上有很多不明白之处,所以结果便成为:依据贯穿古今的‘人情’的普遍性,来建设现在的制度。”[8]61此即欧阳修对改革中变与常的认识。
总之,欧阳修考察古今之变、褒贬善恶、疑古辨伪、讨论正统,乃至批判某些天谴论、神怪之说,有两个最主要的衡量标准,一是圣人和六经是否有言,二是人情之理。人情之理既是他的认识论,也是他的方法论。欧阳修的史观,如其文章一样,简约平易,切合人情,但这个特色也使他一直停留在经验和现象层面,缺少思辨深度。
[1]吴怀祺.对欧阳修史学的再认识[J].史学史研究,1991(4).
[2]刘家和.〈史记〉与汉代经学[J].史学史研究,1991(2).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欧阳修.诗本义·卷十·生民[A].(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四库全书·第70册[C].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58.
[7]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9-111.
[8]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M].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7:753.
[10]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4:50.
Ouyang Xiu's Thought on the Change from Antiquity Down to the Present
Yang Yuanchao
Ouyang Xiu valued human efforts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which he thought it is the personnel but not mandate of heaven that determi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The personnel which determine the change of history,also called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include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experience and common sense.When Ouyang Xiu studied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change and constancy of history,he basically started from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Ouyang Xiu;change from antiquity down to the present;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change and constancy
D092
A
1673-1794(2015)06-0006-06
杨元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
2015-07-11
责任编辑:李应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