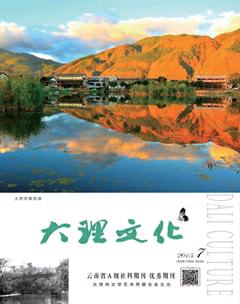六十年前第一次云龙行
2015-08-19刘傅森
搭车
沿着滇缅公路、盘旋于滇西大山间的公路,我已记不清走过多少次来回了。眼下想起的这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那时,我还很年轻,也就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小伙子,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嘉年华。
我要去的这个云岭大山怀抱中的云龙县城,只有一条刚修好的毛路可通,还上不了汽车。不过还好,小县县城距昆(明)畹(町)公路(“滇缅公路”中国境内的路段)边一个叫做大栗树的站口只有六十来华里,如果能找得到去保山的车子,顺搭到大栗树,下车后再顺着正在修的毛路徒步走一天,就可以进到云龙县城了。
我在大理专员公署领受了工作任务后,立即到当时唯一营运汽车公路运输的下关汽车运输总站去找车子。因为时间紧,任务急,我就直接找到总站长,请他优先安排我上路。
总站长是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说,从昆明到保山的客运班车七天才发一班,一班就一辆由货车改的中型客车,连驾驶座旁的座位在内,只有三十一个座位,而且常常超载,规定只售全程票,不卖沿线票,所以在下关是决没有乘客下车的。不是不搭你,是搭不上你。我问,能不能搭从下关发往保山的班车?我可以买全程票嘛,到了大栗树我就下车,行吗?总站长笑了笑说,从下关发到保山的客货混合班车有是有,但昨天刚走,要半个月后才再发一班,恐怕你等不得。我有些着急,说我公务在身,任务很紧急,请总站长帮想想办法让我走。总站长用左手食指敲了敲额头,品亮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闪了几闪,皱着眉头思忖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明天打早有一辆货车放空到小双河林区去,你就搭这趟车去吧。我问小双河在哪儿?站长说,就在永平县往西十几公里的一处山脚。
第二天拂晓,我背着背包赶到汽车总站,总站长带着我向一位驾驶师傅交代了几句话,便忙他的事去了。我把背包甩到货厢上,爬上货厢找了个靠前的地方坐下后,车子便启程了。
车子慢悠慢摇的,有点老牛破车的韵味,足足走了二十来分钟,才离开了下关市区,朝着苍山与哀牢山间的一道峡谷前进。在车厢里摇来荡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天已渐亮,汽车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爬上了一段陡坡,顶着风进入峡谷。车子越过横跨漾濞江的铁索吊桥,就进入云岭西脉的大山区了。
车子要在上长坡前作保养检修,还要加炭加水,我们便在漾濞坡前倚山傍江的河西村稍事歇息。师傅向助手交待必须认真检查的事项和部件后,约我到路边一处简陋的茶棚下喝茶。这种路边简陋的野村茶棚,在滇西公路沿线的山村遍处都有。在路边野村茶棚里喝茶,它的风韵和格调也完全迥异于城镇里的茶肆茶楼。在这儿,你要是只喝泉水、开水,分文不取;要是喝茶,则由茶客随心功德,付给茶主几角甚至几块钱也可以,随便留下点象征性的几分钱茶资也行,茶主决不计较。如果你实在袋中羞涩,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也不必着急,可以不给嘛,茶主仍以礼相待,热情极了。
我喝了半碗茶,见助手师傅正忙着给木炭炉子清灰、加炭、加水、鼓风,根本来不及喝口水,赶紧端了一大海碗温茶给他送过去。他把沾满了炭灰的一双黑手在衣襟上揩了揩,接过茶碗送到嘴边试了试冷热,尝了一口,说好茶好茶,便“咕噜咕噜”一口气把一大海碗茶水甩进肚子里去了。师傅讪笑着说,这家伙哪会品茶,简直是牛牯子吃烂泥塘里的浑水嘛。把我也给逗笑了。
我们从漾濞坡顶一路下坡而去,车子犹如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在大山的波峰浪谷里颠簸起伏。夕阳西下时,就见到一个坝子了。这块坝子并不大,四周山岭余脉的坡地都朝向坝子延伸下去。由于四面山势不尽相同,就形成狭长的南北向坝子,四周的缓坡地带都开拓成了田地。中心低凹的部分,有澜沧江的一条支流从北往南蜿蜒流过,江水犹如一根夺目的银链,点缀着整个坝子,故名银江。江流经坝子中心时,拐了个不大不小的弯子,滇西的一座重镇——永平县,多好的名字啊,永远平安。永平县城就建在这道弯子的两岸。
我们吃过晚饭,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时,滇西的许多县城都没有电,当然也就没有电灯,永平县也一样,天一黑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瓦蓝瓦蓝的天空里闪闪烁烁,映衬着地上游移不定的星星点点的明子(富含松脂的松木柴)火把,给人一种好像行走或飘逸在太空中的幻觉。
驾驶师傅说今晚不走了,到了小双河也找不到人装木料,荒郊野外的林区里,连个睡觉的窝棚恐怕也找不到。于是,我们在永平公路边找了一家鸡毛小栈,要了两个“干号(不供被褥的光木板床位,好在那时干部出差都是白带行李)”,助手弄了几根明子给我们照明,驾驶师傅和我打开自己的背包,将铺盖铺在“干号”上,便钻进被窝里睡了。助手师傅就着明子的光亮出了客栈,去驾驶室里守车,到明天凌晨他还要赶早起床,把木炭炉子准备好,烧足动力上路。那时的汽车副驾驶员是十分辛苦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也不知是几点钟,我们就启程了。那时,全国全民都还很贫困,除了首长戴着组织上发给的手表或怀表外,干部们都没有表,更不要说其他职工群众了。车子刚刚发动,动力严重不足,一开动便像是还没有睡醒似地喘不过气来,走得很慢很慢。
我在车厢上见一弯上弦月悬在幽蓝的天上,发着寒冷的雪青光芒。车子在一个山弯处停下了。我以为是出了什么故障,伸头朝车下张望。天才有点麻麻亮,四面的山林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好像还弥漫着浓浓的山岚,一阵山风袭来,冷嗖嗖的,我不禁打了一个冷噤。
驾驶师傅跨出驾驶室门,回头对我说:“小刘同志,到了。这就是小双河了。你从这里顺着公路上山去,山顶就是李子树垭口,再顺着垭口的公路往下走,不远就是大栗树了。你莫走山上的小路,山上的小路岔路多,走错一步就会岔错到另外一支山上或是走进死箐沟里的。岔错了恐怕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我忙着把背包甩下车去,又从车厢后跳下了车,千恩万谢了两位师傅,他们说还要进林区去,实在不能将我再送一程了。说完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便重新启动车子,隐没在弥漫着山岚的林区里,隐没有狭窄的林区公路的尽头。
步行
我这时才仔细地环顾四周,哪里有什么村子哟(后来我才知道,小双河是个大林区的总称,林区里有个李子树村,村子还藏在深山老箐里,公路边的“小双河”只是进这个林区的岔路口),只有一条山沟,连个人影影都找不着。汽车声响已渐渐远去,整个山弯突然沉寂了下来,寂静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声响。寂静,会让人突然毛骨悚然。
我仿佛听到点什么动静,侧耳细听,又万籁俱寂,什么声音都没有。看看周围,仍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
我背好背包,迈开了脚步,奋力爬了一段傍山公路,天色微熹,山林现出了模糊的轮廓,山与天的界线已依稀可辨了。一直走到太阳已经爬到了山顶了,我好像已经走过十来块公路里程碑了,但仍然没有爬到山梁子上,更没有见到李子树垭口。我心中有些犯疑了。忽然记起那个戴眼镜的总站长不是说不远的,就几十分钟的路吗?我下车时老师傅不是也交代过,顺着公路走,上了坡就是李子树垭口吗?一边想,一边走,终于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一步就跨到了李子树垭口上!
站在高高的李子树垭口上,极目远眺,远山如黛,莽莽苍苍,远天氲氤,云蒸雾蔚,山和天相依相偎,紧紧搂抱着,已然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山了。我把视线从远天远山渐次拉回,顿觉波澜壮阔的大山汹涌着滔天的浪潮向我涌来。
从李子树垭口往下走,一步步走向大山深处,大山和森林逐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此时我虽然有些饿了,但回归家园的温馨感觉,始终萦绕着我,竟至让我忘了饥饿。太阳快要舔到西山头了,才走到群山环抱中的大栗树村。
大栗树村散落在一条江水东边的山坡上,坡下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峡谷,峡谷中可见一条江水,那是澜沧江的主要支流——泚江。山村很小很小,总共就住着十多户人家吧。从山上看下去,房屋倚着陡峭的山势,散落在昆畹公路和去云龙县城的交叉路口两侧。一路上见村里的房屋都是些很简陋、很低矮的平房。屋子的三面“墙”是用杉树皮拼搭后,用树皮搓的绳索将它们互相勾连、捆扎成一大片,然后竖立起来围成Ⅱ形,就成房屋的三面墙壁,房屋的屋顶大多是用山茅草铺的。房屋朝路的门面多是开个小小的铺面做点小生意,或卖点劣质的烟卷、山地的旱烟叶、火柴、打火石,或卖点茶水,亦有卖马匹饲料和山茅草鞋的,还有兼做小炉匠修补一些日用铜铁器具及马蹄铁的。开小饭店的仅只一两家吧。剩下的就是山民农户了。这里还有一种叫做“撒片房”的房屋。“撒片房”的屋顶是用杉木片铺就的。也就是将伐下的杉木撕割成见方两几尺的薄木片儿,一层摞一层大约三至五层串联成片,再叠摞成屋顶。大栗树村的房屋都无一例外地点染着乌黑或褐黑的色泽,靠山的墙壁上还见一丛丛墨绿色的青苔,或是被山雨和山野的潮湿浸蚀的成片乌黑斑点,它们都记载着长年累月风吹日晒和雨淋霜打的轨迹,诉说着这小小山村的风风雨雨和生活的艰辛。
我寻了一间小饭店,一脚踏进门去,就被浓烈的火烟呛得又咳又喘,眼睛也被烟熏得淌出了泪水。我抹抹眼泪,尽力睁大眼睛,才勉强见到四周的墙壁呈现出褐黄色或是乌黑得发亮,到处都是被屋里火塘终年不断的烟火熏成火烤火燎的模样。我问店主有什么吃的吗?店主是位中年的民家(白族被正式命名前的自称)妇女,衣服的肩膀和手袖上都打了补丁,她撩起围腰抹抹双手,有些为难而歉意地说:“你这位工作同志来的不凑巧呀,娃娃他爹今天到宝丰镇(泚江畔的一个大镇)上赶街去了,明天才回得来。我们这里山高路远,七天才赶一个街子哩,前个街子买回来的东西都卖光了,哪样吃的都没得啦。”她想想又说“同志你要是不嫌弃,就搭我们母子俩随便吃一顿。要不,请你另找一家人问问。可好?”我是又累又饿了,忙说:“大妈,不消(云南汉语地方方言,‘需要的连音)另找了,我就和你家吃一顿吧。”
大妈拉了一个草墩让我坐在火塘边上烤火,她说山区天气变得快,一到太阳偏西,天很快就会凉下来,不烤烤火还真的有些冷,会着凉的。她转身从墙壁上取下一个被火薰烟燎得黑乎乎的葫芦,拔开用包谷核做的塞子,小心翼翼地倒出一小撮茶叶捧在手掌心中,又将葫芦挂到墙上。然后转回身来在火塘边蹲下,另一只手拎起放在火塘边沿灰烬上的一个小小的瓦罐,细心地把手心里的茶叶放进瓦罐里。接下来便拾起拨火棍拨弄了一下火塘里的柴火。火焰腾地一下子跳动起来,火舌舔着屋顶,舔着山区里潮湿的空气,“哔哔剥剥”爆出了一串串耀眼的火花,把我惊得连忙用手臂遮住脸。大妈笑着说:“莫怕莫怕,塘火开花贵客到,托工作同志的福,万事如意呢。塘火开的花不会伤人的。哦.同志呀,我这就烤些我们白家种的生茶敬你一盅。”说着便把瓦罐拎起,在火焰上来回上下地簸动起来。一霎时,整个屋子里都弥漫起烤茶的香醇。这盅香喷喷的烤茶还没有到嘴,我心头就颇有点醉意了。
一眨眼,大妈说:“茶烤好了。”她把瓦罐拿到眼下瞧了瞧,说“茶烤得恰到好处,真香啊,再烤就要糊了,味道就会变成苦涩苦涩的。”随即取下架在火塘三脚架上烧得漆黑的铜壶,把烧得滚烫的开水冲到烤茶罐里。随着茶罐里“哧——”的一声响,从罐口里喷起阵阵白里泛黄的蒸气,弥漫着浓郁的烤茶芳香,比刚才的味道更醇厚,更芬芳,更让人陶醉。大妈把茶罐里的茶水往一个缺了口的小茶杯里倒了少许,涮了涮倒掉,才把醇香的烤茶茶水倒在杯里端给了我,说是让我先喝着茶,解解渴,暖和暖和身子,她要到山坡上摘些野菜回来煮汤下饭,便提着竹皮编织的提箩出后门去了。
我坐在火塘边一面喝着烤茶,一面等着大妈回来弄饭,一面还盘算着今晚在哪里住宿,明天的路程怎么个走法……今晚这顿饭是没问题了,可看看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饭馆,要住宿还真的找不出块地方来哩,看来吃完饭还得另找门路。至于明天进县城的路大概有六、七十里吧,听说是逆着泚江一直往上走,坡也不大,也没有岔路,只要问清方向大致是不会走错的。
正在想着,大妈回来了,提箩里满满的一箩小米菜、山芝麻菜,蕨菜什么的。我起坐忙着想去帮大妈择洗。大妈却婉言谢绝了。我说这些山茅野菜我都吃过的,我会择的嘛。她就是不信,说“你们城里人哪会吃这些东西?再说你是客人,还是政府的工作同志,咋个整也不能让你自己动手嘛。”大妈手脚麻利,不一会儿菜便下锅了。
大妈舀来一大钵头野菜汤,又端来一大土碗凉拌蕨菜,那酸辣芳香的味道,惹得我流涎了。但令我奇怪的是她说这些野菜是下饭的,可她连饭也不端便也坐在火塘边的草墩上来了,难道连饭也不吃啦?我想,也许是要等她家里别的人来一起吃吧。便问:“大妈,格是还要等……”“不,不消等他了。我家老大到江边捉鱼去了,一时半时回不来。我们先吃。”吃哪样呢?我实在有些疑惑。正想问,大妈用拨火棍刨了刨火塘里的火灰,在喷起的一阵火灰中,我发现是子母火焐的洋芋。好家伙,多大的山洋芋啊,略带些焦糊的洋芋散发出一阵又一阵糊香味儿来,这次是真的把我的口水引得一滴滴地从嘴角边溢出来了……
正在吃得高兴,外面传来一阵喊声:“阿妈,阿妈,今天运气好,我提了两尾大细鳞鱼,腌起大的一条等阿爸回来吃,小的这条煮酸辣鱼下晚饭吃。”随着这正在变声的兴奋声音,一位十五、六岁的棒小伙子提着两尾用水草穿着鱼鳃的大鱼闯进门来。那鱼还水淋水淌的,活蹦乱扳地在挣扎着。小伙子将鱼递给大妈,同时瞟了我一眼,低声地问:“阿妈,有客?”“唔,专区上来的同志,说是要去石门镇。”“哦,阿妈,那这两尾鱼就一起煮了待客吧。”大妈微微点了点头,却被我发现了,我忙站起来说:“不、不、不要嘛。我都吃饱了。鱼就留着你们自己吃吧。”大妈把鱼放在一只用原木剜成的木盆里,说:“我们自己也要吃嘞嘛,同志你就莫拘(方言,不要拘束,不要客气的意思)了。”“这哪能……”我们就这样推让来推让去的说着,最后达成协议,大鱼腌着,较小的下锅。
晚上,大妈说,你就在我这个小店歇息吧,在火塘旁边打个地铺,暖和着呢。大妈吩咐她儿子抱来一抱干燥的山茅草,铺在地上,又拿来一床厚实的草荐铺在茅草上面,说,“你把背包打开铺在草荐上,就着火塘,头朝外,脚朝火塘。这样就不会冷了,寒从脚起嘛,脚热和了,就好睡了。”我就在这个小店里住下了。
走了大半天的山路,脚又累又酸又疼,但这顿洋芋饭情深意长,吃得很饱,很满足,很舒畅。山村的夜又特别特别地宁静,不一会儿,我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下半夜,我不知为什么醒了,把被子边缘拽到身下压着,还是觉得一股一股的寒气直逼肌肤。我忽然想到,我这是在大山深处的“撒片房”里嘛,“高处不胜寒”,睡的又是地铺,眼下已是五更寒时分,怪不得冷呢。我正想坐起身来去拨弄拨弄火塘里快要熄灭了的柴火,里屋的篾笆门被拉开了,从门缝里透出一线光亮,原来是大妈举着松明子火出来。她轻轻地朝火塘走过来……我连忙闭上眼帘假装熟睡。大妈轻脚轻手的走到我跟前,将一领毛茸茸的什么毛皮轻轻地覆盖在我的薄被子上,又轻轻地回过身蹲在火塘边,用拨火棍拨了拨柴头上的残火,添上几根干柴,拿起吹火筒轻轻地吹燃了塘火,这才站起来拿眼睛瞄了瞄我,便回到里屋去了。此时,我睁开双眼,眼睛已被溢出的热泪模糊了,眼前只有火塘里开始旺盛起来的火焰在影影绰绰地跳动。我浑身的血液也和熊熊火焰一样,涌动着,沸腾着,阵阵热流在血脉中奔突……
天已拂晓,我出门去山溪边洗漱。给大妈结了食宿的账,又向大妈和阿弟(我很自然的把他称作阿弟了)辞别后,一路踏着如洗的青山,从满溢露水的林中小路迂回下到谷底的江边,又沿着傍江的简易公路,逆江而上,朝着我要去的县城赶路。
峡谷里的江流叫“泚江”,是澜沧江的重要支流。泚江水清沏透明,江湾映出天空的朝霞,五彩斑斓,赏心悦目。一条泚江都在流淌着绚丽的彩虹呀。江水缓缓地流淌着,偶尔旋起几圈小小的七彩漩涡,响起几声琤琮流水声,逗留片刻,转个身留下一串愉快的歌声,便轻快地走了。走了一段沿江路之后,拐过一处山嘴,从山坳的深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铓锣”声,“叮——咚,叮——咚——”,铓锣声声,由远而近,整个山谷和森林都响应起来,回声荡漾,动听极了。一声“叮”传来,一刹那就定有一声“咚”的回应。我知道.这是长长的马帮队伍前后互相呼应,用铓锣的悠扬声音,来传递行进在弯弯山路上,头尾互不相见的马帮平安无事的信息:也是“敲山震虎”,警告山林中的猛兽快快回避:同时,这是向附近的村寨和山野中的行人报告:马帮快到了的好消息。
听着这山谷里的声声铓锣,我仿佛一下子从时间隧道回到了远古时代,看到红土地上的先辈们从利用烽烟传递信息到发明锣声传递消息的飞跃。
我循着铓锣的声音,在山嘴的小溪旁三岔路口等着山坳里的马帮出来。不一会儿,果然就见到几匹头骡拐出了山坳朝我走来。马帮的头骡是马帮的向导,不用马锅头(马帮的头儿。拿现今的话来说,是驮马队的队长、领导干部)或是赶马人的招呼牵引,牠们都能一步不差地认出前进的山路,决不会走错路的。所以,它们是马帮的宝贝儿,赶马人对牠们倍加青睐和呵护。我见到的三匹头骡打扮得非常非常漂亮。牠们的头顶都戴着好几朵鲜艳的马缨花,脖子下也戴着一绺分外夺目的红穗儿,红穗中间悬挂着一个较大的铜或者青铜的铃销,前额中央还戴着一面丽寸左右直径的同镜,紧接着脖子的前胸两侧,挂着两串金黄色的小铜铃。牠们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头上漂亮的装饰摇摇晃晃,闪耀着天空灿烂的阳光,分外妖娆;脖子下面和两侧的铜铃走一步就晃动一下,一路留下了串串铃铛声,留下了马帮的艰辛和欢笑。最可爱的恐怕要数牠们前额中央的那面小圆镜片了,镜片把马帮前进路上一切的一切都压缩在镜子里面,好人、坏蛋、观音菩萨、魔王罗刹、钟馗大神、魑魅魍魉、光明坦途、陷阱深渊……统统都收进一块小小圆镜的世界里。“头骡”刚过去,便是望不到尾的长长的一列马帮队伍。在马队之中,我见到了马锅头同志,了解后得知他是县人民政府交通科的马帮运输队。从驮子上看,驮的物品好像是粮食和日用百货之类的东西。马帮正好要进县城,真是好运气,我征得马锅头的同意,便与马帮结伴同行了。
一路上,因为有了众多的旅伴,头一天的寂寞孤单都不翼而飞了。我们沉默赶路时,峡谷里只有泚江水在哗哗地流淌,只有“头骡”颈项间的铜铃不急不缓、很有节奏的铃响,只有前后呼应着悠远的铓锣声。
走着走着,我觉得我的双脚有点蹩崴,脚脖子有些磨疼。我停下脚步解开草鞋绊一看,真是草鞋绊子把脚脖子和大脚趾根都磨红了。糟了,这是我上路的最后一双草鞋了。前两双昨天爬了一天的山全都蹬烂,被我顺手扔在山沟里了,脚上的这一双是我亲手用布筋条绞和着苎麻皮打的草鞋,今早上才穿上的,还有20来里的路,怎么办?
正在踌躇之际,在我后面赶上来的一位姓字的彝族赶马汉子,牵着牲口在我身旁停住,见我在伺弄草鞋,便从马驮子上解下一双半新旧的山茅草鞋递给我,说:“喂,工作同志,你那双潮湿了,一下子也干不掉,穿这双吧。半新旧的最好穿。你试试。”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接了过来,又马上觉得太不过意。这种山茅草鞋很好穿很经穿,在草鞋中是极品,是很金贵的东西。尤其是赶马人自己打的山茅草鞋,那是赶马人在野山里专门挑选的韧性极好的山茅草,这种草鞋柔软、轻便、合脚、舒适,又经磨耐穿,还能抗水、防刺、防荆刺,一双这样的草鞋,走上百十里山路是毫无疑问的,打得精致一些的草鞋甚至可以踏上两三百里的崎岖山路。
我穿上这双情深义重的山茅草鞋,脚步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原来被磨红的地方也不大疼了,连踏在鸡脚刺(山上的一种匍匐地被植物,叶面和叶子边缘长有锐利、坚硬的刺,扎进人的皮肉同时分泌出不易觉察到的毒汁,伤口红肿,疼痛难耐,数周不愈)上,也没得任何感觉,真是太好穿了。
时间不知怎么啦,仿佛过得很快很快,才一眨眼功夫,太阳怎么就偏西了呢,看样子恐怕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的肚子有些饿了,忍不住问:“字大哥,咋个还不到石门?今天也走了大半天了,到底有几里路?不是说六十里吗?”老字带理不答的,淡淡地瞟我一眼,好像是说这有哪样好问的嘛,你莫多嘴,只管走,肯定是会到的。然后,他顺手在路边的树上折了一绺树叶,挑出一片用手指随便折了折,将打了折的叶片放在嘴唇间吹起来。他吹的曲子是《赶马调》。这个山歌小调我在彝山曾经聆听过,怪熟悉的。
我跟着字大哥和长长的马帮队伍一直走到巨大的石门面前,抬头仰望,一眼望不到顶,巨石把我的眼光挡了回来,什么也看不出去。这回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可我发现,前头的马帮不知何时都隐身似地隐去了。莫非他们有遁土的魔法不成?我正一头雾水,字大哥拽了我一把:“同志,走,莫呆脸了,进石门吧。”他拉着我的手朝左手边的江边一拐,绕开高大的岩石,弯进了一处山凹里。啊,啊,我的惊喜不亚于陶渊明翁一脚踏进了桃花源!
跨过石门,就是石门镇了。
县城
敞开的石门让我一睹深山古镇的无限风光。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真正荒废的城镇并不多,更多的是像石门镇这样,被莽莽大山重重封锁,被滔滔大江苦苦隔绝的一座座城镇。就是这样一些城镇,一直飘荡着古朴的民风民俗,保存着人类从古代走进现代的历史足迹,守护着边民们几千年来创造出来的辉煌传统文化。
傍晚的阳光从西边的一摞摞大山空隙之间,从高原特有的蓝天白云上空散射了下来,夕照便成了一道叠着一道、一层摞着一层的光芒。整个古镇的天和地,都笼罩在一种十分神秘又十分圣洁的氛围中。小小的山镇正在镀上一层层金光灿灿的辉煌,把我的眼睛也耀得有些恍惚,染得有点睁不开眼帘。我赶忙抬起手巴掌在眼眉上搭起一道遮阳,遮住有点刺目的夕阳光芒,才在一圈又一圈的光晕中,稍稍看出一点深山古镇的大体轮廓。
我正想着,夜的帷幕已徐徐从天空降落,我忙加紧脚步进“城”去。走过一座古石桥便是县城了。我按照自己对县城的想象,以为桥下定是一条护城河,过了桥当然就是城楼,然后就该是一道拱形城门,有两扇油漆斑斑剥剥的古老城门半开半闭着,人还没有进城,就让你沉浸在古朴而荒寞的历史氛围中。
然而,我四面环顾,连一点点城墙的影子都找不到,更别说什么城楼城门了。在我眼前的是一条有些弯曲的村镇式的小街,小街两侧竖着颇为破败的矮小平房,门口挂着幽暗的灯笼或是燃了几块松明柴火照亮,看起来像是一些很简陋的小食馆吧。
我忙问一家馆子门口坐着的一位老大爹,请问县委会在哪里?老人很热情,先是用他不离手的紫竹烟锅指了指,说:“朝西边过去,再右拐,正对着的那道大门就是。”我朝老人指点的方向看去,黑灯瞎火的,漆黑一片,偶尔有几点灯火若明若暗地在闪烁,我怎能分得出什么东西南北、前后左右,我迟疑了。老人见我不动,抬头望了望我,又说“年轻人,你没有来过我们石门吧?”他咂了一口烟锅,把烟锅头的烟灰在地上磕尽,站起身来,将紫竹烟锅往腰带上一别,说“走,我领你去。”便朝前走了。我忙不迭地跟了上去,深怕把自己丢失在黑暗的夜色里。
县委会果真是在一条背静的小街上,大门敞开着,老人带我到了门内的传达室,交代给一位比我还年轻的值班干事便走了。我递交了介绍信,值班干事提着一盏马灯(桅灯)带着我七弯八拐地绕到了县委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对着正面墙壁上的两幅版画画像.左边的一幅是毛泽东主席,右边的一幅是朱德总司令,他们都戴着红军长征时代的八角帽,帽子上嵌着一颗闪亮的五角红星,一派威武雄姿。画像下面,有几张拼拢在一起的旧桌子,桌面上有三、四盏昏黄的香油灯。门一开,刮进去一阵风儿,灯光便飘飘摇摇地闪动起来。围坐在桌子四周正在开会的人,有的忙着用手掌为油灯遮风,有的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后,就让两位同志把我带到后院楼阁里的一个小间,让我先歇着.工作的事他们说明天再和我商量。
过了几天,公务之余,我在这小得不能再小的古县城里信步闲逛。古县城真的是太小太小了,大街就一条,弯弯曲曲的成了一个S形,店铺也少得可怜,除了街头那几家小饭店外,就是国营的百货公司、县供销社、县人民银行、新华书店、邮电局,县卫生院,而且门面比较狭窄,行人和顾客都稀稀疏疏的。我一会儿也就逛完了。
逛完了新街大街,就去寻老城的小街小巷,我才惊异地发现,这古镇老城的小街小巷倒真是很有逛头哩。小街小巷都很狭窄,路面或铺着被磨得很光滑的青岗条石,或铺着些坑坑洼洼的鹅卵石。两侧的民居都很简陋,很陈旧。房屋大都是木结构的,或平房,或较矮的两层楼房。小街小巷到处散发着松木或杉木特有的芳香,散发着山区民居的一种很特别的风味:极少数几幢砖木结构的深宅大院躲藏在小巷腹地里,那可能是解放前这个县城里的少数几家豪富们的豪宅吧。这些小街小巷的构建,不是沿着曲折的江边摆布,便是绕着起伏不定的山麓排列,逶迤蜿蜒,曲径通幽。所有的小街小巷又都互相通联着,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络,把古镇的家家户户都网罗在一块。我饶有兴致地绕来绕去,好几次竟然又绕回到我进入小街小巷的始发地,好像是迷宫却又不会迷路,从哪儿都可以进入,从哪儿也都可以出来。真是绝了。
有一条小街,我已记不起它的芳名了。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小最小、最窄最窄的小街了。街长不过一百多米,街宽绝不超出两米。我以为这够得上称作世界之最了。一天晚饭后,我又到这条小街上遛达。两侧的小铺正好都开着铺门。铺面很小,货架上摆着的都是些老百姓日常生活少不了的日用小商品:火柴、针头线脑啦,盐巴、辣椒、咸菜啦,劣质香烟、纸拈啦,信封信纸、铅笔笔记本啦,还有家庭白制的草鞋布鞋、草帽、斗笠、蓑衣,蔴索、底线……来买东西的顾客也不多,大多数都是早不见晚见的街坊邻居。他们一点都不像是在做买卖,倒是像亲朋好友在互相馈赠什么礼物似的,拿着商品和钱还要你推过来我让过去的客气老半天才成交。店主人勉强收下钱来,还非常抱歉地说:“阿义(或哥、弟、妹、姐、叔、伯、嫂、大爹、大妈、阿爷、婆婆等等),您看,还收您家的钱,真不好意思了。”顾客此时也会很客气的说:“哪能白要您家的东西呀,您家讨点生活也不容易嘛,给这点小钱恐怕还亏了您家了。”顾客临走时,店主还依依不舍地说“阿义,您慢走啊,要着哪样东西尽管过来拿,有空时就常过来闲闲嘛(滇西一带汉语地方方言,意思是来玩玩、来聊天等等)。”在这里,完全没有生意场上那种令人厌恶的虚伪和尔虞我诈,没有那种讨价还价的冷漠面孔,从他们的对话中和眼神里溢出来的,完全是一种真诚和良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纯真人性的原色。
小街的确是太窄了,没有生意的时候,街对面的小店店主们就隔着小街拉起家常来:什么哪家的小媳妇才过门就挨了恶婆婆好一顿指桑骂槐的詈骂,洞房花烛夜就哭了一夜,那新郎官哄了一夜也把新娘子哄不歇……什么南街的一对新婚小夫妻花烛之夜在新房里烧了一大火盆栗炭火,暖暖和和、红红火火的。临上喜床了,还把门窗关得严丝合缝,深怕春光泄露。第二天,太阳都升到虎头山(县城近郊的一处名胜地)上三竿了,还不见新人起床,真是结婚结婚,都结成昏头昏脑的一对儿啦。又过了一个时辰仍不见动静,小叔子调皮,把糊着大红纸的窗户戳穿了一个洞,从洞眼里往里偷看,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用劲敲了敲窗子,还是没有回应。小叔子跑去厨房里说给妈,“哥哥和他的新媳妇睡得太死了,喊都喊不醒……”阿妈狠狠地瞅了小儿子一眼,亲昵地骂道:“大喜的日子,你这个小挨千刀的,净说些不吉利的话,哪样死不死的,等到你讨媳妇那阵,你怕是要睡上三天三夜才会醒嘞。”妈做完了手上的活,还不见大儿子起床,便去新房门口叫:“儿啊,该起来啦。”连叫了好几声也不见动静,这才着急了。他妈把儿他爹也叫来,儿他爹几脚就把门踹开,一股呛人的浊气迎面冲来,几乎把老俩口呛翻。儿他爹顶着浊气闯了进去,儿子小俩口一动不动地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儿他爹伸手一摸,脖子上没有了脉搏,身子都僵了……县卫生院的医生赶来检查:深度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两小口已经死亡,无法抢救了。
这事也是祸不单行,因为小俩口都是青年团团员,新郎官还是团支书,不仅不带头抵制陈规陋习,还以自身的行动,去违反团组织关于要求团员坚决抵制和改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的三令五申,他们人虽死了,为严肃团纪,提倡新风气,养成新习惯,树立新思想,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两位因喜而丧的新人双双被开除了团籍……
这小小的街还有另一道风景线。那些不做买卖的居家户门口,都镶嵌着几级条石的台阶,门槛上的门枢座或是两个石礅子,或是很结实的栗木(这叫做“门当”)。每当饭后,各家各户的老人(当然是男性),都或迟或早地出门来端坐石礅子或栗木座上,背靠着门棂,或者干脆就倚石阶席地而坐,悠哉闲哉地闭目养神。他们除了手上还捏着一根长长的斑竹烟锅杆外,那心静若水的神态,简直就像是一位高僧正在意守丹田、跏趺入禅的模样。就是面前有行人过路,他们都懒得睁开眼睛,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等到好几家的老人都来了,他们的禅功也修炼得差不多了,他们就来了精神,把挂在竹烟锅上的一个小布袋子慢慢掏开,掏出几绺旱烟叶来,先在两只手掌心上把烟叶揉软揉碎,搓成小团,拿大姆指实实在在地塞在土陶烟锅斗里:又从挂在的竹烟锅嘴下另一个更小的袋子里掏出火镰、火石和艾草,左手拿着火石,把艾草捏拢火石,右手握住火镰,快速地上上下下打擦着火石。铁与火石的碰撞,爆发出一串串灿烂的火星,把个幽深古老的小街炫耀得光华四射,美极了。等到火石旁的艾草燃着了,老人们把刻满了皱纹的嘴唇撅起,对着袅袅起烟的艾草,猛地吹上几口气,吹得火星子四溅,火草更是燃得红亮红亮的,映照着老人们沧桑的脸庞,给我一种人生壮美的感念。紧接着,老人用右手姆指和食指拈起燃烧着的艾草,飞快地按在装了旱烟草的烟锅斗里,将烟锅嘴送进嘴唇里,用力地咂了几咂,烟锅斗里的烟草一闪一闪的燃得更加欢快,老人们也闭上眼睛咂着烟锅,吞云吐雾大过烟瘾。这恐怕就叫做颐养天年吧。看到他们那副惬意舒坦的样子,实在为他们安宁的晚年感到高兴。
编辑手记:
六十多年前,搭上烧木炭的汽车,带着行李、睡地铺、吃烧洋芋,跟随马帮穿着草鞋徒步到县里出差……回想往事,80多岁的老作家刘傅森为我们展示了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