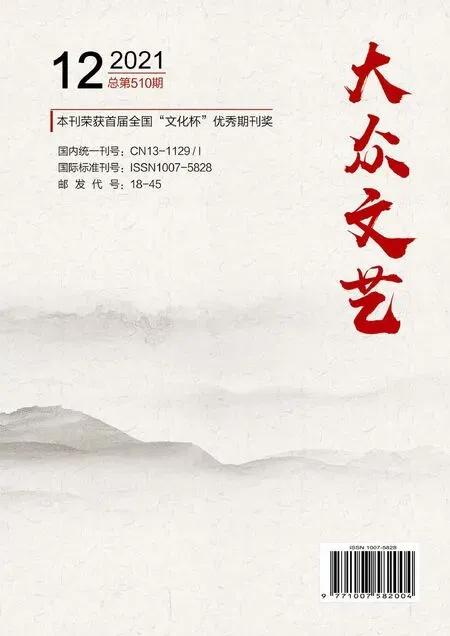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浅析《女勇士》中的鬼和萨满
2015-07-13张慧杰北京语言大学100000
张慧杰 (北京语言大学 100000)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浅析《女勇士》中的鬼和萨满
张慧杰 (北京语言大学 100000)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1976年发表的《女勇士——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美国文坛的轰动,汤亭亭也凭借此书一跃成为美国华裔文坛的佼佼者。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讲述了五个充满东方色彩的故事,并且成功地刻画了“鬼”和“萨满”这两个意象。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入手浅析这两个意象,认为“鬼魂”在文本中就是各种“他者”的代言,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通灵的萨满则是异族发声的主体,汤亭亭期望借助从他者到女勇士的身份转化来改变华裔女性在美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窘境。
后殖民主义;鬼;萨满;《女勇士》
一、“鬼”即“他者”
“他者”这一概念由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在后殖民的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而殖民地人民则被称为“他者”。相对于主体性的“自我”而言,“他者”是处在社会边缘地带不被认可的一个群体。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描写了纷繁复杂的各种“鬼”,讲述了千奇百怪的鬼故事,这些“鬼”在汤亭亭笔下成了美国社会的“他者”——种族他者、文化他者、性别他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鬼”可以是对外国人的一种贬义的称谓,如“洋鬼子”“日本鬼子”等。自小就听母亲讲述中国民间神话和各种鬼神故事的汤亭亭,在写作时对这些素材可谓是信手拈来。在汤亭亭母亲的眼中,她们身边的外国人都是鬼:“美国是一个充斥着机器和鬼的国家——出租车鬼、公交车鬼、警察鬼、水表工鬼……曾经这个世界被鬼占据,我无法呼吸;在白鬼和他们的汽车行驶的马路上,我甚至难以前行。”正如华裔和非裔移民把美国白人看做“鬼”一样,在白人眼中,他们自己也是鬼——“黄鬼”和“黑鬼”。文本中作者写到非裔移民时说到:“也有一些黑鬼,但是他们睁大了眼睛饱含笑容,他们比那些白鬼更明显。”作为美国社会中的“他者”,虽然种族和肤色不一样,但是华裔移民却和非裔移民产生了心灵上的碰撞,在彼此眼中,他们不仅存在,而且还能被看见,这与他们在美国人眼中是“看不见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汤亭亭受到中美两种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其成长环境中的美国文化来说即是“文化他者”。《女勇士》一书讲述了五个故事,全书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的东方氛围和古老的异域风情之中。书中许多奇怪的、甚至难以想象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女孩缠足,生吃猴脑等;还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的人物,如花木兰、蔡文姬等。汤亭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的运用自如,足以说明其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连她自己都说:“我的潜意识是中文,这不奇怪吗?晚上我做梦时,跟厄尔(Earl,其丈夫)说的都是中文。”另一方面,出生并成长在美国,汤亭亭开始反对母亲许多传统的中国做法,她“想制止母亲在公共图书馆或者公用电话前大声吆喝”“试图把自己变成美国女性”。在汤亭亭看来,没有礼貌的粗俗人才会大声吆喝,而文明礼貌的美国人说话都是轻声细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长大,汤亭亭经历了文化冲突的挫折,在美国主体文化的压制下,任何其他文化只能以“他者”的身份在社会的边缘存在。
《女勇士》讲述的全部是女性的故事,在第一个故事“无名女人”中,姑妈背叛自己的丈夫与别的男人通奸,并在生下一个孩子后投井死去,这件事是整个家族最忌讳的,任何人都不能提起。“无名女人”在母亲的讲述中变成了一个不贞洁的、放荡的“他者”形象。第四个故事“西宫门外”讲述的是姨妈月兰不远万里到美国寻夫,却发现丈夫早已又娶一美国女人为妻。深受打击的姨妈月兰从此一蹶不振,最后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女性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群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即女性是二元对立的男女关系中的“性别他者”。“依照译者的见解,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作为女权主义者,波伏娃认为女性一直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被规定为是男性的一个部分。《女勇士》中,作者汤亭亭无非也是想借这些女性“他者”的例子来警示我们:作为女性,一定要做有主体性的“自我”,而不是依附于男性的“他者”。
二、“萨满”要发声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的使用中,“属下”是被消音的,是不能说话的。在小说《女勇士》中,能通灵的萨满无疑是与被消音的“属下”相对的,萨满存在的任务就是要发声。
在中国原始宗教信仰中,萨满充当“神”“人”和“鬼”三界之间交流的媒介,是通灵的。小说的第三个部分“乡村医生”讲述了母亲勇兰在中国学医并成为一名乡村医生的经历,最精彩的当属“勇兰驱鬼”和“勇兰招魂”的故事。在勇兰学医的学校有一间传言有鬼的宿舍,大家都不敢在里面休息或者学习,但是正如她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勇兰并不害怕,而且还主动要求去鬼屋住一晚上。汤亭亭在文本中有对勇兰驱鬼的详细描写:“整个房间似乎被黑暗攫走了,肌肤似乎也被涂黑,骨架子显得醒目……可是她并不胆怯。”“她对鬼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会把你赶走的。’”“我不会妥协的,如果你以为我怕你,那你就错了。”萨满不仅能够通灵,而且可以通过“招魂”的方式来给人治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勇兰的孩子生病了,她就会用一些法术,嘴里念叨着咒语,让折磨她孩子的病痛恶魔离开。
文本中除了有对萨满沟通人鬼神三界的描述,还有对沉默的描述。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强调了属下不能说话的特征,他们是不能言说自己、失去自身主体性的人群。在《女勇士》中,沉默的主人公们便是“属下”最好的表现:因与人通奸而遭到全村人的痛恨却又不能说出自己难处的“无名女人”姑妈;去美国寻夫却难以表达出自己正当理由而最终失去丈夫的姨妈月兰;最初在学校里终日沉默不语的汤亭亭和妹妹;被匈奴掠去而沉默了12年的蔡文姬等。这些沉默不语的女主人公们,在沉默的时候,遭遇总是不好的,她们无法在社会上自立而是要依附于别人而存在。
汤亭亭写下“乡村医生”这个故事,暗示了母亲勇兰是一位勇敢、独立且能发声的女性,汤亭亭从母亲勇兰身上学到,如果想摆脱在美国社会中的“他者”身份,她必须要首先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沟通中美两种文化、两个世界。
三、从“他者”到女勇士
作为从小在唐人街长大的中国女孩儿,汤亭亭早早就体会到了中美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而且知道了中国人在美国被视为“他者”这一残酷的事实。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汤亭亭知道自己必须要摆脱“他者”的身份,成为“女勇士”——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人。
处在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中,汤亭亭时常感到疑惑和痛苦,作为华裔移民,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小鬼,因此她一直在努力摆脱异族他者的身份。在第二个故事“白虎山学道”中,汤亭亭讲述了中国古代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并且日思夜想自己也能成为花木兰一样的女英雄:“母亲的声音变成了我心中女英雄的声音——最后,我感到在听母亲讲故事的时候,自己也有了非凡的力量……我长大了一定要当女中豪杰。”汤亭亭本人纵横驰骋的想象力有时候使小说读起来难以分辨到底是现实还是虚幻的神话故事。女勇士是关于花木兰的故事,也是关于汤亭亭本人的故事。“一开始,她好像是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她是借花木兰女勇士的例子来比喻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奋斗,尤其是她确立自我身份的奋斗。”
文本的最后一部分“羌笛野曲”讲述的是被匈奴掠去的汉代女子蔡文姬,她在匈奴国生活了12年并育有两个孩子,然而她从未忘记自己是个汉人。汤亭亭同样利用蔡文姬的故事来暗指自己生活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不仅如此,蔡文姬在匈奴和平度过12年对汤亭亭也是一个榜样:要利用两种文化来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随着自己在美国生活经历的增加,汤亭亭越来越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要想成为美国社会的“女勇士”而不是“他者”,她必须首先学会美国的语言,这也是汤母勇兰的愿望。早在汤亭亭很小的时候,母亲勇兰就剪了她的舌头:“剪了你的舌头这样它就不会打结了,你的舌头可以灵活自如地学会任何国家的语言,你可以发任何的音。”汤亭亭知道,只有成绩优异,精通英语,她才能彻底摆脱“他者”的边缘身份,才能重新界定自我。才能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意义与价值。汤亭亭成功了,靠自己的努力成了勇于发声并且被美国社会认可的女勇士。
结语
汤亭亭在小说《女勇士》中反复描写了“鬼”和“萨满”这两个意象,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来分析,“鬼”就是美国社会中的各种“他者”,而“萨满”的存在是要发出声音,沟通不同的群体。作者借助这两个意象,表达了自己渴望从华人小鬼变成萨满,即从“他者”变成女勇士的愿望,最终她成功了,为华裔群体,特别是华裔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不仅颠覆了长期以来美国文化中关于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还帮助华裔女性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女性的自我认同,为华裔女性建造了新的精神家园。
[1]西蒙娜·德·波伏娃,陈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漓江出版社,1998.
[4]尹飞舟.《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5]Brownmiller, Susan. “Susan Brownmiller talk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Mademoiselle. March. 1977. 148-216. Courtesy of Stephanie Wallen.
[6]Eliade, Mircea.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cy. Bollingen 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Trans. Willard R. Tr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