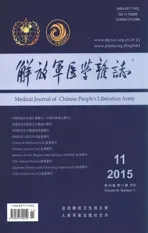战场战伤救治
——一场救治理念的革命
2015-06-28黎檀实付小兵
黎檀实,付小兵
战场战伤救治
——一场救治理念的革命
黎檀实,付小兵

黎檀实,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全军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常务理事,《解放军医学杂志》《人民军医》等多家杂志编委,“十二五”全军医学科技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军队、省部级科研项目20项,主编学术专著5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20余篇。获军队科技成果6项,多次参加中国军事医学代表团,在世界军事医学大会作主题发言。2004年参加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维持和平行动,任一级医院院长,救治伤病员4000余人次,荣立二等功,获“国际健康促进奖”。2008年任北京奥运会五棵松场馆群医疗经理及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VVIP医疗经理,圆满完成奥运会开闭幕式以及五棵松场馆群各项赛事医疗保障,个人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3次参加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四川雅安地震的医学救援任务,6次参加处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的现场医疗保障,3次赴内蒙古参加神舟系列飞船航天员救援保障任务。

付小兵,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解放军总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全军烧伤研究所副所长兼基础部主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研究工作,主要领域涉及创伤弹道学、生长因子生物学、干细胞生物学以及皮肤和内脏损伤后的组织修复与再生等。代表性成果包括:(1)首先报道了表皮细胞可通过去分化转变为表皮干细胞,阐明了细胞表型改变导致过度病理性修复的新机制。(2)探明了在严重创(烧、战)伤条件下机体重要内脏缺血性损伤的发生机制以及基于这些机制建立促进重要内脏损伤主动修复的实用方法和技术,并最终应用于临床患者治疗。担任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执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和咨询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国家新药评委、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创伤修复与再生杂志》及《中华创伤杂志》(中、英文版)编委、副主编等学术职务。获国家97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25项课题。主编学术专著7部,参编28部,发表论文318篇,其中SCI收录论文70余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28.6)。获国家和军队二等奖以上成果21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首届全国百名优秀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求是杰出青年奖、工程院光华青年奖、总后十大杰出青年、科技金星等称号。2008年获“国际创伤修复研究终身成就奖”,荣立一等功1次。
新的军事变革使卫勤保障面临多种挑战,战伤救治理念需要发展并不断更新。本文介绍战场战伤救治理念的提出与发展过程,分析战场战伤救治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特点,梳理《战场战伤救治指南》的组织管理与完善更新,探讨战伤救治的现状及对我军战伤救治理论发展与体系建设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战场战伤救治;创伤和损伤;军事医学
现代战争作战环境与模式千变万化,导致伤类伤情更加复杂,大大增加了战伤救治的难度。战伤救治理论一直是各国军事医学研究和发展的重点[1-2],是军队战时战斗力的重要保障。与我们熟知的民用院前创伤救治理论相比较,战伤救治所面对的伤类、伤情,所考虑的策略和外界因素有本质区别,强调在战场特殊环境中进行的战伤救治是最主要的区别也是战伤救治最重要的特征,包括处于敌对交火的环境中、经常在黑暗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处置批量伤员、有限的救治药械、克服不能及时后送以及跟随部队一同战术机动对战伤救治带来的不利影响等。因此,民用院前创伤救治理论对战伤救治的指导作用有限,必须将战场因素考虑进来,在战场环境中进行战伤救治理论的研究,形成适合于战场条件下的战伤救治体系,才能达到最大降低战斗伤亡率、保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
1996年,由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进行的一项军事医学研究成果,以“特殊行动中的战场战伤救治”为题发表于Military Medicine杂志上[3],第一次提出了“战场战伤救治”(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TCCC)的战伤救治新理念,强调在军医、卫生员和单兵实施战伤救治的同时将高效的医疗救治与部队战场环境相结合,旨在提高院前战场环境中的战伤救治效果,遵循救治战伤、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完成战斗任务三个主要救治目标。其中“完成战斗任务”尤其能体现战伤救治要与战场环境相结合的特点和要求,即战伤救治的任务重点并不仅仅关注于单纯的对战伤的处理,而是在战场环境下如何应用合理的救治策略达到对战伤的有效处置,优先对有望归队参战的伤员进行战伤的快速处理,使士兵尽快恢复战斗能力,归队参战,确保遂行军事任务的完成,这是战伤救治真正需要完成的任务。“特殊行动中的战场战伤救治”一文所提出的《战场战伤救治指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战场战伤救治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火线救治、战场战术救治、战场后送救治);止血带的使用;抗生素的战场应用;有策略的液体复苏;战场止痛;一线救治气道的保护——鼻咽通气道;外科气道——解除颌面部创伤的气道梗阻;高度重视张力性气胸的诊断和处置;汲取战地医务人员的经验,发展《战场战伤救治指南》;在战场情景下进行战场战伤救治训练;高效的救治手段与最佳的救治策略相结合。
战场战伤救治理论是战场一线救治阶梯中对伤员应用的救治策略,强调对战场环境的考虑,强调与部队战术机动的结合,强调以防止进一步损伤、尽快恢复战斗力、完成遂行任务为目标,强调士兵的自救与互救,强调高级生命支持救治技术的靠前应用,实现“医疗与士兵同在”。战场战伤救治分为三个阶段,即火线救治、战场战术救治和战场后送救治[4]。①火线救治是在敌对交火环境中就地进行的紧急救治,是“黄金十分钟”内及时采取救命措施的重要救治阶段,突出士兵的自救与互救,使用士兵标配的救治器材,但救治装备和救治技术较为有限。此时的伤员除采取自救与互救措施,还应尽快战术转移到相对安全的环境中,避免再次受伤;②战场战术救治是在非交火环境中进行的救护,救治的环境优于火线,以卫生员施救为主,使用卫生员标配的救治器材,救治装备、救治条件和救治技术较火线救治相对改善,可提供基础生命支持,为下一阶段的救治创造条件,但救治装备和救治技术仍较为有限。本阶段可对有望归队参战的伤员进行伤口快速处理,继续执行战斗任务。③战场后送救治是将伤员从战场环境后送到提供进一步救治甚至是确定性治疗的安全救治环境的阶段,该阶段以军医提供不间断的、专业的战伤救治措施为主,救治器材和条件大大改善,一些高级生命支持设备和技术可以配置并在转运飞机、轮船、汽车中靠前使用,能够对伤员实施密切监护,实现战场与后方整个战伤救治过程的“无缝链接”,从而获得最佳的救治效果[5-6]。三个阶段的战伤一线救治使救治任务更加明确,救治效率大大提高;先进、优化、整合的损伤控制药械(急救包)和高级生命支持技术装备的靠前应用使救治效果大为改善,避免了因耽误最佳救治时机、缺乏对重要器官的保护措施而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伤亡率。
在《战场战伤救治指南》颁布之初,制定者就意识到它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更新,故通过战场战伤救治委员会定期进行讨论更新,并于2004年作为常设机构,直接归负责卫生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领导,其成员包括战斗卫生员、医助、医师、军医主任、医疗顾问等人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员都要求有作战经历,保证了《战场战伤救治指南》的更新与发展来源于实战、服务于实战。目前,除美国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都将《战场战伤救治指南》作为战场急救培训的标准内容[7-8]。
自2001年开始战场战伤救治委员会每季度对《战场战伤救治指南》进行评估更新,重视从民用院前创伤救治的最新技术到战场战伤救治技术的转化,其理论与技术更新的资料来源还包括公开发表的民用和军用院前创伤救治的科研论文、与军队战伤救治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研究成果、战地军医卫生员的实战经验、在培训过程中学员的建议、经典的案例讨论、军队和地方创伤救治专家的经验和意见等。战场战伤救治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需得到创伤和损伤分委会及国防卫生理事会核心委员会的批准,随后在军队卫生系统网站和院前创伤生命支持网站公布,每隔3~4年公开出版最新的《战场战伤救治指南》。良好的组织管理机制,确保了《战场战伤救治指南》能够代表当前最先进的战伤救治经验和技术,既重视军用民用的转化交流,又重视科研与实战的紧密联系,紧跟现代战创伤救治的发展步伐。
对战场战伤救治理念的研究和思考,能够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借鉴。我军《战伤救治规则》(2006版)依伤情划分为战(现)场急救、紧急救治、早期治疗、专科治疗、康复治疗五个阶段。近年来以信息化为牵引的新军事变革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我军的战略转型,现行的战伤战场救治原则在救治范围、救治技术等领域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虽经多次修订,但在战场急救范围和技术等方面仍停留在传统的通气、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基本技术救治,没有具体的救治任务划分,任务目标也不够明确,战场战术因素考虑相对不足;救治器材现代化程度较低,在功能上不能满足现代战伤救治的需要;器材装备缺乏系统集成,标准化、模块化程度低,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和提高;理论革新机制还不完善,可靠的研究与经验资源较少;军用民用技术相互转化存在障碍,一些先进的民用救治技术和装备尚未在军队中转化应用。
通过加强战场战伤救治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借鉴外军战场战伤救治的理念,结合未来战争对战伤救治的要求和我军卫勤保障实际,应针对不同救治阶段,明确不同的救治任务,配置相应的集约化、模块化救治装备,进行科学性、规范性、可行性的实证研究,不断完善救治体系,顺畅救治流程;重视战场战伤的一线救治,紧紧抓住战伤的“黄金救治时间”,进行损伤控制与生命支持的技术与装备研究;革新救治理念,以“卫生员救治为主”转变为“卫生员救治和士兵自救互救”并重;强化战场战术环境概念,突出救命性生命支持技术和装备的尽量靠前延伸,实现“医疗与士兵同在”;建立战场环境下单兵、卫生员、军医战场急救技术培训和考核标准,构建实战化急救技能训练质量评估机制,全面提升单兵、卫生员和军医的救治能力;建立战伤救治理论革新的长效机制,促进军民创伤救治的沟通交流,紧握现代创伤救治发展脉搏,对成熟的民用院前创伤救治理念和技术装备进行及时的转化军用;加大科研、培训的资助力度,明确单兵、卫生员、军医战场救治的内容及技术要求。从而为我军卫勤保障的战略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技术支持,为全面提高我军新军事形势下的战斗能力保驾护航。
[1]Jiang JX, Li L. Research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war wound /trauma and its perspective[J]. Med J Chin PLA, 2010, 35(7): 781-784. [蒋建新, 李磊. 战伤创伤救治新进展与展望[J]. 解放军医学杂志, 2010, 35(7): 781-784.]
[2]Fan XM, Zhang XJ, Xia ZF. Medical evacuation system of burn casual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urn injuries in US Army in Iraqi War and Afghanistan War[J]. Med J Chin PLA, 2015, 40(1): 71-74.[范晓明, 张学军, 夏照帆.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烧伤医疗后送体系和伤员烧伤特点[J]. 解放军医学杂志, 2015, 40(1): 71-74.]
[3]Butler FK, Hagmann J, Butler EG. 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 in special operations[J]. Mil Med, 1996, 161(Suppl): 3-16.
[4]Introduction To 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EB/OL]. http://www.naemt.org/Education, Accessed 2012-05-15.
[5]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EB/OL]. http://www.health.mil/dhb/downloads/Butler%20TCCC.pdf,Accessed 2012-05-15.
[6]Butler FK Jr, Holcomb JB, Giebner SD,et al. 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 2007: evolving concepts and battlefield experience[J]. Mil Med, 2007, 172(11 Suppl): 1-19.
[7]Butler FK Jr, Blackbourne LH. Battlefield trauma care then and now: a decade of 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J]. J Trauma Acute Care Surg, 2012, 73(6 Suppl 5): S395-S402.
[8]Li LJ, Diao TX. New concepts of combat trauma care in the US Armed Forces during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and Operation Iraqi Freedom[J]. Mil Med Sci, , 2013, 37(6): 477-481.[李丽娟, 刁天喜. 美军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战伤救治新理念[J]. 军事医学, 2013, 37(6): 477-481.]
Tactical war wounds rescue -- A revolution of rescue concept
LI Tan-shi1, FU Xiao-bing2*1Department of Emergency,2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Wound Repair and Tissue Regeneration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853, China
*< class="emphasis_italic">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uxiaobing@vip.sina.com
, E-mail: fuxiaobing@vip.sina.com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ique Foundation of PLA (413EG643), and the Major Project of Military Logistics Research (AWS15J004)
The new military reform has put forward multiple challenges to the defense and medical support abilities, so theconcept of war wound rescue should be constantly updated. The present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tactical war wounds rescue, analyze the echelons for war wound ca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uty of each echelon in tactical war wounds rescue, summarized the management and update of the "Tactical War Wounds Rescue Guideline".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ar wounds rescue, and the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the principles of war wounds rescue.
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 wounds and injuries; military medicine
R826.1
A
0577-7402(2015)11-0862-03
10.11855/j.issn.0577-7402.2015.11.02
2015-07-13;
2015-09-25)
(责任编辑:胡全兵)
军队“十二五”医学科技重大专项(413EG643);军队后勤科研重大专项(AWS15J004)
100853 北京 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黎檀实),基础医学研究所、全军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重点实验室(付小兵)
付小兵,E-mail:fuxiaobing@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