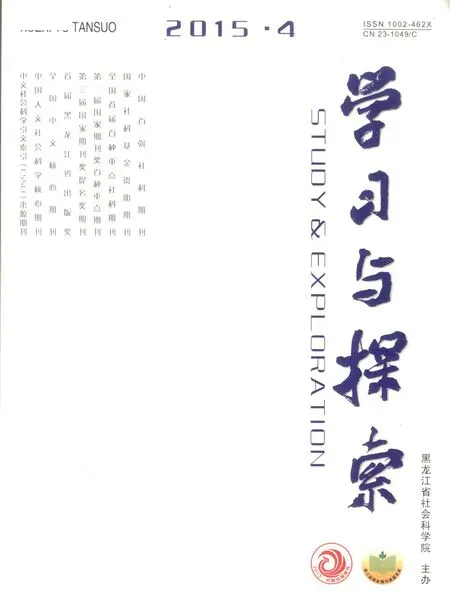论印度哲学中运动
——变化——生灭思想
2015-06-24张法
张 法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论印度哲学中运动
——变化——生灭思想
张 法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印度哲学关于宇宙之动和万物之动的思想,由三大关键词组成:maya(幻力)和karma(业—行)是关于动的宇宙与现象关系层面;vartate(转)和pariāma(变)是关于变的本身的两种基本形态;anitya(无常)和nirvāna(涅槃)是关于生命体运动的内在本质和理想目的。如果说maya作为“幻力”是宇宙的运动变化之始,作为“幻象”是形成之后而在运动变化着的宇宙整体,karma作为“运行”是个体的运动变化、作为“业”是个体运动变化之因果法则,vartate(转)和pariāma(变)是变化的本质基型和现象类型,那么anitya(无常)和nirvāna(涅槃)则讲变化的内在本质和理想走向。这三组词又各以自身为中心形成了三套关联语汇,从而整个地形成了印度哲学关于这一思想的体系。
印度哲学;maya(幻力)和karma(业—行);vartate(转)和pariāma(变);anitya(无常)和nirvāna(涅槃)
西方哲学中关于宇宙之动和万物之变的思想,由motion(运动)-change(变化)-become(生成)这三大语汇所构成,并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西方哲学自现代以来是世界的主流哲学,其关于宇宙之动和万物之动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到了整个世界的哲学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他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但当西方文化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几乎进入一个“困局”的时候,重审印度和中国对此问题的考虑,就变得重要起来。这里以西方关于此问题的思考为参照,来看印度哲学在此问题上的思想。与具有本体论意义的motion(运动)相比较,印哲有maya(幻力)和karma(业—行)两大语汇;与就变化本身谈变化的change相比较,印哲有vartate(转)和pariāma(变)两大语汇;与在具体事物的生灭上的become(生)相比较,印哲有 anitya(无常)和nirvāna(涅槃)两大语汇。以上三组概念,第一组概念是从宇宙的本质讲宇宙万物变化,虽呈现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变化之所由产生的根本;第三组概念则讲变化的根本常态和变化的理想目标;第二组概念则主要讲变化本身的运行,这一运行必然与宇宙的本质和运行的理想目标相关。这三组概念相互关联,但又具有各自的着重点。下面依次呈现。
maya(幻力)和karma(业—行):语汇展开与思想意蕴
maya(幻力)和karma(业—行)从两个方面谈到宇宙万物变化的本体。maya(幻力)是从本体与万物的关系整体讲变化, karma(业—行)是从具体之物的运行规律讲变化。先讲maya。从吠陀经典始,maya就是变化的核心概念。《婆楼那赞》曰:“彼以maya(摩耶),揭示宇宙,既摄黑夜,又施黎明”(第3颂)。“彼之神足,闪烁异光,驱散maya(摩耶),直上穹苍”(第8颂)[1]。正如巫白慧所说,前一颂讲宇宙万象被宇宙之神用幻力(maya)幻化(maya)而出,后一颂讲宇宙万象被宇宙之神用幻力(maya)幻化(maya)而归,因此,万物在其中不断变化的宇宙就是一个maya(幻象)。Maya一词包括了宇宙和万物的生、变、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有印哲特点的是,这个生、变、灭的宇宙是一个幻象,其性本空。性空和假有构成了印哲变化的基础,幻出之生、幻化之变、幻归之灭,都是现象,就是假,如幻(illution)如梦(dream)。在印度教里,吠陀之神进一步演化成Brahaman(作为宇宙本体的梵)与Atman(作为宇宙本体的我),宇宙万象作为maya(幻象)的本质不变,宇宙万象由梵—我的神力中幻化和幻归的结构不变。在佛教那里,否定有梵—我,认为宇宙本空,宇宙万物皆由因缘合和而生,由因缘凑泊而亡,但这由空而来和终回空去的宇宙万物在本质上仍是maya(幻象),而由空而生之“生”仍为幻化,由幻而归之“归”仍为幻归。在性本为空的宇宙中,其大化运行的幻化与幻归的结构不变。在本体论上,印度教实体性的梵—我与佛教的虚体性的空性,性质一样,都不改变宇宙万物的幻象性质,也不改变本质与现象的结构。佛教的理想是空性的涅槃,但又提出了佛性(而且人人内在皆有佛性),而涅槃意味着成佛(而且人人皆可成佛),特别是佛教的发展由最初的无须佛像到后来的必有佛像,诸法无我的“空性”被实体化了,已经在境界和结构上与印度教的梵—我相同了。耆那教的理论略为复杂。其七谛理论,命我(jīva)、非命我(ajīva)、漏、缚、遮、灭、解脱,以一种用更为复杂的方式呈现的一个宇宙的现象—本质结构。而耆那教的七支认识论,表明宇宙与事物是不能被确切定义,只能用“也许如是或也许不如是”的方式来表达的。*参见姚以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23页)中论述摩利舍那(Mallisena,13世纪)的《或然论束》(Syādvādamajarī)的七支公式:(1)或许,一切事物确实存在;(2)或许,一切事物不存在;(3)确实,从一点看,其存在,从另一点看,其不存在;(4)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可描述;(5)或许,一切事物确实存在,而且,或许,一切事物确实可描述;(6)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存在,而且,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可描述;(7)或许,一切事物确实存在,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存在,或许,一切事物确实不可描述。这一“也许”型方式,正与宇宙的maya(幻象)性质相同。七谛结构中,命我进一步区分为不动型命我(只有一个触觉感官的地、水、火、风、植物)和动型命我(触觉味觉两个感官的虫,触、味、嗅三个感官的蚁,触、味、嗅、视四个感官的蜂,触、味、嗅、视、听五个感官鸟兽,五官再加上心智的人),具有不同感官的命我具有轮回的意义,处在轮回最高位的人可以或者应当朝向解脱。因此,对于耆那教来说,运动—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各道中轮回的运动,二是朝向解脱的运动。在两种运动—变化中,命我都与非命我形成相互关联的复杂整体。非命我主要有四:一是作为命我处所的虚空(āgāsa),二是补特迦罗(pudaga,即构成命我呼吸和身、语、意的气性基础),三是支持命我运动的法(dharma),四是支持命我静止的非法(adharma),再加上在动型命我中特别突显出来的时间(kāla),构成了命我在轮回运动或走向解脱运动的复杂结构。在“也许型”的幻象宇宙中,重要的区分就是,处在命我轮回最高级的人,是进行重复轮回的运动,还是走向解脱的运动。对于耆那教来说,与印度教和佛教相对应的是解脱位命我和轮回位命我,轮回的命我相当于印度教和佛教的现象世界,解脱的命我相当于印度教的梵—我和佛教的成佛涅槃。因此,耆那教中的命我,如果战胜了轮回而达到解脱,就成为耆那(Jain—大英雄—胜利者)。七谛中的漏、缚、遮、灭、解脱,正是命我从束缚走向解脱、即现象走向本体的运动。在与印度教和佛教的比较中,耆那教处在束缚位的命我,正处在maya(幻象)世界中,他走向解脱成为耆那之路,正是幻归梵—我或走向涅槃的运动。

梵的maya(幻力)产生的现象世界是一个虚幻宇宙(maya)。这虚幻的现象世界从真理(即梵)的角度看,等于avidyā(无明),maya-avidyā(无明的幻象世界)作为实存的现象世界来讲,其内在的基质是guna(性相)。这个梵语词译成西方和中文都很困难。有四层相关的含义:第一,它如命运之线;第二,内含运动的原则;第三,赋事物以形质,从而成为事物内在之基质;第四,被赋形之物又继续在运动中变化。从其实质一面着眼汤用彤将之中译为与古代汉语的“性”字同义的“德”[2],从其运动一面着眼徐达斯将之中译为“气性”[3]13。德与气,虽一实一虚,但在中国文化里,都是本质性的,而guna是幻象世界里的实,因此汉译为“相性”。重要的是把握住guna(性相)不同于西方和中国的四层含义。Guna(性相)具体来说有三种性质构成:sattva(萨埵),rajas(罗阇),tamas(多磨)。Rajas如天界之性,如气之流动,如能量的发散、运动变化,积极、欲求、吸引、激情,故汉译为“动因”。Tamas如地界之性,如大地之静止,如树荫之昧暗,如止水之懒惰,如愚者之痴顽,故汉译为“静因”。 Sattva如空界之性,纯一、如光,似阴阳之合,若天地之和,带平衡之性,含和谐之心,有智慧、呈喜乐,故汉译为“和因”。三者在现象世界中相互斗争,变化消长;由于三者的组合不同,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宇宙万象,由于三者在现象世界中相互消长,构成了宇宙万象的不断变化。
Guna(性相)的三性互动作用,形成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宇宙万物之成为具体的事物,除guna(性相)之内因,还要加上upadhi(外相)才得以完成。石头之为石头,为这一石头,因为有一个此石头的upadhi(外相);人之为人,为这一个人,因为有一个此人的upadhi(外相)。Upadhi(外相)一词的内涵,同样复杂,具有相互关联的四点:一是从它出现在事物上而言,是偶然的,外来的,不定的;二是从事物的整体而言,它是附属的,是受限的;三是由此,它呈现为一种欺骗;四是从它毕竟已在事物上而言,它的支持使事物成为此物,因而它是此物的载体、乃至是它的名称。*See John Crime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Indian Philosophy: Sanscrik Terms in Defined in English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48,P328.upadhi(外相)之所以有这四点内容,在于印人看来,是由于upadhi(外相)而来的事物在本质上的幻象性质。比如宇宙本为空,有了瓶子,空变成了瓶内之空和瓶外之空,瓶子在现象上改变了宇宙之空的存在方式。当没有瓶子,宇宙之空就合为一体。总之,印哲从本体到现象,maya(幻力)一词上联梵—我、下联guna(性相)和upadhi(外相),组成了由本体到现象的词汇组。当生灭、运动、变化由本体进入具体事物之时、特别是具体事物中的生命体时,其特点,可进入最具个体生命的karma(业—行)这一概念中。
Karma(业—行)虽然也有宇宙的普遍性,但因其词本有的动态性,*Karma的词根kr就是行动、做、制作。 John Crime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Indian Philosophy: Sanscrik Terms in Defined in English,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48,P160.更多的和更主要的是用在生命体上。Karma的词义,第一是行(action),包括心理活动、言说活动、身体动作;第二是业(effect),即身口意活动引起的效果或带来的结果,因此,karma是行动和行动结构的统一,强调行动,可汉译为“行”,彰显结果,可汉译为“业”。第三,karma不仅限于就具体行动和结果而论,而是从行动体系和因果体系立论。这样,一个具体行动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中被看待的。此行是以前行动的果、又是未来的因而决定着未来的果、还关联到当下其他的行和业,而过去的果和未来的果还可以无限延伸,因此,karma把一个行和业与做此行业的人的整体的业相关,还与整个宇宙万物的业相连。在这一意义上,karma(业)是宇宙中每一生命体的活动,是其运动、变化、生灭的整体总结。正因为karma(业)既是具体生命体的活动也与整体相关,因此,karma(业)与dharma(法)关联起来。Dharma(法)是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和基本秩序。印度宇宙的法是圆形的,从象征上可以用法轮来表示,与dharma(法)相关联的karma(业)具有了轮回的印度特色。这是karma(业)的第四个特点。以上四大特点的合一,构成了karma(业)的运动—变化—生灭的特质。
把个体生命的karma(业)与宇宙普遍的dharma(法)关联起来,后者体现了宇宙的本质形态,前者呈现为具体的现象形态。用dharma(法)来参照karma(业),karma(业)的多样性就呈现出来了。生命体的行(karma)可以分为:一是依照dharma(法)而进行的活动,用本词karma(作)来表示。二是违背dharma(法)而进行的活动,在karma词前加一负性前缀,成为vikarma(妄作)。作与妄作,都是指现象世界中生命体的活动,dharma(法)也是指因现象世界出现而随之而生的现象世界之法,即轮回流转之法。印人的理想是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在轮回现世中朝向解脱的活动,在karma前加一正性前缀,成为akarma(无作)。无作即以空心入世,做某事但非为某事本身而做某事,而是带着超越某事的功利性质之心而做某事。作(karma)与dharma(世间之法)的善相连,身与心在法中,是正常的轮之运转,在佛教的轮回图中是轮回在三善道(天、阿修罗、人)中,而妄作(vikarma)则身与心皆与世间之法的善相悖,是非法(adharma)之行,在佛教的轮回图中,是轮回在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上。而无作(akarma)包括两部分,身做(作)而心不做(无),更正确些讲,是在“作”中而不执于“作”且超于“作”,身不离作、在践行着世间的俗务(行)的同时内心进行着解脱的升华[3]25。由karma(业)而展开来的三种行动:作(karma)是在轮回中载沉载浮;妄作(vikarma)是在轮回中走向恶道;无作(akarma)是朝向对轮回的超越。Akarma(无作)是超越之路,是一条yoga(瑜珈)之路,称之为karma yoga(行瑜珈)。瑜珈即治心,印哲中走向解脱的正道。行瑜珈只是四瑜珈之一。印哲不同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瑜珈,各种瑜珈无论怎么不同,都通向解脱。
总之,印哲从个体生命维度讲运动变化生灭的karma(业)关联到三种不同的活动的词汇karma(作)、vikarma(妄作)、akarma(无作),三种活动又关联到dharma(世界之法)和超越世间之法的karma yoga(行瑜珈)。
如果说maya(幻)与karma(行)主要从本体与现象和个体与本体的关系讲运动—变化、即联系到事物与生命讲运动—变化,那么vartate(转)和pariāma(变)则就运动—变化本身来讲运动—变化。在忠实于梵文原义中,vartate可汉译为“转”、pariāma可汉译为“变”,在中西印的互参中,pariāma仍可为变,而vartate可汉译为“化”。两者都与西文的change变化相同,但在parināma之变中,更呈现为看得见可计算的“变”,vartate则主要地呈现为不可见、不可计算的“化”。
Vartate(转或曰化)一词则与本质性的变化有关,它用来指与根本大法紧密相连的存在与活动,指出现又不断变动的存在,体现为Pravartate(不停地向前的时间之流)。无生物的成住坏空,生命体的生老病死,都是这时间之流中。Vartate在《薄伽梵往世书》里,其语义是is(存在的本质形态)、exists(存在的现象形态)、remains(持续)、is here(在此)、happens(突显)等词的统一。这各种形态要强调的都是宇宙大化之中的“化”。在印度哲学的氛围中,vartate是一种宇宙的大法,法轮象征着印度宇宙的运行规律。法轮之转即宇宙的运动。法轮转动的轮回性和规律性给了万物的运动—变化以规律。人按经典(无论是印度教的梵典、佛教的佛经还是耆那教的圣典)行事可称为“人转经典”,经典引导着人的行为可以称为“经典转人”。因此,按印度哲学的原义,vartate可以汉译为“转”。
以“转”体现出来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非本质的变叫vivarta(转幻),可以用来讲从本体到现象的变化,强调本体之“实”转为现象之“幻”。如梵为实体,梵化出宇宙,宇宙为幻,梵虽幻为宇宙而梵仍在。这就是转幻之变。这是一种印度式的虚实合一的变化。又如化身,梵天、毗湿奴、湿婆都有很多化身,比如湿婆的化身就有年轻苦行者、宇宙舞蹈者、毁灭之王、恐怖之神、仁慈保卫者五大类,还有小矮人、摩罗、黑天、王子、伽尔基,等等。这三位宇宙之神虽然转身为他人、在形象和名号都有与原型完全不同的变化,但在本质上还是原来之神。这与西方的非实体变化不同,西哲仅是在科学哲学的界域内讲变,而印哲则可在宗教神话的界域内讲变。
二是本质的变化叫vikara(转变),可以用来讲从非本质的在世现象状态到本质的超越性的本质状态之变化。如由俗心转为佛心,由尘心转为梵心,前者如禅宗的慧可断臂,在达摩说“你把心拿出我看看”的当头一喝中,慧可立即由俗心转到了佛心,即所谓顿悟成佛。后者如《薄伽梵歌》中,周阿那听克利须那之言,在克利须那的“生死无二”“灵魂永恒”的行动责任的圣言中,由尘心转为梵心。在耆那教的理论中,有情生命称为jiva(命我),其存在状态有三:系缚我(即处于不明的轮回之中)、解脱我(通过修行而得了我解脱)、圆满我(即本来圆满)。命我从一种状态转为另一种状态,即是vikara(转变)。
印度的vivarta(转幻),可比于西方哲学的非实体之变,但其变,强调的是内在的精神在变之中的不变;也可以比于中国的“化”,强调是的外在形体上的完全的不同于以往。正是在中西印的比较中,印度的转幻的特点得到了突出。印度的vikara(转变),可比于西方的实体变化,但其变,强调的是决定肉体本质的精神起了性质上的变化,而不是像本质变化那样一事物转为他事物。也可比于中国的“变”,其外在形体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只是在时间之流中有细微的变化而已。正是在中西印的比较中,印度的转变的特点得到了突出。
印度哲学的理想是梵我如一,因此,在转幻中如果要特别强调正方向的转变、而且在正方向转变的行进中最后达到了理想的顶点,就可以称之为cittavrtti(心转),即直接经验到我即是梵。这类似于西方美学中的灵感(enthousiasmos),在灵感中,个人失去原有的自我,成为神的代言。同时,也类似于中国美学中的妙悟。宋人韩驹《赠赵伯鱼》曰:“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言,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成皆文章。”总之,vartate(转)和pariāma(变)构成了印哲关于变化的两层结构,由前者衍出的是与转即本质变化相关联的语汇,如vivarta(转幻)、vikara(转变)、cittavrtti(心转)等;由后者衍出的是与变即具体变化相关的语汇。
anitya(无常)和nirvāna(涅槃):语汇展开与思想意蕴
如果说maya作为“幻力”是宇宙的运动变化之始、作为“幻象”是形成之后而在运动变化着的宇宙整体,karma作为“运行”是个体的运动变化、作为“业”是个体运动变化之因果法则,vartate(转)和pariāma(变)是变化的本质基型和现象类型,那么anitya(无常)和nirvāna(涅槃)则讲变化的内在本质和理想走向。如果说vartate(转)和pariāma(变)是对变化按照事物在时空中的整体性作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段内在逻辑性和外在类型性的把握,那么anitya(无常)则是超越这两个层面、从最内在宇宙本质上呈现事物的整体性和变化的类型性的虚幻本性。vartate(转)是从宇宙大法和轮回规律上讲转变, pariāma(变)是从事物多样和现象多元上讲变化,强调的都是属于现象世界的“常”,而anitya(无常)则是从根本原则上对现象世界的“常”进行了否定。因此,anitya(无常)讲的是变化的内在本质。如果说maya是现象世界的出现及其运动变化之始,那么nirvāna(涅槃)则是处在现象世界中的个人在从这一现象世界解脱出来而达到的人生的也是宇宙本质的理想境界。


① Sue Hamilton在其Indian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说:四圣谛(苦集灭道)第一谛的巴利语dukkha含义模糊,无论是译为suffering(受苦)、pain(痛苦)、ill(病苦),皆易引起误会,应译为unsatisfactoriness(不圆满)。(参此书的中英双语本【英】汉密尔顿《印度哲学祛魅》,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英文部分45页。)但中文的“苦”却有比痛苦更为广的含义。

印度哲学关于运动—变化—生灭的特色,由上面的论述已有所呈现,如果再将之与西方和中国的相同思想进行比较,比如印度的maya(幻力)和karma(业)与西方的motion、中国的易和行进行比较;印度的vartate和pariāma与西方的change、中国的变与化进行比较,印度的anitya(无常)和nirvāna(涅槃)与西方become、中国的生与死进行比较,那么印度思想的特色就会更加彰显。当然,这是另一个更长的故事了。
[1] 巫白慧.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与奥义书解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3.
[2]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40.
[3] 泰奥多.道从这里讲起:薄伽梵歌解读与会通[M].徐凡达,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4] 舍尔巴茨基.小乘佛教[M].宋立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70.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4-12-30
张法(195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学、审美文化、思想史研究。
B6
A
1002-462X(2015)04-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