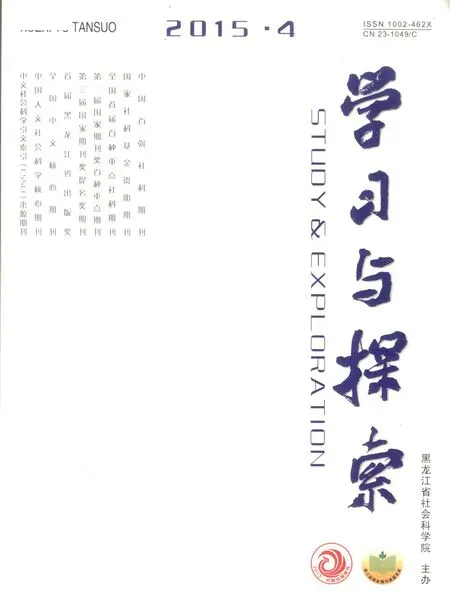时代转型中的民间自觉
——中华卫生教育会与近代中国的卫生教育
2015-02-25杨祥银王少阳
杨祥银,王少阳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社会史研究·
时代转型中的民间自觉
——中华卫生教育会与近代中国的卫生教育
杨祥银,王少阳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近代中国卫生教育问题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1916年3月,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后改称“中华卫生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卫生教育机构。它通过卫生展览、幻灯展示、电影、报纸和演讲等方式,积极宣传现代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为近代中国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其活动和努力也反映了时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在卫生教育等公共事务议题上的民间自觉。
近代中国;卫生教育;中华卫生教育会;医疗社会史
中华卫生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成立的最早以“卫生教育”命名的民间学术团体,它在中国近代卫生教育事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1916年到1930年,它在我国多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卫生运动,积极宣传现代卫生知识和疾病防治方法,培养民众卫生意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论述中华卫生教育会的产生、发展和主要活动,来探析近代中国卫生教育的策略及其影响。
一、近代中国卫生教育的缘起
在历史上,各种疾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一直以来都对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疾病做斗争的医疗史。在古代社会,由于医疗水平有限,人们对疾病的发生原理及传播途径普遍缺乏科学认识,每逢大疫来临,往往会心生恐慌,束手无策,而把治愈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神灵。虽然我国古人也已经注意到了气候变化与疾病传播之间的些许关系,但对于疾病的理解主要是基于经验,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缺乏科学依据,如民间在端午节这天挂艾叶、撒雄黄酒等,希望以此来躲避瘟疫[1]125。明清之际,随着利玛窦、汤若望等一批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一些先进的西医知识得以传入中国,但影响范围有限,仅局限于中国上层社会,加之后来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传教活动的抵制及康熙晚年以后禁教政策的日益严苛,西医东传的这一过程被迫中断了。因此,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够真正认识到西医的价值与功用,也鲜有人对传教士介绍的医学知识做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即使已经传入中国的一些西医知识,也最终淹没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之中[2]。
19世纪初,以“种痘”为代表的现代西医技术开始传入中国。1805年春,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Pearson)在澳门为人试种牛痘取得成功,适值广东天花流行,很多人都去皮尔逊那里接种牛痘,他聘请邱熺等中国人做助手,在一年内即为数千人接种了牛痘,还编写了一本名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的小册子[3]79。同年9月,西班牙皇室医生巴尔米斯(Francisco Xavier Balmis)抵达澳门,协助当地的军医戈麦斯(Domingos Gomes)为人接种牛痘,至1806年2月,他们共为691人接种了牛痘[4]。1817年,邱熺根据自己为人种痘的经验编写出版了《引痘略》一书,将传统中医理论与种痘技术相融合,大大提高了种痘的可信度。此外,还设“菓金”赠予种痘儿童,并将它作为“流浆养苗”的费用,既吸引贫穷家庭的孩子前来接种,又保证了疫苗来源,从而使种痘技术从广东迅速传至全国各地[3]80。在外科手术的应用方面,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街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免费为人看病,第一年便施诊两千余人次[5]。他们为现代西医在我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以后中国本土医疗的现代化开了先河。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条约特权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些现代化的医院和诊所,并在租界地区引进西方式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进行卫生教育和宣传,是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此外,一些宗教组织的先后成立,为中国近代卫生教育事业的发端奠定了组织基础。从毕海澜于1885年在北京通州潞河书院建立学校青年会开始,中经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干事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于1895年在天津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分会,到1912年青年会组织在中国已发展为25处市会和125处校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 M. C. A. In China)亦于同年在上海宣告成立,美国南部美以会教士巴乐满(Fletcher S. Brockman)为首任总干事,华人王正廷为副总干事,后又成立演讲部,由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W. W. Peter)任秘书[6]839。青年会即成立之日起在中国开展了许多与卫生宣传有关的活动,其演讲部人员在全国多个省市和地区开展过卫生演讲,为现代卫生知识的普及起了很大积极作用。
此外,约150名在华医疗传教士于1886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推举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士嘉约翰(J. G. Kerr)为首任会长,并于1905年和1909年先后出版了《护病要求》和《护病新编》,积极宣传西方护理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护理教育事业的发展[6]836。此后,博医会还曾于1910年专门设立了“医学宣传委员会”,计划同青年会合作在中国一些城市开展卫生宣传活动,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两位委员会成员的相继离世而未能实行[1]128。而博医会与青年会终于在1912年就共同开展卫生教育活动达成一致意见,由博医会派一名干事加入青年会讲演部,专门负责卫生教育事宜,并聘请毕德辉主持青年会讲演部卫生科[7]。
在1915年博医会全国会议上,公共卫生问题备受瞩目,中国医生伍连德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卫生委员会,与青年会合作共同推进全国范围的卫生宣传与教育运动[1]128。博医会还决定筹拨专款作为卫生教育活动的常年使用经费,用于制造卫生幻灯片、图表、标本和镜片及开会、游行、展览和演讲等所需开销[7]。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为改变外国人把持中国卫生教育事业的局面,“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8],一些华人医生于1915年2月5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推举颜福庆为首任会长,并附设卫生教育部,这是我国近代影响最大的西医学术团体之一。从此以后,华人医生开始逐步登上了中国卫生教育的舞台,从而扭转了一个世纪以来处处听命于外国传教士的处境[9]5。
博医会、青年会和医学会虽然都开展了一些卫生教育活动,但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卫生教育机构,力量分散,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上述3家机构于1916年3月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Joint Council o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由青年会演讲部的毕德辉博士任总干事,华人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于1917年被聘为副总干事。此后不久,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和中华护士会也相继加入该组织,1920年后便改称“中华卫生教育会”(Council on Health Education),1925年开始出版中英文版的《卫生季刊》,1926年出版《中国的卫生宣传》。中华卫生教育会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公共卫生教育机构,也是中国最早以“卫生教育”命名的民间学术团体[9]5。从1916年到1930年,该会通过卫生展览、媒体宣传、卫生演讲及散发卫生小册子等方式,积极宣传现代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为推动我国近代卫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中华卫生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卫生教育事业终于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卫生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二、卫生教育策略浅析
中国古代的民众对于卫生向来不甚注意,相信“生死有命”,面对疾病,医生们也往往找不出病因,只能根据个人行医的经验为人诊疾,这种情况到了近代也基本没有改变,更是缺乏相应的卫生教育体系。鉴于此,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后,下设总务组、牙齿卫生组、社会卫生组、学校卫生组、婴儿卫生组和编辑组,其执行委员会定会长、副会长、书记各一人,均由执行委员互选产生;会计一人,由执行委员会委派;总干事须为委员之一。凡是想入会的人员必须要在该会正式开会时递交书面申请,该会在下届会议时给出答复。该会地位独立,不附属于任何政府机构和部门,各参与团体需委派一名代表参加该会执行委员会,除有权以该会名义开展各项卫生事业外,还需对维持该会日常运行、募集资金和转派职员等给予量力协助[10]。该会执行委员会在每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开年会一次,评议有关上年会长、总干事、职员和会计等人的工作情况,制定本年会务进行的具体计划,选举本年新职员。此外,每年除7、8、9三个月外,执行委员会须于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九时开会一次。该会办事员可分为总理协理、外埠协理和佐理等,均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并对后者负责[11]。总之,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为该会以后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卫生宣传与教育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华卫生教育会以“由各参与之团体共同保持及促进中国之卫生事业”[10]为宗旨,主要活动是进行公共卫生教育、举办卫生展览、报纸宣传和卫生演讲等。开展公共卫生运动是该会进行卫生宣传与教育的一个主要途径,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民族不图解放则已,若欲民族得到真正自由平等之地位,必须行根本上讲求卫生始。盖谋求卫生,可使人民身体强壮;身体强壮,则精神健全;精神健全,则意志坚决;意志坚决,则民族团结巩固……故卫生运动实为民族解放之基本工作。”[12]1916—1917年,毕德辉领导该会先后在中国的北京、天津、杭州、开封等15个城市开展了卫生运动,共吸引17.5万~20万人前来参加,官方对此颇感兴趣,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此外,各个地方的实力派和一些卫生组织也纷纷向该会发出邀请,希望它能帮助他们发起当地的卫生运动[13]。例如,在当时高涨的卫生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冯玉祥、于右任等人于1927年3月在西安发起了一场清洁街道的卫生运动。他们亲率各机关人员上街进行清扫活动,每人配发扫帚,手持写有“清洁与人生”等标语的小旗子,还派出多组演讲队,随从讲解卫生要旨。冯手推一辆大土车,往返运输清扫的污物,于手握一柄长扫帚,沿街清扫[14]。一些上层社会人物的积极倡导和参与,更加保证了中国近代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卫生知识的普及。
此外,中华卫生教育会还经常举办卫生展览、演讲和散发卫生小册子。例如,胡宣明在1917年去厦门做卫生演讲的时候,就曾设置数十间展览室,陈列大量解说肺病、蝇虫和传染病的卫生图片及幻灯、显微镜等,一时间前来参观的观众多达3万人,“每日上午九时至十时半来参观陈列所,下午二时至五时亦如是。晚间特张电影,如蝇虫生殖之理,蚊蚤除灭之方,肺菌蔓延之故……”[15]1926年,中华卫生教育会趁中华博医会在北京召开年会之际,派人前往会场陈列各种卫生展览品供人参观,从而受到了与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博医会报》载文称此次展览为“展览各品,陈列井然,殊足动目,为该会贺也”[16]。
在散发卫生小册子方面,中华卫生教育会也做了不少工作。1926年11月16日,美国海上大学代表团成员乘船抵达上海,该会于次日即向他们每人赠送一册《中国传布卫生集》,此外还有卫生习惯彩片及种痘免花彩图各一纸,图书目录一册。除上述宣传活动之外,中华卫生教育会还进行过一些实践性的卫生服务工作。1926年江西战事发生之后,一时间伤兵众多,南昌医院人满为患,于是该会受医院委托代为聘请医生,并在短时间内聘请到2名医生、5名护士和3名助手[16]36-37。近代中国乡村地区经常会发生天花疫情,由于医疗条件差,往往造成死者无数。针对此种情况,中华卫生教育会经常在全国各疫区开展形式多样的种痘避花运动,获得了各省医院学堂、红十字会和青年会等机构的协助,通过分贴五彩小儿种痘免花图和施种牛痘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防治效果[17]。
中华卫生教育会领导的卫生运动对当地人而言就是一场场规模宏大的群众集会,人们对此充满好奇之心,渴望参与其中。此外,还有一些人经常利用这些集会为自己和组织谋利,传教士们趁着卫生运动的浪潮满腔热情地推进他们的传教事业,精明的商人们也利用集会来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和兜售卫生药品。在安徽屯溪于1926年举行的首次卫生运动中,当地民众手持写有“卫生能生利”(Health Pays Dividends)和“屯溪医院卫生运动会”等字样的旗子,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在这些游行队伍里,走在最前面的人负责击鼓吹号,其后是屯溪医院的一面大旗和两面国旗,还有一个用纸做成的大苍蝇模型,其后有一面写着“你不杀苍蝇,苍蝇杀你”的大旗,还有一个食物大纱罩,它们后面有一面写着“蚊虫生疟虫”的大旗。此外,还有34名小学生随行,每人胸前都挂着花,全都穿着布操衣服,戴白布操帽,一些护士和教民也排队同行,整个场面蔚为壮观,吸引了沿途广大民众的注意。每日游行过后,当地都会举办卫生演讲,晚上还放映幻灯片,题目涉及肺痨、盲目和城市卫生等,间或也会有学生登台表演,而游行所用的旗帜、图表和模型等物品都摆放在周围,供众人参观。当时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既有商人、士兵和学生,更多的是喜欢热闹场景的普通老百姓,其间共向他们散发卫生小册子数千册。适值疟疾横行,很多人都患上了痞块大肚子病,这次卫生运动便积极宣传一些防治方法,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18]。
同年,在福州卫生运动期间,社会各界争相从中华卫生教育会那里购买各种卫生图表、幻灯、影片和小册子等,还聘请该会葛雷博士为他们做演讲,听众达1 500余人,其中360余人加入了当地卫生组织。演讲过后,当地还放映卫生幻灯片,观众一度达7 500余人,对于它的优点,福建的卫生工作人员说:“幻灯片(时称‘土电影’)是很引人注意的宣传方法,因为它不像看电影能活动,所以功效不如电影来得大,可是成本比电影小得多……在本省语言隔阂,每隔数百里即有一特别的方言,利用幻灯片来宣传是很适当的。”[19]此后,福建协和大学和中学成立农村卫生宣讲团奔赴农村地区进行卫生宣传,英华书院和格致书院添置了学校卫生设施为在校师生服务,三公会和堂会也开始倡导卫生事业,防疫会则散发卫生传单、图表和小册子,还给当地人进行疫苗注射。这次卫生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福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的卫生防疫水平[20]。
除上述活动之外,中华卫生教育会还在北京、天津、卫辉和开封等多个地方进行了类似的卫生教育活动,借以宣传霍乱、结核病、鼠疫、天花和性病等多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在帮助地方制定公共卫生计划、建设公共卫生组织和促进天花疫苗接种等方面提供了一定帮助,为我国近代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各个地区的卫生巡回演出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和需要来确定一个主题,毕德辉还经常把卫生(健康)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演讲的重点,成功引起了广大听众的积极反应。并且,他认为妇女作为卫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他经常会在卫生运动中的妇女日上发表题为“对婴孩的关爱”(The Care of Your Baby)的演讲,向中国妇女介绍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抚养孩子的方法,这也有利于美国育婴产品在中国的销售[21]。
学校卫生教育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创办近代新式学校的开始,此后建立的新式学校中既有官方学堂,又有教会学校,师资建设与课程设置已经部分地涉及医学与卫生。例如,天津水师学堂早在1881年就开始设立校内医生,广州岭南学堂于1898年正式将校内医生定名为校医。当时许多新式学校都已经认识到校医的重要性,有的学校还分别开设了中医和西医课程,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校卫生工作主要还是效仿日本,并以翻译日本的卫生著作为主,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提高民众的防疫意识,来认识学校卫生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中第3章第12节明确规定:“学生因于疾病应予剔退出校。”第4章第6节规定:“中学堂每学生百人应有食堂、盥所各一处,浴所、厕所各三间以上。”这说明当时官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对学校卫生工作给予了一定重视[22]。
而在当时的中国民间,虽然有一些教会人士和非专业的卫生工作者在关注学校的卫生教育,但并未引起当地职业医生的注意。特别是在一些远离城市的乡村学校,卫生条件差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学生普遍缺乏应有的卫生意识[23]。鉴于此种情形,中华卫生教育会从1916年成立之后,就一直把学校卫生教育当作它的一个工作重点,其医学职业委员会坚持每年赞助一些医学校,让它们代为本年度入学成绩最高的学生颁发奖金,每人100元。1926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范权,湖南雅礼大学的易见龙,山东齐鲁大学中院的高学勤,奉天医学校的洪永新以及圣约翰大学医科的章臣梅就曾荣获该项奖金[16]36。通过这种办法,中华卫生教育会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一些学校开展卫生教育工作,从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
此外,中华卫生教育会还经常在学校举办卫生征文比赛,借以传播现代卫生知识,培养学生的卫生意识。例如,该会于1925年6月举行第二届全国学生卫生征文比赛,将题目定为《我家乡的卫生和医药设备的实况及其改良方法》,希望以此提起广大在校学生对卫生的兴趣,比赛分大学和中学两组,为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此次比赛不允许医学专业的学生参与。征稿通知一经发出,各校学生就踊跃投稿,一周之内即收稿件120篇,其中有中文稿件95篇,英文稿件25篇,总字数达40余万,内容涉及各地的卫生实况、医药设备及改良方法等。它们来自全国15省的65所学校,其中中学33所、师范学校10所、大学22所。为此,该会聘请博医会的付乐仁博士,比必博士和青年会的葛雷博士担任英文稿件的评判员,同仁医院的王以敬博士、青年协会的范子美先生、刘湛恩博士为中文稿件的评判员,从中评选出优秀作品,并登报表扬,还给予获奖学生奖金,这次征文比赛取得了圆满成功[24]。次年,中华卫生教育会医学职业委员会举行第三届全国学生征文比赛,将题目定为《中西医理对于促进我国人民之健康与国家之进步,孰较有效,并述其理由》,共备奖金475元,取获奖者20名[25]。通过举办卫生征文比赛,中华卫生教育会的影响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学校,“卫生”二字逐渐成为广大学生的口头词汇,为以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智力和群众基础。
此外,中华卫生教育会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卫生教育工作,还特意在各地建立了一些暑期学校,对学员进行集中的卫生知识培训,其学校卫生部主任宓爱华医生还亲往各省暑期学校担任教授指导。宓医生在1926年夏受华南基督教教育会之聘,主持福州暑期传习所,该校于当年9月9日开学,学员大半为各教会学校、小学、初中的教职工,共151人。学校每日安排的课程很多,学员们须于早晨6点半起床,做深呼吸操,早课从8点半上到11点半,下午则从2点半上到5点半。学员们所学课程分为主课和副课,主课包括国语、宗教教育和卫生教育,规定每天学习时间在1小时以上;副课包括儿童心理、教学、普通科学、心理测验、绘画、手工和音乐。卫生教育课分小学和初中两班,小学班规定学习两周时间,共有小学教师73人,开设“小学卫生教授法”课,授课人员先用国语宣讲,再由翻译人员用福建方言加以说明;初中班则直接采取国语授课,不需要翻译。课程以外,还要进行体检,并先后于3个晚上召开卫生会议,专门放映卫生影片2次,表演卫生新戏1次,之后由该会护士张素娥女士解说儿童卫生展览品[26]。该会通过对中小学教师进行集中的卫生知识培训,培养了一些卫生骨干人员,再由他们将这些卫生知识和理念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在那个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年代,能够开展这样的活动,实属可贵,为以后的卫生教育工作打下了基础。
总之,20世纪早期的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与竞争,而民族自强的根本在于民众身体的健康,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健全的精神,就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中国人要想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就一定要提倡现代卫生,普及卫生教育,提高自身身体素质。中华卫生教育会领导的卫生运动,通过开展各种卫生宣传工作,传播了现代卫生知识,培养了民众的卫生意识,对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促进社会进步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结语:公共事务议题上的民间自觉
在近代中国,卫生开始频繁出现在广告、演讲、电影、招贴画、期刊杂志、报纸和官方宣传中,其具体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很多人将它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对中产阶级而言,卫生可以通过购买某一商品来实现;对于处在社会顶层的精英们而言,中国人的卫生现代性似乎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而必须借助于西方,通过把西方的卫生标准引入国内,进而发动一场医学革命来实现。卫生甚至还被用来突出中国人体质落后的先天性和西方人身体健康的优越性,进而将它上升到隐藏在身体背后的文化话语权的高度,把卫生作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的一个标志,试图把西方的价值伦理观念凌驾于东方的传统道德体系之上[27]240。卫生在中国有了新意义,它不仅包含了政府的科学管理、疾病预防、环境清洁,还预示政府要运用行政力量对细菌进行检测和消灭。卫生在帝国主义的语境中成为文明与现代性的代名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完整主权的一个标准,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府只能被迫接受这一概念,并试图通过改变现有卫生状况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27]178。在这种背景下,中华卫生教育会利用现代卫生知识和各种宣传策略,积极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在客观上,对唤起民众的卫生意识及推动政府在建立现代卫生体系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是近代中国卫生教育思想的启蒙者。1930年,国民政府设立卫生部,中华卫生教育会的历史使命得以完成,宣告解散,而此后开展的一系列卫生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会的影响,其卫生教育的策略与形式被沿用下去。
而民间组织与政府机构在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教育事业中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医疗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余新忠在其《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所说:“一般认为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官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它们其实具有相当的一致性。”[28]从这方面看,中华卫生教育会在推动近代中国卫生行政体系的建立以及提高国民卫生意识的过程中的确做出了一定贡献。以上海为例,其民间社团十分发达,公共卫生教育亦缘起于民间。自1916年该会成立后,即通过各种途径在市民中间提倡公共卫生,宣传各种疾病防治方法,从而促使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逐渐走向组织化、统一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被设为特别市,并成立了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将公共卫生管理与宣传纳入政府职能范围以内,公共卫生事业从此开始突破民办格局,进入政府与民间合办的新格局[29]218-219。由此看来,以中华卫生教育会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力量的崛起,使得“近年医界趋向平民普及……送诊给药比比皆是”[29]224,体现出了较强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社会化倾向以及都市社会的自主性特征。它们在时疫救治和公共卫生宣传方面表现积极,利于加强社会各阶层间的合作与互动,进而促成更为广泛的良性社会行为[30]。总之,中华卫生教育会等民间机构在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它们的许多公益活动不能实现常规化,从而限制了其社会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并且,中华卫生教育会的宗教色彩浓重,其成员大都有基督教背景,因而它开展的许多卫生教育活动都只是局限于教会学校、教堂,以传教为终极目的[31]。该会还因为缺乏专业的医学成员,加之当时动乱的时局,许多活动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无法付诸实践,这极大限制了它的影响。另外,由于条件限制,该会往往在一个城市举行完卫生运动以后,并没有继续跟进当地的卫生体系建设,而是在多年以后重又回到当地举行第二次卫生运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32]。最根本的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人民因战乱、饥荒等原因流离失所,卫生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奢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会开展的各种卫生教育、宣传活动的效果无疑是十分有限的[33]。
另外,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以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名义大力促进公共卫生工作,试图改变中国人的疾病和卫生观念。但他们试图通过强调西医的科学特性以确定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合法地位,改变了传统中医的知识结构和治疗实践。现代医生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他们对传统中医的否定对中医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使中医与西医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之交,以宣扬适者生存观念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促使他们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时代背景下改变他们对于国家存在的理解。而概念化的国家实力是从人民的身体状况、道德素质和科学知识三个方面来阐述的,科学在西方的崛起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开始支配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科学不仅被看成是绝对真理,还被认为是衡量国家先进性的重要尺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把科学看成是西方力量的源泉,通过科学提倡现代化从而使中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抢夺[34]。从这点上讲,现代卫生知识作为科学的组成部分,便开始被渴望摆脱落后局面的中国先进人士所利用。
除中华卫生教育会之外,中国一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和组织,积极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促进本地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譬如,湖南长沙在市卫生科和雅礼医院的支持下于1913年秋天成立了“妇女社会服务联盟”,定期举办卫生讲座,散发卫生小册子,开展儿童种痘。江苏公共卫生协会成立于1916年,由著名实业家张謇担任首任会长,成员包括医学校毕业学生、卫生科官员、教育家和商人等,协会下设医学教育与研究、环境卫生检查、流行病预防及家庭卫生诸科。在上海,一些宗教和慈善团体曾在1918年成立了一个“道德福利委员会”,呼吁取缔当时的妓院,针对妓女开展卫生讲座和性病治疗。此外,1933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防痨协会以“健康民众体魄、预防痨病发生”为宗旨,虽然是一个民间机构,但实际上却是由上海市卫生局发起、市长吴铁城出面组织的,协会成员包括一些社会贤达、政府官员和医学界人士。该协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卫生宣传活动,1934—1936年在上海福音广播电台进行痨病预防知识讲座,1935年3月发起“劝止随地吐痰运动”,1934年11月开始发行《防痨月刊》,还面向儿童发行健康画报。1926年成立的中国麻风协会,主要开展有关麻风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工作[1]132-133。上述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卫生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和中华卫生教育会一样,对促进中国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启发时代转型中的民间自觉做出了卓越贡献。
综上所述,公共卫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事业,需要全民参与,“所谓大众卫生是没有阶级的,就是要人人都知道卫生的真意。社会上各色人等,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分贵贱,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应该具备这种卫生知识,躬行实践,以谋自己和人类的幸福……如何能使各个人能有维护与赞助公共卫生事业之观念与热心,亦惟有籍教育之力始能达到目的也。”[35]在今天看来,中华卫生教育会在促进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教育方面的经验与策略,仍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历史意义并不局限于当时。
[1] 张大庆.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2] 何小莲. 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7-39.
[3]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 岭峤春秋:广府文化与阮元论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4] 谭树林.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澳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222.
[5] 何大进. 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68.
[6] 丁光训,金鲁贤. 基督教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7] 唐泽鑫. 记中华卫生教育会[N].申报,1920-12-19(23).
[8] 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章程草案[J]. 中华医学杂志, 1915, 1(1): 5.
[9] 王东胜,黄明豪. 民国时期健康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0] 中华卫生教育会.卫生教育会大纲及细则[N].申报,1923-09-26(4).
[11] 中华卫生教育会.卫生教育会执行委员会细则[N].申报,1923-09-26(4).
[12] 卫生警察[M].福州:福建省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1923:8-9.
[13] Public Health Work in China[J]. 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1917,(30):468.
[14] 中华卫生教育会.西安卫生运动[J]. 卫生季刊, 1927, 4(1):29.
[15] 胡宣明. 厦门卫生演讲会开会记[J]. 中华医学杂志, 1918, 4(2):55.
[16] 中华卫生教育会.卫生消息[J].卫生季刊, 1926, 3(4).
[17] 中华卫生教育会.叶纳略传[J].卫生季刊, 1926, 3(3):10.
[18] 中华卫生教育会.安徽屯溪卫生运动志[J].卫生季刊, 1926, 3(3):15-17.
[19] 福建省卫生志编撰委员会. 福建省卫生志[M].福州:福建省卫生志出版社,1989:238.
[20] 中华卫生教育会.福州卫生运动报告书[J].卫生季刊, 1926, 3(3):19-20.
[21] SERLIN D. Imagining Illness: Public Health and Visual Culture[M]. Duluth: U of Minnesota Press, 2010:31-32.
[22] 王建平. 健康教育:世纪的呼唤——中外学校健康教育比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263-264.
[23] 中华卫生教育会.山东教会小学卫生状况调查录[J].卫生季刊, 1926, 3(4):17.
[24] 中华卫生教育会.本会第二届征文经过[J].卫生季刊, 1926, 3(2):17-18.
[25] 中华卫生教育会.卫生消息[J].卫生季刊, 1926, 3(3):32.
[26] 中华卫生教育会.宓爱华医士福州暑校报告[J].卫生季刊, 1926, 3(3):29-30.
[27] 罗芙芸.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8] 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51.
[29] 彭善民. 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0] 王名,刘培峰. 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47.
[31] 宓爱华. 在华北宣传卫生的经验[J].卫生季刊,1925, 2(1):16-28.
[32] Woo M. Report of Joint Council o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1917-1919[J].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1920, 34(2):186-189.
[33] 史如松,张大庆. 中国卫生“启蒙运动”:卫生教育会的贡献[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 31(5):75.
[34] BOROWY I.Uneasy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and health in China(1900-1937)[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93.
[35] 高维. 卫生教育浅说[J].中华医学杂志, 1934, 20(3):410.
[责任编辑:那晓波]
2014-12-15
杨祥银(1979—),男,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医疗社会史与口述史学研究。
K258;C913
A
1002-462X(2015)04-01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