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文学评奖
2015-06-01邢丽凤
邢丽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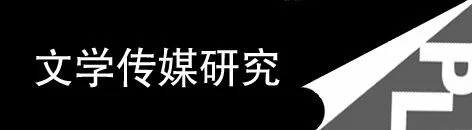
文学期刊与文学评奖
邢丽凤
“文革”结束以后,从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始,文学评奖的种类越来越多,既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备受争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期刊设立的文学奖项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尽管其影响力比不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但在新时期文学评奖的历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与其办刊的定位密切相关,在奖项设置和宣传策略上都追求社会关注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系统考察文学期刊主办的文学评奖,对于探讨新形势下文学期刊和文学评奖的发展策略,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从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各级作家协会、文联主办的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学评奖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民间机构主持评选的文学奖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尽如人意。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授权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举行颁奖大会,首开“文革”后文学评奖的先河。在此基础上,中国作家协会进一步扩大文学评奖范围,陆续增设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奖项。在官方文学奖项中,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于一九八一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保持了评奖的连续性,影响力也最为深远。《小说选刊》在一九八九年十期的杂志上公布了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获奖名单,这也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告别演出。直到中国作家协会在一九九七年启动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全国性文学评奖的拼图才变得完整起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一起,覆盖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文学翻译、儿童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文体和文类。此外,曹禺戏剧文学奖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其前身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于一九八○年创办的全国优秀剧本奖,一九九四年评选机制调整,更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些刊物和重要的文学奖项有特殊的关系。一九七八年第十期的《人民文学》刊登了《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这次由《人民文学》杂志具体操办的评奖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先河,茅盾认为是“空前的、过去没有做过的”。而《小说选刊》的创办,其初衷就是为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遴选初选篇目。茅盾在“发刊词”中说:“为评奖活动之能经常化,有必要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可作年终评奖候选的短篇佳作。因此,《人民文学》编委会决定编辑部增办《小说选刊》月刊。”一九九七年启动的首届鲁迅文学奖,每种文体的奖项分别由中国作家协会直属的一家刊物负责承办评奖工作,譬如《小说选刊》负责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负责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负责报告文学奖、《诗刊》负责诗歌奖等单项奖的评选工作。由此可见,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评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八十年代,文学奖大多为各级作家协会、文联机构主办,由文学期刊独立设立的文学奖项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但奖项的数量较少。一九八四年六月《青年文学》杂志举办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一九八五年一月《小说界》举办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大赛,一九八四年《花城》文学奖开始评奖,这些奖项都是半途而废,在评选几次后终止。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期刊设立的文学奖项中,一直保持连续性的两项评奖都是由文学选刊主办。一九八四年,《中篇小说选刊》设立优秀中篇小说奖,除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为年度奖项外,均为两年一届。同年,《小说月报》设立百花奖,两年评选一次,它是国内文坛唯一采用读者投票方式评选,并完全按照票数而产生获奖作品,也是国内唯一设立优秀责任编辑奖及读者奖的评奖活动。
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学评奖活动花样繁多,文学期刊也不甘寂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陆续设立各类名目的文学奖项。综观这些由文学期刊主办的文学奖项,大致有以下特点。首先,以高额奖金作为基本策略。一九九五年,由《大家》杂志社和云南红河卷烟厂共同设立的“《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金额为十万元人民币,拉开以高额奖金吸引社会关注的文学评奖的序幕。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东海》杂志将三十万元“文学巨奖”颁发给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二○○○年,《当代》杂志也推出“《当代》文学拉力赛”,奖金额度为十万元。二○○二年《收获》杂志宣称将联合几家企业打造“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收获》文学奖”,奖金额度为一百万元人民币,但最终不了了之。二○○六年,《芳草》设立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分设大奖、最佳抒情奖、最佳审美奖和最佳叙事奖,单项文学大奖最高八万元;同年,由《佛山文艺》联合《人民文学》、《莽原》及新浪网共同主办的“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唯一大奖的奖金高达八万。文学评奖以丰厚的奖金来吸引眼球,散发出浓厚的商业气息。对此,作家孙犁感叹:“在中国,忽然兴起了奖金热。到现在,几乎无时无地不在办文学奖……几乎成了一种股市,趋之若狂,越来越不可收拾,而其实质,已不可问矣。”虽然评奖的主办方一再强调评奖的公正性、权威性,但此时文学评奖的运行规律、操作模式并不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和程序的公正性。不同奖项之间比拼奖金的额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丧失了激励独立的文学创造的作用,而是以炒作的形式来制造轰动效应。
其次,青少年文学奖项成为热点。文学期刊设立的文学评奖还以各种形式来紧跟社会潮流,在评奖中加入流行的时尚元素,使文学评奖更加娱乐化、功利化。新世纪最初的几年,少年写作热潮持续加温,在捧红了一大批少年写手的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青春文学赛事。《萌芽》杂志和全国多所重点大学在一九九八年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都借助这个平台一飞冲天,成为文化市场的宠儿。二○○二年由《美文》杂志社主办的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征文大赛被包装为“中国少年诺贝尔文学奖”,自我标榜为全国中学生的最高写作比赛,并以一百零一万元的奖金总额吸引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同年《青年文学》与《中华读书报》、新浪网共同举办“首届中学生性情作文大赛”,之后《青年文学》又举办“首届校园之星文学作品大赛”;二○○四年《同学》杂志社、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首届全球华文青春写作大赛”在京举行颁奖仪式。打着各种名义的青少年大赛与国内众多家长急功近利的教育心态不谋而合,与娱乐圈造星运动一样,激发了青少年追捧文学偶像的热潮。在时尚风潮的推动下,青少年写手很难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而是在跟风中写作,难以成长为大家,造成文学生产的恶性循环。
再次,文学期刊积极与网站、电讯公司等各种新型媒体机构合作办奖,试图引领文学发展新趋势。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形式的普及,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使大众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学评奖中,读者投票方式从邮寄方式转向大规模的网络投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都通过新浪网、中国作家网等网站设立投票平台。与传统的书面投票方式相比,网络投票方式更加快捷,但必须防范一些网络高手通过技术手段造假,网络水军的存在也为人为操作留下了空间。近年,从手机短信发展起来的手机小说成为公众的新宠,《天涯》杂志抓住这一契机,在二○○四年与天涯社区、海南移动通信公司联合发起“全国首届短信文学大赛”,引发文坛对于短信是否是文学的热烈争议。二○一一年,《山东文学》、《齐鲁晚报》、网易共同主办“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大赛声明旨在推动网络文学健康有序的发展,将纯正的文学理念、高雅的艺术格调和专业的评价体系引入江河横流、泥沙俱下的网络文学大潮之中,从而使大赛真正实现“构建网络文学新坐标,引领时代创作新风潮”的目标。纯文学期刊以文学评奖的方式介入网络文学或者短信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是文学期刊以跨界实践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举措。纯文学期刊与新媒体的合作,如果能够深入下去,这有利于提升新兴文体的文学含量,也能吸引大众关注日益边缘化的纯文学期刊。
二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种类繁多,引发公众的审美疲劳。由于评奖需要丰厚财力的支持,如果评奖无法对文学的发展和推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低效的评奖只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进行总结与反思。我个人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定位模糊,变化频繁,缺乏长远规划,评奖活动成为缺乏持续性的短期行为。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浪潮中,为了因应办刊方针的调整,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肯定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或减少奖项。譬如《小说家》更名为《小说月报·原创版》后,《小说月报》的百花奖就增设了原创小说大奖。《人民文学》杂志在获取茅台酒厂的赞助后,将“人民文学奖”冠名为“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原来的奖项设置中只包括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奖项,伴随着《人民文学》的扩版,《人民文学》开始发表长篇小说,二○○七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开始将长篇小说也纳入评奖范围,二○一○年除设立首届长篇小说双年奖外,还新增设了非虚构作品奖。但是,如果奖项设置的变化太过频繁,就会让作家和读者觉得主办方缺乏明确目标,奖项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譬如《当代》刚刚举办《当代》文学拉力赛时,奖金十万,号称全国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随后的《当代》文学拉力赛取消了奖金,《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包括专家奖和读者奖)也不设奖金。此后又推出“五年五佳奖”和“五年最佳奖”。《当代》设立的文学奖项可谓花样迭出,评奖规则也不断改变。由于奖项的设置和评选规则的制订都显得太过随意,无法形成象征资本的积累,比较难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力,这样的文学奖项很难在作家和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文学期刊的评奖活动中,有不少奖项都是一次性的,开场时声势浩大,随后却不了了之。
其二,缺乏特色,追逐时尚,在跟风中迷失。文学的丰富性造就了文学奖项的无限可能性,多样的文学奖项对文学的发展具有监督和促进作用,但无节制的文学评奖容易陷入时时评奖、事事评奖的泥淖中。就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而言,奖项太多,名堂太多,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譬如,二○○四年《青年文学》举办“慈溪农行杯”首届青年文学奖的评选,分设了青年文学成就奖、创作奖和新人奖;二○○六年,《文学自由谈》杂志举办“《文学自由谈》二十年作者奖”评选,奖项包括功勋作者、重要作者和新锐作者;二○○七年,《文学报》、《作家》等国内十二家媒体联合发起的“中国原创小说月月推荐榜”,结果有二十二部作品荣登“二○○六名家推荐年度排行榜”,最终评出“二○○六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奖项太多就显得廉价,给人“排排座分糖果”的印象。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金山杂志承办的第三届(二○○四年度)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就有一百篇作品获奖,分别有十篇、三十篇、六十篇作品获得一、二、三等奖。如何在林立的文学评奖中保持特色,是作为主办机构的文学期刊必须正视的问题。有的通过改革评委构成来推陈出新,《大家》杂志在第三、四届“红河杯”评奖活动中,邀请金庸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主持人李潘作为评委,这种做法引发文坛热议,被认为有媚俗之嫌。《芳草》杂志于二○○七年设立的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就是邀请文学界有影响力的女性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资深编辑组成评委会,以纯女性评委的姿态亮相,吸引大众的眼球。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的评奖活动,越来越重视挖掘和鼓励文学新人。文学要发展,当然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但是,如果以为越早成名的作家越有前途,这显然是走偏了方向。二○○八年,《芳草》又设立“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对低龄作家的看重,显然和商业炒作有关。在韩寒、郭敬明获得巨大的市场成功后,文学期刊的文学评奖也倾向于奖励更年轻的“新人”。二○○○年一月,王蒙在获得《当代》文学拉力赛大奖的十万元奖金后,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春天文学奖”,规定每年奖励一位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上海文学》杂志社二○○三年和东方卫视文艺频道共同主办《上海文学》全国文学新人大赛,短篇小说新人奖没有年龄限制,二○○六年的“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开始设置新人获奖者年限为三十五周岁以下,二○○九年举办的“中环”杯《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大赛直接表明参评者年龄在三十周岁以下。二○○六年《人民文学》杂志设立的人民文学利群文学奖,也明确规定只奖励年龄不超过四十岁的文学新人。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大器晚成的作家。遗憾的是,在如今的消费文化氛围中,成名晚就意味着和很多机会绝缘。《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以“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形成互补格局,成为他们的准备与补遗”为口号,除评选优秀作品外,还独家设立“最佳友刊作品奖”,奖励同期在兄弟刊物发表的优秀作品,这成为该奖项的一个特色。必须指出的是,奖项设置也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如果脱离了自己的办刊实践,这种奖项往往难以持久。
其三,文学性淡化,评奖成为一种功利的炒作行为,还有一些期刊的评奖是赤裸裸的牟利行为。在文心浮躁的年代,无论美丑,只要能出名,有看点,博得关注就行,其背后隐含的是商业的营销策略。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喜欢和旅游风景区、酒厂合作,在获得赞助后举办“××杯”征文奖,来稿都对景区的风景、酒文化进行肉麻的赞美,等奖项评出来,绝大多数的获奖者都是期刊或评委的关系户,那些获得二等奖、三等奖的自由来稿,算得上是一种点缀的花边。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选刊》、《南方文坛》、《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二○○二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揭晓。作家王蒙、张洁分别摘取“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桂冠;阎真获得“进步最大的作家”称号;池莉获得“人气最旺的作家”称号;张者被评为“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海岩、虹影、柯云路则分别获得“最有影视缘的作家”、“最富争议的作家”、“最会变脸的作家”称号。二○○四年一月六日,“二○○三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揭晓,巴金和杨绛分别获得“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的称号。获得“二○○三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称号的还有:“最具活力的作家”韩东、“进步最快的作家”麦家、“人气最旺的作家”贾平凹、“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邵丽、“最富争议的作家”余秋雨、“最有影视缘的作家”刘震云、“最被看好的网络作家”慕容雪村。这样的奖项设置不仅显得过于随意,而且以吸引大众眼球为主要目标。文学评奖和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没有直接关联,奖励的都是话题人物,荣誉称号也采用模糊概念,似是而非,而且冠冕四处派送,“最”字满天飞,这样的奖项显得廉价而草率,这只能助长文坛的浮躁风气。还有一些文学期刊惯于通过文学评奖来敛财,这类评奖往往要求作者在参加征文大奖时就支付评审费,而获奖者参加颁奖大会时还要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一些以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青少年文学刊物,这类评奖行为尤其多见。这种评奖其实是一种欺骗行为,是对文学爱好者的利用和压榨,对文学发展只有损害,没有丝毫益处。
其四,评奖成为一种圈子内的利益分配,缺乏公正性和独立性。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活动,最难做到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那些通过获取商业赞助来支付评审费用和奖金的奖项,赞助方的意志常常会干扰正常的评奖活动。在一些文学期刊举办的评奖活动中,如果仔细留意,会发现获奖名单中有不少赞助方的关系户。作家协会、文联系统主办的机关刊物和各级文艺出版社主办的社办刊物,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核心阵容。在一些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的获奖名单中,也经常会看到期刊的上级单位的工作人员乃至负责人的名字。这表明文学期刊的文学评奖要保持独立性,确实有较高的难度。由李嘉诚赞助一百万元奖金,《读书》杂志主办的志在打造中国的诺贝尔奖的“长江读书奖”,一九九九年启动评选工作。但是,作为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汪晖和作为评审委员的钱理群的获奖,引发了媒体和知识界对其评审的公正性的强烈质疑。当然,要做到文学评奖程序的透明和公正,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全国短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历史上,就曾出现评委获奖的情况。冰心的《空巢》、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和《春之声》都在作者担任评委的年度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而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也是作者担任评委的情况下,因为一名评委提议和两名评委附议而增补为候选篇目,并最终获奖,尽管在牵涉到自己的作品时作者回避,但作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状态,显然无法保证评审的公正性。由于大多数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影响力小,公众关注度也不高,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受到的舆论压力也小,因而更容易进行暗箱操作。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评奖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文学评奖究竟是文学期刊的自我救赎,人文精神的艰难独守,还是不甘寂寞,为浮躁的快餐文化推波助澜?与改革开放之初大众对文学的疯狂膜拜不同,今天的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无法与影视、网络等新兴媒介相抗衡。精神生活正在走向多元化,文学无复当年盛况,文学期刊不再是时尚的焦点,甚至面临生存的危机。在市场主宰、文心混乱的年代,如果要使文学评奖成为文学期刊证明自我存在的砝码,同时通过评奖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形成品牌效应,获得更好的稿源,充分挖掘文学期刊潜在的市场,为市场经济下纯文学期刊的发展拓宽道路,那么,文学期刊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维护文学奖项的声誉。
文学期刊主办的成功的文学评奖,通过奖励那些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创作,向社会和读者推荐好作品,可以扩大获奖作品和期刊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巩固自己的作者队伍,强化办刊特色。如果一项评奖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持之以恒,就像《小说月报》百花奖一样,它一定会成为一种文学品牌。出色的文学奖项会生发出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源源不断地吸引那些有才华的作家加盟,使文学期刊拥有一支可以自我更新的、充满活力的作者队伍。文学评奖也是文学期刊的试金石,在文学评奖中可以坚持艺术标准的文学期刊,在选择稿件时也往往能够择优汰劣,获得广大作者的信任,同时也赢得读者的支持。因为只有严于律己的文学期刊,才能够奉行精品路线,保证不以次充好,使得刊发的作品有品质保障。与此相反,那些由文学期刊举办的乌烟瘴气的文学评奖,媸妍莫辨,不仅难以取信于作者和读者,而且会扭曲文学标准,毒化文学空气,使得作者不专注于艺术的磨练和提升,而是费尽心思地做足诗外功夫。这种充满私心和杂质的文学评奖,对于文学期刊自身的建设不仅无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而且会自己挖坑自己跳,贻害无穷。
发挥文学期刊自身特色的文学评奖,是办好文学期刊的有效手段。评奖间接地宣传期刊定位,对期刊的品牌建设和市场销售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九九八年启动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是《萌芽》的转折点,这一影响广泛的青少年文学奖项迅速提升了《萌芽》在中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像滚雪球一样吸引了大批的少年作者和少年读者,刊物的发行量大涨,那些衍生性出版物也给刊物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和巨大的社会反响。《青年文学》二○○二年举办“首届中学生性情作文大赛”,仅仅一个月就收到五千多份稿件,既在大学生和中学生中传播了刊物,又挖掘了文学新人。以青年读者为直接对象举办大赛,符合《青年文学》的办刊定位,使刊物直接受益,无疑是提高刊物知名度的最简单的办法。文学刊物在整个市场形式下已经边缘化,不宣传自己,本身的市场会进一步萎缩。文学刊物用大赛或评奖来为自己代言,传播办刊理念,稳定和拓展自己的读者群,切分市场中属于自己的蛋糕,这种精准的市场定位,从长远来说对期刊形成稳固的接受群体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评奖推出文学新人和优秀作品,给青年文学作者队伍中增加了新的构成层面,对接受群体或者稿源组合都有更好的引导作用。从二○○○年开始,《美文》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增加了“少年版”。二○○二年,《美文》杂志举办首届“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征文大赛”,自我标榜为“中国少年诺贝尔文学奖”,参赛的全球华裔青少年数量十分可观,也为杂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美文》杂志在二○○○年底征订数不足八千份,举办征文大赛后,仅“少年版”邮购就达到五万至六万册,并且带动了“成人版”,每月增加一千至二千份。获得评奖的作品还以结集或精选的形式出版,给自己的后期市场带来了巨额收益。《美文》杂志除在每年下半年下半月刊中推出获奖作品专号外,还以图书的形式来出版历届获奖作品,如贾平凹主编的《历届少年美文写作大赛获奖作品精选》、《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获奖作品集》(上、下)都十分畅销。
文学评奖和排行榜活动,可以成为文学期刊的营销策略和推广手段,但是,文学期刊千万不能舍本逐末,把主要精力用在花样百出的评奖和炒作上,却荒疏了自己的主业,缺乏扎实的内功和基本功,没有把杂志办好。文学期刊设立文学评奖需要一定的资金作为支撑,尤其是高额奖金,更需要赞助商。只有极少数评奖是期刊自掏腰包,这种自费评奖往往陷入后续资金匮乏,导致评奖不了了之乃至期刊办不下去的尴尬境地。期刊与企业联姻,企业出资金协助办刊、颁奖,文学期刊通过文学奖宣传文学期刊,也为企业形象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了企业的形象,实现企业和文学的双赢,使文学评奖发挥了最大的功用。二○○三年茅台酒厂以协办方式与《人民文学》长期合作,把始于一九八六年的“人民文学奖”定名为“茅台杯人民文学奖”,被誉为企业与文化联姻的成功案例,也为其他失去了财政支持、资金短缺的文学期刊办刊树立了榜样。《大家》刊物封面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得主,在创刊时就声明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目标,以寻找大家和造就大家为己任,打出纯文学期刊的旗帜。另一方面在未创刊时就积极寻求企业的合作,从一九九四年一直到一九九五年初期,刊物的封底都是旗帜鲜明地标明“当今中国一流的大型文学期刊,寻求一流企业携手合作”,实现“共生共长、共存共荣”,希望获得商业资金的赞助。后来因为有一些读者难以接受纯文学期刊上赤裸裸的商业口号,从一九九五年第四期后在读者建议的基础上对封面和封底的装帧设计做了改动。在获得云南红河卷烟厂的经济支持后,《大家》在一九九五年推出十万元的文学大奖,当时给文坛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应该承认,连续评选了四届的巨额奖项确实扩大了刚刚创刊不久的《大家》的影响力,随着作家对刊物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可以吸引名家的重头稿件和处于上升期的作家的力作,从而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聚集起自己的品牌效应。遗憾的是,以巨额奖金为噱头的文学奖项半途而废,《大家》自身的建设也多有漏洞。在第一届将大奖颁给《丰乳肥臀》后,第二、第三届大奖连续空缺,在第四届颁给《看麦娘》后,这一奖项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副主编常振家就对《大家》的空缺策略提出批评:“就是勒紧裤子过日子,也必须要发出大奖。以高额奖金掀起炒作热潮,又以‘空缺’方式一毛不拔的伎俩,《当代》是绝不会的。”《大家》曾经打出“先锋”的旗号,莫言的《丰乳肥臀》也引起过热烈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发表在《大家》上的真正具有广泛影响的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譬如李贯通的《天缺一角》、贾平凹的《制造声音》、唐浩明的《旷世逸才》等等。到了后来,《大家》又推出莫名其妙的“凸凹文体”,加上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大家》编辑团队的扯皮,《大家》的经营状况不断下滑,后来采用一个刊号两本杂志的方式,“理论版”通过卖版面疯狂牟利,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被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停刊整顿。另一个代表性案例是《东海》杂志,在赵锐勇担任主编后,一九九六年推出三十万元奖金的“东海文学奖”,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又举办“广厦杯”五十万元文学征文活动,但缺乏可持续性,二○○○年改名为《品位》后,先后改版为时尚杂志和财经期刊。因此,对于文学期刊而言,只有首先把期刊办好,文学评奖才可能拥有坚实的后盾,否则,文学评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做大做强。
以排行榜名义出现的文学评奖通过排名次,提高作家、作品的知名度,聚敛人气,为后期文学市场的商业运作埋下伏笔。二○○五年《北京文学》杂志举办“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二○○七年由《文学报》《作家》等国内几家媒体联合发起的“中国原创小说月月推荐榜”。二○一○年《钟山》杂志总结三十(一九七九-二○○九)年成就,组织三十年十佳长篇小说、十佳诗人排行榜。各种排行榜名单出来,随之就是批量的作家集、作品集,排行榜对于作品的销售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生活的快节奏使普通大众难得有大量时间在文海里披沙拣金,排行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向导的作用,关注度的提升带来了商业利润的提高。必须指出的是,过度的炒作是对文学的一种伤害,也会催生作家和读者的逆反心理。
文学期刊举办文学评奖活动,如果评奖程序公开透明,坚持公正性,而且持之以恒,这样的评奖显然有积极意义。典型如《小说月报》举办的百花奖评奖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这不仅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打造品牌效应,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由于百花奖有良好的声誉,小说家也以获得百花奖为荣。对于作者来说,虽然荣誉比奖金更重要,但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体系中,以物质形式鼓励文学创作,给好的作家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罗贝尔·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谈到文学奖的作用时说:“奖金的价值在票面上是有限的,然而,得奖作品可以保证得到畅销;作者的收入就此大增。”可见文学评奖对作家作品的肯定,对提升其市场号召力会起到隐形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的是,物质奖励要授予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如果文学奖颁给那些会跑关系、有背景的作家,就不仅无法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还会起到负面作用,使得其他作家也难以安心创作,而是把精力花在公关上,这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公正的文学评奖是建立健全的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环节,能够起到淘沙拣金的作用,让好的作品进入公众视野,乃至流传下去,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环节。
(责任编辑 韩春燕)
邢丽凤,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