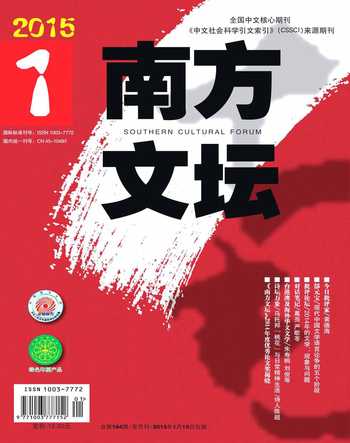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他者”眼中的当代中国
2015-05-31申霞艳
彼得·海斯勒(何伟)的《寻路中国》《江城》出版掀起了一阵何伟热及非虚构写作的讨论,新出版的《奇石》深化了这场讨论(《寻路中国》《江城》《奇石》均为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西之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困难、最持久的一场论争。何伟的著作适得其时,上承马可·波罗的游记传统,下接萨义德关于“东方学”的观察。鲍曼认为流动乃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无论是东方和西方还是欧洲和亚洲,作为文化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变化的。变化正是何伟在其全部著作中以极大的耐心和精湛的细节所展现的事物。
何伟的现代版“东渡记”何为?从“东方学”的延长线来考察其空间维度是合适的,同时还有从当下到历史的逆流而上的时间维度。激励作者不远万里来中国乃是由于西方人的东方想象和对真相的寻求,但促使他待下来并拥有一个中国姓名和系列中国叙事则另有原因。“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不同、活力、值得探寻”将他的中国行程延长并使他决定重返“东方”并在此生活。顯然,这里包含一双“他者”的眼睛和一颗好奇的心。天真和好奇是人类的前进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是我们在成年过程中慢慢丢失的宝贵气质。
新出版的《奇石》是本“去(中)国怀乡”之书,何伟说:“中国就像是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这本书主题比较分散,时空跨度很大,写了不同的国、家、事和人。第一篇就写广东的吃,这是世界闻名的吃!吃什么呢?鼠!怎么吃?霍霍有声地吃,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张旗鼓地吃。“民以食为天”的传统与当下结盟。《胡同情缘》写的是自己旅居北京胡同的经历,其中中国式相亲尤为诙谐,做媒这个古老的职业在今天不仅市场化而且还国际化了,WC俱乐部尤具喜感,像阿Q一样叫人难忘,笑之余淡淡的忧伤来袭。吃、胡同、长城……是典型的中国符号,但吃鼠、在厕所边谋生、看世界杯对一个美国人可能是奇葩般的感官经验,然而我们已见惯不怪。何伟的表述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动滞重的神经,激活我们感官和思想僵死的部分。
彼得·海斯勒用记者的敏锐、文学的表达呈现出他眼中的当代中国,这是符号铠甲里边的血肉之躯,还有微微颤抖的民族命运以及当下与历史的隐蔽勾连。何伟先在四川涪陵师专当外教,他希望学会“够用的中文”,应是指口语交流,但是随着他待的时间越长,他的“够用”扩大了,更重要的是级别提高了,口头交流的欲望发展成写作的欲望,写作意味着对文化的深度介入,还意味着与整个世界对话。他谈到涪陵的岁月对他的重要性——“接通地气”,地气要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成为更时髦的词汇。当一个地道的西方人使用“气”这个神秘缥缈的词汇时,显然作者已经把握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内部特征——“文以气为主”。和过去的传教士不同,彼得·海斯勒尝试以中国的方式感知中国,这也许部分地回答了我的纳闷:为什么这样一部关心中国道路和中国命运的书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这决不仅仅是他山之石的视野问题,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欲望和相应的民族国家认同。我不能不羞愧地看到:中国很多学者要么眼睛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丧失了对大问题大趋势的敏感,要么是以想象中的“西方”方式感知中国。现代性追求已经将一个魔鬼一般的西方范式牢牢地种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对自己的中国经验习焉不察,同时对许多真正的中国问题视而不见,不能有效地在自己内心建立起立体的思想框架。这正是读者欢迎何伟的缘由之一。
《江城》展示了涪陵这样一个小城的变化,并由此延伸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在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四川这种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这是对“天人合一”的古远文化传统的回应。中西、古今对比使何伟的写作获得了纵横坐标。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正在以一个令西方人感到震惊乃至害怕的速度变化着。一切就像匆匆东去的河流,价值观也来不及沉淀。“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国却见到了这样的基础被连根拔起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所有戏剧一律禁演,仅有少数政治作品如《红色娘子军》能够幸免。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也早已不复存在。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马克思,但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夫子。”这种直观的经验如利刃插进了我们软肋,对外语的重视对母语的轻视、疯狂的移民热都在诉说当代中国的真实问题,也印证了何伟的观察。
关于长江三峡的利弊,作者从写作课的范文切入,让学生以写作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是西方培养公民责任的重要方式。从这些作文中也看到兴建大坝的利弊同样明显,难以取舍。作者写道:“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一边是人类的。一个是永无休止的循环产物,另一个——尽管结果不一——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在我看来,在长江之上,如果要把这一切通通捆绑成一体,硬把循环不止的江水组滞在大坝上那长长的一汪死水里,是极其危险的违背自然之举。”这种隐忧没有完全被情绪化,作者将目光投向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类工程具有两面性。这个国家有数千年驾驭和驯服河水的历史——人类文明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把一条条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的确,我们有大禹治水的佳话,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至今仍在有效地工作。作者同时也注意到:“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不是感情用事,而是让历史依据和现实数据说话,所谓冷静节制、以理服人、呈现事实恰恰是非虚构写作的力量来源之一。
《江城》也写到鲁迅笔下的“看客”、写到民间的乌合之众,“在同胞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鲁迅)笔下的人物总是置之不理。”但何伟也将细腻的笔触伸到学生、小商贩、市民柔情的情感世界。他尽量地展示了这个小宇宙内部的复杂、丰富和矛盾。作者不想套用观念来阐释这座城市,而是用异乡人散点透视的方法见证中国大发展如何云谲波诡地震荡到边远地区,这不仅表现为可见的一座城市的湮灭,更表现为当代中国人对待这种变化的坦然态度。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而个体的命运又与这个国家的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隐蔽关联。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被他睿智的双眼连缀起来,成为历史的轨迹。
《江城》像日记,何伟和学生融在一起,为他们的成绩喝彩,为他们的命运担忧,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每种感情都那样新鲜而真挚。《寻路中国》更像“游记”,上承《马可·波罗游记》的伟大传统,不以道德的双眼打量这个发展中国度里的奇人怪事。对于“中国”,彼得·海斯勒是关切的,他带着正面的感情上路,尽量忠实地复现现场。如果借用叙事学的术语,他使用的是限知叙事方式,他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和想到的,甚至还有意地在书中使用国画式的留白,向读者发出参与和对话的邀请。他没有使用公共话语和陈词滥调,对考驾照题目的引用,他也为它们设置了“陌生化”的语境。全书空间跨度很大,分西、中、东三部分,西部的荒凉、消失的村庄与东部随工业区而兴起的城市形成巨大的对比。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就像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中旅行,这就是当代中国。
海斯勒自驾车沿着长城西行,长城乃中国的象征,它勾勒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安土重迁以及防御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使近代中国充满了痛苦并行走在一条蜿蜒曲折的现代性的道路上。今天,长城失去了最初的防御意义,倒意外地成了海斯勒的“导游”,沿着长城西行,他看到了中国许多即将消失的村庄,看到了长城的砖被农民用来围猪圈,看到明知不可能成活的树苗因为方便面的鼓励而被栽种,看到了日趋荒凉的西部。最后一代乡村少年的纯真、好奇和羞涩让他伤感。这些天真的尚怀人生希望的乡村少年最终也会像他的父辈一样“到城里去”,他们的口音、眼神都会“被城市化”,他们会像闰土一样渐渐衰老麻木,乡村少年会像乡村的田园牧歌一样成为恋曲。2010年,学者梁鸿的“梁庄系列”曾经引起学界较大的反响,她以自己的家乡为个案写出了“乡土中国”的衰变,写出一个个乡村灵魂的悲剧,真可谓“悲凉之雾,遍染华林”。
在《寻路中国》的第二部分,海斯勒讲述了三岔村的故事,这个村子躲在深山,但离北京不远,为家庭轿车提供了周末的好去处,申办奥运会也给这个村庄带来了机遇。作者常来住上一段,并与魏子淇一家成为朋友,他甚至覺得这里就是他的故乡。魏子淇一家三口的命运非常有代表性,魏子淇是少数的有雄心和眼光能够抓住了时机的农民。他在家乡发展乡村旅游业,并把事业经营得蒸蒸日上,同时他的酒量越来越大,经常醉酒。妻子曹春梅不仅没能从好转的经济情况中得到想要的生活,反而失去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变得更加操劳,只好将宗教作为依托,由于具体的功利目的,宗教并不能内化为她的信仰。他们的儿子魏嘉是这个村庄里唯一的孩子,他要到很远的学校去上学,他迅速地接受城市的垃圾食品,变成了一个体质虚弱的人,有一次由于免疫性血小板剧减到北京住院,海斯勒目睹了中国医院的霸权,城市医生“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在外国人面前心神不定”。此外,中国农村家庭对医疗缺乏常识,完全可能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拖垮,就是能干的魏子淇也显得沉默寡言,只能听天由命。书中还详细记录了魏子淇竞争村党支部书记失败的过程,中国基层官僚体制的严密性由此可窥一斑。
第三部分,彼得·海斯勒写他经常去的浙江南部离温州很近的一个名叫丽水的地方,可以说他看着这片开发区成长。他突出写了罗守云,一个会操作胸罩调节环的机器的技术员。他80年代就到深圳打工,并将很少的工钱投资到夜校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并凭勤奋和经验掌握了机器的秘密,此后,在不断跳槽的过程中,他掌握了在情大于法的国情中与老板相处的秘密。每次辞职他以老家有突发事件为由请假,将辞职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在丽水王老板厂里,他虚构了一个长子以便使薪水谈判有利于自己,就在工厂陷入低迷的困境之时,他真的有了自己的长子,并让老婆带着刚出月的儿子横跨中国,从贵州的乡村带到了浙江的工业区。新生子迅速适应了机器的轰鸣,适应了工人们的二手烟和人们对他的评头品足,并在返乡途中遭遇了敲诈。除了罗师傅外,海斯勒还写了几位让人牢记的人:同厂的调色师傅小龙,他时常看“励志书”并在墙壁上刻下名言。还有打工妹陶家姐妹,小妹拿着姐姐的身份证来应聘,她的执着使老板只好接受了她们姐妹两人。此时她才十五岁,泼辣精明的她以欺骗的方式获得了工作,敢给自己的领导灌酒,并迅速成为厂里工作速度最快的工人。当她达到法定年龄,她弃厂而去,成为年龄最小却有工作经验的合法打工妹。
在对个案的考察背后,彼得·海斯勒也敏感地发现中国工业区超速发展的秘密在于土地,城市化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MADE IN CHINA”的荣耀背后也有其自身的危机,如环境污染、商业诚信、资源耗竭,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罗师傅“跟靠不住的老板打过交道,自己也违反过合同。他做过那么多胸罩调节环,晚上做梦都想着它们。然而在2009年,他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他开设了自己的公司……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然后卖给中国的工厂”。他的道路是无数打工者的梦想,但也像魏子淇一样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两个人的不同道路代表了当代中国农民可能拥有的最佳出路。他们的背后也同样潜藏着问题,即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而这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未来。海斯勒对魏嘉和罗师傅的新生儿充满友爱与同情。
在《寻路中国》中,“路”既是具体的驾车之路:在西部是一个又一个凋敝的村庄,在东部是一个接一个新兴工业城镇的蓬勃发展,每一个路口都在广告这片土地上经营的事业。同时“路”也是中国通向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的出路。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西方巨大的阴影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主动向西方学习使经济高速发展,但在GDP追求背后潜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海斯勒看来,“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随着产业转型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能否在核心技术和文化创新方面做出贡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20世纪初,我们的祖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我们的学者雄心满怀,《少年中国说》《吾国与吾民》这样大气魄的标题显示了学者的家国情怀,他们主动将个人的学术关怀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今天,数字化掌控着一切,也在切分我们的思想。我们在困顿的现实面前背过脸,躲进自己的书斋里,写离公众甚远的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与思想的分离、论文生产的方式都在日益严重地宰制着这个日趋贫乏的时代。阅读何伟的中国叙事让我为和我们的苟且感到深深的不安。“寻路中国”应是所有人文工作者思考的出发点。
(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