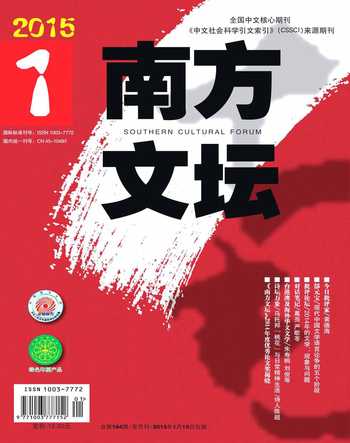隐秘的世界
2015-05-31黄德海
黄德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阅读重点是美学,循着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开列的书单,每天规定自己读起码多少页数的“原典”。当时的想法是,等有一天把这些美学或文学理论的原典全读过一遍,我必将获得开启文学之门的秘密钥匙,写出不同凡响的文章。
那些原典却并未因一个少年的朦胧梦想就轻易打开自己厚重的大门,文学作品里的珍宝也没有因为我自以为是的努力就让我看到光辉。过了一段时间,滥读原典的副作用发作,我不光没有读懂那些大书,甚至连阅读平常书籍的乐趣都失去了。有一阵,我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质疑,竟有段时间废书不观,就更不用谈写作了。
等我在社会里滚过一遭,远兜远转地回到文学评论的时候,半是因为读过的旧理论多已遗忘,半是因为疏于学习蜂拥而至的新理论,这重新开始的写作试验,让我颇为紧张,以致有不知从何下手的感觉。好在,欧阳修和苏轼的一个相关故事及时鼓励了我。欧阳修在颍州任太守时,作《雪》诗,自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字,皆请勿用。”后苏轼效其作《聚星堂雪并叙》,有句言:“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计持寸铁。”白战,即空手作战。虽不像这对师徒一样有而不用,只是腹内原来草莽,但既然已经忘掉了曾经读过的理论,我也就顺势紧紧胆色,试着白手不持寸铁,与作品素面相对,从其本身发现秀异之处。
这个被迫的选择让我有个不经意的发现,澄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美学和文学理论并不是要指导文学创作,也不是要为此后的文学评论提供某种“合法”的理论支撑,而应该恰当地理解为一种有益的写作尝试,用异于文学作品的方式,表达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识。与文学创作类似,美学和文学理论要表达的,也是写作者的独特发现。这个发现一旦完整地表述出来,就确立了其在认知史上的地位,应该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不需要简单的重复使用。进而言之,文学理论最终需要建立在写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系统中,因此,有关文学的系统理論,在起始意义上就几乎杜绝了被挪用的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评论应该回到我们置身的当下,在深入、细致阅读具体作品的基础上,获得具体的感受,回应具体的现象,得出具体的结论。这个生成虽与具体的文学作品相关,根柢却是写作者在阅读时,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有了“发现的惊喜”,并用属己的方式把这个惊喜有效传达出来。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说得确切一点,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一次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那个作者似意识而未完全意识到的隐秘世界。
即使明确了上述的问题,我的写作也并不因此变得轻松起来,甚或说,自此变得更加困难了。每个作品都有具体的语境,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的具体,故此每当面对一个新作品的时候,必须试着去摸清这个作品自身的肌理,并用适合这个作品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每次写作累积的经验,在面对下一部作品时都完全失效,从开头到结尾,都要重新摸索。不断的摸索既迫使我不断回到作品本身,反复体味其中的微妙,却也在很多时候让我三鼓而衰,失去了写作的乐趣。
这个欣慨交心的写作过程,幸赖,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能给人些许鼓舞——并像有朋友期望的那样,形象,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