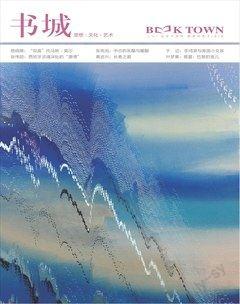“双面”托马斯·莫尔
2015-05-30杨晓雅
杨晓雅

托马斯·莫尔像小荷尔拜因绘于1526年
一
一五三五年七月六日(也有材料记载为7月7日),英国前任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一片唏嘘声中被送上断头台。据历史材料的记载,莫尔因贪污受贿和叛国罪被处死,判词原为:
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街到泰伯恩行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趁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
(《乌托邦》附录中的《莫尔小传》)
最终,亨利八世感念莫尔过去的名望与功绩而“大发慈悲”,将对莫尔的刑罚减为砍头,再将其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乌托邦》1516年版本中的木刻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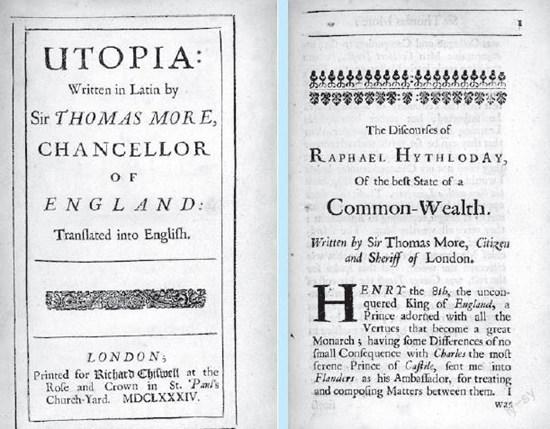
《乌托邦》早期英译本
说到莫尔,他身为作家和空想社会主义先驱的名声已与《乌托邦》一书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伊拉斯谟曾在一五一七年二月给好友的信中写道:“当你阅读莫尔的《乌托邦》时,你就会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一切都很新鲜。”稍过几日,他又忍不住写信对自己的另一位朋友说:“如果你还没有阅读过《乌托邦》……如果你想……弄清楚一个国家中几乎一切罪恶产生的根源,那就请你设法弄到此书来读一读。”通过伊拉斯谟的热情推荐和推广,更多人文主义者慕名拜读,在阅读了《乌托邦》之后对其大加称赞,并一致认为:“只有莫尔设计的乌托邦在社会生活中吸收了……基督教的风俗和真正的明哲,并在个人生活中至今还使它保持一尘不染,这是因为……作者非常赞成维护三条神圣法则:公民平等……对人类的永恒和坚定的爱情……对金银财富的蔑视”,“乌托邦人的这三条基本法规能够成为大家心目中坚定信念的主要支柱”,将“重现美妙的黄金时代”(奥西洛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
现在回望起来,五百多年前,《乌托邦》就像一本在莫尔的“好友圈”里被频繁转发的小册子。它虽被广泛传阅和论及,但也得裹着当时流行的旅行文学的外皮,毕竟,除了带给读者阅读的新奇和愉悦之感,从政治敏感性上说,这在当时又是一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危险之作。尤其是第一部里描写英国现状的文字,用词用意都带有对政治权威与体制的挑衅和指责。从《乌托邦》在欧洲早期的译本传播证据上看,便可知其“命运多舛”。一五一六年,《乌托邦》的首版出现在比利时的鲁汶。到一五一九年,最初发行的五版《乌托邦》均为拉丁语,但具体内容却各不相同。《乌托邦》的译本最早为德语版、意大利语版和法语版,分别于一五二四年、一五四八年和一五五○年发行。但这三个译本都因各种限制将莫尔的原作改得“面目全非”,有的第一部已完全被删除,有的書中人物被更换,有的甚至连书名也并非“乌托邦”。英译本《乌托邦》于一五五一年问世,内容必然有所篡改。直到一六六三年,拉丁语原版《乌托邦》才得以在英国发行,这距莫尔首次将它公之于众已有近一个半世纪。(G.M. Log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Mo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乌托邦》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与它所爆发的顽强生命力,也恰好应和了莫尔不曾坦然公布的野心,与看似谦和背后的强硬。
二
莫尔热爱写作,工作之余便勤奋练笔。按历史材料记载,在莫尔一生的作品中,大约有二百五十多篇诗文用拉丁语完成,其中包括论述性散文和讽刺短诗,当然,还有献给亨利八世加冕的一些长诗。在莫尔的拉丁语讽刺短诗中,以政治题材居多,随处可见对现实政治格局的隐喻描述。从写作修辞技巧上看,莫尔善于运用矛盾式表达,以营造出一种对立冲突的文体效果,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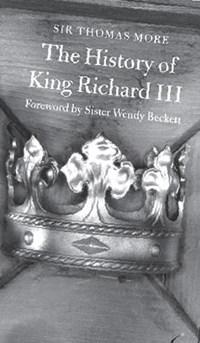
《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托马斯·莫尔著
白玫瑰红玫瑰挨着生长,
他们开始竞相争夺王冠。
啊,红白玫瑰融成一片,
休战,花儿朵朵吐芳香。
(转引自《托马斯·莫尔传》)
以上诗节出自莫尔的一首不知名的讽刺短诗,暗指玫瑰战争和都铎王朝登基的问题。在英国历史上,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徽章里分别绣着红白两种玫瑰。亨利·都铎是兰开斯特王朝晚辈中的杰出代表,在一四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波斯沃尔特会战中战胜了原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三世,夺取了王冠。而他也只有在迎娶了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之后,才能在自己的徽章中把红白两种玫瑰结合起来。莫尔以此做诗,语言精练,题材敏感,他期盼着一个能给予国民幸福生活的新君主的驾临,又提倡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政治体制。这足以让读者一眼瞥见莫尔在政治上的大胆与坦率作风。
在创作《乌托邦》的同时,莫尔还在撰写《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一书。《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是莫尔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历史著作,直接影响了莎士比亚对同名历史剧的创作。因为在莫尔生前从未得以发表,许多研究者曾一度怀疑莫尔并非此书的作者。在书中,理查德三世被刻画成一个老奸巨猾的伪君子、独裁者、权力狂,他杀害自己年幼的侄子而篡夺王位,可谓名副其实的“卑鄙凶手”。从全书的记述手法看,作者似乎对爱德华四世和理查德三世时期的政治生活和官场风流韵事了如指掌。由此推断,作者长年深处政治斗争的中心,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也想通过作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敌意。在莫尔被处死三年后,一位大臣在被审讯时提到莫尔就是《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的作者。莫尔死于叛国罪,当时触及这个话题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一五四三年,《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首次问世时只是被编入了另一部历史纪事中,并且未提及作者的名字。
长期以来,学界对《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的真实作者还存在其它的猜测,比如有学者认为,它是莫尔年少时的启蒙导师红衣主教莫顿用拉丁语所作,而后由莫尔将其译为英文。对此说法,伦敦大学的著名学者钱伯斯在作了大量文献考证之后提出反驳,并指出莫尔应该先是整理并阅读了莫顿去世后留下的一些拉丁语手稿,再把它作为素材来撰写此书。他先是用英语撰写,之后又把它译成了拉丁语。这也是当代学界最具权威性的一种推断。从写作手法上来说,《英王理查德三世本纪》在莫尔的所有作品中评价极高,被赞为“一个精心设计、细心完成的整体,比例恰当,无懈可击”。莫尔通过对十五世纪英格兰腐朽皇权的揭露和批判,将舌灿莲花的修辞技艺展露了出来,让崇拜他的读者透过他平时一贯温和的外表,捕捉到某些危险而具有颠覆性的观点。这无疑也能满足他身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应有的虚荣。但莫尔为何不愿将它彻底完成呢?为何不愿将它在有生之年出版呢?或是言不由衷?或是身不由己?
三
莫尔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歷史人物,这一点在他对于宗教的态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关于乌托邦的宗教设想中,莫尔已表现出当时欧洲罕见的豁达,说道:
不但乌托邦全岛总的来说有各种宗教,在每个城市也是如此。有人崇拜日神,有人崇拜月神,又有人崇拜其他某一种星辰。若干乌托邦人尊敬以道德或荣誉著称的先贤,把他当作神,甚至最高的神。(《乌托邦》)
莫尔提倡宗教自由,他和好友伊拉斯谟都站在了十六世纪主张宗教宽容的先驱者行列,认为宗教自由既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真正的宗教的利益。莫尔这般开放的宗教态度,似乎针对的是当时基督教会对异教徒以及带有异教思想的人所施加的迫害,由此也让《乌托邦》成了一部争议之作,在发表之初便被判定为宣扬异教文化。不过,说到这里,问题又出现了,按历史材料记载,莫尔同时也因其镇压异端的暴行而背上过一个历史的“骂名”。
莫尔支持信仰自由不假,在镇压异端势力时也的确是不遗余力。他在担任大法官一职时,就曾把路德派信徒投入监狱审训,还将六个改革派人士判处死刑,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他逮捕过许多所谓的禁书持有者,亲自在法庭上对他们进行审讯,再把他们送进伦敦塔、弗利特监狱或康特监狱。大多被宣判为异端的人,要被架在马上游街示众,他们面对马尾,衣服上缀着自己说过的各种反叛之词。这些人差不多被莫尔折磨成了记载和惩戒异端势力的“活体书”。曾有一个囚犯的仆人想给主人一点帮助,于是写了一份陈情书上交议会,莫尔得知后便派人把他也投入弗利特监狱。为了搜查禁书,莫尔还突袭过一个商人的家,再把他投入伦敦塔,任其死于阴冷的牢狱。总之,在镇压异端的过程中,这位许多人口中的“软心肠的理想主义者”毫无收敛地表现出了野蛮与残暴的一面。这不但与他平时儒雅温和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大相径庭,更使得我们不愿把这些行为与他的人道主义理想联系起来。

罗伯特·鲍特的剧本《四季之人》

《四季之人》电影海报
不过,莫尔自认为在处理异端的问题上是有分寸的,他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但因为异端肇事在先,他便坚持“以暴制暴”。在《关于异端的谈话》一书中,莫尔写道:“如果他们(异端)不曾诉诸暴力,善良的基督徒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对他们使用那么多的暴力……异端像任何其他罪行一样受到严厉惩罚,完全是罪有应得,因为没有比这更冒犯上帝的罪行了……只要异端不诉诸暴力,几乎不会用暴力来对付他们。”(A Dialogue of Comfort against Tribul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在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在维腾堡教堂大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前,莫尔对异端的这种态度就已形成。我们在《乌托邦》中可以看到莫尔清楚地写道:“在传教时使用任何暴力都是不允许的,如果为宣传自己的教义而在群众中煽动事端,就要受处罚。”
四
莫尔个人形象的风格化,则是基于历史材料记载的后续文学性建构。一直以来,由于自身的悲剧命运结局,再加上《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渲染,莫尔成了人们心中一位正直而博学的历史传奇人物。处于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带有一种孤胆英雄式自我牺牲精神,因而也常被后人称作“四季之人”(the man for all seasons)。“四季之人”作为一句英语俗语,用于形容一个在各方面都能力卓越并表现出色的成功人物,其重要性足以永垂青史。若上升到政治话语的修辞性高度,则用来强调随时随地都会站出来独当一面,并勇于承担国家责任的英雄式人物。
莫尔被尊称为“四季之人”,主要还得归功于二十世纪英国剧作家罗伯特·鲍特的作品《四季之人》。一九六○年,鲍特以莫尔的生平为蓝本创作了这部舞台剧,主要讲述莫尔人生最后阶段的生活,塑造了莫尔正直正义的为人处事风格。几年之后,剧本被改编拍摄为电影,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映,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一致的好评,并荣获次年第三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六个重要奖项,是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传记性佳作。片名“A Man for All Seasons”被译作“良相佐国”“日月精忠”“正直的人”等。由此可见,汉语观众(台湾、香港与内地)对莫尔人物形象与人格力量的认知与接受,显然是再积极正面不过了。
在剧本扉页,鲍特引用了两段前人评价莫尔的话。一段是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对莫尔最为坦诚的赞颂—“这个国家(英国)所产生的拥有最高美德的人”;另一段,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家罗伯特·惠廷顿对莫尔由衷的感叹:
莫尔拥有天使的智慧与非凡的才学,我不知道还有谁堪与他媲美。哪儿还能找到这样高贵、谦逊又亲切的人呢?他既能为我们带来惊喜和愉悦,又能让我们产生一种悲伤的庄重感:他就是一位四季之人。(Robert Bolt, A Man for all Seasons: A Play for Sir Thomas M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Publishers,1996)
按《四季之人》中的讲述,当时的莫尔已因《乌托邦》的出版备受争议,同时也受到了人文主义者和平民百姓的褒奖和拥护。剧中的莫尔:

亨利八世像,小荷尔拜因绘于1537年
年纪已将近五十。面色偏白,中等身材,并不强壮。然而,他的自我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這让他显得容光焕发。他的动作举止大方而敏捷,但又不显粗野,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节制与温和。他长着一副智者的脸庞,随时会浮现出愉悦的表情,但也随时会显得严肃和慈悲。只有在面临高危的情况下,他才会变得像一位苦行僧或禁欲主义者一样阴沉,而后则表现得越来越冷漠。(A Man for all Seasons: A Play for Sir Thomas More)
如此一来,莫尔的深思与善变又为他添加了某种气质上的神秘感与不确定性。鲍特通过细致的描述,凸显出莫尔性格的“双面”化,这也是对莫尔形象的一种更为真实贴切的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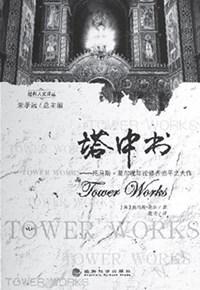
《塔中书》托马斯·莫尔著 殷 宏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对莫尔的“双面”立体刻画,让另一位声明显赫的历史人物亨利八世显得单调“扁平”了许多。在介绍出场人物时,鲍特便用一句话点明:“这完全不是小荷尔拜因肖像画上的那个亨利。”小荷尔拜因画笔下的亨利八世已人到中年,蓄须,稳健而威严。与此不同,鲍特用文字描述的亨利八世则是一个“看似年轻很多的国王,胡子刮得很干净,两眼发光,举止优雅,体格健美。他就似欧洲宗教改革的金色希望。而他在掌控权力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轻浮多变,预示了他今后的腐败与堕落”(A Man for all Seasons: A Play for Sir Thomas More)。鲍特的文字,直指画像上的虚假。很多时候,当后人要了解或瞻仰一位被冠以伟名的历史人物时,首先便会从肖像画上去探其英姿相貌。大多怀着政治雄心的历史人物,会以要求或命令的口吻让画师按自己的意愿来记录和展现自己。那么,不论从神情、姿态,还是从服装、场景上看,画像上的那个伟人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其本人所期望的权力的投射,试图从视觉感知的第一步便让观者臣服。经过画师的画艺雕琢,在真实的人物与遗存的画像之间,常常是临摹混合着虚饰,从而让历史也真假莫辨起来。
《四季之人》中的莫尔一出场便备受亨利八世的爱戴和重用,可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正陷入一片政治的泥潭,而他所坚持的立场显然无法迎合国王的要求,其冲突导火线便是莫尔拒绝参加亨利八世第二任王后安妮·博林的加冕典礼。莫尔陷入矛盾与困窘,他作出决定,就此远离宫廷政治纷争,全身心地回归自我与家庭。可以说,莫尔试图躲进自己的乌托邦以寻求庇护,而这样一个乌托邦似乎更具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世外桃源意味。至于最后的结局,可谓是身不由己又无处可逃。莫尔的行为和态度不但没有得到亨利八世的体谅,反而使得亨利八世对他耿耿于怀,并想方设法对他进行挑衅、陷害和污蔑,将他逼入臭名昭著又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五三四年四月,莫尔被囚于伦敦塔,在独自静候审判的同时,他仍潜心撰写寄托人世与宗教情怀的作品《塔中书》。最终,这位从现实的名望巅峰直坠顶底的“四季之人”,被以贪污受贿和叛国的罪名送上断头台。
五
据历史材料记载,与莫尔同时代的很多正统的理论家都非常厌恶莫尔那种故作幽默的嘲讽姿态。比如教会的僧侣们就曾公然指出莫尔有一种“笑谑癖”,并谴责莫尔玩弄修辞技巧,惯于用双关语、俏皮话和笑话对待最重要的事情。对此,莫尔本人在回敬这些指责时,依旧直言不讳地逗趣说:“作为一个俗人……较之用严肃隆重的腔调来说教,我更爱好以玩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并更青睐这种“在嘲笑中说出真理”的方法。当学者与读者对他撰写的历史文稿表示怀疑或追捧时,莫尔又会异常冷静地表示:“我们不该相信形形色色的人们所说的五花八门的事情,他们好像在说真事一样。”当莫尔自己陷入矛盾和烦闷时,也会如平常人一般写信向好友抱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到处是狠毒的诽谤和强烈的嫉妒,到处是恶魔在统治着人间……”(《托马斯·莫尔传》)总之,不论被厌恶还是被妒恨,莫尔笑谑着,也抱怨着,也看似慷慨大度地为自己招来更多的敌对与争议。
从当下文学阅读和消费的情势来说,莫尔已不再是(或者根本就很难被算作是)一个能让广大读者热烈追捧的作家。但拨开尘封的历史,探入或旧或新的无限文本所编织的巨大网络,细细品察,就会发现,莫尔似乎已化作一个自由的“幽灵”,在广阔而漫长的时空中从未停息地游荡穿行。客观地评价莫尔的一生,他绝对算得上当时欧洲跨越政坛与文坛的“风云人物”,同时还权居高位,身兼数职。他虽言行古板,思想却标新立异;虽深悟权术,却退而与世无争;虽孤高淡漠,却宽容和善地与这个世界相处;虽已不再言说,却润物细无声地对后世作者们产生着不尽的影响,悄悄躲进他们作品中那些争议不断的角落。莫尔无疑算得上是一个博大而谦卑的“有故事的人”,以他不长不短(终年57岁)的一生,傲然而沉重地诠释着一种朴实而跌宕的文学艺术性。曾让人不胜唏嘘的是,正是这位德高望重又受众人夸赞的典型“伟人”,最终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还人头落地(差点被五马分尸)的下场。然而,让人颇感欣慰的是,一切赞颂或诽谤、荣耀或屈辱、褒奖或贬斥,以及真实或虚构,在经过历史与文本的记载、描写、续编与保存和沉淀之后,使得莫尔其人其作在英国、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永葆声名,并散发着持久而厚重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