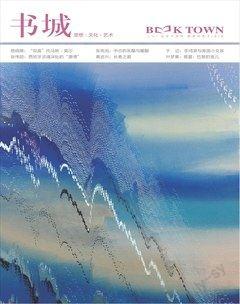在伦敦寻访比亚兹莱
2015-05-30徐霞
徐霞

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
英国十九世纪末的鬼才画家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在当时欧洲文学艺术界引起过轰动,比如为王尔德绘《莎乐美》插图,为文学杂志《黄面志》(The Yellow Book)做美术编辑的一系列作品,都曾引发争议,其颓废唯美的画作成为世纪末艺术的一大代表。在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代,比亚兹莱在中国的新文艺界也引起阵阵战栗。

比亚兹莱故居
一九二三年,田汉将Beardsley一名译成唯美的“琶亚词侣”,出版其翻译的《莎乐美》剧本,并隆而重之地引入原版“琶亚词侣”十六幅插图。而本文所用之“比亚兹莱”译名为后来学术界的定名,实受一九二九年鲁迅的“艺苑朝华”系列刊印《比亚兹莱画选》一书的影响。比亚兹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界卷起的旋风,波及一众作家,如郁达夫、邵洵美、叶灵凤、梁实秋、闻一多等人。本人在研究比亚兹莱与中国这一课题后期,走访了伦敦比亚兹莱故居,也亲临收藏比亚兹莱真迹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向馆方申请翻阅比亚兹莱真迹。本文则为此次伦敦寻访比亚兹莱的一些记录。
一、V&A 探真迹
二○一四年五月七日,星期三早上,伦敦的春天微雨。吃完早餐从Holborn地铁站出发,二十分钟后,就来到了South Kensington站,这里博物馆林立,我的目的地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简称V&A)。

V&A研究画室内部

V&A研究画室的藏品盒子
出发前一星期,我在香港埋首V&A的網页查寻Aubrey Beardsley的资料,果然,通过V&A网页查到他们收了与比亚兹莱相关的作品共一百多件,现时没有一件在展出,但基本上每件作品都有编号、库藏位置、展出历史、收藏源头、内容介绍等。只看网上的数据库,对比亚兹莱已可有相当的认识,不得不赞赏英国博物馆的专业细致。更令人吃惊的是,收藏这些比亚兹莱作品的部门Prints and Drawings Study Room居然有预约观赏服务,每次只限作品五件,提前把要看作品的编号电邮或电话告诉他们,约好时间准时到达即可。我在香港向V&A提出电邮申请后,两三天内,馆方已回复时间可以。到预约日前一天,更收到馆方的提醒电邮,告知详细集合点,并附上地图。
就在这样一个微雨的早春,穿过伦敦地铁站长长的隧道,一上地面就到了V&A入口,问了保安集合点在哪,就看到有个穿制服的中年男子手拿着访客证在等我们。原来同一时段,还有四位预约者,两位是来自意大利读建筑的学生,还有两位是中年教授。我们六人由保安工作人员带领,穿过博物馆大大小小的房间、走廊、楼梯,终于来到Prints and Drawings Study Room。
为什么会找到V&A 博物馆? 一切源于斯蒂芬·凯洛威(Stephen Calloway)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奥博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一书。一九九八年比亚兹莱逝世一百周年,凯洛威在伦敦和东京为比亚兹莱策划纪念画展。此书乃为纪念比亚兹莱逝世一百周年出版。V&A在英国一众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中定位非常清晰,收藏英国以及全世界的工艺美术作品。此馆建于一八五二年,源于艾伯特亲王在一八五一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大受好评,于是索性建成工艺装饰品博物馆,展品收藏横跨三千多年,从绘画到玻璃、从雕塑到服装、从古书到珠宝,应有尽有。
比亚兹莱作为英国十九世纪末代表性的插图、装饰画画家,他的作品理所当然应由V&A收藏。而由V&A的策展人来写作比亚兹莱的专书,在资料方面,肯定更为专业可靠。在凯洛威的书中,基本上所有比亚兹莱的画作,都有作品源数据,而一些属于V&A藏品的,更有博物馆收藏编号,方便有心人查找。

《亚瑟王之死》插图手稿
博物馆规定每次预约只能看五盒资料,V&A收藏比亚兹莱相关作品共有一百四十份左右,收藏在不同的盒子里。我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看比亚兹莱的真迹,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由于我不是从美术角度研究比亚兹莱,此行目的主要是朝圣这位触动二十世纪一代中国文人心灵的英国画家的真迹,心情比较放松。博物馆工作人员叫我放下行李,但可以带相机、计算机,还示意可以拍照。这间学习室放着三张大长桌,其实可供几十人同时看资料,而今早只有我一个人,另外的几位去了旁边的小研习室。工作人员已在长桌上放好一个蓝色大盒。这位中年女士细心地教我如何打开盒子,如何把画片拿在手上观看,如何放下画作。打开这个约一米长的盒子,一百多年前比亚兹莱的《莎乐美》呈现在我眼前。
由于V&A收藏的比亚兹莱画《莎乐美》是一八九三年的印刷品,并不是原画手稿,我就跑去服务台问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拿起凯洛威的书就帮我找数据,还用内部计算机给我看他们手头的数据,非常乐于助人。虽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印刷品,但其质量和今天的没两样,厚实的纸张,清晰有力的线条,想象当年买到王尔德书的读者,看到比亚兹莱的插图,完全被吸引住了,难怪王尔德感觉被抢风头。
比亚兹莱为《阿瑟王之死》(Le MorteDarthur) 画了数百幅的插图,其中有部分的原稿在V&A,我预约的其中一张代表作,《在五朔节出巡的关妮薇王后》(How Queen Guenevererode on Maying)的作品上甚至能看到比亚兹莱擦去的铅笔手稿印痕。《阿瑟王之死》是比亚兹莱初入伦敦艺术圈的作品,在这本书的一系列插图中,能看到比亚兹莱画风成熟的轨迹,其坚定利落的线条不是天生的,从我手上捧着的那些铅笔印痕,仿佛看见一个燃烧自己生命的艺术家,如何努力地在钻研画面的线条,希望在作品中开创自己独特的风格。

比亚兹莱为《莎乐美》所作的插图
十九世纪末装饰艺术好以藤蔓花草入画。比亚兹莱的手稿中,这些藤蔓植物的线条柔媚自然,在黑白构图下,一百多年后,黑色的墨水出现深浅不一的情况,令人更加怀想比亚兹莱当初如何手执墨水笔,在两支蜡烛的映照下,先用铅笔起草,再用钢笔定稿,一笔一画、一点一线慢慢经营画面。这一丝不苟的黑与白穿越了整个世纪,而今以静默的姿态躺在V&A的蓝色大盒里。

伦敦市政府设置的名人故居牌子
V&A收藏的比亚兹莱作品放在这些硬皮蓝纸盒中,大部分都用白色的硬卡纸裱过,一些零碎的作品就用胶片夹着。工作人员在每张画作的硬卡背面都有铅笔的记录,盒中还有工作人员核对画作编号的手写记录、借阅记录,有些特别的作品还有附注,如从哪个画廊买的。在V&A的网页上,很多作品已数据化,但能亲身来博物馆,那么近距离地看,甚至摸到比亚兹莱的作品,是我之前不敢想象的。
二、剑桥街访故居
比亚兹莱在英国艺术史上不算一个大人物,所谓的故居只是门口挂个蓝底白字的牌子而已。在Google年代,计算机能让你在香港看到英国某条街道上开了什么花,所以这次探访比亚兹莱故居前,我在Google地图上查伦敦剑桥街(Cambridge Street)一一四號时,已把故居门面弄得一清二楚。
五月九日的早上,伦敦大风,春天的花粉吹得人眼睛疼。比亚兹莱故居位于两个地铁站中间,我决定把这两站之间的路走一遍,感受一下一八九四年比亚兹莱住在这一区的生活环境。比亚兹莱的居所位于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和Pimlico地铁站中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上阶层住宅区,街道排列整齐,一排排浅黄色三四层楼高的百年住宅优雅耸立。

马车与汽车交互行驶的老街

剑桥街上的圣加百列教堂
一出地铁站,就见到一座石砌哥德式旧教堂,忽然马路上传来一阵马车声,有两位穿着黑色礼服戴高帽的绅士驾着马车,后面还跟着两匹马,由两位穿着骑士服的女士骑着。此等情景,真让人有时空错乱感。明明街道上有许多汽车,到了路口,马车停下,绅士向汽车打手势,原来马车要转弯了。此情此景,让我想象起一百多年前的比亚兹莱,在家门口坐上马车去剧院听歌剧、赴朋友午宴的情形。
伦敦的海德公园特设供马匹散步的沙圈,原来这些骑马的贵族也会把马骑上车来人往的马路。从古旧的石教堂到街头的马车,这一路走向剑桥街的比亚兹莱故居,慢步大约要十五分钟左右。沿途除了三层楼高的民居外,还有一间公立艺术学校。这些白柱黄砖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通常都挂着白窗纱,偶然让人看到地面那一层的客厅。
街道非常寂静,眼前又是一座教堂,名为圣加百列教堂(St. Gabriels Church),在教堂的正对面,就是比亚兹莱住过的一一四号住宅。今天正在维修,屋外搭了棚架,有个中年男人爬在棚架上检查墙面。教堂和比亚兹莱的屋子面对面,走过去五六步就到,相隔才七八米左右。
这一区在一百多年前可说是伦敦的中上阶层住宅区,比亚兹莱在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曾居于此。这段时期,正是他任《黄面志》文学杂志美术编辑的风光时代。比亚兹莱因着奇异而突出的画风,突然在伦敦艺术圈走红,剑桥街一一四号是比亚兹莱在伦敦建立社交圈的重要舞台,而这一切,少不了这所房子中居住的两个女人,梅布尔(Mabel)—比亚兹莱的姐姐,爱伦(Ellen)—比亚兹莱的妈妈。
梅布尔才华出众,音乐、文学、艺术都有相当深的造诣,她和伦敦艺术圈中的人物也相熟,如诗人叶芝(W.B.Yeats)就是她的朋友。梅布尔是歌唱家,伦敦剧场里的舞台剧演员。有这样一位女主人在这所宅子中举办星期四下午茶会,艺术圈的朋友都很乐意来这里喝茶、谈天,更何况,她最亲密的弟弟比亚兹莱是当时最走红、最具争议性的插图画家。在下午茶会时,比亚兹莱会拿出最新创作的图稿,让朋友传阅,请大家提提意见。这个文艺沙龙,在姐姐梅布尔的细心打点下,成为比亚兹莱进入伦敦艺术圈的重要舞台。在凯洛威的《奥博利·比亚兹莱》这本书中,刊印了一张一八九五年这所房子的外部照片,书中更有一九五○年代房子内部装饰的相片,更有意思的是,书中还找来一八九五年比亚兹莱姐弟因经济压力被逼卖出房子后,地产代理人出售此宅的广告。
广告标题与引言如下:“小巧家庭式住宅/位处城市中央地带,舒适方便的住宅区,宅子正对圣加百列教堂,步行五分钟即到维多利亚火车站。”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我从Pimlico地铁站出发,沿途走过这些百年老屋的大街,到达剑桥街后,再走向维多利亚火车站,散步是大约十分钟的距离。维多利亚火车站是百年老站,有开往布莱顿的火车,想来当年比亚兹莱和他的家人正是从这里坐上往返伦敦与家乡布莱顿的火车。虽然比亚兹莱在英国十九世纪末的美术史上颇有名气,但放在整个英国历史上却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比亚兹莱去世时才26岁),这所比亚兹莱居住了三年不到的宅子在一八九五年卖给Miss Pugh后,一直为私人转手拥有,也没有改建成任何供人参观的博物馆。这次的探访当然也只能站在门口及屋子周围探视。当天见房子外墙搭了建筑维修架,有位中年男子在架上做外墙检修。转了个圈,忍不住和维修架上的男子搭讪,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是业主,房子现在除了他自住外,也有些房间租了出去。
看一八九五年这所房子的地产广告,地库作厨房及储物室,地面一层为餐室,一楼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新艺术风格装修的两个客厅,装修颇为别致,有木地板、壁炉、大书架,大大的玻璃窗外是阳台,当年比亚兹莱和姐姐就是在这里和伦敦文艺圈的朋友茶会,在火炉前,画家拿出画稿,歌唱家姐姐准备好了茶点,大家对艺术、文学、戏剧高谈阔论。二楼及阁楼为卧室,这所房子当时已有卫生间,还有煤气及冷热水供应。在当年朋友的回忆中,这所房子有黑色的大门,橙红色的条纹壁纸,黑色大书架,而比亚兹莱的卧室中则挂了日本浮世绘画作。
今天,这所房子的内部当然有了很大的变动,英国人重视隐私,更何况房子也分租给不同的租客,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屋主要求入内参观。于是我问屋主,这房子和一百年前比有什么大变动吗? 他说地下室重整过,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今天看到的装修,应在做外墙维修,这条街上的连排屋都是浅黄色的砖,唯独这间比亚兹莱故居一一四号,砖是深咖啡色的。这所房子建于一八五二年,属于维多利亚时期,但建筑风格却承接乔治亚时期的简洁明快。
正面对着这房子(相隔不到十米)的是建于同期的圣加百列教堂,这座哥特式天主教堂有着相当漂亮的彩繪玻璃窗。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每一天,比亚兹莱出门或回家,从家中的任何窗口望出去,就是这座教堂的正门,高尖屋顶上的十字架,石墙前的大树,幽静的小花园,这些与当时画出颓废、情色、怪异的世纪风格画作的比亚兹莱是那么格格不入。然而没想到的是,在比亚兹莱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在法国南部小城芒通(Menton)的旅馆中,比亚兹莱在好友及神父的影响下,终于信奉了天主教,成为上帝的信徒,在去世前要求朋友把他的一些情色画作烧毁。不知道在他信奉天主领洗的那一刻,有没有回想起生命中最辉煌的三年,和家人一起最温馨的三年,伦敦剑桥街一一四号,门外窗口时时刻刻看到的圣加百列教堂,这座以《圣经》中的守护天使命名的教堂,有没有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后记]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伦敦春天的早上,我从比亚兹莱故居走向维多利亚车站,沿途大风微雨,行道树高而绿,繁花似锦,空气中都是花粉的微粒,我一路泪涕交零。
在回香港的飞机上,维珍的红衣空姐和我闲聊,我抱怨伦敦的天气,说起了自己的花粉症,在街上眼泪鼻涕直流,但奇怪为什么看不到伦敦人戴口罩。空姐调皮地回应我的抱怨:“这才是伦敦嘛! 他们死都要型,怎么会戴口罩呢?”
是啊,死都要型,比亚兹莱二十六岁就去世了,但他的作品,不正是“型到爆”吗? 让整整一个世纪的人都念念不忘,甚至在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