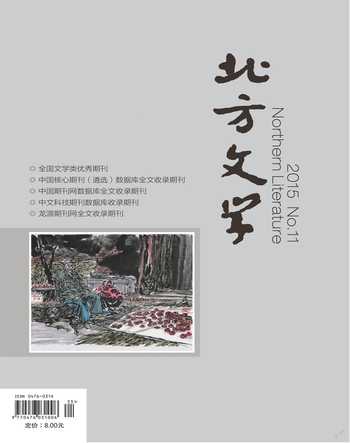《绣枕》:巧妙反讽下对女性精神独立的呼唤
2015-05-30叶倩
叶倩
摘 要:小说《绣枕》以温婉平顺的笔触,叙述了一个深闺大小姐两年前后的故事, 简短而意蕴深长。“绣枕”这一意象贯穿全篇,不仅是古代封建社会对女性“妇功”的要求,也喻示着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凌叔华构建了巧妙的反讽,表达了对女性树立独立自主的意识,争取话语权和追寻自我价值的希冀,从而获得了一种张力。
关键词:反讽;妇德;女性;独立精神
凌叔华以短篇小说见长,其《绣枕》简短而意蕴深长,平静叙述的文字中有其独特的力量。“绣枕”意象贯穿全文,用反讽巧妙地表达了对女性树立独立自主意识,争取话语权和追寻自我价值的深情呼唤。
一、“绣枕”意象:沉默无力的妇德
在这篇小说里,串联全文的意象“绣枕”,承载了别样的意蕴——沉默的妇德。儒家经典《周礼》,曾规定古代妇女应当具备的素质:“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功谓丝枲”①《礼记·昏义》亦有“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②当中的“妇功”,即纺织、刺绣、缝纫等女红。这“四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构成了中国妇女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绣枕》里的大小姐,做得一手好活计,能绣出“真爱死人”的漂亮靠垫。仆人张妈说:“大家看了,别提有多少人来说亲呢。门也得挤破了。”可见女子妇功好,便意味着她贤良淑德,也不愁婚嫁。凝聚了大小姐多日心血的精美绣枕,自是象征了她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四德之一。
但“妇功”本身便包含着对女性话语权力的限制,乃至剥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时代,男耕女织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男子田间劳作,女子料理家事。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力、手工业为辅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男性掌握政治经济权力,女性依附于家庭而没有话语权的事实。《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就有:“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③女子不应该玩闹嬉笑,而是专心纺织,准备酒食。古书中不难见到类似对女性发言的限制。
而《绣枕》里的大小姐,在家庭里几乎可以说是处于失语的状态。小说以大小姐低头绣着靠垫为开端,只语未出,只偶尔对张妈的搭话给予回应。而这听从父命而为的绣制,便已说明了她的依附地位。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她依旧沉默寡言:“忽然心中一动”“没有理会……却只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只管对着这两块绣花片子出神”“默默不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顶片儿。”④以无声开端,用无言收尾,小说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首尾呼应。大小姐对于自己的事情,不曾具备任何话语权。听从和等待便是她的行为模式。得知精心绣好的靠垫被糟蹋、被随手丢给仆人后,她已然明白自己在家庭的地位和价值,却根本无力改变,“摇了摇头算答复了”。绣枕意象,体现了中国传统观念妇德,更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和地位的缺失。
二、对比叙事:巧妙反讽的张力
《绣枕》全文2362字,在叙述场景中出现的人物只有大小姐、张妈及其女小妞儿,其他人物均只存在于三人的对话中。这篇幅简短、毫无冲突情节的小说,在温婉平顺的叙述调子中,却充满各种反讽,表现出一重又一重张力。
大小姐精心绣制半年、光是一只鸟就用了三四十样线的精细靠垫,在送去白总长家的当晚便被糟蹋;小妞儿特意从乡下跑过来只求看一眼靠垫,被嫌脏而不得,却在两年后意外得到;曾经梦见过自己的娇羞傲气和他人的艳羡,大小姐终知那只能是幻境而不愿再想起。上述种种,都比不上最大的讽刺:两年前她熬着酷暑来绣那意味着交好乃至结亲的靠垫,两年后,她仍在深闺里做着针线活。
这个反讽足显作者的匠心独运。小说由始至终只有一个场景:上房,即大小姐的房间。在上半部,小说营造出了一个寂静的、近乎被幽禁的空间。在酷夏的房间里,大小姐低头专注绣制,身旁只有张妈。除了狗的喘气声、绣花针上下穿缎子的声音和扇子呼出的风响外,就剩下主仆二人偶尔的对话声。到了下半部,在同样的上房和夏夜,仆人变成了小妞儿,而“光阴一晃便是两年。”在流逝的年月里,大小姐的生活仿佛从来没有发生变化。她的活动范围一直局限在同一个房间,生活内容依然是针线活。上房似乎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她看不到别人,别人不会来见她。但她又并非隐居世外的超脱之士。外界,实际有着强烈的影响力。男性和长辈,不曾出现在房间里,他们存在于主仆的对话中:“他说了明儿早上十二点以前,必得送去才好。”⑤“听说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适亲事。唔,我懂得老爷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诉太太今年你有红鸾星照命主……”⑥大小姐的期待,来自于张妈和算命先生的谀辞;她的失望,是没有出现预想中的说亲;而她至今仍在等待,重复枯燥的针线活,竟是因为没有婚姻!大小姐安逸的生活,是对他人安排的被动等待;居住的安静房间,实为一种幽禁;而她这个所谓的“大小姐”,实则是封建家庭和男性的附庸而已!那对怀有缔造者心思和期待的绣枕,它们的被践踏,也就意味着大小姐的受辱。没有强烈的冲突,没有激昂的语言,《绣枕》在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着巧妙的反讽张力。
三、无言结局:精神独立的追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常见女性意识觉醒、不堪忍受专制冷酷的家庭,为自由而出走的情节,抑或是对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挣扎的矛盾状态的再现。凌叔华的许多小说,亦是对这个时期家庭生活情状的呈现,对女性思想和命运的探索。她的笔触,围绕旧式中上阶层的太太、小姐、老爷、少爷、官僚、女学生、不长进的青年展开,《绣枕》里的大小姐便是典型。这一形象最为可悲之处,在于其自我意识、人格追求、灵魂深度的缺失。
待在深闺里的她,听到张妈关于亲事的絮叨,那“微微红晕”透出了她的隐隐期待。但她期待的是爱情的甜美吗?不,是“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此生未有过的衣饰”、“小姑娘的羡慕”和“女伴的嫉妒”!这种对华美滋润生活的想象,固然有对嫁做人妇、受人疼爱的期许,却没有个人的精神追求。假如对方不是白家而是另一个高门巨族,对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她的想法仅限于做一个贤惠而华贵的良妇,至于什么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女性解放的思潮,似乎完全隔绝在这个深闺之外。作为男性和家庭附庸的她,没有个人独立的意识,没有精神追求,被动地接受现状。婚姻是她唯一的归宿。小说以大小姐的无言摇头作为结局,预示了她的将来:这朵等待安排、枯等垂怜的花,一旦无人欣赏怜惜,结局除了孤独凋谢还能有什么?
那么凌叔华,是借这篇小说,高举女性解放大旗,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号召女性冲破家庭的束缚吗?或者说,《绣枕》叙述大小姐专注针线活而没有任何冲突的生活,它只是一篇描写旧式家庭无聊生活的小说吗?其实不然。出身官宦人家的凌叔华,是真正的深门大院里的大小姐,她比大多数人都要了解当时女性的生存困境。她对这些旧式中上阶层女性的安逸、枯燥、攀比生活固然有所不满,但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加以表达。《绣枕》通过两年前后的场景对比,揭示了女性对男性、家庭的依附性,而更深一层的,是她作为一个女性要求发声的强烈欲望。不是要求经济独立,不是脱离专制家庭,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女性,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小说里的大小姐,在切身相关的事情上都从未有过独立做主的意识,更未拥有过话语权。可以预见,当她走出一个家庭,又会步入另一个旧式家庭。她虽未自暴自弃,却是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慢慢耗掉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再次上演旧时代女性的命运戏码。对于这样的女性存在的证明,凌叔华仅给予她一个“大小姐”的身份称谓,就是最含蓄而犀利的说明。在历史的长河里,那千千万万的“大小姐”,有几人能留下印记?
凌叔华是绝不愿意这样的。她在看似温顺婉约的性情之下,有着一股内在的自信与傲气。初出茅庐时,凌叔华在写给周作人请求指导的信中就有:“我虽然愚鲁,但是新旧学问也能懂其大概,在燕京的中英日文皆不曾列众人以下,但凡有工夫还肯滥读各种书籍,这是女学生缺少的特性,也是我能自夸的一点长处……因为我自己能作,没有人指点,别提受了多少闷气呢!”⑦字里行间,自尊和自信可见一斑。另据其女儿回忆:“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我记得她跟我说: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这丢女人的脸。她还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⑧一个女性,对爱情婚姻的看法可能随着人生经历而改变,但是独立、自主、平等的思想,应是早已内化为其精神、灵魂的一部分。结合凌叔华中年以后与陈西滢分居、在英国出书,晚年到处讲学的经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女性,凌叔华尽可能为自己争取了发声的机会,把寻找自我存在和价值的信条化作了人生实践。所以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才会是:“我是不会死的。”
同样是女性叙事,主题也是新旧交替时代里女性的遭遇和命运,凌叔华行文不像庐隐那样悲愤,也不似梅娘那般抑郁,却自有一种精巧协调,从容淡然的气质。而《绣枕》的故事和大小姐的飘零命运,是凌叔华的叹息,更是她借此表达对处于变革时代的旧式家庭中的女性建立独立自主的意识,争取话语权和追寻自我价值的希冀。
注释:
①[清]孙诒让著,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2页。
②潜苗金译注:《礼记译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52页。
③[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0页。
④⑤⑥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上)》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7、53页。
⑦ 张彦林:《凌叔华·周作人<女儿身世太凄凉>》,《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
⑧ 陈小滢口述,黎青青整理:《她苦苦寻找的世界—忆我的母亲凌叔华》,《文史博览》,201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宋剑华.<海滨故人>:梦幻的破灭与庐隐的悲歌[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04).
[2]费勇.幽禁中的守望与浮世里的追寻—凌叔华<绣枕>与严歌苓<红罗裙>.小说评论,1999(4).